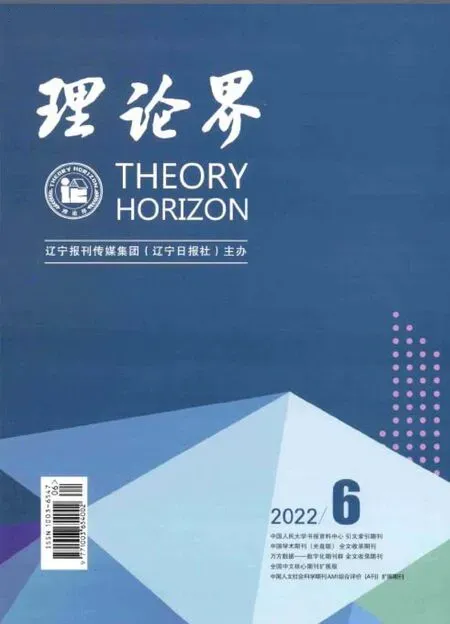布朗肖论卡夫卡的隐喻性写作
——以《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为中心
徐锦辉
布朗肖的《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一书共收集了13篇论述卡夫卡的文章,以文学为起点去思考生命存在与怪异书写的审美风格。面对卡夫卡的写作如何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言说,开启了卡夫卡面向文学的无限追问,即中性。在此,布朗肖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并追问文学与死亡的内在关系,探寻卡夫卡的无人称写作,进而刻画一个缺席的寂静者的文学形象。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的“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1〕从一种“可能性”维度打开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但是卡夫卡的作品本身是无法从传统维度解释存在的“可能性”与“预言性”的。就像《城堡》一样,无法用复述的口吻去描写作品本身的书写状态,因为它作为一个寓言或者总体的象征结构,必须由逃离象征的维度借以记号的手段呈现小说的视域,于是“符号的作用取代了象征的内含理念”。〔2〕换言之,布朗肖对于卡夫卡写作意识的研究,成为一项追问文学何以可能的解谜活动。
一、差异叙事的可能性
布朗肖通过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并在分析卡夫卡写作的基础上,建构起另一种叙事类型。对于卡夫卡而言,书写不是一个对现实的解决方案,而是不断敞开的问题域,进而提供了一种书写不可还原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关于卡夫卡的阅读、研究、阐释的过程便没有本质的终结。因此,对于卡夫卡的阐发只能在他的悖谬逻辑中不断地追问书写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的审美距离产生了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叙事形式。同时,布朗肖在《无尽谈话》《灾异的书写》中,将“碎片”“中性”等片断式思想付诸书写当中,这明显是受到海德格尔与尼采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正是在非连续性抑或散文式的书写体验中寻找文学的书写传统。因为卡夫卡以一种变形、扭曲的书写张力,逃离传统作品之中的固定叙事模式。卡夫卡的书写形式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而是将一种固定的书写程序,转变为可以调节的设置;或者是将现实主义的戏剧场景制造出流动的艺术效果。这也正是写作的问题,正如卡夫卡在小说语言的选择及表达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语法现象,因为他将语言的惯性进行肢解与变形。因此,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获得了另一种视听艺术。就像卡夫卡与游泳冠军对话一样,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却听不懂对方的话。这也说明只有在写作中才可以使语言的视听艺术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视听艺术所关涉的写作现象不是私人审美领域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未完成的写作事件存在。更确切地说,卡夫卡的写作逻辑属于不定形的螺旋式状态。换言之,类似德勒兹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成事件一样,写作无从考究起点,更无法明确终点,只是永远处于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在此逃离或者超越传统书写的可能性内容。
在阿多诺看来,卡夫卡以一种变形的距离效应解构现实主义的舞台场景,并以一种否定运动塑造现代主义的戏剧化舞台。进而,一种不完整性或者断裂化的书写形式在卡夫卡作品中,一直保持着不可知的神秘感,比如在“那些继续运用标准的时间结尾方式的作品,只不过取得了结性,这是因为想突出强调形式的整一性在现代已经是很成问题的了。〔3〕”“总体性”在卡夫卡作品里,永远作为真理的两副面孔显示——谎言与虚假,就像阿多诺将卡夫卡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片断”比作“被打碎的石碑”一样。在阿多诺看来,由于卡夫卡对小说的变形与断裂化处理,给予作品一种无意义的延伸,以此强化对现实生活的非真理性表达。关于卡夫卡早期的研究,本雅明的论述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批评碎片。本雅明在1938年的《致格尔斯霍姆·朔勒姆的信》中,就曾对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诸论断给予批判与回应,并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椭圆。它的遥遥相隔的焦点一个是神秘主义体验(这种体验首先是对传统的体验),另一个是现代大城市人的体验。”〔4〕可见,本雅明将卡夫卡作品的艺术根基,以“椭圆”为中心画出两个不同的扇面,即不可言说的神秘性与正在毁灭的现代性世界。本雅明将“椭圆”的概念引入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以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追寻卡夫卡作品中所体现的“变异”美学。本雅明眼中的卡夫卡,作品在文学空间中所生成的是一种双向聚焦的叙事模式——神秘主义和现代性。由此,卡夫卡的神秘世界赋予时代一种不可明晰之谜。可见,卡夫卡的作品以神秘性与现代性为双向聚焦的叙事模式,不仅将文学世界镶嵌上宗教色彩,还带来阅读的陌生效果。换言之,本雅明对于卡夫卡的刻画,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卡夫卡文学世界中所呈现的神圣景观与城市的低沉状态,并以这两种属性建构起卡夫卡作品中的椭圆世界。
布朗肖在《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书中,详细阐释了卡夫卡的文学思想。他从语言、书写、死亡等维度,开启卡夫卡文学世界的未来之窗,进而发现一种潜在的、否定的对抗力量。正是在中性的书写中,重新赋予语言的本体意义。不管是从布朗肖分析卡夫卡,还是从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反观布朗肖的沉默状态来看,这是一次追问何为文学的竭力嘶吼——彻底的无人称写作。在此基础上,根据布朗肖对卡夫卡的阐释,试图追问一个描述真理死去的理解者与一个中性写作者。因为在卡夫卡的文学空间存在一个可能性,那便是纯粹的文学。换言之,不可言说与不可能性的叙事,正是布朗肖与卡夫卡的相似性书写。在他们看来,书写不是在现实世界里为读者而写,而是承担叙事作品无意义的任务。正是这样的书写倾向,明晰不可言说的缺席,进而提供通向死亡的绝对真理路径。换言之,在布朗肖的眼中,卡夫卡最为独特的本质无疑是“中性”。一个是在黑夜中前行的诗人,以一种沉默的状态刻画着黑夜的无名之状,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异乡人,以一种否定的力量描绘现实生活异化的恐怖画面。这不难看出,布朗肖眼中的卡夫卡始终围绕着“中性”的书写逻辑展现他的文学观。一方面,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主体往往处于一种隐形角色,另一方面,卡夫卡以中性语言为言说基础,将写作放置在一场不断否定的运动中,并重新赋予语言与文学的本质力量,进而避免对文学限定的可能性书写。从布朗肖的非本质或者反文学理论的立场来看,卡夫卡的作品无疑是符合“中性”书写气质的最佳代表,因为“文学之本在于避免限定本质,避免呈现现时固定文学甚至将其实现:文学从来都不事先存在,要不断重找、更新”。〔5〕这不仅是卡夫卡作品抵抗中心的隐喻性表达,也是一种拒绝传统书写枷锁的自在姿态。因此,我们试图以布朗肖的角度,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追问书写的差异叙事与变异美学。
二、铭写陌异世界的语言逻辑
卡夫卡的文学书写如何通过语言来完成一次抵抗日常语言的一般性解读,以此去延缓叙事的时间?在此,我们要明确卡夫卡的语言之意,才可以使语言进一步摆脱符号的“所指”意向,因为传统固定的意义链条变得不再牢固,从而产生了意义字符脱落的现象。卡夫卡正是借助语言符号偏离的内在力量,寻找文学表达的可能性救赎之路。语言对真理的模糊描述,所造成的结果是生成与现实世界的悖论逻辑,即遮蔽性与隐秘性原则。“卡夫卡让语言在这个裂隙中滑动,以证明这个裂隙的存在,逐渐失去被阐释的可能性,这也是他书写的目的之一。”〔6〕基于语言自身的言说逻辑,在卡夫卡作品中它有意识地偏离日常生活化的表达方式,主要是以一种不可见的场域去追问语言的缺席状态,这不仅陷入一种混乱书写对象的境遇,还带来了一场“语言危机”。文学语言在对象(物)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语言自身的追溯,因为在言说的过程中往往充斥悖论式的逻辑,混淆意义之间的边界或者字词之间的所指意向。那么返回语言自身重新思考书写,则是作为书写对象与自身存在的重要前提,因为“当字词被视为对象本身来思考时:‘对象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自行转化,也会停止成为它们之所是,它们总是对立的,无用的,无法接近的’”。〔7〕由此可见,生成差异性与非真理性的表达。
那么,语言所指的对象是否存在于一种否定性逻辑,从卡夫卡书写的对象看,唯有在书写与非书写的差异关系中追问语言的非现实关系,才可以明晰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在回应语言是否存在否定性逻辑之前,我们需要从布朗肖自身的语言观来明晰卡夫卡的文学语言现象。也只有在廓清布朗肖文学语言的表达逻辑的前提下,才可以进一步明确他眼中的卡夫卡或者卡夫卡作品中的语言观。他们共同回答了书写的不同向度,这就指向布朗肖“‘从书写什么也不是’到书写并非什么也不是”〔7〕的叙事逻辑。布朗肖对于“ilya”概念的介入,实则是反映他独特的文学语言风格。“ilya”的概念一直贯穿于布朗肖的文学中,并以一种介质自居。布朗肖从列维纳斯的哲学思想那里,引入“ilya”的语言表达,因为列维纳斯在哲学层面将“ilya”界定为“先于存在的存在”“无世界的存在”。从这可知,列维纳斯试图通过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定义思考,获取异在的表达基础。在此基础上,布朗肖将“ilya”的概念从哲学语境实现了文学表达的转向,从而“ilya”具备了语言的否定性逻辑。
正是语言自身的否定性逻辑,使“ilya”在书写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赋予可变动的意义链条,以此明确语言与否定性的内在关系。由此可见,从书写的否定性逻辑去反观“ilya”自身所存在的否定路径。首先,通过布朗肖在语言的书写实践方面分析,明确他如何从日常书写到文学语言的转向,因为这个转向所需要的内在驱动力,主要是源自黑格尔的否定性哲学。其次,我们在明晰他写作语言否定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语言自身的张力,以及文学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言说向度。最后,明确在传统的语言观中,主要以一种再现的结构进行揭示世界,然而在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实际的工具性意义不再占主导地位。在布朗肖看来,语言在对现实事物进行描述的时候,不仅是对“物”的消解,还对表达本身(语言行为、语言)进行遮蔽,最终明确语言在否定性的表达过程中,才得以进入一种“无名”之境。正如“语言,离开想要成为独一无二的意义,试图成为无意义”。〔7〕换言之,我们从否定性的哲学逻辑到语言转向路径中,明晰了布朗肖语言否定性的合理性依据。
从语言的否定性到文学语言的书写转向,是布朗肖面对文学困境所给予的回应。就像卡夫卡小说里所讨论的政治、文学、日记等书写证据将一并归置到书写差异之中,才可以进一步透过从卡夫卡的书写之物发现,书写背后的纯粹语言,即书写本身。“书写作为虚拟之途的开关被重新启动,然而却是为了卷进现实处境所切换的文学空间之境:一个书写前提的重置。”〔7〕这个前提也在《卡夫卡阅读》和《卡夫卡与文学》中形成一种连续性。布朗肖“以书写为根基的思考而言,书写者所实现的是‘书写我(主体)的不可能性’”。〔7〕可见,从书写前提的预设到主体追问过程中,书写本身赋予作品更多的谜题。创作作品不只是叙事行为的结果,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解谜之旅,就像作品中的时间性、原型意味、无限象征的风格皆存在叙事与文学各自的独立空间。因此,只有纯粹的语言作为书写的前提,那么书写就是在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学空间之中完成写作的任务。不管是布朗肖,还是卡夫卡的书写,皆以书写自身等待未曾到来的书写境遇。因为等待的状态既不是敞开,也不是封闭,只有这样的书写才可以进入一种互不容纳,也互不排斥的逻辑关系之中。可见,“等待,就是等待没有在等待中被给定的在场。”〔8〕这就好像卡夫卡在作品中一直等待着作为一个书写者的证据一样,这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书写者是卡夫卡本人还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马克思·布侯记录下的卡夫卡面孔?在某种程度上,不可确证的身份,明晰了卡夫卡自身的缺席状态。因此,布朗肖从书写的角度,重新赋予语言的纯粹性意义,在此基础上使卡夫卡所面对的语言危机也得到了一种缓解之道,即缺席。因为书写的可能性,布朗肖才可以将卡夫卡关于书写的思考放置于文学空间之内,但是书写不仅是以否定性逻辑辩证卡夫卡书写的真理维度或者差异表达,而是在书写之中生成一种“未有之有”的状态。通过将书写放置在共时的场域中,以差异叙事形式探寻卡夫卡书写的奇异风格,即一种虚拟的转换。而这种怪异与矛盾的书写现象,在《城堡》里想必是一种自证行为。在此,布朗肖通过对《城堡》中K 的行动分析,发现其中的奇异现象。特别是对K 的心理矛盾的分析,让K 在通向小镇的木桥之间的距离被一种“空白”所限定。对此,布朗肖在《木桥》一文中对K 的行动作出文学批注,即K所前往小镇的每一步,不是接近目的而是退回所仰视过的苍茫之境(困境)。可见从木桥到小镇的距离在K 的脚下被滞留了,那么这就陷入一种不可见的困境之中,此刻行动变成了一次绝望的叩问以及徒劳的自证。
换言之,由布朗肖所设置的卡夫卡之路(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看,他制造了一种不可能性的双重逻辑与多重差异形式,正是立于不可能性的路途上(既非起点,也非终点),才可以无限地接近卡夫卡的书写情境。由此可知,只有透过书写的差异逻辑,才能反观文学何以可能的生成路径。这可以视为无限扩展或者延伸作品的可能性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追问卡夫卡作品中存在的匿名状态,换言之,这成为一项拓扑学的解谜任务。
三、中性书写的拓扑学效应
拓扑学(Topology)是作为物理学与数学的等效空间原理,然而在文学空间的建构上也存在拓扑学现象。德国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1886—1956)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一书中就曾界定文学的拓扑学意义,并赋予文学的历史内涵。因为文学空间存在时间的差异性,以此分析文学空间中存在的变异、扭曲,或者压缩与延伸等连续性现象,给予了拓扑学演变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基础。正是布朗肖在分析卡夫卡的书写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一种字词的拓扑学现象,“一个无深度的目的正在于必须根除主体性的控制,使文学产生得以返回文学自身的空间。”〔7〕可见,字词、语言、主体皆成为拓扑学意义上的文学空间,进而追问生成它们连续性的构造原则。
卡夫卡的作品如何再现我们现实的生存世界则需要我们从语言、字词、作品到主体、死亡的审美过程中介入互文性视角,以此展开卡夫卡作品中关于上帝的主题,抑或玛格妮夫人眼中的无神论背影。对于现实一切荒谬与不解,评论者尽量给我们制造一条通达卡夫卡世界的捷径。不管是琼·斯塔罗宾斯基将卡夫卡刻画成一个“理解的毁灭者”,还是“皮耶·克洛索基说道:卡夫卡的《日记》 是……渴望痊愈的患病日记”〔7〕,可见,通过这些字词评述发现,恐惧的因素一直萦绕在卡夫卡的作品与自己的情感之中,比如他在文学中显示出的不安与惊颤,想必是保存谜题的表演课阅读性隐喻。在他看来,卡夫卡的作品多以片断叙事为主。即使是整体,也是片段式的整体,由此产生作品的否定性作用。正是否定书写所衍生的含混性与死亡的模糊性相关,卡夫卡的弥赛亚就意味当下不可获得的救赎。正如卡夫卡自己曾经说过,当人死亡之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善意寂静,并通过与此时死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一种人世激动的慰藉,对于生者而言,这实则是获得喘息的契机,同时也为死亡打开另一扇门窗。“‘就整个客观来讲,在亡者的床边的哀悼的这个事实并非死亡在亡者身上真理的意涵’……清楚表明‘我们的救赎即死亡,却非眼前的这一场’。”〔7〕可见,死亡在卡夫卡作品中所明晰的死亡只是对生命的一种短暂终结行为,并没有彻底结束我们正在死去的可能性,这样模棱两可的意义指向与布朗肖的死亡观念存在一致性。
布朗肖以“沉默音声的缺无,作为死亡的缺无”。〔9〕可见,布朗肖试图以语言的否定性逻辑,构建一种非主体的书写情境。在此基础上,文学意义上的死亡观念便在非主体抑或无人称的写作境遇中,实现文学书写的转向。因为,布朗肖认为死亡书写与传统的哲学语境中的死亡观念不同在于,不将死亡当作生命存在的参照体系,以此来逃离哲学式的概念界定。这便引出了:如何书写死亡之态?对此,布朗肖首先引入文学语言的否定性表达形式,其次逃离形而上的哲学逻辑,从而获得关于书写死亡的路径。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力》一书中,布朗肖主要是对书写客体进行文学式表达,以此明晰语言与死亡的内在关系。因为,布朗肖在重新将死亡放置在文学空间当中予以讨论,语言本身不仅将书写对象进行一种中性化的形式处理,还进一步弱化了书写主体。在此基础上书写逐渐成为书写本身,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非主体式的写作风格。正如布朗肖在《死刑判决》中,对J 所面对的死亡思考那样,“在这里,J 的安乐死既是一个死刑判决,又是对死亡的中断,是在用死亡中断死亡。”〔10〕可见,他认为文学语境中的死亡书写,不管是从语言的表达机制上看,还是从审美倾向来说,这正是死亡的文学表达,即走向一种“非主体性”“非本质”的中性表达或者是异在之维。布朗肖将死亡从哲学境遇中拯救出来,以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重新赋予其内在的否定性前提,从而逃离传统的可能性叙事,指向不可能性的书写维度,因为传统的死亡观念,在哲学语境中,特别是在柏拉图、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那里,他们将死亡描述为理念形态、绝对精神意识、此在—存在等逻辑下的概念形式。对此,布朗肖引入“ilya”的否定性意义之后,随之将死亡引向文学空间之内,以此明确死亡书写的合理性基础。这就是布朗肖文学意义上的“无”,正如“那种永远不会降临我的东西,以致我永远不会死去,而是有人死去,总是除了自己以外有人死去,处在中性的,永恒的他的无个性的层次上。”〔11〕可见,文学式的死亡表达,不再是简单地作为生命存在的参照体系,也不再权限在书写主体的语境当中,从而获得死亡表达自身的契机。
布朗肖的死亡书写逻辑,为我们分析卡夫卡的书写情境提供了思考路径,以此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追问书写如何成为救赎主题。因为一旦面向现实,语言将受到权力的控制或者制造成混淆状态,成为通向自由道路上的阻碍。看来这确实是难以完成的一项任务,就像“《万里长城》(La Muraille de Chine)没有被建筑工人完成。万里长城的叙事也没有被卡夫卡完成”。〔7〕对于这个以失败为主题的书写,一直成为文学上的一种病症存在。由此可见卡夫卡的书写,依然无法自行终止书写的行动,因为书写已经控制住他对于现实的思考,即使他有意识地中断,但中断之后依然是新的书写。这就明确文学始终作为矛盾与悖论的场域,因为布朗肖指出“他知道无法书写赎罪,只能书写活化赎罪”。〔7〕可见,对于卡夫卡来说,救赎一旦释放无法获救的信息之时,书写所接近的是绝望——无尽的成见。就像卡夫卡的《日记》以一种“祷告式”的方式谈论着苦恼的深渊。还有在他作品中的土地测量员,给我们再现了这位无法获救,便一直属于流浪的主人公,同时意味着他不再限制在“家”的概念视域之内,而是游离在一种真理之外的域,如此他才得以行动。“土地测量员几乎彻底摆脱约瑟夫·K 的缺点。他不试图返回故土:抛弃在迦南地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被抹除的真理;就算在他几个短暂脆弱时刻的回忆也几乎不着痕迹。”〔7〕可见,卡夫卡认为现实中的生存与所追求的真理之间存在一种悖论,以此来表现那种不可言说、不可体验、被遗忘的沉默状态。这“对他而言,他只生存于域外,只生存于永恒域外的涓涓不息中”〔7〕。布朗肖在此为我们明晰卡夫卡的书写逻辑,“这即我们从卡夫卡身上学到的——即便这个公式不直接从属于他——这即中性(le neuter)内核的陈述。”〔7〕在此,他摒弃了所有的实体性,以及现实的可能性,只在中性中叙事陈述者的话语,同时也只在叙事的中性空间中,将话语自身放置于非—同一性(non-identification)的逻辑框架之内。正是在中性的前提下,得以明确书写与死亡的本质关系,可知,布朗肖将死亡的可能性引入文学空间中并表达为一种非个人、无名的,以及沉默的状态,目的是逃离哲学意义上对生命的掌握,由此厘清了死亡和文学彼此之间的纠缠关系,进而通向体验隐匿的存在,以及共通体的境遇。这“对卡夫卡而言,都具备一个立即的真理”。〔7〕换言之,布朗肖在对卡夫卡的分析过程中,明晰了书写各个环节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以及生成逻辑,从而完成了一项拓扑学运动。
四、结语
布朗肖眼中的卡夫卡作为一位中性的写作者,试图从语言本身寻找缺席的在场,进而打开文学空间的外在之域。可知,布朗肖眼中的卡夫卡对于中性书写的建构基础是书写的异在本质,特别是在语言缺席与文本自足的基础上,明确卡夫卡书写这一行为本身已经逃离了物质的实体性意义,并将日常表达悬搁一切在场的界限之内,由此他以“变形”的方式去阻碍语言获得稳定性与外在依托的路径。这也正是布朗肖所构建的语言观,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先行前提是对日常语言的彻底否定与缺席。正是在布朗肖语言观的构建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晰从一个致力于思考书写自身的写作者的作品中,寻找永恒游移在“未有之有”的书写之物的思辨路径。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双向叙事逻辑,不仅揭示“从”与“到”字词之间意义脱落的现象,还产生语言指向的“变异”效果。由此可知,卡夫卡本身与卡夫卡作品中的形象,也在写作的矛盾与悖论之中隐匿其真正的主体。同时卡夫卡的身份之谜,正是布朗肖所指向何为卡夫卡的原因之一。换言之,从布朗肖对卡夫卡身份的追问过程中可知,这无疑不是体现他对何为书写的本质追求,从而明确卡夫卡的中性书写多重叙事的异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