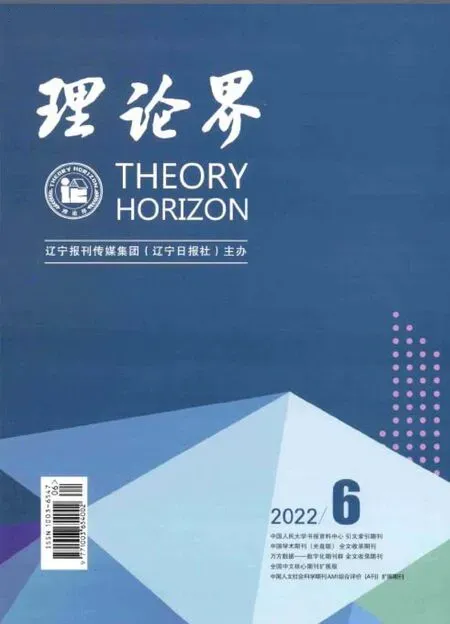隐性作者与神话创制:论“艺术的苏格拉底”
任贺贺
1872 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以独到的眼光强调了本能与非理性的重要性。之后,他溯源了理性及科学思维的滥觞,试图在西方思维的源头重新审视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艺术、哲学与诗的关系。在这一探寻中,苏格拉底成为尼采重点质询的对象。尼采在研究了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及悲剧的消亡历程之后,不无感慨地指出:“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1〕在察觉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非理性的消隐趋势后,这位敏锐的后起之秀便开始思索“人以何种状态生活将更为幸福”的哲学命题。于是,尼采继续追问: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只有对立关系?一位“艺术的苏格拉底”(“künstlerischen Sokrates”,孙周兴译为“艺术苏格拉底”,周国平译为“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是否根本就自相矛盾?
面对这些问题,尼采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实际上,重回苏格拉底的语境去探求“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否可能、何以可能以及何谓“艺术的苏格拉底”等问题仍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关切,因为从古典立场探寻的“幸福”品质将会在现代个体的“幸福”选择中呈现弥长的意味。
一、何谓“艺术的苏格拉底”
西方艺术的流变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而诗歌归入艺术领域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古希腊时期,艺术一词主要指“技术”“技艺”,涵盖从创制城邦到制作陶器的范围,但并不强调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凸显的审美维度。此外,彼时的艺术更多地彰显一种规则和体系,即“技艺依赖于对规则的认识,所以无规则的、非理性的艺术是没有的……离开了规定,仅凭灵感或奇思异想做事情,这无论对古代人来说还是对经院哲学家来说都不属于艺术,这是艺术的反面”。〔2〕需要指出的是,诗一开始并不属于艺术范畴,而是被视为“一种哲学或者预卜”,〔3〕而真正的诗人是柏拉图在《伊安篇》(Ion)中所说的“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4〕柏拉图认为,与模仿类的诗歌相比,在非理性状态下被神凭附所产生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诗歌若欲迈进艺术的门槛,则需拥有一套系统的规则,而这套规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The Poetics)中臻于成熟。
尼采的“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是对“苏格拉底主义”(socratism)的质疑与提防,也是对苏格拉底哲学进行的一次挑战性诊断。“苏格拉底主义”是一种过度理性的趋势,它将“理性——知识——美德——幸福”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实现途径进行连接,从而奠基了一种在个人“德性”(virtue)内部寻求永恒的模式。尼采认为,这种趋势自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悲剧歌队进行限制时便初现端倪。在“苏格拉底主义”的强劲之风下,即使审美的维度试图革除过度理性的弊端,这一主义最终也会将人们审美的努力同化为一种“审美苏格拉底主义”(aesthetic socratism)。尼采指出,这种“审美苏格拉底主义”是“对艺术的一种理论性的、辩证法的、非艺术的评价,它其实并不理解它所探讨的现象”。〔5〕换言之,过度理性会将个体中的审美之维也同化为理性下的逻辑分析。在这两个“主义”的存在下,尼采将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归咎于苏格拉底,并将苏格拉底作为乐观主义“理论家”进行诘难。
“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尼采构想出的一种关于文化和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流露着他对艺术本能与理性判断之间能否调和的深思。实际上,尼采在批判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时也勾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形象。结合尼采本人所述及后世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尼采理想中的苏格拉底有三种形象:首先是“创作音乐的苏格拉底”(music practising Socrates)。尼采认为,音乐中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可以消除“苏格拉底主义”带来的唯理论倾向,这无疑是受到了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影响。其次是前苏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在尼采看来,以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为代表的前苏格拉底的哲人沉浸在神话与哲学并存的“健康”文化中,而神话在如今的语境中“可以被看作生命冲动战胜了知识冲动”。〔6〕最后是尼采本人的“自画像”(selfportrait)。〔7〕尼采在文辞上对苏格拉底的攻讦更多的是他借助批判苏格拉底而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实际上,这三种苏格拉底形象是尼采“艺术的苏格拉底”形象的不同维度,它们都指向了在国家文化和个体幸福方面非理性的艺术向度。在诊断德国文化走向时,尼采用“艺术的苏格拉底”提示“健康文化都必须具有神话性成分”,从而“为了真正德国神话再生的目的而沉思”。〔8〕在个人追求幸福的层面上,“艺术的苏格拉底”以回望的姿态提示着个人成长中感性滋养的不可或缺。所以有学者认为,作为语文学家的尼采“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了他的职业发现,以使过去以一种美丽和建设性的方式服务于未来”。〔9〕
实际上,“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在尼采生前身后的哲学场域中都有回响。维柯曾于18 世纪提出,“诗性智慧”是一种原始而有活力的思维状态,这是他对当时极尽理性之所能的“玄奥智慧”所进行的反思。在他看来,“人们现在用唇舌造成语句,但是心中却‘空空如也’,因为心中所有的只是些毫无实指的虚假观念”。〔10〕20 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歌中看到了走出“二元对立”与时代贫困的可能:诉诸诗人和诗歌。何谓诗人?诗人道说人们未曾经验过的东西,“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11〕面对现代困境,海德格尔也希望通过非理性的艺术力量回到天地人神和谐与共的生存状态。这些回响将尼采“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推向更为宽广的哲学视野,并凸显着这一问题的深刻性与永恒性。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如果是“艺术的”,那他最可能是在城邦建制与诗的领域成为“艺术家”。尼采构想了一个苏格拉底形象,这是一个能够将辩证法、知识、科学与本能、艺术、非理性相统合的个体形象。尼采看到了这一个体形象的矛盾与困难之处,因为“艺术的苏格拉底”“象征着酒神和阿波罗神在哲学本身内结合的可能性”,〔12〕所以他不由得怀疑“艺术的苏格拉底”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回溯到苏格拉底的具体语境中,一个“艺术的苏格拉底”形象也开始逐渐明朗起来。
二、“艺术家”作为“作者”
苏格拉底曾用一种修辞性的语句描摹自己的清醒状态:“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13〕这俨然是一位哲学家的冷峻肖像。但是,苏格拉底果真只有这一副理性的面孔吗?实际上,《理想国》就呈现苏格拉底的另一面,而此时他却是一位“艺术的”“作者”。
“艺术的”苏格拉底之为“作者”(author)在于“艺术”一词中蕴含的创制规则之意味,以及“作者”中的“权威”“原因”“负责人”之意。〔14〕具体而言,“author”可以指“ 话语开创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他们是独特的,因为他们并不仅仅是其作品的作者。他们另有所创:促成其他文本诞生的可能性和规则。”〔15〕在中文语境中,“作”也绝非寻常之事,比如孔子就“述而不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所以孔子才感叹“作者七人矣”。由此观之,“作者”开创规则、制定体例的内涵与精通艺术之人(“艺术家”)创制规则体系之意可以相互发明。
苏格拉底的“作者”身份首先在于他创建起一套城邦秩序。在通过“由大见小”〔16〕而寻求个人正义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将他心中理想城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定。毫无疑问,这是《理想国》构建哲学理想的显性进程。为了看清楚正义在城邦中的体现,苏格拉底将城邦中的阶层划分为统治者、护卫者和为个人利益的人(被统治者)三层。对城邦护卫者而言,苏格拉底将他们与狗的天性进行了比较,发现了城邦中所需要的“勇敢”;〔17〕在城邦统治者身上,苏格拉底又引导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 和格劳孔(Glaucon) 发现了“智慧”这一城邦品质;〔18〕之后,苏格拉底又认为“节制”是三个阶层的人都需要的品质。〔19〕最后,对城邦正义的探讨是在前三个品质被提出之后才逐渐明了的:“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20〕并且,正义使智慧、勇敢和节制产生并保护着它们。〔21〕至此,苏格拉底已经找到了城邦中的四个德性。针对这一城邦创制,有学者认为《理想国》中“最大的一首诗,不是别的,正是苏格拉底倾力打造出来的‘美好城邦’这一‘政制’。”〔22〕实际上,在这“一人一事,各司其职”的城邦之中,城邦阶层相互划分,城邦的军事、教育问题在苏格拉底的创制下也完成了系统化和规则化。
苏格拉底的“作者”身份还在于他以一种逆向的方式构建起一套诗学秩序。所谓“逆向”,即在于苏格拉底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他关于诗歌和诗人的规则。与创制城邦相比,苏格拉底对诗歌秩序的构建迂回曲折、隐微不明。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在论述城邦护卫者的教育以及模仿时兼及批判诗人及诗歌。他意欲以诗人问题来建构自己理想国的壁垒,并对诗歌保持高度警惕。苏格拉底曾对阿德曼托斯说:“我亲爱的阿德曼托斯啊!你我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在这里发言的。缔造者应当知道,诗人应该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许他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但不要求自己动手写作。”〔23〕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以城邦“缔造者”自居,认为自己也完全具有创制诗歌规则的能力,只是自己不去作诗罢了。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认为诗歌由三部分组成:和声(harmony)、节奏(rhyme)和词(words)。〔24〕和声(曲调)只能用多利亚调(dorian)、佛里其亚调(phrygian),并且在城市中只能用七弦琴(lyre,阿波罗的乐器) 演奏, 在乡村地区则须用短笛(piccolo)。长笛和竖琴是被禁的,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情欲与抒情传统。至于节奏,苏格拉底认为它必须是“有秩序的勇敢的生活节奏”,〔25〕因为“美与丑是紧跟着好的节奏与坏的节奏的”。〔26〕显然,苏格拉底对和声和节奏的规定是在规定诗歌中的音乐性。
苏格拉底关于“词”的讨论贯穿整本《理想国》,并且他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建构诗歌中的“词”。在内容方面,他提出“讲什么”“怎么讲”两个问题。至于讲什么,苏格拉底先是将诗歌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将诗划分为史诗、戏剧诗(悲剧和喜剧)和抒情诗的分法,〔27〕苏格拉底在论辩中将其分为悲剧、喜剧、史诗、抒情诗和颂诗。在他看来,悲观地看剧会让人的理性放松对哭诉的监督,〔28〕并且怜悯之情的喷发也不容易被人自身制服;〔29〕至于喜剧,他认为观众会不禁发挥说笑的本能,变成插科打诨之人;〔30〕此外,他还认为“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31〕虽说苏格拉底没有直接说明哪些内容可写,但是除去不可写的内容,我们便可以窥见颂诗的领地。对于诗中不能出现的内容,苏格拉底列出五条:一是赞美地狱生活;二是凄惨的名字;三是英雄人物的号啕痛哭;四是挽歌;五是令人捧腹大笑,不能自制的内容。〔32〕关于怎么讲的问题,苏格拉底明确说道:“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33〕之后,在诗歌或者故事的形式和风格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可以用叙述、模仿或者两者兼用。“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他诗体里找到……”〔34〕至此,苏格拉底以非凡的气势“制礼作乐”,将作诗的不同方面都进行了规定,使得诗歌进入艺术行列。因为“一旦发现了诗与音乐的规则,它们也就确定可以被看作是艺术了”。〔35〕
由此可见,作为“艺术的苏格拉底”以一显一隐的方式创制着诗的传统和城邦政制,显示出他作为“艺术家”制定规则、订立标准的一面。一方面,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诗学的创制在《理想国》中以一条隐线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城邦和诗学的创制都指向了城邦公民的德性教育问题,即诗教与哲学教育。除了“话语开创者”的一面,苏格拉底也无形地展露其感性而富于神秘色彩的另一面。
三、厄洛斯神话与苏格拉底的艺术实践
尼采在审视苏格拉底“抵制”悲剧精神时曾对柏拉图的诗人身份进行了还原。在他看来,柏拉图将自己悲剧诗人的身份一直埋藏于心,以至于“一旦不可遏制的天赋起来反对苏格拉底的戒条,其力量连同伟大性格的压力总是如此强大,足以把诗歌推举到新的前所未知的地位上”。〔36〕尼采始终相信柏拉图作诗的倾向,并认为柏拉图对话“犹如一叶扁舟,拯救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给世世代代留下了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原型,小说的原型”。〔37〕在这里,苏格拉底似乎完全成为一股压制弟子柏拉图的理性力量,与诗站在对立面,并与诗势不两立。可是,苏格拉底果真如尼采所说囿于理性之中而独善其身吗?实际上,《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不动声色地表露着他作为诗人感性而神秘的一面。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尾声所讲的厄洛斯(Eros)故事是他根据自己定立的作诗原则而创作的神话。在讨论诗中有关神的内容时,苏格拉底专门谈到写神时的两个准则:首先,“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38〕其次,“谈到神的时候,应当不把他们描写成随时变形的魔术师,在言行方面,他们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去的角色”。〔39〕在面对荷马的诗歌传统时,苏格拉底并未展示新神话的样态,但是他深知要“对诸神的古老观念进行转化,以使正义呈现为城邦保护神的基本品质”。〔40〕所以,死而复活的厄洛斯完成了他受之于天地之间法官的任务:“传递消息给人类。”〔41〕根据旁观者厄洛斯的描绘,灵魂通向地下或天上与否取决于天地之间法官的审判;之后,来自不同地方的灵魂便在绿草地上聚集,其间他们可以相互交流各自在天上或地下所遇到的经历;随即,这些灵魂将会来到拉赫西斯面前,抓阄然后选择生活模式;最后,这些灵魂在经过勒塞之河后,丢失记忆而回到新的生命之中。实际上,苏格拉底讲述的这个神话因其结构曲折和环境的陌生化呈现使得故事本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比如,在描述灵魂即将出地下洞口时,“凡罪不容赦的或者还没有受够惩罚的人要想出洞,洞口就会发出吼声。有一些样子凶猛的人守在洞旁,他们能听懂吼声。于是他们则把他们捆住手脚头颈,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在路边上拖,用荆条抽打”。〔42〕这样阴森恐怖的描述与苏格拉底认为诗人“不能描写凄惨的名字”的主张相抵牾,但它确实起到了神秘、震惊的故事效果。而作为能够想象出一个宇宙纺锤图景、改造一个塞壬女神形象、编出众多生活方式的故事讲述者,苏格拉底在厄洛斯神话中将一种诗性想象力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实际上,苏格拉底通过讲述神话来将《理想国》卷九之前的哲思进行重构,正是看到了语言在表达哲学时的含混与多义性,因为“有关事物最终本质的谈论都不可能是字面上的,最好的情况下也必定具有隐喻性”。〔43〕
此外,苏格拉底对神谕的绝对遵从与伊安在神凭附后的作诗状态颇为相似。苏格拉底能够完全相信神谕的原因便是他已经通过厄洛斯的新神话传达了他对人神关系的新认识,即“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关”。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已经扭转了以往人神同形同性的传统,而把神视为“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44〕所以,当神谕存在的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苏格拉底便坚信在神的指示之下,人可以追求真与善。事实上,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牛虻”比喻就是他对神谕的绝对性回应:“像我这样,受命于神,献身城邦的一个,这城邦就如同一匹高头大马,因为大,就很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在我看来,神就派我到城邦里来当这样一个牛虻,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一个,我整天不停地在各处安顿你们”,“而我恰巧就是神派给城邦的这样一个。”〔45〕此处,苏格拉底用“辩证法”展开的对话都是在神凭附之后而展开的,而这些对话如同诗人吟唱诗歌,目的在于省察自己、省察他人。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我认为并意识到,是神安排我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而如果我不服从神谕,怕死,以不智慧为智慧,那才是可怕之事……”〔46〕苏格拉底遵从神谕与诗人被神凭附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处于对神的绝对信仰之中,而这种绝对信仰有时会让他们陷入一种绝对的迷狂,只不过苏格拉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包括自己的无知,而诗人“并不理解自己所说的”。〔47〕
苏格拉底的诗人身份也隐微地在一些外部文本中流露出来。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曾在《名哲言行录》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帮助欧里庇得斯和卡里阿斯完成创作的事迹,〔48〕并且苏格拉底创作的颂诗片段和一则伊索寓言的开头也被保存在了这部著作之中。〔49〕无独有偶,柏拉图也曾以雅典人之口表露过他与乃师的诗人身份。《法篇》中的雅典人曾说:“尊敬的来访者,我们自己就是悲剧作家,我们知道如何创作最优秀的悲剧。事实上,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就建得相当戏剧化,是一种高尚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这是所有悲剧中最真实的一种。”〔50〕这一雅典人的说法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二人的城邦建制归入到一部“城邦悲剧”之中,而剧作家便是这师徒二人。正如有学者指出:“苏格拉底的诗产生的效果,恰恰与荷马及其他悲剧诗人的诗相反。苏格拉底没有述诸我们灵魂中的低下部分,我们的激情,从头至尾,他述诸我们的理性。”〔51〕进一步而言,苏格拉底在《理想国》卷二到卷九中对“言辞”的重视使得哲学对话处于隐喻性的言辞——诗的统领下,从而将苏格拉底的“哲学诗人”〔52〕形象呈现了出来。
因此,苏格拉底感性与神秘的一面在他讲述的厄洛斯神话中得到了体现,并且他也按照自己确立的作诗原则进行了一次文学实践。苏格拉底在着重讲述冥府的神秘中也传递着他关于诗中神之形象如何塑造的观念,即“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关”。〔53〕这与《理想国》卷二和卷三中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提出的神之形象形成对比。此外,对照其他文本对苏格拉底诗人身份的指涉以及柏拉图在对话作品中的隐微表露,一个作诗的苏格拉底逐渐走向前台。至此,“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无疑又触及了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而“哲学诗人”苏格拉底也隐微地表明“诗与哲学一样,如果两者分离,就有用部分代替全体的危险”。〔54〕
四、结语
尼采“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实质在于探寻如下问题:感性与理性能否在一个人的灵魂中同时发挥作用并引导人走向一种幸福的生活。需要指出的是,尼采轻视了苏格拉底时代中的“艺术”现场,从而对“艺术家”身上的“作者”之维关注不够。《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大力倡导一种“省察”的哲学理性生活,另一方面也通过创制新诗规则和实践新诗,隐晦地表达了对感性和想象力的强调。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理性一面在于培养灵魂的德性,使得理智能够统摄激情(high spirit)和欲望,但“艺术”的一面则使个人灵魂拥有创造力,在诗的“灵韵”(aura)中保持一种对理性的反思。在这两种状态之中,个人“选择中庸之道而避免两种极端”,〔55〕从而在两方面完成对德性的教育。
因此,“艺术的苏格拉底”确有可能,而不是一种“自相矛盾”。此种人格不唯哲学家所有,而是具有普遍性。它的实现需要寻求幸福者在哲学训练中添加诗意的成分,也需要他们在读诗歌时进行清醒的加工。这种个人幸福的追求路径是我们现代人借“艺术的苏格拉底”之问回望古典智慧之后得到的久远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