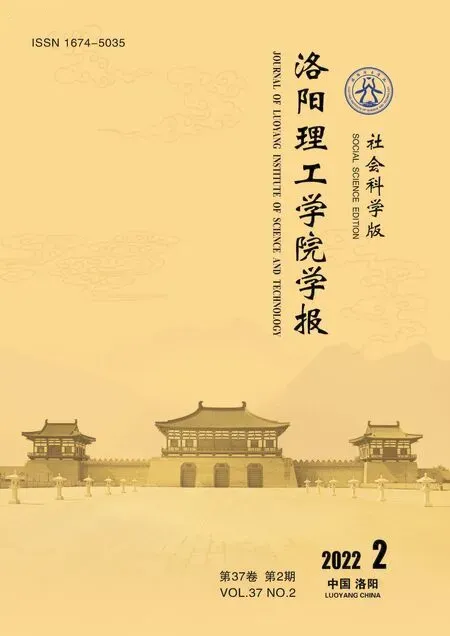论《燕岩集》的“序跋”创作及朴趾源的文学观
张 丽 娜
(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燕岩集》是朝鲜李朝汉文创作的巅峰之作,作者朴趾源(1737~1805)是朝鲜李朝时期的最著名的实学思想家和文学家。朴趾源出身世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接受实学思想,并为之著述宣扬,于思想领域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朴趾源著述甚丰,思想深邃,精通各种文体,留有大量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等文学作品,是李朝时期最重要的文人之一。《燕岩集》是其作品汇编,其中序跋类散文数量可观,内蕴丰厚,可作为今人窥探朴趾源及实学派文学创作的窗牖。
一、《燕岩集》中辑录的“序跋”类散文
“序跋”是中国文学以及域外汉文创作中的特殊体例,是为著作、文章、绘画等文艺作品撰写的文词,具有叙事、说明和议论等功能。序在古代多置于书后,又称“叙”“叙文”“序文”“引”等。跋,又称“题跋”“跋尾”“书后”等。《尔雅》云“跋,蹭也”,有“踩”“践踏”之义。凡题词于书籍、诗文之后者称跋。序跋的内容、体例大致相同,故合称序跋文。孔安国《尚书序》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1]638跋与序虽然类似,但文风仍有差异。跋的篇幅更为短小,言简意赅,内容多为赏鉴、评价、考释。跋或后序、题后之类多为序文之补充,故更加简括,不如序之详尽丰赡。
《燕岩集》共17卷,其中卷4《映带亭杂咏》为诗歌,共32首;卷8《放璚阁外传》为小说,共9篇;第12卷至14卷为《热河日记》;第16、17卷为《课农小抄》。除此,《燕岩集》还有政论散文、书简序跋等文体。“序跋”类散文在《燕岩集》中比重较大,以“序”名篇的序文24篇,题跋7篇,跋文3篇,引1篇。
(一)序类散文
《燕岩集》中的序文有自序和他序两大类。《燕岩集》中朴趾源自序有4篇,依其在《燕岩集》中的编次,为《孔雀馆文稿自序》《映带亭腾墨自序》《钟北小选自序》《放璚阁外传自序》。他序是对作者、作品进行介绍和评论,或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燕岩集》中他序共18篇,可粗略分为论说性序文和叙事性序文两类。
论说性序文以议论为主,阐明作序人的某种观点和主张。作序人可借序文抒发个人文学观点,或借题发挥,表达对历史、社会、人生问题的看法。《燕岩集》序类散文中论说性序文数量比重最大,共14篇:《楚亭集序》《洪范羽翼序》《自笑集序》《蜋丸集序》《绿鹦鹉经序》《愚夫草序》《菱洋诗集序》《北学议序》《枫岳堂集序》《柳氏图书谱序》《婴处稿序》《炯言挑笔帖序》《绿天馆集序》《冷斋集序》《旬稗序》等;古代的序文,除写作“叙”外,有时还称“引”,如唐代刘禹锡的《彭阳唱和集引》、宋代苏洵的《族谱引》等。《燕岩集》中的《骚坛赤帜引》也属此类,论述为文之法,是一篇论说性序文。
叙事性序文在中朝两国的文集中均不多见,一般叙述作序原因,或叙写与所序之文有关的故实,夹叙夹议,间或抒情。唐代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便是中国文学叙事性序文的典型,韩愈为李翰所作的《张巡传》作序,却大施笔墨铺写张巡事迹以补原文之缺,《燕岩集》中该类序文仅有《遁庵集序》一篇,补写作者生前之事及超逸洒脱的风神。另有一类与文人雅士的集会有关,是宴饮逞才时而作,《燕岩集》中《李子厚贺子诗轴序》《会友录序》《海印寺酬唱诗序》《大隐菴唱酬诗序》等4篇便属此类。
需要说明的是,序文大都难以排除说明的成分,以阐明著书立说的动机、经过,介绍著作的内容、编次体例等,但《燕岩集》的序文往往不拘窠臼,泛泛的内容较少,所以将集中的序文分为两类,而未设说明性序文一类,是侧重其内容特点而言。此外,《燕岩集》中还有6篇赠序,即《赠白永叔入麒麟峡序》《族兄都尉公周甲寿序》《赠季雨序》《送沈伯修出宰狼川序》《送徐元德出宰殷山序》《赠悠久序》。赠序始于中国唐代,唐人常赋诗赠别,并于诗前作序,说明赠诗缘由及对方人品、境遇,如韩愈《送董邵南序》。后世也有文人送别仅作序,不作诗,这类文章被称为赠序。赠序虽以“序”名篇,但只是临别赠言性质的文字,内容多为勉励、推重、赞许之词,言辞恳切,意味深长,到明代逐渐与序跋文脱离。《燕岩集》中6篇赠序主要抒写离别之情和朴趾源的坎壈情怀,相当于散文小品,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序跋文,故不在本文研究之列,以避枝蔓。
(二)跋类散文
题,是置于著作、字画、碑帖之前的文字;跋,指写在著作、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字,二者总称“题跋”,内容多为品评、赏鉴、考订等。《燕岩集》的题跋文共计10篇,可粗划为4类。
《燕岩集》中评价性跋文有《为学之方图跋》《题友人菊花诗轴跋》等2篇。《为学之方图跋》高度评价赵敬菴的《为学之方图》,认为其对学习者而言“如夜之悬灯,如瞽之有相,如兵阵之按图,如医药之循方”(《燕岩集》卷4)。《题友人菊花诗轴跋》点评画花的技法与品评标准。赏鉴性跋文共5篇:《天山猎骑图跋》《清明上河图跋》《观斋所藏清明上河图跋》《日修斋所藏清明上河图》《桃花洞诗轴跋》等,以描述性文字为主,介绍卷轴的基本情况、何人收藏,并再现图画内容。考证性跋文有《题李堂画》《湛轩所藏清明上河图跋》等2篇,考证画卷年代、来历、真赝,并对其价值进行评判。感想性跋文仅有《绘声园集跋》,阐发朴趾源的交友之道,颂扬友谊可贵,情感充沛。
朴趾源的跋文创作以说明为前提,进而对著作、人物进行评价,或对书画进行鉴赏考释鉴定,或因事因文而感发。《燕岩集》中跋文数量少,篇幅也更为短小,研究空间不及序类散文。研究《燕岩集》序跋文中的思想艺术价值,当以序类散文为重点。
二、北学精神的表述
在应用文体中,序跋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或史料价值。序跋相对于正文,是辅助性次要文本,但这并不表示其可有可无、无作所为。作为“副文本”,序跋与其他副文本如扉页引言等不同,它的内容直接指涉正文,其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与正文构成了说明、评价的关系,呈现出“互文性”“共生性”,并“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可变化的)氛围”[2]71。《燕岩集》中的“序跋”类散文中渗透着朴趾源的实学思想。朴趾源生活在暗流涌动、波谲云诡的18世纪李朝社会,这是实学派蓬勃发展的土壤与契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贵族日益腐败,身份制度受到冲击并瓦解。李朝中期的进步人士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开阔了视野,他们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呼吁学习中国以及通过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实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十分兴盛,形成“北学派”。“北学”一词来源于《孟子·滕文公章句》:“陈良乃楚国人,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学派富有自主意识,对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他们活动于京城,对现实社会的观察更为广泛,深切地感到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主张扩大流通,改进生产工具,鼓励技术革命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城市庶民的正常生活,又被称为“利用厚生”派。
倡导学习清代中国“利用厚生”的先进科学技术是18世纪实学思想的核心旨归。因此,围绕实现学习中国的目标,他们坚定地批判传统的“华夷论”,主张结合朝鲜实际,面对现实,认识并接受清王朝文化科技中的先进性。对“华夷论”的批判与纠正,是朝鲜全面、深入认识清王朝文化进步性的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一根本认识问题,才能进一步排除“斥清尊明”的障碍。朴趾源是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深知朝鲜保守固执的“华夷观”是“北学中国”最根本的阻碍,必须彻底地予以批判,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清朝的进步性。在《会友录序》中,朴趾源指出:
吾岂不知中国之非古之诸夏也,其人之非先王之法服也。虽然,其人所处之地,岂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履之土乎?其人所交之士,其非齐鲁燕赵吴楚闽蜀博见远游之士乎?其人所读之书,岂非三代以来四海万国极博之载籍乎?制度虽变,而道义不殊,则所谓非古之诸夏者,亦岂无为之民而不为之臣者乎?[3]11
中国虽然已为满人统治,但中华大地依旧是先哲圣贤的故乡,存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虽然统治者发生变更,但是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却并未质变。朴趾源从实际出发,呼吁正视满族一统中国的现实,认清中华文化在清朝统治下良性延伸和发展。只有正确看待中国在“利用厚生”方面诸多可取之处,引进中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取长补短,才能富强朝鲜。朴趾源无意科举,在清贫生活中潜心学问,大约在30岁前后已是名扬朝鲜的著名学者了。朴趾源表明,自己既非上层士大夫,也不是中层知识分子,而是一名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反对朝鲜贵族有关斥清尊明乃至灭清复明的脱离实际的荒谬主张。借同为实学家的洪大容之口,朴趾源表达了李朝与中国之间交流互利的可能:
然则彼三人者之视吾,亦岂无华夷之别而等威之嫌乎?然而破去繁文,滌除苛节,披情露真,吐沥肝胆,其规模之广大,夫岂规规龌龊于声名势力之道者乎?[3]11
朴趾源在30岁时结交洪大容,接受其地球自转等西学,讨论北学和利用厚生之说,深受其思想影响。乾隆三十年(1765)冬,洪大容随李朝使节团来到清朝首都北京,结识“古杭三才”,即乾隆时期杭州的文人、诗人、画家严诚、潘庭筠、陆飞。他们谈古论今,“至诚恻怛”,结下终生友谊。洪大容在中国滞留两个多月,结交了20多名中国文人,就政治、哲学、文化、科技、文学、风俗等问题广泛地进行了交流。朴趾源借洪大容之口以明己志:清朝文人以广阔的胸襟接待了朝鲜来客,朝鲜士人的向学之心又何必拘泥于声名势力?可见朴趾源北学之心的炽热。作为18世纪最有建树的实学思想家,当时李朝其他学者如朴齐家、李德愁、柳得恭等,都虚心问学于朴趾源,共同谈论“利用厚生”之学,谋求国家兴盛之策。朴趾源的实学观可概括为:“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德可以正矣。”事物的实际功用是造福苍生的前提,而百姓获利是正德之源。利用—厚生—正德,三者是逐次递进关系。在《洪范羽翼序》中朴趾源谈及“北学”的具体内容:
今夫水蓄池以前,值岁旱干,溉田以车,通槽以闸,则水不可胜用矣。今子有其水,而不知用焉,是犹无水也。今夫火四时异候,刚柔殊功,陶冶耕耨,各适其宜,则火不可胜用矣。今子有其火而不知用焉,是犹无火也。至于我国百里之邑三百有六十,高山峻岭,十居七八,名虽百里,其实平畴不过三十里。民之所以贫也,彼崒然而高大者,四面而度之可得数倍之地,金银铜铁往往而出。若采矿有法,鼓炼有数,则可以富甲于天下矣。[3]13
把握利用自然规律,发展矿业、林业,各异其材,物尽其用,以求国家富强。朴趾源的实业观念明显与李朝主流的性理学相背,他肯定实践的第一性,反对空疏的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倾向。朴趾源不仅继承了早期实学家的基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出“利用”的北学。朴趾源以“利用厚生”代替前代实学家的“经世致用”,这是他对实学派发展作出的理论贡献。不但如此,朴趾源还指出了“利用”的范围:冶金业、农业、建筑业,还细化到车舆及农具制造等操作环节。他劝前往中国的朝鲜人虚心学习清朝先进的“文物”:
自农蚕畜牧,城郭宫室舟车,以至瓦簟笔尺之制,莫不目数而心较,目有所未至,则必问焉。心有所未谛,则必学焉。[3]105
朴趾源“利用厚生”的涵义大致可概括为以下方面。利用资源技术,以求富国强民。韩国史学家全海宗提出:“唯独燕岩以‘利用厚生’来代替‘经世致用’。他的这一主张是有根据的。在经典上也可找出‘利用厚生’一词,但是解释为‘工制什器,商通财货,以利民生,使衣食图谋民之厚生’。如此看来,我们不难理解燕岩将农工商相提并论,不谈修己治人,提倡“裕民益国之效’;无须执迷于‘六经’,主张‘利用厚生’的原因。”[4]383朴趾源重视实用和实践,主张同等对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朴趾源不同于前代正统实学家的“实心”“实德”,而强调“实用”“实践”,不必执着于“六经”,淡化理学色彩的观念在当时十分先进。“燕岩实学,即北学派实学是游离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派)实学的一种理论”[4]383。朴趾源的北学措施在《燕岩集》到处闪光,以《热河日记》最为集中,其序文中大多为高屋建瓴之语。
三、文学观念的阐发
作为朝鲜李朝成就最高的汉文作家,朴趾源充分利用序跋的文体功能,将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序跋创作中。朝鲜李朝的前期、中期一直奉行性理学的文学观,提倡所谓的“古文文体”,标榜先秦两汉的经典史书和唐宋古文,文风陈旧迂腐。正祖(1752~1800)统治时期,两班文人愈发执著朱子学“道文一致”的文学观,强调六经古文为“纯正的文风”,对于从事非经学创作的文人予以严厉打击,严重束缚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实学派文人批判这种忽视文学规律的文体政策,主张文学创作的“自然”“真情”,积极反对形式主义、模拟主义的文风。
(一)文学本体观
作为一名实学思想家,朴趾源的文学观始终扎根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叛逆性。朴趾源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文学表达的是人心的真性情,文学的本质是反映自然万物、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的“真”:
虫须花蕊,石绿羽翠,其文心不变;鼎足壶腰,日环月弦,字体犹全。其风云雷电,雨雪霜露,与夫飞潜走跃,笑啼鸣啸,而声色情境,至今自在。故不读易则不知画,不知画则不知文矣。[3]103
现实世界是人感觉的源泉,客观生活是人认识的基础。文学源自自然界的山形水状,月缺日圆,外界环境及其变化,创作者的心灵冲动和灵感由此产生。依照社会生活的本来存在,观察揣摩,“曲情尽形”,“声色”俱佳的文学于是产生。朴趾源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及社会性:
语不必大,道分毫厘。所可道也,瓦砾何弃。故梼杌恶兽,楚史取名,椎埋剧盗,迁固是叙。为文者惟其真而已矣。[3]57
切近现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是朴趾源文学观念首要的审美原则,作家在创作时无须粉饰、具体真实地直抒真情便是最本色的文学。文学不必非写空廓虚诞的内容,只要观察现实,如实描摹,即使微小的景观或事件,平俗市井的人物,也能塑造出真实深刻的艺术形象。
朴趾源认识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提出“日月滔滔,风谣屡变”,文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朴趾源指责当时文坛模拟抄袭的风气:
文以写意则止而已矣。彼临题操毫,忽思古语,强觉经旨,假意谨严。逐字矜壮者,譬如招工写真,更容貌而前也。目视不转,衣纹如拭,失其常度,虽良画史,难得其真。为文者亦何异于是哉。[3]57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而时刻向前发展的社会要求文学必须与时代共进,若固步自封,刻意模仿古人,相仿的程度愈高,那么离现实就愈远,就“难得其真”,偏离了文学本质的文学,自然没有可取之处。时人批判李德懋的作品“非古之诗也”,朴趾源为李德懋作序,为其正名,同时表达其变化的文学观:
今懋官朝鲜人也,山川风气地异中华,言语谣俗世非汉唐,若乃效法于中华,袭体于汉唐,则吾徒见其法益高而意实卑,体益似而言益伪。[3]107
地域环境的改变,文化风俗的差异,朝鲜民族的独特性必然不允许其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亘古固守。朴趾源指出,性理学派无视现实的文学创作,模仿相似度越高,文义就越卑下,就越脱离现实,失去“真”趣。真正而有价值的文学,应该像在《婴处稿序》中所说的“法古而能变,创新而能典”。法古和创新是文学的两翼,必须适度把握,“陈言之务祛则或失于无稽,立论之过高则或近乎不经”。可见,朴趾源的创新观并非毫无根基和法度,而是强调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密切契合。于大千世界“俯仰观察,曲情尽意”,发现社会的“即事有真趣”。朴趾源试图从民族的生活环境、文化的民族差异和时代性入手,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在本民族的现实中发掘创作素材,从人民语言和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创作出符合朝鲜实际的优秀文学作品。
(二)文学创作观
关于创作者修养,朴趾源在《炯言挑笔帖序》中提出:“虽小技有所忘,然后能成,而况大道乎?”该序结合历史上艺术家专注钻研而得道的事例,提出“忘荣辱”“生死不入于心”:
夫二子用心于内者欤?夫二子游于艺者欤?将二子忘死生荣辱之分,而至此其工也,岂非过欤?若二子之能有忘,愿相忘于道德。[3]107
心思虚静,精神清爽,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知所蔽,非此不能深刻地认识外物,以至于领会、掌握“道”。在《遯庵集序》中,朴趾源又一次提到“相忘于声名势力之外”“殆若忘饥渴而遗形骸”。真正理想的创作状态,应该是充分保持其自然本性、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心投入、与表现对象合二为一的精神状态。朴趾源的文学修养论与庄子的“心斋”“坐忘”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作为一名实学家,朴趾源的相忘“道德”又带有叛逆的反理学色彩,他反对道学为本,强调末端之用,即文章的实用意义应先于道学价值。关于文章的内容、形式及体制,朴趾源的议论更为精辟:
善为文者,其知兵乎?字譬则地,意譬则将也。题目者,敌国也。掌故者,战场墟垒也。束字为句,围句成章,犹队伍行阵也。韵以声之,词以耀之,犹金鼓旌旗也。照应者,烽埈也。譬喻者,游骑也。抑扬反复者,鏖战厮杀也。破题而结束者,先登而擒敌也。贵含蓄者,不禽二毛也。有余音者,振旅而凯旋也。[3]25
《骚坛赤帜引》通篇使用比喻,系统表达了朴趾源的文章学观念。文章写作如同行军布阵,立意为“将”,统帅全篇之掌故、字句、声韵、词藻及其他修辞方法,最终“破题”。文章采用精当的构思,无浮词漫语,句句出新:
善为文者,无可择之句。苟得其将,则钅且耰棘矜,尽化劲悍,而裂幅揭竿,顿新精彩矣。苟得其理,则家人常谈,犹列学官;而童讴里谣,亦属尔雅矣。[3]25
文章立论正确,若行军得“将”,日常事理,乡谣俚语均能入诗成韵,顿新精彩。朴趾源高度重视“立意”,文章的各个成分都要围绕文章的主题思想,任何题材、内容,只要是紧衬文章的中心主题,就是恰当的成分。《骚坛赤帜引》可视为朴趾源的创作方法论之集中体现,为文的最终目标是将“立意”阐明,在不偏离主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技巧,表情达意,推陈出新,便为上乘之文。
(三)文学风格观
朴趾源怀抱天下,忧时伤世,朴素务实。朴趾源无意于专门论述文学的美学风格,只是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个人的价值取向。朴趾源在《遁庵集序》中认为,文风的高妙处在于“闳中肆外,不事雕琢,苍朴老健,出于独得”,这可作为他风格论的核心内容。朴趾源评论文学始终不离客观实际,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在健康充实的主题下,不拘格套体例,不囿词藻技巧,即事缘情,表达个人的独特感受,“出于独得,径造妙域,不为诸生训诂所拘缠”。在《自笑集》序中,朴趾源也采用同样的价值标准:“若序记书说百余篇,皆宏博辩肆,勒成一家。”不囿于程式的宏大文风与个人独创性,是朴趾源论文风的两大标准。李朝时期两班文人将经学篇章及中国唐宋古文奉为典范,将四六骈体文用于科举考试和外交文书及公文写作中,甚至当时很多文人受中国明代文学的影响而热衷“拟古文”写作,这些倾向束缚了创作者的思维和创造性,脱离现实,违背了文学的本质,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朴趾源呼吁,只有发自现实和本心的创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苍朴老健”是朴趾源的美学评价标准,也是朴趾源的行文风格:
达士无所怪,俗人多所疑。所谓少所见,多所怪也。夫岂达士者,逐物目睹哉!闻一则形十于目,见十则设百于心,千怪万奇,还寄于物而己无与焉。[3]105
朴趾源的散文不追求文学形式,以意气行文,语简意赅,精练生动,笔力雄健。在其序跋文创作中,朴趾源关于文学风格论的表达最不明显,关于其文学风格论的研究,应以其论说文和《热河日记》为主。
(四)文学批评论
文学批评,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认知、阐析与评价。这种活动是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提高,不同的评价者对同一文学作品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朴趾源深切认识到不同的鉴赏者的评价原则极可能相差甚远,其在《蜋丸集序》中提出:“一以为龙珠,一以为蜋丸”,“真正之见,故在是非之间”;文学的正确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变化、争论中形成,在存在差异的观念中摸索矫正,才能导引文学进入前进的正轨。
朴趾源反对蹈袭,倡导独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个人独立精神的体现,即在《绿天馆集序》中提出的“求似者非真也”。文学追求的绝非形似,为文切忌拟古,只要能够反映现实及真情,便为妙文:
片言稍新,只字涉奇,则辙问古有是否。否则怫然于色曰:安敢乃耳。噫,于古有之,我何更为?……仓颉造字,傲于何古;颜渊好学,独无著书,苟使好古者,思仓颉造字之时,著颜子未发之旨,文始正矣。[3]107
当时朝鲜文坛泥于模仿、固步自封的风气令朴趾源十分忧虑,他呼吁文学创作要领悟前人的精神而非模拟形式,为文要发前人未发之意旨。朴趾源既在个人创作时力求突破前人,也在文学批评中肯定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品。朴趾源高度评价李德懋的创作:
为文章,必求古人旨趣,不为蹈袭虚伪之辞,一字一句,皆切近情理,摸写真境。每篇可读,曲尽其妙。[3]66
贵古贱今,信伪迷真是李朝中后期文坛的一大弊端。朴趾源肯定李德懋创作理念,学习的是古人的精神旨趣,而非古人的体例辞藻。李德懋的创作是扎根于时代、真实摹写朝鲜现实的文学,每篇都有独立价值。
朴趾源推崇《国风》,认为“文而无诗思,不可与知国风之色矣”。《国风》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民情风俗,以多姿多彩的画面反映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国风》用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普通人的春耕秋收、悲欢离合。朴趾源认为文章有“声”“色”“情境”,只有贴近生活,因事缘情,才能具有《国风》的精神。《国风》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受到朴趾源推崇的根本原因:
呜呼!三百之篇,无非鸟兽草木之名,不过闾巷男女之语,则邶桧之间,地不同风,江汉之上,民各其俗,故来采诗者以为列国之风。考其性情,验其俗谣,也复何疑乎此诗之不古耶?[3]107
朴趾源认为《诗经》的内容就是鸟兽草木、闾巷男女、民风地俗,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便是文学真境。优秀的文学作品,应立足现实,反映社会,描摹民生,展现真情,与“兴观群怨”的儒家评价标准有相通之处。朴趾源对于李德懋《婴处稿》不吝褒奖:
考请婴处之稿,而三韩之鸟兽草木,多识其名矣,貘男济妇之性情,可以观矣。虽谓朝鲜之风可也。[3]107
李德懋的创作再现了朝鲜的山川草木、民风世情。读李德懋的文学作品,可以了解江原道的男丁、济州道的妇女的生活画面,堪称“朝鲜之风”。文学应具时代意义和现实精神,身为朝鲜的文人,下笔时刻不能脱离朝鲜的风土民情,文学应为民、为时、为事而作。李德懋是朴趾源的学生,潜心跟随老师研习北学。文学观是北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朴趾源之所以如此推举李德懋的现实主义创作,是欲通过革新文学而宣扬实学,使新文学成为实学思想的羽翼,进而改造社会,以图朝鲜之国富民强。
四、不拘俗套的体例与风格
《燕岩集》序跋文中涉及朴趾源的北学思想及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如北学的精神纲领及实施领域,文学与自然、时代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提出了“即事趣真”“法古创新”的文学观。朴趾源的创作与其文学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身行力践,在序跋文中展示着个人的创作技巧与风格。
(一)坦率中肯,感情真挚
序跋的作者肩负多重责任,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为人作序者必须深入了解作者,认真研究原著,不能凭道听途说或浮光掠影的印象去敷衍成篇。朴趾源的序跋文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有助于读者深入原著之堂奥。如“学问之道无他,有不识,执塗之人而问之可也,僮仆多识我一字姑学”(《北学议序》,《燕岩集》卷七),这种言论在当时朝鲜社会中极其少见,为文治学者,不分等级、族姓、华夷,若能使朝鲜国富民强,都要虚心学习。不错失他人任何可取之处而“姑学”,这句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语,可视为朴趾源的北学思想的出发点。
朴趾源对于所序之文的评价绝不流于表面,他观点明确,有的放矢,敢于做出评价,体现出一代文宗的气魄:
此有明诸家于法古创新,互相訾謷而俱不得其正,同之并堕于季世之琐屑,无裨乎翼道而徒归于病俗而伤化也。[3]12
朴趾源看到了有明一代的中国文坛,在“法古”和“创新”问题上的夹缠与阙失。创新派呼吁“务去陈言”而导致“无稽”,不切实际的立论也会“不经”。这是朴趾源对于自己的门生朴齐家的忠告。朴齐家(1750~1805),字修其,号楚亭、贞蕤,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人,是18世纪朝鲜朝思想家,代表18世纪后半叶文学高度的卓越诗人,散文家,画家和书法家,朝鲜“诗文四大家”之一。朴齐家当时23岁,年轻气盛,容易好高骛远,朴趾源因材施教,针对他的个人情况及文学发展空间,在肯定鼓励的同时也给予坦诚的警醒,不要一味追求新变而失去根柢。李朝文坛流行学习明代的“前后七子”及唐宋派的风气,朴趾源敢于直截了当地指出明代文学的不足,充分展示出他的胆识与见地。
朴趾源珍视志同道合的友谊,于静夜里在大隐岩下感怀先贤,想见昔日士人交游赋诗之盛景。世事沧桑,不屈权贵的志士已然谏死,其所履之地尽为颓垣废址,朴趾源发出“盛衰之有时,而知善恶之不可磨也”的慨叹:“呜呼!当二子之游于此也,其意气之盛,顾何如哉!剧饮大醉,两相吐露,握手嘘唏,气可崩山岳,辩可决河汉,尚论千古,顾何尝不严于君子小人之辨哉!”(《大隐庵唱酬诗序》,《燕岩集》卷三)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自然可贵,但面对暴君佞臣傲然不屈的凛然之气更与山河长存。朴趾源借作序而抒怀逞才,通过大隐庵的名人故事抒发个人的交友之道,尽诉对先贤志士的景仰之情,悲思跌宕,慨叹淋漓。
(二)结构灵活,风格多样
序跋创作的个人色彩很浓,是作者申明个人的思想、见解、主张的园地,作者个人的性情、风格在序跋中常有鲜明体现,因此序跋文能见到作者的“一家之言”。朴趾源作序,杂文性很强,形式灵活,恣意漫笔,不拘一格。
尝于友人申元发、俞士京同宿白华庵,有缁俊者深夜独坐,佛灯迥然,禅榻明净,几上有般若法华诸经,因问俊:“尔颇晓法华经否?”谢:“不能。”又问:“尔能解作诗律否?”又谢:“不能。”又问:“山中又异僧可与游乎?”对曰:“无有”。明日坐真殊潭下,相与言,俊公眉眼清朗,若能粗解文字,诗不必工,可与联轴,谈不必玄,足以写怀,则岂不趣吾辈事耶?因相顾叹息而起。[3]106
该序先言李朝专尚儒教的背景下,佛教衰微,庙宇破败,高僧难遇;次写偶遇缁俊,与之问答;再写于《枫岳堂集》中发现海印高僧与缁俊之唱和,方知“缁俊”是“能诗”“能谈经”的“高僧”。朴趾源不直接写枫岳堂的著者,而从侧面烘托入手,通过缁俊的遗落世事映衬海印高僧的脱俗,进而启示读者,深山荒寺中亦有“独行自得”之人可与“方外之游”,其文集也定大有可观之处。该序欲扬先抑,前后对比,下笔利落,兼有余味,虽无颂美之词,却富褒赞之意。
《柳氏图书谱序》写连玉刻章,详细描写连玉篆刻时的出神入化:
连玉善刻章,握石承膝,侧肩垂颐,目之所瞬,口之所吹,蚕饮其墨,不绝如丝。聚吻进刀,用力以眉,既而捧腰仰天而唏。[3]106
又如《孔雀馆文稿自序》描写鼾声的铺陈:
尝与乡人宿,鼾息磊磊,如哇如啸,如叹如嘘,如吹火,如鼎之沸,如空车之顿辙,引者锯吼,喷者豕狗。[3]57
朴趾源为文深于取象,用语精当,长短不拘,庄谐杂出。连玉篆刻,全神贯注,浑然天成,有《庄子》里“解衣磐礴”“承蜩如掇”之风神;写人睡中鸣鼾,一连串铺陈,令人读之不禁哑然,又心领神会。如《骚坛赤帜引》的全篇作喻,譬行文同行军,破题立论如同征战凯旋,与杜牧《答庄充书》有形神之间的类似,朴趾源的序文较杜牧论述更加细致,不但涉及立意与言辞的关系,还阐释文章写作的具体环节。朴趾源散文天马行空,不拘常体,不受羁约,被当时文坛誉为“燕岩体”。金泽荣称赞他说:“夫何朴燕岩先生者,其生也在清之中世,其文欲为先秦则斯为先秦,欲为迁则斯为迁,欲为愈与轼则斯为愈与轼。壮雄闳钜,优游闲暇,杰然睥睨于千载之上,而为东邦诸家之所唯有也。”[5]灵活多样的结构及艺术特征是朴趾源序跋文的显著成就,由此可见朴趾源散文创作的风格与高度。
朴趾源的序跋文创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构成。作为李朝中期最重要的汉文创作者,他在《燕岩集》序跋中深入融合实学精神和文学改革观念,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传统儒学与文学的精神。朴趾源的序跋文不拘体例,精警凝练,饱含坦诚中肯的真知灼见和高屋建瓴的文论内涵。只有深入分析和把握域外汉文创作序跋文的思想蕴涵,才能一窥朝鲜汉文学世界的堂奥,也有助于今人把握和理解中华文化对东亚汉文创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