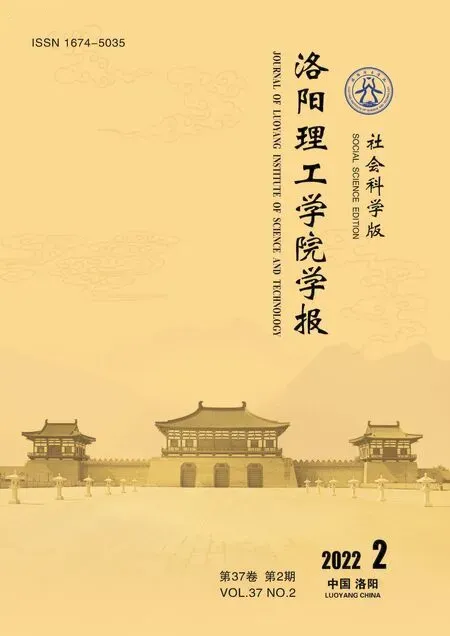王莽迁都洛阳刍议
王 丁 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710119)
就王莽迁都洛阳这一事件,过去的研究集中在王莽迁都洛阳的各方面原因。尽管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不过对王莽为何迁都洛阳一事的深层次原因探讨却稍显不足①。以长安和洛阳及其所在地区在两汉政治演进过程当中的地位变化为视域,也是较为可取的研究路径。笔者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汉初期至王莽迁都洛阳前的史料加以爬梳,由此寻找相关线索,从而厘清王莽迁都洛阳一事的前因后果,并借此求教方家。
一、西汉至王莽时期洛阳的城市地位
对西汉末期王莽迁都洛阳的原因进行探讨,离不开对西汉时期洛阳的城市地位进行分析。
这一问题可以追溯至西汉建立伊始。随着刘邦打败项羽,一统天下,统治集团内部对定都长安或洛阳孰优孰劣的争论便已展开。《史记·高祖本纪》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1]380-381汉初刘邦建都洛阳,一方面可能因为此时关中故秦都城宫室已有所损毁,而此时的洛阳南宫仍在,相对长安来说无需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从另一方面来看,建都洛阳与洛阳地区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只不过洛阳地处四战之地,地理区位优势在汉初分封诸王的特殊背景之下较之长安来说显得相对逊色。张良等谋士建议以长安为都也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1]2044刘邦舍弃洛阳建都长安,究其原因理应是对汉初特殊的政治局势加以考虑后所选取的理想方案。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这一决策,开启了自西汉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尊都城长安为正统的滥觞。
在西汉初期人们的认知观念当中,并没有像周人一样将洛阳作为可以与长安相提并论的东都加以重视,他们只是简单地将洛阳视作“天下要冲”。《史记·三王世家》载:“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1]2115汉武帝认为洛阳是“汉国之大都”,实际上只是在强调洛阳是汉王朝辖境范围之内较大的城邑。形容城市为“大都”之例,还可见于《左传·隐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2]3725左传所提及的“大都”与汉武帝将洛阳所视作的“大都”在字面意义上区别不大,其意均为一国当中仅次于国都的较大城邑。汉武帝并没有将洛阳封给皇子,应是为了防止所封皇子依靠洛阳的战略地位及武库的军事储备发动叛乱,危及国家社稷。
到了西汉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对于洛阳与长安的定位随着经学的渗入逐渐发生了新的转变。《汉书·翼奉传》载:“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3]3175在翼奉看来,汉家现行的宗庙祭祀制度有违古制,同时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由此他认为汉家必须以迁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为了给自己所主张的迁都观点寻求更大的理论空间,翼奉以三代迁洛的历史作为其理论依据,对汉元帝说:“‘昔成王徙洛,般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戆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3]3178翼奉的迁都主张虽然并没有被汉元帝采纳,但其为了解决宗庙祭祀问题所做的努力被匡衡等人继承下来。
探明翼奉的思想主张,离不开对翼奉的知识结构进行梳理。翼奉所学之诗实为《齐诗》,这在《汉书·翼奉传》就有所体现:“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3]3167翼奉所学的《齐诗》,当传自齐人辕固。《齐诗》学派的鲜明学术特点之一便是极言变革。早在汉景帝之时,辕固就曾因思想激进而被窦太后加罪,落得“刺豕”抵罪的下场,幸得汉景帝施以援手才幸免于难。辕固在与黄生的辩论中,极力支持汤武革命这一举措,也可能对汤武的统治政策有所支持。《史记·封禅书》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1371三代建都于河洛地区,并依靠这一地区走向繁荣。因此,在《齐诗》学派的学术思想中,河洛地区可能被塑造成为一个极其理想的定都之地。翼奉的建议当中也提到了“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这一重点,他可能会认为汤武之兴在于择都。尽管翼奉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以实现,但却开启了西汉迁都洛阳的思想滥觞。
随着西汉统治危机的到来,王莽得以代汉称帝。易代之际的王莽为了使新室获得正统地位并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与知识分子进行紧密合作的态度。就《齐诗》学派来说,他们与王莽改制的联系不可谓不密切。有的学者认为:“哀平之际以及新莽朝初期,《齐诗》学者纷纷采取与王莽合作的态度。师丹见知于王莽,满昌为王莽《诗》学祭酒,张邯为新莽朝明学男,又以大长秋进封大司徒,伏堪与伏黯也都曾出仕于新朝。对于这些人与王莽的关系及与新莽朝的合作,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贪图富贵或屈从于权势……与其说这些人是无节操的贰臣,还不如说他们试图通过与王莽的合作,来实现其盛世的乌托邦理想,是为民与为君理念的博弈结果。”[4]如此说来,王莽与《齐诗》学派学者展开紧密合作后,也可能会受到《齐诗》学派变革思潮以及先前翼奉迁都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使得王莽在“以洛阳为新室东都,长安为新室西都”[3]4128、单纯模仿周代两都体制之余,更加笃信迁都洛阳可以使得统治安稳,王朝兴盛。总而言之,巩固统治的现实需求使得洛阳所处的河洛地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以长安作为都城的观念已然在臣民心中根深蒂固,这使得王莽难以进行迁都,于是出现了民众不配合王莽进行迁都的现象:“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3]4132王莽仅凭一己之愿难以迁都,只能先将此事作罢。
二、现实因素与王莽迁都
单纯以《齐诗》学派的政治参与作为王莽迁都洛阳的解释似乎略显单薄,实际上《齐诗》早已亡佚,这使得试图从《齐诗》当中获悉对迁都思潮施以影响的具体内容变得并不现实。西汉时期,与迁都举措有关的学说思潮及经义材料稍显不足,使得以往学者转向从现实因素中寻找并探讨王莽迁都的原因。这不失为一条可取的路径,但还可以对他们的既有认知进行一定的补充与修正。
以往学者注意到三辅地区的人口在王莽之时超出容纳极限,但三辅地区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并不能作为王莽迁都的现实原因。《盐铁论·园池》说:“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菜,不能相赡。”[5]172实际上在汉昭帝召开盐铁会议前,三辅地区便已经出现了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这一问题必然不会被搁置到王莽时代再加以解决。以往学者认为迁都洛阳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加以耕种,实则不然。早在汉初,张良便认识到了洛阳地区其实并不适合大规模的人口居住,即《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1]2043-2044洛阳地区可耕种土地面积早在汉初人口凋零之时就已相对狭小,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人口增加,这一地区的可用土地必定会再次捉襟见肘。王莽以迁都洛阳来缓解人口压力,很有可能于事无补。
汉宣帝在位之时也曾敏锐地察觉到了三辅地区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汉书·食货志》说:“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3]1141汉宣帝之时耿寿昌注意到从关东漕运粮食到京师的弊端,建议就近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转运到长安,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京师人口过多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并减省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然而,好景不长,西汉中后期是西汉历史上自然灾害发生的高峰期。有的学者统计,汉元帝、汉成帝及以后约发生大小灾害1 052次,占到西汉时期总数的81%。其中,这些灾害不乏破坏性极强的重大灾害[6]。《汉书·成帝纪》载:“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甚。”[3]318《汉书·谷永传》载:“百川沸腾,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3]3470《汉书·王莽传》载:“是月,大雨六十余日。”[3]4162从传世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可见元成时期及其以后的自然灾害有着影响范围广、波及人数众多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与西汉前期的自然灾害相比,无论是波及范围还是破坏力,都更大。关东地区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这一地区民众的生活变得极为困难。王莽迁都洛阳,除为了缓解三辅大众的生存压力外,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自然灾害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政府的统治危机。西汉时期,尽管政府对受灾地区进行一定的帮扶,但是频繁的自然灾害令政府越来越难以承受。灾害发生后,多数失去家园及产业的普通百姓被迫成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一旦对流民处置不当,流民转瞬之间就会变为危机统治的力量:“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3]4125有人认为,关中与关东经济状况的反差,造成了东、西关系的紧张。东方纷乱,东方流民大量涌入关中,也带来不安定因素。饥民聚团劫掠本就是迫于生计,而王莽却视之为反新复汉,严酷镇压[7]。
与此同时,东方旧有的刘姓诸侯王势力也开始转化为反莽势力。《汉书·王莽传》载:“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3]4110旧有的刘姓诸侯王势力与屡遭自然灾害从而流离失所的东方流民,对王莽来说均为不可小觑的力量。王莽面临的东方危机与周公辅政时所面临的东方危机如出一辙,均是既存在着以宗室为主体的反抗力量,同时也存在着以平民为主体的反抗力量。错综复杂的东方局势使得原本定都于关中地区的王莽疲于应对,潜在的统治危机使王莽认识到定都长安不利于长久地对东方地区进行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王莽迁都的欲望。
王莽的迁都规划可能酝酿已久并有所流露,这使得王莽的意图在具体实施前便已暴露,于是才有了前文所引长安地区的民众得知王莽欲要迁都洛阳后不再修整屋舍的不配合之举。为了应对民众对迁都一事的抵触行为,王莽采用了惯用的符命手段辅以天象征兆对民众进行心理疏导,说:“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3]4132然而,从后续史实来看,王莽的心理疏导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礼仪制度与王莽迁都
王莽迁都洛阳有益于新室在规避汉家已有宗庙祭祀制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宗庙祭祀制度。这从王莽代汉称帝后,对汉家宗庙社稷的态度可以看出:“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3]4108王莽将自己的祖先与汉家的祖先分别假托为虞舜与唐尧,意图借唐尧禅位给虞舜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继承汉家社稷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源自刘氏祖先唐尧让位于贤能之人的政治实践。由此,王莽承认汉家宗庙社稷的合法性也是在对自己从汉家手中取得的皇权合法性的一种认可。不过,王莽对汉朝统治者的态度远没有对待刘氏宗庙的态度那般恭敬。王莽认为:“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3]4109王莽在迫不得已遵奉汉家宗庙的同时,采取了刻意抹除刘氏影响力的办法,甚至与“刘”字相关的“卯、金、刀”三字及其所代表的字面意义也在消除之列。
新室新立,除迫不得已遵奉原有的汉家宗庙外,新室或早或晚地也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宗庙与陵园区,但王莽对这一问题一直采取搁置态度。这可能与王莽本人在礼仪制度建设上的矛盾心理有关。王莽本人十分尊崇礼仪制度并按此行事,甚至曾一度达到几乎不通人情的地步,这在王莽安葬汉平帝之时便已有所体现。有人认为:“平帝时期是王莽主政的,平帝的陵墓自然也少不得王莽的谋划,王莽个人的经历和思考势必影响康陵的选址。有迹象表明,王莽十分痛恨‘为人后者’违背礼仪尊崇本生父亲的做法。”[8]王莽在对汉平帝陵墓进行布置时,十分注重礼仪制度规范,这才有了汉平帝与汉哀帝平辈相继为帝,却相继葬于渭北主陵区的奇异现象。
此外,待到新室文母皇太后王政君去世后,王莽在处理她的丧葬问题时也采取了尊崇礼仪制度的作法。王莽对具体的葬仪细节进行了奇怪的改动:“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3]4132即王莽一方面将王政君与汉元帝合葬在同一陵墓之内,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王氏与刘氏已然有别,有意地将二人分沟而绝;为了突出新室的正统地位,王莽甚至还为王政君立庙,并以汉元帝配食王政君。王莽的这一离奇举措,既表明王莽在处理丧葬问题上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规范②,又可见王莽在处理王氏与刘氏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的矛盾心理。传世文献当中迟迟未见王莽为自己进行陵墓规划一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王莽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陵园的布置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以便新室的宗庙祭祀制度会尽量符合礼仪制度的要求。这一时期的长安地区,很可能已经难以寻找到一片区域适合布置新室的陵园,以缓解刘氏在礼仪制度上对新室带来的冲击。葛剑雄认为,汉元帝之时,长安地区就已经布满陵县,没有能力再去广泛地吸纳移民,于是汉元帝停止了西汉历代统治者所进行的迁徙民众充实陵县的举措[9]151。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长安地区已然帝陵密布所致。为此,将新室宗庙及陵园建在哪里以及怎样建立新室宗庙及陵园,也就成了一个困扰王莽的问题。前文所引有关翼奉为了解决汉家宗庙祭祀问题所提出的方法即迁都洛阳,这有可能给王莽带来启示。这时对王莽来说,另起炉灶迁都洛阳,继而重新规划陵园区域与创立宗庙,也可以回避这一问题,将刘氏给他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化。
王莽决心迁都洛阳,很有可能也是效仿周制所进行的礼仪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这离不开对西周初年建立东都洛邑的经过进行分析。西周在营建东都洛邑之际,最先考虑到的是四方缴纳贡赋的成本以及便利程度问题。《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133洛邑的营建考虑到便利四方缴纳贡赋的现实因素。《逸周书·度邑解》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10]480-481周武王选择在洛邑营建东都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地区“无远天室”,即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适宜。王莽信奉周礼,在《周礼·地官·大司徒》也有着关于“地中”的说法。“地中”与“天下之中”概念类似,从地理区位上来看均指代洛邑地区。这可能也给王莽迁都带来启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2]1516-1517即统治者一旦对“地中”寻找得当并在“地中”所在之地安邦建国,“地中”这一特殊的区位因素就可以发挥使政治变得安定清明的作用,民众也可以由此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
王莽是在西汉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基础上擅汉而立的。王莽为了挽救西汉中后期以来的危机并巩固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改革。针对西汉后期以来的社会危机,有学者认为王莽坚信“制定则天下自平”,故而王莽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11]。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王莽为了解决由来已久的危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王莽笃信“制定则天下自平”的乌托邦式理想,其改革思想大多数源自周代的礼仪制度和典章文献。在王莽看来,迁都洛阳,有利于借助“地中”这一特殊区位优势,解除统治危机,稳定新室。
四、结 语
西汉建立伊始,就对定都洛阳、长安有过短暂的讨论。西汉统治集团结合汉初的政治形势,最终决定定都长安。此后,失去都城地位的洛阳仅仅被认为是一座较大的城邑。直到翼奉提议以迁都的方式解决汉家礼制问题,以洛阳为都的想法才再次被提及。到了王莽时期,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汉家礼仪制度对新室带来的影响,王莽愈发笃信迁都理论,并试图迁都洛阳,借以稳定新室统治。但由于王莽的想法招致了臣民的一致反对,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注 释:
①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详见吴从祥的《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23-27页;沈刚的《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0卷第3辑第95-100页;柳华的《两汉时期“择都”观念及其影响研究》,山西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
② 关于王莽在处理丧葬问题上坚持礼仪制度规范之例,还可参考王莽坚持毁去丁、傅太后坟茔一事.《汉书·师丹传》载:“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见班固的《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