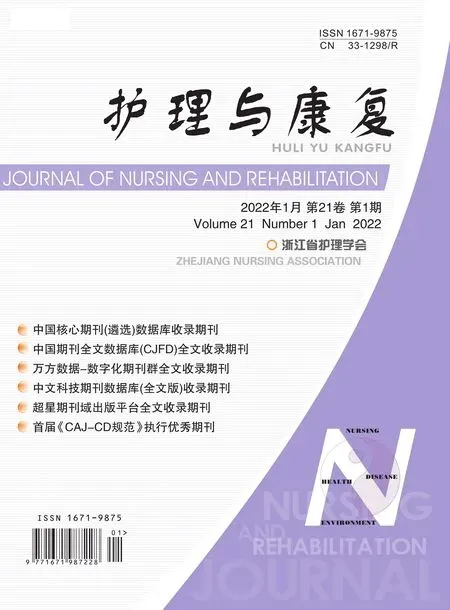肿瘤照护者预期性悲伤的评估及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王陆宇,李 岩,杨先荣
1.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00;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00
肿瘤作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年发病率持续上升[1]。2018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约1 810万,死亡人数约960万[2]。多数患者是在肿瘤中晚期确诊,此时其照护者由于未来的规划无法实现以及自我意象丧失等原因出现身心、情感等方面应激反应,其中包括预感到至亲会离去而出现的预期性悲伤(anticipatory grief,AG)[3-4]。调查显示AG广泛出现在肿瘤患者照护者群体中,严重时可高达25.9%[4]。AG会导致肿瘤患者照护者出现生理、心理、认知及精神方面等问题,降低其照护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同时影响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恢复。本文对肿瘤患者照护者AG的相关概念、评估及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以期为研究肿瘤患者照护者AG提供借鉴。
1 概述
悲伤主要包括基本性哀伤和AG两种表现形式[5]。基本性哀伤为照护者在失去至亲之后产生的悲痛感[6]。AG指对未来的预见性悲哀,是个体预感到亲人即将离世而产生的情感变化过程,包括悲痛、应对、计划等[7]。1994年Lindemann[8]首次提出AG并定义为面对失去至亲之前的悲伤反应。1988年Rando[9]把AG重新定义为在失去至亲的刺激下引发的悲痛、应变、策划和心理社会重构及其协同作用的结果。1996年北美学者定义AG为个人或社会在预感到可能有损失的情况下作出自身认知、理性、感性的反应和行为改变[10]。2014年Lindauer等[11]把AG的发生时间规定为患者临终前的6~18个月,照护者这段时间感知到患者即将离世所产生的持续性情感及生理性负性应对。此后,AG发展为照护诊断。Nielsen等[12]研究显示,约有15.2%的肿瘤患者照护者有严重的AG,负性情绪直接或间接影响患者及其照护者的情绪,从而影响生活质量。因此,肿瘤患者照护者的心理及身体健康需要更多的关注。
2 评估工具
2.1 预感性悲伤量表(Anticipatory Grief Scale,AGS)
AGS是由Theut等[13]以其他悲伤评估工具为基础编制,用于评估并测量痴呆患者照护者的AG。AGS共有27项,应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得分与照护者AG呈正相关,Cronbach’sα系数为0.84。目前,AGS已同时应用于肿瘤、危重症、姑息治疗等患者照护者中[14-15]。我国针对该量表有两个汉化版本,2005年刘乃志等[16]的AGS,Cronbach’sα系数为0.82,但有一定的文化思想差异。2016年辛大君[17]重新汉化形成新版本的AGS,保留原量表的27项,主要分为悲痛、愧疚、失落感、焦虑、性情易怒和完成任务的能力,条目容易理解和回答,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为0.788~0.896。焦杰等[18]应用该量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肿瘤患者的配偶AG处于中等水平。
2.2 Marwit-Meuser悲伤量表(the Samuel J Marwit and Thomas M Meuser Caregiver Grief Inventory,MM-CGI)
MM-CGI由Marwit等[19]编制,从个体牺牲感(18项)、内在的渴望和悲痛(15项)、害怕/感受寂寞(17项)三个维度测量痴呆患者照护者的痛苦程度,应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得分与照护者痛苦程度呈正相关,得分>175.6分表示照护者需要悲伤辅导或社会支持以应对负性情绪,得分<112.4分说明照护者存在悲伤否认。高钰琳等[20]在2009年对MM-CGI进行汉化,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均值为0.856,主要用于测量痴呆患者居丧期哀伤水平,尚缺乏应用于肿瘤患者照护者的研究。
2.3 照护者悲伤量表(Caregiver Grief Scale,CGS)
CGS是2015年Meichsner[21]等研制,该量表主要从悲痛感、关系丢失、情感剥夺和对剥夺感接受四个维度对痴呆患者的照护者行悲伤评估。采用Liker 5级评分法,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得分与照护者的痛苦程度呈正相关,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在0.67~0.89。CGS增加了避免悲伤情绪表露相关内容的评估,对悲伤情绪的评估更为全面,但CGS对一个因素的评估仅靠两或三项,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倚,且目前国内尚缺乏CGS的汉化。
3 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影响肿瘤患者照护者AG的人口学因素有性别、年龄、照护时间、患者自理能力及有无照顾经历等,其中患者自理能力被认为是影响照护者AG的主要因素。李佳倩等[4]研究显示,男性肿瘤患者照护者的AG水平低于女性照护者,这可能与男性与女性思维差异有关。且肿瘤患者的病程越长,其照护者的AG水平越高[22]。郭婷[23]研究指出肿瘤患者的自理能力较差会加重照护者的照顾负担,从而影响照护者AG水平,同时肿瘤患者的年龄与其照护者的AG水平呈负相关。有亲属离世经历的照护者的AG水平更高[17]。
3.2 社会支持
研究发现肿瘤患者家属AG水平同社会支持呈负相关,社会支持水平高的家庭有来自同事、朋友、领导等层面的照护和鼓励,可提升其主观幸福感[24]。同时,对生活环境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AG。研究显示,非母语国家居住者的AG程度更严重[25]。我国各城市医疗水平差异明显,患者多选择异地就医,就医地是否为居住地对肿瘤患者照护者AG的影响需进一步探讨。
3.3 心理因素
研究指出AG水平同心理弹性呈正相关,心理弹性得分越高的人群,缓解悲伤情绪的能力越强,且面对死亡的心态和看法同肿瘤患者照护者的AG水平呈负相关[26]。Holm等[27]研究发现,当照护者存在焦虑、抑郁时,其AG水平更严重。肿瘤患者照护者的AG水平与诸多心理因素相关,但目前我国较缺乏关于肿瘤患者照护者AG水平与心理因素关系的研究。
4 结语
AG会对肿瘤患者照护者生理、心理及生活质量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但目前我国缺乏对肿瘤患者照护者AG的研究。建议今后的研究在国外量表基础上编制适用于我国肿瘤照护者的评价工具,进一步分析照护者AG的影响因素,探究针对肿瘤患者照护者AG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肿瘤患者及其照护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