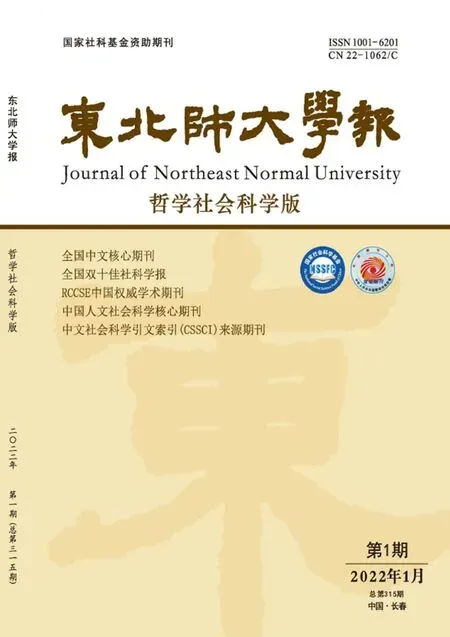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及其裁判路径
王 春 梅
(天津师范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87)
伴随《民法典》的实施,《民法总则》等九部民事立法失去效力,但《民法总则》 第185条对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却直接并入和转化为《民法典》第185条,继续发挥规范和保护英烈人格利益之作用。与此同时,继《民法总则》之后,2018年4月27日通过,并于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在第25条、第26条亦对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至此,《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与《民法典》第185条共同搭建起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制度,传承英烈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诋毁、侮辱英烈的事件却依然不断发生,甚至在2018年5月《英雄烈士保护法》刚刚实施不久,就相继发生“暴走漫画”在“今日头条”等平台发布戏谑、侮辱董存瑞烈士和叶挺烈士搞笑短视频事件(1)2018年5月8日,“暴走漫画”在“今日头条”等平台发布“王尼玛”戏谑侮辱董存瑞和叶挺烈士视频。叶挺后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暴走漫画被判决公开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并向叶挺烈士近亲属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暴走漫画公开道歉,暴走漫画侮辱烈士事件全程回顾》,https://www.sohu.com/a/273407661_100151758.,2020年4月26日。,“抖音”和“搜狗”侮辱邱少云烈士广告事件(2)2018年6月6日,“今日头条”旗下短视频平台抖音在搜狗搜索的广告投放中出现了侮辱英烈邱少云的内容,被北京市网信办工商局依法约谈并责令整改。《抖音和搜狗因“侮辱英烈内容”被立案处理》,https://kuaibao.qq.com/s/20180607A0K3KJ00?refer=cp _1026,2020年4月26日。,以及腾讯平台侮辱刘胡兰、董存瑞烈士及其家属等一系列事件(3)2018年6月13日,腾讯平台旗下多款产品出现侮辱烈士刘胡兰、董存瑞及其家属等内容,被腾讯采取删除/下架视频、封停帐号、删除信息和公众号文章等方式予以处理。《网友称腾讯多平台再现侮辱英烈内容 腾讯回应》,https://finance.china.com/tech/13001906/20180615/32533670.html,2020年4月26日。。此外,2018年还发生了我国首例网民侮辱消防烈士被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4)2018年6月12日,全国首例网民侮辱消防烈士公益诉讼案开庭,网民曾某对谢勇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在微信群中公然发表侮辱性言论,侵犯了谢勇烈士名誉权,被判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全国首例侵犯烈士名誉案宣判被判公开道歉》,https://www.sohu.com/a/235595686_100034669,2020年4月26日。。2019年仅上半年,就发生了河南理发店调侃英烈刘胡兰事件(5)2019年3月28日,河南驻马店某理发店出现侮辱烈士刘胡兰的广告词。工商、公安等部门启动行政执法程序责令其停业整顿,并要求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理发店广告调侃英烈刘胡兰 官方:责令停业整顿》,http://news.sina.com.cn/s/2019-03-30/doc-ihsxncvh6816585.shtml,2020年4月26日。和十余起在网上侮辱四川木里县森林火灾英雄事件(6)2019年3月30日18时,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发生森林火灾,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队员壮烈牺牲。在举国哀悼之时,陆续发生泉州尹某云、陕西孙某发和张某、重庆唐某、都江堰伏某某、甘肃杜某等十余起侮辱救火英雄烈士的事件。《全国12起侮辱救火烈士事件,他们的身份曝光,都这样的人在骂英雄》,https://kuaibao.qq.com/s/20190406A0HZB800,2020年4月26日。。甚至在疫情肆虐期间,侮辱英烈事件仍然没有停止发生(7)2021年2月19日,仇某明以“辣笔小球”为网名在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5名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南京市公安局抓获。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仇某明批准逮捕,其或可成为依据2021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这一新罪名判决的第一人。《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正式入刑!他或成新罪名判决第一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034183967152067,2021年9月10日。。这些频繁发生的诋毁、侮辱英烈事件在不断挑战良知与道德底线的同时,也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立法,思考其规范的内置冲突与局限问题。
另一方面,英烈与死者不仅具有身份同质性,在规范内容上亦具有极高的重合度,甚而可以认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是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对侵害英烈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8)杨立新:《对民法总则草案规定第185条的看法》,http://www.chinanotary.org/content/2017-03/16/content_7055561.htm?node=82573,2019年5月9日。,由此使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与死者利益保护具有了某种关联。应该说,对于死者利益保护,我国立法层面曾经长期处于规范空白状态,仅在司法解释层面有相应规定(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文中简称最高院《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和第7条。。《民法典》吸收司法实践之成熟做法,将死者利益保护纳入其人格权编,并在第994条作出具体规定(10)《民法典》第994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填补了我国死者利益保护之立法空白,彰显了《民法典》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那么,在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和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均指向和涵盖“死者”身份,并在规范内容上具有极高重合度的前提下,能否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之请求权基础,并依死者利益保护之裁判路径,弥合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之内置冲突与局限,以强化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就成为本文之主题。
一、请求权规范基础扩张: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之弊囿弥合
(一)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之局限与内置冲突
《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作为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基本规定,具有共同的规范目的,可以统称为英烈保护规范,在保护英烈人格利益、弘扬和倡导英烈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从两部法律规范的条文内容看,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内置冲突,而且存在着一定的规范局限。
就内置冲突而言,主要表现在由两部法律规范行文表达所内置的保护主体范围之差异,并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虽然《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泛以“英雄烈士”为保护主体(11)对于“英雄烈士”的范围,一则从“英雄”“烈士”两者关系角度,本文将“英雄”作名词认定,与“烈士”并列使用,二则将“英雄”作狭义解读,限定为牺牲之英雄。,但前者采“英雄烈士等”之表达,后者则表述为“英雄烈士”。该“等”字之差,不仅使《民法典》第185条所保护的主体范围表现为一种开放式结构,带来对该“等”字所涵摄的主体范围的阐释问题(12)对此可以认为,第185条在《民法总则》中虽然规定于责任规范部分,但其并非针对一般民事主体而设定的责任规范,而是作为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的专项条款而存在的,故该“等”字既不能理解为设定了一个“框架式的主体范围”,从而将其保护范围扩展和涵盖到其他自然人主体,也不能因英雄烈士的死者身份而扩展到一般死者,而只能特指与“与英雄烈士具有相同社会意义的人”。,而且造成了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所保护的主体范围之不一致。另一方面,两部规范的历史维度设定内置了二者保护的“英雄烈士”范围之差异。《民法典》第185条渊源于《民法总则》第185条,而后者作为我国第一个英烈条款,在行文内容和立法意旨上并没有任何历史维度之考量与限定,由此意味《民法典》第185条所保护的“英雄烈士等”亦不存在历史维度限定问题。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本身虽然没有历史维度的内容,但该法第2条在彰显英烈历史功勋,要求国家和人民尊崇和铭记其牺牲与贡献的同时,又在第2款对所保护的“英雄烈士”设定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维度,从而限定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所保护的“英雄烈士”的历史之维,明确昭示出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重点突出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英烈予以保护的立法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王思丝:《崇尚捍卫英雄烈士 传承英雄烈士精神——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805/a6477c46470f49dab13745152b12a133.shtml,2019年5月10日。。
就规范局限而言,亦有两方面局限:一是由两部规范所采取的列举式立法技术带来的保护客体范围之局限。也就是说,《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均采取列举式立法方式,且将所保护的英烈人格利益范围限定为“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四大范畴利益,其后既没有“权”字,也没有“等”字,这在昭示出利益保护模式且符合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规定之同时,亦使其封闭式的结构特色与局限性呈现无余,既无以涵盖英烈的其他具体人格利益,也无以容纳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更无以覆盖英烈的遗体、遗骨等人格物的救济与保护。二是两部规范均以英烈个体之人格利益为指向,无法涵盖对英烈整体之人格利益的救济与保护。就《民法典》第185条而言,其作为责任规范与救济规范,自然应当以英烈个体之人格利益受侵犯为适用前提,这亦是私法规范本质之要求。与此同时,其在行文上虽然采用了“英雄烈士等”为保护主体之法律表达,但既不能将该“等”字理解为设定了一个“框架式的主体范围”,也不能理解为英烈个体之集合,而仅应特指“与英雄烈士具有相同社会意义的人”(14)房绍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不容侵害》,《检察日报》2017年4月25日03版.。
对《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亦应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虽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英雄烈士保护法》之解读,该法所规定的缅怀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等制度是将“英雄烈士”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规范(1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王思丝:《崇尚捍卫英雄烈士 传承英雄烈士精神——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22条亦规定有“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但是其第25条、第26条作为救济规范,却只能在英烈个体之人格利益受侵犯时才有适用之余地与可能。但问题在于,“英雄烈士”既可能表现为整体性之存在,也可能表现为个体存在,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亦应有个体保护与整体保护之问题。实际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个案(16)2018年12月30日,李某换上其收藏的一套仿“一战”德军军服及军帽,并将一套仿“二战”德军纳粹军服提供给吴某,在萧山烈士陵园持手机拍照,并在好友数为1940人的QQ空间发布,短时间内相关内容被转发扩散达36 800余条,社会影响恶劣,引发网友强烈不满。2019年1月8日,公安机关对李某和吴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4日和7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4月4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李某、吴某侵害萧山烈士陵园烈士荣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5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判决被告李某、吴某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浙江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判决》,《中国青年报》,http://zqb. cyol. com /html/ 2019-05/22/nw.D110000zgqnb_20190522_9-02.htm,2020年5月28日。就报道来看,一则该案中李某和吴某的行为似不符合侵犯荣誉之构成,以侵害荣誉为案由提起公益诉讼非谓妥当;二则李某和吴某的行为并非侵犯某个或某些特定烈士的人格利益,而是指向萧山烈士陵园烈士之整体,是对该烈士陵园英雄烈士整体人格尊严之侵犯。,不仅提出英烈其他人格利益保护之必要,而且揭示出英烈整体人格利益保护之现实必要性。
(二)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规范基础扩张之可能
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的内置冲突与局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宗旨与立法目的之实现,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其规范之实效性,由此产生在现行法框架内扩张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之请求权规范基础,强化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之问题。当然,请求权规范基础之扩张不仅要求被扩张适用的请求权规范与原有规范之间存在紧密的有机耦合,而且要求规范内容不存在扩张适用之障碍。就此而言,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虽然在立法目的、保护主体、保护的利益范围,以及救济程序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英雄烈士”与死者的身份同质与伦理同质完全可以形成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之间的有机耦合,而两类规范在保护内容上的高度关联与重合则可以消弭请求权基础扩张的法律适用障碍。
首先,“英雄烈士”与死者的身份同质与伦理同质铺就了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规范基础扩张之可能。对于第185条所指“英雄烈士”的关系及“英雄”的范围,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初,我国学者就曾进行过探讨,但从汉语修辞和我国语言的通常表达习惯,以及考虑《民法总则》第185条出台的背景及实践应用,同时秉持体系解释原则,宜将“英雄”“烈士”作名词使用,解释为并列关系,故“英雄烈士”应为牺牲之人,亦如死者在表象世界中丧失了身体之物质存在性与生命属性。而对于逝者,无论是一般之“死者”,抑或是“英雄烈士”,善的伦理社会生活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尊重。而且,每个人在其生命存续期间,亦具有一种正当的合理期待,即期待其人格利益在物质生命消失之后仍然能够获得和享受到这种最基本的尊重。而不得侵犯为尊重之底线要求,由此使死者利益保护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具有了相同的伦理性。
其次,两类规范的立法模式与保护的利益范围高度重合。在立法模式上,《民法典》第994条与前述英烈保护规范同出一辙,均采取间接模式提供保护。但是,在保护的利益范围上,第994条却放弃英烈保护规范的单纯列举式技术,而代之以列举加概括之方式,为死者提供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五大人格利益范畴,外加之遗体等的保护,在使其保护的利益范围呈现出极大开放性的同时,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四大人格利益发生高度重合。
再次,救济和保护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对于主体来说,利益是其行动的动机与内在驱动,主体为利益内在结构所必要(17)武步云:《人本法学的哲学探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9页。。而利益之主体亦如权利之主体,均应为民事权利能力人,故无论是“英雄烈士”抑或“死者”,既不能为权利之主体,亦不能为利益之主体。盖因如此,在我国司法实践对死者利益提供救济和保护之初,保护主体这一问题就伴随着死者利益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之争被提出来过,最高院的立场也几经变迁(18)王利明:《人格权法》(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0—91页。,《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最终采取了“近亲属利益保护说”,《民法典》第994条延续了该相同立场。《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亦借助于对死者近亲属之人格利益的保护来实现对死者人格利益之救济与保护,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由其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而《民法典》第185条虽然没有对请求权人作出规定,但基于体系解释,应当认为其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的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应当是一致的,即近亲属。由此,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在救济和保护的对象上也实现了同一。
最后,两类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属性均具双重性。“一切法律都必然维护一定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法律首先是一定利益的表现”(19)武步云:《人本法学的哲学探究》,第81页。。同时,“制定法对利益的保护从来不会在真空中,而总是在一个充满着利益的世界进行”(20)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页。,利益亦为动员、组织和联结社会成员的力量,从而展现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外在结构(21)武步云:《人本法学的哲学探究》,第86、89页。。对于英烈人格利益立法所保护的利益属性,我国有学者认为其核心要义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22)迟方旭:《〈民法总则〉第185条的核心要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红旗文稿》2017年第3期。。这种观点虽值肯定,但不能由此否认我国英烈立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崇尚、缅怀和捍卫英烈合法权益,彰显着人们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与朴素的民众情感,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之价值取向,《英雄烈士保护法》第1条亦开宗明义地宣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立法目标,其第25条、第26条和《民法典》第185条在行文中亦含有“社会公共利益”之表达与要求。但是,英烈规范所保护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四大利益范畴属于典型的私法利益,近亲属亦为典型的私法主体,而且《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6条在进行救济程序配置时,更将民事诉讼程序设置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从而体现出民事诉讼救济的首要性和公益诉讼救济的辅助性,也彰显了近亲属私益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双重立法理念之调和(23)康天军:《英烈保护司法实务问题探析》,《法学论坛》2018年第6期。。
对于死者利益保护,理论上通常认为是对自然人现世人格在其死后所给予的特别关照,是自然人人格伦理属性的体现与承载,属于对自然人人身私益保护之死后延伸(24)杨立新、王海英、孙博:《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但是,死者利益保护中亦含有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之价值取向,被保护之死者利益亦含有公共利益之属性,故最高院《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在行文中含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之字样与要求。《民法典》第994条虽然没有延续司法解释这一要求与行文表达,但尊重和保护死者利益亦应是具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由此,“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是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原则的体现,本质上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25)王利明:《人格权法》(第二版),第92页。。当然,死者利益保护的公共性仅是伦理社会生活秩序基本要求之体现,在价值高度上略逊于英烈人格利益之社会属性与公共属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公共性。
综上,英烈与死者不仅具有伦理同质与身份同质,且两类保护规范在内容上高度重叠,将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引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范畴,以其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之请求权规范基础和裁判依据,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规范适用上的极大可能性与操作性。
二、逻辑调适: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
将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引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无疑扩张了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一是直接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为内容的《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二是直接以死者利益保护为内容,却可以援引用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民法典》第994条。不过,该两类保护规范毕竟在立法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以及规范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冲突与内在张力,故将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扩张适用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时,需要在厘清某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逻辑调适。
第一,《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和第26条能否直接作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问题。这一问题源自于我国部分学者对《英雄烈士保护法》的行政法认识与定位(26)李宇航:《民法总则英烈条款与英雄烈士保护法关系浅析》,《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6日第7版。。果如是,则以《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和第26条为近亲属保护英烈人格利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就存在很大障碍。除非将第25条和第26条“作为民法的前提性规定”,进而发生“行政法的连带效果”(27)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12页。,但这里似乎与此无关,故该问题的解决和回答就需要重新审视和厘清《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法律属性。
从表面上看,《英雄烈士保护法》属于行政法规范的认识并非无据。因为无论就《英雄烈士保护法》在立法目的与规范内容上的社会公共性属性(28)《英雄烈士保护法》第1条及其很多规定都彰显出对英烈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还是其调整对象与调整内容指向的行政主体色彩(29)《英雄烈士保护法》第5条、第7条、第8条、第11条、第12条等规定,均涉及和指向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有关部门等行政主体,并为这些机构保护英烈设定监督、保护和管理等职责。,抑或更多地借助公权力运作与行使的调整方法(30)见《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3条、第24条等。,以及法律责任配置中向行政责任的倾斜等(31)见《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等。,都说明《英雄烈士保护法》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行政法规范,但据此将其定性为行政法规范仍有失偏颇。实际上,《英雄烈士保护法》中除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范外,还存在着少量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刑法规范。第25条和第26条即有存在于其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其以英烈人格私益为救济和保护对象,以民事责任方式为主要救济手段,英烈近亲属和侵权行为人亦处于平等法律地位,二者之间属于典型的民事侵权纠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英雄烈士保护法》定性为行政法,只能说其中多属于行政法规范,但亦有民事法律规范。从法源的角度看,《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和第26条有存在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民法渊源。由此,依据《民法典》第11条(32)《民法典》第11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英烈的近亲属完全可以直接以《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和第26条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保护英烈精神及其人格利益。
第二,“英雄”“烈士”的身份类型及其请求权规范基础问题。身份是人相较于其他人被置放的有利的或不利的状态,具有比较性、被动性和区分性(33)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上),《法学》2002年第6期。。“任何身份安排的目的都在于区别对待,都意味着赋予特权或课加受歧视状态”(34)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上)。,以自由、平等为主要价值诉求与价值取向的近现代民法整体上是“去身份”的,并呈现出“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和走向。但是,不仅现实社会中身份无处不在,而且民事立法对人身关系的调整本身也决定不可能完全“去身份”。及至当代,各国立法更是基于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等政策取向,出现了“从契约到身份”,即“入身份”的反向发展。无论是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还是死者利益保护,都是立法相较于自然人权益之一般保护而进行的特殊规定,“英雄”“烈士”与“死者”亦是相较而言的一种“身份”。
如果说“死者”是区别于“自然人”的一种身份,那么“英雄”“烈士”即是相较于一般死者之“特殊死者”,其不仅具有一般“死者”身份之比较性、被动性和区分性,还具有该种身份所独具的公共性和授予性,也即“英雄”“烈士”是基于生前为人民利益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彰显与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为我国政府、军队机关或者社会所授予(35)我国对烈士实行评定制度,故“烈士”源于政府或部队机关授予。对于“英雄”虽然没有评定制度,非政府或部队授予,但却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可以认为源于社会授予。。由此,“英雄”“烈士”身份类型之复合性及其特质,决定了其请求权规范基础的适用差异。
具体而言,在英烈的人格私益受到侵犯时,其近亲属既可以基于“英雄”“烈士”之特殊死者身份,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也可以基于一般“死者”身份,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寻求和实现英烈人格利益之救济与保护。但是,在英烈的人格公益受到侵犯时,因一般“死者”身份不具备“英雄”“烈士”身份之“公共性”与“授予性”特质,故只能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寻求救济与保护,亦即检察机关只能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从而排除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之可能。
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因程序设置而引发的问题,即《民法典》第185条没有公益诉讼的规定,检察机关能否以其作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规范基础问题。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初,即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程序缺失构成第185条之不足,并建议增加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程序的规定进行救济(36)如房绍坤和王杏飞两位教授都认为在侵害英烈人格权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救济和保护英烈人格利益。房绍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不容侵害》,《检察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2017/20170425/20170425_ 003/20170425_003_4.htm,2017年4月25日。王杏飞:《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3日。。应该说,该问题实际上涉及民事实体法规范与民事程序法规范的对接问题。从立法技术的通常设计来看,民事实体法规范意在为民事主体提供行动的依据和合法权益救济的规范基础,却并非一定要载明对民事权益的救济程序,当事人径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一般程序规定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在民事实体法规范中,通常隐含有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是以,即便《民法典》第185条没有关于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亦难谓其不足,且亦不影响英烈近亲属以其为请求权规范基础提起民事诉讼。问题在于,公益诉讼是救济民事合法权益的特殊程序,难以直接隐含于民事实体法规范中,通常需要程序法予以明文规定。但是,鉴于《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与《民法典》第185条之关系,同时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增加了公益诉讼之规定(37)《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出台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故遵循体系解释原则,可以认为《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关于民事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之程序规范是对《民法典》第185条之细化,检察机关可以同时以《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为请求权基础提起公益诉讼,发挥《民法典》第185条责任规范之功效。
第三,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的限定问题。通常而言,基于伦理社会秩序而生成的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意在为自然人死后提供一般性的保护,以此实现民法对“自然人”全面周延之关照,故在规范目的与规范内容上只能以死者之人格私益救济和保护为目标,并配置普通的民事诉讼救济程序。而英烈却属于死者之特殊类型,承载着英烈精神和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这不仅生成出英烈保护规范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之间的异质性,而且引申出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救济英烈人格利益的第一个限定,即其只能作为英烈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的请求权规范基础,而不能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救济英烈人格公益之请求权规范基础。
第二个限定是由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内容本身所带来的保护利益范围的限定。如前所述,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和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在保护的利益范围上高度重合,但前者保护的利益范围广于后者,故此才得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弥补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利益范围之局限。但是,该种弥补仍然是有限定的,即只能扩展限定为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广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的部分,即死者的隐私和遗体等。
英烈的隐私保护问题在《民法总则》通过后即受到学者关注,进而认为可以依照《民法总则》第185条的规定给予保护(38)房绍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不容侵害》。。应当说,侵害英烈的隐私确实可能同时造成其名誉之损害,我国司法实践也曾经一度借助名誉保护寻求隐私利益之保护,但侵犯隐私却未必一定构成名誉侵犯,而且即便同时侵犯名誉,也是侵犯了两种合法利益,以名誉保护替代隐私保护势必造成对英烈隐私利益的消解,加之司法实践的上述做法已经被我国名誉与隐私分别保护之立法、理论及新的实践所废弃,再借助对名誉的扩张解释实现对英烈隐私的寄生式保护将是历史的倒退,不如借助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寻求英烈隐私利益保护更为妥当。
此外,遗体等是蕴含了特定人格利益之物,对近亲属具有重要的精神利益和情感价值,相当部分还体现了伦理与道德的基本要求(39)冷传莉:《论民法中的人格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页。,亦具有保护之意义与现实必要性。以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为请求权基础,扩展及于英烈的遗体等进行保护,亦在死者利益保护规范要义之中。不过,《民法典》第994条在列举死者之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与遗体之后尚有“等”字,由此意味我国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所能够保护的死者利益尚有其他,但该“等”字所能够涵盖的利益是可以扩展及于前述列举的人格利益之外的死者其他人格利益,还是可以扩展及于遗体之外的其他人格物,尚需要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肯定的是,该“等”字所涵盖保护的利益范围亦可以扩展用于对英烈利益保护之强化。
三、裁判路径: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司法裁量
将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扩展作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由此在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之外就生成出另外一种裁判进路,即死者利益保护路径。但是,由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之间,乃至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内部存在着某种冲突与张力,无论选择何种裁判路径,都将面临某些需要考量与调处的问题。
对于裁判路径的选择与确定,既要考虑诉讼本身的性质,也要考虑原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也就是说,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其请求权规范基础的唯一性决定了法院裁判路径的唯一性,即受案法院只能依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进行审理和裁判,别无其他选择。但是,在近亲属提起一般民事诉讼保护英烈人格私益时,其请求权规范基础存在二元选择,则受案法院需要进一步查看其请求权规范基础而确定裁判路径。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在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时,要对达到其法律效果想要的请求权目标规范进行查找和检索(40)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1页。。在有多项请求权规范被纳入考虑范围时,越是特别的请求权,越是较早地被纳入审查和考虑范围(41)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第13页。。故而,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通常会优先被英烈近亲属锁定并加以援引,受案法院亦应依照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进行司法裁判。但是,如果英烈近亲属在检索后发现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因其自身局限而无助于其法律效果实现时,则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将被纳入检索范围,成为其提起诉讼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和法律依据,受案法院也将依死者利益保护路径进行审理和裁判。如此决定着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仍将是我国法院审理和裁判此类案件的主要路径,死者利益保护路径只是辅助适用,但却是现行法框架内强化英烈人格利益保护不可忽视与缺少的路径。
此外,法院依据不同裁判路径进行司法裁判时,还需要注意调适和处理不同的问题。就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而言,需要注意调适和处理因《民法典》第185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关系认识带来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总则编是一般法,英烈保护法是特别法,在涉及英雄烈士人格权案件中应当优先适用(42)李宇航:《民法总则英烈条款与英雄烈士保护法关系浅析》。。果如是,则受案法院在依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裁判此类案件时,《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将成为唯一的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85条遂被架空,其作为民事责任规范的属性与作用也将被忽视。因此,更宜将《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看作对《民法典》第185条之细化,而非特别与一般之关系,并进而根据二者的规范目的、规范内容予以选择和确定裁判依据,尤其需要注意两部法律规范在历史维度设定和保护的主体范围上存在的内置冲突,从而避免发生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死者利益保护路径在适用时,则主要需要注意纠纷定性与案由确定问题。就纠纷定性而言,虽然英烈近亲属可以援引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以寻求和实现英烈人格利益救济与保护之欲求,但此时其所凭借的并非“英雄烈士”及其近亲属之身份,而是一般“死者”及其近亲属身份,故受案法院应当将该类纠纷定性为死者利益保护纠纷。由此也意味着,只有在死者利益保护规范保护的利益范围内,英烈近亲属才可以援引其寻求扩张救济,法院亦才能依死者利益保护路径进行司法裁判。
至于具体案由,因死者利益保护规范在请求权基础检索与援引中的劣后顺位,以及该种裁判路径的辅助与延展作用,更主要是基于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本身之限定,决定此类案件的案由大体应该是侵犯死者隐私纠纷和侵害死者遗体纠纷等。当然,根据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43)为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对2011年2月18日第一次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无论是侵犯英烈人格利益纠纷,还是侵犯死者人格利益纠纷,都没有作为独立的纠纷类型而设立一级案由,侵权责任纠纷项下亦没有为此设置二级案由,故只能在一级案由人格权纠纷项下寻找和确定其案由,并具体根据侵犯的人格利益确定二级案由,如姓名权纠纷、肖像权纠纷等。不过,借助死者利益保护规范扩展英烈人格利益规范保护之局限主要指向英烈的隐私、遗体等利益,仅在侵犯英烈遗体等涉及前述二级案由问题,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如果是侵犯英烈的隐私,则应当则在“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的二级案由项下,以三级案由“隐私权纠纷”来确定具体案由。
当然,无论是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规范基础问题,还是法院裁判路径问题,作为司法适用层面的操作,都只能在法律规范文本内涵之内寻求法律效果目标之实现,无以从根本上弥补和解决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本身存在的局限问题,如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仅以英烈个体为指向,且仅以四大具体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无以对英烈整体之人格利益和英烈一般人格利益提供救济与保护;再如《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为英烈人格利益保护配置了民事诉讼与公益诉讼两种救济程序,并将民事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虽然契合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的双重价值取向与双重立法目标,符合借助私益保护实现公益保护之惯常,亦秉持了公权力不过度介入私权之理念,体现了检察权的谦抑性(44)张丽丽:《论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但第25条第2款以“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为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的事由,没有为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形预留空间。在前述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被告李某、吴某侵害萧山烈士陵园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李某和吴某的行为并未对萧山烈士陵园的任何一个具体英雄烈士构成侵犯,也未侵犯英雄烈士的任何一个具体人格利益,而是侵犯和损害了萧山烈士陵园烈士整体之人格尊严,侵犯中华民族崇尚、尊重英烈的精神与情感,进而揭示出个体利益总和并不等于公共利益问题,其保护亦需要从立法层面才能获得根本解决。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45)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译,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5页。我国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制度彰显着尊重和崇尚英烈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彰显着对英烈牺牲奉献之缅怀与铭记,彰显着对英烈人格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救济与维护。但是,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规范立法目标之实现,不仅需要我们每个个体、我们的社会努力培育、落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司法层面努力调适、消解与弥合既有规则的内置冲突、张力与局限,也需要立法层面不断趋于良善的制度与规则构设,以此最终实现尊重缅怀英烈、爱国向上、复兴强国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