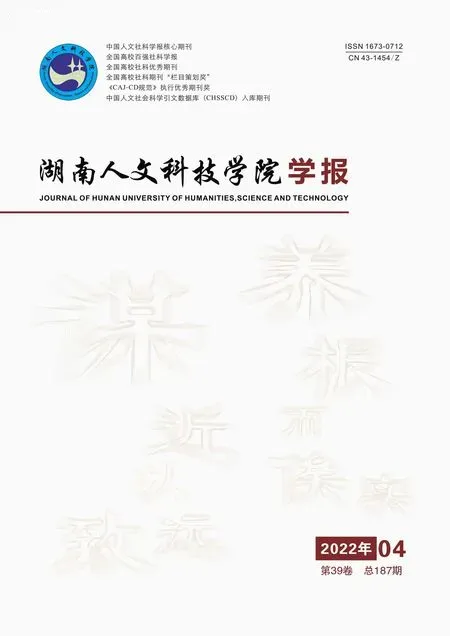论柳宗元对永州地方景观的建构与书写
陈 彤,王湘华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
在唐人心中,荆楚之地向来是一个极为荒僻的所在,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唐人在文化上严守夷夏之辨,故历史典籍在提及荆楚湖湘时常称该地为“南夷”“异域”“荒服”等。受到史书典籍及楚辞文学的影响,柳宗元对湖湘的认知亦有着“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1]215的愁懑之感。潇湘山水胜景,在唐宋文学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都有着异乎寻常的地位。柳宗元并非第一位于诗文中提及“潇水”的文人,但他依据自身的地方经验,建构了潇湘主题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记忆。
元和元年至元和九年,永州零陵治所就是柳宗元的生活空间。当地山川名胜、物候节气是他面对的自然环境;地方的士人百姓、民俗宗祠则是他面对的人文环境。迈克·布朗在讲到文学地理景观的时候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2]40柳宗元以矛盾的心态铸就了愚溪园林居所,并由此开启了对永州音景的聆察。
一、“客有故园思”与“幸此南夷谪”:柳宗元与永州之间矛盾的人地关系
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与湖湘之地永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历经永贞革新事件之后,柳宗元有上十年的时间生活在永州。即使被贬谪至南方蛮瘴之地,他仍写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3]1213的诗句,似乎透露出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意味。若看他写下的《惩咎赋》《梦归赋》等抒情之作,文中吞吐的却是“梦之为归”[3]60的乡思情结及“死蛮夷固吾所兮”[3]56的宿命之感。诗人被贬永州,坐困丑地,孤囚穷絷,却无计可施。说明柳宗元谪永数十年,思想上无比矛盾,对永州的主观态度在积极与消极间游走不定。
永贞之罹难,殃害自身,亦累及家人。初到永州贬所,适逢慈母见背。忆起母亲生前对自己“明者不悼往事”的劝慰,柳宗元深感子无孝道,无以报母恩。在追悼亡母的过程中,柳宗元清晰地叙写了他在永州的艰难处境:“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窜穷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实,苍黄叫呼,遂遘大罚”[3]325。柳宗元与永州本就矛盾的人地关系被进一步激化。至亲辞世,自己又处于缺医少药的贬所。自此,“瘴疠”与柳宗元的贬谪情绪产生深刻关联,成为一种文化地理上的感受和意象,一再出现在诗人笔下:“恐没身炎瘴,卒无以少报于阁下”[3]923。在书信等私密性较强的文体中,柳宗元也向友人详细描述了患病的症状。如《与杨京兆凭书》中说:“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3]790柳宗元诗文中的多处疾病书写,从侧面表现了永州节气日候、地理环境对诗人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与瘴疠有关的书写,也多与诗人忧患、恐惧、慌乱的心理结合在一起。
柳宗元对贬谪的不满常年郁积于心,虽然其前期谪永之作只于只字片语之中,流露出对年华老去、健康不再、无以建尺寸之功的痛苦与焦虑。但饱受煎熬与折磨的心灵,终究要吟咏出其对永州的真实认知,柳宗元的《囚山赋》就是这种生命悲歌: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涌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沍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3]63
柳宗元一贬十年,被永州一地的重峦叠嶂所围困,“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3]801,内心苦闷到了极点。《囚山》一赋,写尽永州山林之荒恶。楚地风物,凡山势、地形、气味、耕食、丛林、兽嚎,无不令诗人为之生厌。永州山川是困锁诗人肉身的牢笼。《柳宗元集》晁太史评论曰:“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也。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3]63这段评论交代了柳宗元对于楚地的矛盾心态与其文学作品生成之间的关系,亦即对永州既喜爱又厌恶、对朝市虽厌倦却盼归的态度。
但贬谪生活也砥砺着柳宗元,让他在不断地藻雪精神,于楚地寻求自我安顿与超脱。柳宗元与永州矛盾的人地关系是他观看永州、体验永州、适应永州的过程。最终,诗人通过不断克服、超越,实现了心理上的突围。而在突围过程中,打造愚溪园林空间与聆察永州山水是两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二、“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空间生产中的自我疗愈与精神超越
柳宗元谪永十年,有过半时间居无定所,四处寄住。柳宗元拒绝在永州买田置业,说明他在心理上未曾真正接纳永州。直到元和五年,柳宗元才接受现实,买下小丘,卜筑并定居于愚溪园林。柳宗元培丘浚池、造堂置亭、栽花莳木,易名“愚溪”,开始因地制宜打造他在永州的活动空间。
在柳宗元的永州书写中,园记与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有所不同。“园记”,顾名思义,是记述“园”的建造经过、包括构园法则、取名用心和景观之美的文学品种。祁志祥《柳宗元园记创作刍议》一文将柳宗元园记与山水游记区分开来,他提出:“‘园主’‘文人’‘园林欣赏者’三位一体,所以园记多诞生于文人园主之手。以此来定义归类柳宗元的永州园记作品,有《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愚溪诗序》。”[4]38“愚溪”原名“冉溪”,柳宗元首次为其更名:“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3]642诗人为其更名,是由于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但楚地山水和诗人本身并非真的“无以利世”,而是为世所弃,无法利世。
人类依托自然地理而生。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则以命名的方式选择性地推重自然。在物我相待的人地关系中,天地自然凭借“杰特有文之士”的命名,方可名扬天下。正如马中锡《书兴隆八景诗卷后》所说:“天下之胜地,待人而名,亦必其人之言语文章足以信今传后,而斯取重东林,非惠远其人,则庐山一丛薄耳。永之山水非柳子厚,荒服外之丘垤行潦耳。”[5]597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多为“唐氏之弃地”,得不到人们的发现与命名,则等同于“弃物”。永州山水,本是籍籍无名,却因柳宗元书写永州而得以建构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打造愚溪居所,并为其定名的过程中,柳宗元也获得了一种同感共应的肯定。柳宗元通过为潇湘山水景观命名而在贬所中留下印迹。如此一来,他不仅在自然山水中得到了精神满足,也在命名活动中凸显了自我,增强了对地方的认同感。正是这种人地相待的关系,使得柳宗元与永州的关系初步由尖锐对立转化为相互依存。再看《钴鉧潭西小丘记》: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3]765
“余怜而售之”中的“怜”,乃是“同病相怜”的“怜”,是“弃逐之人”与“弃地”的心灵共鸣,亦是作者的身世投影。作者买下小丘这一“人弃我取”的做法,说明他重拾起对人生的信心。柳宗元不仅“取”,且在取得弃地之后,刮垢磨光,积极改造,使得“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些积极改造的举动,表明柳宗元对永州的态度发生了极大改变。
此外,在栽花莳木的过程中,柳宗元还以花木书写彰显自我品性,进行自我疗愈。这同样带来了人地关系的缓和。贬谪永州期间,栽培花木事宜多次成为柳宗元的诗咏主题。“离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3]1231。“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3]1232“贞根期永固,贻尔寒泉滋。”[3]1224当诗人与楚地芳草遭际相似时,他与所植之物间的相互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诗人孤芳自赏的情绪,使二者之间达到了精神的沟通与互动状态。除却常铸文人笔下魂的丹桂芙蓉,柳宗元笔下摇曳生姿处亦有仙灵毗、白蘘荷等缓解疠病的草本良药。
种植诸作,俱兼比兴。柳宗元将自我情性熔铸于园林景观之中,通过建构山石、泉池、花木、建筑等客观景物来书写迁谪之思。由此,愚溪园林成为制造永州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永州园记书写展现了柳宗元身处个人专属空间时心神的游冶和精神的安置。卜居于愚溪园林,并在其中与友人交游往来,极大地缓释了柳宗元的苦闷心理,也逐步建立起了柳宗元对永州地方的归属感。
三、“回风萧瑟参差影,山水清音慰惊魂”:自然审美中的音景聆察
正如柳宗元对贬谪之地其它事物的拒斥心理一般,最初他对永州的山水也是不予接纳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出游一事的态度之上:“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3]801“游复多恐”传达了诗人内心对于游览楚地的真实顾虑。
永州山水景致是柳宗元根据自己的感官经验在文学作品中建构的审美空间。观看风景意味着空间经由视觉而呈现。若对既往山水诗文创作中的观照方式作一番回顾总结,便不难发现,音景的缺位乃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中的听,并非只与耳朵有关,更多时候是诉诸所有感觉器官去体察世界。如《庄子·人间世》借仲尼之言,告诫人们不能局限于“听之以耳”,而应追求“听之以气”与“听之以心”,如此方能达到“心斋”“坐忘”“虚静”的审美境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既有视觉意象,又有触觉感受,还有声音叙述。柳宗元在描绘永州山水过程中,多次运用到声音意象。并且最终进入了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3]766的澄明之境。
相较前代山水文学,柳宗元的山水书写具有综合性的审美经验。柳宗元以全新的方式来感知体验永州的山水人文之声。柳宗元对永州地方的认同与融入,亦体现在听觉空间的形塑之上。以谢灵运为代表的魏晋山水诗,集中描写吴越地区的山水。通常以“清涟”“涟漪”“微波”等视觉印象来描绘水景,如“绿筱媚清涟”“涟漪繁波漾”等诗句。这些水景描写着力呈现视觉感受,更强调水的清澈、柔媚,给读者以清秀、俊美之感。而以荆楚风物为代表的潇湘山水诗,则是南迁文人所传达的关于自身客居他乡的陌生化审美体验。湘水在零陵县与源出宁远县九嶷山的潇水汇聚后流入洞庭湖。米芾《潇湘八景图诗总序》云:
潇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经,至湘阴始与沅之水会,又至洞庭与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潇湘名水。[6]676
曾经有学者指出:“风景是一种文化想像,一种表述、建构或象征环境的图绘方式,风景被书写、被描绘都是经由选择,形成带有主观视角的文化符码,暗藏着值得探索的形式与意义。”[7]通过柳宗元的音景书写,可以略见吴越山水与潇湘山水的相异之处。柳宗元的永州书写主要展示了“泉”“潭’“溪”“涧”“渠”等水意象。除了视觉感知外,柳宗元着力描摹了这些“水”意象的音景:或“于高者坠之潭,有声潨然”[3]764;或清脆响亮,“如鸣珮环”[3]767;或“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使得“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3]767;或“流若织文,响若操琴”[3]770;或“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3]773。这些声音景观的描写,明显表现出吴越山水与潇湘山水不同的审美特质。以永州“水”意象群为代表的潇湘水景,呈现出浩荡、淼漫、奔腾之美,给人以粗犷、豪放之感。
柳子厚诗文中形形色色的声音意象,与视觉描写共同交织出他对永州的主观感受。柳宗元在书写永州过程中对声音的敏锐捕捉,体现了他在心灵上对贬所的拥抱与体察。
四、结语
柳宗元是潇湘文学的创作者,也是潇湘文化空间的建构者。作为有志难伸的迁谪之客,柳宗元在潇湘的山间水湄中寄予了客旅之愁和望归之情。在潇湘山水满足了柳宗元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后,他选择了接纳和拥抱永州,并将自己安顿于此,最终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救赎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