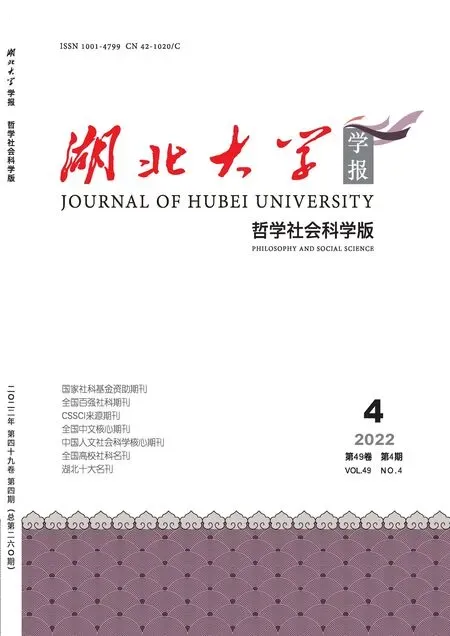人工智能: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又一条探索之路?
舒红跃, 陈 翔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海德格尔早期从此在这一他认为在存在论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存在者来追问存在,后期则认为存在之思在存在者中找不到先验的根据,可以通过“诗”来直“思”存在。海德格尔早期和后期有一个共同点:排除从非人类存在者追问存在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生活的年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后人类生命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想象的,故而海德格尔排除的是从前人类的动物来探究非人类存在者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写作《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与孤独》一书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在今天,作为一种新型生命的后人类存在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的出现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此,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深入和人类身体奥秘(特别是人类大脑的组成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日益披露,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一步一步地由“专用”到“通用”、从“弱”到“强”不断演变),我们面临一个在当代科学技术的“逼迫”之下来深化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研究的契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后人类存在者在理论和逻辑上如果可能,它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存在论研究路径,即从不同存在者(不同生命)的延续和共在中来探究海德格尔“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这一存在论命题?
一、海德格尔:从存在者出发追问存在到直面存在
存在论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但存在因各种原因让我们无法直接面对,所以只能通过存在者来追问存在,缘由是“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世间存在者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就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的存在者(此在),因此存在论研究需要一种基础存在论准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人类向来所是这一存在者极为青睐,因为此在不仅在存在者层次上与众不同,而且在其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关联:“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页。海德格尔对此在的优先性做了三个方面的说明: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其存在中通过生存得到规定,其他存在者并非如此;第二层是生存论层次上的优先地位,此在以生存为其规定性,它本身就是“存在论的”,它不仅领会着自身生存,而且同样原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存在者存在的领会;第三层上的优先地位在于此在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和存在论层次上得以可能的条件。
要想证明此在的独特性,海德格尔必须证明所有非此在存在者仅在存在者层次上存在,而非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在《存在与时间》创作的那个年代,具备类似人类思维能力的机器还未出现,此时在存在上最接近此在的是动物,但该书甚少涉及动物的存在,偶尔提之也是为了在对比中突出此在存在之独特性。海德格尔详细探讨动物问题的著作是《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与孤独》,该书在动物与其他存在者关系上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动物能否把某物理解为某物,把某物理解为一种存在者的问题。如果动物做不到,那么它就被一条无底之渊跟人分隔开来”(2)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World,Finitude,Solitude,William McNeil, Nicolas Walker,tran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264.。海德格尔排除了从动物等前此在存在者研究存在者存在的可能性。
唯有此在这种存在者,我们才能由之出发研究存在问题。这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受到不少批评与指责,有人认为他为了突出人而贬低其他存在者,仅从人类出发研究存在的路径是有问题的。鉴于各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以此在为优先方向来追问存在,而是从存在自身出发研究存在,他的前后期哲学有一个“转向”的问题(3)海德格尔前后期哲学之间有无“转向”,这是一个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公案”。一方面,只有从前期海德格尔所思出发才能通达后期海德格尔的思考,前期海德格尔也唯有被包括在后期海德格尔中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前后期海德格尔在研究的对象、路径和方法上均存在重大改变。。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都纠结于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转向前,存在是从存在者(此在)的角度通达的,转向后,存在者是从存在的视角得以理解的;转向前,海德格尔研究的重点是存在者的存在,转向后,海德格尔研究的重点是存在本身。“就研究的侧重点上说,前期放在亲在的存在上,后期则放在存在本身;就研究的方法而言,前期侧重于亲在在世生存的‘现象学还原’,后期则侧重于存在本身的‘解释学释义’”(4)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转向之后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存在者(此在)为视角找不到存在的先验依据,他不再在存在者(此在)中寻找存在的先验依据,他的目光转向了存在本身和存在的历史。“存在史”在海德格尔后期文本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有着“深不可测”的一面,这一面先于任何存在论奠基,而且本身不能被奠基,也无须奠基。转向之后的海德格尔放弃的不仅是存在者层次上的科学探究,而且包括存在论层次的探究,此时他认为存在论探究还是与存在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存在的存在论追问”和“存在的追问”作了严格区分。后期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不会为追问存在提供出发点,“存在之思想在存在者中找不到任何依据”(5)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3页。。后期海德格尔不再从此在追问存在,而是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及其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倾听诗人的细语、沉思简朴的生活及其日常的奇迹,试图铺设一条直达存在的道路。这一转向引起了不少哲学家的关注,如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一书有过这样的描述:“海德格尔在其晚年哲学中放弃了与人的存在的关涉,企图去表现不涉及我们存在的那些存在的涌现形式。”(6)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5页。
海德格尔早期从存在者出发追问存在,后期开启了一条从存在本身追问存在之路(7)海德格尔直面存在的主要途径是诗:“诗,是存在的神思”,“诗通过词语的含义神思存在”(王庆节:《海德格尔:走向澄明之境》,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279页)。后期海德格尔试图跳过存在者,通过“诗”直“思”存在,然后再说明存在为何势必走向存在者,走向存在的“晦蔽”。海德格尔通过“诗”所“思”的存在并非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本身。。一方面,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多次说明存在与存在者可以作出区分,但这种区分不能被视作是一种割裂。“存在之真理包含着这样一回事,即:没有存在者,存在决不现身成其本质,而没有存在,也决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8)海德格尔:《路标》,第357页。。存在不是存在者旁边或之后的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另一方面,虽然海德格尔多次强调不可割裂存在与存在者,但他又多次表达相反的论述:没有存在决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但没有存在者,存在是能现身成其本质的。事实上,在追踪存在者存在的路径上,《存在与时间》已展示了一个教训:从存在者,哪怕是此在这一“最优(高)”存在者入手,仍然很难成功地追问存在。于是海德格尔夸大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距离,以便为放弃存在者而优待存在进行辩护。“牺牲乃是在通向对存在之恩宠的维护的进程中对存在者的告别(Abschied)”(9)海德格尔:《路标》,第362页。。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者的舍弃是必然的,因为存在者在现代性中已完全被抛弃,现代社会的存在之思已经在存在者中找不到决定性的依据。对存在者的舍弃关系到的不是某一存在者(如此在),而是存在者的整体。
海德格尔之所以想放弃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者,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生命哲学还是(哲学)人类学,它们对人的研究同实证科学藕断丝连,无法做到纯粹的存在之思。对于生命哲学来说,此在只是诸多生命(存在者)之一;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把此在看作一种生命只会把对存在的追问变成人类学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拒绝对此在这一存在者作人类学研究。“这种存在论差异观念——在此观念中,存在者与存在不仅在认识论上被区分,而且在存在论上被割裂——让海德格尔备受责难,因为他回避了具体的生存而偏向于支持神秘主义”(10)约斯·德·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吕和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339页。。事实上,存在之思不能与科学研究、哲学(人类学)研究割裂开来。在《存在与时间》中已显示出这一倾向,那就是将存在问题与存在者的科学研究割裂,赋予前者以优先性。
不同于海德格尔,很多哲学家认为哲学奠基与实证科学有关联。“哲学以双重方式与非哲学相关。它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现存领域,以便从中抽取出转为己有的潜能;此外,它还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生成领域,以便令其自身的潜能向那里流通,从而以相互包容的方式产生新效应”(11)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页。。无论是历史学、人类学还是(哲学)生物学,它们不仅有其“现存领域”,而且有其“生成领域”,存在论研究既需要利用经验性研究的“现存领域”,也需要利用它们的“生成领域”。只有与经验科学合作,存在论才能从中汲取新的潜能,并令自身潜能流向不同的实证领域,从而以互补、互利、互赢的方式产生新效应。在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这一重要的存在论问题上,我们不能割裂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而直面存在,我们的生存经验依赖于我们对外界实证经验的接受性。只有通过对存在者的经验这一路径,我们才有资格获得必然有限的存在经验。如果像海德格尔,既排除在经验层面上从非此在存在者来研究存在(早期),也拒绝在经验层面上从此在这一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后期),那么只能拒斥对所有存在者的研究而走向存在本身,走向容易让人指责的“神秘之思”。
虽然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有着割裂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联的倾向,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被完全割裂的。海德格尔倾向于不仅要净化科学研究中的存在问题,而且要净化哲学分析中的存在问题,但这种倾向是很难成功的,严格说,它并没有被海德格尔本人切实地付诸实践。存在(世界)深不可测,每一种理论体系都只是借助于某一(些)存在者对存在的理解,因而只能解释存在的某一个(些)侧面。“海德格尔不断激烈批判存在—神—逻辑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具有的末世论,在他似乎赋予存在以自主地位的地方,他是否仍然陷在那种末世论中呢?”(12)约斯·德·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第349页。与这些总体主义的末世论不同,我们可以面对生命的绵延,面对一个个前后延异、生生不息的生命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生命演化的无限多样性。如果不能一次性地从某一个存在者来通达存在——这是《存在与时间》试图完成但没有完成的任务,那么,能不能由此就排除从存在者入手来通达存在的路径?能不能从由人类和非人类存在者所组成的“绵延”(柏格森)的存在者链条,从不同存在者的“延异”(德里达),从一个个有代表性的“高原”(德勒兹)来通达存在?虽然哲学从某一个存在者通达存在的任务完成得并不理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排斥从存在者入手探究存在,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思”与“诗”。对于有限地存在着的人类,存在的真理无法被我们一次性完成,甚至存在的真理也不可能被人类这一种存在者穷尽。穷尽存在的真理是人类这一种生命无法承受的重任。
“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可以有别于海德格尔,不是从某一个在存在论、存在者层次上具有优先性的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而是通过一个存在者的共在系列来研究存在,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绵延、延异、差异与重复。在存在者的共在系列中没有一个在存在论、存在者层次上具有优先性的中心,共在的存在者系列也不存在一个绵延、延异的终点,存在者共在系列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这个绵延系列中一个过渡性的点,任何一个共在系列中的点都不可能是这个共在系列的终点。在海德格尔生活的时代,后人类存在者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今天,随着人工智能从“弱”(技术)向“强”(生命)的演变,我们要从基础存在论转向绵延、延异、差异与重复的存在论,从不同存在者的共在序列中研究存在。这应是人工智能时代推进海德格尔存在论研究的一条可能性路径。
二、能否从非人类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者的存在
从逻辑上讲,从存在者角度通达存在有三条路径:一是从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来追问存在。这条路径最完美,前提条件是追问者具备无限的理性、无穷的时间。很显然,人类并不具备这一条件,故而我们做不到从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来研究存在。二是从某一存在者的存在来研究存在,前提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在存在者、存在论诸方面有着优先性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早期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存在者,那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这一论述隐藏着一个前提:人是所有存在者中“最优”,即“最高”和“最后”的存在者。所谓最高,是指唯有人具有操劳在世的存在能力,所有非人类的存在者均不具备这一能力,在人与非人类存在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把它们隔离开来。所谓最后,是说人是生命演化的终极阶段,作为本体论的“操心”、“世界”等现象到人这里戛然而止。世界上不存在后人类存在者,也没有后“操心”的操心、后“世界的”的世界存在。三是从某些有代表性的存在者的存在来研究存在。存在者是一条由人和所有非人类存在者组成的永无止境的“绵延”之流,是一条由一个个有代表性的“高原”组成的演化之链,其中不存在所谓最优、最高和最后的存在者。所有存在者,它们最终要么灭绝,要么汇入其他存在者之中,人亦如此。“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要用一生的生命加以描述,要设法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13)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43页。。
存在者是一条无止境的绵延之流。如果不同的生命代表着一个个“高原”,那么,存在者就是一个个“高原”组成的演化之链。柏拉图认为唯有人才有灵魂,其他生命体是没有灵魂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植物和动物都有灵魂,生命以多种方式显现。生命通过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来实现自身。有多少种生命(形式),就有多少种生命在世界中显现的方式,就有多少种研究存在者存在的路径。人类不过是生命演化史中的一环,我们既可以从人这一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者的存在,也可以从前人类和后人类这些非人类的存在者入手来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生命哲学在这一点上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柏格森哲学是创造进化论,他尝试追踪整个生命的进化。虽然生命进化的历史尚未完成,但我们已经隐约看到智力是如何通过一个不间断的进程,沿着从脊椎动物到人类的上升路线来形成自身的。生命进化史向我们展示,理解能力只是行动能力的附属物,在理解能力中有一种生物的意识对为其所设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准确、复杂和灵活的适应。“我们的智力,就其狭义而言,是用来确保我们的身体完美地适应其环境,表象出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简言之,是被用来思考物质的”(14)Henri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Arthur Mitchell,tran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44,p.xix.。智能是被用来确保我们的身体完美地适应其所处环境的,这一论断适用于所有生命,也就是动物、人类乃至后人类生命。
问题在于在生命演化史上后人类生命是否可能?现有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只不过是人类用于自身生存的技术手段。目前的弱人工智能最终是否会演化成类人类、后人类存在者,在弱人工智能的行为和生命体的行为之间有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机械化智能就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在创造最终真正能思维的机器时,每跨越一个旧的障碍都要产生一个新的甚至更多的障碍。迄今为止,很多人认为在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谁也不知道非智能行为和智能行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事实上,认为存在明显界限也许是愚蠢的”(15)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郭维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4页。。智能的基本能力包括对于环境的灵活反应、充分利用机遇、弄懂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的信息、区分环境中重要和次要的因素、提出新观念等等,这些能力有的是形式化能力,有的是非形式化能力,似乎相互矛盾,但人工智能研究必须直面并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存在于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生命和非生命的事物之间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说,正是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我们能描述从物质到意识、从非生命到生命、从形式系统到非形式系统的绵延之路的具体路径。
从物质到意识的跳跃,对于人脑而言就是从低层次神经元的构造到高层次意识的涌现。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神经元网络,该网络在局部层次上(神经元)表现得与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没有区别,但它完全没有产生出高层次的具备意向性特征的意识。低层次由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组成,这一事实不一定能导出高层次的意向性。“高层意义是神经元网络的一种带有随意性的特征——一种作为(进化中)环境压力的后效而出现的东西”(16)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第751-752页。。在生命进化史上,人类大脑低层次的神经元最终的确导致了高层次意向性的出现,但意向性的出现不是必然的,它是拥有身体、在世界中生存的人类必须克服环境压力而逐渐进化出的东西。现有人工智能的网络构造是与神经元对应的低层次的物质,这一层面是否也会出现从物质到意识的“跳跃”?人类在世界中存在靠的不是神经元,而是神经元、大脑都是其一部分的身体,人类是凭借肉身在世存在的。像人类一样,人工智能也有其周围环境,它是凭借其硬件在环境中存在的,人工智能出现意向性也必须是其硬件随环境改变而演化的结果。
如果说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什么鸿沟,那就是人类是凭借身体在世界中生存的,人工智能是通过硬件在环境中运行的。人类在世生存主要依靠的不是具有明确规则的理性知识,而是由身体操作的不可言传的半本能性知识。德里福斯(Hubert Dreyfus)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研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身体在智能行为中的作用、不依赖于规则的人类行为的有序性、人类需求函数与情境的关系,其中核心是智能的知觉身体性。人类的心智出自身体知觉而非纯理性计算,身体知觉处于特定情境中,这样一种心智—身体—世界的交织蕴含整体,又是置身于人类历史文化和自然世界之中的。故而,如果要想从非人类存在者研究存在,关键就在于关注的重点应从人类的大脑转向身体。“为了理解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智能体如何工作,我们不得不考虑整个智能体,而不是只考虑智能体的程序……单独思考大脑是毫无意义的:认知发生在身体之中,而身体又处于环境之中”(17)Stuart Russell,Peter Norvig,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Modern Approach(3 edition),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c.,2009,p.1026.。
我们意识到的空间和时间都是连续的,把空间和时间划分为事物和过程是由于理智的缘故,理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生物学上的需要。我们之所以感知事物,是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需要这样做。比如记忆,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起精选作用的筛子,没有身体,我们的心灵就会事无巨细地样样记得,这在生物学上不但无用,而且是一种灾难。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免于这种危险,并使我们只筛选那些在生物学上有用的东西。对于强人工智能来说,它之所以强,不仅是因为它有更好的软件—程序,而且必须具备更好的硬件—身体。作为后人类的人工智能,它不仅在软件—程序上是后人类的,同时在硬件—身体上是后人类的。
智能依赖于身体或物质硬件,这是当今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协会(AAAI)创建者布鲁克斯(Rodney A. Brooks)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智能系统的具身性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只有一个具备身体的智能体,才能充分满足智能体应对真实世界的条件。其次,只有凭借物理的基础,任何内在的符号系统或其他系统才能得以运行,并给予系统内部运转的进程以‘意义’。”(18)Rodney A. Brooks,Cambrain intelligence: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w AI,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9,p.167.一个仅仅具有表征和计算能力的符号系统并非真正的智能体,真正的智能体必须能够实现在真实物理世界中的运行。而要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运行,智能体必须在这一世界中具备自己的身体—硬件,必须以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实体为根基。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产生智能,不仅是因为人类拥有引以为傲的意识,更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在真实物理世界中存在的物质实体。虽然人类有机体的功能和作用比其他有机体更复杂,但他与其他事物仍属同一个层次。“除了其内在的模式极其复杂和稳定之外,完整的身体事件(bodily event)与一切其他事件处于同一个层次”(19)Alfred North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Lowell Lectures,1925),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48,p.75.。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经验是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主体的经验,但复杂经验如意识却非每个现实实有具有的主体形式,经验只有达到一定强度之后才会涌现意识。从经验到意识,是一个现实实有的物理复杂性增加的过程。只有现实实有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意识才会涌现。人工智能创始人纽厄尔(Allen Newell)和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过类似观点:“任何足够大的物理符号系统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组织而表现出一般智能。”(20)玛格丽特·A·博登:《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
2012年7月7日,当代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权威专家签署了《剑桥意识宣言》:“来自各方面的证据显示,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基质,以及表现出有意识行为的能力。因此,充分的证据显示,在拥有产生意识的神经基质方面,人类并非唯一的。”(21)“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https://fcmconference.org/img/CambridgeDeclarationOnConsciousness.pdf,2022-01-30.产生意识的神经基质不是人类独享的,人类之前的动物具备这种基质,人类之后的人工智能也将具备这种基质。动物、人类和后人类存在者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存在论差异。“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在动物和人之间,我们将只看到程度的差异”(22)吉尔·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张宇凌、关群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在动物和人之间只有差异甚至是门槛,生命演化一旦突破某个门槛,人类就会出现。人类和后人类生命之间也只有差异和门槛,人类在其演化中一旦突破某个门槛,后人类存在者就会出现。今日人类正面临这一门槛。随着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不断逼近,人类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类人和后人类存在者的出现不再是梦中花、水中月。从由人类和非人类存在者组成的存在者之链来研究存在,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迫切性越来越强的现实问题。
三、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与新的存在论研究路径
人类既非演化的起点,也非演化的终点,但把人看作最终(高)存在者的说法在历史上却是主流。究其缘由,因为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后人类存在者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认为此在在所有存在者中具有存在者和存在论上的优先性,柏格森创造进化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人类是进化的目的。“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人类是进化的‘终点’和‘目的’”(23)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20页。。不同的是,柏格森给后人类存在者的出现留下了一面窗口。今日,正是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探究后人类存在者的希望和可能。
迄今为止,已有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的技术手段。作为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演变到作为生命的人工智能需要多长时间,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虽然现在人工智能不是真正的生命,但它开启了一条通往后人类生命之路。人工智能研究很长时间内认为机器不可能具备智能,因为人类智能的很多特征是机器不具备的。比如人能从经验中学习,但机器不能。深度学习算法让机器具备自身的构造功能,这是人类意义上的学习。“它在训练中得到的不再只是规则、对象信息,而且还能获得对象出现的可能条件。换言之,它已经能够开始‘感受’和捕捉可能性,而不只是现成之物了”(24)张祥龙:《人工智能与广义心学:深度学习和本心的时间含义刍议》,《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海德格尔认为人之本质不在于现实性而在于可能性,深度学习让人工智能从一种现成存在变成了可能性存在。在很多人眼中,深度学习被看作是真正智能的一个特征。但是,即使具备深度学习能力,人工智能是否就成了真正的智能?在那些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存在鸿沟的人看来,尽管人工智能能够做人能做的一些事情,但与人相比,计算机仍然存在某些缺陷:就算你真的能让一台机器完成你提到的所有那些事情,但是你绝不可能让一台机器做到X。X曾经是学习、情感,现在主要是心智。
理解智能生命最困难的问题应是如何理解心智、自我。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提出了一个在认知科学中很知名的观点:意识的核心是“怪圈”。他认为,对于我们大脑中出现的现象,如希望、意识、自由意志的解释实际上都基于一种怪圈,一种层次的相互作用,其中顶层下到底层并对之产生影响,同时自身又被底层确定。如果简化对心智的解释,必须引进层次、映射、意义等软概念。“正是一种类似的层次交叉造成了我们几乎不可分析的自我意识”(25)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第938页。。必须承认,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一个层次上发生的事件能“导致”其他层次上的事件发生。比如事件A“导致”事件B,只因事件B(心智)是事件A(神经元)在其他描述层次上的翻译。这是对心智与神经元关系的又一种解释。
神经科学家斯珀里(Roger W. Sperry)设想了一种新的大脑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人脑内是一个由不同动力组成的世界。沿着大脑“命令链”向上攀登,我们会在顶端发现那些全面组织起来的动力和大规模的脑兴奋模式,它们和心理状态或精神活动相关联。在大脑这一命令系统离顶点不远的地方可以找到思想。人比黑猩猩“高级”,因为人有思想、观念。在这一模型之中,一个个想法的潜在动力变得像一个个分子、细胞或神经脉冲所具有的动力那样真实。“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与同一个大脑或相近大脑,以及不同的、外脑中的各种心理力量相互作用……它们还和现实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在这个星球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26)Roger W. Sperry,“Mind,Brain,and Humanist Value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22,No.7,1966.。斯珀里的大脑模型告诉我们,思想的运作以大脑神经脉冲的流动为基础,智能的运作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思想可以进化,但这一进化以神经元为媒介,只有借助于神经元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
当今认知科学的一种主流观点是,人脑中较高层次的智能是从较低层次的神经元中涌现出来的。实际上,“涌现”这一现象是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一基础性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大脑和心智,一个是神经元纠缠,一个是符号纠缠,前者是后者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符号与符号纠缠在一起,它们是思维在其中流来流去的层次结构,这是心智层面。在心智层下面是由无数神经元组成使得上面的纠缠得以产生的、不受干扰的基质。对于心智的运行,由符号构成的软件纠缠被由神经元构成的硬件纠缠支持着。“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给自己编程序。的确,我们无法产生别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被屏蔽于底层——也就是神经原(神经元)缠结——之外了。我们的思维好像是在自己的空间中运行,创造新思想,而且我们从未注意到任何神经原(神经元)会给我们帮助!”(27)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第914页。在硬件纠缠和软件纠缠的关系中,物理定律具有最终决定权,虽然高层的心智—符号纠缠不能完全还原为底层的物质—神经元纠缠,但所有高层级的非物理对象都随附于低层级的物理对象。
今日的计算机之所以不是智能生命,最主要原因是它在物质硬件和程序软件层次上远未达到人类智能的层级。当前公认的人工智能“分层”图景是晶体管—触发器—寄存器、数据通路—机器指令—编译程序—Lisp-嵌入的模式匹配器—智能程序。虽然现有人工智能有分层,但通过几层就达到智能程序是不可能的。“在机器语言层和真正达到智能的层次之间,我认为可能还需有十几层(甚至几十层)。每一个新的层次都基于下面一层,同时也扩展了下一层提供的灵活性”(28)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第389页。。尽管与人类大脑相比,目前的人工神经网络结构简单、层级太少,无法产生智能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因目前的机器不具备产生人类智能的能力,就断定机器永远不会产生人类智能。智能生命能否产生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哲学层面(逻辑上有无可能),一个是技术层面(现有技术下能否产生)。
很多学者之所以认为机器不可能产生智能,除了他们在现有层级的人工智能中看不到人类智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机器不具备自己的意向和意愿,“机器所表现出的所谓人工智能由于缺失了意向性和意识,因此算不上真正的智能”(29)高新民、罗岩超:《“图灵测试”与人工智能元问题探微》,《江汉论坛》2021年第1期。。“机器学习之父”塞缪尔(A. L. Samuel)认为,机器永远不会生成事先没有放进去的东西,机器表现出的“意向”是程序员的意向,或依照程序员指定的规则从这些意向中导出的子意向。虽然可以假设不仅能修改子意向,而且也能修改导出规则的机器,甚至是会设计其他具有更强能力的机器,但是,“在得到如何去做这些事情的指令之前,机器不会也不可能去做。这里有一条逻辑上永远存在的鸿沟,一边是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人类的极力的扩展和精心的构造,一边是在机器中开发的过程中属于机器自己的意愿”(30)A. L. Samuel,“Some Moral and Technical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A Refutation”,Science,Vol.132,1960.。与此相反,侯世达认为机器和人一样可避开这种指责,因为机器和人都由硬件构成,而硬件则按照物理学定律独立运行。这里不需要“允许你使用规则的规则”,因为最底层的物质层面的规则是嵌入硬件中的,它们的运行无需经过许可,只需按照物理学规律运行即可。
“丘奇-图灵论题”是支持最终会产生后人类智能的主要理论之一。该论题的微观形式是,生物体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都能用计算机模拟,这包括任何一个细胞行为都能用一个Floop程序(一般递归函数)——在给定元素的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的一个足够精确的描述之后——计算到任意精确的程度。尽管大脑的思维过程拥有更多组织层次,但它并不比胃的消化过程更神秘。为了解释大脑中的思维过程,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解释:一是解释低层次的神经发射通讯如何导致高层次的符号激活通讯;二是自足地解释高层次的符号激活通讯,建立一个不涉及低层神经事件的理论。“如果后者是可能的——这是目前进行的所有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中的一个关键假设——那么智能就可能实现于不同于大脑的其它硬件上。那将表明智能是一种可以从它所在的硬件中‘抽取’出来的性质——换句话说,智能将是一种软件性质”(31)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第467页。。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智能是较高层次才会出现的现象,而大脑—神经元是较低的无意识的物质层面的现象,但较高层次的智能的产生依赖于较低层次的大脑神经元的运转。随着较低物质层面大脑的演化,较高层次的智能会从较低层次的物质硬件中涌现。第二,虽然高层次的智能依赖于低层次的物质,但这一物质并非某种特定类型的物质,智能依赖于物质并不等同于依赖于大脑。高层次上出现的智能是随着低层次的物质—硬件演变跨过某一临界点(门槛)之后涌现的,智能的出现并不依赖于特定的生物结构,因此,人工智能作为后人类存在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如果人工智能作为后人类存在者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不仅需从动物、人类这样的存在者研究存在,而且也要从人工智能这一后人类存在者研究存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某一个存在者,而是从某些存在者的存在来追问存在,我们就既要研究这些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更要研究这些不同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存在论研究最困难的任务不是研究动物、此在、人工智能这一个个存在者的存在,而是研究这些不同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有一个共同的地基,那就是所有存在者——前人类、人类和后人类——都从属于一个绵延着的生命共同体。从共时性看,任何一种生命都是同一个绵延着的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它与这一生命共同体的其他生命一同存在,每一种生命都是在与共同体其他生命的共在中获得其存在意义的。从历时性看,任何一种生命都只有在同一个融贯性生命共同体的绵延中才能获得其存在意义。现有生命,既是过去生命在今日的延续,同时又是未来生命的铺垫和准备。“生命的过去的和当下的意义都有可能仅仅在于:它们构成未来生命意义的一个阶梯,或者说,一个前阶段。与这个‘未来生命的意义’相比,以往动物的生命和当下人类的生命的意义是初级的、偶然的、有限的,因为它们很可能会随未来生命的开启而终结”(32)倪梁康:《人类意识与人工意识——哲学还能说些什么?》,《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在漫长生命演化史上,人类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只不过是其中又一个环节、又一座高原而已。与其他存在者—生命体相比,人类并不具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的在存在者、存在论诸层次上的绝对优先性,也非追问存在者存在的唯一路径。“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对于人类这一生命而言,就是存在总是人类的存在。研究这一命题,不仅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追求,也不仅是某一时代人类的追求,而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只要作为一个物种不灭绝,人类就会前赴后继地、一代接一代不停地研究这一命题。“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对于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存在者来说,它们既包括已经存在的前人类的动物,也包括可能存在的后人类生命。对于海德格尔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除非是在科幻小说之中,否则,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后人类生命都是不可能的。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生命的人工智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们不仅要从此在来探讨存在者的存在,还要从此在之前的动物、此在之后的后人类存在者的存在,以及这些不同存在者存在的关系来追问存在。我们的目的,既在于通过一个融贯的生命共同体来研究存在,也在于确定人与其他存在者,尤其是后人类存在者的关系。如果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后人类生命是可能的,那么,能否找到,特别是如何找到人类与其共生共存(而非你死我活)的方法和策略,这将是人类在未来所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