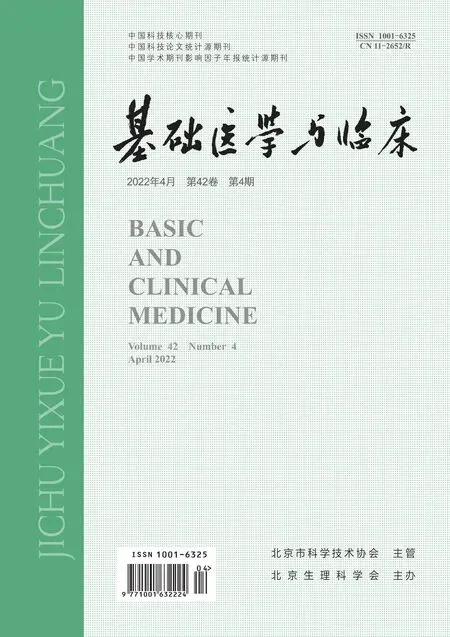细胞外囊泡在心房颤动发病中的作用
何 丹,阮中宝
(泰州市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江苏 泰州 225300)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简称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随着人口老龄化,房颤的发病率、致死率和致残率逐年上升,造成了巨大的医疗负担。目前药物和手术对房颤干预效果不佳,临床治疗主要集中在预防并发症和改善症状上[1]。随着对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的研究,EVs作为载体能将体外功能性miRNAs递送到受体细胞[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EVs在房颤的发病机制中起作用[3],因此EVs有望为房颤提供更有效的、全新的诊断、评估和治疗方法。
1 EVs概述
EVs是从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中释放出来的具有膜结构的囊泡,按大小和起源分为:外泌体(30~100 nm)、核外颗粒体(100~1 000 nm,包括即微粒、微囊泡和脱落囊泡)和凋亡小体(1~5 μm)[4]。外泌体是通过膜向内出芽(内吞作用),随后形成多泡体,并通过外泌作用释放。核外颗粒体通过质膜向外起泡而形成,然后通过细胞表面的蛋白水解作用释放出来,凋亡小体由凋亡细胞的萎缩和坏死而产生[5]。EVs包含细胞质成分,如蛋白质、mRNA、miRNA和DNA。EVs表达的细胞表面蛋白与其来源细胞相似,因此EVs可以黏附并融合到循环中或远处的驻留细胞上。这些被远处细胞捕获的特性允许EVs携带核苷酸或蛋白质穿梭在细胞间,并提供多种生物分子的水平转移[6]。EVs是目前影响细胞、组织和器官生理的一种细胞间信号传导过程的关键介质。EVs释放后通过与靶细胞膜融合或配体受体相互作用被靶细胞吸收,而参与调节其生物学功能。由于EVs能携带物质信息并在体液中自由循环,循环EVs的数量和分布会根据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而改变[7],因此EVs有天然的诊治和评估潜力。
2 外泌体miRNA在房颤中的作用
外泌体作为EVs中的一种,是由细胞分泌释放的脂质双分子,存在于人体各种体液之中,包括血液、尿液、分泌液等,通过携带和运送细胞物质信息,在细胞间通信中发挥重要作用[8]。病变器官中的异常细胞由于细胞质生理学的改变而产生更多的外泌体,并非常准确地预测疾病亚型[9]。外泌体miRNA占循环miRNA的10%~15%,其可通过外泌体包封保护不被降解,保持高度稳定的状态,并通过与Argonaute蛋白结合而免受细胞外环境的干扰[10]。
从血清中分离外泌体进行miRNA的微阵列分析,发现持续性房颤患者中5种miRNA(miRNA-103a、miRNA-107、miRNA-320d、miRNA-486和let-7b)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提高了4.5倍以上,并在验证阶段证明这些miRNA及其靶基因参与了心房的结构和功能[11],通过高通量测序在房颤组血浆中发现了39个差异表达的外泌体miRNA,其中miR-483-5p与房颤独立相关[12]。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血循环中研究发现血小板及内皮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量显著升高,伴随着血小板的激活和内皮的损伤[13]。房颤患者血浆组织因子浓度升高可能部分原因是含组织因子的EVs水平升高,提示EVs有潜力作为房颤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的预测因子[14]。在房颤心肌细胞中,外泌体miR-320d表达降低,心肌细胞凋亡增加,存活率降低。转染miR-320d模拟物后,细胞中miR-320d水平均升高并改善了房颤对心肌细胞的影响。表明外泌体miR-320d与房颤心肌细胞凋亡和存活有关,并进一步发现miR-320d对心肌细胞的作用是STAT3依赖性的[8]。将房颤来源的外泌体miR-107递送至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发现miR-107可能参与调节细胞存活、迁移、凋亡和细胞周期进程。另外,miR-107过表达可能影响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增殖。这表明miR-107可作为房颤潜在的治疗靶点[15]。上述研究为房颤的分子基础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房颤精准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方向。
3 核外颗粒体在房颤中的作用
核外颗粒体是许多细胞类型在细胞活化和凋亡时脱落的膜泡,既往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核外颗粒体是细胞碎片和生物过程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检测技术优化刺激了其在各种临床情况下的作用的研究[16],目前的证据表明,在正常情况下,不同类型细胞的核外颗粒体形成不仅仅是凋亡、坏死或细胞功能障碍之后的被动过程,而是促进各种细胞类型之间交流的平衡机制。核外颗粒体影响重要的生理功能,如炎性反应、凝血、细胞凋亡和细胞分化,并可能引发病理生理改变[17]。
核外颗粒体在止血和血栓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血液中,最常见的循环微粒(70%~90%)是血小板源性,微粒的促凝血特性与各种疾病血栓栓塞事件风险的增加相关,血小板源性微粒水平是非瓣膜性房颤血栓形成的有效标志[18]。在持续性和永久性房颤中观察到循环微粒(如血小板和内皮源性微粒)水平升高,这提示循环微粒的增多可能反映了血栓前状态,进而增加了心房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的风险[19]。一种利用特异性单克隆抗体AD-1捕获血清微泡后,用ELISA法测定白介素-1β(IL-1β)和P-选择素在这些微泡上的表达量,结果显示非瓣膜性持续性房颤组血清微泡水平、IL-1β和P-选择素均升高,这表明血清微泡可作为研究炎性反应与血小板活化关系的有用指标[19]。此外超敏内皮源性微粒和C反应蛋白可预测肺静脉隔离后早期房颤的复发[20]。上述表明核外颗粒体可以作为传统风险因素之外的额外生物标志物,以早期识别未来房颤风险较高的患者,使可靠的房颤风险分层和评估治疗成为可能。
4 凋亡小体在房颤中的作用
相比之下,目前对凋亡小体的治疗应用探索很少。越来越明显的是,凋亡小体是死亡细胞释放的关键信使,调控细胞清除、组织稳态、病原体传播和免疫等过程,因此其具有诊断和治疗潜力[21],富含钙的凋亡小体可能引发病理性钙沉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管钙化[22],但在房颤方面,凋亡小体的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5 问题与展望
EVs在临床评估和治疗中都有作用,可以为房颤的病理生理提供新的见解。EVs作为细胞通信者的角色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EVs可以通过传递一种特定的miRNA来影响受体细胞,这种miRNA可以改变受体细胞中的蛋白质生成和基因表达,为靶向治疗提供可能[2]。同时,EVs也在止血和血栓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与卒中和血栓栓塞事件密不可分,可作为识别房颤风险分层和评估治疗的生物标志物[14]。
在临床领域对EVs进行分析可为患者提供精确的诊断和准确的治疗,个体化治疗反应往往能让人们深入了解疾病的过程。新型模型系统(如类器官系统)正被用于推动个性化医疗,并提供了更多与病理生理相关的体外状态,以了解EVs的功能作用[23]。然而,在临床研究中EVs的分析仍然存在以下挑战:1)到目前为止,EVs在房颤中的研究已经招募了一定数量的患者,但仍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的跨国研究来精确定义EVs谱在特定房颤中的益处。2)缺乏标准化的方法来分离纯EVs。核外颗粒、外泌体和凋亡小体起源不同,一旦被释放到细胞外间隙(如血液),就没有明确的识别或分离方法。由于没有从血浆中分离和检测EVs的标准方案,对EVs的研究结果往往不一致。此外,EVs测量技术的标准化还存在许多困难。3)大多数了解EVs功能作用的研究仅在体外和细胞模型进行分析,从培养条件或患者样本中分离的EVs用于研究细胞间通信,而EVs在体内病理生理条件中的作用尚不清楚。4)房颤的发病机制是复杂的,并且有不同的阶段,进一步将生物标志物进行区分将是有益的。这里引用的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但仍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随着高端质谱仪和新的RNA测序技术的出现,将更深入地剖析EVs,从而能够更多地发现EVs生物标志物并更好地对其亚群进行分类,以应对EVs异质性的挑战。5)房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更有效的靶向治疗。EVs因其特定的细胞靶向性和稳定性而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药物载体。尽管EVs在研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查EVs的免疫原性特征和产生自身抗体的可能性,这可能会降低治疗的有效性。
但不可否认EVs是一种天然的纳米载体,在房颤疾病中仍有很大的潜力,其生物学特性(如旁分泌、自分泌和内分泌)允许更有效地在细胞间穿越生物屏障传递特定的miRNA,并且在临床研究中突出了潜在的应用价值,为精准治疗提供可能,新的EVs技术和更标准更大规模对EVs的研究将为房颤的不同疾病状态提供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为房颤患者风险分层和评估、个体化诊治反应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