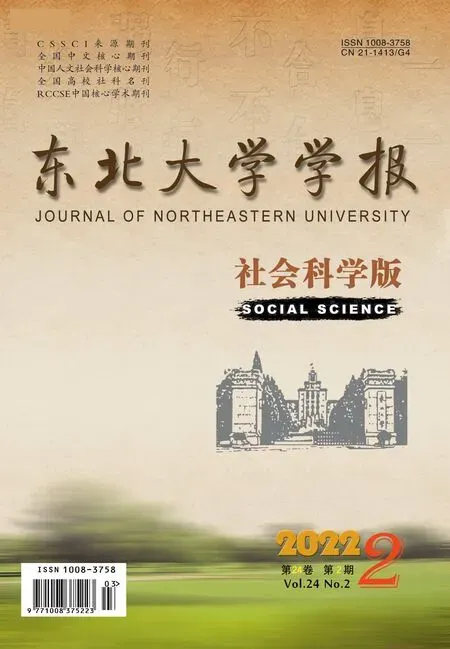人工智能是面相盲人吗?
——从维特根斯坦的知觉哲学看
李国山, 袁菜琼
(1.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2.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维特根斯坦和阿兰·图灵(Alan Turing)就机器能否思维展开的论战,为人所熟知。图灵从计算主义和表征主义出发,假定机器能够思维,并将能思维与可计算等同起来;而图灵测试就是计算主义的范例,是传统符号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维特根斯坦却不认为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维,他的论证集中在他后期关于面相知觉的论述中。在他看来,只有与人类主体拥有相同生活形式的生命体才具有正常的面相知觉能力,才能进行真正的思维,才能参与到日常语言游戏中。他写道:“机器会思想吗?——它会疼吗?——该把人体叫做这样一台机器吗?它可是极接近于这样一台机器啊。但机器当然不会思想!——这是一个经验命题?不是。只有说到人,以及和人相似的东西,我们才说他思想。”[1]174
一、 面相盲人与机器思维问题
图灵是基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模式而假定机器能思维的。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他通过测试实验提出了“机器能够思维吗?”的论题。所谓图灵测试,就是用来判定机器是否拥有与人相当的智能的方法。这种测试遵循以计算和表征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式,从可计算性与外在行为来判定一台机器能否思维,并将人类心智活动与计算机的工作程序相类比:人类主体的认知过程就像计算机进行符号操作和信息加工的过程。
然而,受身心二元论主导的计算主义是“离身心智”的典型代表,它完全忽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第二代认知科学则拒斥表征主义和计算主义,强调“具身心智”和“具身认知”的重要性。从第一代认知科学向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意味着从笛卡尔式的离身心智到具身心智的发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知觉哲学与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在很多方面相呼应,它们共同反对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模式。
从根本上说,机器能否思维的问题,涉及到机器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主体。那么,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像人一样的认知主体呢?能否拥有人类的意识或意向性呢?机器智能与人类思维本质上是一样的吗?能思维的机器是否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能动性呢?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对认知主体以及思维本质的理解。在《哲学研究》中,他坚决反对笛卡尔式的主体观。他此时谈论的主体,不再是其前期所假定的形而上自我,也不是纯粹的内在心灵或离身的心灵,更不是无心灵的自动机,而是能够进行正常的面相知觉的认知主体。这样的认知主体在感知过程中不只是追求如实再现对象,亦即不只是满足于看见(see)什么,而是能充分展示自己将什么看作(see as)什么的能力,并能在所看见的不同面相之间实现自如地转换,“我在面相闪现里知觉到的东西却不是对象的一种性质,它是这个对象和其他对象的内在关系”[1]331。“你必须考虑到,在每个例子中对相互转变的面相的描述都是不同种类的描述。”[1]332
在对面相知觉的讨论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引入“看”的两种用法,亦即对看见和看作的区分来界定“面相”(1)汉语学界研究者将“aspect”(德语为“aspekt”)翻译成“面相”“模样”“方面”。文中主要采用“面相”这一通行的译法。“面相”总是与知觉动词结合在一起使用,比如面相知觉(aspect-perception)和面相观看(aspect-seeing)。另外,维特根斯坦还使用“相貌”(physiognomie)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刻画人的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以及面孔(face)。维特根斯坦通过引入看见和看作之区分来界定“面相”概念。我们可以说看见一个面孔,可是还必须看出一个人面部表情中活生生的情绪,比如一张愤怒的脸。若仅仅看见一个面孔或一个面部表情,这仅仅属于看见层面,只有看出带有情绪的面孔或面部表情,这才属于面相知觉。概念。面相知觉即是看作(see as),是主体看见面相的能力。面相盲人是缺乏面相知觉能力的认知主体,包括初学者、新手、非理智动物以及机器等。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第十一节中,维特根斯坦集中探讨了面相盲人的问题:“现在来了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人不具备把某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的能力?那会是什么样子?后果会是什么?这种缺陷可以和色盲和缺乏绝对音高听力相提并论吗?——我想称之为‘面相盲’”[1]333。在他看来,面相盲人并不缺乏识别知觉对象的能力,但却无法在对同一对象进行感知的过程中看见不同的面相并在这些面相之间实现自由转换:“对于他,这示意图不会从一个面相跳到另一个面相。……‘面相盲患者’对图画的关系会和我们的根本不一样”[1]334。也就是说,面相盲人只能看见某种东西,而不能把某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在知觉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基本主张却是: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具备将某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的面相知觉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人不同于动物和机器的根本之一,一个人只有在经过必要的训练具备了这种能力之后,才能参与到日常语言游戏中去。只有根植于相同生活形式中的言语行为才具有可理解性,计算机、鹦鹉和狮子并不享有与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它们的言语行为对于人类主体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1]350。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面相盲人”与塞尔的“中文屋论证”中的被试者相类似。后者通过中文屋的设计来反对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认为,“恰当编程的计算机其实就具有心灵”[2]。塞尔通过这个思想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整个中文屋系统能够通过汉语测试,也不能说被试者懂得汉语。按照笛卡尔心智主义路径,计算机系统是否具有智能只有它自己知道,而这要求它必须具有反思能力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类比于中文屋论证,被试者似乎也得具有反思能力,必须意识到自己并不懂汉语。这么一来,即便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能够非常逼真地模仿人类的一切言语行为,我们仍然无法断定机器能思维或具有心智,因为完全无法保证计算机具有自我意识。
可以说,正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模式导致了面相盲人的出现,而图灵机就是面相盲人的典型形象。对此,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图灵的‘机器’。这种机器的确是一个进行计算的人。也可以把这个人所说的话用游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饶有趣味的游戏可能是这样,即人们按照规则却得出一些没有意义的指令”[3]。通过将类似于面相盲人的人工智能同人类主体进行对比,我们便可发现,机器与人在思维、言语和行为等方面存在着深刻差异:“但难道我无法设想我周围的人——尽管他们的行为方式一如既往——都是机器人,都没有意识?……你对自己说:‘那边的孩子都只是些机器人;他们活蹦欢跳,却都是自动装置发动的。’要么这些话对你什么都没说,要么会在你心里产生某种吓人的感觉,或诸如此类的感觉”[1]194。
有学者指出,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与符号人工智能的预设相一致:“图灵的语言和思维观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语言图像说可谓异曲同工”[4]。在身心分离的框架下,注定会产生面相盲人,而面相盲人仅从语言的逻辑句法看待语言,无法体验到语词丰富的意义。但是,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转而在思想和语言相统一的模式下来思考语言的意义。在他看来,意义是在主体对语言的使用中不断生成的,人的思维及精神活动对于理解语言至关重要。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勉强让面相盲人参与到日常语言游戏中,但它们只会按照既定的规则来采取行动和执行命令,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得非常机械和僵硬,无法将行为表现与内在心智相统一,不能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形。
那么,与人类主体的言说活动相比,计算机和动物模仿人的言说活动所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倾向于把机器和动物都视作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面相盲人,是因为它们都只能机械性地按既定规则进行认知和沟通活动,而人类则在有意识地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完成一切言语行为。人类的言说带着理解或心灵内容,是有意义的表达;而在一台计算机或一只鹦鹉发出“我疼”的声响时,我们会认为这个声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在非意向性的状态或无意识的状态下来言说和行动的。维特根斯坦写道:“人们或许可以教一只聪明的狗痛得嚎叫,但是它绝不会有意识地模仿。”[5]也就是说,动物或智能机器人据以行动的规则是固定不变的,没有自由决定的空间。它们没有内在情感体验,缺乏真正的心智能力、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相比之下,人类主体能够自主地和有意识地遵守规则。在遵守规则的过程中,一个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进行正常的面相知觉活动,自主作出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二、 共同的生活形式是智能思维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经过学习和训练的认知主体才能看见面相并在不同的知觉面相间实现自由转换。看见面相、体验意义和理解语句不纯粹是认知主体的心灵状态和过程,而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实践能力。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面相盲人却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从而缺乏知识储备、过去经验、专业技能、概念框架和语言能力等规范性因素,这便导致它们无法把握各种要素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从而无法看见面相并在不同面相之间来回转换。我们认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人类的面相知觉能力和一般思维能力,因为这些能力负载着整个语言、文化和生活形式。
从认识论上看,主体是在学习和训练过程中不断提升认知能力,而这主要表现为知道如何做事的实践技能。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不再关注静态的知识表征问题,亦即不再着力探讨命题知识,而是将注意力聚焦于非命题性的、动态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主体的行动和技能知识上。这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学习活动富有启发意义。传统符号人工智能依赖于以计算和表征为范式的认知主义,通过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知识表征来模拟人的心智。然而随着以具身-生成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人工智能研究发生范式转变,以形式化为目标的符号人工智能受到挑战,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转向实践领域。由于我们人类是通过不断学习和训练而掌握各种认知和实践规范的,所以我们自然也会想到以此为参照,来训练人工智能在具体情境下掌握各种技能知识。这是当下人工智能研究者正努力去做的事情,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但其前景如何仍难以判定。
此外,机器能否思维的问题还可以转化为机器理解语句与人类主体理解语句之间有何不同的问题。这也是以维特根斯坦的成就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用武之地。机器能否思维,关键要看它能否理解符号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类主体要真正能理解语句的意义,就必须理解语句所属的整个语言文化及生活形式。语言之意义是在生活形式或生活之流中得以确定的,而计算机与非理性的动物都是面相盲人,他们不能享有与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机器思维”是“思维”概念的派生用法,就像说布娃娃、数字和石头有疼痛是“疼痛”概念的派生用法一样[1]174:疼痛属于活的生命体,而当我们说像布娃娃或机器人这样的非生命体具有疼痛时,实际已经与这个词的本来用法相去甚远了。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研究者们尝试运用深度学习和算法来进行信息储存、数字计算、医学图像处理、无人驾驶、人脸识别等活动,并已取得许多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参与到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之中,比如朗诵诗歌、演奏乐曲、创作艺术作品等。最近清华大学推出了首个虚拟数字人“华智冰”,“她”兼具美貌和才华,“她”拥有一定的推理能力和良好的情感交互能力,“她”还会唱歌和画画,等等。然而,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吗?人工智能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是它们心智的外在表现吗?人工智能可否将内在精神、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等融入到它所创作的作品中呢?人工智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这是否就说明它们能够进行思维或具有心智能力呢?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可以按照设定的程序非常逼真地模仿人的言语和动作,但机器并不是真正的人,不能拥有人的心智,因为人的心智不仅必须由身体与社会历史环境加以塑造,而且也要受到生活形式的影响。我们总觉得,即便人工智能能够模仿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可它们根本不能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更不能理解艺术作品所从属的整个文化背景。即便它能写出合辙押韵的诗来,但由于缺乏真正的情感体验,它还是无法将它的诗歌写成有血有肉的作品,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等主题对它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说,理性思维、审美情感、生命体验等都是嵌入到生活形式之中的;而人工智能由于无法与人类主体享有同样的生活形式,所以他们的所谓创作活动就不是真正的实践活动。同样,由于缺乏内在生命和情感体验,即便智能机器人能够按规则正确地朗诵诗歌,我们仍然不认为它是带着理解和情感来朗诵的,因而也完全不能说它可以欣赏艺术作品。维特根斯坦在描述人类的审美活动时,这样写道:“我声情并茂地阅读,念出这个词,这时它整个由它的含义充实着”[1]336。我们很难想象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真正理解语句的意义,比如理解十四行诗,因为对十四行诗的理解要精通英语文字,知道英语单词的意思以及具备理解它的语言能力,最为关键的是要理解十四行诗所从属的整个文化背景和生活形式。
此外,人工智能也无法真正参与“注意面相”的语言游戏,因为它无法注意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谈到面相之间的相似性,比如注意到两个面孔之间的相似性,父亲与儿子面孔上的相似性,等等。一个人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他在相貌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面容轮廓和神情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相貌上的相似性:“我遇见一个多年没见的人;我看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没认出他来。我忽然认出他来,在他已经改变了的面孔上认出了从前的面孔”[1]307。
朱利安·弗里德兰(Julian Friedland)设想以十年为间隔来识别同一个人的照片的例子,然后让计算机来进行识别:“它将测量面部特征的精确关系,用一个编号的网格覆盖每一张脸,然后比较所有具有相同坐标的正方形中的图像……它只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相同外貌比例的面孔,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6]。同样,可以设想计算机如何识别两篇风格相差不多的文章,一篇是文学家的优秀作品,另一篇是计算机模仿文学家的风格所创作的,两个文本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仅有极其细微的差别。从形式上看,计算机完全能够按照精确的规则来识别二者的相似性:“对于文本属性,计算机将比较语法结构、词缀变化以及相同单词以相同方式使用的频率,以便确定作者的文体习惯”[6]。然而,一旦涉及到文本意义,尤其是其隐喻意义,计算机便一筹莫展了,它仍然是一个面相盲人,无法真正把握两个不同面相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此,尽管机器人能严格按规则模仿人的思维,能够与人进行交谈,还能写诗、画画,甚至能非常精确地模仿艺术大师的作品,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我们仍然觉得,它们还是不折不扣的面相盲人。
三、 人工智能体存在着社会交互困难
维特根斯坦的“面相盲人”形象对于理解人机交互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人机交互方面的研究,旨在探究机器人与人类如何进行有意义的社会交流和互动。那么,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能实现真正的交流吗?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从人工智能的微笑表情中能读出它有情绪吗?戴安娜·普劳德富特(Diane Proudfoot)结合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论述,对这一论题作了专门探讨。她指出,当机器人面带微笑地与我们进行交流时,我们根本无法感受它面部表情或言语行为中的喜悦。人工智能的面部表情与人类主体带有情绪的面部表情存在根本差异:“它可以移动棋子(按照国际象棋的规则)而没有在下棋,或者发出‘汉语的语音’而没有在说中文,或者表现出一些与悲伤相关的表情而并不悲伤。”[7]182我们希望机器人不仅对人的语言和行为进行模仿,而且也对人的情绪和情感进行模拟。然而机器人仅仅表现出一些面部表情而并不真正处于某种情绪状态之中。它可能表现出微笑的表情,却没有高兴的情绪。 因为机器人的内在情绪和外在行为或面部表情相分离,它们是没有任何内在生命、意识和情绪的自动机。在图画—脸的例子中, 人工智能仅仅能看见一个笑脸, 而不能将图画—脸看作一张带有情绪的笑脸。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仅仅在纯粹视觉意义上来看见面部表情和身体特征, 而不能直接感知到面部表情中活生生的恐惧或情绪。面部表情(比如微笑)是依赖于语境的。 微笑以整个一大群人的行为或者生活形式为背景。 正常的面相知觉者不仅仅看见一张笑脸, 而且还能够根据具体的背景或语境,将一张笑脸一会儿看作是善意的, 一会儿看作充满敌意的。 人类主体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同一个微笑图画, 这完全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
我们说,人工智能是面相盲人,也是表情盲人:它们无法感知事物所呈现的完整面相,往往对他人声音中带有的情绪等充耳不闻,对一张脸上的丰富的表情熟视无睹。因此,它们无法看见带有情绪的面部表情:“这就产生了将‘表情’面部机器人在哲学上刻画为一个心灵盲的微笑机器”[7]173。它能够准确地描述一张图画脸的几何特征,清清楚楚地看见画中的线条、颜色和形状,可它却无法将微笑的表情看作是带有情绪的微笑。微笑和皱眉等不是纯粹的身体表达,而是带有情绪的面部表情。
维特根斯坦本人对相关论题作过许多探讨。他写道:“微笑的嘴只在人脸上微笑。”[1]238在他看来,看见悲伤的或友善的面部表情,不仅依赖于纯粹视觉(看见颜色、形状和线条),也依赖于主体对概念(比如友善或悲伤的概念)的把握,甚至更要依赖于对整个知觉背景的把握。看见某种面相的能力是在生活实践中反复学习和训练的结果,而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就是对生活形式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风俗、习惯的熟悉和认同过程。因此,若要实现真正的人机交互,就得看机器能否有朝一日与人类共享同样的生活形式和文化传统。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能进行计算或作出表征的机器根本上不同于能思维的人类主体。关于机器能思维的假定,受到身心二元论的支配。机器的内在状态与外在言语行为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机器即便没有情感体验、主观感受以及意识状态,它仍然能够按照规则正确地输出语句,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得与人类主体并无差异。然而,当机器在输出一些情感类的表达时,比如“我喜欢你!”“你真是个大美人儿!”“你真优秀!”“你是个笨蛋!”,它们不过是按照指令或算法输出一串串符合句法规则的语音符号。我们说,机器的言语行为是不带有意义或理解的。机器难以真正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它们与人之间难以真正完成社会交互活动。因为当你对着机器夸赞或诋毁它时,它可能毫无情感体验,仅仅机械式地进行回应。在机器人的言语行为中,我们感受不到它受褒奖时激动的心情以及受挫败时低落的情绪,因为机器人行为原本就缺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精微莫测的层次,所以它们无法将内在生命、情感体验、意识活动、审美情趣、目的愿望、价值追求等融进社会互动中。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作了大量富有启发的考察,这对于我们理解人机交互问题也很有帮助。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就是用法”的论断,计算机虽然能够按照句法规则构造出语句,可它们根本无法识别出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例如,同一个语句可以用来描述事实,也可以用来表达情感和态度,而情绪是对主体内在精神生活的表达,呈现于语气、语速、语调和面部表情等行为的精微层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在葬礼演说中,‘我们哀悼某某人……’这话的确是用来表达哀悼的;而不是要告诉在场的人什么事情。但在墓前的祈祷中,这话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传达出什么。”[1]293
在其后期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始终坚持以生活形式或整个语言游戏为背景来思考语言的意义问题: 只有参与到语言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才能够经验到语词丰富的含义,语言不再仅仅通过指称、表征、断言或描述事实获得意义,而是在具体场景或语言游戏的使用中获得。 我们通过公共语言完成主体间的相互交流, 比如,一个正在遭受疼痛的人说“我疼”, 这一方面可视作说话者对自己当下心灵状态的直接表达, 另一方面,这句话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目的。 也就是说,她说“我疼”, 主要是向他人寻求安慰, 而当他人看到遭受痛苦的人的种种表现时, 一般都会作出适当的反应,比如安慰正在遭受疼痛的人, 或者采取一些方法来帮助她缓解疼痛。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行为的精微层次”,比如身体动作、相貌、面部表情、姿势、眼神、情感共鸣、声音韵律和语气语调等,在社会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写道:“精微莫测的证据包括眼光、姿态、声调的各种精微之处。”[1]358“问问你自己:人是怎么学到某方面的‘眼力’的?这样一种眼力又是怎样使用的?”[1]358在朱利安·弗里德兰看来,面相盲人的缺陷直接暴露在行为的精微层次上:“这种现象最常出现在手势、音调、图像和音乐等纯粹的表达领域”[6]。计算机缺乏情绪感知,无法理解他人的心灵状态,因而它们一方面无法展现像人一样丰富的精神和行为层次,另一方面也无法意识到他人面部表情或言语行为的多重含义,从而无法与对方实现真正的互动。作为情绪盲人,机器人与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没有情绪体验,也无法把握他者的情绪反应。它更不能像人那样去掩饰某种情绪,或者伪装出另一种面部表情:“一个孩子要能伪装先得学会好多东西”[1]359。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知觉哲学,只有正常人才能自如地完成面相转换。情绪体验也是一种面相知觉,而智能机器人所欠缺的就是获得这种知觉并从一种知觉跳到另一种知觉的能力,因此,它们仍然只是面相盲人。
维特根斯坦主张直接感知论,认为我们能直接看见或感知他人行为或身体表达中的心灵和意图。他甚至还倾向于主张:心灵即行为或行动。他的这种直接感知论为理解他心问题和心身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人类主体是语言游戏或语言实践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不是孤立的观察者或旁观者,他们以一种具身的方式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并实现社会互动,并能直接感知到他人行动或行为中的意图。
从人类主体的相互交往来看,公共可理解的身体动作和言语表达是促成主体间相互理解和互动的基础和关键。但是,人和机器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交流呢?我们说,人和机器之间最理想的交流方式是:以直接感知的方式而不是间接推论的方式在具体情景中实现交互。维特根斯坦关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的论述为理解人机交互问题打开了一个新视角:在语言游戏中,心灵直接呈现在公共表达之中,心灵不再是隐藏在行为之后的不可见的精神实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在可设想的未来情境中,人和机器人或许可以共同参与到交互性游戏和实践活动中,直接感知到彼此的心灵状态,从而完成面对面的动态交互。
四、 结 语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知觉哲学在当今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发展心理学等领域彰显着自身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自闭症患者、计算机和非理智动物都可视作面相盲人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面相知觉理论中获得的启示是:早期符号人工智能显然就是面相盲人,在二元论模式支配下,它将内在心灵和行为表达相分离,始终依照程序来执行命令,无法体验语词丰富的意义。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更加注重具身性、生成性、互动性的阶段,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实现新的突破。然而,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仍然只能从旁观者的立场来模拟人类的心智,并没有以具身的方式直接参与到语言游戏和社会互动之中,人和机器之间尚无法实现充分的社会交互。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已充分意识到强人工智能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症结所在:如何才能将堪比人类的心智植入一台机器中?严酷的现实是:哪里能够找到现成的心智呢,或者,如何才能制造出可供植入的心智呢?所以,曾经雄心勃勃、信心满满地预言奇点临近的库兹韦尔,也只能寄希望于人机互联的实现了[8]。然而他所设想的那种“四不像”的人机合体,总让人觉得怪怪的。不过,探究是无止境的。我们或可期待,目前看来仍难以摆脱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面相盲人”形象的智能机器人,有朝一日会在认知能力、情感体验、意志行动、审美情趣、实践关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令我们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