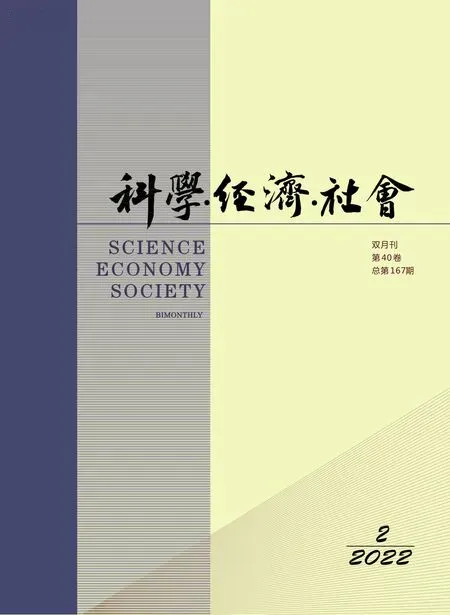存在与本质之间:论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及其阈限
岑朝阳
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物的结构性、功能性、效用性等维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消费活动已然完全融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了一种本能性行为。与前工业时代相比,后工业时代人们的消费活动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经济层面的交换活动,更在其现实性上成为了一种具有社会性与结构性的文化层面的建构活动。结合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与消费主义的社会浪潮,物的存在性在当代表现出一种符号化与象征性的特征,时尚、艺术、潮流与风尚更成为了托生于消费逻辑指涉的文化编码,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鲍德里亚认为身处后现代的人类主体陷入了符号以及拟象的幻象之中,因而对现实逐渐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的掌控,面对此种情形,他藉由“生产之镜”映射出的“拟真”幻象与隐性共谋,通过哲学思辨与逻辑推导,得出了在理论中介方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且以符号权力控制为理论基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这成为了他针对消费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乃至社会基本生产过程批判的理论武器。撇开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不谈,鲍德里亚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当下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新视角:探寻符号、象征性和主体——人的关系。
国内学界对于鲍德里亚的相关研究较多偏向于早期思想形成时期,领域多属艺术理论及批评层面,研究内容也以介绍、解读思想为主,涉及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兴研究相对较少,但也不乏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蔡垚力图由“超真实”的概念探索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规训秘密的揭示①蔡垚:《加速社会中的“超真实”体验——鲍德里亚、罗萨对资本主义规训秘密的揭示》,《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52-58页。;张雄等通过分析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预测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漠然性②张雄、李京京:《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初探》,《世界哲学》2020年第4期,第15-24,160页。;李恩来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完全是生产与消费的简单颠倒③李恩来:《生产与消费的颠倒——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批判逻辑》,《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2期,第26-30页。;张进等则将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放置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并以此进行物质媒介研究,以分析物性压制研究人与物的对立关系④张进、姚富瑞:《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物质媒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62-70页。;而张一兵由符号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差异性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进行了文本性批判⑤张一兵:《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现代哲学》2009 年第4 期,第26-34页。;周嘉昕尝试证明符号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疫苗”作用⑥周嘉昕:《鲍德里亚之后,再无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28-34页。。笔者认为,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仍然蕴含着隐而未彰、亟待探索的内容,即处于物的存在与其本质之间的象征的符号性其构效关系及逻辑理路。这需要从分析物的符号化过程入手,明确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超越性和阈限性来得以澄明,这对于研究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本真范式亦具有现实性意义⑦岑朝阳:《缘起、现实与展望: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二十年(2000-2020)》,《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5期,第32-42页。。
一、物的符号化: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逻辑
(一)从物的差异性到物的等级性
第一阶段,物的差异性在其持存方式上直接孕育诞生了物的等级性。鲍德里亚以其怀疑主义倾向,在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建构中不仅首先解构了一般的物质形式,还实现了物质形式主要与次要的特征、作为使用价值的等级性以及人类对于符号崇拜的结构,并使之缘起于物的差异性这一存在属性。
物的符号化缘起于物的差异性,物的差异性涵盖着物质组成、功能、材质、特点、基本属性、效用(使用价值)等方面的内容,而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物的差异性主要指向物的效用的差异性。众所周知,不同物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同一主体的效用满足程度并不相同(如一把木斧的使用价值一般而言远低于一把锻造精良的铁斧,一只烹调得当的鸡给予人的满足程度远超一只烤焦的鸡),而同一物品对于不同主体的效用满足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在物的差异性操持下,物的使用价值出现了被动化的社会性延伸:物的广义的差异性——一种功能上的无用性,即“摆设恰恰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①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衍生为了区分人的标准:主体间因为把持的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其所占有物的操持的总的数量性产生了质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不同主体所占有的物的使用价值在其现实性上具有了一种等级性的分野,从而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如有闲阶级、夸富宴等)。一切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似乎均将我们由痛苦的物质生产年代放置到舒适的消费年代中去了,物的差异性既表现为一种基本属性的差异,又显现出一种时代性的差异,物的等级性与社会性的逻辑程式也正隐含于此,物的差异性不再为其自然属性而确定,而是由被衍生出来的物的等级性所确定,因此物也迈出了不同于使用价值的第一步符号化的等级性。
(二)从物的等级性到物的社会性
第二阶段,物的等级性的明晰化与结构化推动了物的社会性的展开。在物的等级性阶段,物逐渐开始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且物本身也在消费与技术的推动下发生着变化:首先,物的生产过程逐渐加速,数量增加幅度有所上升;其次,物的种类增多,物的类别化的等级性依然存在;再次,由于新的消费需要被创造出来,主体对于物的需求从数量上与范围上都更强化了物的等级性;最后,物的等级性蔓延至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而由物的差异性引申出的物的等级性成为了区分人类群体的物化准则,等级性的错位蕴含着符号连续性的涌动及其消退的潮汐趋势。物的等级性成为了人们在社会中彰显地位的唯一标准,有闲阶级的资产被持续继承,其后代才能在物的等级化过程中继续推崇瞬时性以及相关的艺术与时尚。
人类个体性的集合与群体性分层在文明演化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社会交往的结构形态与基本单位。在商品交换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物的等级性逐渐衍生为物的社会性,物的差异性因此也演变为群体的物的分野。生产的社会化并没有相应地消除物的等级性,物的等级性驱使人们把握符号世界的规律,并将其转化为向上流动的推动力,映照出社会的内部矛盾,物的等级性在人类生活环境之中存在与意识方面的双重普遍化愈发使得物本身成为了“社会意指的存在者”与“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存在者”②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也正是在物的等级性向社会性的进化之中,物建设了符码(code)体系。在社会性的阶级话语(discours)体系中必须要用物的话语进行自我指认,通过物的等级性,首先出现了以物为基础的分层的社会,继而产生了阶级社会(une société de classe),最终将自身器具化为一种符号理论。符号的普遍性使得精英的选取被“物化”了,他们只有通过“物化”的自我表现与物质投射才能被区分并被筛选出来,并通过消费“力”与“民主”的幻想获得认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愈加结构化的物的等级性推动了物的社会性的展开,物的社会性也愈加指向一种象征。
(三)从物的社会性到物的象征性
第三阶段,物的社会性的弥散及蔓延呼唤着物的象征性的最终出场。符号将物品的价值形态由单一的操持领域拓展至社会领域,对消费者进行消费培训、社会驯化①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63页。,并对主体意识产生了冲击,最终使自身深入至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领域,一个人在景观中的自我状态“并不属于他自身,而属于将这一状态赋予他的他人”②道格拉斯·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振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从而消灭了一般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束了再现和符号的制度”③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开启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新境域。
物的象征性激活了主体间集体无意识的虚拟性意指拜物教,将隐藏在物的实存背后似真的符号性予以澄清。不妨这样说,符号—象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必须在符号化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并在象征性的构成体系中发挥作用。鲍德里亚看到了物的象征性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本质之间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的束缚手段,消费者对物的消费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符号价值生产功能,消费越多,符号价值越大,并通过产出的符号价值维护着符号社会的社会秩序、组织结构、信息系统与交换功能。尤其是信息消费的信息通过对世界的裁剪、曲解与艺术化,更呈现出了一种象征性的功能。最终,“人们认识到自身只有通过他们的物才能获得确证”④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0页。,物的象征性成为了人们寄托自身欲望的一种归宿:一种处于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暧昧地位,“隐秘地宣布了社会生活的失败”⑤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1页。。对物的象征性的攫取由炫耀、选择性地使用转变为内在的社会仪式,最终蝶变成为植根于文明内部的文化行为,物的象征性作为一种文化特权必然被取代,一种新的文明性的特权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显现了出来。以艺术品为例,象征价值成功地成为了人类交互性逻辑影响下的某种审美准则,而表现出一种“超符号”(super-signes)特征,等价于理性的奢侈的物化与升华。
二、存在与本质之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及其阈限
(一)本体论实存上的超越及其阈限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本体论视角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鲍德里亚在他的理论世界中解构了当代的消费主义与象征交换,将世界重构为藉由符号源生而泛滥、蔓延的一个非“本能”的符号世界,符号政治经济学成为了这种符号世界的理论性公证。环顾鲍德里亚的理论王国,符号的连续性只是许多观念、错误与怪诞的思想。路德曾对自由意志进行过批判,他指出,“自由意志真是一个幻影和没有实在的标签,因为人力根本无法掌控任何的邪恶与善良”⑥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近代哲学的兴起》,杨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页。,而因自由意志幻化、异变而成的符号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单纯用符号而不是人类作为主体的意志决定物品的价值,日常生活与人类文明、社会制度、伦理准则都会失去一切意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力地说明了符号化的时代比起距离我们亿万光年外的星星,并没有给予人类更多的自由。人类意志附属于符号时代的符码化,且无力在自身的意指中进行自动自觉地改变,沦为富于单纯器用化且指涉符号存在的“官能性的人”。正如语言的存在使我们能够将心内的思想表达出来一样,符号的存在使人们将内心的欲望表现出来,但这种欲望是物的无用功能的赘生以及“空洞的勃起”①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26页。。
从本体论角度上看,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有其局限性。鲍德里亚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语境与逻辑构境,而是悬设了一个脱离使用价值大地的“符号王国”,使物品在使用价值的功用宇宙中缺席,即“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②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页。。在表面上,鲍德里亚的理论虽未明显地造成其理论间的迷误与脱节,但追溯其源,鲍德里亚忽视使用价值的逻辑推演与其理论的基本预设有着根本性的矛盾。物的符号体系不过是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交换价值的一种派生形式,鲍德里亚轻视一般物的基本的使用价值,是他沉迷符号批判的结果,他相信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谈论物的这类属性已经是无关宏旨的了。而事实却是,鲍德里亚过早地抛弃了维系物的现实维度的使用价值,将他的全部目光投射到了后工业时代物的符号价值之上。一方面,物的差异性的操持以其使用价值为前提。我们并不能设想一个个体的人在不能保证其基本日常需要(即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状态下单纯追寻包括物的等级性、社会性乃至象征性在内的符号化性质,这是不符合社会常识的,而从逻辑推演的角度上看,这也是对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基础预设的背离。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也并未完全完成符号与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祛魅任务,符号政治经济学因其价值悬置性与哲思迷惘性,并未完全解构符号的本体论意义,在其本质上说依然归属于复魅的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在对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从本体论角度上进行分析与梳理后,仍会窥得其局限性。
(二)认识论指称上的超越及其阈限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认识论角度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鲍德里亚强调人类理智以及基于其上的认识的局限性,并说明物的普遍符号化的不可能性,以此获得开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道路。鲍德里亚强调主体在心理层面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物的认知和效用程度,以此开启理论境域:因人的认知方式、社会结构与时空分布受数字媒介的影响,物的符号化历经差异性、等级性、符号性与象征性的道路,使人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世界中发现了符号功用的“确定性”并作为自身的信仰对象,“表征着人类的存在现实”③王荣:《鲍德里亚符号拜物教的存在论阐释》,《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75-79页。,即所谓的能指拜物教。鲍德里亚企图重新定义劳动而向我们指明的能指拜物教说明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物的符号性并非先天被给定的;而另一方面,物的符号性也并非由主体之间交换得来,符号—物“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④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6页。,成为了处于物质实存及其本质之间的一种中介实存,“特有的道德秩序凌驾于整体的秩序”⑤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对意识形态的技术结构具有符码化的显豁作用。因此,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入符号政治经济学,就需要深入到作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层面,用符号解构意识形态,“取消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er)的反复叙事”⑥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演算主体认知视域下介于存在及其本质之间物的文化结构,分析能指与符码在人的觉知领域的形而上学。从中可以看出,语言学也是鲍德里亚符号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以及勾连情境主义的深入思考为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层面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可能:从前工业时代社会的社会性符号萌芽到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符号自觉,符号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结构阶段而进入了分形阶段(fractal stage),象征交换成为了社会交往的终极形式,富有特定意义的完整符号系统为此提供了实施平台。符号政治经济学通过呈现不同力量所交织的符号存在建立其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体系,并且复合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构成分野。
从认识论角度上看,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有其局限性。鲍德里亚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对于马克思的批判,不过是其为达成其符号——拟象理论自洽而所必经的论证道路,因而“生产之镜”所倒映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过是鲍德里亚急于跳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与认知上的挣扎。他指出,“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构模式”①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9页。,符号作为社会及主体自身效用机制运行的功能预演,是社会生产力在符号层面的一种幸存与再生。生产的终结缘起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偏向,社会交往坠入“拟真”深渊所明证的也正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头脑中的启蒙思想的黯淡。与此同时,鲍德里亚在其理论批判中存在着主观性质上对人类科学技术成就的既与性犹疑,在其所建构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圣殿中的先进科学技术是被功能性美学的牢笼所束缚与监禁着的“囚犯”,似乎只要解决这一问题,物的符号化异变便可得到缓解或者遏制。鲍德里亚将自己的理论自诩为“来源于一般的人类学或美学的分析”②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3页。,但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过程上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表现为社会认识的综合个体性在外延上的倍增、内涵及品质上的不断递减符号,因此政治经济学并未成为一般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的通用理论。
(三)价值论路向上的超越及其阈限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价值论角度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技术发展的哲学理论并不能长久地被掩盖,在当下它以各种形式被各种学科所蕴含着并表现出来,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生境域之中天然蕴含了技术发展及技术哲学的有关内容。可以说,没有技术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没有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论向度上,鲍德里亚的批判由商品拜物教转化为能指拜物教,物恋(fetish)性质的符号劳作催生的是能指的物——一种基于当代社会符号系统的自我赋码的符号物,而基于编码消费的混同能指所意指的也正是符号的消费性神话。在鲍德里亚看来,具有实存形态的物质商品形象坍塌之后,符号意指的“神圣形象”又被树立了起来,消费成为了“一种交往性而不是物质性的实践”③让·鲍德里亚:《物体系》,第197页。,符码而并非马克思提出的剥削成为了资本主义丰富自身的崭新途径,从而指向科学技术维度单向发展时间线上的一种黑暗与虚无,昭示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迷惘发展趋势,即对于虚拟征象釜底抽薪式的过度追求——“消费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④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8页。,而超越介乎存在及其本质之间的物的象征性则要求我们向符号宣战。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阶级逻辑的批判过程中,鲍德里亚提及了伪装在当下普遍崇尚“用户友好”的消费主义背后的人文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的虚幻性,是一种符号的反哺,他指出,人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竭力解决消费符号性的问题上,而应该走向另外一极,即注重人的欲望和需求本身。
从价值论角度上看,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有其局限性。例如,针对身处符号社会的人是否具有完全或接近完全道德状态的问题,鲍德里亚并未作出明确回答,虽然鲍德里亚认为理论家的职能就是预见系统性问题并予以阐释①Gerry Coulter,“Baudrillard in the Future”,Lo Sguardo-Journal of Philosophy,2017,Vol.23,No.2,pp.17-28.。说到底,符号政治经济学指向的是批判符号化的社会生活,而不论社会生活的意指如何,它及其附属物总归是要站立在基于丰富物质生产的坚实大地上的。然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是以批判符号——物的体系为指向,但其理论内在蕴含着符号场域与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脱离,釜底抽薪般地过多强调了社会意识在符号化的拟象仿真过程中的倾向性作用而使之占据当代社会生活绝对地位,更甚者,鲍德里亚预设的基本前提是“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将他所有的社会行为都集中在财富的积累之上”②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3页。的经济人般预设,在物质与意识的分野中进行了以意志为先的根源性错误排序,从而使得价值论角度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种“悬设”的、头重脚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鲍德里亚对于物的符号化过程中主体自由的丧失、精神世界的空虚、本能的丧失、自我的异化的理论解释也缺乏历史与时间的革命性力量。正是因为这样,鲍德里亚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的相关理论“带来的是自我侮辱”,而要求人们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原则,那么社会进步将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只需要通过人们的思辨以及理性推理,而非社会现实中通过具有现实性的物质生产实现社会进步了。
三、余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
与列斐伏尔、居伊·德波等人类似,鲍德里亚无疑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过程进行了深入地考辨与历史性地考察,他藉由对符号王国的叙述与描绘作为理论工具来构设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批判符号时代的商品生产及其消费,他认为,符号系统象征着一种激进他者的宿命③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New York:Verso,1993,p.138.,而基于其上对于世界的过度认知是错误的,这会使得我们滑入幻觉、拟象与似真。毋庸赘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有力地攻击了符码对于人类文明以及社会运行的入侵、批驳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的带有符号逻辑印记的意识形态幻象、力图破除符码化过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鲍德里亚虽然始终偏执地宣称自己力图超越马克思,甚至“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要求”④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但追本穷源,其理论建构事实上从未离开马克思的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正是通过与劳动、价值等概念相关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从这一角度上看,鲍德里亚的批判不仅提出了一些新颖的、亟待当代学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所建构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还在理论向度上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说服力。要超越鲍德里亚,我们必须从物的符号价值还原到物的使用价值,在当下的时代建构具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过程中,应当着力关注并提升以国家为统摄商品符号价值外在化的制度理性,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帅的正确消费、生产与交换层面的价值观念体系,以此为基本着力点统筹生活在技术社会与数字经济时代个体的人的消费观念与处世理念,从实现物的象征性的祛魅、物的社会性的重构以及物的等级性的消弭(物的差异性却是客观不可撼动的)。
循此思路,不论是马克思抑或是鲍德里亚,其理论的最终批判指向殊途同归,均面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鲍德里亚所构建的介乎存在及其本质之间的后现代性符号批判系统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经济学的延伸与扩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现实活力。例如,数字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理论丰富思想、指导实践、指挥工作,同时也应当积极吸纳、借鉴、扬弃包括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兼具现代指向与学理内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重建具有当今时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