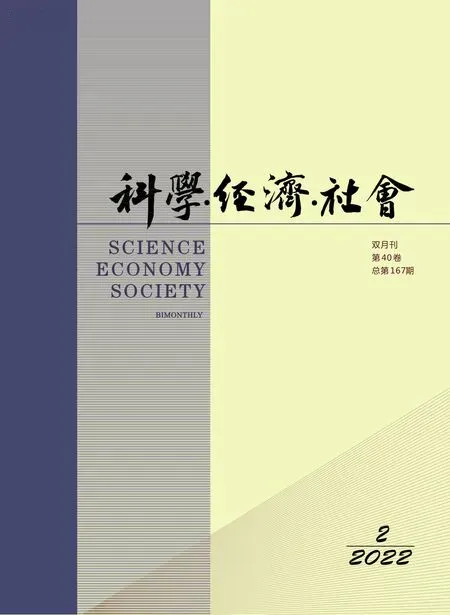从《表记》《坊记》的内容和形式看子思的思想“转换”
末永高康
佐藤将之 监译
我们在推测《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及《缁衣》四篇,以及《五行》的“经”部分均为子思之著述时,需要进一步说明《中庸》文献的古层部分及《缁衣》与《中庸》文献的新层部分及《五行》“经”之间存在的思想上的差距。
按照朱熹的分章,《中庸》古层系第二章到第二十章前半,也就是以“中庸”为中心议题的部分①关于将《中庸》一篇分为新旧两层的讨论,请参阅末永高康:《〈中庸〉“诚”的思想》,《科学・经济・社会》2021 年第3期,第82-87页。,在此我们将这部分暂称为“中庸古本”。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庸古本”及《缁衣》的作者几乎没有表现出对人内在的兴趣。二者根底上的共通之处是:将“名”所附随的“中庸”作为行为基准的思考模式。比方说,通行“君”“臣”“父”“子”等名的集团中存在集团成员普遍认定的各名称的“合宜性”,那么各名的使用就以这种“合宜性”为标准①相关论述及“中庸古本”、《缁衣》的思想内容,请参阅末永高康:《郭店〈缁衣〉的形式和思维中的子思思想之特质》,《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4期,第89-102页。。但是,二者仅讨论了“言”和“行”的理想状态,对“言”“行”背后的“心”却没有涉及。只要“言”“行”在他者的观察中保持一致,且具备“恒”的话,就足够了,“心”的理想状态则不在论述范围内。
与之相对,《中庸》新层部分(即《中庸》古层之外的部分,以下称“中庸新本”)的主题是“诚”②关于“中庸新本”的“诚”思想,请参阅末永高康:《〈中庸〉“诚”的思想》,《科学・经济・社会》2021 年第3 期,第82-87页。。《五行》“经”则主张在“仁”“义”“礼”“智”“圣”之中区分“不形于内”的“行”和“形于内”的“徳之行”,并讨论了如何通过修行从前者达到后者③关于《五行》“经”部分的思想内容,请参阅末永高康:《郭店楚简〈五行〉的修养论》,《科学・经济・社会》2021 年第1期,第106-117页。。于是,我们清楚地观察到“中庸新本”及《五行》“经”关于“诚”或“徳之行”的探讨是出于对人内在的深厚兴趣,这一点正显示了它们与“中庸古本”及《缁衣》之间的思想差异。
不仅如此,两拨文献之间的形式差异也很明显:“中庸古本”及《缁衣》(以及《坊记》《表记》)的文章每每以引用孔子言的“子曰”为开头,“中庸新本”和《五行》则基本以论述的形式直接展开讨论。基于这些差异,过去学界(尤其是日本学界)认为“中庸古本”及《缁衣》,与“中庸新本”及《五行》乃出自不同作者,尤其是对于后者的“中庸新本”及《五行》,大多学者都以与子思全然无关的态度来阐述其思想史的意义。
自郭店楚墓同时出土《缁衣》和《五行》“经”之后,学界主流开始将《五行》“经”与《缁衣》同视为子思作品。笔者也赞同将《五行》“经”与“中庸古本”《缁衣》《表记》及《坊记》三篇看作是子思著述。但对“中庸新本”和子思之关系的判断,前稿《〈中庸〉“诚”的思想》尚有所保留④下文“前稿”都指《〈中庸〉“诚”的思想》(《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3期,第82-87页)一文。。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表记》的“仁”思想和《坊记》的“礼”思想,阐明子思思想中如何生出对人内在的兴趣,从而在“中庸古本”及《缁衣》篇,与“中庸新本”及《五行》之间架构一条思想史的桥梁,并对前稿保留的“中庸新本”与子思之关系的问题做出解答。
一、《表记》的“仁”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自不待多言,然而在《缁衣》与“中庸古本”中,“仁”的存在并没有那么显著。“仁”字在《缁衣》中只出现了以下三次,且并非主要探究对象。
(1)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
(楚简本第六章⑤本稿中郭店楚简的引文都根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之释文。但仮借字改为通行字体。另外,此条对应的今本第六章后文也有“仁”字:“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简一〇、一一)
(2)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岂必尽仁。
(楚简本第七章,简一二、一三)
(3)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仁不坚①与此对应的今本第二十一章作“则好贤不坚”,没有“仁”字。,而恶恶不着也。
(楚简本第二十二章,简四三、四四)
“中庸古本”中也仅见“修道以仁。仁者人也”②《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页。(第二十章③本稿使用朱子《中庸集注》的分章。)这一处。其中与第二句相同的语句还见于《表记》篇第二段第五章④《礼记正义》,第1718页。。实际上,《表记》第二段及第三段中有不少论及“仁”的内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段第五章的以下部分: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⑤《礼记正义》,第1717页。
很容易看出这是以《论语·里仁》中的两条孔子言为基础:
(1)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⑥《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2)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⑦《论语注疏》,第51页。。
除《论语》的“安仁”“利仁”之外,《表记》第二段第五章中还讨论了“强仁”,笔者推测“强仁”部分或为子思所加。而这三者又很明显可以联系到“中庸新本”中的“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中庸》第二十章有如下内容: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⑧《礼记正义》,第1683页。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将“仁”区分为二或三时的观点。“仁”并非因外表举动或举动带来的“功”(正面的结果)而被区分;而是在实行“仁”的动机上被区分。“安仁”的“仁者”想要这么做,或者不这么做就会不安心,所以实行“仁”;“以仁为利”的“知者”认为这样做(于人或己)有“利”;“强仁”者则出于“畏”,害怕不这么做就会使“罪”(负面的后果)殃及自身。“利仁”或“强仁”者因“仁”带来的“功”或“不仁”造成的“罪”而实行“仁”。相较之下,“安仁”者即使遭遇伯夷、叔齐那样饿死的结果,也还是会实行“仁”。正如《论语・述而》所说,“安仁”者“求仁而得仁”⑨《论语注疏》,第99页。,也就是说,即使遭遇被別人评价为“过错”、没有获益的结果,也不会抱怨。相反,“利仁”“强仁”者如果预测“仁”的实行没有好处,恐怕就不会实行;如果实行“仁”却遭到出乎意料的不利结果,恐怕就会对实行“仁”感到后悔。或许正是这样的思考,“仁”才被区分为二或三。可以说,这样的思考其实已经蕴含了《五行》区分“不形于内”之“行”与“形于内”的“德之行”的观点。因为它对于外表同样实行“仁”之举动的人,根据其内在动机加以区别。
虽然笔者使用了“动机”一词,但是对“安仁”者而言,动机一词或许并不恰当。“安仁”者只是实行其想要实行的事情,而其所行的举动恰恰合于“仁”。即便向他询问实行“仁”的动机,恐怕也只会得到“因为我想这么做所以这么做”这种不成回答的回答。相反,如果询问“利仁”“强仁”者,他们就会回答“因什么什么的缘故而这么做”,也就是将“仁”的实行作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根据这种回答便能明确他们的动机。很难说“安仁”者是以“仁”为目的地行“仁”,他们是自然而然地行“仁”。处在“安仁”状态的人,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目的─手段”的模式,“求仁而得仁”的“安仁”者自然而然地求“仁”。如果这个“求”的意义转为以“仁”为目的而朝着“仁”进行努力之义的话,那恐怕就无法称之为“安仁”。另一方面,一般人只能以“仁”为手段,或者顶多以“仁”为目的来努力,因此,处于“安仁”状态是非常困难的。《表记》第三段第三章中说:“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①《礼记正义》,第1722页。第二段第四章中也有类似的句子②《表记》第五段第一章也有:“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③《礼记正义》,第1717页。这些很显然可以看作是《论语·里仁》中的孔子之言“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④《论语注疏》,第53页。的展开。由此可见,《表记》的作者认为“安仁”或“好仁”的状态非常困难,因而把二者排除到引导一般人的标准之外。其第二段第四章接着又说:“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而第三段第七章则更明确地说: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之。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⑤《礼记正义》,第1723页。
“安仁”者的举动过于崇高,因而无法以之为标准而强加于民众。不过,虽然标准过高,但是“安仁”者所示的举动仍然是卓越的,在这种思考下,势必要区分“安仁”者所示的“道”与一般人跟随的“道”。
我们不妨来看《五行》中与此相关的记载。《五行》“经”一开头便说:
五行。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
徳之行五和、谓之徳。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徳、天道也。
(简一至简五⑥关于这段内容的解释问题,请参阅末永高康:《郭店楚简〈五行〉的修养论》,《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1期,第112-114页。)
将“五行”区分为“徳之行”和单纯的“行”,且将前者与“天道”之“徳”搭配,将后者与“人道”之“善”搭配。同样,“中庸新本”中也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①《礼记正义》,第1689页。(第二十章)
区分“诚者”和“诚之者”,并将前者与“天之道”、后者与“人之道”搭配。由此可见,将“道”一分为二加以探讨的做法在《表记》的思想内部就已经存在了。
二、作为“民之坊”的“礼”
这种思考进一步拉开了“君”(统治者)与“民”(被治者)之间的距离。《坊记》第三章说:“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②《礼记正义》,第1636页。这当然是基于《论语·学而》的孔子言“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③《论语注疏》,第13页。的产物,说明了“富而好礼”的君子非常稀少。相比之下,《坊记》第二章记载了作者对一般民众的认识:“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④《礼记正义》,第1635页。然后,为了统治这样的民众,《坊记》第二章中有如下说明: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⑤本文依据郑玄注“慊或为嫌”,将“慊”解释为“嫌”义。
此处对“礼”之特征的说明值得注意。对“富而好礼”的君子而言,“礼”是通过“克己”来履行并借此提升自己的事物。此处认为,“礼”就是民众应该顺从的标准,通过使民众顺从该标准而得以防止民乱。以“礼”为“民之坊(防)”的思想在《坊记》中是一以贯之的,比如第一章有“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⑥《礼记正义》,第1634页。其中“礼”与“刑”并列,同样被当做防止民众作乱的方法。与之相对,《缁衣》(今本第三章)则说:“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⑦《礼记正义》,第1752页。可见《缁衣》的作者与《论语》的作者相同,都认为“德”“礼”与“政”“刑”相互对立。因此,当我们看到《坊记》作者将“德”与“政”并列时就难免感到惊讶。
或许有学者将《缁衣》与《坊记》的差异视为矛盾,并以此差异为两篇作者不同的旁证。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样的差异不如说正好显示了子思思想的发展。《缁衣》中一以贯之地讨论了治民者所需的态度心得⑧也有说明臣下之心得的部分,如楚简本《缁衣》第四章有“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则君不劳”(简六、七),但这种例子极为稀少。,且如下文所示: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⑨《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尚未隶定“表”字,本文依据今本(第四章)读为“表”。也。
(楚简本第八章,简一四,简一五)
将其心得视为引导并统治民众的条件。将这样的观点与《论语·子路》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论语注疏》,第196页。比较时,《缁衣》中的“正其身而慎其好恶”一事,与其说是君子应当所为,不如说更接近于治民的手段。在《缁衣》的思维中,先有治民的目的,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才有统治者被要求躬行恰当的行为。只不过,《缁衣》的措辞表面上仍止于谈论君子应当所为的范畴。但是到了《表记》,则更加明显地将之解释为治民的手段。比如:
(1)子曰,裼袭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渎也。②《礼记正义》,第1714页。(第一段第三章)
(2)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③《礼记正义》,第1715页。(第一段第七章)
(3)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体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④《礼记正义》,第1716页。(第一段第九章)
如上所述,上位者的举动或者其所应当遵从的“礼”,是以“希望民众做某事,或担忧民不做某事”为前提的。《表记》的这种论述基于与《缁衣》同样的“下位者模仿上位者”的想法⑤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模仿被当成前提也是《缁衣》的一个特征(如今本第四章“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第六章“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人”等),《表记》也有同样的特征。。按照此思路,《坊记》第九章有:“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⑥《礼记正义》,第1641页。理论上如果上位者辞让,民众也应该会辞让。但问题是,现实中下位者未必会模仿上位者。如《坊记》第八章又说:“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⑦《礼记正义》,第1641页。可见也有民众不辞让的例子。这是《坊记》中的阶段性认识。在这种认识下,《坊记》又提出了作为“民之坊”的“礼”。我们通过并列比较,就会知道子思的想法按照《缁衣》→《表记》→《坊记》的顺序逐渐发生了改变。
有趣的是,论述形式也按照《缁衣》→《表记》→《坊记》的顺序发生了改变。在楚简本《缁衣》中,以言行为主题的文句统一出现在第十四章到第十九章,从这样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内容相关的文句有统一整理的意识,但是这些句子尚未发展为可划分的段落。相较之下,《表记》依据主题整理出章节,并在每章节首冠以“子言之”来区分段落。这反映了编者对文句进行了加工的事实。《坊记》以“民之坊”之“礼”为贯穿前后的主题,因而没有区分段落,但正如第二十五章的“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⑧《礼记正义》,第1647页。或第三十二章的“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⑨《礼记正义》,第1653页。那样,作者在十几个地方设置了“以此坊(示)民”的句式,因此将全体论述统一了起来⑩另外还有:“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第三章)、“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第六章)、“以此坊民,民犹偝死而号无告”(第十章)、“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第二十三章)、“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第二十六章)、“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第二十九章)、“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第三十章)、“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第三十一章)、“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第三十三章)、“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第三十四章)、“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第三十五章)、“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第三十七章)、“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第三十八章)、“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第三十九章)。,而这一点是《缁衣》和《表记》两篇未有的特征。笔者推测这些句式是由子思新添加的。因此,虽然三篇均采取引述孔子言的形式,但却可以看出《坊记》经过了最大程度的加工。毕竟“礼”作为“民之坊”这样的想法,应该并非出自孔子本人①伊东伦厚指出:在《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五年》《周礼・地官・大司徒》《礼记・经解》(《大戴礼记・礼祭》),以及《汉书・董仲舒传》《春秋繁露・度制》《汉书・艺文志》等的思想中也含有以“礼”作为“民之坊”的思维。伊东把作为“民之坊”之“礼”的这种想法归于受荀子影响的思想成分,因而认为《坊记》代表较晚时代的思想。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楚简本《缁衣》的存在,所以无法接受伊东的相关主张。但是伊东也认为《坊记》中的如上思想与孔子对“礼”的说法不同,这一点是值得参考的。请参见伊东伦厚:《〈礼记〉坊记・表记・缁衣篇にxiiiⅩⅣて──ⅩⅣ(ⅰ)ttitf〈子思子〉残篇の再检讨──》,《東京支那學報》,1969年第15期,第19-24页。。
《缁衣》《表记》两篇中,以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模仿为前提,探讨了统治者为治民而需要具备的境界;然而《坊记》中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模仿并非总是成立,因而无法再作为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坊记》提出了作为“民之坊”的“礼”这样的想法。但是该篇中反复出现“以此坊(示)民……”的语句,这同时也表明了单独的“礼”本身已经无法发挥作为“民之坊”的功能。譬如《坊记》第三十章说:
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②《礼记正义》,第1651页。
其第三十九章也说: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③《礼记正义》,第1658页。
在这样的认识下,如果要进一步追求治民手段,所能想到的一个方向应该就是借由比“礼”更有强制力的“法”或者“刑”来统治民众。然而,《坊记》的作者并未往这个方向前进。如上所述,《坊记》确实提到了“刑”。但是作者仅论述了与“礼”相同的、发挥“民之坊”功能的“刑”而已,没有提及超越“礼”的、具有强大强制力的“刑”。而且《坊记》中,“刑”字只见于上文所引的那一处。因此,不能认为《坊记》的作者在“刑”之中追求超越“礼”的统治功能。
三、超越“民之坊”
那么,《坊记》作者的论述是往哪个方向展开的呢?关于这一点,《后汉书·王良传》中保留的《子思子·累德》的遗文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累德》中说:“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④请参见《后汉书・王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34页。即便君主身为民众的“表”(仪表),率先揭示“礼”,民众也未必会顺从它。这里就需要另外一点动力。《累德》的作者向君主内在的状态去寻找,并由此抽出“诚”(或者“信”)的状态作为这个动力。
如序文所述,“中庸古本”、《缁衣》都是对人内在关心薄弱的文献。到了《表记》,虽然可以在“仁”的论说中看到对人内在的关心,但是此关心仍止于萌芽阶段。《坊记》也是一样。另外,《缁衣》《表记》两篇中无条件地以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模仿为前提行论。而《坊记》则意识到一个难题——为民之“表”的君子所揭示“礼”未必会使民顺从,因而逐渐开始向人的内在去寻找。
在此便发生了一个逆转。在《缁衣》的“故君子顾言而行,以成其信”(楚简本第十七章,简三四、三五)的阶段中,某人为了使别人认为他是“信”(诚信)的人,就需要实践具有“恒”的、言行一致的举动。相形之下,在此《累德》的阶段则先关注到了人的内在,从而抽出了“诚”这样的概念,然后又与人的内在状态缔结因果关系,而在此思路上推断某人因为具备内在“诚”(诚信)所以备受人们信赖。在关于“诚”的这种设想之下,《缁衣》等篇中作为前提的“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模仿”,将被重新归结为“诚”所具有的感化力。这里的思路也就变为:因为君主的内在有“诚”,所以民众的教化能够被施行。“中庸新本”中所见的作为化育条件的“诚”,显然就是此一方向的发展①在“中庸新本”中,“诚”的感化力的内涵被扩大了,如第二十三章中的“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提出了可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之作用的“诚”。关于推行化育之条件的“诚”的详细考察,请参阅前稿,第93-95页。。
另外,《缁衣》中说道:如同喜好“缁衣”那样喜好美(美好的事情),讨厌“巷伯”那样讨厌恶(恶的事情)。如果结合《论语·里仁》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起思考,那么能够做到喜好该喜好之事物、讨厌该讨厌之事物的人其实仅限于“仁者”,尤其是“安仁”者。“安仁”者自然而然地采取“安仁”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在此前提上,若转而关注这类人的内在状态,而其内在与上述的“诚”重合,那么“诚”的状态也会被理解为能够发挥“性”之固有好恶的状态。“中庸新本”中的作为“性”之发挥条件的“诚”便是此例②关于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其与“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够发挥“性”本来好恶的状态的探讨,请参阅末永高康:《〈孟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论》,《科学・经济・社会》2020 年第4 期,第1-15 页。在《性自命出》中,正如“喜怒悲哀之气、性也”“好恶、性也”等例所示,将天所赋予的作为“生存方式”的感情和好恶规定为“性”,认为天赋感情及好恶没有扭曲,能够以最初被赋予的状态来发挥其功能才是理想的状态。“中庸新本”中以“诚”这样的术语来阐述了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条件,也就是下文中作为呈现“性”之条件的“诚”。详细考察请参见前稿,第89-93页。。由是观之,基于《缁衣》等篇思想的人,只要将视线转向人的内在,就会开启通往“中庸新本”的“诚”之思想的道路。
子思在朝向人内在的同时,也改变了其著述形式。前引《累德》的著述形式我们无法得悉③武内义雄从《淮南子・缪称》中引用了十三条,将之当作《子思子》的遗文。请参阅武内义雄:《易と中庸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版,第65-68页。不过,假设真如武内所说,这些全部是《子思子・累德》的文句,那么其中没有“子曰”“孔子曰”等字样的事实似乎代表《累德》没有采取引用孔子言的形式。但是,考虑到诸书所引《子思子》(含《缁衣》《表记》两篇)也没有“子曰”等字样,这一点或许无法成为证明《累德》撰写特色的证据。,但至少到《五行》“经”的时候,子思就已经不再采用引孔子言的形式。他在《坊记》中反复使用“以此坊(示)民”一句,就显示了引用孔子言的形式已经无法全面承载他自己的思想。只不过,子思最初可能认为可以在孔子思想的架构之内著述自己的思想,所以《坊记》时仍然采取了引用孔子言的形式。然而,到了《五行》“经”的时候,子思抛弃了这个形式。这种转变或许反映了子思的自觉,也就是说子思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孔子思想的架构。《表记》中,在孔子的“安仁”“利仁”之外加上“强仁”时,子思还是处于孔子思想架构之内的。但随着对人内在探究的加深,子思将“安仁”阐述为“形于仁内”,将“利仁”“强仁”阐述为“不形于仁内”的时候,应该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孔子的思想架构,所以《五行》“经”才抛弃了引用孔子言的形式。
这种著述形式的变化发生在子思生平的哪个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一边发展《五行》“经”的新形式,一边继续采用引述孔子言的形式。不过,《五行》“经”的存在明确揭示了一个事情:子思在某个阶段之后开始采用与《缁衣》等篇不同的著述方式。基于此,此处我们也该重新探讨,因“中庸新本”与《缁衣》等篇形式不同而被保留在前稿之中的“中庸新本”与子思之关系的问题①请参阅前稿,第82-101页。。
笔者刚才指出,不能只依据形式的差异,就推断“中庸新本”与《缁衣》的作者不同。笔者前稿已经论及,“中庸新本”的思想基本上还在郭店楚简所示的思想架构之内。另外,如上文所述:基于《缁衣》思想背景的思想家,只要将目光转投向人的内在,就会开启朝向“中庸新本”的“诚”的思想的道路。若以上观察属实,就意味着对“中庸新本”为子思之作的怀疑是没有确切理由的。今本《中庸》中相当于“中庸新本”的部分,特别是以第二十八章为中心的部分,的确存在着疑为后世所加的内容,但如果根据这一点就立刻将“中庸新本”的全部内容与子思思想完全割裂的话,难免怀疑太过。如前稿所示,以和《孟子》内容重复的文句为中心,“中庸新本”中似乎包含了部分源自子思思想的内容。固然,这并非意味着今本《中庸》整篇(包含“中庸古本”)都是子思之作。不能排除其中一部分,甚或整篇都出自子思后学的可能性。然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就目前的资料状况来看,我们无法将子思本人与其后学严密地区别开来。我们能够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承认“中庸新本”有经过子思后学或后世加工的可能,另一方面只能暂时将“中庸新本”视为子思之作来进行讨论。至于更加严密精细的分析,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出现更新的资料。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表记》的“仁”思想和《坊记》的“礼”思想,从而在“中庸古本”及《缁衣》篇与“中庸新本”及《五行》之间架构一条思想史桥梁的目的,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达成了。但是前章末尾提到的对“中庸新本”的处理方式,恐怕会引起读者的疑问。被视为后学所出的内容明明存在,却要将整篇当做子思之作,这样的文献处理方式在学术研究上恐怕不够严谨——诸如此类的质疑是无可避免的。确实,笔者也认为有欠慎重。明明无法确认全篇皆出自子思,却将整篇视为传达子思思想的内容。这种想法中,的确存在着将范围远超子思实际面貌的内容归属给子思本人的危险。然而,将今本《中庸》与子思完全割离的“慎重”态度,也同样不安全。因为会存在原本属于子思思想的内容被从子思处夺去的危险。无论是将“中庸新本”与子思完全割离还是完全连结,都会有冒险。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资料将源自子思的要素与后世所加的要素从今本《中庸》中分离,那么就可以据此单独讨论子思思想。问题是,目前并没有那样的资料,也没有能够分离两者的研究方法。既然如此,要选择哪种立场,只好由研究者各人衡量各种立场的危险性高低,从而做出选择。对笔者而言,既然“中庸新本”中含有被认为源自子思的部分,就无法将“中庸新本”与子思完全割离。假设“中庸新本”中源自后世的成分远远超过源自子思的成分的话,那么将“中庸新本”整篇归于子思的作法的确会导致不合理的思想史建构。话虽如此,笔者认为将“中庸新本”全视为子思之作,并不会在思想史的建构上产生太大的不合理。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用主观的“笔者认为”来论述,而应该先建构出这样的思想史,再请读者加以批判。其实,笔者迄今在本刊发表的系列论考中已经隐约暗示了笔者所构建的思想史面貌①《〈孟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论》(2020 年第4 期,第1-15 页),《郭店楚简〈五行〉的修养论》(2021 年第1期,第106-117页),《孟子与〈五行〉》(2021年第2期,第104-113页),《〈中庸〉“诚”的思想》(2021年第3期,第82-101页),《郭店〈缁衣〉的形式和思维中的子思思想之特质》(2021年第4期,第89-102页)。。现在终于到了按时间顺序对此进行整理统合的阶段。对此,笔者将在本刊下一期中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