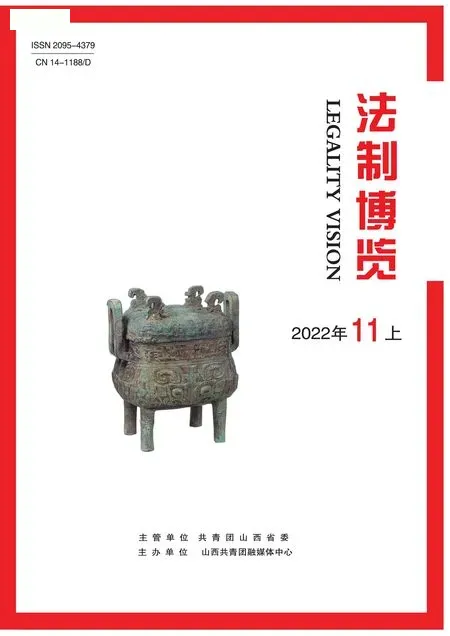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儿童性侵害的预防与保护机制探索
——基于贵州P村“儿童保护”的项目实践
李 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2021年发布的《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年龄最小的为1岁。报告指出,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报告还透露,家庭成员作案曝光量较上年(12.74%)有较大幅度上升,由于其作案更具隐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也更大。其中,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占九成,小学和初中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例高。儿童性侵害呈现出低龄化、影响恶劣、隐匿性高、报案率低、性教育滞后及对性侵行为认识严重不足的态势。[1]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女童保护”认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从近年来曝光的案例来看,农村地区的性侵儿童案往往有持续时间长、受害儿童多等特点。
一、儿童性侵害概念
儿童性侵害一般又称为儿童性侵、儿童性虐待。目前,“儿童性侵害”在国内外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世卫组织将“儿童性侵害”概括为儿童卷入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性活动,或因不具备相关知识而同意的性活动,或因发育程度限制而无法知情同意的性活动,或破坏法律和社会禁忌的性活动。我国香港特区防止虐待儿童会《预防儿童性侵犯训练手册》将“儿童性侵犯”定义为:为满足侵犯者性欲或其他目的,而透过暴力、欺骗、引诱或其他办法与儿童进行性活动。这包括有身体接触和没有身体接触的性侵犯:有身体接触的儿童性侵犯,如非礼、强奸、乱伦、引诱儿童触摸侵犯者的私人部位、触摸儿童的私人部位;没有身体接触的儿童性侵犯,如强迫儿童看色情电影、录像带,用猥亵言语挑逗儿童,吩咐儿童露体,向儿童露体和拍摄儿童裸体照片等。在我国法律概念上对应的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在儿童保护领域里,通常使用的是“儿童性虐待”,是指对儿童进行任何形式的性接触,它与身体虐待、忽视和情感虐待一起构成“儿童虐待”。[2]
结合相关研究,本文的“儿童性侵害”概念较倾向于我国香港特区防止虐待儿童会的概念界定,是指任何人为满足其性欲或其他目的,侵犯不满14周岁儿童的性权益,实施的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包括:强奸,猥亵,嫖宿,引诱、组织、强迫儿童卖淫,向儿童传播淫秽物品,以儿童为题材制作淫秽物品及以其他方式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项目背景
贵州省P村位于贵州南部,该村有10个村民组,686户,2600人,85%为水族。P村境内设中心校一所,在校生有280余人,住校生103人,儿童入学率99%。P村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居多,学校教育较为传统保守。家庭教育中,监护主体多为隔代抚养的祖辈,几乎不会涉及儿童性教育,儿童防性侵相关教育几近空白。该项目与当地教育部门的合作,通过对P村6~12岁儿童及其家长开展宣讲、小组游戏、图册宣传、个案辅导等方式,并吸纳当地教师加入项目,作为项目结束后的延续力量,以保证该地儿童保护的预防机制有效建立。
三、项目实践
(一)调研走访
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在正式开展专业服务介入之前,对P村的部分6~14岁的儿童、儿童监护人、学校教师及P村村委部分工作人员等进行了随机走访。走访以结构化访谈为主,涉及问题有关于儿童性侵害的行为界定、隐私部位的理解、儿童性教育的情况、遇害时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以及若不幸遇害后如何处理等问题。
(二)P村儿童性侵害认知现状
经走访发现,孩子们对儿童性侵害概念认知几近空白,无法准确识别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大部分儿童对隐私部位有一定的认知,更多表达出来的是羞耻感。在问及如若不幸遭遇性侵害或是遇害后的处理方式,大部分孩子会选择“挣扎自救”,及告诉家长或者很信任的人此类应对措施,也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感到被害是羞耻行为或是怕遭到报复不知如何处理。此外,绝大部分孩子都认为“陌生人”才会存在危险,且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儿童性侵害只存在于女童,男童不会受害。
在家长方面,受访家长大多非儿童父母,多为孩子的祖辈。大家表示对孩子有过简单的性教育,一般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后,低龄的孩子几乎没有做过任何性教育,甚至会担心相关信息会把孩子教坏。只是提醒孩子别太晚回家,不要轻信陌生人等等。在受害者性别上,也几乎都表示对男孩子不担心,更没有给男孩子普及过相关自我保护知识。
在学校教师和村委工作人员方面,均表示相关性教育开展不足,且缺乏儿童自我保护相关知识的系统教育。老师们表示有必要给孩子们普及性教育和防性侵的常识,但是又担心自己不够专业,表达或者定位不准确会给孩子们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对本项目的开展也表示存在一定忧虑,担心对孩子的引导是否得当,家长是否赞同等。
(三)社会工作介入儿童性侵害的预防实务
1.防性侵课堂
该项目所有志愿者讲师均已经参加“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考核,均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平等地和孩子互动,利用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孩子们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学习相关自我保护知识。
课堂内容严格按照“女童保护”所提供教案,在用词用语、互动模拟等等方面都有专门设计,由小游戏引入,自然过渡到性侵害的各种知识与防范的学习。为孩子们讲述“分辨和防范性侵害”“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防范性侵害”“遇到性侵时该怎么做”“万一遇到性侵害后该做什么”几大板块的内容,同时普及报警及求助维权电话。课堂引导孩子们注意、保持、行为强化等,让孩子们轻松学到自我保护的技能、培养科学的性观念。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提醒孩子们易形成的误区,例如“只看看裸露图片不属于性侵害”“只有女孩子需要小心性侵害”“只有陌生人需要注意防范”等等方面。更进一步清晰界定性侵害的行为范畴,提醒男童一样也需要识别与防范。尤其是“陌生人”误区,事实证明,所有的性侵害案件中,超过七成是熟人作案,提醒儿童对身边的邻居、亲戚、老师等等“熟人”要有防范意识。
2.小组游戏
本项目以小组工作的方式,七到八人为一组开展小组游戏,内化相关防性侵知识。通过“认识自我”“这里不能碰”“紧急呼叫”等几大主题,以现场模拟、角色互换等方式,吸引孩子们进行互动,让孩子们主动且开放地获取了自我保护的知识。并在每个游戏之后,教师们带领孩子们做引导交流分享,充分保障小组中每个孩子都有表达及询问的机会,不再害羞,不再“谈性色变”,以此达到既定目标,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四、项目实施效果
(一)儿童方面
经过对P村儿童基本全覆盖的授课及小组活动,该村的孩子对预防知识基本从一开始的羞涩、茫然,逐渐过渡为自然接受。孩子们懂得了隐私部位的意义,知晓了属于性侵害的几种情况、日常生活中如何防范,知道了不光是“陌生人”才会存在侵害的风险,学会了若遇到性侵害该如何视具体情况做出正确处理,以及如若不幸遇害后,该如何应对。同时,通过小组游戏,帮助孩子们对敏感内容进行脱敏处理,对场景进行模拟及角色互换,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加清楚的认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防范意识、安全意识、防范技能等均得到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课程结束后,有孩子主动找到讲师交流,自己曾经遇到过可能是性侵害的可疑情况。此类情况已委婉与其家庭沟通,将视情况进一步列为个案予以跟进。
(二)家长方面
在家长方面,项目实施效果喜忧参半。该村留守儿童居多,监护人主要构成大多是祖辈,隔代抚养情况比较普遍。老人对此类课堂一开始持排斥或者疑惑态度居多,在项目实施后,再次与家长交流此类情况有一定转变,但完全取得家长信任与支持还需一定时间,但总体上家长的防范意识有一定改观与提升(例如对待男童的态度,从基本毫不担心到认同增加防范意识)。
(三)学校方面
在学校层面,通过项目的开展填补了乡村儿童保护领域的空白。项目开展前,老师们还抱有迟疑态度,担心对孩子们引导不利,也担心家长意见较大。校方表示项目实施后,将父母不敢讲、老师不好讲的防性侵知识通过有效适合的手段传递给了村里的儿童,补充了学校和家庭在儿童性教育方面的不足。
五、建议与思考
该项目在P村已经顺利结束,此次在农村开展儿童保护预防性侵害的尝试有一定的成果与收获,尝试做如下建议,以期形成良好的氛围与机制。
(一)建立健全儿童保护系统
儿童保护从来都不只是个人或是家庭的单独责任,应该是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去完成的一项任务。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应该建立一整套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维度儿童保护系统,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逐层履行相关保护职能。[3]
在家庭方面,要注重提升性教育意识与儿童保护意识,不可将性教育或预防教育的功能与责任全都寄托于学校和老师身上或期待孩子“长大就懂了”。尤其在留守儿童居多的乡村,监护人不应该只有孩子身边的祖辈,更应让孩子的父母参与到儿童性教育及预防教育中。应增加孩子与同性监护人(父母及直接照顾者)的深入交流,关注生活中孩子们好奇的问题。社工还可延续项目,介入重点家庭开展家庭社会工作,协助做好家庭性教育及预防教育,提升防范意识,降低侵害风险。学校方面,应营造儿童保护的常态氛围,开展合适的性教育及预防教育,引导正确价值观主流。诸多研究表明,性侵害案件是可以通过教育预防提升认知有效避免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咨询室,老师们轮流担任咨询老师,为孩子们提供可倾诉渠道;建议老师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留心孩子们的动态,尤其是一些可能高危的家庭(如监护人监护不力等),善于发现问题,及时与孩子家庭沟通,在让孩子遇到情况时即可懂得求助,获得支持。
(二)协助落实强制报告机制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增加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发现人有法定报警的义务。[4]传统的儿童性侵害案件主要依靠儿童自我、同辈群体、父母或照顾者以及专业人员的观察与发现。现代社会性侵案件问题多样化,应集合多方机构或者人员及时关注发声,如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等,发现儿童遭受或疑似遭侵害时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强制报告机制在预防或处理儿童性侵害过程中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保护儿童远离侵害,降低儿童性侵犯罪率及提高破案率。应在当地宣传及强制报告机制有关内容,提升各机构和村民的法治意识,促使报告人感到“有法可依”,营造安全有效的社会环境。[5]
(三)探索项目效果延续方式
为保证儿童保护项目效果的有效性和延续性,建议在项目即将结束时,吸纳当地教师为志愿者讲师,一对一帮扶传授相关知识与授课经验,并鼓励参加“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考核,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学习适当的工作手法与理念,确保项目效果不是“昙花一现”,不会因为某项目结束而终结,而是能在项目完结后将余热继续保持。如此让儿童防性侵预防教育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儿童保护能辐射到更多领域,为乡村里的儿童营造一个安全、温暖、健康且友好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