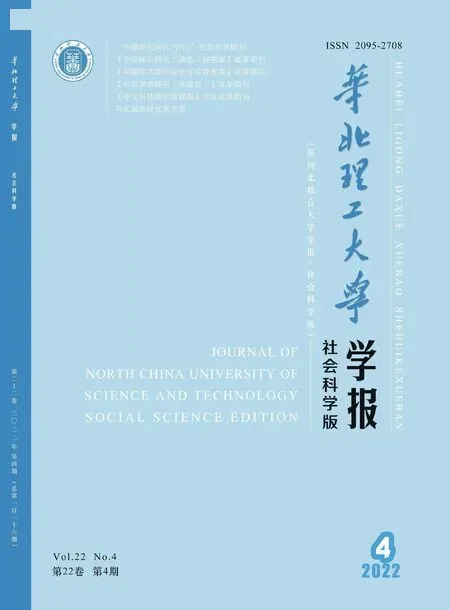“识同”与“寻异”:浅谈清东陵文化发掘与保护的路径
高馨,黄文学,范玉双,何小凤
(1.华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唐山063210;2.中共唐山市委党校,河北 唐山 063000;3.华北理工大学 图书馆,河北 唐山 063210)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变化的历程,但大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探讨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进而由文化到民族,通过对文化趋同性与特异性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提供参考。本文围绕清东陵的文化发掘与保护,通过对这一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化较为突出的民族在文化趋同性与特异性上的分析,探寻少数民族文化发掘与保护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并进而探讨合适的实施路径。
一、民族与民族文化:从“满人汉化”到满汉文化的融合
做好清东陵的文化发掘与保护,首先需要了解满族自身的特点,才能进而了解满族的文化。满族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民族。满族从其来源组成到政治影响方面都具备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作为一个曾经建立过近三百年封建王朝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特点以及文化的发展与改变都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这样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族群的大小而是文化的独立性存在,在与先进而庞大的汉文化的对抗和融合的矛盾发展中,最终实现文化的汇通和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了解满族,就必须从“满人汉化”谈起。
(一)满族从来源组成到政治影响都有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具备的特殊性
从来源和组成上来说,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满族的名称来源于满洲,现代意义上的满洲具有地理名词和民族名词的双重意义,但在满清早期,满洲是部族名称而不是地名,对此问题,傅朗云、孙静等人都曾从“女真”到“满洲”的演变进行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部分学者将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例如王景义在《关于满族形成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认为,“满族是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为主,吸收其他女真部族和其他民族部分成员而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1],这里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苑杰在《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在1635年满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称谓时,满族即是一个由女真人、汉族、蒙古族以及朝鲜族等东北民族共同组成的复合体,其中作为满族主体的女真人虽然不是金代高度汉化的女真人的直系后裔,但也是在‘东北边境上’‘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2]正是因为满族的特殊性,因此在文化构成以及民族发展中满族与汉族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处于族群独立性的需要,满族拥有自己的文字以及很具特殊的文化习俗,但不可避免的从一开始就已经打上汉文化的烙印。
满族的发展深受政治的影响,通过民族歧视政策保持满族的独立性。满族作为一个曾经建立三百年王朝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产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满族在近三百年的统治中,一直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坚持以满洲八旗作为其统治的支柱,在全国划分旗藉、民籍,并在全国要地建立满城,带有很强的种族隔离色彩,并在初期通过废除中国传统的衣冠礼仪发型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具有汉文化特征的东西以稳固其统治。对于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姑且不谈论其所具有的非正义性,而仅仅从其弱文化的自身保护来说,确实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就算是这种保护,也最终没有改变其被融合的命运。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民族歧视政策成为发起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反清排满”的口号在革命派的鼓吹下曾经产生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后,很多满族人不得不隐姓埋名、隐匿族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并给民族识别带来困难。
(二)学术界关于满族“汉化”与“非汉化”的争论
“满人汉化”曾深受学界关注。学界基本认为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经开始接触并学习汉文化,并重用汉族官僚,建立起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入关以后,更是对汉文化愈加倚重,大力提倡和模仿。清王朝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满族汉化的历史,到了近代,满族已经基本上完成被同化的历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很多,不再一一赘述。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来寻找“满人汉化”的依据。例如王海燕在《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一文中,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传统的汉化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王海燕认为:“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3]
罗友芝则是“非汉化”观点的代表。她反对何炳棣的观点,否认“汉化论”和“汉族中心论”,强调汉族帝国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何炳棣则对罗友芝的非汉化论进行了尖锐的批驳,认为,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清朝之所以能够统治三百年之久,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欲统治中国,首先应具备统治中国芸芸众生的能力。中国人口在1650年—1800年间剧增,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满族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就在于其运用了汉族传统的政策和制度。”[4]可见两者关于满人“汉化”和“非汉化”问题所持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也是大多数学者所持的两种基本观点。
另外,还有学者从汉化的主动与被动方面进行探讨。其中,郭成康在《也谈满人汉化》一文中,在分析满人汉化的过程时,认为满人汉化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时自觉地进行抵制,“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5]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欧立德认为用“汉化”没有用“同化”更为准确。他认为何炳棣和罗友芝的观点都具有极端性,对于汉化问题应该将“汉化”与“非汉化”折中理解。他说:“有些人认为满族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们完全汉化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满族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避免了汉化。我觉得折中理解可能更为合理。”[6]
简而言之,“汉化”、“非汉化”甚而“同化”均属于目前学术界的重要观点。文化的形成则更多是互鉴互生的过程,可能因影响力不同从而各自所受对方的影响大小不同,但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对于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则更应该成为学界探讨的中心所在。
(三)满汉文化是一个互融发展的过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正如前文所述,在满清入关之前,处于对汉文化的警惕,为保持满族文化的独立性,对于汉族文化是吸收但拒融。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采取的方式则是将满族文化置于文化的顶端,并刻意凌驾于汉文化之上。栾凡的《清前期满族民族意识与满汉文化交融》一文就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态度与以往少数民族政权具有很大不同,既不是吸收,也不是破坏,而是融合后的君临。常书红在《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一文中,以北京地区为研究区域,从聚居、婚姻、司法、教育等方面来论述清代北京地区的旗民一体化的过程,展示满汉文化的交融情况。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大多侧重于作为统治阶级满族怎样学习汉文化,而忽视汉文化自身的特点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对满族文化产生影响时的主动性。
在这里更倾向于满汉文化融合发展的观点。文化的发展壮大是一个运动的不断融合的过程,积成春的《从乾隆时期满族文化传统的迅速转变看汉文化的影响》一文就认为满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清朝文化,认为这一文化的形成是在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满族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迅速调适、变异、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清代文化。期间,尽管乾隆帝极力想保留满族旧俗,但在满汉文化交融的强大洪流面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先锋。”[7]正如现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停留在被动的保护层面,这种被动式保护往往造成文化的生命力逐渐衰弱。事实上,一种文化要得到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吸收外来的新鲜血液,满族文化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满汉文化的融合其实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互促发展模式。这一观点的实物性证据非常之多,比如清东陵的布局、祭祀风俗等都是这一融合的力证。
二、“识同”:认清满汉文化的趋同性
少数民族的特点在于人口稀少以及文化相对单一,因此要保持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更加注重文化特色的保留。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汉文化的兼容性面前往往很难一直保持自身特点。特别是曾经作为统治者的满族,要延续和发展自己所创建的王朝,三百年的王朝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在保持特殊性与不得不融入汉文化的矛盾挣扎中发展的历程。
(一)满汉文化的趋同性首先开始于清代前期满族特有的民族风俗在汉文化面前展现的落后性使之难以避免淘汰的命运
风俗是文化的载体,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征的具显,往往受到政治、历史、经济、自然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满族传统风俗的形成就经历了这一过程。同时,满族文化在发展中还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并通过风俗活动展现出来。总的来讲,满族文化具备的更多的是草原文化的特征,这使得满族在进入中原后,这些风俗就变得不合时宜起来。特别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其最初的文化特征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多的落后性,裁汰旧民俗,发展新民俗是文化革新的要求,并成为了满族文化与汉文化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
满洲形成初期,因其还带有很多奴隶制度的特征,因此很多的民族风俗都较为原始。例如在婚姻风俗上,皇太极向汉族、朝鲜等文化先进民族学习,认为“夫明与朝鲜皆礼仪之邦,故同族从不婚娶。彼亦谓既为人类,若同族嫁娶,与禽兽何异,是以禁止耳。”[8]于是下令禁止原风俗中存在的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等行为,并为此设立了刑罚措施。再如,满族的丧葬风俗还保留着人殉制度,这是早已被汉文化淘汰的奴隶制时代的陋俗。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甚至入关以后多尔衮等人死去时还都采用了这一制度。直到顺治皇帝曾经颁布禁止八旗以奴仆殉葬的禁令,康熙皇帝亦曾下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这一落后的丧葬制度才逐渐废除。
社会风俗是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属于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表现。满族在发展过程中裁汰落后的社会风俗的过程其实是剥离其原有民族特征的过程。随着移风易俗的不断进行,满族某些特有的民族表征削弱,汉文化表征逐渐增强,社会风俗中具有积极意义的表征逐渐与其不断增强的汉文化表征结合起来,加快了满汉文化的趋同性。
(二)汉族宗族文化对于满族的影响——文化礼俗趋同性增强
清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对宗族组织积极倡导和维护,满族各族群都受到这一影响。宗族文化的核心在于族长制,族长的产生与职权的行使等诸多礼俗是汉文化的重要表现,满族在发展中逐渐吸收和沿用了这一礼俗。何溥滢的《从吉林他塔拉氏看清代后期汉族宗族文化对满族的影响》一文,对吉林他塔拉氏这一满族的分支对于宗族制度的运用和沿革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认为满族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存在与汉族趋同的趋势。虽然在趋同性的过程中,满族也在竭力保持其特殊性,尤其是民族意识方面仍很强烈,特别是以“保姓”作为最紧迫的事务,例如在修家谱时,修的是“他塔拉氏”家谱,而不是修采用汉姓唐的“唐氏”家谱;并且在家谱的内容增设《移驻篇》,这些都是致力于显示与汉族家谱不同的表现。
修谱的活动是深受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影响的一种行为,但更是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外显为宗族意识的群体认同行为,因此被广泛的运用。族谱反映的是家族乃至族群共同体层次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发挥功能的层面主要还是家族或宗族而非民族。也正因如此,族谱的修纂并没有起到所谓保护满族民族意识的意义,反而因为对修谱这一具有浓厚汉族文化特质行为的借用,对于其汉化反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北京旗人的变迁对挖掘清东陵满汉文化趋同性的启示
北京旗人的变迁是文化趋同性的明证。定宜庄先生曾经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来对满族史进行研究。她将清代旗人按照当时的八旗分布格局的不同分为三类,即北京旗人、东北旗人和各省驻防旗人。她经过研究认为生活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生活经历下的旗人,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强弱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清朝入关后,将北京内城的汉官与商民人等迁移到南城,从此形成清代京城独特的满、汉分居格局,旗人与非旗人畛域明显,也就形成特殊的文化圈层。清朝灭亡以后,经过百年变迁,北京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旗人原来的生活圈子早被打破,也使得作为满族典型群体的旗人所独有的民族性在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中逐渐淡化。虽然还能够看到满族民族特殊性的影子,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影子必然日益消减。
清东陵作为清朝规模最大的陵寝建筑之一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是文化趋同性的生动载体。在建筑形制方面,清东陵与明十三陵具有很多的类似性,建筑的样式、规格,甚而雕刻、雕塑等都有充分的体现。如何发现这种趋同性发展的过程,在此以龙为例,作一简要的介绍。龙在中国政治文化和民间文化中一直占据主角的位置,对于龙的认同和崇拜是文化趋同性的重要表现符号,也是研究文化趋同性的重要途径。清东陵石雕艺术作品中龙雕刻就是文化趋同性的明证。据尹庆林在其《浅析清东陵石雕艺术的文化包容》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东陵各类龙雕刻达2587条。对此更期盼的是看到这一统计的更为详细的部分,也就是每座皇陵龙的统计。正如定宜庄将旗人分为北京旗人等三类一样,对于清东陵的文化符号也应该进行分类,诸如龙等文化符号应该如北京旗人一样,展示了满族文化在发展中对于汉文化的吸收过程,这一过程也就如北京旗人一样,我们应该展开对清东陵历代陵墓文化符号的整理与研究,从中窥视满族文化变迁的历程,特别是趋同性的过程。
三、“寻异”:从梳理满族民族意识开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趋同性的担忧愈加强烈。怎样才能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异”,成为学界普遍思考的问题。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借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多。”也就是说,挖掘各民族的文化优势进而发展民族特点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持独立性的应有之路。如何保持这一个“异”,其中,对于民族意识的认识,进行民族识别,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起到这一作用。民族意识的载体有很多,其中历史遗存就是较为重要和显著的一部分。清东陵作为满族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必然要肩负起保持满族文化独立性的历史责任。开展清东陵的文化发掘与保护,展对满族民族意识的研究和梳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真正做到在文化发掘和保护过程中有的放矢。
(一)认清并梳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前提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核心源泉,因此要拯救民族文化,首先必须了解并剖析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并进而开展民族识别,拓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路径。认清民族意识的特点是开展民族文化鉴别和研究民族文化发展历程的基础。首先,民族意识的呈现包括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等诸多的文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并深刻的影响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等。其次,作为民族的引领者或者上层阶级,往往代表着民族意识的总体方向。另外,民族意识的发展具有延展性,是不断发展的,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在不断的调整,这也是民族意识极为重要的一点。
作为一个建立三百年王朝的民族,满族的民族意识不仅仅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还表现在对政权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认同和依附。因此学界在研究满族文化时将满族所独有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和数百年清朝政权以及不断发展的各类制度结合起来,以剖析梳理对于满族和满族文化的认识,将其与汉文化的趋同性和自身特异性充分发掘出来,展现出来。例如,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就对于满洲一词从满族氏族组织的形成角度展开剖析,他在《满族的氏族组织——满族社会组织研究》一文中认为“满洲”一词其实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复合体的名称。”[2]
(二)充分认识八旗意识作为满族民族意识的主体最能体现满族文化的“异”
八旗意识是在满族入关以后逐渐形成的。满族作为居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在面对经历数千年民族融合,包容性和坚韧性无比强大,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汉族文化时,为了保持其独立性,满族原有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逐步过渡为满族的民族意识。这就使得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本身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更多的一致性。同时围绕满八旗为核心的满蒙汉八旗三层结构的形成,在满族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受到内核化保护,加快了满族意识的形成。例如,汉八旗作为八旗制度的最外围,与满族的共聚生活的过程中相互认同的心理逐渐形成,并受到的满族民族意识的影响,因此在其意识中相对于关内的汉族,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就要弱化的多,心理意识的归属也要弱的多。
八旗意识是满族民族自信的充分体现,八旗也就成为满族文化的鲜明符号。这首先得益于满族政治上的不断成功,以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千万平方公里疆域的统治者,在这一过程中满族的民族自信得到充分发展。而能够以少数民族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达到顶峰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则使得这一民族自信达到顶峰。正如张佳生在《满族的八旗意识与国家意识——清代满族民族意识的形成发展(续)》一文中所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满族不仅从未将自己视为中国之外的‘殖民者’,也从未将自己视为中华之外的异族。”[9]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康熙和乾隆这几位在清王朝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几位皇帝,也是在他们的统治下,满族的民族自信得以充分展现。开展清东陵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就必须了解这一问题,从而围绕八旗意识扩而为民族意识的过程开展满族文化的研究。
(三)驻防旗人对研究清东陵满族文化的“异”的启示
正如北京旗人随着满汉界限的打破,其文化发展以趋同性为主,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各省的驻防旗人则更多的表现出文化发展的特异性。驻防旗人则因为所在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口流动相对较小,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反而使得他们保留了比其他地方的满族旗人更多的满族文化特性,并通过风俗习惯彰显出来。定宜庄先生在进行实地考察时曾经对呼和浩特的绥远驻防城的居民进行过访问,“今天呼和浩特的绥远驻防城,是建在旧有的归化城附近的,生活在这里的八旗官兵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许多当年从京城带去的习惯,特别是语言。我访问的两个老人都操一口地道的京腔。对我说话时也都称‘咱们’,‘咱们的人’,‘咱们满洲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10]
通过对清东陵特殊群体守陵人的考察,发现这一群体与驻防旗人颇有类似之处,特别是因为其大多因为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所从事的主要事务是看护陵墓,并筹备祭祀礼仪等,使得满族文化的特异性在这一群体中充分彰显出来。清东陵重视满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比如祭祀文化、饮食文化等不仅研究的人较多,更形成清东陵重要的旅游看点。但清东陵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不仅是将其外显并传扬,更应该挖掘其所体现的民族意识,研究其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将满族文化的独特属性彰显出来,让人们更深的认识满族文化,保护满族文化。
四、结语
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往往是先进文化在对落后文化的融合中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过程通过趋同化实现,伴随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削弱乃至湮灭。建国初开展民族识别对满族等少数民族起到的是外显性保护,但无法改变内涵的变迁。因此如何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到80年代开始的民族身份的恢复和改正,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的民族身份确认体系。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的是社会、风俗、文化等各方面的趋同化和一体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利益驱动面前民族意识的逐渐削弱,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再是基于民族文化等特征,诸如此类问题,成为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化特征的迫在眉睫的重要挑战。
清东陵作为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其承载的满族文化数百年的变迁,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趋同性的研究,能够更为清晰的探析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靠拢乃至同化的原因,考察文化融合过程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路径。通过特异性的研究,则能够更好的挖掘满族文化的独特特征,而对于满族民族意识的研究特别是开展清东陵文化与满族民族意识关系的研究,无疑将推动清东陵文化研究的深化并拓展研究的范围。因此,清东陵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应该注重“同”和“异”,将清东陵打造成少数民族文化挖掘和保护的基地,以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特别是文化多样性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