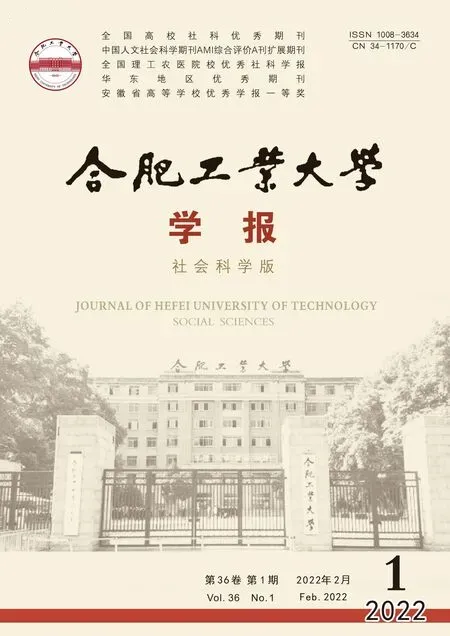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诗文观
李双扬, 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儒林外史》历来被认作中国古代史上讽刺小说之巅峰,因而研究《儒林外史》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社会的形态与世人思想之状态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同样,小说也是了解吴敬梓的社会人生及其文学创作观的重要依据。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等均有着深入研究,如吴敬梓家族历史考证,这部小说对科举的批判、文人形象分析等,而鲜有人对这部小说中吴敬梓表露出来的诗文创作观进行研究。
一、诗文并重
受明清科举政策的影响,当时大部分文人都重文轻诗。推崇八股、轻贱诗赋,是《儒林外史》中诸多热衷功名富贵之文人的共识。如书中第三回中描写的童生与周学道的一段对话,就透露了这一思想:
“童生诗词歌赋都会……”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1]18
何谓“正务”?何谓“杂览”?在周学道眼中,“天子”所重视者为“正务”,反之不重视者便是“杂览”。童生精通诗词歌赋不但不被褒奖,反而被视为“务名而不务实”的行为。可见在当朝大多数读书人眼中诗词歌赋的地位远比不上文章写作。文章与诗赋的地位差别由此可见。
又小说第十一回中写道:“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1]74凡八股文做之极者,诗赋便能游刃有余;若八股文不规范,则诗赋也都会做成不入流之俗物。纵观古今之论,这话显然狭隘之至。文章与诗赋虽同为文字,但写作方式、技巧、内容、风格却大相径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气为主”[2]435等观点,阐明文章在内容上主要围绕着国家大事而议,而文章风格更是应该根据作者的才情、本质而定;然其却认为“诗赋欲丽”,与典雅正经的文章相比,绮丽才是诗赋之特点。陆机在《文赋》中更是对十种不同文体的风格与作用进行了详细划分。虽然不同的文学家对不同文体各有看法,但却鲜有人表明著文若好,则“要诗就诗,要赋就赋”。这些皆足以说明文章做之优者不可等同于诗赋做之妙。然而在明清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世人眼中,文章就是比诗词歌赋位高一等,并且做文还有其特定的一套“规章制度”,若是不按规矩行出之文便皆是“野”“邪”之物。虽然这是对八股文的盲目崇拜与过分吹嘘,由此却能看出八股文地位的正统性与不可动摇性,诗词歌赋的地位也可见一斑。《儒林外史》中不少读书人均持这样的看法:诗赋与文章存有高低贵贱之分。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其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辞采文笔、人物塑造,更在于其思想观念的超前性、深刻性。与明清普通文人不同,这种过分抬高八股而贬低诗赋创作的行为恰是吴敬梓极力反对的。吴敬梓借小说中王冕、杜少卿等淡泊功名富贵的文人表达出诗词歌赋不是“杂学”,是同样值得被人重视和学习的观点。如小说第一回就批判以文章取仕之法定的不好。“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7《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3]《论语·述而》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4]“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作者借王冕之口明确提出了八股制之害。在吴敬梓眼中,八股会让考学者模糊自身品质与初心,而将写作文章过分功利化。这既突出了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想要批判世人被荣华蒙蔽双眼的主题,同时又阐明了他对八股弊病透彻的理解。
又如小说第十七回景兰江与匡超人的一段对话,从另一个层面表露了对诗文的肯定:“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不瞒匡先生你说,小弟贱号叫做景兰江,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1]118短短的一句从侧面反映出两个事实:首先,在杭州城会做八股者并不是成为名士的绝对指标;其次,“各处诗选”透露出诗选刊物在杭州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读物。杭州作为南方最富庶、发达的城市之一,它代表着思想的超前性、眼界的宽阔性与文化的多元、包容性。而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对诗赋地位的一份肯定,文章不再具有唯一不可取代性,诗赋也能被社会名士所认可。短短一句话虽不能断言吴敬梓对八股写作持反对态度,但这确实是对文章独尊地位的一次冲击。
除此之外,一直被后人认为是吴敬梓原型的书中人物杜少卿也在文中发表了一些他关于诗词歌赋的看法。如杜少卿与马二先生、迟衡山等人在家中闲谈事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篇……。”“‘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只是说他‘不淫’,还有甚么别的说?”迟衡山道:“便是,也还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1]233
杜少卿说到的《凯风》为《诗经》里的一首小诗。虽然小说并未明确提及杜少卿对诗词歌赋的态度,但从字里行间可以判断他对《诗经》之所思、所感。除此之外,杜少卿还涉猎与《诗经》相关的“诸儒之说”,甚至对此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可见其对《诗经》之重视与专研。相比之下,当提到《诗经》中《女曰鸡鸣》篇时,马二先生与迟衡山却表示“不能得其深味”,更有甚者还予以轻视。传统儒生对诗赋的陌生与偏见也由此可见,这也恰恰反衬出杜少卿于诗赋之精通。
以上种种都表明吴敬梓对诗赋的态度是肯定的,而现实中的吴敬梓也是这样做的。吴敬梓自从决定放弃“博学鸿词”后便潜心诗文与小说的创作,用他的后半生写出了《文木山房诗文集》《文木山房诗说》《儒林外史》等优秀作品。
尽管时人皆认为八股文的写作才是正统,而诗赋仅为杂学,但在吴敬梓的审美认知中诗赋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不应被忽视轻贱。独尊文章的社会状态在这个不拘于时的人眼中是一种畸形的存在,应被批判和纠正。这是吴敬梓为诗词正名所发起的呼吁,也是对当时八股文极端之风的有力批驳。
二、文章创作:“才”不可疏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仅只表达了其诗文并重的态度,同时也阐释了他对文章创作中“才”与“法”关系的理解。
明清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文章写作盛行于世,但朝廷对科举文章的写作内容与格式均有着严格的规范,考生不可自由发挥,不能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华。慢慢地,儒生的文章便趋于格式化、制度化,“创新”一词离文章写作也就愈发遥远了。针对此现象,吴敬梓提出了与时下“格格不入”的见解,即“才”不可疏,为毫无生机的文坛带来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小说里吴敬梓叙述了新旧两派对于文章写作的不同看法,他们在“才气与法则谁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旧派(1)为便于行文,本文将与吴敬梓有相似文章观的人物称为“新派”,而将那些坚持“法”重于“才”的称为“旧派”。坚持传统观点,认为理法重于才气,且理法为本,不可或缺。小说第六回中,严贡生道:这倒不然。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就如我这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1]40又有第七回梅玖言:“先生最喜欢我的,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些不合规矩,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一丝也不得差。”[1]48尽管两段文字都提及“才气”二字,但显然“有才气”在如上的语境中并不算得上是一种褒奖。相反,“才气”永远是与“法则”“规矩”捆绑在一起的,它在一篇文章中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罢了。而文中的关键词“理法”才是真正决定文章优劣的核心,它甚至直接决定着科举的成败。时人对才气的疏忽和对法则的重视都在这短短的对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小说第十三回明确提到了社会公认好文章的写作标准:
公孙问道:“尊选程墨,是那一种文章为主?”马二先生道:“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1]90
文中公孙先生与马二先生的对话主要围绕当朝科举之文进行探讨。其中点出文章写作的三大要点:一是以“不变之理法”为主;二是不带注疏气;三是切忌词赋气。至于对“才气”的理解则以一句“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匆匆略过。“不过”一词让“文采”变得无足轻重,彻底抹杀它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性。朝廷都对此如此轻视,更何况参加科举的儒生们,这也是为何“才气”之学往往被社会所忽略的原因。
小说第十八回虽然同样强调了理法、法则的重要性,但它还另外补充提到了读书人写文之作用——“代圣贤立言”,解释了读书人不可“随手乱做”文章的原因。卫先生道:“……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1]125明清科举规定用八股作文,题目出于《四书》《五经》,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决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故称“代圣贤立言”。文章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与规范不仅是因为它是朝廷选拔官员之工具,还因为它也代表着对古代圣贤之尊敬。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若想精通八股,就必须隐藏自己的思想,将圣贤所思了然于胸。如此一来,八股文无疑将大众思想个性化抹去,致使人人都变成了趋同的统一体,八股的弊端也由此显现出来。
这一段话既提出了文章写作之准则,也向读者说明了八股文对文章理法的重视程度和重视原因。虽然旧派儒生从未否认一等文章需要一定才气,但他们却将才气视作锦上添花之物,而将理法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上。
与之相对,新派观点则灵活变通,认为一篇文章尽管理法有缺,但若才气突出,同样值得肯定。他们对理法之地位既未如旧派一般刻意强调,同时又对才气出众的文章表示赞许赏识。《儒林外史》第六回与十六回述:“因汤父母前次入帘,都取中了些‘陈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时目,所以这次不曾来聘。今科十几位帘官,都是少年进士,专取有才气的文章。”[1]40“‘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虽略有未清,才气是极好的。”[1]114此二段不再将“理法”放于首位强调,反而大肆宣扬了“才气”对文章的写作作用。前段讲述了因旧派官员录取了些“陈猫古老鼠”的文章而被撤下考官一职,换成了新进的几位“少年进士”的事例。这些新晋进士冲破旧制,“专取有才气的文章”。此举是对历来文章评判一直以“理法”为核心准则的重大突破。虽然王仁在发表完观点后即刻被严贡生所反驳,但通过作者对严贡生愚昧腐朽儒生形象的塑造,读者也能知道吴敬梓对此类一成不变、毫无新意的文章所持的批判态度。他的文章写作理念也正是透过这些正面人物话语所传递。
另一边,学道则发表了“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的言论。他认为判断文章的优劣先不看作者的文辞表达,而是注重写作者的内在品行。这一点,是对后晋赵莹思想的承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5]赵莹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心胸,培养自己对社会、人生的基本价值观,然后才能学艺。这正是吴敬梓对儒家注重人的品质塑造,重视人伦道德的继承,也是对理法不是评判文章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强调。因此,即使学道在评价匡迥的文字时做出了“理法略有未清”的批评,却依旧高度肯定了他的才华横溢。此种现象表明,评论者评判文章不再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固定的文法规范,而是站在文学创造主体的角度,用长远发展的角度考察此人是否具有天分、有灵性,是否适合文章的创作。而这样的眼光于当时那个社会环境而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新派对于文章的写作强调的是才气的重要性,旧派强调的是理法的不可或缺性。一为创新,一为守旧;一重内在,一重外在。《儒林外史》中新派人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吴敬梓本人的审美倾向。虽说“重才轻理”早在《文心雕龙》等批评学著作中就有过系统描述,但置于明清以“理”为天的时期,这一观点的提出仍然是值得颂扬的。
两种对立观点的表现一方面是对死气沉沉的科举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提出了他的文章评判标准,以此来传达他理想中的科举选拔模式。
除了谈到文章才气与法则的问题,吴敬梓还提到了做文章的人应当拥有优良品行的理念。他认为一个能担起国家重任之人,不仅需要有出色的文章写作功底,还要有良好品行,可以做到文如其人。如差官在送给杜少卿的文书中写道:“巡抚部院李,为举荐贤才事……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品行端醇,文章典雅。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引见擢用。”[1]226文中的杜仪即为杜少卿。杜少卿成为县儒学教官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其“文章典雅”,还因他“品行端醇”。只有这样品学兼优者才能担此职责。“巡抚”作为“钦奉圣旨”挑选官员,代表着当朝圣上的旨意,因而他对杜少卿品行的肯定也直接反映出清代科举选用制度的一些标准。另外,虞华轩在与他人讨论儿子师从何人的问题上也涉及相关观点:“论余大先生的举业……却也不是中和之业。”虞华轩道:“小儿也还早哩,如今请余大表兄,不过叫学他些立品,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1]315当他人“好心”提出建议,认为师从余大先生之学并不利于科举之业时,虞华轩却不以为意。他反驳称“叫学他些立品,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特地强调了品行端正的重要性。
从杜少卿到虞华轩,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情感态度皆是赞扬的。而杜少卿更是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吴敬梓的生活原型,所以小说中作者对读书人品行的论调也能间接代表着他自己的思想。虽然当时所有想考中科举进士的儒生皆会读书作文,每个人也都拥有自己的个性理念与思考,但为了迎合当朝的要求,难免思想被束缚、理念模式化。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与世同的文章观身后是他追求思想自由、勇于冲破世俗的一种表现。
三、诗歌创作:情由心生
除了文章,吴敬梓对诗赋也有自己的认识,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诗歌的热爱。在现实生活中,吴敬梓就对诗赋表现出了高于常人的喜爱之情。当时大多数人的眼光都只局限在文章的撰写上,常常将诗词忽略。但他却不停坚持着诗词的创作,最终耗费后半生的时间完成了《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与《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其实吴敬梓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词作品是他由少年意气到自觉放弃科举考试乃至‘功名富贵’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6]38“其诗词还有对亲情和友情的书写,对内心复杂的‘家园’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感受,因而有其文学价值。”[6]38这些独特的经历也是他与众不同、不流于世俗的重要原因。尽管在小说中吴敬梓并未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诗心、诗才,但作为一名诗人,他却依旧抑制不住自己的写作欲望,表达对诗歌创作的观念看法。《儒林外史》中针对诗歌写作提出了一些建议,详细阐述了吴敬梓的诗歌创作观。如第二十九回杜慎卿对萧金铉的诗做出了如下点评:
杜慎卿看了,点一点头道:“诗句是清新的。”……“如不见怪,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诗以气体为主,如尊作这两句:‘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岂非加意做出来的?但上一句诗,只要添一个字,‘问桃花何苦红如此’,便是《贺新凉》中间一句好词,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下面又强对了一句,便觉索然了。”……杜慎卿道:“……我也曾见过他的诗,才情是有些的。”[1]199
这段对话中杜慎卿一共表达了三点作诗要求:一是诗句要清新;二是诗以气体为主;三是诗应有才情。其中,上述之语大部分都围绕着“诗以气体为主”这一观点展开论述。那何谓“气体”呢?对此前人早已做出了相关的论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435甚至还用音乐举例以便更好诠释:“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435虽然这是对文章中“气体”的解释,但是能看出曹丕认为“气”“体”体现出的是一个人的个人风格,由天分素养所致。而杜慎卿所解释的“非加意做出”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他所举之例,每首诗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整首诗的“气”不可为了用词工整而强行对仗,而应当从心出发,因情而作,并一以贯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景物描摹与情感抒发的高度和谐统一,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
再则,杜慎卿还说到了好的诗句应当是“清新”、有“才情”的。“清新”在此可理解为有新意、不落俗套。而“才情”可拿来与文章写作时的“才气”相对比。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刘勰就此对历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论述,并提出了“褒贬于才略”的论言。“才情”与“才气”间虽仅差一字,但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才情”强调“情”字,指的是感情、情调、情绪。诗人将个人之情抒发于诗句中,再通过文字这个媒介传递给读者,让读者为情所动,达到用最简短的文字传递出最真挚的情感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就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的见解;刘勰则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8]。诗词本就源自人最真挚的情感,同时又因人的感情而抒发,可见“情”对于诗之重要程度。而“才气”重在“气”字,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述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可见,“气”乃文人自身之个性,不同的人会写出不同脾性文字,既不能用外力强做改变,也不会因为血缘而遗传,此乃天分。做文章的目的不如写诗赋一般是为了与读者共情,而是为了展现作家之风骨,显现作者之才华。吴敬梓注意到了诗文之别,同时能够清楚地分析差别之处,仅用一字之差就表现出来。他对文体的领悟能力和炼字能力都证明着他的文学素养之高超。虽然他并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在其小说和诗集中都渗透着或多或少的个人见解。
另外,小说于第二十九回还补充了杜慎卿对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杜慎卿笑道:“先生,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1]200明清时期正值诗社盛行,对此,谢国桢先生曾谈到:“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9]根据对话得知,“即席分韵”为当时诗社流行的一种普遍的作诗方式。可杜慎卿却认为循规蹈矩地作诗是一种落俗的表现,诗歌应当是大家自由发挥才情的途径,而不应有模式的限制,所以“还是清谈为妙”。少一些形式上的规矩,多一些内容上的创新,这便是杜慎卿欲表达之意,也是吴敬梓欲述之言。
四、结 语
对于明清时期处于热议中心的文章与诗词两类文体,吴敬梓借助《儒林外史》表达了要诗文并重、不可厚此薄彼的态度。《儒林外史》一方面从个人角度出发,投射出作者独特的诗文个性与观念;另一面则站在社会的高度,对个人思想的独立、个性的解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追求是多元化的产物,是思想碰撞后的成果。吴敬梓能在地位“低贱”的“小说”中为“诗词”正名,这种行为体现了他对文学观念的思考和对文体平等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