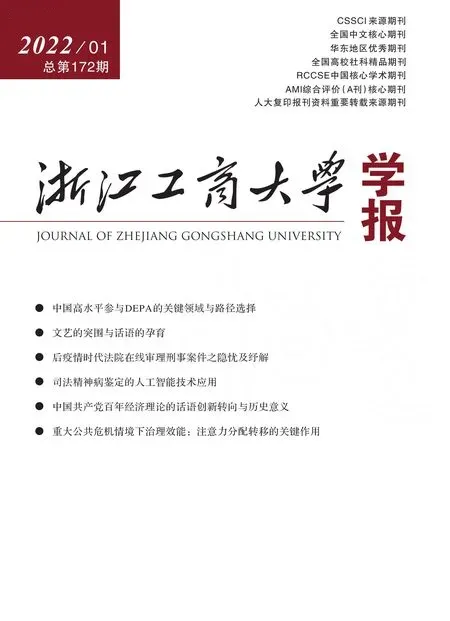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评点者从事小说评点,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小说“以史为鉴”的取向,让其深受史传叙事和史传精神的影响。小说评点在这种影响中,很重视史传叙事的“春秋笔法”及其对所叙事件和人物的伦理评价,导致小说评点中也有一种慕史情结,用史传叙事中所惯用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德目作为小说人物和事件的判断标准,也作为解读小说主旨的伦理依据。同时,“知人论世”方法对小说研究的影响,让评点者很自然地以外在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衡量小说内容,也很自然地以现实社会中儒家的伦理规范来审视小说的伦理寓意。这意味着,小说评点不仅与评点对象有关,也与评点环境有关。小说评点的慕史情结和“知人论世”的研究路径,使得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一般是用儒家伦理德目作为规范来进行伦理说教。虽然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大致不脱离说教宗旨,但由于评点的具体环境不同,其伦理意图的形成又不尽相同。伦理意图和伦理意图如何形成固然关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两回事。学界对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探讨较多,但伦理意图究竟如何形成,研究还不充分。由于小说评点在明代开始兴盛,文章集中论述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就明代小说评点而言,其伦理意图的形成,既有其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土壤,更依赖于具体的文本路径。
一、 评点者伦理意图的历史渊源
谈到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就需要从评点如何形成说起。有论者指出:叙事文学评点形态的形成与经学注疏体式、选学传统和文章学传统有关[1]8-19。具体来说,经学注疏,既随文注疏,又注疏释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小说评点都有影响。选学的背后有一个取舍标准的问题,这个标准折射出选学家的价值取向,与评点者的伦理意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有些选本(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已经有总评、夹批、抹、点等诸多形式,已暗合小说评点的诸多要素。文章学的一大贡献是文法论,小说评点对文法的讲究与此不无关系。《古文关键》既是古文选本,也教人如何写古文,是文章学著作,卷首有《古文关键总论》,包括“看文字法”“论作文法”“论文字病”。“看文字法”中先是“总论”:“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然后是具体的“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2],无论是“总论”与“分论”结合的“读法”,还是“看文字法”中提及的“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对后来的小说评点影响都很大。
经学注疏、选学和文章学各有侧重,经学注疏讲究“微言大义”,侧重经学内容的伦理意义;选学以选家的价值取向作为取舍标准,对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有所关注(如《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3]);文章学讲究文法,侧重行文的形式技巧。小说评点兼采三者,既重视小说中的文法,也重视文法所蕴含的伦理内涵。《水浒传》第十三回,李贽回评云:“《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也。不妄,不妄!”[4]174侧重对形式技巧的评点;第二十四回回评云:“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4]175无意识间,已经兼评文字技巧和小说内容。最早标明“读法”的《阅东度记八法》(崇祯八年刊本)所说的“不厌伦理正道,便是忠孝传家。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5]已明确指出小说评点需要兼顾“错综铺叙”的文法和“伦理正道”的宗旨。金圣叹明亡前在《水浒传序三》中一方面指出《水浒》“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并将其和《庄子》《史记》同视为“精严”之文[6]10;另一方面指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6]9从文法出发,金圣叹删节原本;从忠恕出发,金圣叹“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6]11。这样看来,金圣叹删改评点《水浒》,其伦理目的很明确:“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6]8由于李贽和金圣叹的巨大影响,这种对文法和伦理的共同关注,自然也影响到后来的小说评点。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关注形式技巧的伦理意义就很有代表性:“《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7]17-18
二、 评点者伦理意图的现实土壤
评点的形成与经学注疏、选学和文章学有渊源,小说评点在明代的盛行,除了这些渊源,还有其现实土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人评点者乐意为之,二是书商愿意刊刻。
就第一个方面看,由于小说是小道,从事小说之人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这给小说的艺术水准和小说的流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改变小说的这种情况,文人评点者应运而起。一般认为,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眉批》,开启了小说评点的先河。到明代,小说评点蔚为大观,与评点者的喜好乃至自得其乐有关。评点者从事小说评点,一个直接的动机是认为小说评点可以宣扬自己的伦理意图。刘辰翁从事评点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身为南宋遗民,虽隐居不仕,但故国乱离之痛始终萦绕心头,在评点中“托文章以隐”“纾思寄怀”以及“留眼目开后来”[8]24-25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二是受陆象山心学影响,倡导“赤子之心”[1]24,欣赏《世说新语》对人物真性情的描绘,应该是刘辰翁青睐《世说新语》的重要原因。《世说新语眉批》由此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家国情怀,二是对人物的真性情表示赞赏。
刘辰翁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真性情的推崇,在明代文人评点者身上多有体现。李贽等人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与刘辰翁受陆象山心学影响类似。李贽以“绝假纯真”的“童心”为标准来评点小说,提倡以“最初一念之本心”[9]276来反对假道学,较之刘辰翁的“赤子之心”,更加注重人物自然性情的流露。刘辰翁的“赤子之心”是为了明自然之道,李贽则以“童心”作为衡量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将《水浒》《西厢》推为“天下至文”,高出《六经》《论语》《孟子》[9]276-277,可谓石破天惊。同时,阳明心学的兴起有一个背景,是社会上假道学流行,口头上讲程朱理学之人,却做了不少违背儒家纲常的事情,阳明心学说到底还是为了让传统的儒家观念能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深入人心,李贽虽然比较极端,为反对假道学而提倡“童心”,但同时他将“童心”和“发愤著书”联系起来。其《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9]272其《忠义水浒传叙》云:“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6]28所云“蓄积已久,势不能遏”和《水浒传》乃“发愤之所作”,意味着像《水浒传》这类小说是发愤著书的产物,而“发愤著书”又回到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意有所郁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样一个悠久的儒家传统。“发愤”而成的小说,不可“不谓之忠义”。如此,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虽从反对儒家的假道学出发,最终又回到儒家的“忠义”上来。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与李贽类似,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直呼“卓吾老子吾师乎”[10]882;冯梦龙倡导小说“主情”,同时宣称“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10]780,其《新列国志·引首》通过对历史的简单梳理,也得出“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11]4这样一个符合儒家正统观念的“胜败兴亡”的结论。
虽然具体情形和刘辰翁不同,但明代的评点者都有和刘辰翁类似的想法,既然评点可以从一己之性情出发,又能“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何乐而不为?刘辰翁在借助评点发表自己艺术见解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时代哀痛和气节,以遗教后世。刘辰翁的这一伦理意图,在明代的小说评点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大致可区分为三个层面:其一,小说不是“异端”,而是于小道中有大义。道学家将小说视为“异端”,是因为小说的虚构有别于史家的“实录”。为驳斥道学家的“异端”偏见,评点者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说明小说虚构的合理性。元人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已将实录和虚构结合起来,既指出小说“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又指出小说“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并特意表明“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12]92,既让小说立足于实录,又为小说的虚构张目。到明人那里,对小说虚构有更明显的自觉意识。谢肇淛《五杂俎》则将虚构看作是小说之必需:“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12]167-168小说既然可以虚构,违背史家的“实录”原则就是必然的,谈不上“异端”。小说既非“异端”,它的虚构就不妨碍它的伦理旨归。玉茗主人《北宋志传序》指出:虽然“杨氏之事,史鉴俱不载”,但不妨碍其与“政纪”有关:“作传者特于此畅言之,则知书有言也,言有志也,志有所寄,言有所托。故天柱地维,托寄君臣,断鳌炼石,托寄四五,不端其本而僇谪其实。”[10]974-975其二,小说代我立言。既然评点可以从一己性情出发来解读小说,小说也就可以契合我之性情,代我立言。而且,“代我立言”与春秋时的“赋诗言志”有类似之处。“赋诗言志”乃儒家传统所推崇,《汉书·艺文志》将其解释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3]。在与邻国结交时,诸侯卿大夫往往通过引《诗经》来相互交流,通过引诗,可以看出引诗之人的贤或不肖,可以看出该国风俗之盛衰。“赋诗言志”暗合后世所说的“六经注我”。既然可以“六经注我”,小说自然也可以“代我立言”。由于小说不像经书、诗文那样有崇高的地位,加上阳明心学的影响,小说评点者更容易用自己的性情来理解小说,评点中用情绪性语言来解读小说,甚至和小说形成对话。《三国演义》第八十二回,李贽“总评”云:“或曰:关兴、张苞如此英勇,皆云长、翼德虚空扶助,故有此耳。未知和尚谑之曰:‘缘何尊公不扶助公?’一座大笑。未知和尚又曰:‘想是尊公扶助公,所以公有此语。’一座又大笑。”[7]1002完全从评点者自己的性情出发,借助小说内容对现世情形加以讽刺。这种从一己性情出发来评点小说,反映出文人评点带有一定的自娱性特点,这也是文人乐意从事评点的一个原因。其三,评点可沟通作者和读者,让一般读者领会作者的伦理意图。《〈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6]31,指明评点可成为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桥梁。林梓在《于少保萃忠传》序言中指出:小说作者孙高亮“裒采演辑,凡七历寒暑,为《旌功萃忠传》,夫萃者,聚也,聚公之精神德业……其为演义,盖雅俗兼焉,庶田夫野叟,粉黛笄袆,三尺童竖,一览了了,悲泣感动,行且遍四方矣……予嘉而叙诸首简,为翼忠致孝者劝。”[14]2-7评点者指出作者为于公作传是为了“聚公之精神德业”,让其流传,自己作“叙”,既嘉奖作者,更劝勉“翼忠致孝者”,希望读者能受于公精神滋养,这也正是小说作者的希望。与林梓类似,评点者沈国元在评点中,有时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谈感想。第十八回,王竑等人因“忠义激发”,怒打奸党马顺,此处眉批“快哉快哉”[14]237,这种随文而发的感想,可以说是代一般读者发声。由于晚明心学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评点者可以借助评点来抒发乃至发泄自己的情感,所以乐于从事评点。
就第二个方面看,书商刊刻小说的直接动机是赚钱。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小说不再仅供文人士大夫来休闲,也给市民阶层提供精神愉悦,为了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能理解小说,评点就在所难免。这样看来,评点可以看作是一个推销手段。当时的“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为评点的流行提供了强劲的内在动力。商人伦理是儒贾相通的结果。随着商业的兴盛和士商合流的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划分,已不能满足商人群体与财俱增的对社会地位的要求。新安商人汪道昆曾发出“良贾何负闳儒”[15]的呐喊。既然“良贾何负闳儒”,书坊主完全可以弃儒经商,用刊刻小说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刊刻小说时加以评点,在评点中阐发小说的微言大义,既作为商人来推销小说,又作为儒生来张扬理想,二者兼得,何乐而不为?商业伦理一方面是经商时遵守行业规则,另一方面是借助伦理来经商。前者无需多言,后者通过评点将伦理说教和商业营销结合起来,很有时代特色。余象斗刊刻《水浒志传评林》,正文前有《题水浒传叙》,称赞《水浒》“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16]4,并在《叙》之眉栏处写有《水浒辨》,说“《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16]1-3这显然是在为自己的刊本做推销。推销而不忘小说的“忠义”主旨,让人有理由相信标举“忠义”也是推销的一个手段。
具体来说,书坊主往往将评点作为自己刻本的卖点,或请文人评点,或假托文人评点,以抬高自己刻本的身价。不妨以《三国演义》为例来看书商的评点动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评点为卖点来追求经济利益。《三国志演义》在明代刊刻有二三十个版本,万历年间就有十几种,周曰校江南本和余象斗刻本可为代表。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识语:“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17],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该刊本评点的具体情况。万历二十年建阳余象斗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在书名中标注“音释补遗”,“是最早正式标榜‘批评’的《三国志演义》版本”[18]214-215,卷首《题全像评林三国志叙》上方板框内有《三国辩》,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19]这显然是在推销自己的版本。版面上方为“新增评断”,中间是图像,下方是正文,和以前的刊刻本相比,“新增评断”显然是自己的一个卖点[18]73。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设计奠定了余象斗后来刊刻的“评林”本的基础。其二,以评点来抬高自己刻本的文学品质。评点的本意是为了帮读者理解小说,但有时也被书商当作噱头来提高自己刻本的文学品质。万历三十三年郑少垣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书名标以“京本校正”字样,当是在周曰校本等江南本的基础上加以“校正”,周曰校本影响已然很大,“京本校正”当比“京本”要更好。但事实上,该本刻工较粗陋,偶有夹注,如卷十一“轩辕之乐,八佾之舞”后夹注:“轩辕者,堂下之乐也……”[20]737在诸多《三国演义》版本中,无论是刻工、排版,还是文学品质,都很平平,尤其是其评点,寥寥无几,实在看不出其品质好在哪里,却以“京本校正”“全像”等字样来标榜自己刻本的文学品质。与郑少垣本相比,余象斗“评林本”在刻工上也比较粗陋,但在文学品质上可谓精益求精。此前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已有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设计,《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即“评林本”)在继承这一版式的基础上,特意注重“评林”特色,上方评点栏有“音释、释义、考证、补遗和评点”等多种形式,“正文中也偶有双行小字注”。“评林本”在评点方面所花的功夫,的确提高了刊刻小说的文学品质[18]215-218。其三,借助评点中的伦理内容来彰显自己刻本的特色。郑少垣刊本封面版心题“刻三国志赤帝余编”,卷首有顾充的《新刻三国志赤帝子余编序》,《序》云:“此赤帝子余编也,不应称《三国》,自陈寿志三国,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国待汉,故《通鉴》目之以魏纪年,《纲目》始以昭烈承献帝。大书章武之元绍昭烈于高光,则魏其紫色蝇声。余分闰位者,宁顾一时无实录,万世无信史?不得旧史,奚以作《春秋》?微是志,《纲目》亦病……志仍其旧,特标其额曰‘志帝余编’,倘亦存正统意乎?”[20]将蜀汉故事看作为“赤帝余编”,给蜀汉以正统地位,和此前刻本相比,可谓一大特色。余象斗“评林本”则在眉批中显示出对伦理的关注。卷一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张世平、苏双送马匹金银等给刘备“以资器用”,此页眉批云:“评张苏助汉:此见张苏乃有安民扶汉之心,遂送马赠金,非有激于中义而能乎?”[21]28此处内容,实平淡无奇,且刘备刚出场,事业毫无基础,评点者即称张苏义举为“扶汉”,伦理倾向非常明显。稍后,“刘玄德斩寇立功”页,眉批云:“评玄德初功:斩寇之功,英雄自此而名具矣。”[21]29所谓斩寇,实乃张飞、关羽所为,但为了突出刘备,正文中将“刘玄德斩寇立功”单列一行作为则目,眉批中又借机将刘备评点为“英雄”,伦理意图昭然若揭。这两页眉批相邻,且是该刻本最初出现的评点(前面的几页眉批是简单的“释义”,而不是“评”),这无形中传递出一个信息:该刻本的评点关注小说的伦理倾向。
三、 伦理意图形成的文本路径
评点者在评点中表现自己的伦理意图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土壤,但最终还需要通过评点将自己的伦理意图通过文本表现出来。评点者伦理意图的文本表现非常复杂,(1)评点者伦理意图的文本表现,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对小说内容的伦理解读;(二)对小说形式(包括刊刻形式,如插图)的伦理阐释;(三)对评点内容和评点形式背后评点者伦理动机的发掘(其中涉及评点者伦理动机和作者伦理动机的关系);(四)同一部小说不同评点者之间形成的伦理张力。前三个方面可参看笔者的系列论文《小说评点的伦理阐释》(《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小说插图与接受伦理》(《学术界》2021年第12期)、《古典小说叙事的意图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古代小说的“春秋笔法”》(《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和《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1辑,2015年版),第四个方面笔者已撰文《从版本差异看小说的接受张力》。后两个方面直接关系到评点者伦理意图的形成。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此详加论述,只想表明评点者伦理意图的形成最终依赖于评点的文本表现,离开文本中评点的具体情况,评点者的伦理意图也就无法形成。就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看,其文本表现不是指对小说内容进行伦理阐释,而是指通过阐释小说所体现出来的评点者伦理意图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路径一,通过解读小说主旨来表现评点者的伦理意图。《武穆精忠传》(即天德堂藏版《精忠全传》)前有李春芳的《岳鄂武穆王精忠传叙》,《叙》云:“天地之间,正与邪不两立,故人心之公,好与恶不容已。今之言桧者,辄加唾骂若污口然。至于王则景仰不替……历古至今一也。王之庙与墓俱焉,在杭之西湖栖霞岭之下,岁久屡修复敝。”[22]从后人对岳飞、秦桧的态度出发,指出小说主旨在于“正与邪不两立”,通过这样的主旨,评点者表现出对岳飞“精忠”的赞扬和对秦桧奸邪的贬斥。
路径二,通过对人物事件的解读显示出评点者的伦理意图。就人物评点看,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对小说主要人物的分析可为一例:“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贼奸,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12]109评点者在具体分析人物的表现之后,既对其加以伦理判断,最后还通过“遗芳遗臭”和“君子小人”将自己的伦理姿态表现出来。就事件评点看,《列国志传评林》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该书卷二“周郑大战于繻葛”一节,郑伯拒绝周王征田的命令,周王出兵征讨时也以兵对峙。此处眉批云:“宋岳飞灭金一点忠,不违旨而功废。郑伯若如岳飞之忠,见兵至束手,其身亦丧……岳飞当日若观此节,违旨杀入沙漠,救出二主……岂有丧身者乎?其不明矣,令人恸乎!惜哉!死忠也。”[23]292-295从郑伯抗命引出岳飞奉旨,陈述了一个事实:郑伯抗周王虽不忠,但能保命;岳飞虽忠却丧身。折射出评点者对“忠”的态度:忠固然需要,但不能“死忠”。
路径三,通过作者“婆心”的揭示来表现评点者的伦理意图。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4]218明代小说的评点者往往在解读“作书之人”心胸时贯穿自己的伦理意图,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揭示小说表面现象背后的伦理用意。《隋炀帝艳史·凡例》云:“《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知宣淫等书,不啻天壤”[24],评点者点明小说表面上“荒淫之事”所蕴含的“讥讽劝谏”之意,显然深得作者“婆心”。二是对小说人物进行伦理导读。或是认为作者和自己表达了同样的伦理诉求,或是以自己对小说的伦理判断来取代作者在小说中的伦理姿态。不妨以李贽的《三国演义》评点为例。第一回“总评”评董卓:“说着‘白身’,即救命之恩亦遂不报,董卓真小人哉,如此势利小人不杀待何?虽然,今天下岂少董卓哉!那里杀得许多也!那里杀得许多也!”[7]11既认同作者在小说中对董卓的评判,又借助这一评判对当时的世道加以衡量。第七十九回“总评”诸葛亮:“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之罪人也。彼何尝为蜀,渠若真心为蜀,自不劝杀刘封矣;即其劝杀刘封,乃知借手剪蜀爪牙,实阴有所图也。”[7]970显然不认同作者对诸葛亮的推崇,通过否定作者“婆心”来显示自己对人物的伦理评判。
路径四,通过小说文本的伦理重建来表现评点者的伦理意图。小说评点中伦理重建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金圣叹评《水浒》:“削忠义而仍《水浒》。”[6]8《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云:“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6]6,于是腰斩七十一回之后的内容,将宋江等人受招安以显忠义的情节全部删除,并改动文字,以显示宋江非“忠义”之人,且就改动后的文字加以评点,以此进行伦理重建。在金圣叹看来,“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6]6,宋江等人上梁山反抗朝廷,是败坏纲纪,无忠义可言。百回本《水浒传》的“忠义”主旨在金圣叹这里由此重建为“治乱”[25]。明代小说中极少像金圣叹这样大幅删改原作并改变小说主旨的评点,但局部改动文字,然后加以评点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换言之,小说评点中局部伦理重建的情况很常见。
通过局部伦理重建,评点者的意图得以体现。具体表现有二:其一,某一处的伦理重建,体现出评点者针对某一具体人事的伦理姿态。上文所言《列国志传评林》卷二“周郑大战于繻葛”一节,评点者以岳飞“死忠”来显示郑伯抗周可取。冯梦龙改写的《新列国志》第九回,叙同一件事,较之《列国志传评林》,文字颇有改动。以其中的祝聃射周王为例,《列国志传评林》云:“郑将祝聃拈弓搭箭,望王左肩射中一矢,王倒坠马下,聃将近前斩之。郑伯大叫曰:‘君子不欲多上(伤)人,况敢凌天子乎!且勿动手。’遂令鸣金收军。周兵始救得天子回寨。是夜,郑伯遣大夫祭仲于周寨中,问王安否……潜渊居士读史诗云:‘君臣大义死无仇,郑伯如何敢拒周。败后徒兴安否问,春秋首恶抗王侯。’”[23]293-294《新列国志》云:“祝聃望见绣盖之下,料是周王。尽着眼力觑真,一箭射去,正中周王左肩。幸裹甲坚厚,伤不甚重。祝聃催车前进,正在危急,却得虢公林父前来救驾,与祝聃交锋。”[11]179此后庄公觉得“兵威已立”,于是遣祭仲往周王营内问安。“史官有诗叹曰:漫夸神箭集王肩,不想君臣等地天。对垒公然全不让,却将虚礼媚王前。”[11]181两处文字有异,但都讲究君臣之礼,评点则表现出巨大的伦理差异。《列国志传评林》眉批云:“郑伯……止将不得害于王,致自不受渠害,岂不忠乎?……潜渊二诗云云,不合郑伯引兵出敌,为之抗拒,其不知郑伯无罪有功。诗该断周之过,不该断郑伯之罪也。”[23]293-297对小说叙述者透露出来的君臣之礼不以为然。《新列国志》眉批云:“郑庄奸雄悖逆,多祭仲替成之。”[11]180显然以君臣之礼来衡量郑庄公抗周,郑伯抗周王,是为不当。对照小说正文和评点,不难发现,《列国志传评林》评点者不再盲目恪守君臣之礼,有重建伦理之企图;对照不同的评点,《新列国志》评点者想推翻《列国志传评林》评点者之伦理企图,实际上也是在重建伦理。
其二,在一部小说的多处评点中表现出不同的伦理立场,虽然不能从总体上对小说进行伦理重建,但可以对具体的人事进行伦理重建。《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卷首有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和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序》云:“《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豁然于心胸矣。”[26]5-6《引》云:“《三国志通俗演义》者……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26]1-2两位评点者都认为《三国演义》有教化之用。万历吴冠明刊本有李贽“总评”,通过对其不同回目“总评”的解读,可以发现另一种伦理姿态。《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李贽“总评”云:“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那一处不是戏场?那一人不是戏子?那一事不是戏文?倂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7]981第一百二十回李贽“总评”云:“到今日不独三国乌有,魏、晋亦安在哉?种种机谋,种种算计,不足供老僧一粲也。哀哉,哀哉!”[7]1457三国人事的纷纷扰扰,在评点者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惹人发笑的大戏,最终都会散场,如此而已。《三国演义》所写的正统窃位之分,也只不过是供人一笑。这意味着,在评点者看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正统窃位这样板着脸孔的说教,小说主要是供人娱乐而已。
综上所述,明代小说评点者伦理意图的形成,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土壤,更离不开小说评点的具体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评点者的伦理意图需借助评点者对小说内容的见解得以体现,但二者仍有区别:评点者对小说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从小说的具体内容出发的;评点者的伦理意图,是从评点者从事评点的动机出发的。前者归属于文本的伦理解读,主要通过小说的随文评点来完成;后者归属于文本伦理解读背后的动机,往往要结合“读法”“凡例”“总评”等来完成,有时还要结合评点者的思想意识和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