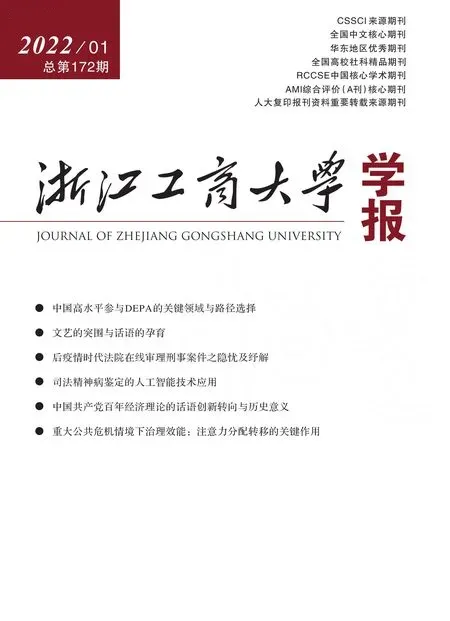唐代窦氏《述书赋注》的体例创新与著作成就
黄大宏,吴健超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成书于鲜卑后裔窦蒙、窦臮兄弟之手的《述书赋注》是唐代书学的扛鼎作品之一。文章拟探讨其著作体例的创新和相应的著作成就。
按学界目前的共识,通常所说的《述书赋注》由三个部分构成,包括窦臮所撰的《述书赋》,臮兄窦蒙为赋文作的注,①以及旧题《述书赋语例字格》(以下简称《语例字格》)一文。事实上,《语例字格》是由《字格》和应当被题为《题述书赋后》的两部分组成的,《述书赋注》由此具备了一个“赋注格”相结合的新著作体例。著作体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部著作的理论思考和全部内容在著作形式上的完整体现,成熟的研究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著作体例,创新的研究则必有著作体例的突破。事实上,《述书赋注》的体例既是对传统书学著作体例的创新,在中国传统著作体例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自窦臮始作《述书赋》起,其以散体赋为“述书”之形式、以评论历代书家成就为“述书”之本位,结撰周唐一十三代书法发展史的宏大体例,就并无前例可循。再因窦蒙注与《语例字格》的完成,共同造就了一部汉唐书学史的创新之作。细绎起来,这一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由于窦蒙注对书家事迹的补充强化,使《述书赋注》成为汉唐以来规模最大的周唐书家传记体书学史著;其二,窦蒙注是魏晋南北朝史注体例在书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又使《述书赋注》成为第一部史注体的书史著作;其三,《语例字格》是对《述书赋注》所采用的书学批评术语的汇集和意义界定,既可以深入阐发自身赋注的内涵,也有建构书法审美评论体系的理论自觉,更有规范书学概念表述的体例特征,因此又是第一部具有建构书学概念表述规范意义的书学论著。概而言之,《述书赋注》的著作成就与其体例创新密切相关,是对汉唐间文化与学术传统的遵循和发扬,也是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 汉唐间规模最大的周秦书家传记体书学史著
传统书学研究的基础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记录历代书家事迹,二是评论历代书家的书法成就,三是历代书家作品批评。围绕这三个方面,传统书学研究涉及历代书家的书学传承、擅长的书体及其成就、代表作品及其特色,时代及个人之书体、笔法与书风的形成与演变,书写载体(如笔、墨、纸、石等)、行款和装裱等一系列物质和形式要素,以及历代书法理论观念及评论实践的发展变化诸内容,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邃、积累深厚、传承有素的融合书法理论、创作实践与作品评论于一体的文化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根本,历代书法大家是书史、书论乃至书学的核心。因此,自秦李斯《用笔论》、汉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笔论》《九势》、后汉赵壹《非草书》与东晋王羲之《自论书》等作品产生以来,即使是论笔法、书体、书风等,亦不能不涉及书家,只是语焉未详不成体系。明确以书家为撰著本位,具有历代书家传记性质的著作体例约起于西晋,南朝宋虞龢在《上明帝论书表》中提及卫恒的《古来能书人录》一卷,并有所改正,知当时尚存。今卫恒书已佚,但从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的性质推测,应当具有书家传记属性。今天可见的有书家传记性质的最早著作,当是晋人琅琊王愔的《古今文字志》三卷,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著录该书目,知其上卷收“古书三十六种”,即36种书体;中卷收“李斯”至“诸葛融”等“秦吴五十九人”,下卷收“韦诞”至“桓玄”等“魏晋五十八人”,合录秦晋间书家117人。(1)案《古今文字志》又著录于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题《古今文字志录目》,仍是“上卷古书三十六种”,但中、下两卷共收“古今字学二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书势五家”,包括“中卷秦汉共六十人”“下卷魏吴晋宋齐梁陈共八十七人”,超过了《书苑菁华》所载117人的规模,因为出现了三国吴及晋以后的人,显然有后人窜入的痕迹,又在单个书家之外增出“二十七家”的概念,已失原书体例,故不取。其书的中、下两卷具有书家传记体例特征。
继王愔《古今文字志》之后出现的是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今见此书乃南朝齐王僧虔于建元元年(479)奉敕条疏羊录而上呈太祖萧道成的一卷文字,自秦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至三国吴人张弘,凡42条,记诸体书家68人,其文简者只记时代、官职、姓名及所善书体;其文繁者则言及书风、书体、代表作及逸事。其中,如韦诞条兼记其子事迹,可见父子相承关系;记弘农张芝四弟子一条汇集了师门传承之风;有关琅琊王廙、晋丞相王导、王恬、王洽、王珉、王羲之、王献之至王绥等14人的10个条目,则勾勒出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的传承轨迹与鼎盛之状,是承自南北朝正史中流行的一门集传的史法,呈现出集传体书家传记的样貌。虽然不能确定王僧虔上呈的文字忠实于羊录原貌的程度,但王僧虔所撰《答齐太祖论书启》仍是典型的书家评论,如“索靖”条是对羊录“索靖”条的补充,“卫觊”条则连带记录了子瓘、瓘子恒,与前述《采古来能书人名》记韦诞及王氏一门是同一机杼,这显然是流风所及,有所依傍的产物。综上,以历代书家为记述本位,以书家传记体例结撰书史著作的风气,在晋宋时期已经形成了。此后,跨越齐梁以来涌现的大量以品评书家风格、书体、笔法为本位,涉及历代书家的书学著作,如庾肩吾《书品》、张怀瓘《书断》等,能上接卫恒、王愔、羊欣等著作的体例传统的,当属《述书赋注》,窦蒙的注尤其使其成为这一传统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
《述书赋》共述及275人,在征求宝玩27人、印验14人、裱装10人、商贾8人、押署缝尾7人之外,涉及历代书家209人,既在同类著作中征引数量最巨,又取舍有据,入选书家都是有作品传至唐代,且经窦臮目验可以采信者,即如《述书赋序》所云:
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并今朝自武德以来,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亦书之,并错综优劣,直道公论。……其所不睹,空居名额,并世所传搨者,不敢凭推,一皆略焉。[1](2)本文所引《述书赋注》及《语例字格》文字均出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不一一注明。
这一“今记前后所亲见者”的收录原则是窦臮著书严谨的表现,稍微对照一下王愔和羊欣的著作,可知见于二书的许多人物,如秦狱吏程邈、扶风曹喜等,就不见于《述书赋》。事实上,这一原则不仅约束了窦臮自身,也约束了窦蒙,此点详见后文。
但《述书赋》的体例仍是书家评论体,其卷上是以书体统摄书家评论,自周史籀至隋赵孝逸等,涉及162人;卷下逐一评点唐代书家,自神尧皇帝李渊至马氏妻刘秦姝等,共有47人,两卷体例虽略有差异,实与此前的书学著作并无根本不同。但是,窦蒙所作的注则不仅使《述书赋》的书家评论产生由虚落实的效果,而且造成了《述书赋注》兼具书家传记体的重要变化。窦蒙在窦臮序文之下先列周秦至唐209位书家的时代和名讳,形式上有类史传的目录,既是对赋中书家的概括,也是作注的纲领;其注文在功能上是对赋文的注解,其形式则是书家传记。如卷上窦臮赋文云:
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蔡邕,当代称之,俱遗芳刻石,永播清规。……伯喈三体,八分二篆,棨戟弯弧,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峻极层巘。周秦汉之三贤,余目验之所先,石虽贞而云亡,纸可寄而保传。
窦蒙据此一一作注,如注蔡邕云:
蔡邕,字伯喈,陈留人,终后汉左中郎将,今见打本《三体石经》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稀。惟《稜隽》及《光和》等碑,时时可见。
以上注文的内容涉及史籀、李斯、蔡邕三人的史事、作品、成就及遗迹保存诸方面,所谓“石虽贞而云亡,纸可寄而保传”的概括,都可以从三人作品的石刻及打本存亡状况中得到回应。
窦臮赋文又云:
业盛琅琊,茂弘厥初,众能之一,乃草其书,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稜载蓄,高利有余,类贾勇之武士,等相惊之戏鱼。有子敬伦,迹存目验,以古窥今,调涉浮艳。尚期羽翼鸿渐,芝兰香染。与兄拓而弟真,将奢也而宁俭。绳绳宜尔,杰出季炎,露锋芒而豁怀,傍礼乐而无检,犹抟扶揺而坐致,超峻极而非险。
窦蒙注则云:
王导字茂弘,琅琊人,晋丞相,谥曰文献公。今见具姓名草书两纸共六行。王劭,字敬伦,即导子,晋车骑将军。今见具姓名草书一纸六行。兄即恬、洽,不见真迹。洽子珉,字季炎,晋中书令。今见具姓名草书一纸凡八行。
注文涉及王氏自王导以下5人,与赋文所述一一相合,是对赋云“业盛琅琊,茂弘厥初,……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的具体说明。事实上,“今见具姓名草书两纸共六行”及“不见真迹”等四句,既是对窦臮采录书家原则的具体体现,亦是对赋文的补充,尤其具有重要的体例意义。因为在《史记》《汉书》以来的正史及别传中,凡名列儒林、文学等传者,都把记录其作品行世情况作为一项基本义例,而窦蒙注揭明此点,正是书家传记向史传靠拢的表现。事实上,是否有真迹传世也是窦蒙有无为之作注的一个标准,“兄即恬、洽,不见真迹”一句,只是为引出“洽子珉”的事迹作铺垫的,对此二人并无更多笔墨,故与注“茂弘”“敬伦”“季炎”等人不同,此所谓注书有体,一丝不紊。
此外,如窦臮赋云“文深、孝逸,独慕前踪。至师子敬,如欲登龙。有宋齐之面貌,无孔薄之心胸”者,其语简意晦。窦蒙注则云:“赵文深,天水人,后周为书学博士,书迹为时所重。孝逸,汤阴人,隋四门助教。深师右军,逸效大令,甚有功业。当平梁之后,王褒入国,举朝贵胄皆师于褒,唯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俱入隋,临二王之迹,人间往往为宝耳”,历叙赵氏二人事迹、书法渊源及当时影响,其文字绝不可少。至于“论署证徐僧权等八人”“论印记太平公主等十一家”“论征求宝玩韦述等二十六人”“论利通货易穆聿等八人”等部分内容,固然是为《述书赋》所独有,而若无蒙注,也是难以确知其含义的。
综上,在窦蒙注出现后,《述书赋注》已成为汉唐间规模最大的书家传记体书学史著,这是因体例创新带来的一项重要的著作成就。
二、 第一部史注体书史巨著
《述书赋注》体例的又一特点仍在于窦臮赋和窦蒙注的关系之中。从《述书赋注》的书名看,似应把窦蒙注归于赋注类,但其实不然,它是延魏晋南北朝史注体入于赋注,同时延于书学著作的一个重要革新和发展。概而言之,《述书赋注》还是第一部史注体书史巨著,这是因体例创新带来的又一项重要的著作成就。
赋注是为赋所作的注,有自注,有他注,有汇注。赋中的自注始于宋谢灵运《山居赋》,以宋人吴淑的《事类赋注》最有名,因与窦蒙注不相类,故可不论。他注有同代人作注与后人作注两类,前者始于东汉班昭的《幽通赋注》,也是最早的赋注。后者如《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的《杂赋注本》,收录了三国魏至南朝梁期间后人注赋的概况,以两晋人所注数量最多,其中有多人注《三都赋》的情况,也可能与汇注的起源有关。显然,窦蒙注《述书赋》,就是以上述赋注的兴盛为背景,属于同时代作注的他注传统。问题是,自东汉至唐代的赋注,在谁在注、注什么、为什么注的问题上,遵循的是同一条学术路径,即“由常规的注音、释词、句解到后来重凡例、擅题解、撰序跋等批点形态嬗递的过程,其内在理路是由释义而训理,在‘尊题’的原则下兼采批点、品评、注解、阐释等法,考订翔实,注重理据,得以疏文达意,开示匠心”[2],这和窦蒙注是有根本区别的。窦蒙注采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史注法,其源头在《水经注》《三国志注》《世说注》等书。
注史之风也起于东汉,大儒马融注《尚书》,服虔注《左传》《汉书》,应劭注《汉书》,贾逵注《左传》《国语》,高诱注《战国策》等,都是开创时期的产物,旨在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及典故,不乏章句之学的性质。自三国以来,史学迅猛发展,史体日增,史著倍出,也推动了注史风气趋于深厚和注史体例的重要发展,出现了以增补事实、条列异同、考辨史料、发表评论为内容特征的史注体,或称注体史注,代表作是《水经注》《三国志注》《世说注》,“它们开阔了史注的范围,扩大了史注的内容,不失为注书之良法”[3]。尤以刘孝标的《世说注》与《述书赋注》最为接近。宋代高似孙的《纬略》卷九“刘孝标世说”条概括《世说注》的内容和体例特点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并开列刘注所引书166种,多是史部书[4]。而据晚清沈家本研究,《世说注》共征引诸部书414家,仅史部即有288家之巨,这是为《世说》增补人物事迹、评论人物及史事的文献依据。刘孝标注与《世说》本文互相发明,相互倚重,不可或缺。且因所引书基本失传,刘孝标注还具有独立的文献价值。窦蒙注同样具有这些特点。
窦蒙是因为《述书赋》的赋文意有未详、言有未尽而作注的,其增补人物身世、经历、书法成就及艺术史的第一手资料,使赋文内容无者有,隐者显,略者详,虚者实,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补足赋文及注的史料依据。这是给出赋、注的文献出处,更是对赋文内容的印证,即对窦臮所定“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原则的回应,是以史注法注书的基础。赋文开篇历数自“古者造书契,代结绳”以至于唐天宝以来的书家,蒙注为之注出“唐四十七人”人名,末云“应亲见者所言”,是揭明其人事迹出于时人之口,与见于记载者不同,这是注文交代史料依据非常特殊的一例。此外揭示注文出处的例子比比皆是,或本于传世文献,如称“梁元帝书亦云”“吏部侍郎苏朂《叙记》卷首云”;或本于金石,如注李斯小篆遗作,乃据“至德中,安史败后,四从弟沼于河阳清水渠下得传国玺”,注蔡邕之书,既有“打本《三体石经》四纸”,更有“《稜隽》及《光和》等碑,时时可见”,都是当时可见而后世无闻的。尤其对窦臮“今记前后所亲见者”原则的书迹印证信息,则只见于注文,每条注文都有诸如“今见(杜操)章草书五行”“今见(韦诞)隶纸草书具姓名一纸十一行”“见(贺邵)章草书带名一帖五行”“今见(司马攸)正书带名凡四段共三纸”一类文字,以涉字体、行款、篇幅、形制等特点,语简而要;而以注“今见(刘讷)《康帝启》四纸共有三十五行也”“(田琦)写《洪崖子张氲雪楼并雪木》行于世”和“今见(张澄)咸康八年带名正书《上成帝启》一纸七行”这类记录书作名称和标注书写年代的条目最为可贵。
其二,补足赋文所未备的内容。窦蒙注以添补人物名讳、籍贯、仕历、事迹等为基本内容,因逐条可见,故无须详论。应肯定的是那些点明赋文虚、隐内涵的注文,如赋文述太原王氏之蒙、述兄弟书风,其评语交错成文,难辨归属,蒙注于“结束体正,肆力专成”句下云“即王蒙也”,于“高利迅薄,连属欹倾”句下云“即王述也”;又注赋文所述张茂度“或大言而峻薄”句出于其子“景初对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之体’”语,注“或寡誉而拙奇”句指“王僧虔书用拙笔以自容”本事,皆以斩截一语,廓清疑义。注“谢氏三昆”之谢安“书轻子敬”句,以“安得献之书,时断作纸夹焉”一语,将“轻”字落到实处;又注羊欣条“尔后王、羊谬同”句云“所言‘王羊谬同’,谚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言虚也”,对了解王献之书法之影响、流传特点等都是无以取代的史料,非亲见者不能得其详赡。
更具价值的注文是增补原赋所没有的内容,使注文具有独立的价值,如其补注历代书家的血缘关系、书学承传等,触目即是,皆有裨考证。其独到处有四点。第一,详述著名书家书作的形制。此点可以记三国吴人皇象为代表,赋文描述其书“朴质古情,……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之风,而注云:“今见带名章草帖表七行,并写《春秋·哀公上》第二十九卷首元年,余自二年至十三年,尽尾足其纸,每一大幅有一缝线联合之,六元凯押尾云。此是茧纸,紧薄有脉似桦皮,以诸茧比类,殊有异者也。”此条描述其书写内容、书帖形制、卷帙规模、用纸及行款特点等,材料极为难得。
第二,记载书家的书迹。可以天后时书家殷仲容、王知敬为例,赋文只云“殷公、王公,兼正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骐驎将腾,鸾凤欲翥。题二牓而迹在,叹百川而身去”,内容概括而难得要领。注文详记殷、王二人所题寺额七种,所谓“题二牓而迹在”,当指“天后诏一人署一寺额,仲容题资圣,知敬题清禅”之事,二寺皆在长安,此二牓为殷、王之代表作,二人所长亦当在“题牓”。另如殷令名题普济寺额、王知敬书洛川长史贾敦实德政二碑即“棠棣碑”事,在唐代文献亦仅见于此条。
第三,记载书家作伪故事。赋文叙及“爰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已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但不详其事;又云“吠声之辈,或浸余波”,但不详其人。而注文详注怀琳作伪情事,又以谢道士落实“吠声之辈”,都以历史细节充实了抽象的概括。至于注征求宝玩、印验、裱装、商贾、押署缝尾数十人之文字皆极难得,而别无分店。
第四,记载书家生平。可以注贺知章条为代表,足可见其增补书家事迹之可贵。前已指出,注文的基本内容是补注书家事迹,其补注唐前之人已颇多不传之书,记唐人尤多独得之秘,而记贺知章善书大字特点最详,记生平则犹在《旧唐书》本传之前。注云:
贺知章,字维摩,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孙。少以文词知名,工草隶书。进士及第,历官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迁秘书监、太子宾客、庆王侍读。知章性放善谑,晩年尤纵,无复规检,年八十六,自号“四明狂客”。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天宝二年,以老年上表,请入道归乡里,特诏许之。重令入阁,诸王以下拜辞。上亲制诗序,令所司供帐,百僚饯送,赐诗叙别。
以此丰富的内容与赋文中“湖山降礼,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词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的概括性文字相比,可知注不妄言,而裨补史实之力尤大。
赋体有擅于铺陈、断语凝练的文体特点,也有拙于叙事、短于细节陈述的文体局限。《述书赋》虽然颇享美誉,也不能掩盖其源自文体局限的不足。窦蒙注的价值在以散行文字既注又补,既发明赋文内蕴,也弥补了赋体拙于叙述的缺陷,使《述书赋注》既是史注体的赋注,更是史注体的书史著作,于赋注,于史体,其功皆大,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赋注和史注,对传统书论著作的体例和内容都有突出的革新与发展。
三、 第一部具有书学概念体系建构意义的书学论著
《述书赋注》的第三个体例创新,是“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今见九十言,并注一百十一句)的《字格》部分,体现了建构书学概念表述体系的自觉意识,也是一种初步的成果形态,是窦蒙把悠久的文化与著作传统再次延伸到书论领域的一项成就,也是唐代书论在理论意识和著作形态上的重要进步。
但是,上述《字格》部分通常与“语例字格”一词相纠缠,迄今并未见到对“语例字格”一词含义的明确解释,使该词与《字格》的关系十分模糊。但要阐明《字格》的体例创新意义,绕不开对“语例字格”一词内涵的理解。在《述书赋注》的语境里,“语例字格”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指《述书赋语例字格》一文;二指《述书赋语例字格》的“字格”部分;三指《述书赋语例字格》中概括《述书赋》、注及“字格”用语规范的一段文字。因此,通常所说的“语例字格”不是一个无须界定即所指明确的概念。就第一层说,即使有文献著录和传承渊源,《述书赋语例字格》也不是一个可以准确概括文意的好题目,因为“语例字格”不是一个有概括力的题目关键词。该文中涉及用语规范的一段文字,主要是与《字格》部分起到照应作用,所论亦不全面。因此,一般提及“语例字格”时,其实就是指“字格”部分,它不仅是《述书赋》的一个独立部分,也是其体例的创新之处,直接称为《字格》更为合适。下面对此作一分析。
据现存文献,在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四和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十所收录的《述书赋》的后面,都有一篇题为《述书赋语例字格》的文字,“语例字格”一词即出于此题。细绎《述书赋语例字格》的文字,包括“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四百余字的叙述部分,和“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的《字格》部分,按照命题的逻辑,这些内容都是《述书赋》的一个部分,“语例字格”即是统括上述两部分内容的命题关键词。但是很明显,无论用“语例字格”还是“语例”,都与“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四百余字的内容不相符合。窦蒙在这段文字里至少表达了三项内容,首先陈述窦臮的生平事略和对他的怀念与景慕之情,其中提到窦臮晚年撰著《述书赋》一事;其次概括撰著《述书赋》及注的行文义例和用语规范问题,因为“虑学者致疑,仍施朱点发”;最后提到“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的“字格”部分,他特别说,“此则语之理例,别有《字格》存焉”。这就是前文指出“语例字格”一词包括三层意义的依据。这一内容特点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段文字的功能和文体属性与传统著作的序或跋是一致的,即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同出一辙;同时,“此则语之理例,别有《字格》存焉”一句,不但说明《字格》即是语例,也表明了《字格》的独立性,“凡一百二十言”云云是对《字格》行文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在“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四百余字中出现这项内容,是符合一书之序跋应涵盖全书内容的要求的。
事实上,从《法书要录》等文献在收录《述书赋语例字格》时的文字格式看,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这一命题的纠结和对《字格》独立性质的坚持。《法书要录》卷六在“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的文字之下,有“右语例”一语;在罗列了“不伦”至“宏”九十言之后,又有“右字格”一语,这显示出“语例字格”虽是一个总题,但“语例”和“字格”仍是分开的,而如前述,“右语例”的说法并不符合相应文字的实际内容。《墨池编》卷四仍以《述书赋语例字格》一题统率全文,却没有“右语例”和“右字格”二语,而且“字格”九十言的顺序是自“亡情”至“宽”字,这显然是另一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它取消了“语例”和“字格”的分别,似乎取得了题、文的统一,却没有消除“语例字格”在统括全文内容上的含混倾向。《书苑菁华》卷十虽然延袭了《墨池编》中《字格》九十言自“亡情”至“宽”的排列顺序,却又给这一部分重新加上了“字格”二字。这一系列变化的共同点集中在是否应标明“字格”的独立属性,纠结的是以“语例字格”为题与内容的矛盾,只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有所改变的是《全唐文》卷四四七的收录,在窦蒙名下只收录了“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的文字,题作《题述书赋语例字格后》,却不录“字格”部分。这就是说,《全唐文》编者并不把“字格”部分视为文章,又给原题加上“题……后”二字,确认其文体属于序跋,虽然这改动不彻底,有迁就文献旧规的痕迹,却较前三者更接近事实。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其实,“吾第四弟尚辇君字灵长”讫“哀缠骨髓”的四百余字,如果题作《题述书赋后》,或《述书赋后序》《跋述书赋》等,都是符合其文字性质和命题惯例的;同时应当承认《字格》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立性,使之成为《述书赋注》体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汇集与约定《述书赋注》用语规范的那个部分,从而形成一个着意于规范书学概念表述体系的体例设计。张伯伟据《法书要录》本将《字格》九十言作为诗歌艺术批评的一种参考资料,列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的附录,应该说是给了它比较恰切的位置。简而言之,是《字格》,而不是“语例字格”,才是一个所指清晰、可以指称《述书赋注》内容特征和体例特点的名称。
学界现有关于《字格》的研究集中在对其内容的性质和来源的讨论,总体上是确认其建构了一个唐代书学观念和美学思想的批评体系,这些观念和思想是基于《述书赋》与注的实践运用又补充阐发之,相关术语及其释义,以及成文形式与唐前及唐代文学批评已有的某些资源有关,以尹天相、张伯伟和大野修作的研究较早并具有代表性。尹天相认为,窦蒙做《语例字格》是要弥补注文不能表达深微难明之处的缺憾,“其语言表述体例,是先把原著中涉及到的书学批评专用术语一一罗列出来,然后给这些概念一扼要的阐释”,目的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关注书家事迹“一步转移到对书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些实质性意念的思考上去”,因此“从用心和效果看,似乎《语例字格》比《注》更为重要”,“是一篇颇具匠心的,在书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专门著作”[5]。张伯伟指出,“《字格》对《述书赋》所涉之论书概念,均作简明扼要之解释”,进而,“《字格》尽管主要对《述书赋》作进一步阐发,但其以简洁语句揭示某种风格,体现其论书标准及法式”,与皎然《诗式》“辩体一十九字”相通,其论“逸”“高”等字,尤可与《诗式》互参。[6]这些判断都是谨慎恰当的。大野修作认为《字格》体现和概括了《述书赋》的批评标准和语汇,这是对的,但说“为了《述书赋》的理解,窦蒙考察了其中含有很多问题的特殊语汇进行了注说”,以及认为窦蒙是“以臆测提出了新的概念”的观点则颇令人费解;所谓“在《述书赋》以前,类似于‘字格’这样的另类别项的注释,限于管见尚无看到”的说法,如果局限在书学著作传统中,也大抵可以接受。[7]此外的研究与上述诸论多是同一轨辙,在探讨《字格》对建构唐代书论审美术语体系的贡献,更细致地研究《字格》九十言涵盖的书论范畴及其内涵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绩。(3)薛永年《窦氏兄弟与书论》将《字格》中的术语分为书体、书品、书法造诣和风格技巧四类,《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王扣香《唐代书论的用词与审美——以窦氏兄弟〈述书赋〉与〈语例字格〉为例》分为五类,“一、表书体的术语,二、表书品的术语,三、表师承关系的术语,四、表书法法则的术语,五、表书法风格的术语”,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王晓庆《唐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书法审美术语阐释研究》将其分为“体”“力”“势”和“格”四个范畴,对九十言进行了逐字考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尹冬民《〈述书赋〉笺证》以偏于褒贬和中性为标准划分《字格》九十言的属性,并逐条笺证了《述书赋》文字,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其他相关论著不一一列举。总之,这些研究肯定了《字格》九十言在进一步阐发、明确赋与注的内涵,以及体例创新意义和建构唐代书论审美评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对《字格》中的批评术语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的关系仍有待于深入研究,而《字格》的成文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亦复如是。这是本文欲再申说的要点。
旧题《述书赋语例字格》部分对《字格》的成文方式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
此则语之理例,别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且褒且贬,还同《谥法》。
《说文》卷三上言部云“论难曰语”[8],故“语”指言语、论说、交谈的行为。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字”,与“语”的含义是相通的。“格”有法式、标准、规格的含义,《礼记·缁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郑玄注:“格,旧法也。”[9]《孔子家语·五仪解》云“口不吐训格之言”,王肃注:“格,法。”[10]《后汉书·傅燮传》云“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李贤注:“格,犹标准也。”[11]综括而言,在《述书赋注》的语境里,“语之理例”即是语例,是赋与注在行文时的表达方式,既是言语规范,也是行文义例。《字格》中的“字”意同术语,《字格》就是汇集与阐释这些表达的部分,即汇集并解释“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的书法批评术语的专门著作,是具有建构书学概念表述规范意义的书学论著。在这个意义上,“语例”和《字格》的确是术语化批评方式在书论领域的一个体现,必然有唐前尤其是唐代文学批评方式的深刻影响,是“诗格”“诗式”“诗法”“文格”“赋格”“四六格”等方式相通于艺术领域的表现,也是如“谢赫六法”等绘画批评方式的历时性嬗递。另外,窦蒙描述《字格》时所说的“且褒且贬,还同《谥法》”一语的内涵尤应引起重视,它不但指出了《字格》中批评术语的属性,也指出了《字格》成文的体例渊源,这两点都是直接关乎著作体例的要素,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注重行文义例的著述传统在自身著作中的具体实践。
古代著述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凡行文必有义例,下字必有规范,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从著述形态上说,古代的很多经史著作都集本文、注、疏于一体,本文写作遵循“春秋笔法”而成文,其内蕴亦如《春秋》一样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特点,其中的嫌疑、是非、犹豫、善恶与贤不肖等并不易为人所体会,故须以注发明之;注之不足,再以疏阐扬之,本文、注、疏既是一部著作的完整内容,也构成一部著述的完整体例。在本文看来,完整的《述书赋注》就是由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四部分组成的,它的内容和体例在书学领域里的典范性,只能在这一著述传统中得到认识和解释。但《述书赋注》又具有独特性,在于它是窦氏兄弟紧密合作的成果,因此与其他经史著作往往因为他人注、疏的原因产生巨大的理解和阐释空间不同,《述书赋注》的著作体系在构成上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书学观念上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既是因为“弟文兄诠”的著作方式,更是因为他们有长期的共同鉴赏体验,此点后详。因此,窦氏兄弟在赋注中记录、评判历代书家,辞约而旨丰,语简而义长,或褒或贬,“婉而成章”;再把这些评判性的术语汇为《字格》,逐字赋义,明确术语内涵,其本身类似批评术语辞典,与赋、注形成意义照应,使“微而显,志而晦”,从而构成完整的观念表达。窦蒙即云:“注有未尽,在此例中;意有未穷,出此格上。”他对赋、注与《字格》之间的意义阐释关系具有清醒的认识。总之,源于“春秋笔法”的中国著述传统是催生《字格》的内在学理逻辑。
进而,窦蒙指出《字格》的体例同于《谥法》的原因,仍在于二者在意义和形式上的一致性。谥法即追谥之法,在古代是主要针对政治人物一生功过的一种终极品评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方式,是根据人物的一生表现形成具有强烈道德评价意味的谥号,且多是一字评。将谥号汇集成文,则为《谥法》,也是推行谥法制度的依据,其中所汇集的谥号及其释义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谥法起源甚早,今存最早的《谥法》是伪托周公所作的《谥法解》,见《逸周书》卷六,有晋孔晁注本,汇录谥号并释义二百二十余条。今据《四部丛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分褒贬两类略举数例,即可知其体例大概,如:
一人无名曰神;称善别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德像天地曰帝;靖民则法曰皇;仁义所往曰王;立志及众曰公;执应八方曰侯;名实不爽曰质;……
不悔前过曰戾;怙威肆行曰丑;好变动民曰躁;华言无实曰夸;啬于赐与曰爱;逆天虐民曰炀;……
以此与《字格》相较,从意义到形式是何其相似!窦蒙的自陈绝非虚语,他只是把针对政治领域的人物评判制度应用于书论领域而已。张伯伟曾提醒重视《字格》与《谥法》的渊源关系,只是没有展开论述。进而,与其说皎然《诗式》的“辩体一十九字”的论述标准与法式与《字格》相通,不如说是《字格》与《诗式》分别受到同一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毕竟唐代是“诗格”类著作盛行的时代,皎然与文人交往频繁,唐代佛家重谥之风亦不亚于世俗社会,他和窦蒙对这一文化传统都不陌生。至于窦氏兄弟博采历代哲学、美学、文学、书学概念为书论批评术语,用于评陟历代书家及书学,则是追究《字格》九十言及其内涵赋义渊源的问题,也是体例之外的问题了。
综上,《字格》的撰著上追中国著述传统,集中阐释《述书赋》及注文中的批评术语,体现出赋、注在观念、概念上的内在一致性,具有统一书学、书风表述的意味和追求,是《述书赋》中颇具学理性质的部分,在唐代书论著作中是应予标举的创举。
四、 时代造就与文化融合的典范
作为北魏鲜卑贵族后裔,窦氏兄弟何以能在汉文化传统和特色高度集中的书学领域有如此显著成就,未免令人疑惑。事实上,《述书赋注》的成功是魏晋以来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窦氏兄弟所拥有的胡族血统和文化基因不是文化融合的障碍,恰恰是有利于融合的积极因素,再加上个人才华与时代因素,使他们成为历史悠久且成就杰出的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首先,唐代书法与书论的高度繁荣是《述书赋注》成功的时代条件,也是促成其体例创新的重要因素。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12],这确乎是唐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隋唐革命后,历史重新进入大一统的时代,书法一道携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变革发展所蓄积的能量,在唐初迎来爆发的际遇。这是历史的风云际会,也缘于唐太宗的倡导与推动,与书法可以在文化上融合南北,以再造文化正统的政治需求不无关系。唐太宗大力搜求二王的书作,推崇并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树立了有唐一代尊王的书风;又亲撰《笔法诀》《论书》《指意》和《王羲之传论》等论书著作,也带动了唐代的论书之风,产生了如虞世南《书旨述》、李嗣真《书品后》、徐浩《论书》、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估》《书议》《书断》、韦述《叙书录》和卢元卿《法书论》等一批作品,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也多有论书文字。总体来说,初盛唐时期的书论数量大幅增长,体例趋于多元,多有理论创获。唐太宗还把书法教育列入官学,诏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弘文馆,跟随虞世南、欧阳询等学书,并把考较书法列为吏部选官的四项标准之一。正如进士科考诗赋推动了唐诗发展一样,以上做法和制度促成了唐代书法风气高扬、人才辈出、佳作叠出、论书风气繁盛的局面。这是书法史的盛世,也是窦氏兄弟所处的时代文化氛围。南宋马永卿不无歆羡地说:“盖唐世以此取士,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13]在安史兵火洗劫、权贵私窃后,大量书法真迹、论著焚毁散失的现实,又促成了书学史的勃兴。窦氏兄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愤然而起去抢救书法遗产”[5],独出机杼的《述书赋注》可谓是应时应运而生。
其次,北魏书法传统的历史影响与窦氏家族书法实践的现实积累,是窦氏兄弟撰著《述书赋注》的充分条件。应该说,窦氏兄弟在唐代书法领域拥有的独特深厚的基础,当时的文化世家无出其右。窦氏源出代北鲜卑贵族,窦氏兄弟是“窦氏三祖”中窦善的后裔,其先是没鹿回部,据于意辛山(今内蒙古五原),归魏后改为纥豆陵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改姓为窦。显然,窦氏在北朝是尚武的军功世家。而当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时,窦氏顺应时代潮流,立足武功,亦推崇文化,开辟文武互用的新局面,出现了窦瑾、窦遵这些以文化立身的新成员。据《魏书》本记载,窦瑾少以文学知名,其少子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也”[14],文学与书法的基因从此融入窦氏血脉。进入唐代后,窦氏以外戚之重享有显赫的政治地位。(4)案窦氏在唐代的政治地位十分显赫。“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见《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旧唐书》卷一八三《窦德明传》则云“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此外家即是窦氏,太后指玄宗生母昭成窦皇后。特别是窦氏兄弟,既有“诸窦戚里,荣盛无比”的地位,又有“温陈才位,文蔚典礼”[15]的文化品格,多有擅长文学、书法、绘画、音律的人才及作品,其中,书法是窦氏家族最突出的家学特色。
检阅史籍,知窦臮的母族及父祖中工书、善画、解音律者代不乏人,其曾祖太府少卿窦师纶善画,(5)案《历代名画记》卷十载窦师纶“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方、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新唐书·艺文三》即著录“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三代祖河东太守卫尉卿窦庆工草隶,扶风太守窦琎既工草隶又解钟律,[16](6)案《隋书》卷三九《窦荣定传》,窦琎字之推,窦抗季弟,颇晓音律,撰有《正声调》一卷。伯父窦瓒、族兄窦锡、窦绍均善鉴藏;其外家五代祖刘珉、珉子玄平、母舅刘绘及姨兄明若山皆有书迹传世,刘珉还是北齐唯一书家。其后辈中仍多善书之人,窦庠为韩愈所撰《窦牟墓志》书丹,牟即庠兄,此志2005年在河南偃师首阳山出土,“有丰腴宽博之感”[17];翁方纲推崇窦易直所书《左拾遗窦叔向碑》为晚唐碑的上选,又赞窦巩所书《心经》(元和二年十一月立)和《幡竿颂》(长庆四年十月立)是“唐楷之足录者”;(7)案窦易直字宗元,叔彦子,《宝刻类编》卷五著录其所书二碑,一是裴度撰《司马乌重胤碑》,一是羊士谔撰《左拾遗窦叔向碑》。对于《窦叔向碑》,叶昌炽记翁方纲“选晚唐碑极严,此碑独登上选”,见《语石》卷七《窦易直一则》。《心经》和《幡竿颂》亦见《宝刻类编》卷五著录,皆在青州。翁方纲认为“是二刻皆在长庆间,……书法兼有欧、虞、褚、薛之长,唐楷之足录者”,见《复初斋文集》卷二四《跋唐窦巩残石刻》。此外尚有窦牟撰、窦巩书《唐袁亮墓志铭》和窦浑正书《唐窦季余墓志铭》等。(8)案《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收录窦牟撰《唐故河南府河南县尉袁府君(亮)墓志铭并序》,署“季甥扶风窦巩书”。《全唐文补遗》第一辑收录《唐故茂州刺史扶风窦君(季余)墓志铭并序》,署“浑正书”,浑正即志主窦季余子。无怪叶昌炽说“窦氏一门群从皆工书”[18]。由此知窦氏家族的书法修养一直处于高位,家族成员耳濡目染,奕世传承,在书法园地里不断结出硕果。事实上,家族承传是书法传统延续的重要条件,这是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书法世家的重要原因。在安史之乱后官学益废,生徒流散的情况下,要维持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准,家族传承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窦氏自北魏以来地位长盛不衰,本来就享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追求艺术造诣的充分条件,家族内浓厚的书法传统,现存的大量碑铭之作,是证明这一规律的又一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窦氏家族几百年的书法实践是造就窦氏兄弟书学成就的深厚基础。
最后,窦氏兄弟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和深厚的情谊是《述书赋注》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开放繁荣的盛唐时代和文化传统深厚的家族环境中,窦氏兄弟并非无名之辈,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多样的艺术才华,是有一定成就的诗人、学者和书家,在艺术领域和修养上各有其所长,而在书法鉴赏的领域则有着共同的追求。
窦蒙曾涉足于画史,有《齐梁画目录》和《画拾遗录》各一卷;(9)(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著录“《齐梁画目录》一卷,唐窦蒙子泉录”,《新唐书·艺文三》又著录“窦蒙《画拾遗》(卷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云:“窦蒙有《画拾遗录》,率皆浅薄漏略,不越数纸。”案《画拾遗》当即《画拾遗录》。又通阴阳五行之术,有《青囊书》十卷;于书法一道也颇有所得,《述书赋》赞其“书包杂体,首冠众贤”,虽不乏溢美,也绝非虚语,他曾用篆书为张谓撰《宋武受命坛记》题额,是今知的一例[19]。窦臮的才华与造诣显然更突出一些。窦蒙在旧题《述书赋语例字格》中着力表彰窦臮的文学成就,称其“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较其巨丽者,有天宝所献《大同赋》《三殿蹴鞠赋》”,又誉其“作诗通小雅,献赋掩长杨”[20](《题弟臮〈述书赋〉后》)。这些作品大都不存,却是窦臮能够撰成《述书赋》的注脚。窦臮的书法成就当更有说服力一些,《语例字格》称其“翰墨厕张王、草隶精深”,现存两方书碑之作,皆为正书并篆额,《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原出于句容茅山玉晨观;《大唐赠司徒毕国公扶风窦(希瓘)府君神道碑》于2009年8月出土于陕西咸阳,或称是窦臮存世唯一可靠作品[21]。明盛时泰《苍润轩碑跋》“唐窦臮正书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条评其正书特色,称其“有《瘗鹤》之遗意”[22];尹冬民认为此碑的“篆书有秦之‘简直’,汉魏之‘奇伟’”[23];李明等评《窦府君神道碑》“其正书中宫紧缩,笔势险劲,转折方正,有大王遗意而雄强过之”[21]。总体来说,窦臮的书风既有北魏书法的雄强之气,又融合了晋书的风韵,与唐代主流书风相一致而独具品格。
除了这些能够证明兄弟二人各自成就的史料外,有材料显示他们在当时书坛得到较高认可的是对古今书迹的鉴赏能力。建中四年(783)三月,唐代著名书家徐浩撰《古迹记》,记录唐代法帖的收录情况,着重强调鉴别书迹真伪的重要性,推举了包括其子徐璹在内的三位“别书人”,另外两位就是窦氏兄弟。徐浩称赞窦氏兄弟“并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24]。鉴别书迹的能力必然基于他们对书法的深入体悟与实践,以及饱览历代书法真迹的丰富经验。窦臮采历代书家入赋,以目验其作为收录原则;窦蒙为书家作注,逐一开列存世作品的数量、书体及相关特征,都是对徐浩的荐举最有力的支持和呼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述书赋》及注在书学观念上的一致性,正是在长期共同的书迹鉴赏活动中建构起来的。颇感遗憾的是,如果窦氏兄弟能够为所寓目书迹留下详细的题跋,必是极为珍贵的书论、书史文献。当然,从窦氏以书法为中心的家学特色,窦氏兄弟十分接近的艺术特长与成就,以及弟赋兄注的通力合作,完全可以推断窦氏兄弟的情感之切、相知之深,这是令《述书赋》在窦臮亡故后终成完璧的另一因素,也使我们能够且必须将《述书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看作他们人生的共同结晶。
窦氏兄弟的书论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魏晋至唐的文化融合与书法书论史为背景,依托于其家族文化传统、个人文学与书法修养和兄弟亲情,精心设计体例并结撰而成,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堪为窦氏家族文化和中国传统书论代表的巨著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