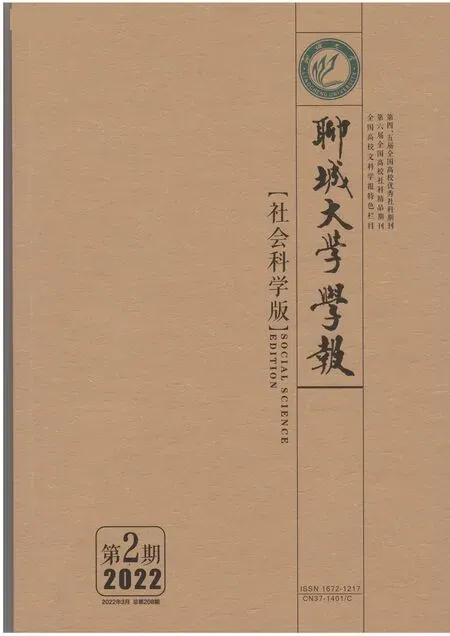王充实用赋论的文化意蕴
倪晓明
(贵州师范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贵州 贵阳 550001)
罗宗强先生对汉代文论的实用性有精当的概括:“两汉文论主要倾向是重功利的,儒家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大抵从政教之角度着眼,多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而较少从文学自身之特点着想。”①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页。接着罗先生的话头讲,汉代的赋论、诗论均受《诗》教影响而具有实用性特征。王充赋论也是这种文化语境的产物。对于王充赋论,学界已有众多探讨。②例如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有《王充汉赋观试说》一文,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有《经学与王充的辞赋观》一文,都是在各自专著中专列一节,探讨王充的赋论。此外,徐复观、周桂钿、吴从祥、王治理、王惠玉以及邵毅平、张峰屹、许结等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也对王充的赋论观有所涉及。然以往研究大都能意识到王充赋论的实用属性,但对这种实用属性的成因及其文化意味的解读则略显不足,诸如王充赋论与其士大夫身份的关联、赋论与经学的依违、赋论的“国德”意识等,均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官吏视角与汉赋语言批判
汉大赋“巨丽”③[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7页。“深闳”,赋作家为之激赏不已,赋论家却讥刺不休。王充所处东汉明、章时期被称为经学“极盛时代”,④[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页。受《诗》教尚用思想影响,其认为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⑤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95页。本文所引《论衡》之文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出注。(《自纪》)秉持《诗》教尚用观念,王充对汉赋语言“丽”与“深”予以批评: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
“文丽而务巨”与“言渺而趋深”是王充对马、扬大赋所作概括。具体来讲,“丽”侧重于辞藻之雕丽丰赡。“深”侧重于旨意之深闳难解。二者本质上都是汉大赋语言的批判。结合汉赋文本,更有助于领略王充所言之义。
(一)“文丽而务巨”批判
相如大赋为“文丽而务巨”的典范。《上林赋》纵谈天子园林之盛,言飞禽则“鸿鹄鷫鸨,鴐鹅鸀玉,鵁鶄鹮目,烦鹜鷛鸜,鷻鴜鵁鸬”,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8页,第3664页,第3664页,第3671页,第3658页。论山势则“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钜木,崭岩嵾嵯”,②[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8页,第3664页,第3664页,第3671页,第3658页。叙草木则“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③[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8页,第3664页,第3664页,第3671页,第3658页。述果木则“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遝荔枝”。④[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8页,第3664页,第3664页,第3671页,第3658页。同旁奇字层见叠出,辞兼夸饰、铺排、类举,诚如章学诚所论“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⑤[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4页。
上林苑“八川分流”景象,更能诠释“文丽而务巨”的含义:“汨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湃,滭弗滵汩,湢测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灗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壧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急漂疾”。⑥[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58页,第3664页,第3664页,第3671页,第3658页。清方廷珪《昭明文选集成》评道:“字字各有意义,或就形取意,或就声取意,或亦字义取意,与枚乘‘广陵观涛’一段,可谓异曲同工。”⑦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相如赋“巨丽”,在于极尽铺陈、雕琢、藻绘之能事。
然在王充看来,赋作固然“文丽而务巨”,但徒“丽”无益:“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一转,表示与“丽辞”相比,所重在“定是非”“辨然否”“崇实化”。实际上,王充并不否定“修辞”,甚至强调“文”是“德”的表征,如《书解》篇言“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章者文弥明。”又说“人无文德,不为圣贤”。《须颂》篇也说“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一言以蔽之,王充认为“文”“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不过,当“修辞”与“实用”两个范畴需要做出选择时,他更看重后者。此时,王充所秉持的是一种官吏视角。此处“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一语便透漏出关键信息:王充十分看重民众对文本的接受。这意味着王充对辞赋进行评判时始终存在“实用”“化民”“正俗”等概念构成的期待视野,其辞赋评判标准及其赋论观念的核心都是“实用”。从身份角度讲,王充是汉代的基层官吏,有着明确的“正俗化民”任务,《对作》篇言:“《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王充的官吏身份使其撰文时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所思所想与所写文章高度一致,与本职工作深度交融,或许可以称之为“人文合一”的典型。问题是在官吏视角下,辞赋非但不能使民众“务实诚”“薄丧葬”,反而“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对作》),恰恰是官吏视角的对立面,诚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汉代文论)大抵从政教之角度着眼……而较少从文学自身之特点着想”。⑧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页。。
概括来讲,王充以“实用”评判“巨丽”的赋论反映了两方面意涵:
其一,赋“丽”让步于赋“用”,其实质是文体风格让步于文体功能的批评策略,它背后所蕴含的是王充重实尚用的价值判断,而这与王充的官吏属性密切相关。
其二,王充著书以“正俗”为旨归。这个层面与《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的理念殊途同归,两者皆致力于“移风易俗”。进一步讲,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论,讲究崇实尚用、反对雕琢丽藻的赋论,本质正是对《诗》教理念的传承与转化,而《诗》本位意识是王充实用赋论得以生成的文化范式与学术基础。
不过,王充“尚用轻丽”的赋论在汉代并不罕见,扬雄所谓“文丽用寡,长卿也”,②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页。班固言“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5页,第3547页,第3564页。诸家多能认识到相如赋之“弘丽”,但对此颇多非议。这说明作为赋体重要特征的“丽”,在汉代文化语境中未能彻底独立,尤其未能获得赋论层面的认同,以致呈现出赋体尚“丽”,赋论轻“丽”的乖离现象,直到魏晋“诗赋欲丽”观念的提出,方才有一定改观。这种现象说明汉代赋论家在谈文论艺时总是背负了经学赋予的沉重枷锁,其赋论总归要落脚在“实用”主旨层面,这是汉代与魏晋的差别所在。
(二)“言渺而趋深”批判
从“赋用”出发,绕过“赋体”的赋论,是王充赋论的总体风貌。这又体现为对汉赋“言渺而趋深”的批判。王充认为“深覆典雅,旨意难睹,惟赋颂耳。”(《自纪》)无论“旨意难睹”还是“言渺趋深”,都是王充对汉赋艰涩深覆的语体风格所作的概括。就大赋文本而言,马、扬赋作之深,与用字、用笔有关。
前引《上林赋》描写飞禽、山势、草木、果木、水势之文,多为同旁奇字,洋洋洒洒,鳞次栉比。《文心雕龙·物色》篇称:“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4页,第699页。关键在于,《上林赋》与《子虚赋》所写物类相近,但用字几无重复。清俞瑒评道:“如此长篇,却与《子虚赋》无一语略同,何等变化!且合二赋观之,仍有渊涵不尽之致,所以不可及。”⑤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第198页,第185页,第156页,第219页。然大赋作家驰骋才学的同时,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深闳”的文风。明邹思明评《上林赋》“八川分流”道:“学者畏其难,读者未竟而索然。”⑥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第198页,第185页,第156页,第219页。相如逞辞作赋,后人读赋畏难。
类似“言渺趋深”的情况也见于扬雄所撰“四赋”。《校猎赋》言:“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摼象犀;跇峦坑,超唐陂。”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5页,第3547页,第3564页。明胡应麟云:“马、扬诸赋古奥雄奇,赘涩牙颊,何有于浏亮?自浏亮体兴,而江、谢接迹矣。”⑧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第198页,第185页,第156页,第219页。胡氏所云深得赋史三昧。汉大赋难称“浏亮”,却足以称“学”,而无论“博物的取资”,还是“字词的繁难”,⑨易闻晓:《汉赋为“学”论》,《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都是汉大赋文本存在阅读障碍的原因。
除“奇字”外,大赋之深又与作家用笔有关。《长杨赋》原为扬雄讽谏成帝之作,然行文寄托遥深,以至字面多颂美之辞:“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韩,东震日域。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⑩[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5页,第3547页,第3564页。赋作原想劝谏成帝放弃田猎,不能明言,只好“主文谲谏”,结果“言不尽意”,以至被后世批为谀辞。清洪若皋言:“《羽猎》《长杨》皆谀多而讽少。大抵子云善谀,《剧秦》谀新,而《羽猎》《长杨》实谀汉。《羽猎》犹寄讽于谀,而《长杨》则徒谀耳,亦劝百讽一作之俑乎?”[11]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第198页,第185页,第156页,第219页。洪氏讥刺子云善谀固然偏颇,但另一方面,这的确与《长杨赋》《大人赋》等大赋自身的笔法有关。《文心雕龙·才略》篇载:“子云属意,辞义最深”。[1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4页,第699页。从立意角度讲,相如大赋与扬雄“四赋”都有一定的讽谏意味,但“主文而谲谏”的行文方式却使讽谏的用意大半淹没。据此,大赋之深固与赋家用笔有关。
王充虽意识到汉赋具有深覆的文风特点,可其非但不认同,更转而提倡浅白文风。《对作》篇言:“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自纪》篇载:“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文露”“旨直”“明言”“露文”,都是对“直白浅近”文风所作表述。显然,马、扬大赋“言渺而趋深”,与之方枘圆凿。王充之所以倡导“直白浅露”的文章风格,也与其官吏身份有关。
作为以化俗教民为务的士大夫,王充在长期与民众交往过程中,自会对民众接受能力有一定认知:“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自纪》)“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自纪》)简单讲,王充认为“雅不通于俗”,但可“以俗化俗”,即运用民众能够接受的语言体式为津梁,实现其正俗目的。这种理念延伸至赋论层面,便体现为对汉赋“深覆”语言体式的批判。据此,王充对汉赋“深覆”的批判与其身份密切相关,化俗是其官吏身份的内在要求,赋论则是士大夫身份的话语表征。
需要明确的是,士大夫身份对王充赋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不仅限于语言评判层面,也体现为对汉赋“虚妄”的批评和对汉赋“颂美”的认同,此处仅为行文方便计。另一方面,文学史上继承王充“以俗化俗”理念者不乏其人。白居易《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①[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清顾炎武也有“文不贵多”“文须有益于天下”②[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3页。之论调。这种文章理论注重文章之“用”。其功利目的的实现,正是通过有意降低阅读难度的方式达成。
赋论是对赋的总结,然往往与之乖离。汉赋崇“丽”尚“深”,汉代赋论却将其视为批判标靶。王充赋论虽仅为汉代赋论之一斑,借此却可窥全豹。值得一提的是,王充对“巨丽”“深闳”的批判,与其自身观念密不可分,尤其与其士大夫身份密切相关,而无论秉承《诗》教移风易俗理念,还是坚守士大夫正俗化民的身份要求,都使王充赋论与汉赋文本之乖离渐趋难以避免,这是身份对言说予以影响的明证。据此,王充实用赋论是其《诗》本位意识与士大夫身份相融合的产物。
二、经学语境与汉赋“虚夸”批判
汉赋文本虽凭虚建构,③易闻晓:《汉赋“凭虚”论》,《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汉代赋论却疾“虚”若仇。王充赋论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汉赋“虚夸”的批评。《遣告》篇载:
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杨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
王充认为《大人赋》与《甘泉赋》都善于凭虚夸饰。《大人赋》侈谈神人轻身高举,漫游天际,皆属荒诞不经之辞。关键相如不是“言仙无实效”,而是“顺人心以非应之”,所谓“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④[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07页。是对汉武帝“好仙”心态的顺承附和,实为“赋劝而不止”⑤[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5页,第3526页,第3526-3527页。的典型体现。《甘泉赋》与之类似,如写“通天台”之高:“洪台掘其独出兮,㨖北极之嶟嶟,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5页,第3526页,第3526-3527页。颜师古注:“言高台特出乃至北极,其状竦峭,嶟嶟然也。”“言屋之高深,虽鬼魅不能至其极而反。”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5页,第3526页,第3526-3527页。在王充视野中,类似“虚妄”描写只会加剧帝王的“惑而不悟”。
王充所秉持的是“疾虚妄、务实诚、求真美”的创作原则,又据此对前代、当代文章予以权衡评判。这意味着王充的赋论深受其“崇实黜虚”观念的影响,又把汉赋的夸张虚构纳入于“虚妄”范畴”。①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崇实黜虚”本身没有问题,“疾虚妄、务实诚”原本便是《论衡》的立书之本,问题在于不应对“虚妄”不加区分,更不应当将作为艺术手法的“虚夸”视为“虚妄”,毕竟,“凭虚”也是汉赋的立体之本。然而,这些评判只能算是后见之明,若从中国文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毕竟,汉代文学处于先秦文学向魏晋文学之间的转型期与过渡期,此时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都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色彩。举凡体裁、题材、艺术特征、创作手法、审美趣味等方面,既对后世文学有开创意义,又保留了先秦文学的原初色彩与混沌状态。即就赋论而言,概念层面有“丽”与“用”的混沌,也有“虚夸”与“虚妄”的混沌。然而,没有此时期的混沌状态,也不会有魏晋时期“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文体辨析的诞生与“丽”范畴的独立。
若从赋论史的角度来看,批评汉赋“虚夸”不仅限于王充。仅就汉代而言,司马迁指责相如赋“侈靡过其实”,②[汉]司马迁:《史记》,第3689页。班固不满相如赋“文艳用寡,子虚乌有”,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4255页。转而提出“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④[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1页。的赋论观。要之,汉代学者对汉赋“虚夸”的批评主要着眼于汉赋内容之“妙称神怪”,如班固批评《离骚》“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⑤[汉]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8页。这是赋论家批判的标靶所在,也是王充赋论所处的文化语境。
魏晋以后,赋论家仍旧对汉赋的“虚夸”加以批判,但矛头逐渐由“怪力乱神”转向“殊方异物”。左思《三都赋序》言:“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⑥[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第174页。皇甫谧亦云:“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⑦[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57页。卫权所撰《三都赋略解序》云:“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⑧[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6页。三者皆体现两晋赋论家“稽之地图”“验之方志”⑨[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第174页。的崇实倾向。随后,《文心雕龙·夸饰》篇言:“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⑩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08-609页。刘勰论调显然继承两晋赋论而来。唐刘知幾《史通·载文》认为马、扬大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1][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4页。直至清刘熙载在其《艺概·赋概》中相对客观地评价汉赋“虚夸”:“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12][清]刘熙载撰,袁津琥笺释:《艺概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96页。可见,历代赋论对汉赋的“虚夸”确以批评为主。
总体来看,历代赋论之所以抨击汉赋“虚夸”,其原因在于论者以经义为准绳,以《诗》教为尺度,将赋作视为落实经学旨意的材料,不是“就赋论赋”,而是“以经论赋”。较为显著的例子如扬雄晚年自悔作赋,称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清人黄承吉却用文字考证之法层层剖析,并得出“‘雕虫篆刻’四字与赋无关”的结论,可见黄氏分明是“以治经的方法探讨赋学问题”。[13]孙晶:《黄承吉“雕虫篆刻”与扬雄之微意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由于始终处于《诗》教传统构成的文化语境之中,王充对汉赋语言“丽”“深”的批评,以及对汉赋内容“虚夸”的批判,都未能超脱汉代赋论习见的概念范畴。这显然与王充“有赋论”而“乏赋作”的短板有关。毕竟理论源于作品,扬雄、班固等赋论家本身也是汉赋巨擘,因其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故其赋论意味深长,不仅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范畴,甚至能够起到引领创作风潮的作用。例如,扬雄后期作品便体现了汉赋由“凭虚”向“征实”的转向,①易闻晓:《论扬雄与汉大赋的转向》,《复旦学报》2018年第6期。而班固所倡导的“颂汉”理念则对东汉前期赋作由“讽谏”向“颂美”的转型提供了理论资源,《两都赋》本身也具备重要的范式意义。二家赋论之紧要,自不待言。反观王充,因缺乏创作实践,其赋论或流于片面,或流于表象,总归隔靴搔痒。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王充赋论没有意义。王充抨击汉赋“虚夸”,是其整体文化观念的局部显现,与其“疾虚妄”的理念密不可分。盖因古代作家思想多能融汇贯通,赋论仅为其文论乃至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察王充对汉赋“虚妄”的批评,应与其文章理念、整体思想相结合。这种贯通性尤其体现为王充对经学“虚夸”的抨击。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语境会影响特定时期赋作、赋论的生成、演变,但并不意味着掌控一切,决定一切,更不意味着作家对文化语境只能俯首帖耳。即就王充而言,其批评汉赋“虚夸”固然受经义影响,但反过来又对经学本身之“虚夸”加以批判。这种“反噬”现象在赋论史上较为罕见。具体来讲,《论衡》“九虚”“三增”系列之《艺增》篇,集中对经艺中的“虚夸”之辞予以驳难。《艺增》篇载: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诗》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
在王充视野中,经艺不乏増饰之语,诸如“靡有孑遗”“子孙千亿”“血流浮杵”等写法都言过其实,故应当一一辩难,还其本原。表面看来,这种做法略显胶柱鼓瑟,甚至有些执拗。后世学者认为,夸饰原本便是一种写作手法,与文辞相比,更应看重言外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指出:“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08页。在刘勰视野中,“夸饰”是文章写作的自在规律,且刘勰所论列的“夸饰”例证,恰恰就是王充《艺增》篇中所辩难的内容。
王、刘二人,所用材料相同,旨意却大相径庭。与刘勰等赋论家更多着眼于汉赋本身的“虚夸”现象不同,王充不仅否定汉赋之“虚夸”,也对经典中的“虚夸”予以批驳。这体现的是王充其与经学话语的违离。这意味着,尽管王充实用赋论产生于《诗》教传统构成的文化语境之中,但其并未对经学话语亦步亦趋。
儒家《诗》教传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文论、诗论、赋论往往因之而来,王充赋论也是在此文化语境中诞生。然王充赋论虽源于经学语境,却转而又对经学话语予以批判挑战。这固然与其“疾虚妄”思想的一以贯之有关,其实质则是对赋论理论原型、文化背景的瓦解。这种“反噬”现象虽属罕见,但其提醒论者文化语境并非万能,不仅应注意赋论与赋史的乖离,更应察觉到赋论与经学的依违。
三、“国德”理念与意识形态建构
赋兼讽颂,王充赋论亦兼包“讽”“颂”二义。对汉赋颂美功能的肯定,是王充赋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易闻晓先生指出:“王充盛推赋颂,总是带着‘国’的意识……但不定著眼歌颂帝功。”①易闻晓:《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笔者对此十分认同,并欲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王充的“颂美”赋论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与坚实的学理依据。《须颂》篇载:“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据此,“颂汉”是王充自觉追求的结果。
另一方面,这种观念的形成与王充取则经典有关,其在《诗经》等典籍中寻得颂美的学理依据。《论衡·须颂》篇载:“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在王充看来,历朝历代凡有善政必有颂音。君王励精图治而后有善政,臣子切磋琢磨而后有颂音。王充从《诗经》“三颂”中寻得颂美当代的学理依据,认为“颂汉”是合乎经义的正当追求。
其次,王充颂美的核心要义在于称颂“国德”。《须颂》篇载:“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王充主张称颂“国德”,既是其自觉追求,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
东汉前期政治相对开明,在稳定政局后帝王有余力进行意识形态建构,举凡经学领域中的白虎通会议及《白虎通义》,史学领域中代表正统史观的《汉书》,文学领域中的“颂汉思潮”,②张峰屹:《东汉初期文化创作的颂世思潮》,《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4期。皆为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其中,文学领域尤以兰台文士所撰赋颂为代表。如班固所撰《两都赋》《终南山赋》《竹扇赋》,崔骃所撰《反都赋》《大将军西征赋》《大将军临洛观赋》,傅毅所撰《洛都赋》《反都赋》,以及班固所撰《高祖颂》《东巡颂》《南巡颂》《安丰戴侯颂》《窦将军北征颂》《神雀颂》《汉颂》,崔骃所撰《明帝颂》《四巡颂》《北征颂》,傅毅所撰《显宗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贾逵所撰《永平颂》《神雀颂》,杨终所撰《神雀颂》等皆为“颂汉”为主题的赋颂文章。王充对这些赋颂十分认同: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须颂》)
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佚文》)
据引文可知:永平年间的《神雀颂》是一次“同题共作”式写作;这次写作是汉明帝授意的命题作文,形成了“百官颂上”的恢弘场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所撰等“五颂”是众多颂文中的佼佼者;王充肯定这次写作,认为具有“彰汉德于百代”的重要意义。
关于撰写《神雀颂》的原委,《后汉书·明帝纪》载:“是岁(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③[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第1235页。永平十七年,祥瑞频出,四夷来朝,百官上寿,兰台文士所撰《神雀颂》极有可能作于此时。又据《后汉书·贾逵传》:“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④[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第1235页。据此,贾逵正是凭借《神雀颂》的写作升迁为侍郎,并获得校书兰台的机会。《神雀颂》原文已亡佚,今日仅能见到“履武、戴文”①侯文学校注:《班固集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8页。之类的只言片语。尽管兰台文士之《神雀颂》未能流传,然班固之妹班昭所撰《大雀赋》却能提供一定参考:“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②[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96页。班昭与贾逵都认为雀集京师是“德优怀远”的象征,《神雀颂》所写当亦也不出此范畴。
王充虽未撰写赋颂文章,但其通过“以论为颂”③倪晓明:《王充文体意识的文学史价值——以“论”体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的方式颂美汉德。《须颂》篇载:“国无强文,德暗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如此一来,王充便将三代经典与当代文章相交融,将经义中的“颂美”与兰台文士的“颂汉”相交融,将汉赋作品与汉赋评论相交融。总结来讲,王充在《诗经》“三颂”、兰台文士所撰赋颂、自身的赋论观之间形成了“视阈融合”,这一“融合”的焦点便是“颂美”。
客观来讲,王充赋论与兰台文士赋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互文”效果。班固《东都赋》载:“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讋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④[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4页。据此,东汉明章时期,汉代在疆土层面已经远超上古三代,这正是王化遍及四海的典型呈现。王充也有类似表述:
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周家越常献白雉,方今匈奴、善鄯、哀牢贡献牛马。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牧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宣汉》)
殷、周之地,极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汉氏廓土,牧万里之外,要、荒之地,襃衣博带。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别通》)
“国土”的扩张意味着“国德”的延伸。这种“德优怀远”的观念可溯源至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⑤[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03页。“守在四夷”强调修治德行,使王化遍及海内。《汉书·王莽传》《新书·春秋》《淮南子·泰族训》《潜夫论·救边》均有类似表述,可见其不仅是王、班二人的共有观念,更堪称汉家学术共识。
“国德”不仅仅局限于疆土、版图等物质层面的扩张,还体现为文化层面的“以夏变夷”。班固在其《东都赋》中指出:“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予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⑥[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4页。服饰具备了明尊卑、别贵贱,彰德显善的重要内涵。王充也有相关表述,《恢国》篇载:“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中国文化语境中,服饰具备表德行与明贵贱的含义。《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⑦[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孔安国注:“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⑧[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白虎通义》言:“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綌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⑨[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2页。因此在班固与王充二人视野中,服饰是礼制的体现,“国服”是“国德”的象征,这是“互文性”构成的文化基础。
虽然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建构,但就结果来看,无论作品的广博性、主题一致性、体裁丰富性、创作集团性、书写自觉性,都表示这次创作活动具有广泛影响。概括来讲,班固等人以赋颂以“颂汉”,王充则以赋论“颂汉”,二者皆为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
最后,从王充对待赋颂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从文体角度而言,王充赋颂不分。实际上不只王充,汉人大多存在赋颂二体“交越互用”的情况,①易闻晓:《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盖因赋体本身便存在铺张扬厉、润色鸿业的内在属性,因此“赋体颂用”较为常见。其二,从价值判断角度来讲,王充对“颂汉”文章较为肯定,体现的是其对汉赋“颂美”功能的认同。此外,尽管“讽”“颂”操作路径不同,但归根结底皆属于“用”。王充赋论深受《诗》教思想影响,既体现为对“讽谏教化”的追求,又体现为对“颂美当代”的热诚,既是对西汉赋体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当代赋体创作实践的总结。
结语
王充赋论是实用型赋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注重赋用,轻视赋体。王充是一位“有赋论”而“乏赋作”的赋论家,尽管著述宏富,但其创作集中于“论”体文章,对辞赋几无涉及。这种辞赋理论与创作相违离的局面,使得王充赋论立论基点在“用”而不在“体”,其对汉赋语言“丽”“深”的批判,对汉赋内容“虚妄”的批评,对汉赋“颂美”功能的认同,皆是其重“用”轻“体”的明证。其二,赋论与其士大夫身份密切相关,是其整体文化思想的局部显现。士大夫以移风易俗,辅政安民为旨归,王充对汉赋语言“深覆”的批评,与其倡导“浅俗”文风相表里,皆为其士大夫身份的话语表征。“疾虚妄”与“颂汉德”是其文化思想的两大主题,“讽”“颂”结合的赋论是其文化思想的反映。其三,与扬雄、班固等汉赋大家相比,王充赋论缺乏原创性概念。其赋论是汉代赋论发展实情的反映,但未对汉代赋论发展提供实质性帮助,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故应客观、审慎地评价其赋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