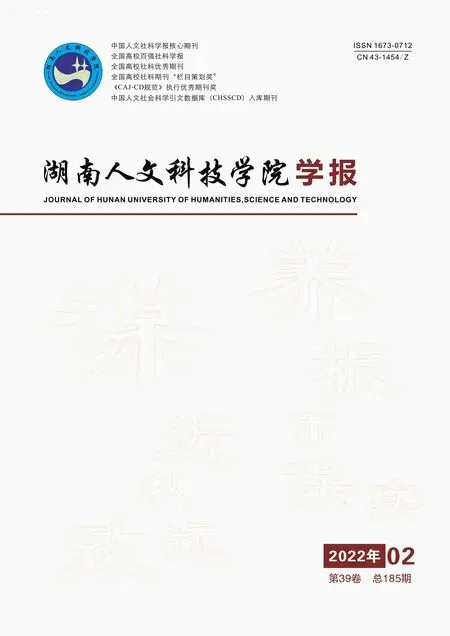北宋边塞诗的军储保障与重农思想
丁沂璐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关于北宋的军储认知,学界成果或从整体论述北宋官府的军需粮食购买与物资保障问题,或聚焦一路论述该路的粮食补给意义,或从仓储功能上论述军储的意义之重,或论述北宋职官在军储保障上的作用。 魏定飞《北宋官府军需粮食购买研究》一文从北宋的安全危机与粮食需求、军需粮食的供给情况、官府粮食购买中的时估与官府军需粮食购买的资金来源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北宋官府的军需粮食购买。 作者指出北宋的粮食收购活动“由最初的惠民政策逐步演化为增加民户负担的强制性征购”[1],反映了官府在供需问题上的平衡失当与吏治缺陷。 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2]与《论宋代军需粮草的储备与管理》[3]认为军需物资储备的多寡、物资储备在布局上的合理性,直接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安危。 程龙[4]从军事地理、粮食补给的角度论述了河北安抚使路的设置意义。 真定府路保证陆路粮食运输线的完整和安全,高阳关路保证水运粮食补给的畅通和安全。 大名府路坐镇后方,对军需粮食的统筹调拨和分配,更具有战略意义。 杨芳[5]认为宋朝的军政形势决定了仓储在整体功能上军储重于备荒。 从宋朝仓廪制度的实际运作来看,军粮仓与备荒仓虽各有所专,也能相互配合,大体无误军储、救荒之大事,说明宋朝国家调控能力的提高与实力的增强。 贾启红《宋代军事后勤若干问题研究》一文指出,转运使在北宋初年专门负责军队的军需保障,中后期也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籴买军粮、检验军粮存储与支用、检验籴买粮草好坏、奖惩籴买官员、吸引商人入中等职责[6]。 观上,学界从政府管控、机构设置等方面论述北宋的军储观念与统筹调拨。 至于北宋边塞诗的军储保障与重农思想,学界未有成熟结论。围绕边情提出问题、表明态度、总结经验是北宋边塞诗的理性特征,这种救边出路的军粮考察,在杨亿、梅尧臣、韩琦等人的边塞诗中体现得最充分,折射出可贵的价值理性与开拓精神。 下文试从军储之重的战略意义、飞刍挽粟与役力征调、粮食生产与军储购买分论北宋边塞诗的军储保障与重农思想。
一、高度认可军储保障的战略意义
北宋边塞诗高度认可军储的战略意义,并贯穿其创作始末。 北宋初期,杨亿反复论述军储之重。 “三军粒食资心计,一月星邮待捷书”将军粮供应与书信邮传并举,意在说明前者可以保障战略探索,后者能够传递情报。 “由来百粤地,曾督九年储”指出广州作为汇集百越的南方重边,曾有监管九年军粮的重要使命。 北宋中期,黄庭坚在《和谢公定征南谣》中表达出对生民艰难、粮草难继的控诉。 “汉南食麦如食玉,湖南驱人如驱羊”“未论刍粟捐金费,直愁瘴疠连营空”,仁人之心为其正谏不讳注入力量,增强了北宋边塞诗的战斗色彩。 同时的苏辙亦站在边民的立场,痛斥:“壮夫奔亡老稚死,粟麦无苗安取食。”北宋后期,晁说之对粮草不足、装备不精的军政现状深表忧惧,“莫问糇粮难卒岁,且无甲马在今朝”,便凝练地传递出诗人的忧国之情。
叮嘱与劝勉边地转运使亦为北宋边塞诗传输粮食之重的重要途径。 杨亿“泥书双笔迁郎署,粒食千金仰县官”,前句歌颂将赴任陕西转运使的黄氏升迁郎署,出守重郡,后句直指转运使调拨分配粮食的责权之重。 同样是叮嘱,晁说之的“黩兵烽燧息,积粟犬羊平”则是将息烽偃武、屯粮畜牧当作经营陕西、守卫西陲的重要策略。 晁补之“金城那可无粟守,尧舜与民宁并耕”叮嘱即将赴任陕西转运使的岳父杜纯,守卫兰州必须粮食丰裕,并指出贤君尧舜宁肯与民稼穑,也要保证粮食丰足。有时,宋人对边地财赋与粮食保障的书写并不针对转运判官所在边地,而是放眼矛盾更尖锐、冲突更激烈的其他边事现场。 冯山《送江衍巨源提举赴阙》由江衍的入蜀实况切入,中间大量笔墨围绕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展开。 其中“连兵巨费久乃定,得失未可相偿陪”“精强挽运一蹉跌,十存四五良可哀”以及“况今秦人极疲敝,菽粟贵重如琼瑰”数句,均将话题引向开支巨大、粮运艰难、役力耗损、秦人疲惫等现实问题。
当然,一旦遇上贤臣辅政、治边有术,宋人又会对边粮充足自信满满。 苏洵“郡国远浩浩,边鄙有积仓”借助边安廪实、物阜民丰来表达对田待制治边高明的赞美;吕南公“京观酋豪肉,军储府藏钱”描述了战败酋豪堆积成山、军需物资充盈府库的事实。 这种认识之重,不仅体现在对己方军储的认知上,也体现在对敌方军储的实力认知上。晁补之“降羌当有甲齐山,叛虏应无马量谷”,便是对投降羌部战甲齐备、叛宋胡人马匹不足的诅咒。当击败对手,缴获战利时,得粮多寡则成为宋人高度关注的话题。 例如,杨亿“陇右行收万里地,关中坐致九年储”勾勒郑氏出帅陕西的美好蓝图,即收复陇右万里疆域、保证关中数年的粮食供应。沈辽“槖驰牛马以万计,白米青盐归我储”真实叙述了宋夏交战中宋军缴获敌方战马、牲畜以及粮盐无数。
二、飞刍挽粟与役力征调的深刻认识
北宋边塞诗对飞刍挽粟及其背后的役力征调亦认识深刻。 除了静态地认识军粮本身的战略意义,宋人更注重动态考察军粮运输的畅通与否、役夫保障与补给情况。 北宋诗家,梅尧臣对馈粮之重剖析最深。 庆历元年,宋夏激战,圣俞呼吁:“塞上备胡羌,关中调兵食。 秦民尚苦输,汉吏勤求职。”嘉祐五年(1060),宋夏边界冲突,圣俞作《送陕西都运彭待制》重申军储之重:
塞下兵难去,关中粟未多。 君心同汉帝,粮道得萧何。 函谷马蹄入,渭桥车辙过。 地形终险固,山色旧嵯峨。 不愧先贤传,重听得宝歌。 归来奏天子,安稳看鸣珂。[7]1144
都转运使“经度一路财赋”,主要负责核实收入与供耗、储备与帐籍,因此圣俞反复论述粮储充足、粮道畅通。 当年刘邦坐定关中,封侯授赏,萧何功居第一,在曹参之上,正因其于楚汉之争中“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鉴于关中地势险要而粮食不丰的事实,诗人渴望粮道畅行堪比汉代萧何治理之时。 “马蹄”“车辙”营造的事境贯联将紧锣密鼓、源源不断输送粮食的场面描绘得十分生动。“先贤传”是记录汉晋时期乡里贤达的人物传记,收录于《隋书》。 圣俞勉励彭氏勤政爱民,治绩昭著,定入此传。 今人永田拓治认为“上计制度”对“‘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8]起着根本的导向性作用,作者与圣俞为谙熟吏治与颂贤之辩证关系的隔代知音。 “得宝歌”,唐玄宗时乐曲,因颂当时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治绩而作。 “重听”此歌,寄托了诗人对彭氏通运渠、引租赋、聚物产等甘棠惠政的期待。 结尾两句顺势而出,描绘出彭氏面圣奏事、载誉而归的盛景。
在《送河北转运使陈修撰学士》一诗中,圣俞传递出同样的寄托:
河隍多宿兵,兵食固所须。 幸时不战斗,畜养安可无。 古兴十万师,七十万家辍耕锄。今来岁调饷,且与往昔殊。 不使民转挽,但使民归租。 急缓实塞下,商贾以利趋。 关西河东亦如此,军食虽足民实虚。 公乎抱长才,当有所画谟。 应不贷内府,重锦象牙明月珠。边城预自足,宁待临事谕。 莫令汉庭臣,独言桑大夫。[7]631
此诗开门见山,指出北宋御夏河湟,居安积储等现状,继而揭示由此带来的战事伤农、转饷累民等事实,因而建议陈氏对边需巨大、边民穷困等问题做深入思考。 针对北宋边情,梅尧臣认为陈氏身为河北转运使,决不能寄希望于内府拨配,而应未雨绸缪,自给自足,推行有助于边事与边民的经济政策,再现当日“桑弘羊”屯田实边的丰功伟绩。题为送友,实为议边,重农爱民之心,如见肺肝。在《孙子注》中,梅尧臣结合征发、馈粮、作战等诸事表达了爱惜民力的深刻思想。 言征发者,“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公家费,害也;”[9]言调饷者,“举师十万,馈粮千里,日费如此,师久之戒也”;言征战者,“速则省财用,惜民力也”。 这些减少征发、速战速决的思想无不是基于爱民、节用等爱国情怀的深切思考。 除此之外,送别泾州良原县主簿何鬲,圣俞叮咛:“胡马自偷牧,汉农宁废耕……县版固当重,调轻无与程。”送祖择之赴陕府,又有“天子忧民切,行当务劝桑”之劝勉。 由此可见,尽管圣俞不得亲身对边民抚慰爱养,却能够将其治边之切化作激劝鞭策,鼓舞边臣大展宏图。
除梅尧臣外,北宋中期还有大批诗人关注馈粮之重。 蔡襄“赐衣靡国帑,走粟填边庾”指出宋夏交战频繁,不得不厚赐边卒,填充边仓。 欧阳修“荷戈莫言苦,负粮深可悲”直指负粮之艰远、稼穑之苦,强至“萧相馈饷堪仰给,马卿建节忽西之”将萧何转漕馈粮之功与司马相如持节谕蜀之力相提并论,以此激励新任的益州转运使。 相较于上述诸人的理性与深沉,刘挚的馈粮认识要轻松许多。“河湟虮虱玩天恩,饷馈驱驰不足论”表达了宋人对河湟吐蕃不以为然的坚定态度,指出对阵吐蕃的粮食补给与后勤供应皆易如反掌。 事实上,交战与备边的粮食运输远没有刘挚想象的那么简单。 陈师道“馈粮千里古无策,木牛流马功不极”,指出长途馈粮的运载需求恐怕木牛流马也不能实现,况且除了负载,粮道通畅、安全保障也是馈粮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 晁补之就元丰四年五路伐夏展开议论,“将军拳勇馈不继,痛惜灵武奇谋空”,指出王中正与种谔所率东北路军队恰恰是因粮运不济而未能围攻灵州,为其无功罢兵而深表遗憾。 至于截人粮草,更是难上加难,蔡肇“奇兵缭背断馈粮”就将宋人绞尽脑汁阻绝夏军粮道阐释清晰。 与上述诸诗稍有不同,沈辽与郑獬均从漕运角度揭示馈粮之重。 沈辽“翻蒙羽檄督军粮,灵渠首运三千石”指出宋将卢总在对阵安南大将时羽檄频传、监督粮运,首次就以灵渠运粮三千石之实;郑獬则纯粹以汴河为题,对其漕运功绩予以高度赞扬,其中“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指出汴河的承载之广,金银、粮食均在其运载之列,稍后的“因以转实边,边兵皆饱腹”两句则客观陈述了汴河漕运以实边、馈粮以养兵的至伟巨功。
北宋后期,诗人李复创作了大量心系粮运的边塞诗,记录夜宿宋夏边地之事。 “督运晚宿明堂川,凿冰饮马沙冈窟”指出诗人监督粮运夜宿明堂川,天寒地冻,护粮役卒只好凿冰以饮马,夜宿沙冈洞穴;“护粮将军夜不来,敦然独宿在车下”指出护粮将军夜不巡逻,役夫只好夜宿粮车之下以保军粮无虞。 诗人经过河东临晋县,恰逢朝廷调发,“千里馈粮人未返,百丁团甲户无余”聚焦馈粮路遥、险不可测、征调五花八门、壮丁无一漏网的人间惨剧。 诸作之中,《兵馈行》注目防塞役夫,堪称巨制:
调丁团甲差民兵,一路一十五万人。 鸣金伐鼓别旗帜,持刀带甲如官军。 儿妻牵衣父抱哭,泪出流泉血满身。 前去不知路远近,刻日要渡黄河津。 ……
古师远行不裹粮,因粮于敌吾必得。 不知何人画此计,徒困生灵甚非策。 ……
来时一十五万人,凋没经时存者几。 运粮惧恐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馈军。 比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 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 ……将军帐下鼓无声,妇人在军军气弱。 星使奔问来几时,下令仓皇皆遣归。 闻归南欲奔汉界,中途又为西贼窥。凄恻自叹生意促,不见父夫不得哭。 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望北。[10]
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11]葛晓音教授以杜甫歌行为例辨体,指出“行”诗“以波澜不惊、连绵起伏的节奏平稳推进”[12]适宜叙事的特点。 就此诗论,体式的确带来了连贯叙事的便利。 开篇八句径直叙述官府征调役夫之实,役夫持刀械甲,登程鸣鼓扬旗。 冠冕堂皇的出征背后,是役夫与家人的抱头痛哭,生离死别。 一旦征调为役,他们就要完全服从行军计划与上级安排。 之后十六句展开叙述役夫的职责与艰辛,他们既有千钧重负,又要备敌偷袭,加上道路险阻,行进缓慢,真正运至边地的粮食并不能维系多久。 鉴于此,诗人痛斥馈粮之弊,呼吁学习“因粮于敌”,既反映了探求韬略之切,又彰显了救世济民之诚。 诗人之所以大声疾呼,除了基于运粮艰辛、耗损巨大等现实考虑,还与其深切的民生情怀密不可分。 因此,诗人于下文中花费大量笔墨来论述役夫凋零的凄惨、官府征役的狰狞以及人户对催征的反抗与畏惧。最令人叫绝的是,李复选取女扮男装、冒充役夫这一典型事件,既有利于推动情节趋于激烈,又将官府的穷凶极恶、吏役的残酷贪鄙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果,在家不得相伴的夫妻与父女却在馈粮队伍中得以团聚。 后来,冒充男丁的妇女被查验遣归,返乡途中不幸为夏人欺凌,生不如死与团圆心切交叠缠绕,五味杂陈,去住两难。 这种“一层紧于一层”的效果乃七言长篇的体式优势所成,叙事的深化与情感的推进在层递复沓的结构中圆满实现。
三、高度重视军储保障背后的生产与购买行为
北宋边塞诗高度重视军储保障背后的生产与购买行为。 寓兵于农,因能兼顾粮食生产与保家卫国的双重需要而备受宋人青睐。 对此,欧阳修明确表示:“从来汉粟劳飞挽,当使秦人自战耕。”诗人认为依靠运输根本无法解决陕西的军粮供应,陕西人民应耕战兼善,才能自给自足。 较之欧阳修,王陶对寓兵于农的追慕更加具体,“君不见镇戎千顺弓箭手,耕种官田自防守”便一语道明镇戎弓箭手耕战两不误的特殊性质。 关于弓箭手,知镇戎军曹玮最早对其性质与职能予以界定,并结合当地边民的应募情况出台如下政策,即“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13]4712。 庆历年间,河东都转运使欧阳修借鉴镇戎经验,意欲将弓箭手推广至河东多地,范仲淹奉诏实地考察,认为可行,遂支持其说。于是,宋廷于“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余户,岁输租数万斛,自备弓马,涅手背为弓箭手”[13]4712。 可惜,此议最终为并州明镐挠议乃止。 至和二年(1055 年),知并州韩琦再次派人考察,认为忻州、代州、宁化军与火山军等地若长期废弃不耕恐为敌方耕占,建议代州与宁化军仿照之前的岢岚军例,“距北界十里为禁地,余则募弓箭手居之”,最终“得户四千,垦地九千六百顷”[14]4317。 观上可知,尽管欧阳修未于诗中细论弓箭手的耕战兼善,但是,他却在边议中畅谈此策,并于边地躬行实践,其因地制宜、学习先进的钻研精神的确令人敬服。 这种通达的御边理念,亦见于《乞与闻边事》《再奏与闻边事》两章,表达了自己身为转运使亦应参预边事的诉求。 文中所论“所贵稍得与闻边事,至于储蓄粮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体紧慢,不至乖方”[15]1815,“臣伏以转运使虽合专掌钱谷,不与兵戎,然河北事体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经营……则本司得知边事缓急,凡于计置准备,不至紧慢乖方。”[15]1816这些预边诉求正折射出欧阳修本人对转运使统领财赋、知晓兵事的职能诉求。
儒将韩琦对寓兵于农认识最深刻,实践方案也最有效。 在《次韵答运使杨畋舍人》中,韩琦充分表达了对昔日民兵制度的追慕:
轺车勤按问,并部此先行。 籴重伤农业,年丰报力耕。 几时苏俗困,异日复民兵。 公策方经远,提封可坐清。[16]
此诗寄答河东转运使杨畋,李之亮先生编定此诗作于至和元年,与杨畋仕履相合。 韩琦之所以与杨畋谈论并州农事与边情,原因有四:一是基于杨畋河东转运使的身份;二是杨畋氏出于并州的地缘关系,杨畋曾伯祖即北宋名将杨业,杨业为并州人;三是杨畋进士及第后,入仕最初的职务即为并州录事参军;四是韩琦当时出知并州。 以上四个因素,成为韩琦与杨畋探讨并州民生、农业发展、兵力保障诸事的前提。 之所以在至和元年讨论,亦关乎时艰。 至和元年,北宋多地罹灾,民不聊生。 正月,开封大寒,民多冻死;二月,陕西、河东军衣不足;三月,京西饥馑。 面对天灾民困,政府全力营救,或为民疗疾,或输出缗钱,或鼓励富人纳粟赈灾,以救时弊。 除十一月传来河北丰收佳讯,即令“缘边州郡便籴军粮三百万、马料三百万”[14]4290,可稍宽圣心外,其余消息确实堪忧。
全诗按照勤政、重农、纾困的理路贯穿,指向早作谋划、安民济物的边功激励。 “籴重伤农业,年丰报力耕”承接首句的勤政劝诫顺势而出,为民减负、鼓励耕种之意毕现。 鉴于至和元年的民力困乏,宋人对冗军耗资之巨与边地虚估之弊都纷纷展开议论。 其中知谏院范镇指出殚竭民力既有损天合,又催生灾害,于是建议参照天圣年间的民赋数据,减免百姓租赋。 可知,韩琦“籴重伤农业”的呼声绝非平地惊雷。 关于河东和籴之弊,韩琦早在庆历年间即作《论河东税外和籴粮草奏》,直指河东籴粮数目巨大、税外负担摊派严重、官吏富民惟务掊克等弊端。 “几时苏俗困,异日复民兵”两句,既凝结了爱惜民力的深情,又表达出恢复民兵的愿望。 事实证明,韩琦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实施的。 韩琦的重农爱民,不仅体现在对和籴的思考上,还表现在反对盲目兴役,保障农业生产。 康定元年,韩琦力沮征民修城,提出以兵代役与富民助役相互参用的方案,以免妨害农事。 至于其恢复民兵的构想,亦曾落实到实践。 庆历元年知秦州时,韩琦便建议除常规兵马驻扎外,再增置鄜、庆、渭三州各三万人,对于益兵数目之大与“骤然招置”之难,韩琦力陈“拣刺土兵”以为预备。
观上,宋人思理清晰,诗意深刻,致力于寻求军储保障与后勤供应等物质层面的支持。 从军储之重的表象,到飞刍挽粟的消耗,再到和籴伤农、寓兵于农的出路探寻,无不镌刻着鲜明的突围色彩。
四、结语
北宋边塞诗在军储保障、军粮馈运等论述中彰显出剖析边情、突出重围的理性精神,这种深刻清晰的献策理路与陈情言说缘于诗人身份的巨大转变。 北宋诗人集显宦、学者、诗人于一身的“复合型身份”,决定了其诗已渐染学人之诗、政治家之诗的鲜明色彩,即便张大豪情,亦有清晰理路,并在粮食生产、军储馈转、役夫征调诸事中彼此勾连,由表入里。 若要探究诗人理性的根源,还应回到取士与用士制度寻找答案。 重策论、轻诗赋的取士制度与广言路、重纳谏的监察制度催生了人的理性精神,亦渐渐影响其诗歌创作的态度。 北宋诗人既怀有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同时又保持着忠君体国的治世情怀,在边防动荡、作战不力的时事催生下,其参政议政、谈边论兵的主体精神难免被激发放大,其边塞诗亦呈现出持重务实、激壮慷慨的风格特征。 加之指向明确,论辩清晰,因此共同推助了北宋边塞诗在突围谋划中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