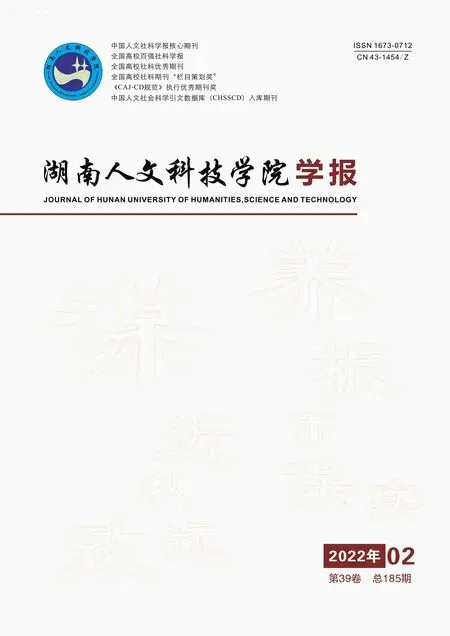文学“乡土”的民族国家精神
——新世纪湖南西部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郭景华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进入新世纪,对中国文学而言,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时序更迭,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一些促使文学必须完成自身革命的社会时代变化。 从1990 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有管理体制方面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改革,也有作家自身和文学创作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和选择。 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造就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机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骚动之后,中国作家们“大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创作心态,虽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仍然不免要受读者市场乃至大众传媒的影响,但较之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一窝蜂地涌向市场,却少了许多盲目性,增加了许多自觉和自主的意识。 在题材选择、主题确立和艺术表达方式乃至文体和风格的追求方面,作家的自我定位一般都比较明确,大都是本着自主的选择而不是追随市场潮流,因而像90 年代出现的那种一浪接着一浪的创作‘热’潮现象不复出现,这表明作家的创作主观能动性已大为增强”[1]。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中国作家们还得逐步接受全球化、网络化的挑战。 那么,作为在1930 年代和1980 年代就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精彩华章的湘西文学创作,在新的世纪到来以后,能否再创辉煌,实现对前辈作家的超越?在艺术地掌握湘西世界的文艺符号表现行为中,湘西文学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想象共同体”作用?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旨所在。 本文想就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做一番巡礼,通过检视一些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描述当下湘西长篇创作的整体风貌,总结湘西作家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地域文学经验,发现湘西作家在湘西文学创作中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国家精神,为我们重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一、历史记忆:湘西长篇写作里的地域历史文化图景
任何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与其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风民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促使地域作家总体风格的形成。 同时,地域文学的写作又加深了人们对该地域的总体性印象,强化后来的作家在继承前辈作家创作传统时刻意去凸显那些地域文学所谓的“成功”风格特征。 封闭、野性、雄强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1930 年代的湘西书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1980 年代,一部《乌龙山剿匪记》的电视剧再次激发了中国观众对二十世纪中期发生在湘西地域“匪事”的历史想象,鄙陋、狡诈、凶残是“湘西土匪”在影视剧里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休闲旅游流行,在表现湘西文化的文艺作品里,湘西的血性暴力主题有所淡化,而展现神秘的湘西民俗风情的文艺作品开始流行。可以说,在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版图的绘制中,“湘西”已变为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符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以鸿篇巨制来全面反映湘西历史、表现湘西民俗文化的长篇小说创作,便应运而生。
在新世纪后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队伍里,除了早先1990 年代在全国文坛就已爆得大名的王跃文、向本贵继续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还涌现出田耳、于怀岸、邓宏顺、刘箫、蒲钰、李怀荪、黄光耀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 这些湘西作家以他们的丰厚的创作实绩,有力地表现了新世纪湘西文学创作的强劲实力。 具有远大抱负的湘西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新世纪以来湘西作家们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达40 多部,其中王跃文的《苍黄》(2009 年)、《爱历元年》(2014 年),向本贵的《凤凰台》(2006 年),于怀岸的《巫师简史》,田耳《夏天糖》(2011 年)、《天体悬浮》(2015 年),邓宏顺《红魂灵》(2006 年)、《贫富天平》(2010 年)、《天堂内外》(2014 年)、《铁血湘西》(2015 年),蒲钰的《我还活着——一个湘西土匪的自述》(2008年)、《脑袋开花》(2009 年),李怀荪的《湘西秘史》(2014 年),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2013年)、刘箫的《筸军之城》(2014 年),黄光耀的《土司王国》(2013 年)等作品曾引起过相关论者的评论,但更多的湘西长篇如江月卫的《女大学生村官》(2014 年)、《回不去的故乡》(2018 年),蒲海燕的《高考来了》(2017 年),还未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评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在诸多的湘西长篇小说作品中,湘西作家对湘西历史文化图景的诗意建构,是一个突出的创作现象,在整个的湘西文学写作当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不仅反映出湘西作家对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那份自觉,而且还反映了湘西作家对于中外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它越来越显示出湘西作家自信、成熟的风范与气度。
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湘西作家,对挖掘、表现湘西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这些湘西作家,其中有些本身就是对湘西地方文史有着精深研究的地方学者,因此在他们创作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自然不会满足于前辈湘西作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湘西历史认知;同时他们对近些年为了开发大湘西旅游而刻意去凸显湘西巫蛊传说等神秘文化的“伪民俗”行为更是非常反感。 这些湘西作家立足于田野调研、文献考索,以艺术的形式,诗意地建构着恢弘的湘西历史图景,完全刷新了读者对湘西历史的认知。 例如创作了《湘西秘史》的老作家李怀荪,在写作这部号称湘西民俗“百科全书”的巨著之前,长期从事地方民俗研究,尤其是对明清以来的湘西地方民俗、地方戏曲浸淫颇深,以湘西民俗和地方戏曲研究享誉业界,但他退休后,仍然觉得有些遗憾:“二十年来,虽然我已有一百多万字的著述行世,但我所掌握的资料,有许多都还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 我的那些研究湘西历史文化的著述,虽然也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但除了发表在报纸上的随笔短文以外,受众还是非常有限的。 一些发表在海外的专著、论文,内地很难见到。 我不希望多年的辛劳,变成了自个儿的孤芳自赏。 湘西这片土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湘西,了解湘西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我想,只有写一部反映湘西历史文化的大书,我多年的研究成果、生活积累才能更好地派上用场。 我认定,通过几十年对湘西的了解与研究,再加上早年从事戏剧、文学创作的经验,我完全具备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条件。”[2]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宏愿,李怀荪不顾身体不便,历经14 年,终于精心创作出了一部80 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湘西秘史》。 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以湘西四大名镇之一浦市(小说中为浦阳镇)为原型,借用张、刘两家商业巨贾儿女的情感纠葛为主线,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湘西沿河沿江的商业重镇如何由盛转衰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湘西秘史》这部长篇小说,与过去同类题材相比,在对湘西历史文化的纵深呈现上有了巨大的突破。 一是《湘西秘史》对近代以来的湘西商贸文化有非常生动的、详实的再现,弥补了过去的湘西长篇小说在表现历史题材时过分倚重军事(匪事)或神秘民俗的创作路向的不足;二是借助从江西迁来的张、刘姓等汉族商业巨贾在湘西地域的商业或婚丧嫁娶等生活日常的书写活动,非常细腻地呈现了近代以来湘西地域汉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与李怀荪创作立意追求相类似,湘西龙山作家黄光耀作为一名矢志研究并表现湘西土家族文化的地方学者,他也有建构整个湘西土家族历史文化大厦的雄心壮志。 “我发现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陨落,土家族的文化因子正在嬗变——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正经受着外来文明最强烈的侵蚀与冲击,如若不加以有效的传承与保护,这个痛苦嬗变的过程将从此加剧! ……我想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保存下来,于是我选择了小说作为包装的外壳。”[3]正是怀着这种文化自觉,黄光耀一口气推出了其自称“土家三部曲”的《白河》《虎图腾》《土司王国》三部长篇小说。 在《土司王朝》中,作者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与细微处,选取最能体现和代表土家族文化和土家族人精神的巫傩巴文化作为书写对象,以田氏容美土司三代的兴衰更替为中心线索,编织出一部集合了南明政权、农民军与清王室等各种政治势力以及土家族各色人等百年历史的宏大画卷,从而使小说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生活广度方面,皆具有了鲜明的史诗意识和史诗品格;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白河》以家族命运书写切入,让生活在白河边上的“凡夫俗子”的命运音符,随着白河今昔变迁在不断地变奏,表达了白河是一条“生命之河,人性之河,宿命之河”的写作宗旨。
湘西凤凰作家刘萧的《筸军之城》以一个充满魔力和奇诡风俗的小镇——镇筸为背景,既着力展现了湘西凤凰历史上筸军兴衰存亡,也非常生动地描写了生活于此的普通湘西“饮食男女”的家国情怀与爱恨情仇,从而艺术地再现了湘西地域文化的灵魂。 “历史上,这个石头城出生的男人,无一例外都被送到朝廷绿营军队里去当兵,磨炼他们的品质和意志。 有一种信念一直随着他们成长,那就是为国打仗,立功受奖,舍身成仁。”[4]女人们则执着一生守候她的爱情,直至生命萎去。值得注意的是,《筸军之城》的写作,作家非常刻意地用那些颇具民族文化意味的符号来命名笔下的人名、地名、称谓,非常细腻地镂刻着原先只存留在地方史志文献里的苗汉民族杂居的集体记忆秘史。 文本借助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充满张力的人物性格,古老神秘的地域文化,让筸军的灵魂、湘西的精魂,再次复活,揭示了湘西人尤其是苗族人的一些内在的、本质的、与众不同又不乏共性的生存秘密。 这是一部虚构的历史,但的确是真实的虚构。
二、现代转型:湘西地域近现代变迁中的“文学想象”
新世纪以来的湘西作家们,不仅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对二十世纪以前的湘西历史做了回溯,而且对处于现代历史文明进程中的湘西地域社会艰难的社会转型,也有不同以往或流俗的表现,在小说文本的表现技法上也有长足的进步。 如果说以往湘西作家的历史观念受制于既往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对湘西历史认识稍显单薄片面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湘西作家们立足于民间立场,广泛吸收新时期以来先锋作家对人类或民族历史的文学表现的新技法,并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体验,对过去的湘西历史作多方位多层次的检视,并以各自擅长的文学叙事形式,竭力追求湘西历史世界呈现的“陌生化”效果。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耄耋之年完成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5](以下简称《无愁河》),以非常“私人化”的叙述笔调,儿童化的视角与成人历史记忆相交织,回望湘西近百年的历史风云。 在随心所欲浪漫无羁的语言文字背后,是作家深刻的故乡记忆和生命体验,《无愁河》第一部集中笔力展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朱雀城”(以湘西凤凰城为原型)社会构成的各个侧面,它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生活其中的“三教九流”人物的各种欢乐与悲苦,呼吸和悸动。
《无愁河》可以说是一部浓墨重彩的历史生活画卷,一幅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边城风俗图画。 被誉为“湘军五少将”之一的于怀岸,将1980 年代中期就传入中国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技法与湘西地域的神奇的巫蛊等民俗文化融为一炉,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家族小说的情节模式,创作了一部颇具湘西地域文化风格和气派的长篇佳作——《巫师简史》[6]。 这部长篇以一个虚构的村庄“猫庄”历史变迁作为故事表现的空间场景,以一个“巫师”家族的兴衰作为故事情节编织的线索,讲述了一个湘西土著民族部落如何从一个简单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一个复杂开放的近现代社会的艰难过程。 由于小说在表现“猫庄”这个湘西土著民族部落的社会转型或者说是文明进程时,跟整个乡土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具有“同形同构”的特征,我们可以把“猫庄”看做是一个“乡土中国”的缩影,《巫师简史》简直就是一部传统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型的“文化寓言”[7]。这样一个乡土中国的转型故事,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其他地域所创作的各种类型的乡土小说中,多少可以看到非常近似的书写,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所兴起的家族小说,更是让我们在讲述乡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故事中多少有些审美疲劳之感。 但是在阅读《巫师简史》(初版原名《猫庄记》)时,我们还是不时会被作者那种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符号形式激发出相当的阅读快感,同时也会被作者在特定语境中构想出来的人物形象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感动。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征,不仅在于它可以对某一地域的文化作一种生动地呈现,而且反过来也会强化这种文化自身的建构。 湘西的巫蛊文化,本身作为湘西一种有代表性的神秘的宗教或民俗文化,在新时期孙健忠、蔡测海等湘西作家的文学作品里已有表现,但在整体上它们大多都还只是从属于现实题材,仅仅只是作为现实生活场景中的“陌生化”的一种表现手段。 但是在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中,巫师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贯穿了小说的始终。 巫师赵天国面对历史大潮对“猫庄”的冲击,怀抱着传统士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让充满传统道德伦理的“善”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承受普遍的精神拷问,从而构成小说叙事的全部架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
蒲钰的《我还活着》[8]以一个普通湘西土著农民狗娃的视角,以一种恢弘的视野,展现了湘西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直至新时期差不多40 年的历史变化历程。 小说主人公凭着一种痴情的信念,一股坚忍的生命力,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岁月,克服种种艰险,顽强地活着,最后终于等来国家政策的落实,晚年享受着一份军人的光荣。 《我还活着》的叙事既是一个普通人的坚韧生命传奇,也是一部湘西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传奇。 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活着》还构成了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学精神建构的某种补充。 如果拿《我还活着》的狗娃形象与余华的《活着》里的福贵形象做一个比较,出生山野的狗娃显然比“先富后衰”的福贵有更多的生命硬度和抗争精神,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普通民众的多样性、复杂性的精神气质也由此自然得到呈现。 蒲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脑袋开花》[9],主题也是表现湘西普通人的顽强生命精神,但叙事角度和艺术特色又有了一些变化,它是一部带有家族传记色彩小说。 小说中以“我”爷爷蒲地流的传奇人生作为叙写对象,通过对一个具有侠肝义胆、本领高强同时又不乏风流的地方自卫队长的形象刻画,写出了一代湘西人的爱恨情仇,讲述了一个另类的湘西剿匪故事。在这部小说里,蒲钰的语言更加汪洋恣肆,古朴、粗野、粗犷的山歌荤调子,跟他笔下生猛鲜活的人物形成自然对应,但有时也缺乏节制。 由于这部小说故事强烈的传奇性和曲折性,因此2009 年曾被改编为电视剧《边城汉子》,在文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邓宏顺的《铁血湘西》[10]取材于发生在湘西地域的真实的“湘西事变”历史事件,通过对湘西纵队陈策、湘西王陈渠珍、匪首张玉琳等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写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域各种武装势力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这对以前那种敌我对垒战线分明的湘西现代政治军事历史的文学表现是一个极大的拓展,尤其是小说在对湘西各种武装势力的对抗描写中,湘西民众包括进步地下力量遭遇的苦难和牺牲,有着直逼人心、惊心动魄的力量,让人生动地感受到过去湘西儿女生存、生活的异常艰辛,感受到现在湘西和平宁静生活的来之不易。
三、现实写真:湘西普通民众当代生活变迁记录
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不仅在历史题材的拓展上和创新手法上各擅其长,各呈其彩,在现实题材的书写和表现上,也不遑多让,颇具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过去那种长期的封闭状态已有很大改观,湘西地域大多数县市,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民众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此,对于长期处在“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氛围中的创作主体来说,长篇创作要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非常不容易。 湘西的作家们迎难而上,在各自擅长的题材领域,做出新的探索,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在表现湘西地域多民族生存、精神状态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紧密联系方面,以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历史文化变迁的长篇最具特色。
王跃文的《苍黄》[11]以乌柚县县委办主任李济运为视角人物,以县政府选举事件为线索,展示了一幅触目惊心而又光怪陆离的基层官场百像图。 李济运面对官场人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困顿,让其呈现出灰色人生的一面,在满足了普通民众窥视欲望的同时,也让我们对置身其中的官员的复杂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小说以《墨子·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作为扉页题辞,又以一幅画有一个欲倒非倒的花瓶的油画及小说按语继之,尤其可见作家的良苦用心。 王跃文的另一部长篇《爱历元年》[12]以一对都市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发展历程为主线,通过叙写他们恋爱、结婚、生子、事业、婚外情、亲子错抱等生活事件,来反映都市知识分子随着境遇和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各种情感追求和欲望挣扎。 围绕这条主线,小说还展现了近30 年来社会时代变迁中诸如房地产开发、上访、拆迁等各种社会矛盾和纠葛。 小说最后,让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的各色人等殊途同归,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恢复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 在小说故事的叙写中,作家竭力想表达出一种维持正常婚姻家庭的真义,那就是对亲情的守望或家庭责任的维护。 为此,作家对社会现实中各种有可能影响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功利因素都作了某种程度的过滤,他对男女情感的表现进行了提纯,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书写。
苗族作家向本贵早先凭借主旋律作品《苍山如海》声名鹊起,他在21 世纪初出版的《凤凰台》[13]以长工出生的退伍军人刘宝山回到家乡凤凰台担任基层干部为主线,刘宝山一心带领乡亲们“吃饱肚子”“住上瓦房”,历经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折腾了20多年,越折腾越穷,甚至眼睁睁看着亲人活活饿死,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这两大愿望才得到实现。
邓宏顺的《贫富天平》以一群地级党委行政领导在处理前来投资的商人侮辱和损害底层弱势群体事件时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处置措施,提出了内地发展经济中引人深思的问题:发展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文明、伦理作为代价? 为了保持一地的繁荣,是不是一定要容忍“为富不仁”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尊严? 小说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当下值得关注并深思的问题:“在我们身边,贫与富,强与弱正朝两极加剧,作为党政部门的领导,如果当不好二者之间的天平,那就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大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14]小说的结尾,市委市政府官员在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的做法上殊途同归,让读者看到基层官员的良知和人性的温暖。 邓宏顺另一部长篇《天堂内外》[15]通过刻画一对从旧时代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夫妇半个世纪的人生遭遇,形象地展现了湘西民众生存状态和精神上的悲苦,它有点类似于新时期的《李顺大造屋》。 湘西底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在这个追求路上所遭遇的快乐、挫折和悲伤,与国家政治、经济等强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息息相关。
蒲海燕的《高考来了》[16]以某省重点中学南边一中高三学生在迎接高考复习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以及家长和学校领导师生采取的不同的处理办法和方式,形象地揭示了现阶段师生面对高考那种复杂的人生态度、情感和道路抉择。在被誉为“国考”的高考面前,中国人那种普遍的焦虑和共同的期待,袒露无遗。
如果说王跃文、向本贵、邓宏顺、蒲海燕等长篇小说旨在通过不同现实题材的人物形象刻画,表现出作家们对共和国成立以来湘西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共同关注,同时也表达了作家们对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层面的理性思考。 那么,青年作家田耳便把目光集中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大潮激荡下的社会底层人物身上,非常“客观”地展示着他们的离合悲欢。在他创作的长篇《夏天糖》[17]里,就是一幅由农民、司机、小贩、妓女、流氓、“白痴”、教师、医生,县城群艺馆职员、地下导演、无所事事者、游手好闲者等底层人物构成的多元的基层社会生活场景图。 场景图依次陈列出来的这些草根人物,大部分本该是与大地血脉相通、血肉相连的生命,但他们却随着新世纪以来的城镇化建设大潮逐渐远离了泥土与乡村,成为彷徨无根、漂泊轻飏的流浪者。 《夏天糖》是作家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一次整合,更是其观察时代进程的一种深度开掘。 与其前辈作家沈从文相比,同样是写“凡夫俗子”,田耳小说没有集中展现迷人的乡村习俗与田园风光,也没有着意刻画朴素的乡村道德与民风民俗。作家尽管在凤凰生长,但时代带给他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已让他无法再把笔下的乡村模拟成他的前辈作家沈从文笔下的世外桃源。 在田耳笔下,我们看到,城市化进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发展趋势,普通个体要融入城市,寻找出路,就需要培植他们的理性意识与个体精神,而这正是当下普通中国民众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所缺乏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通民众还来不及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就与城市化乃至全球化文明进程发生了遭遇战。 正是基于对于城市化或全球化进程的反思与忧患,以及对底层生活的深入观照,田耳不仅让作品更为真切具体地再现了当下农村现代化进程失序的图景,也生发了有识之士关于城市化进程更为深刻的思考。 由此看来,与其说田耳是在为农村牧歌情调与朴素道德精神的丧失而眷念伤感,还不如说作品在感喟新的文明秩序与市民道德未曾生成。 他的另一部长篇《天体悬浮》通过内地“佴城”基层派出所两个辅警符启明和丁一腾人生命运的沉浮,表现出作家对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的某种批判和人性的深度勘探。 在故事讲述中,作家尽可能充分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和复杂性,把自己的批判立场淹没在故事场景和画面中,通过一些细节不露声色地呈现出来。小说塑造的符启明这个形象非常具有人性深度。符启明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生性倔强又精明能干的城市青年。 按照小说叙述者的说法,符启明是“道士命”,这种人物最大特点在于不认命,“他们通常都会离开家乡,凭着自身古怪的才能,百折不挠的个性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到处折腾。”[18]在作家笔下,主人公凭借近乎“神化”的社会和人性洞察能力,游走在社会灰色地带,他一方面“哗啦啦地造钱”,一方面又痴迷于高倍望远镜仰望星空,这是一个充满人性悖论的角色。
四、结语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湘西历史文化题材挖掘,还是对政治权力文化异化、对社会现实的底层写真,都弥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 从纵向来看,从黄光耀的《土司王国》、李怀荪的《湘西秘史》、于怀岸的《巫师简史》、邓宏顺的《铁血湘西》,直至向本贵的《凤凰台》、田耳的《天体悬浮》等,湘西近300 年的恢弘历史画卷,依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历史或现实书写,其底色灌注了地方文化生命的“国家”精神,呈现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元素。 《土司王国》中的最后一任容美土司,终结于十八世纪雍正时期的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既是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生动写照,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融于国家主体文化的必然归宿。 《湘西秘史》中从江西汉地迁来湘西的张、刘两大商业巨贾的商业活动和婚丧嫁娶的生活日常,在完全刷新了旧时湘西昔日蛮荒印象的同时,民族文化融合的历程也得到了形象的再现。 《巫师简史》更是以一个深居湘西僻地土著家族的充满悲壮色彩的现代变迁,揭示了湘西现代性的被动性。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数量极为可观,在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上都较以前具有了长足的进步。 湘西作家们在保持着和时代同步,广泛借鉴国内外文学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对湘西这片热土上发生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生事象,进行着满腔热情的书写。 一方面,湘西作家以巫风楚雨浸润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一个非常宏阔的历史时空视野中,大胆地想象、虚构、描写、反映了湘西地域自明清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以艺术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湘西社会发生的巨大转折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前景。 另一方面,湘西作家又继承了五四以来“写人生”的良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益于二十世纪以来来自异域的文学经验的撒播,在湘西这片沃土上进行广泛的耕耘。 可以说,湘西地域文学创作,既得益于中外文学传统经验,同时,也以沉甸甸的文学实绩,丰富和补充着新世纪的当代中国文学。 新世纪的湘西文学创作主体,或是湘西历史文化精深专研者,或是湘西现实巨变的见证人。 他们都以各自的艺术符号方式,感悟着湘西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不管这些湘西作家生活经历如何,职业差异,文学表现的功力如何,他们对湘西地域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抱有热烈的书写的愿望,表达着自己的审美感受和价值评价。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对旧时代历史风云的再现,对新时期地方乡镇城市镜像的描摹和世道人心的刻画,还是对地方丰富的民俗事象的精心描绘与展现,均呈现出一种地方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响,体现出一种文学“乡土”的民族国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着一种“共同体意识”。
虽然湘西作家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目前还未引起省内外评论界的特别关注,以高级别的课题项目形式对这一时段湘西作家创作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非常罕见。 但在笔者看来,湘西作家群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写作队伍,也是一群充满雄心壮志,希望书写历史人生大书的逐梦者。面对这样一群还在写作路上不断成长的作家,笔者进一步期许作家们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视野中,大胆地突破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充分发挥想象力,拓展着湘西文学表现空间,同时还要继续借鉴好中西方文学资源,继续提高编制故事技巧的能力,丰富小说语言的表现能力,讲好湘西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描绘好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湘西人的快乐和忧伤。 百余年来的国家整体层面的社会政治革命、经济文化变革已经给“湘西”这片昔日的“化外之地”带来了山乡巨变,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可谓日新月异,湘西传统封闭的乡村世界与乡土经验几乎土崩瓦解,人们被迫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命运,许多人或选择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或者在自己祖辈相传的故土寻求变革以及新的可能,或者在城乡二元选择中挣扎徘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湘西人原先那种传统农业文明形成下的稳定的心理文化结构已被完全打破了。 如何表现湘西传统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带有泥土气息的人格与人性在巨大的现代化潮流面前那种失语、不适与尴尬的普遍状态,如何在表现湘西文学自我的地域性、民族性的同时,呼应着国家文化建设层面的“共同体意识”,即在文学“乡土”中凸显民族国家精神,这是湘西作家们必须继续深思的问题。 另外,处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作家们,不仅要遭受一场改变心灵和精神的阵痛,还要遭遇着各种物质充盈的诱惑。也许他们暂时还无法对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巨变作合理的价值评判,但他们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的形象传达和表现,为这场历史巨变留存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记忆,继续叙写着“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进程。 他们应该具有这样的雄心,我们也满怀着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