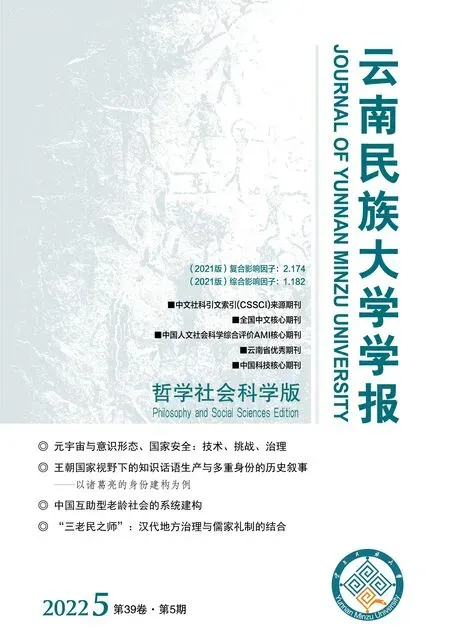从糯米到饭米:西双版纳傣族主食变迁之动因及影响探微
杨筑慧,来慕淑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食物为人的身体机能提供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其他多种营养来源,是人类生命延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其中的主食则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主食即餐桌上的主要食物,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富含碳水化合物。一般来说,人类的主食多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稻米、小麦、玉米等谷物,以及土豆、甘薯等块茎类作物。而以之为基础的种类繁多的主食创造,则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与想象。其中,稻米为全球约20亿人口提供了主食,20%的热量和13%的蛋白质。(1)[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韩良忆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36页。从传统上而言,一个区域或某个族群以何种作物为主食,往往与自然环境、文化传播、人口流动、自身机能等有密切关系,且可能还隐藏着政治、阶级与权力的话语,以及象征符号的意义。本文所探讨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的主食变迁包含着复杂的内外动因,隐喻着特定社会机制的构建和逻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陲,气候湿热,降水充沛,适宜于多种作物的栽培,稻谷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2021年末,全州户籍总人口101.81万人,其中傣族33.4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2.9%(2)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西双版纳州概况》,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xsbn.gov.cn/88.news.detail.dhtml?news_id=34206,2022年6月5日登录。。
傣族自称为“傣”(Dai),西文中作“Tai”或“Thai”,古时有 “摆夷”“水摆夷”“僰夷”等称谓,与我国的壮侗语族其他民族及泰国的主体民族泰人、缅甸的掸人、越南的泰人等东南亚民族有同源异流的关系,概称“泰傣民族”。西双版纳境内以傣泐支系为主,兼有傣讷、傣雅(花腰傣)支系。 与世界许多地区的泰傣民族一样,西双版纳傣族也多居于河谷、平坝、半山区,地势相对平坦,水热条件十分适宜于水稻的种植。从有关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泰傣族群先民是世界上较早驯化野生稻和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在景洪、勐腊等地还发现了多处普通野生稻,其地方志称,2000多年前,当地居民已开始了水稻的种植。(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但其最先种植的是非糯性水稻(粘稻)还是糯性水稻(糯稻),却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以及从诸多地区泰傣民族近现代仍以糯米为主食的习俗来看,食糯习俗的历史应非常久远。Tadayo Watab认为,糯稻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地区,(4)Tadayo Watab:Glutinous Rice in Northern Thailand. Kyoto.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1967.pp8.且多与我国西南地区接壤。日本学者渡部忠世也认为在历史上该区域形成了一个“糯稻栽培圈”,约十世纪前糯稻是这一地区占优势的稻种,之后逐渐衰退。(5)[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尹绍亭,等译,程侃声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6页。还有学者认为,在东南亚地区,以糯为主食的民族历史上以泰傣民族为主。(6)Golombl.The origin,spread and persistence of glutinous rice as a staple crop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6,7(3)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水稻种植仍是西双版纳傣族主要的生计方式,其稻谷以糯稻为主,兼种玉米、花生、茶叶、水果 、甘蔗等作物,许多村寨的傣族亦以糯米为主食。一些学者认为,“一种合理的饮食结构总是在对外部的合理适应中产生的。傣族地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宜种植糯谷, 这便是长期选择的结果,以此为基础必然形成以糯米为主食的传统习俗。”(7)王文光, 姜丹:《傣族的饮食文化及其功能》,载《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3期。进入21世纪后,与许多地区的族群一样,西双版纳傣族以糯米为主食的习俗以不可阻挡的颓势在衰微,这一现象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既是历史发展使然,也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
一、作为主食的糯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下册)记述:“傣族通常是日食三餐,以大米为主食,喜食糯米饭。赕佛和节日里常用糯米做成粽子、黄米饭、毫诺索、毫崩、糖米花等食品……”(8)《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糯米是糯稻的颖果,具有胀性小、黏性大的特点,曾是西双版纳傣族的主食,“凡到过西双版纳的人都知道傣族喜欢吃糯米饭, 糯米饭是他们的主食。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傣族认为不管有多少饭米, 只要糯米不够便说缺粮。”(9)王文光, 姜丹:《傣族的饮食文化及其功能》,载《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3期。此与许多其他地区的傣泰民族有共性,如云南红河地区傣族,老挝泰泐人、黑泰、白泰,越南黑泰,以及泰国北部、东北部泰人等。(10)参见郑晓云:《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及东南亚泰傣民族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43、147、160、180页。糯稻,当地人称为“毫糯”,非糯性的籼稻称为“毫安”,即饭谷,籼米则叫“饭米”。虽然傣族先民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但关于其以糯稻为主食的记载则出现较晚。目前笔者所看到的较早相关史料是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文中提到傣族地区的饮食“蒸、煮、炙、煿多与中国同,亦清洁可食。酒则烧酒,茶则谷茶,饭则糯爙。不用匙箸,以手搏而啮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11)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清代后,有关西双版纳傣族食糯的习俗渐多,如乾隆《滇省西南诸夷图说》(贺长庚本)称:“水摆夷,属宁洱。性和软。种田、捕鱼为业。男穿青衣、白绔,女著青白短衣,下穿花布桶裙。食糯米及酸辣之物。”道光《普洱府志》载:“摆夷,又名僰夷,称百夷,……喜食糯米、槟榔及酸辣之味。”(12)鄭紹謙、李熙齡續纂修:(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土司”附种人条。同时代的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云,思茅、威远、宁洱等地的水摆夷,以季春为岁首,届时以糯米蒸熟染成五色以斋供。及至民国时,不少文献资料在记载西双版纳傣族的农业和主食时,都提及了以糯稻种植为主,以糯米为主食。“摆夷的水田只种稻米一种粮食,……他们的稻米有两种,糯米是摆夷民族的主要食粮,糯稻要占十分之七八成,饭米专门供给外地人来贩卖。”(13)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中国边疆学会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1950年版,第160页。又如:“摆夷不食粳米而食糯米,米粒很柔糯,所含油腻质甚丰富,饭用瓦甑蒸熟,蒸法先将米用水浸六七小时,然后蒸之,蒸至半熟,揭开甑盖在饭上洒以冷水,再加盖续蒸,蒸至米粒柔而无核时便可吃。热时饭粒柔软可口,稍冷便硬不能下咽。”(14)江应樑:《摆夷的生活文化》,北京: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三十七年,第167页。在普思沿边地区,“农作物以饭米糯米为大宗,仅供外来商人(饭米)与自给(糯米)之需。”(15)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辑:《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册),云南财政厅印刷局印刷,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第88页。其意显然是说外来者多以饭米为主食,而当地人,主要是摆夷则以糯米为主食。同书还写道,摆夷习惯不吃隔夜米,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冲(舂)米,“所冲(舂)均为糯米,冲出以后,则用甑蒸熟,有事外出者,则以各竹盒盛之而去。日间时饿时食……。”(16)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辑:《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册),云南财政厅印刷局印刷,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第103页。吃时就用手抟成团放入口中,或放在芭蕉叶上取食,一般不用筷子。民国时期的西双版纳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粮食生产占农村经济的80%以上;(17)《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1949年全州的总耕地面积为54.36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就达51.36万亩,(18)《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且以糯稻的种植为主。
虽然西双版纳傣族及其先民以糯米为主食的习俗在清代以前记载较少,但一个族群以某种粮食作物为主食显然要比其所见的记载早得多。20世纪70—80年代,在农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了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包括了“阿萨姆—云南多点”地区,其中就涵盖了西双版纳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不是十分频繁,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双版纳的傣族人仍多以糯米为主食。当地传统的地方糯稻品种主要为高杆、大穗、大粒型的“毫勐享”“毫哈”“毫弄索”“毫弄干”“毫尖温”“毫龙良”“毫龙冷”“毫龙勐”等。据相关资料记载,勐海、勐腊等地的糯稻种植在20世纪60年代前还占当地稻谷产量的90%以上。种植少量的粘稻主要是为了交纳公粮,有的则用于制作米线与米干。(19)李尧东整理:《佛海县情况(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调查)》,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云南省勐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勐腊县志》(卷六,农业,第三章,种植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如前所述,傣族人传统的食糯方式是将舂好的糯米于前一天用冷水浸泡,次日早上用甑蒸熟,然后装入竹木器皿,冷热均可食,香软可口,且随时取食。吃时多以手抟团,蘸盐、辣椒以及各种“喃咪”(蘸料),如小螃蟹酱、西红柿酱、蔬菜酱、青苔沫等。糯米饭不仅油质大,营养丰富,且便于携带、耐饥饿,即使不用菜肴亦十分宜味,一些地方良种更有一家蒸饭全寨香之誉。而“饭米”往往需要配菜才适口。此外,对于炎热的西双版纳地区来说,糯米的蒸食之法和冷热可食的特性也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不仅如此,当地傣族人还以糯米为原料,制作了品种繁多的食品,如“毫诺索”“毫栋”“毫崩”“毫吉”“毫惦”“毫冷”“毫良”等,这些糯米食品往往具有其特定的制作场景与社会文化意义,(20)金少萍:《西双版纳城子傣族村寨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2页。是族群认同的表征。它们既是食品也是祭品,是人神共享、人神区隔的圣物。除此,稻米在社会交往中还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连接着彼此的情感;而以糯米发酵制作的酸食、酒,则是傣族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食物。可以说,历史悠久的糯稻种植与食糯习俗,是傣族传统社会文化的母本,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其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双版纳傣族的糯稻种植与食糯习俗经历了过往不曾有过的际遇,传统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消解。
二、主食变迁的主要原因
西双版纳傣族主食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较为缓慢,90年代后期速度渐快,21世纪后仅一些村寨老年人尚保留以糯为主食的习惯,“虽然糯性不足的饭米之食用, 在数量上如今已呈普遍之势, 但仍不改糯性十足的米饭在傣族饮食中的主食地位, 尤其在老人的日常饮食之中, 以及在重大节庆、人生礼仪、新房落成和婚丧仪式中。”(21)徐伟兵:《稻米、信仰与秩序——以西双版纳曼景傣族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9期。以糯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在变迁过程中存在代际差异,且不同区域或村落,其变迁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变迁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就其变迁原因来看,主要有4个方面的影响。
(一)政府主导下的“糯改籼”与“糯改杂”影响
籼稻、粳稻均有糯与非糯之分,此处所言之“籼”,是为非糯性大米,即西双版纳傣族人所说的“饭米”,亦属粘稻。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瘴疬影响,除了少量从事茶叶等生意人、政府工作人员、军人外,西双版纳地区鲜有内地人前往或长期居留,非糯性稻谷不仅种植较少,本地傣族也不以之为主食。在此之后,随着大量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场职工、退伍军人、驻防部队、归国华侨,以及后来的知青、从事买卖者等外来人口的大量拥入,以“饭米”为主食者越来越多。以农垦职工为例,1955年不足2000人,1959年过万,1974年时达90419人。(2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与此同时,与非糯性稻谷相比,糯稻产量相对要低,加之国家在征收公粮时是以非糯性稻谷为主,于是在政府主导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推动下,非糯性的籼稻在西双版纳地区逐渐得到广泛种植。不仅如此,还渐渐改变了傣族人长期只种一季稻的传统。1954年冬和1955年6月,景洪的曼暖龙等9个寨子开始种植双季稻,后在全州进行推广,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到1979年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一年,全州种植面积达212722亩,平均单产162公斤。(2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由于西双版纳特殊的水热条件,国家对战略物质的需求,从1955年起到1993年,在当地共建立了10个县级国营农场和一批局直单位,总人口达14.23万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18.1%。这部分人员不仅以“饭米”为主食,且自种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如到1964年已种植水稻29640亩,至1978年达37961亩。(2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种植的稻谷品种最初为本地的大白谷种,之后又从其他地方引进了昆明小白谷、德宏小白谷、寻甸插子谷、台北8号、西南175、科情3号、广场矮、白壳矮、珍白154等等。在其影响下,一些地区的傣族群众也开始种植非糯性稻谷、吃“饭米”。
杂交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用普通方法育成了杂交稻,70年代,在袁隆平等老一辈水稻专家的努力下,我国的杂交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于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既有非糯性稻谷,也有糯性稻谷,但其育种方式和种植过程与传统稻谷有一定区别,且更为依赖农药、化肥,同时,农民一般不能自己制种,需从市场上购买。1979年,西双版纳农垦部门开始从云南省种子公司引进了12个杂交稻品种,1983年又从湖南等地引进其他杂交稻品种,而地方的杂交稻种植也同时推广,如从1980年开始,西双版纳州农科所与勐海县农业局配合,先后在勐海县的330多个村共计92115亩水田实行综合试验水稻种植。(25)《西双版纳国土经济考察报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所推广的杂交稻均以粘稻为主,种植面积渐渐扩大。
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力量的推助下,西双版纳傣族的糯稻种植面积在不断缩小之时,其主食也随之而改变。如今,“饭米”已成为绝大数人家的主食,用电饭锅煮饭,也成为每家每户不可缺少的选择,方便且快捷,省时省力。糯米则多在起房盖屋、婚嫁和年节、宗教活动等场景中出现,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食物,有时也是外出携带的干粮,“因为糯米即使冷了也非常好吃,通常用芭蕉叶包起来,加一点豆豉、腌菜、酸扒菜等咸菜就可以下饭了。在节日、婚丧嫁娶和各种聚会之时,除了吃之外糯米还有祭祀的用途。”(26)高黎,刘芳,陈刚:《傣族饮食文化变迁的饮食社会学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载《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二)经济作物大规模种植的影响
历史上,傣族先民即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并延续至现当代。但不同的是,这种粮食作物种植的单一经济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其副业生产开始向经济作物方向发展。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傣族人充分利用各自的自然环境发展茶叶、橡胶、砂仁、樟脑、甘蔗、香料、西瓜、西番莲、香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景洪、勐腊等坝区傣族依据气候和水土优势,并在农垦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力发展起橡胶种植业;勐海、景讷、普文、勐混、尚勇等地傣族以种植茶叶为多;而勐遮、勐捧、勐润等地傣族则以甘蔗种植为主。据2020年西双版纳国民经济统计,全州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28.09万亩,比上年增加0.26万亩;甘蔗种植面积20.35万亩,增加1.30万亩;蔬菜种植面积35.70万亩,增加1.20万亩。年末茶叶面积142.98万亩,比上年末增加3.56万亩;水果(含瓜果)面积70.14万亩,增加10.98万亩;橡胶面积447万亩,减少5.61万亩。(27)西双版纳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双版纳调查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西双版纳州统计局窗口https://www.xsbn.gov.cn/tjj/67471.news.detail.dhtml?news_id=2174404,登录时间2022年6月6日。由上可知,西双版纳的产业结构较以前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作物种植占据了大量耕地面积,而其中的橡胶和香蕉种植则深刻改变着许多地区傣族人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生活习惯。
天然橡胶多生长在热带雨林,为乔木树种,树干上打开一个缺口后会流出白色的汁液,以之制作的产品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工业、军事等领域。大约在18世纪30~40年代,两位法国人查德拉·康德曼和索瓦特·弗雷诺将橡胶介绍给了欧洲人,从而激发了人们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19世纪中期后,通过英国殖民政府的栽培,橡胶开始传播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28)李闵,袁方:《橡胶林――绿色的沙漠》,载《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4期,第63~65页。西双版纳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年代被选为我国重要的橡胶种植基地,云南省也发展成为我国第二大天然橡胶基地。
20世纪90年代,由于橡胶种植能带来大量的现金收入,激发了西双版纳各族群众种植的积极性,民营橡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少的人家十几亩,多的则几百亩,其收入远远超过稻谷种植。由于橡胶种植与收割占据了人们大量时间,使许多人无暇顾及稻田耕种,如笔者调查的勐罕镇傣族村寨,自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村人基本上不再从事稻作农耕生产,稻田多出租给外地人种植香蕉;又如金少萍所调查的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1984年全村有橡胶地114亩,1990年为1850亩,1997年达到3076亩。橡胶收入在2010年占全村总收入的57.9%,成为主要经济支柱。(29)金少萍:《西双版纳城子傣族村寨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8页。种植橡胶在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同时,许多稻田也被出租为他用,香蕉就是其中重要的作物之一。一项对打洛勐景来村的调查说:“稻米的种植被香蕉种植逐步替代,当地的傣族村民的生计方式也不再是传统的水田稻作,直接获取的生存来源被间接获取的生存资本取而代之,……”(30)黄巧:《勐海打洛景来傣族稻米文化变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6页。传统的小农稻作农耕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自然经济,一般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目的,主要是为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橡胶与香蕉,是与市场紧密关联的经济作物,直接以获取货币收入为目的。稻作与橡胶、香蕉种植目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所牵涉的价值认知属于不同的意义体系。故而,橡胶、香蕉种植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认知以及生活方式,更使传统的稻作农耕受到猛烈的冲击。且不要说糯稻种植,高产的杂交稻种植也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昔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的同时,还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包括粮食。而在西双版纳市场上供应的粮食作物以非糯性的粘米为主,杂交稻的高产量也理所当然使之成为不二的商品粮。随之而来的还有当地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如以粘米制成的米线、米干或面条等成为人们普遍食用的早餐,传统意义的无固定的一日三餐或四餐与内地的三餐无异。食物的基本功能是裹腹,维系生命的延续,但在“吃”的问题上,对人类而言却远非生物属性如此简单,往往隐藏着政治、阶级、宗教、性别、认同等社会文化因素,“是一种我们可以拿来思索、谈论、概念化的东西。”(31)[美]西敏司:《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林为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经济作物种植虽然也是一种生计方式,却与主食无涉,从某种意义上对于西双版纳傣族人来说,是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其将他们引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轨道,是其让他们看到“钱”与市场勾连中的“魔性”。
(三)外来人口不断增多的影响
长期以来,西双版纳远离中原统治中心,被视为“边缘”的蛮雨烟瘴地,人们视之为畏途。元明清以来在汉文史籍中常有官兵在该地染“瘴气”得疟疾(俗称“打摆子”)死亡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除了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外,汉族人较少。据李拂一《车里》一书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十二版纳人口约有39681户,其中男84674人,女83716人,共168390人,摆夷约占十分之八。(32)李拂一:《车里》“户口”,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1931年版,第23页。在1951年,汉族仅占勐海县总人口的6%,傣族占65%。(33)李尧东整理:《佛海县情况》,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进入景洪地区的汉族人,有史料记载较早较多的时期是清代,时思茅、普洱等地汉族陆续迁入景洪境内经营茶叶。柯树勋时代,召垦滇西、滇南及广西、贵州等地汉族进入西双版纳开垦土地、经商、做工,其中一部分落籍车里境内。民国十六年(1927年)设制后,汉族流官和茶商、盐商从腾冲、玉溪、思茅等地进入景洪境内,汉族人口逐渐增加,这些商人且多集中分布在景洪城。20世纪40年代期间,民国政府陆军九十三师进入景洪境内,部分官兵与当地民族联姻,又增加了一批汉族人。据1951年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调查,景洪仅有汉族250人,占景洪总人口的1.8%,(34)刘杰整理:《车里县情况》,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且没有定居点。1950年代后,西双版纳建立起多个国营农场,迁入了大量外来人口。农场人员主要是来自内地,尤其是湖南祁东、醴陵两县移民。改革开放后,到边疆地区进行贸易及务工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如开店经营茶叶、服装、民族工艺品、旅馆,以及卖菜、理发美发、机械修理、日常用品销售、房地产开发、建筑、餐饮业等,同时旅游人数也不断增多。
时间的流逝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历史长河驻足的印迹。外来人口的增多,使得傣族人与外来族群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在此过程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并趋向于以非糯性稻米为主食,面条、馒头、包子、面包在人们在日常生活渐渐占据了一定位置。目前,除了一些老年人还习惯吃糯米饭外,中青年人大多已以饭米为主食了,有调查说:“一个例子是关于糯米和大米的喜好问题,村里的老人会告诉我们他们更喜欢吃糯米饭,尤其是早餐,基本都吃糯米饭,但是年轻人和儿童会说,如果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会吃糯米饭,早餐他们更喜欢吃米线或者其他食物。”(35)高黎,刘芳,陈刚:《傣族饮食文化变迁的饮食社会学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载《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一定意义上与粘稻的广泛种植是相辅相成的,移民也是文化的携带者,广泛的交往交流给迁入地带来许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饮食习惯。
(四)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影响
旅游业被视为当代的“朝阳产业”“无烟工业”,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西双版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使其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诸多优越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旅游业逐步被提上区域社会发展日程,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快速发展,如今西双版纳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前往。不仅如此,“避寒胜地”的打造,还使西双版纳成为除海南外,我国另一重要的避寒胜地,在此购房、租房、住店的内地人趋之如骛。目前该州已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多个旅游城市、旅游景区、旅游景点、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系列旅游产品。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旅游业是西双版纳重要的产业之一,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全州“接待国内外游客1985.4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59.1%。”(36)西双版纳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双版纳调查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西双版纳州统计局窗口https://www.xsbn.gov.cn/tjj/67471.news.detail.dhtml?news_id=2174404,登录时间2022年6月6日。2021年,旅游人数逐渐回升,全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721.1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432.08亿元。(37)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西双版纳州概况》,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xsbn.gov.cn/88.news.detail.dhtml?news_id=34206,2022年6月5日登录。可见,即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旅游。在旅游业开发中,一些傣族村落快速城镇化,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有的则成为规划中的旅游景区和景点;还有许多人卷入旅游行业的大潮中,参与“吃、住、行、娱、游、购”的行列,而基于“吃”的品种、口味、进食方式乃至情趣,在当地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主食亦不例外。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大量游客的拥入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游客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一定意义上对当地人带来了深刻影响,推助了多层次多维度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随着现代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物流的顺达,交通的便捷(高铁、飞机、高速公路均俱)、互联网多媒体的使用,以及理性需要,糯稻和糯米本身的生物特性影响,许多傣族人也不再以糯米为唯一的主食选择,多样性的食物来源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可能。
三、主食糯米变迁的影响
傣族人的食糯习俗既是为身体机能所需,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文化意义与神性,而糯稻的种植不仅是技术的体现,也是传统社会文化构筑的基础。就当下来看,尽管西双版纳傣族还在种植少量的糯稻,也食糯,但往往是年节或仪式所使然,作为主食的糯已退隐于餐桌之外。糯稻或糯食在某些场景下所具有的神性与象征性,是其仍旧留存于民间文化的巨大推动力,换言之,文化的韧性某种意义上是糯食得以存留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种植量大幅度减少,糯米产量有时供不应求,故而,市场上出现了东北糯米、泰国糯米和老挝糯米的销售。
以糯为主食习俗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环境的变化。稻作农耕与经济作物种植在技术和耕作方式、种植目的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稻谷种植在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不产生废物的有机循环生计。而今,过去为稻作农耕提供灌溉水源的葱郁茂密神林“竜林”被大量砍伐而种上了橡胶,稻田则种上了香蕉,一些种植豆类、棉花的旱地也被种上了橡胶、茶叶,不仅改变了土壤环境,而且民间习惯食用的竹笋、野菜、野生菌,以及一些草药等越来越少,自然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
二是传统糯稻品种在杂交稻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中渐渐消失。如曼远村傣族过去经常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有“毫蒙享”“毫滚干”“毫禾禾好”“毫达哥”“毫黑章”“毫场竜”“毫场囡”“毫火汗光”“毫乃列”“毫孟样”“毫拱笼”“毫嘎木龙”“毫嘎木到”“毫哄勐养”“毫哄孟仑”等18种糯稻和“毫岸笼”“毫岸波咏”“毫岸档”“毫岸满”等4种粘稻(非糯性稻谷概称)。现在因较少种植地方品种,许多传统稻种也在这种无意识中消失了。
三是集体互助思想逐渐式微。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互助、务实及乐命安天的思想,是傣族村寨长期和谐的重要原因。民谚也说:“要吃饭,同出主意,想丰收,互助帮助”“栽秧时要约寨上的人相助,水沟边塌方要互相抢修”等。随着稻作农耕生计方式的消失,基于此生计而形成的集体互助思想似乎也不再为人们所乐道。需要提及的是,橡胶种植是一种个体化程度较高的作物生产方式,从栽种到收割,个体均可独立完成,且时节性远不如稻谷种植强。
四是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由于稻作农耕渐趋减少,传统的自给自足生计方式也失去了根本的依托,畜禽也没有了基本的饲料来源。不仅粮食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其他许多副食品和肉蛋等也需要从市场上获取。当地傣族人从未如现在一般依赖于市场的供给,市场的波动也带给他们一种不稳定和不安全感。随之而来的是,对现金的需要更加迫切,“赚钱”成为人们生存和生活的主要内驱力或动力。
五是建立在稻作农耕基础上的许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渐渐被消隐在历史的烟尘中,如稻作耕作技术、以稻米为中心的礼仪等。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主食的变迁,傣族人餐桌上的食物和味觉感受较过往更加丰富,而与外界交往的频繁,也带来他们社会关系与思想观念的变化,由村寨向地方、由稻田向市场、由族内向族外、由边疆向中心形成了纵横拓展,地方文化的多元性愈加突显。
四、结论
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稻米本身具有复杂的品格。(3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5页。稻米品格的复杂性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可以从其生物性中看到,如淀粉含量、颜色、形状、味道、构造、软硬、适应空间,等等,也可以呈现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空间中。作为人类延续生命的基本物质资料,稻米生产是世界许多民族最基本和最日常的社会实践,并以之为基底而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也成为一定群体的社会特质和族性,有西方学者认为,食用米的人们“比较有生产力和创造性,较勤奋,在技术上有较丰富的创意,也比较骁勇善战。”(39)[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韩良忆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36页。而从其生产和食用的变化中,我们亦能窥见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西双版纳傣族主食的变迁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内外联动的结构性变迁。就外因而言,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导所致。在现代化发展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对高产的追求使糯稻的低产成为生产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而用手抟饭进食的食糯习俗则成为落后的潜台词。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改变使稻谷种植的效益得不到彰显,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旅游业的发展,资本的嵌入,不仅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收入,也使傣族人能够过上与内地人相同的生活,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内在看,理性选择也是引发西双版纳傣族主食变迁的原因之一。傣族主要生活在坝区,也是西双版纳粮食的主产区,稻作生计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主要作物,不仅满足了身体所需的主要营养物质,也提供了社会文化建构的基础和人们交往的媒介。但随着时代的前行,稻谷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经济作物相比,显然难以企及,尤其是一些市场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它们能在较短时间里带来过往傣族人无法想象的大量现金收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从事稻作生产之后,需从市场上获得粮食,而市场上的粮食又以高产的杂交稻(粘稻)为主。同时,随着对外交往交流的深入,外来文化、饮食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影响到当地人,与“外”的趋同,成为顺应时代的重要体现。正如美国学者明茨所言:“社会的饮食习性常因各种权力、影响力的介入而改变,而这些的来源,运用的方式、目的,以及人们所采取的应对方式等,也都会促成食物偏好的转变。”(40)[美]明茨(Mintz,S.W.):《吃》,林为正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如此,在政策、市场以及自我理性需求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下,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农耕生计不断发生变迁,并引发传统主食的改变,而原本附着于糯稻种植的文化也慢慢消失,当地傣族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且在世界经济体系的逻辑和规则中实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市场的依赖,还有嵌入经济的社会文化。可见,由糯向非糯主食的改变,不仅是食糯者传统的生计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变化,而且也是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交往交流逐渐深入的典型范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西南边地的全球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