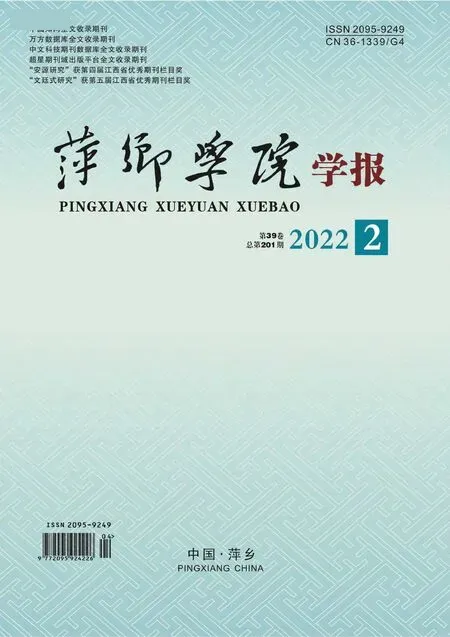“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
唐井环
“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
唐井环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公共管理系,江苏 镇江 212000)
建立以自治、法治、德治为要素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基本路径。文章基于社会实践政策视野,探讨“三治融合”治理的缘起,进而从“三治融合”的构成要素以及“三治融合”的理论交叠两个方面梳理了学界对“三治融合”的总体研究,厘清了“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联。研究表明,实践中,“三治融合”应注重地方性知识观念、树立包容性治理思想、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以促进“三治融合”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功能,凝聚基层多元治理力量,推动基层治理走向善治。
基层治理;“三治融合”;治理体系
一、缘起:“三治融合”的社会视野
社会转型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异质性因素,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困境迫切需要树立整体性治理思维,整合和激活基层治理的有效力量,健全基层制度体系并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确保基层政府“元治理”角色的充分发挥。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和模式是回应新时期基层治理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应由之路。乡镇政府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吸纳和重塑基层治理力量方面具有重要的“向心力”作用。
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历来是学界讨论的焦点议题。在社会实践层面,从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的尝试到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再到桐乡市高桥街道的“三治融合”试点,基层治理实践模式及其功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设计目标。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规划明确提出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并为“三治融合”确定了具体施工图。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从相关实践和政策文件层面来看,“三治融合”不断得到完善。“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也已具备较为完备的政策与实施指引。
二、“三治融合”的构成要素
“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超越微观性的个案示范[1],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并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典范。2013年浙江省桐乡市推行现代意义上的“三治融合”试点工作,率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尝试,有助于缓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难题,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力。厘清“三治”的理论内涵及其要素关联是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前提。对“三治融合”学理内涵及其要素再检视,可为新时期基层善治提供理论路径。“三治”作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精炼表述,既是对三种治理手段及其组合的强调,又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治理理念与方法。
“自治”即自我治理,充分地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自治”作为“三治”中的基础,在基层民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其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中关于“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规定。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换言之,作为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强调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democratic rights),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由国家强力推动,自治实践成效显著。但透过村民自治实践不难发现,“自治”在村级组织层面多表现为民主选举,而实践中由于基层民主参与意识不足也可能引发低质量、低水平的自治。新时代的自治更加凸显基层民众的自主性,突出基层民众自主参与治理,确保基层群众性组织自治功能的切实发挥。
“法治”即依法治理、公正治理,就是依照法律来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必须遵守法律条文,但它更重要的是指法的精神,是指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一整套规则体系[2]。中国古代的法治是在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下运行的,因而是皇帝意志的反映,即为统治者服务,法律的运作过程更具经验理性和伦理化色彩。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民主理念下建构起来的社会机制,即民主型法治。法治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中逐渐凸出的治理方式,也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对依法治国的宣传和教育不断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工作。
“德治”相比较于“自治”“法治”而言,更具抽象性。德治历来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方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常常将道德法律化(legalization of morality),使之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自孔子开始,中国传统德治就在独特的自然经济、宗法社会结构、专制体制、一体化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等背景下展开[3]。基层社会治理中常借鉴和运用儒家“德治”思想,采取说服、劝导等道德教化的方式,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伦理自觉性,进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故而,德治以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良传统和良好风尚进行软治理,更可称之为一种温和有效的方式。“德治”是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治理观念和方式[4],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的发挥。随着时代的变迁,“德治”一词语义外延更为丰富,在继承传统优秀德治思想基础上注入了现代化元素,实践边界和外延不断拓宽。现代意义上的“德治”囊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内容。此外,现代的“德治”还包括其自身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和规则的合理化运用。德治作为一种“软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中“硬治理”手段的有益补充。因此,德治也因其对良好道德风尚的追寻和对社会行为的道德化调节机制的构建,而成为“三治融合”的重要维度。
三、“三治融合”的理论交叠
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发展、良性互动,是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基层“三治融合”中的“三治”并非三种治理方式的随机组合或简单叠加,而是三种治理方式的有机融合。因此,“三治”是整体性的“三治”,而非分割、孤立的路径。在实践中,既要考量三种方式“合”的内在逻辑性,更要考量“融”的有效性。就目前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三治”的逻辑关系可概括为“一体两翼”论、“三治组合”论和“融合平衡”论。
(一)“一体两翼”论
“一体两翼”论认为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是一体两翼的关系[5],主张“自治为体,法德两用”[6]。“三治”并非平行并列关系[7],而是“三治合一”的整体性关联。易言之,即将“自治”作为“三治”的主体,同时,将法治与德治作为辅助的“两翼”,进而形成了稳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维空间格局。由此可见,“三治”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自治激发主体能动性,法治规范治理边界,德治塑造共同体意识。同时,“三治”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法治作为自治和德治的底线保障,以德治作为自治和法治的价值支撑”[8],共同构筑基层治理的“三脚架”,创造形态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二)“三治组合”论
所谓“三治组合”论,即主张“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方式组合起来,能够发挥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9]。“三治组合”论将“三治”作为基层治理的构成要素予以科学划分和理性选择,进而发挥不同组合模式的比较优势。通过不断优化“三治”的组合方式和结构性配比,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内生性创新发展[10]。
(三)“融合平衡”论
所谓“融合平衡”论,则与“三治组合”论不同,“融合平衡”不只是“三治”之间的排列组合,更是三者有机成分的相互内嵌与融合共生,寻求三维互为嵌入的融合治理方式,弥补“三治”简单组合而引起的治理失序或失衡。由此可见,“融合平衡”体现了“三治”的多维互动与有序交织,进而不断寻求最优治理的平衡点。
综而观之,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的逻辑出发点不同,但都强调“三治”的有机组成和协调共生。“三治融合”强调基层治理的动态性,即通过治理方式的“三维”互嵌实现治理的立体协调和动态平衡,而非“三治”的简单组合或无序叠加。“三治融合”建立在“三治”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各种治理方式的理性选择和深度包容。“三治融合”通过不同治理方式的嵌入式组合和系统性融合,寻找基层善治的最优运行机制。
四、“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的实践指向
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单囿于某一治理方式或模式的选择,而是转向更具包容和弹性化的多维治理方式的策略性选择。在实践运行层面,“三治”是可以组合、融合或拓展的,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三个向度,在结构、功能和效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内在张力,可以依据地方治理的实际进行有机结合与协同运行。
(一)挖掘地方性知识,助推基层治理的本土化
“三治融合”作为一种基层实践探索,折射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观念。将地方性知识融入“三治融合”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有益探索。“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11]。从基层治理情境看,“三治融合”的要旨不在于考察普适性治理的准则,而是着眼于挖掘地域性治理实践所蕴含的情境条件及其实践机理。“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地方文化拥有者的实践,是一种由当地人基于本土文化与利益诉求编织的知识系统、意义系统[12]。地方性知识嵌入“三治融合”的地方实践凸显出地方性知识之于“三治融合”在价值赓续、体系重构、文化规训等方面的建设性功能。地方性知识以其物质层面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文化层面的延续性和有序性、精神层面的内敛性和适应性以及价值层面的互助性和公共性,成为推动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资源[13]。“三治融合”是对基层治理实践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性吸收和有效运用。在基层治理之维,“三治融合”作为一种治理理念的效用性恰好来自其自身所蕴含的建设性意义,而非地域性治理经验的简单映射。
(二)树立包容性治理思想,促进基层治理的协同参与
“三治融合”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理念,包含了包容性治理思想。包容性治理是通过制度的安排,能够确保所有公民平等参与政策的制定,并享有平等分配资源权利的过程[14]。包容性治理内含合作治理之意,合作亦是包容的深刻体现,换言之,合作寓于包容之中,包容中实现合作的价值目标。“三治融合”与包容性治理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三治融合”是包容性治理内在价值的体现。“三治融合”既关注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又兼顾基层治理的善治目标,因而是一种包容性治理思想和模式。“三治融合”效力发挥的关键在于激发基层自治的内生力,内生力则源于公众对自治事务的参与。包容性治理通过变革传统单中心治理模式,向乡镇基层主体开放更多的分配资源和决策议题,充分发挥“包容性”“共享性”特质,进而构建多中心、多元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包容性治理充分肯定和培育了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在塑造新的“我们”意识中形成社会认同,通过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15]。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基层治理需要拓宽治理视野,吸纳更多的治理主体,拓宽基层治理资源,推动基层合作共治。
(三)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创新基层治理的模式
“三治融合”作为一种治理组合方案,体现了整体性治理思维。从桐乡“三治”实践来看,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形成了“三团两会”的核心工程,破解了传统社会管控模式的“碎片化”窘境,转向注重协同创新与整合重塑的整体性治理再造。“三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构成,在实践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拓宽现有维度,通过“3+X”治理组合和理性选择,提升基层动态治理的有效性。随着基层“三治融合”实践的不断深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适宜本地特色的“三治融合”实践模式,“三治”的外延不断拓宽,衍生出“多治融合”形式。例如,南京市六合区的“1+1+3”乡村治理模式(即“1网格1支部+‘三治’”模式);广西蒙山县的“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即“‘三治’+智治”模式);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的“四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即“政治+‘三治’”模式)。此外,在信息技术不断嵌入治理的背景下,部分地方不局限“四治融合”,积极探索“五治融合”。例如,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村等地方,探索推动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治理模式,更加注重基层智慧治理。此外,亦有部分地方在“五治”基础上加上“共治”,形成了基层治理的“六治融合”实践模式。从系统的角度看,建立在多种治理方式策略性组合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可以有效化解单一治理模式“碎片化”困境,发挥基层整体性治理的优势。
[1] 张明皓.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7.
[2] 郁建兴, 任杰.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 学术月刊, 2018(12): 64—74.
[3] 孙莉. 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6): 95—104+206.
[4] 郁建兴. 法治与德治衡论[J]. 哲学研究, 2001(4): 11—18.
[5] 邓建华.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8(6): 61—67.
[6] 徐勇. 自治为体,法德两用,创造优质的乡村治理[J]. 治理研究, 2018(4): 4—9.
[7] 何阳, 孙萍.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6): 205—210.
[8] 张景峰. 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探讨[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94—100.
[9] 邓大才. 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4): 32—38.
[10] 唐皇凤, 汪燕.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28(6): 63—71.
[11]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 哲学研究, 2000(12): 36—44.
[12] 汪华. 政治动员、地方性知识与区域合作的困境——基于长三角的考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0(3): 134—142.
[13] 王乐全.“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重构——基于对徽州地方性知识的考察[J]. 中州学刊, 2021(4): 92—97.
[14] 尹利民,田雪森. 包容性治理:内涵、要素与逻辑[J]. 学习论坛, 2021(4): 66—74.
[15] 魏波. 探索包容性治理的中国道路[J]. 人民论坛, 2020(29): 16—18.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under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TANG Jing Huan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bei College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0, China)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with the elements of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is the basic path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and poli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origin of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sums up the overall research on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from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 theoretical overlap,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practice, the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establish the idea of inclusive governance and apply the thought of holistic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function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unite th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for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promot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efficient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governance system
D630
A
2095-9249(2022)02-0012-04
2021-12-29
江苏省教育厅202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SJA2249)
唐井环(1988-),女,江苏淮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