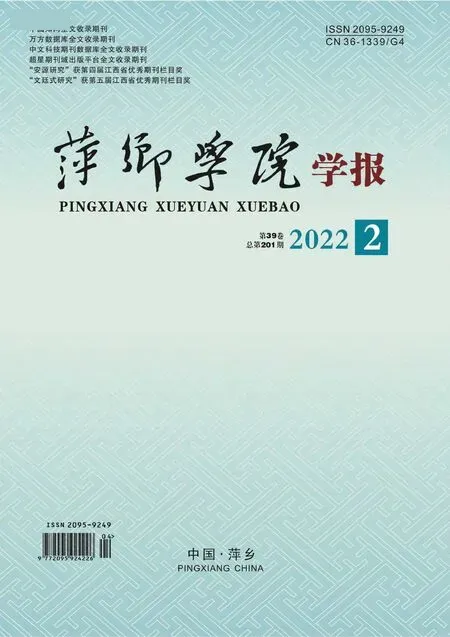论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白宇棚
论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白宇棚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近年来平台经济不断发展,平台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断增加。由于平台经济具有的多边市场性与网络效应,使平台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呈现出以数据和流量为核心进行跨领域、跨行业竞争的特征。这导致在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产生了主体身份界定不明、竞争关系难以认定以及损害结果评估不清等问题。鉴于此,可将单一主体规则引入主体身份界定中,把握平台企业集团化的发展特征分情况讨论;以平台企业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以争夺数据与流量为目作为判断竞争关系存在的标准;另外将竞争效果这一特定法益是否受到破坏作为判断损害结果的依据,既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作用,同时防止过度干预。
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
依托于互联网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的发展,社会大生产的分工迎来一场新的变革,商业生态体系不断创新演化。平台经济在此过程中快速发展,推动数字经济迈入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的2.0时代。在国内,“阿里”“腾讯”等超级平台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引擎。平台企业的发展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分工合作的模式与价值分配的形式,而且拓展了经济法的理论框架、催生出新的分析范式,成为一场经济社会领域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变革。在这场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平台企业之间出现了许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新行为,需要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为平台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由于平台企业间竞争行为认定规制的模糊性,学者在研究新出现的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时,经常出现既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去探究行为的违法性,又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去探究该行为危害性的情况。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的是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追求的是竞争自由,这两部法律虽具有极大的共通性,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不同的。一旦某一行为既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中认定,又放在《反垄断法》的视域下考量,就会增加行为的可苛责性,反而会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产生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的局面。因此,本文拟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域入手,对认定方式进行探究以求理论上的扩充。
一、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的典型特征
在数据时代,平台企业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平台能够搭建起资源聚集、交易便捷的高效率产业生态体系,达到商品的生产、流通以及配套服务等一系列环节的高度统一与融合,进而成为具备创新与发展特色的新型经济形态。但是,平台企业本身并不加工和生产任何产品,它是一种具有虚拟性却又真实存在的交易场所,通过促进各方的交易来收取一定的费用或者赚取中间商的差价进而获取收益。因此,平台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双边市场性,即平台企业居中,两端维系不同的用户,利用其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双方的联系与互动,以此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平台企业同时具有“企业”和“市场”双重身份,它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是平台市场的“守门人”。因而一个平台企业的存在就相当于一个市场的运行,平台企业实施的危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垄断行为的范畴。对平台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首先要从行为的特征入手,只有从特征中把握行为的本质,才能对行为有正确的认定。
(一)以流量、数据的争夺为核心
平台是一个虚拟的数字场所,其本身并不生产实体的产品,是通过提供场所、促成交易来赚取利润。消费者的关注度越高、流量越大、用户黏性越好,平台的经营状况也就越好。数据是平台能够吸引、捆绑消费者的关键。平台企业通过收集、处理数据,能够了解消费者的喜好与市场的趋势,进而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经营策略。因此,数据库的大小、流量的多少是决定一个平台市场地位的关键。平台企业越早进入市场,其所占有的数据与流量也就越多,后进入市场的平台企业与之的差距也就越大,其更容易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就呈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后进入市场的平台企业只能靠新一轮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模式来吸引用户的关注,以积累自己的数据和流量。这导致后进入市场的平台易实施恶意从大平台身上获取数据和流量的“搭便车”行为,衍生出流量劫持与数据抓取行为。流量劫持通常表现为强制访问网站、强制插入链接、恶意修改、锁定主页等形式。在以流量为王的平台经济中,平台企业恶意强迫或者在用户不知情时产生虚假交易,会干扰互联网的价值判断,阻断技术创新[1]。数据抓取以网络爬虫技术为核心,其预先设定好浏览网页内容的路径,利用自动化的算法程序,抓取相关信息并保存下来[2]。
(二)手段隐蔽性强
平台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隐蔽性首先体现在技术层面。互联网世界是一个由数字代码组成的地方,平台企业借助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而难以察觉。若不借助专业人员对平台企业进行查验的情况下,难以将其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是在经营方式方面,平台经济的本质是一种依托于流量的“眼球经济”,其运作模式是通过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以获取点击量、浏览量进而获利。平台企业在运作初期通常会采取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提供的网络服务与应用的方式培养一定数量的黏性用户,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收费的增值服务、广告等盈利项目的投放。在某一方面盈利之后,平台企业通常带着已有的流量向多领域进发,以不断增加自身的流量。由此可知,平台企业在任何能够获取关注、流量或者吸引用户注意力的项目上都会产生竞争,而不再局限于同业之间。打破了竞争市场之间的行业壁垒,传统行为认定中的竞争对手概念已不再适用,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难度进一步增强。
(三)跨领域经营,损害后果严重
与传统行业依赖于技术、人力资源不同,平台企业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经济的全球实时性互联互通的效果,其搭建起来的网络平台市场可以在全世界范围登录使用。这使得平台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多个领域中同时收集数据信息,内容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平台企业可以凭借由此累积的流量与数据优势,整合多方资源,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向跨行业、跨领域的方向发展。如阿里巴巴经营的范围涉及电子商务、金融、文化娱乐等多个产业,只要能赚取流量、吸引消费者的行业,平台企业都会开展竞争。这就导致当一个平台企业受到不正当竞争侵害时,受影响的不只是平台企业本身,还有大量的用户群体权益保障、多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经营环境。尤其是在数据信息泄露方面,因为平台企业通过数据抓取直接获取消费者个人数据信息,以此获取经营优势,当平台企业受到不正当竞争侵害时,数据信息很可能泄露,对消费者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四)获利与责任不成比
平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数据信息与用户流量的支撑。对于数据信息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收集,并需要不断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担负着技术不稳定的风险。对于用户流量,平台企业需要不断推出新活动、变化经营方式、紧跟热点以吸引用户的关注,防止流量的流失。然而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平台企业也可以恶意利用爬虫技术以很低的成本直接从其他平台窃取已经收集处理好的数据,或者采用插入跳转链接的方式从其他平台截取流量。通过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平台企业可以跳过前期的经营风险而直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行为人的处罚则显得十分轻微,不足以对其形成规制。甚至有些平台企业在受到处罚和媒体批判后,利用不当的辩驳混淆消费者视听,为自己增加影响力,再获取一些关注和流量。进而导致被侵权的平台企业维权成本增高,常常陷入需要以公开己方商业秘密为代价来维权的两难境地。
二、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问题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过程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平台经济这一新兴领域,只有在对行为进行明晰认定后才能对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平台企业有自己独特的运营方式,同时运用了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搭建自己的市场平台,前期采取以提供免费服务的方式吸引流量,增加用户黏性,之后以推出增值服务、广告服务等方式盈利的运营模式。在这种新型经营模式下,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方式中带来了主体身份界定不明、竞争关系难以认定及损害结果难以评估等问题,导致难以对平台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清晰认定。
(一)平台企业的主体身份界定不明
平台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与多边市场性使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实施主体界定不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需为“经营者”,并在第三款提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平台企业虽不生产、经营具体的商品,但其为平台的运营提供服务,因此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经营者的规定。但以往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多为单一的个体,各自为战,为自身利益从事经营活动。现今平台企业均朝着集团性的角度发展,集团旗下子公司、分公司与分支机构数量众多,他们常以“交织互补”的方式为集团整体谋取利益。对于分公司与分支机构等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应将其行为统一认定为集团企业自身的行为。而对其子公司的认定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实践中很容易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行为混为一谈或错误区分,导致行为主体不明。对于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身份,不能仅站在民商法的视野,运用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的概念去理解适用,还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站在竞争法的视野下综合考量。
另一方面,在平台经济领域不仅存在着平台企业还有平台内经营者,如“淘宝”电商平台中的商户。他们依托平台企业从事市场经营行为,也会利用平台实施一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平台企业自身来讲,其主体责任内容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如欧盟出台的《数字服务法》与《数字市场法》中明确提到平台企业是平台的“守门人”“管理者”,它是互联网上信息交流匹配,贸易开展的关键行为者,凭借规模经济、数据获取以及网络效应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平台企业算法技术的设置也会对用户信息安全、社会舆论话语权的塑造以及线上交易模式产生重大影响[3]。因此,平台企业具有对疑似违法行为的审查义务。若无法区分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就难以确定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增加其承担责任的风险。
(二)竞争关系认定标准难以适用
传统以同业竞争来确定竞争关系的方式,在认定平台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难以适用。竞争法视野下,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键在于竞争关系的认定。在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坚持以竞争关系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前置标准,竞争者之间实施的直接或间接损害对方利益并对竞争秩序造成侵害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4]。以往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通常发生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内部,局限于同业竞争之间,只有在同业之间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然而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模式的迭代,平台企业的经营呈现出跨领域、跨行业的特点。平台企业以获取数据与吸引流量为核心在多领域展开竞争、提升自身实力、破坏其他平台的经营效益,使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竞争关系产生了多样化、复杂性的特征。在流量效应、网络效应的加持下,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突破同业的限制,只要能够增加用户黏性、吸引流量、获取数据的领域,平台企业都会展开竞争,如平台企业为构造完整的消费者信息版图也会针对不同行业实施数据抓取行为等。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产生了较大的模糊性,导致在实践中执法机关对竞争关系判断的难度增加,甚至出现了以经营者是否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来认定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的实用主义[5]。
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反不正当行为认定中的竞争关系也处于从严格到扩展的过程[6]。传统的以同业竞争为视角进行竞争关系认定的分析范式在适用时遇到瓶颈需要突破。甚至有学者提出取消将竞争关系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起点的主张。但这会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变得过低,可能使正常的竞争行为,或者本应属于其他法律规制的行为都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不同的法律制度相互交织,在适用上产生冲突,影响法律的执行能力。
(三)损害结果的评定标准不合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以经营者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并以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作为判断损害结果的标准,在平台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无法适用。早期平台企业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的,除了大量科学技术的支撑,平台经营的流量与数据的支撑也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过程。然而新兴平台企业对大型平台企业实施的流量劫取与数据抓取等“搭便车”的行为,能够快速获取大平台企业长久积累的竞争优势,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对于大平台竞争利益的损失,以及新型平台企业获取的流量与数据的竞争利益,都难以用传统的金钱数额来衡量。《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的“互联网特别条款”也是从行为和法益两方面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本质上只是将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并未从实质上把握住信息技术加持下互联网竞争的不确定性。对于既有互联网因素又有平台因素加持的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加难以评价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结果。
损害结果难以确定,执法机关就难以认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会产生放纵破坏市场竞争行为的效果。即使认定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机关也难以据此确定惩罚数额,只能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要求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者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对于平台企业利用网络效应、流量效应获取的大量利益来说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甚至会出现平台企业利用噱头再赚取一些消费者的注意力。
三、对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完善建议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未来必将会出现更多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完善平台经济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方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对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进行完善时不能仅局限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目前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之中。要在现有的理论知识框架与法律规范体系下进行创新,结合信息网络环境下平台企业自身具有的“互通性、开放性、跨界性”等特点完善相关理论。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关于主体界定、竞争关系与损害结果这三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将单一主体规则引入主体界定之中、以平台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认定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的标准,以竞争行为对竞争效果的影响来评估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结果。
(一)将单一主体规则引入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界定
引入单一主体规制理论判断实施不正当竞争的平台企业数量。对于企业主体独立人格,与民商事法律侧重从民事行为能力、民事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的角度揭示不同,竞争法注重从功能与事实的角度认定企业是否构成独立稳定的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从双方是否构成实质上的竞争关系来认定市场中存在的主体个数及相关关系。某些在民商法中本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由于某种事实或法律上的因素,在竞争法的适用过程中会被视为同一个市场主体[7]。在平台经济中,平台企业的发展明显呈现出集团化的特征。一家控股公司可能直接支配着多家平台企业进行同业态竞争,母子公司之间联系极为密切。由此,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状态会出现三种控制情形。第一,子公司完全受到母公司的控制性影响,子公司丧失独立经营权,没有真正地自主作出决策的自由;第二,母公司与子公司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协同进行决策,这种行为在实质上属于一个集团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进行的任务分配;第三,在母公司的控制影响下,各子公司之间协商制定经营策略,相互实施数据抓取,流量互通等行为。在这几种控制情形之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及各子公司均不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关系,在竞争法实践中应视为同一个主体。其针对其他平台企业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视为集团整体的行为,共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平台企业的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是判断主体个数的重要因素。当然不能仅从母子公司之间存在控股关系就一概认定为是整个集团公司的行为,也不能仅从行为的表面特征去认定平台企业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把握好平台企业之间的主体关系,界定双方是否构成实质上的竞争关系。子公司若具有独立经营权,完全可以自主决策的情况下,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从而对其行为进行判断。
另一方面,在平台经济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平台内经营者。平台企业作为平台市场的提供者,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平台内的经营者对于平台企业具有极强的经济依赖性。因此,平台企业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就具有了相对优势地位,甚至于可以控制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8]。此时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平台内经营者施加控制,实施影响,甚至可能侵犯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权利,进而达到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影响其他平台企业正常经营的目的。故应根据平台企业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控制关系进行主体界定。
(二)将平台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竞争关系认定的连接点
以平台企业的竞争行为是否针对竞争对手的流量与数据等核心利益作为判断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的标准。平台经济的核心要素包括平台、用户与大数据这三部分,互联网经济的去结构化与去中心化的特征使跨界竞争成为平台竞争的主要模式[9]。传统的模式化竞争关系分析范式集中在同业竞争,继续适用会加大执法的适用难度,造成规定与适用的冲突。因此,需要对传统的竞争关系的认定模式进行拓展,以打破同业竞争的限制[10]。在确定平台企业竞争关系的界定方式时,一方面要确保达到有效规制平台企业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同时也要防止因认定标准的扩张而导致对正常竞争行为的不当打击。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不涉及具体产品、服务,故应摆脱传统分析范式中的行业领域、经营性质及商业发展模式的限制与经营者之间是否经营具有相似性、相同性或者可替代性等传统固化要素的影响[11]。在认定竞争关系时,要以平台企业实施竞争行为是否针对其他平台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为切入点,来判断各方平台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关系。同时对竞争关系进行扩张,只要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具有可替代性,或针对的客户群体相同,抑或间接促进了他人的竞争,都可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从动态的角度衡量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纠纷,是否对市场竞争秩序有破坏。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执法机关也通常以具体的经营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请求制止行为、赔偿损失为起点的,而非直接判断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是否受到损害。因此,以平台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的标准,既方便了执法适用,也有利于维护其他市场参与者与潜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
另外,为保障《反不正当竞争法》功能与目的的恰当实现,在平台经济领域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竞争关系不能只局限在平台企业之间,还应包括为自己或他人争取竞争利益而针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破坏其公平竞争所产生的竞争关系,即正当的经营利益受到他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市场主体都应被认定为有竞争关系。
(三)以竞争效果作为评估平台企业损害结果的因素
将平台企业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对市场竞争效果产生破坏作为判断损害结果的依据。经营者在市场中展开竞争行为并不断造成竞争性损害是市场经济运转的正常状态。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形下,企业实施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行为才会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仅有损害是无法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但没有损害也就必然没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损害的对象也可能会是特定的法益[12]。只有选择适当的损害结果评估方式,才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明确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执法机关通常以原告法益的侵害作为认定损害结果的依据,即以原告经济利益的损失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结果。缺乏了站在竞争机制的角度,对市场竞争效果影响的评估。因此,要突破传统的行为与法益两方面认定的限制,尝试从经营者的竞争行为对市场竞争效果的影响的角度入手。在遵从市场充分、自由竞争的前提下,考察平台企业实施的行为是否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是否破坏了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具体去考虑是否损害了某一具体平台企业的经营利益或符合某种行为的构成要件。采取这种符合动态竞争和竞争性损害特性的评估方式,一方面可以发挥市场的激励创新与自由开放的作用,营造宽松有效率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防止了平台企业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破坏了市场秩序,却因没有具体的损害对象而难以追责的情况发生。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者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针对这一赔偿数额较低的问题,应提高处罚的数额以弥补损害与赔偿的不对等的漏洞。在侵权人所获利益与经营者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前提下,该条款给了执法机关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数额自由裁量权。然而该赔偿数额对于发展日渐壮大的平台企业来说有些微不足道,难以形成有效威慑。若单纯提高处罚上限也难以应对市场经济的多变性,一旦经营环境发生变化,该项规定仍难以适用,这无疑加大了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对此,可以改变以具体数额作为处罚上限的规定模式,设置为以经营者年度营业额的百分比作为处罚的规定模式,以增强法律的适用性。
四、结语
未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仍会不断创新发展,平台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多样性、跨领域的特征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如果仍然以同业竞争加法益侵害的双重认定标准来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增加法律的适用难度,难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阻碍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将单一主体规则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分析方法,引入平台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方法之中,以把握市场中的竞争者的数量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实质竞争关系。另外可以把视野从保护竞争者回到保护竞争本身,突破行业的限制,以平台企业间竞争所谋取的核心利益为抓手确定竞争关系与竞争对手,判断平台企业是否通过损害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利益谋取不当的竞争优势[13]。任何竞争都会造成市场主体利益的损失,对于新型竞争行为,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给企业预留一定的自由空间,权衡好规制框架与创新的内在兼容性,以增强认定范式对其的适用性。
[1] 刘佳欣.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的流量劫持——以流量劫持典型案例为分析样本[J]. 法律适用, 2019(18): 80—88.
[2] 蔡川子. 数据抓取行为的竞争法规制[J]. 比较法研究, 2021(4): 174—186.
[3] 张新宝. 互联网生态“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设置研究[J]. 比较法研究, 2021(3): 11—24.
[4] 廖建求, 陈锦涛. 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认定与立法改进[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9(4): 43—50+134.
[5] 焦海涛.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J]. 中国法学, 2017(1): 150—169.
[6] 王先林.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完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6): 64—72.
[7] 刘武朝. 欧盟竞争法中的单一主体规则及借鉴[J]. 比较法研究, 2014(4): 135—142.
[8] 王玉辉. 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违法性判定与规制路径[J].当代法学, 2021, 35(1): 106—116.
[9] 陈兵. 互联网经济下重读“竞争关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意义——以京、沪、粤法院2000~2018年的相关案件为引证[J]. 法学, 2019(7): 18—37.
[10] 王艳芳.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解构与重塑[J]. 政法论丛, 2021(2): 19—27.
[11] 叶明, 郭江兰. 误区与纠偏: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87—94.
[12] 孔祥俊. 论反不正当竞争的基本范式[J]. 法学家, 2018(1): 50—67+193.
[13] 张占江.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范式的嬗变:从“保护竞争者”到“保护竞争”[J]. 中外法学, 2019, 31(1): 203—223.
Research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Platform Enterprises
BAI Yu-peng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the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also increasing. Due to the multilateral market nature and network effec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platform enterprise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 domain and cross industry with data and flow as the core, which leads to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subject identity, difficult ident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and unclear evaluation of damage results when identifying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view of this, the subject identity can be identified by introducing the single subject rule and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the enterprises since they are incorporating into groups; whether the platform enterprises implementing unfair compet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ting for data and flow should be taken as the standard to identify the existence of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the specific legal benefit of competition be damaged should be taken as a basis for judging the damages,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prevents excessive intervention.
platform enterprise;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D922.294
A
2095-9249(2022)02-0048-05
2022-03-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FX098)
白宇棚(1997—),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竞争法。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