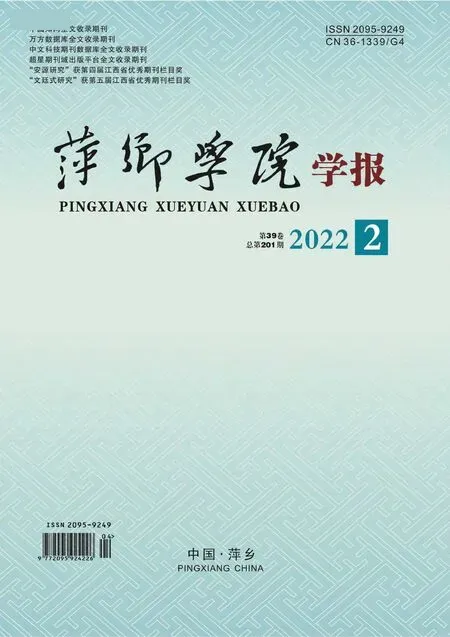身份政治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困境
廖玉林,金承志
身份政治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困境
廖玉林,金承志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身份政治作为西方当下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现象,以突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身份政治产生有着时代共性和整体脉络,是多重因素催生的结果。身份政治基本内容的阐发是基于特定群体对应的政治实践的,其理论困境包括消解阶级政治、诱发民粹主义、阻碍国家治理、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理清身份政治的理论困境,不仅有助于认清当今大变局环境下国际政治走向,也有益于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身份政治;阶级政治;全球化;理论困境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等及文化冲突带来欧美政坛的喧嚣与争斗。党派抗争、政治分裂等政治运动纵深发展。在纷繁复杂的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期许出现统一的政治规范与机制。由此,在西方社会的广泛碰撞交流下,身份政治成为21世纪欧美政坛的焦点问题。国内学术界在身份政治议题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但系统梳理身份政治思潮产生、内容及局限性则罕有论及。准确把握身份政治理论困境,厘清其实质与危害,对于预测身份政治未来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身份政治的产生
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转变,正是后工业社会的衍生导致传统的阶级政治逐渐走向没落,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逐步取代阶级政治,成为当下流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现象,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大体而言,西方身份政治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身份政治中种族问题的凸显。这个阶段种族问题爆发于多个国家,美国民权运动、西欧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等,这些运动无不包含身份政治的特征。这些不同的族类群体,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为争取相关利益诉求,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抗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身份政治中移民问题的崛起。随着欧美种族问题的平息,移民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登上历史舞台。欧美持续的移民热潮,给迁入国带来突出的政治社会问题。当移民在迁入国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时,便衍生出以移民为单位的移民族裔,为获取相关权益联合起来抗争。欧美移民人数的激增,多是受其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和福利政策的吸引。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00—20年代,身份政治中多数人群体的崛起。当下少数人的身份政治仍旧活跃,但21世纪期间,欧美身份政治却以多数人的身份政治为突出特征,在这20年来的几起重大事件中可寻其佐证。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2020年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三起重大事件。综上得出,多数人为主体的身份政治之间的互动与对抗,将是欧美新一轮身份政治的重要表征[1]。
身份政治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蕴藏着其产生的缘起,多重因素在不同阶段中作用于身份政治。主要是复杂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在矛盾催生了身份政治。
首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资本、商品、信息技术、生产力和文化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城乡、地区、民族、区域、国家等的联系愈加密切。密切的交流带来的是人们在价值取向、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趋同。除此之外,国内外开放的现代化体系刺激人口的流动速度和频率,相对于以前的封闭状态,现代人身份则变得不再单一,人们拥有着多重身份,也在不断变更着身份。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着全球经济的运行,但全球化融合过程中断层情况也逐步凸显,在不同国家及国家内部间产生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2]。例如,随着移民潮的流行,移民的大量迁入对迁入国造成重大影响。迁入国的社会结构和人口比例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频频洗牌。身份认同突破传统的群体限制,从主流的、大规模的、同质的等群体向“边缘化”、小规模的、异质的等群体偏移[3]。
其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第一,事物的发展总是由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当代精英政治主导地位丧失,被历史逐渐淘汰,成为一种旧事物被新兴的身份政治逐步取代。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即是如此,美国两党价值观上的冲突,导致双方相互扯皮、互不相让,在涉及各大民生问题决议时分歧不断、相互否决,这必然激发作为草根政治的身份政治的崛起。第二,利益集团操纵着西方政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民意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实现。为争取自身的权利,民众自发以种族、肤色、地域、宗教等来划分群体,通过某种特定身份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通过群体的力量争取各项权益。第三,身份政治不自觉地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分离出来,表现为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对抗,显现出政党与民众的对抗。一方面,这体现出西方政党政治领导的不力,民众对领导阶级的不信任造成了“传染性”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就营造了不同身份群体政治对抗的氛围。
最后,多元文化主义内在矛盾。作为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产物,多元文化主义可作为西方身份政治产生的重要动因。从多元文化主义本身积极意义出发,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把尊重、承认、保护不同群体的差异和权利作为核心理念。其目的就是追求差异上的平等。从辩证的角度看,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多元文化主义指导第三世界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也推进了西方国家族群平等和内部多元民主的进程。多元文化政治为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与尊重,致力于推动“包容他者”的文化多样性,提出了“身份政治”“文化多元主义”“差异政治”等理论口号。但身份政治的兴起,则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消极层面。第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脱离人的思想实际。不同身份群体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然而,不同身份群体却站在各自立场均要求一切平等。不同群体作为不同利益方,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这严重影响国家整体的身份认同。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寻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文化价值的平等,强调在教育、就业、语言等方面实施“平权行动”。凡事过度都会走向所追求的对立面,当追求身份平等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国家运作也会出现重大危机。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着自身矛盾,就文化而言,不同的群体文化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及价值,但并不是每个群体文化价值都是平等的、先进的。多元文化主义矛盾点在于:一方面追求绝对平等,另一方面群体文化本身又不平等。这就会造成群体之间相互扯皮无法达成共识,各自形成“单位”的碎片化分布。
二、身份政治的内容
依赖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我理解的环境,“身份”(identity)或译作“认同”,可用于回答“我是谁?”以及“我归属什么”之类的问题。身份政治即是一种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形态,即为了获得身份认同反抗他者对自身的支配。文化政治与差异政治用于理解身份政治尤为贴切,身份政治就是在文化领域内强调自身身份与他者的差异性,且身份政治寻求认同时都是抱团取暖。这个“团”可定位至种族、肤色、性别、特殊性取向的人群等等。身份政治作为当下流行的新事物,不能仅停留在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也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解读。身份政治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其他形式,因此,对于身份政治的理解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本文对于身份政治的理解是:身份政治是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准,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的政治形态[4]。
身份政治的内容剖析可从其基本内涵处入手,本文对于身份政治界定的三个方面都有其相对应的政治实践,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身份政治的内容。
首先,身份政治下的不同群体把寻求平等作为首要诉求,平等的诉求无法得以满足时则另辟蹊径寻求某种补偿性正义。这些特定群体并不一定要求群体的优先性,抑或宣扬把特定群体的诉求作为政治判断的标准[4]。因此,这些特定群体的行动出发点就是基于对平等的诉求,而不是对身份独特性与崇高性的极端追求。当群体的平等权益得不到满足时,群体则希望获得相应替代品作为同等意义上的正义补偿。因此,某个特定群体寻求一定的诉求时,这些诉求也必然是具体的、可实现的,这些泛化的诉求得以满足后,身份政治的目标才算实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特定群体身份政治斗争才算完结。
其次,身份政治以特定身份的群体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具有明显的排斥性。当群体具有排斥性时往往涉及利益难题,并以群体的形式谋求解决。这时群体往往会把自身摆在优先位置,在全局利益、集体利益面前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特定群体具有的排斥性特点,促使其将矛头指向竞争对手,以身份为标签的群体之间便基于群体利益相互博弈。在此趋势下,身份政治所携带的文化特性,成为特定群体实施集体行动与实现团体利益的重要方式,不断发展为特定群体获得特定利益的手段。
最后,所谓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落脚点主要是表达。与上述两种身份政治的内容不同,以表达为动力的身份政治,单纯希望通过一个宣泄途径传递自身身份的积极意义,即可视为“我就是我”的自我确证。特定身份群体远离权利和经济利益诉求,同时也不强调自身的优越感,仅仅通过表达,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通过“自我定义”确定自身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而拒绝任意其他群体的规范。他们也正是通过持续表达的方式,防止被定义、被命名,以表达为窗口划定属于特定群体的生活领域。
三、身份政治的局限性
随着西方身份政治的演进更迭,我们的确不能避而不谈身份政治在推动西方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譬如,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权利争夺过程中,更广泛的平等取得了极大推进。身份政治的产生本就源于不公正对待,它助推社会朝着抵制霸权、拒绝歧视与不公、保护少数人正当权益与自尊等方向前进。但身份政治不乏凶险与局限,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身份政治的局限性,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身份政治的局限性尤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抛开阶级分析方法并遮蔽与消解阶级政治。任何身份群体的社会政治运动仅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当利益诉求触碰其他群体权益时,就会引起其他群体或者国家的排斥和攻击。身份政治的形式体现出两种样态:一是族群性,二是狭隘性。这就与全民认同的理想政治相背离。然而,以文化的方式进行利益抗争的身份政治,无法完全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先天缺陷,因而难以达到彻底革命的效果。一方面,身份政治作为阶级政治后续的新生物,原则上就绕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阶级分析方法,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剥削的事实,极有可能被身份政治围绕的种族、性别、肤色等议题掩盖。另一方面,身份政治作为文化领域的运动,无法产生实质性的革命效果,大概率会将解放政治沦为表演政治。“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意,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是基于少数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治理,资产阶级借助统治地位用以实现其少数人共同利益[5]。“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单个的文化差异群体,必须重返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干预才可能形成普遍化的斗争。身份政治学表面上看似极具反抗力量,实际是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框架。身份差异中的解放力量并不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企图从这些被主流符号排斥的边缘群体中寻找真正的革命力量是无法实现的。”[6]
其次,助长极端矛盾冲突,诱发民粹主义极端行为。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下,身份政治成为西方当代社会一抹重要的色彩。但西方社会贫富差距大、中产阶级萎缩、下层阶级扩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情形加重。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的常态化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形成的。2008年经济危机后,身份政治下产生的多元文化并未使不同文明之间和谐相处,少数恐怖分子的极端行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民粹主义由此做出应激反应,以保证自身经济安全与人身安全。民粹主义泛滥,这是底层群众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博弈。当代,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身份政治化下的民粹主义深化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危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联合“朋友”与“敌人”斗争。总的来说,身份政治是建立在话语体系上的文化抗争,远不及实际的行动产生的效果,理论上激进的批判无法替代实践的革命。由此可见,身份政治状况下的实践助长民粹主义极端行为。
再次,不可避免地增加国家治理的困局。身份政治作为当代西方复杂政治运动的产物,难以为西方社会提供稳定的社会意识,也就难以实现优质的政治统治[7]。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局,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正确道路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地位也稳步提升,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时也显得游刃有余。而身份政治作为西方的新兴政治,对西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多元的,包含冲击主流政治格局、削弱国家认同、造成民主政治危机等方面的局限性。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发起的反移民浪潮、“酷儿运动”、“Me Too”等群体性社会运动,都具有明显的身份政治特征。身份政治话语操控下的特定群体,将围绕相关文化议题展开抗争,而无法承担起凝聚社会力量的任务。这就表明,这些带有身份政治特征的运动导致的后果,无疑会给西方国家治理带来更大的困局。
最后,身份政治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身份政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带来了激烈的社会与文化冲突,从国际上看,这种冲突与对抗已经传导至国际领域。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新世纪的身份政治浪潮涌动,迫切重构新兴的西方社会规范与文化认同。全球化创造出的市场、技术等,为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更为优渥的盈利环境。他们为使得利益最大化,把产业转移至劳动力密集、生产成本低的不发达国家。反向而言,发达国家内部则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以及产业的空心化等问题。发达国家民众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充满焦虑,民众对现存状况的不满极易诱发逆反情绪。就全球化的背景看,身份政治的影响将持续扩大,身份政治的崛起将为全球范围内的激烈冲突与对抗蓄力,必然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发展。
综合来看,身份政治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吸纳,且在发达国家活跃实践。当身份融入政治,特定的群体便坚定自身的身份立场展开斗争,涉及了身份的政治议题就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分裂。上升至国家层面,身份政治亦会影响国家对外交流,严重威胁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和平相处。就身份政治的发展方向上看,当代的身份政治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按事物本身发展规律看,身份政治也不可能一直存在。身份政治可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差异政治,它源自于群体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框架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的控诉。可以大胆预测,身份政治一定会给西方发达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带来连锁性的消极影响。因此,身份政治的发展是不容乐观的。这就需要世界人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身份政治隐藏了阶级政治,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科学的理论对于反思身份政治理论困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身份政治对内易诱发极端民粹主义,对外易引起“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政治格局下的身份政治将持续运行,由此衍生出的消极影响将严重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反观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所建构出的共同体思想,就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只有付诸实践的共同体思想才能回应人类解放事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出路问题[9]。因此,身份政治问题有效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全盘抛弃和否定资本主义,并站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王军, 黄鹏.欧美身份政治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困境[J]. 民族研究, 2020(4) : 42—60.
[2] 方敏, 朱韵.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历史局限性反思[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10) : 81—90.
[3] 庞金友, 洪丹丹. 大变局时代的身份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危机[J]. 行政论坛, 2019, 26(6) : 5—13.
[4] 谭安奎. 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J]. 探索与争鸣, 2020(2) : 99—111.
[5] 梁宇.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J]. 哲学研究, 2015(5) : 31—35.
[6] 郑薇,张亮. 身份的迷思——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学的兴衰[J]. 探索与争鸣,2018(6):42—59.
[7] 陈志刚.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发展——从马克思到习近平[J]. 人民论坛, 2019(12) : 102—104.
[8] 刁大明. 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0, 37(6) : 48—73.
[9] 梁宇. 走向共同体治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1) : 30—37.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Dilemma of Identity Politics
LIAO Yu-lin, JIN Cheng-zh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trend and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West nowadays, identity politics plays a role in the global context with its prominent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The idea of identity politics develops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reflecting the commonality and overall context of the time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identity politics i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practices of certain groups. The theoretical dilemmas of identity politics include the elimination of class politics, the elicitation of populism, the obstruc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threat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dilemmas of identity politics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oday’s climate of great change, but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dentity politics; class politics; globalization; theoretical dilemma
D035
A
2095-9249(2022)02-0016-04
2021-12-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KS005)
廖玉林(1997—),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
〔责任编校:吴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