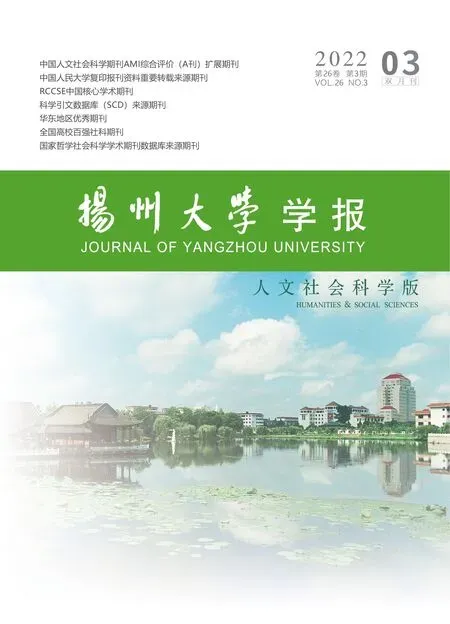刑事司法中情感考量的基本维度
万国海,高永明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在通常的认知中,情感被认为是感性的存在,甚至是和理性对立的非理性,法律作为理性的化身,因此不可以与情感产生交集,更不应有协作。有学者认为,情感是理性的敌人,情感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理性的、混乱的和特殊的。(1)Gerald L. Clore, For Love or Money:Some Emotion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ity”, 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80, no.3(2005), pp.1151-1165.因此我们不需要哭泣的法官,刑法不应相信眼泪。从我国的现实看,传统司法并不是完全与情感隔绝,这体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在悔罪、宽恕等情感已为我国立法确认的现实下,(2)《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在诸如宽恕的治愈力量已经被倡导了几个世纪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冷静的神话”。在历史上,情感与刑事司法有交集,在当下现实中,刑事司法的过程越来越重视情感的影响。在最根本的理论依据上,情感本身具有影响刑事司法的性质和功能,因此本文分别从历史、现实以及理论依据三个维度对刑事司法中的情感因素予以考量。基于中西哲学观的不同,情感影响刑事司法虽呈现出不同的分野,但在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情感转向”的现实下,必须重视情感的刑事司法功能,构建新时代的司法文明。
一、刑事司法中情感考量的历史维度
(一)西方刑事司法与情感的分离与转向
在历史维度上考察刑事司法与情感的关系,中西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或知、情、意三分)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而且一般而言,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情感之所以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在西方传统中,理性被理解为纯粹的认识理性,是对“事实”“真理”“规律”的认识,与价值无关,由此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是根深蒂固的。(4)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这实际上导致西方哲学的情感缺陷,理性与情感的对立和分离成为西方法律的基因。西方法律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与情感切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创立的三段论推理意图精准地实现法律判断,排除法律中的一切情欲。亚里士多德说:“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统治,这就有如说,唯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 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68-169页。自此,西方法律走上了与情感的对立之路。
启蒙运动使欧洲进入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的核心即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倾向于认定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不理性的情感应被排除在法律之外。(6)Terry A. Maroney, Law and Emotion: A Proposed Taxonomy of an Emerging Field”, Law and Human Behavior,vol.30, no.2(2006), pp.119-142.比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官……条件第一要对……公平要有正确的理解……其次,要有藐视身外赘物——利禄的精神。第三,在审判中,要能超脱一切爱、恶、惧、怒、同情等感情。”(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0页。刑事审判中超脱一切感情,法官只能机械司法,这是霍布斯创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其所言的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形成的一部人造的机器人,而作为国家机器的法律同样是机器,故而当然不应受情感的影响。此后,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情感表达虽然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是有用的,但就像阑尾这种遗留下来的退化器官一样,现在不再起到任何积极作用。(8)李柏杨:《情感不再无处安放——法律与情感研究发展综述》,《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第162-177页。由此,情感与法律对立,情感需要从刑事司法中完全剥离,成为西方刑事司法的主流。
晚近,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在讨论情感问题,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及研究领域都相继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9)郝强:《从“感觉结构”到“情感转向”——雷蒙·威廉斯与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关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2-19页。目前这种讨论很快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批评这些本土地块蔓延开去,波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10)陆扬:《“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30-38页。而在刑法领域,有人认为,“法律和正义的情感化”或情感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已发生,但一些人将这种情感转向的根源追溯到更早的时间——重新发现犯罪受害者。(11)Nina Persaka, Beyond Public Punitiveness: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Criminal Law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vol.57(June 2019), pp.47-58.2015年7月26日至8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举行了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第27届大会,与会学者围绕“法律与情感”“理性与情感”“刑事法律、理性与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12)章安邦:《“法律、理性与情感”的哲学观照——第27届IVR世界大会综述》,《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132-137页。
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毕贝斯(Stephanos Bibas)、墨菲(Jeffrie G. Murphy)等专门研究情感与刑法关系的学者。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大法官在《法律理论的前言》一书的第七章“法律中的情感”专门论述了法律与情感的如下五个问题:1.不法行为是被情感激发的,这一事实应如何影响法律对于这一行为的评价?情绪性应当使法律对违法者更严厉还是更宽松?2.法律是否应当以及应当如何运用情感?3.法律的管理人——无论是法官、陪审员、检察官还是警察——的情感状态应该如何?他们应当像计算机一样没有情感吗?如果不是,情感到底应当怎样进入他们的判断?4.应当用什么样的屏蔽或过滤器来保证法律的管理人在执行法律职责时处于正确的情感状态之下?5.法律如何可以避免诉讼过程的情绪性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阻碍解决案件的努力?(1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言》,武欣、凌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日本的内海朋子、林美月子等学者对此研究亦有相当建树。总的来看,域外研究具有一个清晰的线索:情感是否在法律中扮演一个角色,转向情感如何与法律互动,进而在刑事司法情境下,应该哪一种情感发挥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目前,西方多国已经在刑法中确立了情感的作用,(14)典型的立法有:《德国联邦刑法典》第33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出于慌乱、恐惧或者惊吓而超越防卫的界限,那么,他不受处罚。”《瑞士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人防卫过当的,法官以自由裁量减轻处罚。正当防卫人由于可原谅的慌乱或者惊慌失措而防卫过当的,不处罚。”《斯洛伐克刑法典》第 25条第3款规定:“如果在侵害所导致的强烈的激情状态下(尤其是困惑、害怕、惊慌所导致的后果)以第2 款所指的方式避免侵害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罗马尼亚刑法典》《葡萄牙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加拿大刑事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等在这一方面均有相关规定。对因恐慌、惊吓、被激怒、惊慌失措、激情等导致的犯罪均作出了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在西方,刑事司法的情感转向已经形成。
(二)我国刑事司法与情感的传统交织
我国法律与情感的关系体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特征。就法律的实质内容来看,无论国法或民间活生生的法律,都深受儒家伦理的强烈影响。(15)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而儒家伦理的要义即在于“礼”以及由此决定的情、理、法的架构形式。(16)栾爽:《情、理、法与法、理、情——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特色与现代转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47-51页。中国古代立法中的“情”包括了司法判例中的“感情”和“同情”。(17)王斐弘:《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情理法辨析——以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为例》,《中西法律传统》2009年第1期,第49-90页。因此,情感与法律在我国自始即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乃基于其中国哲学背景。中国哲学的首要特点是情理合一,不同于西方的重理性,而是重在于情。中国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情感也不是单纯感性的,情感能够通向理性,具有理性形式。或者说,情感本身就是形而上的,理性的。或者说,情感是理性的实现或作用。(18)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这实质上是说我国法律与情感具有同质性,二者不具有西方那样的基于基因的势不两立,这是根本。除此之外,我国社会的司法传统是“情理法”结合处断案件,在争端的解决上,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再次是 “理”,只有最后才诉诸 “法”。(19)[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86页。尤其是将“情”放在第一位,“情”与“法”一起定分止争,二者共同构成“规范多元主义”,因此在解决纠纷的视角下,二者具有协助意义,故而所谓“法有限而情无穷”。
徐忠明教授认为,我国明清时期司法心态模式即为付诸情感。(20)徐忠明:《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第5-38页。可以说,我国近代的司法改革也是在耻辱情感之下产生的,“中国近代的司法改革是在强烈的耻感情结触动下展开的。耻感包括外耻感和内耻感:外耻,是国人在西方列强攫取在华司法特权、被人欺负后引发的羞辱感;内耻,是国内司法弊端丛生、明显滞后于近代司法文明,国人自我观照后产生的羞愧感”(21)张仁善:《论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中的耻感情结》,《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32-141页。。近代以来随西学东渐,伴随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是西方化特征,但情感因素在司法中一直得以传承。“动之以情”即是民间司法者通过运用“情感因素”促使纠纷当事人的内心产生触动,从而影响、感化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22)吕廷君:《民间司法的情、理、法》,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卷,第141-149页。
二、刑事司法中情感考量的现实维度
(一)我国当下刑事司法对情感的不当疏离
在现实维度上考量刑事司法与情感的关系,中西方均体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虽然情感与法律的交织构成我国一直以来的刑事司法现实。但晚近以来,受形式正义、罪刑法定以及奉行严格的三段论推演、刑法教义学等影响,产生了并不关注受害人等各方的情感诉求的司法倾向,导致出现了违背正常情感、令舆论哗然的判决,结果又不得不通过二审或者司法机关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新时代司法文明的建构和进程。当然,这种机械司法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刑事司法过程中对情感的忽视无疑是重要原因。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依然是坚持封闭性的刑法教义学立场,局限于对现有规定的适用而对法律明文规定之外的、合乎公众认可的情理因素置之不顾。(23)崔志伟:《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的“合情理”路径——枫桥经验中的情理观及其启示》,《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6-31页。从情感与刑事司法交织的传统看,这种现状实际上背离了传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此外,关于情感对刑事司法的影响,理论研究也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并提供应有的解释。只是近年以来,我国学者才开始零星关注情感与刑法、情感与刑事司法问题。总体来看,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不够,主要表现在研究重心集中于量刑问题,情感影响刑事司法的理论依据这一基础性问题没有被关注。同时,研究内容集中,过于单一。目前基本只研究作为情感的宽恕的量刑影响问题,其量刑之外的其他功能没有被关注。研究视角相对单向,只注重情感的量刑影响,但忽视了其量刑影响的限度。研究只注重情感入罪、量刑的意义,但忽视其出罪的意义。研究着力于定罪量刑的具体问题,没有从宏观的司法文明建构的高度展开。情感与刑法的理论关系未被深入研究,甚至有人认为在法律中尤其是在刑法中不可能、不应该存在情感,讲情感与刑法是个错误的命题,这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情感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的普遍幸福,应对人类的情感作共同的关切。在此背景下,必须关注诸如怜悯或同情、忠诚、愤怒或厌恶、宽恕、憎恨以及忏悔、羞耻等情感之于刑事司法的角色功能。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法律并不是冰冷冷的法条,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情感人。”第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新时代刑事审判要“尊重人民群众朴素情感”,“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兼顾天理、国法与人情”。这为新时代情感影响刑事司法的制度建构提供了依据。但国外的研究已经把“情感与法律运动”发展为包括“情感与刑事法”在内的诸多子学科研究,这势必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因此,加强情感因素对新时代刑事司法文明建构影响的研究,不仅是急需研究的刑事司法文明理论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晚近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对情感的捍卫
如上所述,西方国家刑事司法的主流传统是与情感的分离,即便如此,仍难以抵挡情感对法律的渗透。贝卡利亚(Beccaria, Marchese di)富有激情地指出,法律必须以人类的自然情感为基础,“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2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29-30页。。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代大陆法律体系并不像它们有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具有理性倾向。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关于情感在司法决策中的讨论一直在不断进行,许多法律学者都捍卫一个相当积极的观点,认为情感是法官审议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5)Pavel Vasilyev, Beyond Dispassion:Emotions an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Modern Europe”,Legal History,vol.25(January 2017), pp.277-285.1923年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大法官在其书中感慨道:“即使我们已竭尽全力,我们仍然不能使自己远离那个无法言传的情感王国,那个根深蒂固、已经成为我们本性一部分的信仰世界。”(26)[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费伏尔(Lucien Febvre)在1941年首次强调了法律与情感的历史关系。在其描述的16世纪的刑事审判中,国王的仁慈、怜悯或恩典在司法上比公正更强大,更被接受。(27)Lucien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in Burke & Peter,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24.对法律与情感的关系做出推进性研究的是美国联邦法院已故法官布伦南(William J·Brennan)大法官,他在1987年的一次演讲,对情感与法律关系的发展产生具体的启发与带领作用。布伦南大法官主张,一般人对于某状况而生的情感与直觉反应在人们意识到其存在之前,其实已经介入人的认知之中,影响了法律论证,因而他反对理性与激情(passions)在概念上切割与对立。(28)William J. Brennan, Jr., Reason, Passion,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Law”, Cardozo Law Review,vol.10, no.3(1988),pp.3-23.
我国刑法理论资源在2000年之后从苏联转向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此前的刑法理论基本来自苏联,但却忽视了苏联早期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情感运动。法律运动的创新思想在20世纪前几十年的俄罗斯帝国后期开始流行,强调法律的道德起源,甚至提出将法律本身视为一种情感。在20世纪初俄罗斯革命时期,情感的司法化运动开始在俄罗斯的法庭进行。法官的理想发生了变化:激情取代了冷静,革命的法官强调法律的道德根源,提出将法律本身视为一种情感。(30)Pavel Vasilyev, Beyond Dispassion: Emotions an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Modern Europe Legal History”, Rechtsgeschichte-Legal History,vol. 25(January 2017), pp.277-285.情感影响刑事司法和法律行为者的行为成为早期苏联法庭的辩论框架。早期苏联法学家非常强调法律判决中的情感,并为法官个人确立了高度的自主权,甚至在苏联早期出现与法律和情感有关的“革命正义”理念——法官应该以革命的正义情感为指导,而不受正式的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31)Pavel Vasilyev, Revolutionary Conscience,Remorse and Resentment:Emotions and Early Soviet Criminal Law,1917-22”, Historical Research,vol.90,no.247(2017),pp.117-133.在英美判例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陪审团的多数决定作为情感“规范表达”的基础;但在大陆制定法体系中,对情感的“规范表达”所依赖的,虽然也是议会内部多数决定的归纳体系,但其基础并不是个案中的情,而是“类型化事物”中的情。(32)谢晖:《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10-15页。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人们对法律和情感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了兴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家们挑战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法律是缺乏情感的东西的观念,并研究了情感在法律规范和实践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三、刑事司法中情感考量的理论维度
(一)情感是人的本质要素
在刑事司法中之所以能够对情感因素予以考量,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维度上情感是人的本质要素以及情感的理性认知功能。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情感影响刑事司法有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理论基础。受黑格尔自由理性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不同著作中也有不同的具体界定,但无论何种认识,情感因素一直是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中心。马克思一贯反对片面地看待和考察人的本质,认为情感是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强调重视情感在人的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了情感,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更不可能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理性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双重维度。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人都不是完整的人,情感是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33)熊治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情感”思想及其现实价值》,《理论月刊》2017年第10期,第22-27页。在情感的作用之下,人的实践活动才会成功,因而情感具有实践的特征,由此,情感可以推动人的实践活动的进行,这意味着实践本身即包含情感因素,因此将价值判断、行为评估与情感完全分离的做法是没有依据的。
刑事司法的过程本就是一个兼具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实,即便是事实判断,有时也需要司法共情,即通常说的设身处地进行判断。比如在于欢案中,如果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于欢角度考虑当时的情况,就应该能够理解于欢当时的愤怒以及他此后的行为选择。二审认定于欢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于欢的角度合理理解其当时的行为选择。人本身是情感性动物,行为人选择犯罪并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结果。犯罪后行为人的情感变化体现了犯罪人可罚性的变化,刑事案件审理上的认知体系不能通过玄学、宗教来进行,唯有通过科学才可以实现,但科学并不是完全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以逻辑推演作为认知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3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因而刑事司法的过程要注重犯罪发生的情由,关注人的情感本质, 需要移情来理解犯罪发生的前因后果,需要司法共情来理解犯罪发生的因果,离开人的情感本质判决案件,有时导致的结果是刑事案件判决结束,但受害人和加害人仍然势如水火,仇视的情感依然存在。被害和加害关系的恢复首先是情感的恢复。因此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应关注人的情感本质要素。
(二)情感具有理性认知功能
传统上,法律被认为是理性的保留,而理性则与情感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情感不一定是非理性的,而是恰恰相反。(35)Nina Persaka, Beyond Public Punitiveness: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Criminal Law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 vol.57(June 2019),pp.47-58.在通常情况下,人都是情感的非理性存在,我们的许多行为受情感和理性的双重驱动。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存在,也是非理性或感性的存在。(36)许全兴:《情感简论》,《现代哲学》2004年第3期,第19-27页。同时,情感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我们甚至无法区分人的行为究竟是受理性的驱使还是情感的自然体现。我国儒家哲学认为,情感本身能够理性,在情之自然之中便有必然之理,这就是所谓情理,(37)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情感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38)K.R.Scherer,On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s:Or,When are Emotions Rational?”,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55,no.3-4(2019),pp.330-350.其实休谟早就提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理性的作用只是辅助的,它只能是情感的奴隶,即理性是并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39)[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9页。休谟哲学事实上成为情感与法律关系的论证基点。因情感本身的理性特质,故而一种正常情感的产生不是任意、任性的,它本身就包含着认知,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对事物的情感反应。情感绝不是自然的反应。人们必须首先评估问题,然后他们才能知道如何感受。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参与了情感的产生。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情感影响人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认知、决策和行为。(40)Michael W. Morris and Dacher Keltner, How Emotions Work:The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Negoti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22, no.4(2000), pp.1-50.情感更多地和社会性需要、社会认知、理性观念及观点等相联系。情感因它基于对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概括而深入的认知和一贯的态度,不仅具有情境性,而且具有稳定性和深刻性。(41)章光生主编:《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情感会对认知过程产生影响,甚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情感思维不仅先于理性思维,而且在认知过程中,情感思维也先于理性思考,从而经常取代理性思考。由于每个人的大脑都有情感和理性的并行运作,所有的判断、知觉和决定必然都有情感和理性的成分。(42)Douglas S. Massey,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The Origin and Role of Emotion in Social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7, no.1(2002), pp.1-29.在情感哲学中,认知主义者强烈反对那些把情感描绘成纯粹非理性、污染人的更高层次灵魂的无法控制的激情。机械性的、生理学的情感概念——将情感置于施动者的理性控制之外并将其简化为生理过程,应该让位于评估性、认知主义的情感概念——它认识到判断在情感形态中的作用。(43)Mihaela Mihai, Emotions and the Criminal Law”, Philosophy Compass,vol.6, no.9(2011),pp.599-610.
至少目前来看,心理学中情感与认知的密切关系并没有对刑法和刑事司法产生有效影响。因此张明楷认为,我国现行的刑法罪过理论中是缺失情感因素的。(44)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然而,许多犯罪人在犯罪的时候根本不会进行所谓利益衡量来做理性的选择,而通常是靠情感直觉进行。对于审判案件的法官而言,也无法不将自己的情感带入案件。情感是审判法官对案件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45)Jerome Frank, Say It with Music”,Harvard Law Review,vol.61,no.6(1948),pp.921-932.但即便是非理性的情感,也和法律具有莫大关系,比如刑法对激情犯的从轻处罚即为适例。因此,从犯罪发生的情感宣泄,到庭审时犯罪人可能的情感表演,进而到司法人员的情感管理,整个刑事司法的过程都离不开情感问题。故而,情感,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渗透到法律的制定之中,也渗透到法律本身之中。(46)Nina Persaka, Beyond Public Punitiveness: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Criminal Law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vol.57(June 2019),pp.47-58.情感并非对理性的污染,相反,理性只有与情感相结合,才能获得合理的认知,做出合理的决策。情感的缺失对理性的思考是有害的。大多数心理学家倾向于一种双重过程模型,即情感和非情感认知都能影响道德、法律判断。(47)S. Zeki and O. R. Goodenough, A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 to Normative Judgment in Law and Justice”,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Biological Sciences,vol.359,no.1451(2004),pp.1709-1726.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情感已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刑法体系中,每一种形式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48)Mihaela Mihai, Emotions and the Criminal Law”, Philosophy Compass,vol.6, no.9(2011),pp.599-610.
四、结语
虽然情感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刑事司法过程中,但刑法理论对此并没有提供应有的解释,近年来的零星研究还不足以推动情感与刑事法运动的进行。中国法学研究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对三段论演绎推理的过度重视,以及近年来刑法教义学的风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刑事司法过程中对情感的忽视,由此产生机械司法的困境。由于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现实,出于对情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恐惧,一定程度上导致刑事司法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然而,情感不同于具有情境性、易变性和冲动性的情绪,情绪有时不受意识的支配。情绪性立法、情绪性司法都是需要避免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情感在刑法中无处不在,就像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一样。(49)Dan M. Kahan and Martha C. Nussbaum, Two Conceptions of Emotion in Criminal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96, no.2(1996), pp. 270-372.法律规制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理性建构的,社会秩序离不开情感的存在。情感已经成为现代法律诉讼的核心成分,(50)B. Kuvaas and G. Kaufmann, Impact of Mood, Framing, and Need for Cognition on Decision Makers’ Recall and Confidence”,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vol.17, no.1(2004), pp.59-74.刑事司法的情感化现象已经发生,生活刑法中的情感正义在刑事司法中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