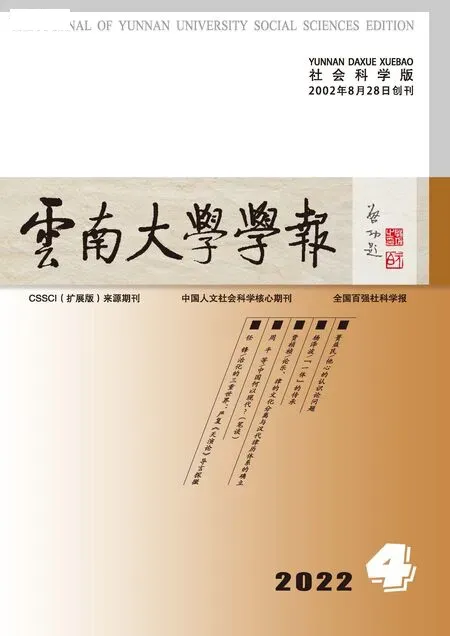谢林的政治哲学期待
——从沃格林的角度看
王 丁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尽管从谢林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许多他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看法,(1)参见:Ryan Scheerlinck,Schellings Politische Philosophie,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7, S. 386.但不同于费希特和黑格尔,在谢林的著作和讲演稿中,直接的政治哲学论述的篇幅极其短小。而且这些只言片语要么仅仅是在讨论人类之恶后一笔带过,要么就是在讨论神话之间插入的寥寥数语,唯一算得上直接“政治哲学”著作的,或许只有1796年的《自然法新演绎》(NeueDeduktiondesNaturrechts)。所以尽管我们实际上难以从谢林的正面阐述中“建构”出他完善的“政治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谢林哲学缺乏“政治哲学”维度。相反,在《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中,沃格林强调,在泛政治观念历史的意义上,“谢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是在与柏拉图、奥古斯丁或阿奎那同样的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2)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李晋、马丽译,贺晴川、姚啸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0页。这一论断乍看之下颇令人惊讶,且不说在德国唯心论内部谢林是否堪当这个评价,即便在哲学史上,或许这也是头一次把谢林提到如此高的位置。而沃格林之所以如此拔高谢林,是认为他在政治观念上的伟大在于“使一种容易爆散的经验复合体保持了生存上的平衡,(并且)以辩证法的方式将平衡融入了一种体系当中”。(3)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90页。从谢林的哲学总体建构来看,沃格林所指的“经验复合体”的“生存平衡”可以认作是谢林从“世界时代”开始,一直拓展到作为一种“哲学的经验论”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的进路;而“体系”则可以认为是谢林始终坚持的“自然—同一哲学”体系和由之衍生出的“否定—肯定”体系。但沃格林也承认,这种“伟大”不是一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直接参与了时代精神构造的伟大,而是一种来自“时代的荒凉精神氛围和学术氛围”的“绝唱式”的伟大。(4)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42页。因此,这是一种来自某种已然被时代精神遮蔽的另一传统所包含的“伟大”,亦即来自布鲁诺-斯宾诺莎传统,并像阿奎那那样立足于“调和”与“平衡”,而非把某种时代精神的趋向发挥到极致的“伟大”。这种“伟大”在于谢林的著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现代哲学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定向点”。(5)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43页。或许从这种“定向”中才能明白,何以谢林一方面认为黑格尔哲学只是“插曲”,(6)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但同时也在认真研读和批判黑格尔的著作。也只有从这种“定向”中才能明白,为什么谢林在德国唯心论所谓的“理性体系”建构过程中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黑格尔批判完了本原设定之后他继续保留,黑格尔批判完了“直观”概念后他仍继续坚持——这种格格不入或许恰恰在证明,德国唯心论在围绕体系的建构中只有一种基本话语上的“家族相似”,但争辩的焦点反倒在于,在“体系”这种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哪一种传统和建构方式才能充实这种时代精神。
因此,从谢林关于“政治哲学”的直接阐述中得出他真正的政治哲学意图只会流于表面。沃格林至少提示了我们,谢林如何在体系中以“平衡”的方式面对时代的问题和经验,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应当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经验目前仍遮蔽在“体系”时代的话语下,因此首先对之进行重新整理。
一、沃格林和谢林对时代经验的定位
沃格林把整个“现代”的实质理解为“现象主义”,它指的是“将作为科学对象的诸现象关系解释为事物的一种实体秩序”。(7)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0页。而“现象”作为“偶性的偶性”,决定了与之相关和考察现象关联的“现象科学”取代了“实在的自然秩序的科学”,因而也“取代了关于实体的知识”。(8)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4页。因此,当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现象科学高歌猛进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颇为吊诡的傲慢式颓废:一方面人获得了以数学为范型的探索无穷现象的工具,但另一方面,现象及其科学的无限性将反过来规定人的自我生存理解。人终究会发现,在这种无穷的探索背后是对整个存在中心的废黜,这种废黜迫使人不得不对宇宙的实在秩序进行不断的碎片化,只有如此方能保证现象科学的成功和傲慢:“我们也许能将我们的诸观念扩展到超出可以想象的诸空间之外,而一旦以牺牲万物的实在为代价,那我们除了原子外什么都无法产生”。(9)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2页。与之相伴,伴随着“我们的诸观念”在数学-科学意义上无限性的扩张,这种扩张由以可能的出发点,即人自身也就成了问题。沃格林引用帕斯卡的话说:
真奇怪,人竟然想通过无限多的假设——假设就像其对象一样无限多——以此理解万物的原理,并且以此为基础去认识万物……我们备受一种欲望的煎熬,那就是想发现一个坚实的位置和一个终极的恒定基础,以便在其上竖立起一座伸向无限者的高塔;但是,我们的根基破裂,大地也敞开了深渊。(10)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3页。
换句话说,一种现象探索上的“无限性”要以“根基破裂”为代价,这就体现为一种“生物学的现象主义”,即用一种本来作为“现象科学”的生物演化序列来理解人,并且把人理解为这个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11)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5页。如此一来,通过这种把人类自身置于现象关联中的做法,人的生存位置就被牢固地设定在了“一种内在俗世的秩序中”,一种古典的实体性超越式人类生存定位也就由以丧失了。(12)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6页。诡异的地方在于,这种现象科学式的“人类学”行为本是为了去“理解万物的原理”,以及去“发现一个坚实的位置”,但它反倒恰恰通过把它的出发点——也就是人——内化于自身中,而使得自身成了一种失控的、仿佛无限的“欲望的煎熬”,进而把人也卷入到了这种失控的无限中。
如果对比谢林在“启示哲学”中的说法,就会发现沃格林与谢林在这种“现代性生存经验”上的高度重合,这种重合也能提供一种从沃格林所谓的实体性的生存哲学出发看到谢林区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之必要性的视角。在《启示哲学导论》中,谢林更为极端地抛出了沃格林所谓的“现象科学”对生存根基的摧毁性问题:在区分哲学和其他那些自己“迄今为止从事的科学”之际,谢林分别列举了数学、古典语文学、物理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先验哲学自身的“无根基性”,所有这些科学“都建立在那些没有在这些科学自身中得到正当性确证的前提预设上”。(13)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3页。有趣的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下在各门科学中逐渐占据支配性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大体也没有超出谢林这里列举的范围。而所有这些科学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如帕斯卡所说的,通过无限多的“现象”把“原理”延异到无限中,同时也能通过“严格”的细节探究而不断内部再生产,并以此来合法遗忘对于原理的探究。而谢林的自我回顾最终落脚在先验哲学上,而他对先验哲学的困惑,这可以看做对帕斯卡问题的重提:
就算人类不可否认地就是一切生成和创造活动的终点,并就此而言也是目标,我难道因此就有理由,把人类即刻也说成是最终目的吗?……(人类)意志的自由——我承认这是人类应有的,我也许还期待过能从它出发去解开巨大的谜团——本身成了一个新的,乃至最大的谜中之谜……恰恰是他,人类,把我推向那个最终的、充满绝望的问题:究竟为什么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14)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46-48页。
按照沃格林的看法,只有把人从某种“实在秩序”中“解放出来”,或者按谢林的说法,让人迷失自身的真正目的,以人类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先验哲学”才是可能的。(15)参见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27页;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47页。但这种先验哲学式“人类中心”的确立,和把人类放在一种“内在秩序”演化中的做法,除了能够不断加强整个作为“偶性的偶性”的“现象科学”的合法性和内在扩张之外,对于人类的自身理解并没有任何裨益。因为既然所有这些科学都没有在自身中为自己提供正当性确证,那么人实际上也就在把自身双重偶在化:一方面是从实在性的、排除了任何超越性的视角来理解人,同时以先验—内在的进路来强化人的这种自身理解;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通过整个现象研究的科学-社会机制使人把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建立在这种偶性的无限上。对此谢林总结道:
自从唯心主义(先验哲学)在我们这里出现以来,它所确立的整个方向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生活和公众看法里面,性格、美德、力量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与此相反,本来应当以那些东西为基础的所谓“人道”却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这个世界仅仅是一副肖像,甚至是肖像之肖像,无之无,阴影之阴影,而人也仅仅是一些肖像,仅仅是阴影的迷梦。(16)谢林:《世界时代》,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0-481页。
综合沃格林和谢林的说法,可以看到在这种先验哲学—人道主义通过对人生存的双重偶在化而导致的“现象科学”中,通过以“偶性”的东西取代“实体性的秩序”,人和事物都成了“阴影”,进而使得人也在这片阴影中成了“阴影之梦”,更使得一种以此出发的“国家学说”也同样成了“阴影之梦”。沃格林强调,谢林有意识注意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既非城邦也非帝国,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分化”的产物,即中世纪崩溃和启蒙-人道主义的后果。(17)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80页。所以理解这种“世俗国家”必须理解其世俗性,而要理解这种世俗性就需要在它与“精神实体间的关系中理解它”,进而“首要的政治问题不是国家的内在组织”,而是考察“分化出来的世俗化政治单位与精神实体间的关系”,如若不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放在现代世界的精神历史背景中,那“阴影之梦”的危机既无从察觉,也无从克服。(18)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82页,译文有改动。而既然“阴影之梦”如前文所言,是一种通过脱离“实体秩序”和超越性对人进行的重新定位——或者按沃格林的说法,是通过“大写理性”来否认“精神的实在性”,进而把“合理性”仅仅限制在世俗的内在性(19)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38页。中,——那么一种直面“首要政治问题”、能够考察国家之当下生存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是“绕行的”。而这种“政治哲学”如果得以实行,需要两重维度:1.重新恢复一种对精神实体的知识。2.在这种知识中理解现代国家的历史处境。
二、谢林对精神实体知识重唤与体系建构
沃格林的诊断至少提示了我们一点:尽管在德国唯心论内部“体系”是一个主导词语,但各体系之间关切的那种“精神实在性”,或者说各体系背后真正的、为其提供一种基本生存经验的“历史性要素”是不同的。如果说谢林首先要与之抗争的是先验-人道主义,那就可以理解,何以从他所谓的“早期哲学”到“晚期哲学”,主要的争辩对手是费希特而非黑格尔,而他对费希特最大的指控就在于,费希特彻底摧毁了自然的实存。现在的问题是,自然的实存对于一种精神实体的知识来说为什么是必要的?
“自然”概念在谢林哲学中是多义的,它首先指与先验哲学对立的“自然哲学”中的自然,即一种自生的、具有自身性和自身规定性的自然。其次指构成神性基础的“野蛮本原”,一个“应当被征服,但不应当被消灭的本原”,这个本原构成了“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的基础”,而种种当代现象“都是(先验哲学)那个方向的必然后果”。(20)谢林:《世界时代》,第481页。最后,“自然”也指所有“潜能阶次”在神话中的运作方式,以此区分于通过超越性自由的参与而出现的“启示宗教”。(21)F.W.J Schelling, Sämmtliche Werke.14 Bände=SW,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Cotta, 1856-1861, XIII, S. 182.因此总的来看,在谢林的整个哲学演进中,“自然”既是“先验”的对立者,也作为“野蛮本原”是某种生存性的基础。从这种意义的“自然”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自然在谢林总体体系建构中的意义:“人类自我”的他者,为人类重新进行超越性自我定位提供基础。第一,就体系建构上来看,自然哲学作为与先验哲学对立的一极,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先验-人类哲学作为“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先验哲学所引为体系本原的“自我意识”并非费希特所设想的绝对无条件者,尽管自我意识是对我们而言最具自明性和切近的东西,但它的源初性并不由其自明性提供,所以“这个所谓的直接确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不可理解的”。(22)谢林:《近代哲学史》,第7页。荷尔德林在他著名的《判断与存在》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只要“自我”能被道出,就意味着有某种超出自我意识结构的“他者”存在。(23)参见佘诗琴:《荷尔德林的〈判断与存在〉与早期谢林》,《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换句话说,正因为“自我意识”的实存前提并不在它作为“我思”的运作范围内,所以在对费希特的批判中,谢林同时也揭示出了所谓“阴影之梦”的前提,即它建立在把某种源初与“自我意识”对立的东西,也就是自然排除在外的前提上。因此,自然哲学不仅意味着在体系建构整体性上的补充,更意味着一种对远比笛卡尔开启的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先验哲学更深刻的“生存经验”。在出版了自然哲学相关论述之后,谢林就在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对先验哲学的概念进行了一种“版本更新”。一种是笛卡尔-费希特传统的“普通意识”的先验哲学,在这里,“我在”和“我外有物”这两个其实一体两面的基本命题,构成了使这个版本的先验哲学得以可能的“基本成见”,而当这种先验哲学极端化为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的时候,“我在”的条件,即“我外有物”就被完全消融了。(24)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页。另一种更高的“先验哲学”则是那种只有分别在知识、实践还是审美中,“在自己的本原内(在自我中)证明(自我与自然)同一性”才会完成的“先验哲学”。(2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15页。因此后一种先验哲学是一种“体系中”的先验哲学,而非纯然的、去自然化的先验哲学。而当更高的先验哲学在自我中证明的并非“自我是自我”,而是“自我与自然的同一性”之际,先验哲学也就超出了自身。所以从这一点可见,谢林以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为两端,但又超出两者之上的“同一性体系”所囊括的那种“自然”并非抽象的、主观化了的自然,而是一种双重化的自然:1.它作为先验性-主体的对立物,通过与先验哲学在本原上的对立,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先验哲学能以通过排除自然而得到“自我”的方式确立,同时也使它只能因而停留在自己的片面性中;2.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作为一般先验哲学的对立面,所以在“体系性”的先验哲学中,它能让“升级版”的先验哲学明确自身的任务并非确证“自我”,而是超出自身,去证明自身与作为自身他者的自然间的同一性,而正是这一点,使得自然得以成为让自我—人类得进入某种精神的实在性知识的基础。
作为这种基础的,就是自然的双重含义,即“野蛮的本原”。就实质上看,自然在生存上作为“野蛮的本原”,和它在体系结构中作为呈现“绝对同一性”、并与先验哲学对立的另外一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自然”在谢林的整个体系中除了作为“自然哲学”的相关项来实现体系本身之外,同时也具有一种理解人类生存的旨趣,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谢林从“绝对同一性”哲学向所谓“晚期哲学”的过渡是顺理成章的,其中外在呈现出来的“断裂”或者“转向”仅仅是一种论说策略上的迂回,而非体系本身的彻底改变。同时更要注意到,正因为如若缺乏“自然哲学”则体系不可能完满,所以“自然哲学”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重唤“精神实体知识”的可能。尽管在谢林哲学的演进中,对这种知识的获得分别有“去潜能阶次化”“理智直观”“绽出”等等不同说法,但总的来看,对于通过前述的双重化“自然”而看到某种“精神实体”这一点的核心,仍然在于看到整个先验哲学路径的片面性:
我们的自我意识绝不是那个经历过一切阶段的自然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恰恰只不过是我们的,进而绝不在自身中包含关于一切生成过程的科学……如果有某个目的在这个生成过程中被达成,那它也只是经由人类,而非为了人类被达成的。人类的意识不同于自然的意识……人类已经脱离了自然……注定在自身中扬弃自然,超出自然。(26)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46页。
因此,自然始终意味着人类走出自身、走出“我们的意识”的必要性,而通过这种走出,人类会重新意识到自己只是某个“生成过程”所“经由”的一个点。但与此同时,人类意识与自然的生成意识毕竟有所不同,人类已经“脱离”并且要“扬弃”自然。“扬弃”这个词已经明示,人对自然的“脱离”绝非一般意义上先验哲学的那种作为与自然对立的一极而把自然排除在外式的“脱离”,相反,这种脱离的实质在于“扬弃”,也就是在一个连续的生成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上出现了某种能够使人类获得不同于自然存在方式的“法则”。换句话说,“自然”在更高的意义上不仅意味着人类走出“自我意识”的片面性,同时也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到自身的“精神位置”,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然才作为“野蛮本原”是应被克服的东西。
三、作为“实存之根据”的双重化自然
对于这种具有超出先验哲学,且同时作为人类在真实精神秩序中可以对之进行“扬弃”、进而作为人在这种秩序中得以实现某种目的之基础的双重化自然,谢林最为清楚地阐述在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以下简称“《论自由》”)中。如果从上文“自然”概念在谢林体系建构中的双重化入手,就可以清楚看到在这个文本里,自然概念完全对应于“体系要素”和“生存-精神实体根基”这两个一体两面的含义。在开篇的序言中,谢林就强调,精神与自然间的对立“已经被连根拔除了”,而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更高层次的对立”,即“必然和自由的对立”,而这个对立是“哲学最内在的中心点”。(27)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精神与自然的对立可以理解为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对立,当它们已经被揭示为具有更高的同一性之际,“自由和必然的对立”也就出现了。从上文可知,双重化的自然既代表着一种整体性的生成过程在人类出现之前的阶段,也代表着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因此,“必然和自由”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作为不可缺失的基础的自然的必然性和人类能够“脱离”和“扬弃”自然的自由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之所以是“哲学的中心点”,恰恰就在于如沃格林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要考察人类之所以会进入当下处境的生存前提,也要考察人类得以进入更高精神秩序的可能性。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谢林在这个文本里对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近代欧洲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无视自然界的存在,从而缺乏一个活生生的根据”,(28)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31页。但与此同时,“直到唯心主义作出揭示之前,近代的所有体系……都缺失真正的‘自由’概念”。(29)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8页。也就是说,整个近代哲学对自由的理解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自由理解,因为人类的自由需要自然作为其基础,而非仅仅“意味着以智性本原统治欲望”,(30)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8页。这种传统自由观只可能在一个精神实体临在的世界理解中生效。而现代所开启的先验-人类哲学模式,已经让“自由”成了人自身理解和世界理解的唯一出发点。而这一点是唯心主义揭示出来的,在谢林的语境里,“唯心主义”通常指的费希特哲学,而它所揭示的恰恰在于,人现在不再通过某种更高的精神实体和秩序来理解自己,而是仅仅从自身出发理解自己,人的自由成了本原性的东西。但实质上来看,不管是“缺乏根据”还是“做出揭示”,实际上都意味着人“脱离了”自然,只有自然作为根据已然缺失,唯心主义才可能对“现代”的实情进行揭示,因此“唯心主义概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更高层次的哲学,尤其是对于一种更高层次的实在论而言,都是一个真正的洗礼”。(31)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26页。也就是说,唯心主义一方面是“缺乏根基”从而导致遗忘根基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人类已然以先验-人类哲学的方式在理解自身之际,一种更高的“实在论”,即能够把自然自身纳入这种理解的实在论就显得急迫了,所以谢林强调他的努力在于“让实在论和唯心主义达到相互融贯”。(32)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24页。而这种融贯也如前文所说,在于以让人走出“自我意识”的方式,回归“唯心主义”能够让人以自身的自由为出发点的那种精神秩序中,而这种精神秩序也正由于唯心主义的产生被遮蔽。
也正由于唯心主义的“缺乏根基”,它“一方面仅仅给出了最一般的自由概念,另一方面仅仅给出一个形式上的自由概念”,因而“不足以揭示出人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属差,亦即人类自由的特殊规定性”。(33)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25-26页。对应于沃格林的诊断,可以认为,这其实就是在说,正因为整个先验哲学路径已经遮蔽了自身的根基和前提,自由才仅仅成了“形式上的”和“一般性的”,并且反过来以人类的这种形式性的自由规定其他一切,但问题在于看到人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本真差异,即人类自由的“特殊规定性”。也就是说,当谢林随即把人类自由“实在的、活生生的概念”规定为“向善和从恶的能力”时,(34)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27页。谢林并没有推翻整个先验哲学路径把人类自由规定为“自我规定”的传统。相反,谢林在这里只是要追问,既然“自然”的实在性已经使人类不得不走出自身意识,进入一种更高的精神秩序,那么在这种精神秩序的视野下,“自律”作为“自我规定”是如何可能的?因为“自我规定”绝不仅仅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自律,同时更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扬弃”和“脱离”的能力,因此,只有把自律式的自由概念转换为“向善和从恶的能力”,才能在同时把握自律这种现代存在方式之根基的情况下,理解自律式自由在更高视野中的实情。
在《论自由》中,谢林对此给出的阐述方案是对存在整体中“实存的根据”与“实存者”的区分,即“神中的自然”和“实存着的神”的区分,(35)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33页。前者是一种遮蔽性、封闭性的趋向,后者则是一种开启性的趋向,因而也被“拟人地”称作“自我主义(Egoismus)”和“爱”。(36)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32页。总的来看,这一区分一方面为整个体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生成过程”的结构,另一方面,也通过把自然理解为“如其所是”的神存在的根据,使得被近代哲学的先验-唯理性主义排除在外的“野蛮本原”成了理解神性的不可或缺环节。但着眼于对人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在于,谢林把人类理解为自然和神性之间的中介,即从自然中被创造出来的精神:
人来自根据(是一个受造物)……同时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即精神,在人里面冉冉升起……自主性本身就是精神,换言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特殊的本质,就是精神,而这个联合恰恰构成了人格性。自主性是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它就从一个受造物提升为一个超越于受造物的东西;它发现自己具有完全自由的意志……超越整个自然界,位于整个自然界之外。(37)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41-42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谢林在“更高精神秩序”和为表达这种秩序而构造的体系中对人类的核心规定。在《论自由》之后,谢林从“世界时代”开始的整个哲学努力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为这种规定不断调整叙事方案。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让现代精神“回忆”起自身真正秩序位置的叙事方案,让谢林之后的哲学显得颇为另类。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理解双重化的自然在人的规定中的核心意义:一方面,双重化的自然即是人类得以开启“现代”叙事的基础,也是克服这种叙事的实在性力量。正因为人类能被提升为精神,他才成了一个“体系的开放点”,(38)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46页。也就是说,本应“经由”人类完成的整体目的,有可能落入由于人类的自由而不断延异的危险,这就使得体系在叙事整体上具有完满性,但也能通过这种完满性始终对整个“现代”叙事构成批判并理解其无目的性,即沃格林所谓的现象的无限性。
四、人类之恶与阴影之国
作为“体系的开放点”,谢林把作为精神的人类能够无视或者说扭曲真正精神秩序的能力理解为“恶”,这并非道德上的恶,而是生存上的恶。按照谢林的术语,作为根据的自然是相对于更高秩序而言的“非存在者”,而神则是“绝对存在者”,但人作为精神,则是出自非存在者的存在者,因而也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由,成为“存在着的非存在者”,而“恶不是别的,恰恰是一种相对的‘非存在者’,一种作为存在者而崛起,随之驱逐了真正的存在者的东西”。(39)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60页。也就是说,人之“恶”恰恰在于把本该在更高秩序中作为基础的“非存在者”提升到“存在者”的层次上来,但被提升的东西并非自然本身,而是“自然里面已经开始的演进过程在人里面重新从头开始”,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人作为精神,作为一个居于更高秩序的本质,仍然被回置到……第一个潜能阶次的层次”。(40)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60页。按谢林的描述,自然中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从狂暴走向温和,从“野蛮”走向精神的过程,只有如此,人才可能在作为自然产物的同时也是自然与神之间的中介。但现在的问题是,人的这种“回置”跟整个先验-人类哲学叙事有何关系?
如前文所述,这种“现代”叙事的核心在于遗忘自然的根基作用,以及遗忘人在更高精神秩序中的使命,这其实是一体两面。一方面,遗忘自然的根基作用并不意味着真正“取消”了自然作为根基的实在性,先验-人类哲学叙事的根本在于把自然从存在整体的叙事中排除在外,使之成为对立于人类的一极。因此,在这种排除中,自然也就始终作为一种“野蛮本原”对立于人,这种对立并非现在那种人与所谓“自然界”的对立,而是更多体现为一种现代人类学叙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体现为法国大革命式的癫狂,以及对于诸多精神症候的“心理学化”,以及沃格林所谓的以数学方式自以为征服自然之际反而落入的无限性等等。(41)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37页。而另一方面,这种“自然”的癫狂构成了人类作为精神的基础,而人类的使命则在于使之保持为“非存在者”,进而通过这种保持进入更高的秩序中。归根到底,通过先验-人类哲学,人仿佛一块白板一般的重新开始的整个“现代转向”,实际上就是在遗忘整个精神历史的进程,而这一历程则被谢林刻画为“自然”在其中起支配性作用的“神话时代”。(42)谢林说:“神话进程跟疾病一样,是一种自然进程,由此,在这一进程中自行产生的宗教,亦即在神话中自行产生的宗教是一种以自然的方式自行产生性的宗教”。引自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页。因此,通过排除自然而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实际上就是“观念的人”和这种意义上的“前史的人”,即“实在的人”间的对立,进而根本上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对立,即人与自身历史性生存的对立,正如谢林在“启示哲学”中一再提醒的:
我们并不处在一个抽象或者普遍的世界中,当我们仅仅守着事物最普遍的特质不放,而不去探入它们的现实关系中时,我们就会乐于装出世界就是普遍的样子。我们也不能取消支撑着当下的无限过去。在世界上,并非一切都是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直截简单地关联在一起的。(43)谢林:《启示哲学(下卷)》,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96页。
在谢林看来,现代国家就是这种“取消”的产物,它以一种与先验-人类哲学相对应的世俗-内在性方案被构造,因此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统一体”,一种“人类无奈接受下来的统一体”,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是“人类头上的诅咒的一个后果”。(44)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63页。现代国家的“诅咒”就在于人类以自身为统一体之本原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对手并非“非人道主义”,而是作为人类真正历史性实存前提的实在性“野蛮本原”。因此国家的“自然性”就体现为,现代国家的主导词并非“精神”,而是“自然的权力”,也就是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潜能阶次间力量的角逐。在谢林看来,国家如果是“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条件”,要么结局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进而取消国家,要么是费希特式的“封闭商业国”,进而取消自由。(45)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164页。国家绝非“行走在地上的神”,因为神绝不行走在大地上。真正的“人类统一体”绝非现代国家,也绝非先验-人类哲学开启的“世界公民”理念,而是某种值得期待的东西。人类的自由必须在与作为其根基的自然之必然中,才能在一种精神秩序的历史性人类生存叙事中得到理解,因此,整个“现代”所产生的“现象主义”—“现代国家”总体机制,绝非真正的自由得以实行的场所。因此,现代人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始终是实在性的精神秩序的缺失所投下的“阴影”,在阴影中既没有真正意义上整全的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但谢林也并不认为,通过简单地回归教会,或某种现成的“理想国”就能解决这种生存-政治危机,更不认为新教改革催生出的“现代国家”就带来了真正的自由,(46)谢林说:“新教应该认识到,自己仅仅是一种过渡和中介活动,它仅仅关联于某种还要更高、它自己必须对之进行中介的东西才是某种东西。”引自谢林:《启示哲学(下卷)》,第384页。也绝非要预言约阿希姆式的“第三基督教”的来临。(47)谢林说:“上面提过的修道院长约阿希姆,就是这种关于来临中的永恒福音学说的支持者中的代表人物,而且他或许还对三一性学说做了下述发挥,即他把三重人格设想为仿佛三重前后相继的时间级数或者说潜能阶次,这就为他落下了被指控为‘三神论’的口实……对我们来说,三重时间的次第相继才是更具宏阔且普遍意义的要点”。引自谢林:《启示哲学(下卷)》,第86页。而这也是沃格林推崇谢林的地方:在精神的历史上,最高的政治哲学成就在于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在一种总体叙事中把人类的生存危机经验转化为基本哲学符号,进而始终让这些危机经验得到保留,使之能够汇入精神的历史中。(48)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7卷,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