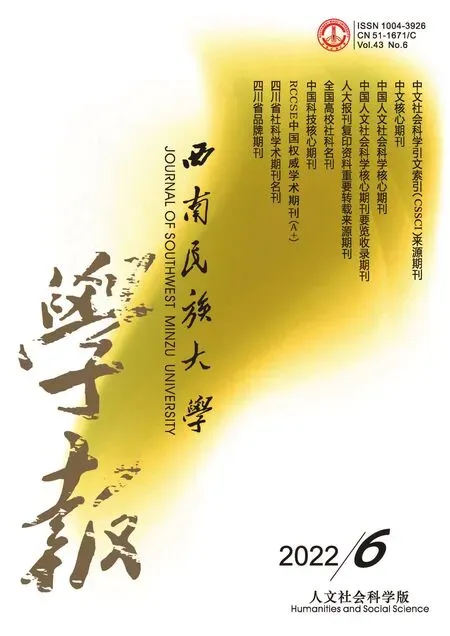“油印”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构建
汤巧巧
[提要]如果从印刷实践层面来看,“油印”之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结构性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表渴望与发表空间逼仄的矛盾中,“油印”释放了其中被压抑的创作能量,并真正锲入到一种新的诗歌空间的创造中。本文从油印诗集、诗刊的研究出发,在诗歌新人推广、“诗江湖”构建和诗学品格等层面,讨论了“油印”与新诗场域构建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经由它形成的诗歌实践与创作的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诗歌的“江湖”。
在关于1980年代诗歌概念的描述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极富新意的名词,比如“民间诗歌”“诗歌民刊”“先锋诗歌”“诗江湖”等等。多年来,经由学者和诗人们的命名与阐释,这些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成为讨论此时期新诗场域的基础。即使在某些方面的讨论尚未达成共识,也只是概念纵深所必需的思境,并不影响基础的逐步夯实。因此,我们也需要不时检视它们,在历史的叙述中寻找其发生源。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与这几个词频繁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个并不新的名词——“油印”。
如果细读1980年代诗歌的诸多相关叙述,其中频繁出现的“油印”“油印诗集”甚至“油墨香”等等词语,带来了特有的1980年代诗歌的气息。它不再单纯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被触摸、可被感知甚至可被操作的实体。当我们回溯1980年代诗歌的盛况时,除了一个个流派和诗人的名字,最具有历史在场感的还是那些装帧简单、字体各异、黑白分明、没有出版社和ISBN号的“油印”诗集和刊物。过去,我们将这些刊物命名为“诗歌民刊”,多从“民间”“先锋”的视角去阐释它们,很少从与之有深刻关联的印刷实践层面来理解它们。如果细致地品读,“油印诗集”“油印诗刊”与同时期工业印刷机和正规出版物相比,无疑是某种难看的“刺点”。刺点居于晦暗地带,如罗兰·巴特所言,恰好位于可被集中分享的编码和总体性描述之外。它们仿佛光鲜的“展面”上游离的、断裂的“暗钝”。[1](P.151-152)罗兰·巴特使用这些词语是对摄影的讨论,他发现在光鲜的摄影海报或者作品中,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反而是某些不起眼的,与整个画面的稳定结构和意义层面断裂的“暗钝”。如果说“油印”及其相关作品也是正式出版物之外的“暗钝”,而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景观”,那么,我们如何从中来理解1980年代新诗场域的生成呢?
一、“油印”与诗歌新人的推广
1980年代,在中国诗歌场域的上空,飘荡着一阵阵清新的油墨芳香。油墨香气的背后,诞生了一本又一本“油印”诗刊、诗集,部分年轻未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从“油印”中走出,突破精美的主流诗歌印刷品的包围,成为当代诗歌场域的新兴力量。《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主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推出诗歌流派60多家,诗人107个,大多自“油印”诗集和刊物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主流印刷品和社会的关注,在诗歌场域中获得了声名。这段历史,是自油印诗刊《今天》在1970年代末成功后,一个“油印机主导”的诗歌场域逐渐构建的过程;也是在印刷出版大一统的格局中,部分诗人通过“油印”即“出版”的方式,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的过程。如洪子诚所说“‘民办’的诗刊、诗报,在支持诗歌探索、发表新人的作品上,是‘正式’出版刊物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展现最有活力的诗歌实绩的处所。”[2](P.251)
新中国成立以降,诗歌场域长期处于一种稳定、单一的结构之中。这个结构有个习惯的称谓:“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诗歌场域的人事、内容和美学建构等都必须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一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伊始才有所松动。1980年代,经由文革时期停刊,又分别在1976年和1978年复刊的《诗刊》《星星》等经典官刊重新开始建构场域,在诗歌人事、内容和美学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然而,长期形成的一体化结构的惯性依然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而诗歌新人们正在成长,他们被压抑的写作、交流和发表的强大愿望,在狭窄的官刊通道里仍然得不到释放,作为补充,具有边缘性但天地更广阔的“油印”刊物和诗集就成为重要的通道,在时代的缝隙中生长并蔚然成风。当然,当代“油印”刊物、诗集的历史并非从1980年代伊始,文学、诗歌的“油印史”在建国到文革时期一直存在,它们是1980年代“油印”精神的源头,必然是不能被遗忘的。只是,真正将“油印”锲入进诗歌场域构建的时期是1980年代。
诗歌场域变化的关键首先是诗人结构性组成的变化。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时期,据学者陈宗俊的研究,此时期的经典诗人是来自“解放区”的诗人田间、郭小川、李季、闻捷、阮章竞、严辰、方纪等;来自“国统区”的诗人郭沫若、臧克家、袁水拍、徐迟、沙鸥、冯至、田汉、力扬等;青年诗人顾工、未央、严阵、傅仇、梁上泉、李冰、李瑛等;当然还有王老九、李学鳌等经典化的“工农兵诗人”和毛依罕.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等少数民族诗人。[3]这些诗人的共同特征就是从“国家计划”的政治体系中、从具有严密规则和等级的出版制度中走出的新中国的歌唱者、合作者,并且,这个诗人队伍是不断在政治标准中增删发展,形成长期以来较为稳定的构成。如若被取消资格,比如艾青,在1957年以前都是最有资格的诗人,但1957年下半年被打成“右派”后,各种诗歌选本包括他的个人诗集都被取消,这意味着他的诗人身份被国家取消。但是,这个诗人结构到了文革时期也全部被摧毁,在此就不赘述。
新时期伊始的“今天派”,从油印刊物《今天》进入《诗刊》的视野①,再经由《朦胧诗选》②、《新诗潮诗集》③《五人诗选》④等非正式和正式出版物,走出了新时期诗歌最早被经典化的一批“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等。这部分诗人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三十年单一的诗人构成,在诗人身份、诗歌观念和创作等方面带来了“令人气闷的朦胧”[4],也带来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的新“一代人”[5]。
“朦胧诗”后的更年轻的一代沿着油印本《今天》的足迹,开始独立创办诗歌刊物。据统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6](P.560)而据民刊收藏家姜红伟说:“1980年代中国民间诗歌报刊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大约有2000余家,参加创办民间诗歌报刊的诗歌爱好者大约有10000人左右。”[7]这些数据记录了1980年代活跃的民间诗歌报刊的大致数量和印制方式,油印(非正式打印)占了比较大的比例。从这些数据中走出了1980年代诗歌场域的新一代诗人,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命名就是“第三代诗人”。
需要注意的是,学界对于“第三代诗人”的界定一直有分歧。有广义的即按照诗歌代际来划分,“第三代诗人”就是“朦胧诗”后的新一代诗人。也有基于风格相近的狭义界定。学者魏巍等对此命名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辨析[8],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由于本部分主要谈代际意义的新人构建,所以此处依据“第三代诗人”的广义界定。
“第三代诗人”是1980年代诗歌场域的新兴力量,虽然它最后呈现出一场群体运动的整体性,但它是经过一个个流派刊物、自印诗集、诗歌选本和一系列诗歌事件等等分散的方式逐渐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最基础的即是创办流派刊物和编印诗歌选本。如学者罗执廷所言:“‘第三代诗’一开始大都不是出现在正规刊物上,而是自发地汇聚于各种民间诗刊,如四川的《大学生诗报》《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等,然后才引起诗歌界注意的。”[9]
胡亮在《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中,对“第三代人”“第三代诗会”“第三代人诗会”“第三代诗和第三代诗人”这些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从梳理中可以看出,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人”的确立,是从自印刊物《普通人》(1980油印,西师大中文系78级学生创办)、《同代人》(1981油印,西师大中文系79级学生创办)以及《第三代人宣言(草稿)》(郭绍才手书,1982年9月8日黛小冰日记手抄记载)到《第三代人》诗刊(油印1983;赵野、北望编印),再到《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铅印1985;万夏、杨黎、赵野编印)、《第三代人诗报》(铅印1985)、《新诗潮诗集》(老木主编;铅印1985)、香港刊物《大拇指》的“四川诗人专辑”(廖希和香港诗人叶辉编;1986)至《深圳青年报》“第三代诗专版”(1986年9月12日)以及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现代主义诗群大展”(1986年10月21-24日)集体出场,身份实现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迁徙,从“油印”等非正式出版到官方正式出版的转变,乃至1986年后各种民间、官方、学界的刊物、选本最终共同完成“第三代诗人”的文学史定位。[10]比如《诗刊》1986年11月发表了“第三代诗人”韩东、于坚、翟永明等的作品;《关东文学》从1986年4期开始推出“第三代诗会”栏目,1987年6期又推出“第三代诗专辑”,1988年4期推出“第三代诗专号”,由少渐多,由个别至群体,成为一代“油印”诗人们自我推广、构建的重要推力。当然,在胡亮梳理的谱系中,尚未将其时的“油印”流派刊物包括其中,在1986年推出的“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的各个流派,基本都是建立在“油印”诗集和刊物的基础之上的。
上述从整体的角度呈现了在”油印”中建构的“第三代诗人”群体。不管最后是被正式刊物经典化了抑或是参与其中的新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不再是政治化的结构符号,而是经由“油印”的自我推广,逐渐成为1980年代诗歌场域的新生力量。
如果从个体来看,这些诗歌新人的自我推广也无不与“油印”相关。比如贺嘉钰在论文《自“油印”走出——翟永明组诗〈女人〉发表考叙》中,详细考察了当代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从“油印”出发的经典化过程。她指出“诗作见诸油印诗集、非正式刊物以至公开发表、正式出版的经过勾勒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诗人诗作被铭记的一种轨迹。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获得正式出版机会前,自印个人诗集是青年诗人们‘波西米亚’式写作与生活状态的重要表达之一。《女人》经典化的路径作为一个集体经验的样本,既较为特殊,又清晰地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青年诗人如何从幽暗处走到聚光灯下。”[11]
与其时声势浩大的大学生诗人相比,诗人杨黎高中毕业,因为喜欢写诗和过自由的生活,辞去了银行工作。他油印《鼠疫》等刊物发表自己和朋友的诗歌,后经由《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和《非非》作为头条诗人推出,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极具实验性的诗歌探索如果不是经由“油印”,几乎不可能得到认可和正式发表的机会。我们以他的《怪客》为例,分析这首诗最终确立的过程。
杨黎自述了一段他在“油印”刊物上发表《怪客》,从不被接受到籍此获得声名的过程。1983年秋天,他写作了《怪客》《中午》等诗,首发在他和两个朋友油印的刊物《然而》上。这首诗的叙事写法,戏剧场景等与当时大多数诗人的写法完全不同,“我以为他们会为我的诗感到惊奇,但实际上不是,成都的诗人们当时倾向于史诗和文化诗,对以《怪客》为代表的这类先锋的叙事诗普遍带有抵触和批判态度,比如骆耕野就批评说这是‘假叙事’”⑤。杨黎因诗歌得不到承认一度非常沮丧,这一点在周伦佑回忆《非非》杂志创办的历史中得到印证:“他(指杨黎)当时已写了一些诗,正处于不被接受的苦闷中,我读了他通过李娟转给我的和随后寄给我的一些诗稿后回信告诉他‘你虽然暂时不被人理解,但只要坚持写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诗坛会接纳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的’”。[12]
然而,同样从“油印”诗歌起步的“莽汉诗人”万夏认为《怪客》这类诗歌和他们(指“莽汉”)的创作一样,非常先锋。1985年1月,在万夏、杨黎、赵野等共同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杨黎的《怪客》作为“第三代人诗会”栏目的第一首发出,因其与以北岛为代表的第二代(该刊第一个栏目“结局或开始”)以及以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海子等为代表的“文化史诗”风格(该刊第二个栏目”亚洲铜”)的截然不同,成为代际划分的标志性符号之一,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当年尚不认识杨黎的何小竹说:“我在写给万夏的信里说,《怪客》和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是这本刊物中我最喜欢的。”⑥此话笔者也从对万夏和何小竹的采访中得到确认。何小竹还认为,这首《怪客》有受罗布.格里耶小说叙述客观化的启发,但用于诗歌分行叙述,绝对是创举,超越受影响的范畴,这也是“当时那本杂志上杨黎的诗歌让我眼睛一亮的原因”。⑦
经由“油印”的推广,1988年,《关东文学》第4期“中国第三代诗专号”上,正式发表了杨黎的《怪客》以及《后怪客》等诗作,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1989年《作家》杂志又再次发表了《怪客》。从1983至1989年,这首诗作为“第三代诗”的代表作品之一,最终确立并得到巩固。
另有一些诗人在“油印”之前就已经在正式期刊中发表过诗歌,比如韩东的《我是山》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7期),《山民》发表于《青春》(1982年第8期);于坚于1980年代初期,就在当时的大学生诗歌“圣地”《飞天》杂志发表诗歌并获得过“飞天大学生诗歌奖”,但他们作为有代际意义的“第三代诗人”代表的身份和作品,却是自“油印”流派刊物的创办、传播,然后再经由一个个选本反复确认的。韩东被视为具有划代意义的诗作《有关大雁塔》,最早出现于他在西安自办的油印刊物《老家》中。该版本一共两节,第二节延续了朦胧诗评判历史和追求“光荣”的英雄主义风格,仍然具有精神上的审视与内涵上的强调,“可是/大雁塔在想些什么/他在想,所有的好汉都在那年里死绝了/……最后,他们到他这里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13]如刘春所言:“特别是最后两句:‘这些猥琐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一不留神就呈现出英雄主义的自矜。”[14]这个版本充分显示了一代新人与朦胧诗的“血缘”关系。但是,到了《他们》时代,这一代人已经有了和朦胧诗“断裂”的雄心。发表于《他们》第一期(1985年3月7日)的《有关大雁塔》,删掉了第二节,将第一节内容分成两节编排成一首完整的诗,这就是现在的23行版本,它标示着“断代意识”和“新的写作”的觉醒。同样,在《他们》之前,于坚于1983年发表在《飞天》杂志的《圭山组曲》是关于云南高原土著生活的组诗,他的《罗家生》《尚义街6号》还要等到“油印”《他们》第二辑(1985年9月)的到来。而《有关大雁塔》《尚义街6号》后来在《诗刊》中正式发表,实现了两首诗歌的经典化。
从以上论述可见,“油印”是诗歌新人们的出发点,是在有限的发表、传播资源中,写作者的一种自我推广和身份确认。在此基础上,诗歌新人们也通过在校园售卖“油印”刊物或诗集、邮寄给朋友和正式刊物编辑部等方式,实现和外界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增强自我的信心和知名度。晓音谈到当年曾经在四川大学食堂门口摆摊售卖《女子诗报》,后又送了一些给川大的诗人朋友。在西昌,《凉山文学》的诗歌编辑胥勋和先生在向外寄《凉山文学》时,“在每个邮件中夹寄了一份《女子诗报》”[15](P.324)。
事实上,在“油印”刊物中获得推介和认同的新人,往往会成为正式出版物关注的对象。“油印”与正式出版物一直处于互动之中,前者是推介新人,进而经由后者经典化。比如诗歌新人们从“油印”再到登上《诗刊》《星星》《关东文学》等正式出版物,比如《诗刊》编辑唐晓渡编选出版新人们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比如《凉山文学》“夹带”《女子诗报》等等,证明了“油印”在其时并非完全是一种民间的孤立行为,诗歌新人们也并非如想象的与“官刊”势不两立,它是在渐次开放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中,经由时代的缝隙深入诗歌场域结构调整的一部分,也是1980年代文学结构调整的动因和部分结果。晓音说,文革结束后,白航从西昌的“五七干校”回去后,“在他主编的《星星》诗刊上用较大的版面刊发西昌诗人的诗歌。……可以说,他们对西昌诗人诗歌的认可和推崇也是西昌诗人创办民间诗歌刊物自信的重要来源。”[15](P.324)
二、“油印”与1980年代“诗江湖”的构建
张清华在《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一书中,提出“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学”的范畴;[16](P.9)何平进一步提出,“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学”只有在与“国家计划文学”的“一”与“多”的张力中显现意义,“正是客观上存在的‘国家计划文学体制’,以及同样客观存在的对‘国家计划文学’体制僭越的‘弥漫的新空间’,当代诗歌地理美学才有了讨论的前提和意义。”[17]他进一步说,这个提法其实有一个更容易被参与其中的诗人接受的词——“江湖”。
“江湖”一词本就有从地理到文化的概念演变,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有详细的考察,他提出:“‘江湖’当然不只是现实世界中江湖的简单摹写。经过无数说书人与小说家的渲染、表现,‘江湖’已逐渐走出历史,演变成为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18](P.116)本部分讨论的“诗江湖”即是指这个具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它至少包含三重含义,其一是与体制内(官方)诗歌空间相对的边缘诗歌空间,如“江湖”对“庙堂”;其二是这个边缘空间里散落的各个诗歌派别和群落,由此形成与“武林世界”相似的群落关系:即相互关联又彼此斗争;其三象征着“相忘于江湖”的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19](P.30-34)
当然,这是在较宽泛的范围下对“诗江湖”的界定。当代诗歌的“诗江湖”现象从1980年代兴起,发展到今天,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是“油印”的“诗江湖”;1990年代以降的二十年是“网站”的“诗江湖”;近十年是“自媒体”的“诗江湖”。后两者的“江湖”实际已经淡化了与“庙堂”对立的张力,基于网络技术基础上的优势和消费市场发展的语境,它甚至成为主流,实现了当代诗歌场域江湖空间的翻转——这和1980年代“油印”的“诗江湖”的性质已经有了分野。油印机的笨重和较低的效率,决定了1980年代的“诗江湖”,真正体现出作为边缘空间,是如何被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历史过程。
首先,与按照组织关系建构起来的官方文学主体不同,“油印”时期“诗江湖”群落的主体是由熟人发展而来的“诗歌游民”,“熟人文化”是江湖的基础。由于其时信息网络、交通尚不发达,这里的“熟人”主要是同学、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之间以及由此发散开来的交叉关系,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李亚伟在叙述莽汉诗歌群落如何形成时有一段话,具有代表性:“‘莽汉’这一概念是1984年1月由万夏和胡冬在成都提出的,主要人物有万夏、马松、胡冬、二毛、梁乐、胡玉、蔡利华和我。其中我和二毛、梁乐是中学同学,万夏和胡冬也是在中学就混在一起的,而我和马松、万夏、胡玉又是大学同学,在大学是一个诗歌团伙,梁乐在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二毛是涪陵师专数学专业的,胡冬在四川大学又和之前发起‘第三代人’的赵野、唐亚平、胡晓波、阿野等是一个诗歌团伙。也就是说,‘莽汉’是当时一个典型的校园诗社互相勾结的结果。”[20]这段话中“诗歌团伙”“混在一起”等表述就具有明显的江湖气,而他勾勒的这个作者群的关系,也可见其时这个熟人关系中的主体是四川的校园诗人。我们从于坚的那首著名的《尚义街6号》,也可以看见1980年代以同学为主体的云南文学青年群像,更别提其时名震一时的重庆“大学生诗派”。
“非非”的组成是另一种熟人关系。“非非”两名主将周伦佑和蓝马(王世刚)都是西昌人,早在1970年代经由周伦佑的哥哥周伦佐介绍相识。据周伦佑妻子撰文回忆:“他(王世刚)一直称呼伦佑为‘三哥’(伦佐为‘二哥’),经常在他们家随便的进出,他们基本上是把他当作自家兄弟看待,伦佑的母亲也把他当成小儿子,有时家里吃点好东西还要给他留一份。”[21]这段叙述不是在讲人情关系,而是直观地反映出在“非非”成立之前,两名主将就有了超乎寻常的“兄弟”情谊,这种“兄弟情谊”在江湖社会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建基在地域之上,为了生存发展而形成的“类血缘”关系。王学泰先生在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到失去土地或者游离于土地之外的“游民”是“江湖”社会的基础。这些“游民”为了生存发展,必然最后要以结成“异姓兄弟”的形式形成群体,“异姓兄弟”就是模仿家族的类血缘关系。[22]
1980年代,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中心,诗歌爱好者数量之多是难以想象的,再加之出版发表的限制和阅读的巨量需求,产生了大量“诗歌游民”。当然,在另一个层面,“诗歌游民”也不仅仅是得不到在正式刊物发表机会的诗人,比如韩东、于坚、翟永明等在1980年代初就有诗歌发表在正式刊物之上,但他们坚持做一种精神上的“游民”,与主流诗歌精神相对的精神的“游民”。这些“游民”基于对诗歌探索的共同兴趣、边缘的诗歌身份和相近的地缘关系,建立起“兄弟情谊”,这是1980年代“诗江湖”的重要主体。
一般来讲,“油印”的“诗江湖”,其作者和读者群呈现出交错重叠的现象,基本建立在熟人的“圈子文化”基础之上。与有国拨经费的正规出版物长期培育出来的稳定的作者及面向全国范围的读者群不同,“油印”诗集或者刊物,首先是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也即同行之间互为读者进行交流的资料。由于当时通讯不方便,“油印”的经费也多是自筹或者熟人资助,所以这些作者、读者一般都是某地域群体的熟人。向以鲜谈到当年油印《红旗》,从经费到主办,都是他们几个诗人作者,“一人凑一份钱”,“在极度贫穷的时代,要创办一份刊物,哪怕是简单的刊物也并非易事。《红旗》主要是老式铅版打字油印,用订书机装订,没有什么讲究”,因为“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只有把诗印出了,能够传播给一些同行看就行了。”[23]当时诸多油印刊物取名为“内部交流资料”,比如《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他们》创刊号在作品目录前标“他们文学社交流资料”等。虽然取“内部交流”一说是规避风险,但也确实道出了“油印”的传播范围其实更多是“地域小圈子”。从“小圈子”出发,不断吸收一些志趣相投的熟人,扩大影响,“小圈子”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诗歌群落、江湖的坐标。“小圈子”与“小圈子”之间又互相碰撞、分化、融合,在此过程中,诗歌群落的江湖地理坐标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确认。
这里讲的“熟人文化”,虽然主要强调基于地理学的同学、“兄弟”情谊和“圈子文化”,却并不否认其中的突围精神:突破地域的限制,在更广阔的“江湖”上建立诗名。1980年代,“诗江湖”中的“油印”作品主要通过邮寄、书信、朗诵的形式发表和传播,还常常伴随着一种更“江湖”的方式:“诗歌游历”。它是指诗人们背着“油印”诗稿,四处游历、朗诵、喝酒、交友,既完成了诗歌的再发表,也广交了“江湖豪杰”。刘禾在编《持灯的使者》一书时,发现了以“白洋淀诗群”和“今天”派为代表的诗人的“游历”的重要性,那些手抄本和油印诗歌的游历,“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必不可少的传播手段,它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24](P.IV)
李亚伟的《中文系》《硬汉们》等诗歌在最初的邮寄传播之后,又通过“诗歌游历”的方式完成了另一种发表。他说:“我和二毛去涪陵拜访在文工团做演员的何小竹和在党校当教师的巴铁,并在闹市区街头一个小茶馆里给诗人何小竹、批评家巴铁以及诗人冉冉、杨顺礼、小说家朱亚宁、画家梁益君、钟刚等涪陵城内扳着指头数得上的文化人士朗诵了我的诗歌。其间,我的朗诵一会儿被茶馆里兜售零食的小贩打断,一会儿被门外送丧的吹打声干扰,但朗诵很受朋友们欢迎,成功地完成了那个年代‘莽汉’诗歌的另一种发表形式。”[20]这种发表方式突破了原有的熟人文化圈(“莽汉”内部诗人圈),在更广阔的“江湖”上赢得了不同身份的读者。
激动的诗人柏桦,诗歌流浪的足迹在从广州、重庆而成都后,于1984年终于去了北京,第一个拜访了《诗刊》社的唐晓渡,“给他留下一册我的油印诗集”[25](P.122)。然后径直去了川籍老诗人陈敬容家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见了北岛,“我拿出一本我的油印诗集送给他,他随便翻了翻,然后仔细看了一遍《表达》,他好像赞扬了这首诗。……就在我略为失神的刹那,他已从里面一间屋拿出他的一本油印诗集送给我……我们在书籍和油印诗集中交流着……”[25](P.125-126)
高校学生之间的“诗歌串联”也是一种“诗歌游历”,常常是某学校有诗人来了,该校的学生就动员大家捐饭票、腾床位。1982年,西南师范学院的廖希邀请四川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的胡冬、唐亚平、赵野、万夏等赴“重庆论剑”,“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25](P.150)“共有十多个与会者,把诗稿都拿出来,一摞摞,放满了桌子、床和地板。”[10]
“诗歌流浪”的形式将诗人们从小圈子突围到更大的“江湖”之中,按照万夏的叙述,“到了1985年夏天,四川的诗人们已经揉结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诗歌江湖,并且还在无限地蔓延。成都、重庆、南京、上海、北京和东北的诗人,正在以一场诗歌和酒会的名义,向成都靠拢。”[26]由四川南充而重庆、成都、南京、上海乃至全中国,诗人们以另一种非组织的形式建立起当代诗歌的全新空间,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诗江湖”。
三、“油印”与“诗江湖”的诗学品格
从此时期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油印“时期“诗江湖”的生成恰恰回应了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主体性、现代性、平民意识等。我们通常会从理论的角度获得关于1980年代“主体性”“现代性”的阐释,或者从作家作品中获得何为主体、何为现代的认知。但是,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生成,不仅仅是理论和作品构成的,现实语境中的实践行为和关系,往往更能在细部提供一些历史的细节。此时期“诗江湖”的构建中,“油印”作为一种重要的印刷实践,恰好在历史的细部回应了1980年代关于主体性、现代性等等一些关键词。
我们先看一段“莽汉派”诗人李亚伟对1980年代油印诗歌文化的叙述:“当时,地下诗人们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很多新奇的诗歌来,并很快通过有别于官办刊物发表的渠道——主要是朗诵、复写、油印、书信,进而传抄和再油印四处流行,其效果相当强烈,诗人们也随时都能看见外地刚刚寄来的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20]
这一段叙述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就是将复写、油印诗集等与“地下诗人”联系在一起,以有别于官办刊物的渠道。虽然1980年代的“地下诗人”的语境,已然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但这样的表述,是对“油印”和诗人自我关系的主体认知:“油印”将诗歌的发表权掌握在诗人自己手中,这使得未名的诗人的作品得以快速发表和传播;而随着“朗诵、复写、油印、书信,进而传抄和再油印”等方式联接起来的圈子,是那个时代青年人自主交流常见的组织方式;更有意味的是他认为“油印”刺激着新鲜的诗歌创作,“名诗和明星在没有任何炒作的情况下不断出现……本人甚至亲眼看见上述诗歌在这些作者的名字传来不久,就随着作者本人鲜活的手写字迹出现在某个地级市的一台油印机前。”[20]
在这段充满激情的重述中,“油印”就是这个年轻的“诗江湖”的“荷尔蒙”,对于诗人们的创作有一种隐秘的催化作用,它是1980年代新的诗歌空间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首先,“油印”突破了传统的发表和传播的格局,是一种建立在自主意识基础上的主体性行为,它使得未名的诗人的作品得以快速发表和传播,进而形成交流和创作诗歌的热潮。在主流诗刊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1980年代的诗人们从油印刊物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自由的气息,因此他们热情地张扬着“油印”精神,并以此为傲。此时期大量油印诗歌刊物和诗集,都是在一种异常热烈的氛围中产生,刺激和鼓励着青年们的创作冲动,并以此获得自我的建构和诗人身份的认同。大学生诗派代表尚仲敏说:“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其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随着诗歌运动,一个思潮、一个浪潮,我们被卷入里头,我们不得不被卷入里面,不得不这样,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里面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啊,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种内心的愉快和激动,我以我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27](P.513)从自我的建构、诗人身份的认同进而到对整个时代的认同,源于“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形成的“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油印”是1980年代“诗江湖”“主体精神”形成的基础。
其次,“油印”隐秘地催化着青年们追求自由和新鲜的创作方式,同时也确立了青年诗人反叛主流诗坛的美学立场和探索实践,建构起一些富有新意的思想和鲜活的诗歌文本。“油印”即“出版”,由于不需要官方出版繁琐又严格的审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青年们追求自由和反抗的精神得以释放。恰逢其时思想文化的适度解禁,青年们得以在交流学习中大胆写出有别于主流诗歌的作品,催化了1980年代“探索实验诗”的热潮。徐敬亚不仅在著名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1986-1988》的前言中,批判主流公开的刊物对青年诗人的漠视,看不到青年实验诗歌的全部面目,还分析了其后果就是:“朦胧诗后,这种对公开刊物的不信任,以一场局外的艺术大循环的民间形式出现了:巨量的自印诗集废弃了先进的文字流通形式旁若无人地自生自灭起来。”[28](P.4)
今天重新来看1980年代具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和作品,最早都是出现在“油印”诗集或者刊物上。比如当时震惊整个理论界的蓝马的《“前文化”导言》,最早出现在《非非》创刊号上。后来成为一个诗歌时代标志的”第三代人”的提法和相关表述,不管之前有多少口头的争论,但最早正式出现在1983年1月由北望作序的《第三代人》油印诗集中。
大胆的、具有冒犯属性的写作实验-油印-小群落分享-更大范围的传播,这是1980年代诗歌多元化实验空间得以生成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在当时进行各种诗歌实验的小群落中,在整个1980年代此起彼伏的诗歌的革命浪潮中,“油印”作为中间环节和物质技术保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从时间序列的中国诗歌史,还是从空间序列的共时写作来看,1980年代诗歌观念中的平民意识和女性意识,追求幽默、调侃、反讽和解构的美学风格以及口语化的语言策略等,也都是经由“油印”精神的洗礼和“油印”作品的传播,从不同方向凝聚成了“诗江湖”的诗学品格。
最后,作为容易出错、比较粗糙的“油印”本,呈现出1980年代的“诗江湖”既粗粝直白又生动鲜明的个性色彩。笔者在一些收藏家比如“世中人汉语诗歌资料馆”以及荷兰莱顿大学的“unofficial poetry jounals from China”的“特藏室”⑧中,见到较多字体、形制各异的“誊写油印本”和“打字油印本”(1980年代后的油印本,大多是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印刷)。与那些整洁、统一、美观的正式出版物相比,这些油印本的粗糙是一眼可见的。特别是手刻的字体,同一本刊物或者诗集,由于不同的人来刻印,就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字体。
比如我在莱顿大学“特藏室”见到的《今天》创刊号影印本[29],就是由不同的字体刻写而成,印证了芒克回忆当时多人轮流油印的情节:“由于陆焕心两口子住的那间屋子没多大,不能同时容下多人在一起干活,我们就事先商量好大家轮流来油印《今天》第一期。”[30]与此同时,这些油印本印好后,错漏比较多,就留下了诗人删改和增补的笔迹。比如《今天》创刊号中,北岛那首著名的《回答》中的“冰川纪过去了”中的“纪”在油印时写成了“己”,“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在油印时是“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竞争”,这些地方都有刻印好后人工修改的痕迹。
另外在诗人王家新的收藏中见到万夏《枭王》的油印本,经采访得知,万夏1985年在重庆涪陵廖亦武家中一个码头边的小房子里写下这首诗,廖亦武夫人阿霞当时是文化馆的打字员,她帮万夏打印然后油印出来的。⑨油印诗集封面上“枭王”的“枭”字,像孩子画的一只鸟,有点朴拙的意趣。封面左下角题写:“王家新老哥哥指正;85.10.14;万夏。”翻开第一页,第一章《女》就有两处修改的痕迹以及油墨分布不均导致的字体粗细与深浅的不同——这是当时油印本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经常讨论的1980年代是“个人化写作”的肇始,就隐藏在这些深深浅浅的各色字体的细节之中。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绘画出现在诸多油印本中,比如笔者在“世中人汉语诗歌资料室”里见到的唐亚平的个人油印诗集《黑色沙漠》,封面绘有沙砾一样的线条构成的沙漠形状,“唐亚平”中的“亚平”两个字设计成了流沙一样的波浪形状,内页第7、9、10、11右下角都配有几笔线条画;石光华油印诗集《企及磁心》,封面左下部分绘有一个太极阴阳图,联系到诗集封面的时间“一九八四年春”,契合他当时正与宋炜宋渠讨论的“整体主义”诗学的构想。这些油印本中的绘画,原始粗糙,多是作者或者同道信笔勾勒,显示出其时的诗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试图改变油印白底黑字的单调,突出个性和主体的努力。
结语
笔者认为,1980年代是真正实现了将“油印”锲入到诗歌场域结构性构建的时代。其时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碰撞和交锋,给社会、文化留下了一些可供发展的“缝隙”。这个缝隙也决定了1980年代的“地下油印”并非某种危险的政治倾向,而是被压抑的文学艺术审美的释放、对“现代性”的想象和追求。“油印”者们对这个时代是有信心的,甚至怀抱“理想主义”的探索精神,因为它是有“缝隙”可以“呼吸”和操作的,有前景可以想象和期盼的。正如有关学者总结的关于1980年代的历史体认,“80年代作为一个告别50-70年代历史的‘前现代’与‘革命’的‘现代化’时期,作为一个似乎重新接续了打碎古老中国‘铁屋子’的‘五四运动’传统的新的文化启蒙时期,同时也作为一个挣脱了传统中国‘闭关锁国’谬见而‘走向世界’的开放时期,这种历史意识和时代认知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共鸣。”[31](P.2)与此同时,过去高度统一的政治化生活也慢慢发生变化,日常的、世俗的生活开始重建。“油印”作为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对资源有限且较为正统的正式出版印刷活动的一种有效补充,它是诗人们的自我推广和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基础。
在本文中,“油印”具有几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是与油印机、油墨、蜡纸等有关的印刷技术;其二是一种精神符号,是在特定时代的缝隙中,在审美“现代化”的想象中,青年人对固有诗歌美学和生产方式的反叛和实践精神;其三是这种印刷技术和印刷精神的产品:诗歌“油印”文献资料。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诗江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它构成了此时期诗歌场域丰富的文学文化景观。当“油印”锲入到一个较为僵化的诗歌空间中,整个空间的边界被不断冲破、拓宽并形成与旧空间的交流与融合,诗人的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先锋观念伴随着油墨的清香不断深入人心。当然,“油印”的即时性、实用性也会刺激诗歌写作产生求快、求胜的功利化追求。当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1980年代“油印”的“诗江湖”,形式和内容的复制和粗制滥造者也不乏其数。为了快速成名,“油印”刊物上充斥着宣传鼓动的自我推销和传经布道式的语言,“江湖”圈子文化展现出一种时代集体文化的余绪和斗争精神;而在自我经典化的策略性编排和追求轰动效果的写作中,似乎暗示着一个消费主义文学时代的前夜?这些思考在本文中尚未展开,期待与诸位更多商榷。
注释:
①《诗刊》在1980年前后就转发了舒婷、北岛的诗,对朦胧诗在全国范围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②《朦胧诗选》有两个版本,我们大家熟知的是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事实上,1985年版是在1982年阎月君编选的非正式出版的铅印内部读物《朦胧诗选》基础上正式出版的。
③《新诗潮诗集》是老木1985年1月编选的影响甚巨的非正式出版诗歌选本,分上下两本,上本主要是朦胧诗入选。
④1986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包括北岛、江河、舒婷、顾城、杨炼五人。
⑤参见作者于2021年10月26日对杨黎的采访文本。
⑥参见作者2022年2月1日对何小竹的采访文本。此说也与1997年何小竹发表于民刊《今天》中的文章《我与非非》相印证。该文章后被“诗生活”网站转载发表。
⑦参见作者2022年2月1日对何小竹的采访文本。
⑧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经过多年搜集,拥有中国民间诗刊的独特收藏。这些资料现在正式具有“特藏”地位,并且被保存在一个具有温度控制等功能的专业收藏室,正如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珍本和古籍一样。参见莱大图书馆举办的中国民间诗刊数字化先期项目开幕式柯雷讲座录像:https://weblectures.leidenuniv.nl/Mediasite/Play/cb8fd345efb34e6098c85a191b673d7c1d
⑨参见笔者2021年10月15日采访万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