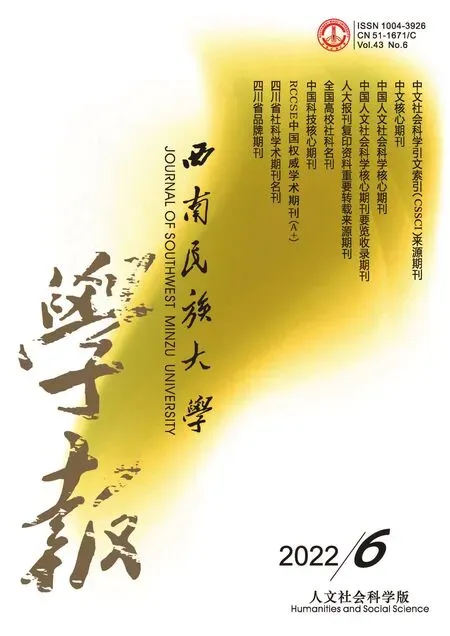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
——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谭嫦嫦
[提要]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以《女神》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和从《棠棣之花》的公演开始的抗战时期,是郭沫若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最多的两个阶段。如果不拘泥于具体的观点或结论,而从整体思路和学术范式的角度来看的话,迄今为止的研究,实际上都把两个阶段当作了“两种类型”。无论是最初表彰郭沫若的发展和进步,从政治性和现实斗争性两方面高度评价他的“抗战史剧”,还是后来从所谓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出发来褒扬《女神》而贬低后者,观点和结论变了,但自我和集体、审美和政治的二元对抗立场,却一直沿袭了下来。
然而,《棠棣之花》从1920年未完成的“诗剧”,经由不断的补充、调整和修改①,最后在1941年定型并搬上了舞台的创作过程表明,这样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品由“半成品”到五幕历史剧的最终完成,既见证了社会历史现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纠缠,也表明了郭沫若一贯的政治革命热情。不是极力想要廓清,而是极力想要在相互纠缠中展开自我的历史想象力,让郭沫若把《棠棣之花》从浪漫主义的“诗剧”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史剧”,造就了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文学景观。
一、“革命精神”与“个人牺牲”的有机交融
事实上,《棠棣之花》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抒情诗的“神来之笔”,而是在一个充满了政治性的特殊情境中诞生的。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时事新报》的编者为纪念“双十节”设立专刊而向自己约稿,而自己则应邀“也做些文章来凑趣”的产物。②专刊约稿,表明了特殊的语境和对作品性质的可能要求。而后者则说明了郭沫若私心里或许不是那么愿意配合纪念特刊的要求,但事实上却也只能“硬写”一篇前来“凑趣”的复杂心情。
当年的“双十节”,是国民政府为庆祝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了国民政府而设立的“国庆节”,本来就有纪念革命先烈、张扬革命精神的特殊政治含义。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的《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也同样围绕着“革命精神”做文章。“增刊”首篇文章为郭绍虞《我的“双十节”庆祝观——革命的精神》,谈的就是“革命精神”的重要性:“现在人喜欢谈什么运动,我以为无论哪种运动多少总是带有一些革命性的,不于革命的精神充分培养,贸然去从事什么运动,总不会有多大的效果。”其他作者如毛泽东、恽代英、余家菊等人的文章,也都没有脱离“革命精神”这个纪念增刊的根本主题。刘叔雅的《旧式革命与新式革命》,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时事新报》张东荪和李石岑诸位先生向我要一篇文。在“双十节”的报上发表。我正在这个‘秋霖腹疾俱难遣’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并且提起这“双十节”来,更增我无限的感喟。要说也无从说起。只得把我心里一起一落的这些凌乱无序的想头随笔写来聊以塞责吧。④
刘叔雅(文典)的“聊以塞责”,说明了“双十节增刊”的约稿确实有着相应的主题要求。郭沫若拿来“凑趣”的《棠棣之花》,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约稿要求之下诞生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诗剧”《棠棣之花》的“革命精神”和“个人牺牲”两个最明显的主题了。聂嫈和聂政两姐弟一出场,就对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乱而“田畴荒芜”,到处充斥着“乌鸦与乱草”的苦难景象,发出了深切而沉痛的感叹:“人类底肺肝只供一些鸦雀加餐,人类底膏血只供一些乱草滋荣”。
对郭沫若来说,战争不仅毁坏了人类的生活家园,造成了“田畴荒芜”的悲惨景象,更重要的是还毁坏了个人“生命的源泉”,造成了生命的空虚和荒芜。他借聂政之口,愤怒地喊道:
战争不熄,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消逝。这几年来今日合纵,明日连横,今日征燕,明日伐楚,争城者杀人盈城,争地者杀人盈野,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近年来虽有人高唱弥兵,高唱非战,然而唱者自唱,争者自争。不久之间,连唱的人也自行争执起来了。⑤
既然战乱带来的不仅仅是“田畴荒芜”的外部世界的苦难,更有“生命的泉水”日渐枯竭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毁灭,那么反过来,在“革命精神”的引导下牺牲自己而阻止战乱,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政治革命与自我救赎的双重价值。作品借聂嫈之口,说出了郭沫若对政治革命与自我救赎之间的有机关系的理解:
母亲在时,每每望我们享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们一个个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假使我们能救得他们,便牺牲却一己底微躯,也正是人生底无上幸福。所以你今晚远赴濮阳,我明知前途有多大的牺牲,但我却是十分地欢送你。我想没有牺牲,不见有爱情;没有爱情,不会有幸福的呀!⑤
这也就是说,先行在《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发表,随后又收入诗集《女神》的《棠棣之花》,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半成品”。它对“人类底肺肝只供一些鸦雀加餐,人类底膏血只供一些乱草滋荣”的苦难景象的诅咒,会让人想到《凤凰涅槃》对“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宇宙”的愤怒。伴随着聂嫈的箫声而来的“离别在今宵”“汪汪泪湖水”等充满了感伤色彩的夸张言辞,也很容易让人从整体上将其纳入郭沫若早期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中来理解。而事实上,郭沫若在这里已经为连绵不断的战争找到了它的历史根源和相应的“根本解决”之道:
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废,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底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⑤
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中的感伤,实际上也就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闷式感伤,[1](P.166)而是不仅找到了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更找到了获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之路的甜蜜的感伤,充满了自我表演和自我张扬意味,也充满了激越而高昂的杀伐之声。聂嫈的悲抑和苦闷,便不是纯然的个人感情,而是个人突进现实的创造意志受到了阻碍之后的生命力的显现,一面指向个人自由,一面指向了社会解放。为了社会解放的“个人牺牲”,也就成了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有机桥梁。
一个人既可以通过张扬自我意识,或者如通常所说的高扬主体性精神,在征服自然、控制他者的高歌猛进中,也可以在受难和牺牲中来寻求自我肯定,获得相应的身份认同。《天狗》代表了前者,“诗剧”《棠棣之花》则代表着后者,表明了《女神》的另一副面孔。所以,按照剧情的发展本来应该是第二场的《聂母墓前》,也就应和着《时事新报》“双十节增刊”以“革命精神”为主旨的约稿要求,率先以《棠棣之花》为题,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这样也就是说,郭沫若虽然用了“凑趣”的说法,表明了自己对“双十节增刊”约稿的态度,但事实却对“革命精神”情有独钟。为此,也才不惜打破“已构想数年”的结构和逻辑顺序,②率先把表达不惜“个人牺牲”以求得社会解放的第二场捧了出来。“双十节增刊”约稿的政治要求,其实不是束缚,而是让他获得了另一种自我建构、获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的历史道路,让身处“五四”思潮之中的郭沫若,率先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转向”。而这,也就解释了郭沫若为什么会在宣称《棠棣之花》是“凑趣”之作的同时,又不无得意地说这部作品是“由灵感迸出”的诗,而不是“努力做出的戏剧小说”,“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2](P.26)将其收入诗集《女神》,无疑就是对“由灵感迸出”和“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的追认。
在这个意义上,1922年发表的第二幕,反而像是对郭沫若诗性激情的一个回顾性的说明。在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地抒发完“个人牺牲”激情之后,再反过来说明这种激情的根源。经历了漫长的忍耐,严格遵照封建礼教的相关要求,守完“三年之丧”的聂政猛兽一样,爆发出了《女神》所特有的连绵不绝的浪漫主义喊叫:
我如今成了自由的身躯,你不知道我的血液在我心中怎样地沸腾着在哟!我早愿见我鲜红的血液溅染他们的尸骸!我的力!我的血!我的愤懑!我好像饥渴了的苍鹰哟!我好像脱了牢笼的虎兕哟!我饥渴着恶人们底血液了!……⑥
原因很简单:那个早就摆在眼前的,融合了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两大神圣理想的“个人牺牲”之路,在前面已经等得太久了。聂政的渴望和焦虑,也就是郭沫若的渴望和焦虑。压抑得多久,激情就爆发得多激烈。
综合上述情形,可以看出:第一、《棠棣之花》的创作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是浪漫主义创作灵感及其“自我表现”的产物,而是个人激情和外在的现实要求相互纠缠、相互激荡的结果。第二,社会解放事业及其相应的政治形式,不是压抑了“个人自由”,破坏了“文学自身”的完整性和纯洁性,而是为郭沫若的“个人自由”提供具体而切身的历史可能性,也催生了《棠棣之花》。社会解放所要求的“个人牺牲”,为郭沫若提供了一条获得“个人自由”的思想和历史道路。
二、《聂嫈》:“个人牺牲”与“民众的觉醒”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如果没有“五卅”惨案的刺激,《棠棣之花》就会止步于已经发表的第一幕第二场和第二幕上,以“半成品”片段的形式留在文学史上:“自从把第二幕发表以后,觉得照原来的做法没有成为剧本的可能,我把已成的第一幕第一场(聂政之家)及第三幕第一场(韩城城下)全行毁弃,未完成的第三幕第二场(哭尸)不消说是久已无心再继续下去的了。”[2](P.26-27)但就像《时事新报》的约稿这个看似与“文学自身”毫无关系的外部事件意外地催生了《棠棣之花》一样,突然爆发的“五卅”惨案震动了郭沫若,也催生了《聂嫈》。他后来回忆自己站在街头,目睹中国民众的英勇无畏和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的情形说:
我平生容易激动的心血,这时真是遏勒不住,我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这个意想不消说是没有决心行得起来,但是实现在我的《聂嫈》的史剧里了。我时常对人说:没有五卅惨剧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
这样的激情,推动着郭沫若“在五卅潮中草成了这篇悲剧”[2](P.29),从而延续了已经发表的《棠棣之花》,也进一步推动了五幕“抗战史剧”《棠棣之花》的成形。和收入了诗集《女神》的《棠棣之花》不同,郭沫若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史剧”这个词。
作为“五卅”惨案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聂嫈》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聂政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国宰相侠累和国王的故事。其二是酒家女春姑、聂嫈两位女子,为聂政而赴死,由此感动了更多的普通民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对两个故事作了一显一隐的处理,前者由功能性人物盲叟转述,后者则在第二幕里正面呈现。
放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里看,《聂嫈》讲述的是“个人牺牲”逐渐唤醒了民众,最后走向了社会解放的革命史故事。从郭沫若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历程的角度来看,则是“个人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从自己形影不离的亲人聂嫈开始,经由酒家女春姑、艺人盲叟而逐步扩大到广大的普通人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的英雄主义故事。“士为知己者死”的古代性故事,被郭沫若改写成了不仅仅是为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而赴死,更是为了春姑、酒家女,乃至最终觉醒过来,决心“杀死这一些没良心的狗官”,“由山里去做强盗的”普通士兵的“知己”而赴死。[2](P.44)
两个故事,同样也一点都不矛盾。
鲁迅早年曾经在日本筹办《新生》,试图以此唤起民众,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结果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应,既没有赞同,也没有人来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一样。鲁迅说,“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由此而陷入了沉默,“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1](P.5-6)
郭沫若的《聂嫈》,则截然相反。聂政的英勇无畏的“个人牺牲”,感动了周围的所有人。自己的姐姐聂嫈不用说。仅有一面之缘的酒家女春姑,也被其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义无反顾地献出了青春的生命,成为了他的“知己”。其他如盲叟、酒家女之母等人,同样也无一不为聂政“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加入了“知己”的行列。最典型的,当然是看守聂政尸体的众卫士,也在聂政英勇事迹的感召之下站起来,杀死了他们的长官,加入了反抗的行列。这是一个觉醒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汇成了群众反抗的历史洪流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郭沫若“五卅”当天在上海街头的见闻和感受的投影,也和当时流行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想象一样,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期待。
但换个角度看,群众觉醒的过程,同时又是聂政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过程。受其“惊天动地”的英勇事迹感召而觉醒的群众越多,聂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形象,也就越光辉,越高大。事先潜含在“个人牺牲”的刺杀行动里的愿望和期待,通过群众的觉醒而得到了满足和兑现,反过来强化了“个人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也强化了聂政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让郭沫若“慷慨激昂”的浪漫主义激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释放。
换句话说,群众觉醒、集体反抗之类通常被认为是压抑和中断了“五四”个人主义传统的外部因素,实际上不是压抑和中断,而是推动了郭沫若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使之沿着“慷慨激昂”的英雄想象,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个人牺牲”与社会革命相互激荡、相互生产而又相互强化的有机结构。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双重身份,在这个社会承认和个人表现互为因果的有机结构里,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为此后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成奠定了源初的基础。
三、《甘愿做砲灰》:“个人牺牲”与“主张团结,反对分裂”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民族危亡之际,郭沫若再次提笔整理和修改《棠棣之花》,使作品初具五幕史剧雏形。
如前所述,聂政的英雄形象,是通过为民众牺牲逐渐获得社会的“承认”确立起来的,这一点早在《聂嫈》中就已经做好了铺垫。然而,《甘愿做砲灰》这个版本中聂政的走向行刺,在第一幕就借聂嫈之口点明其流血牺牲是要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二弟想到‘士为知己者死’,他今晚想赶到濮阳去探访严仲子。”[3](P.68)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将过去版本中聂嫈哀婉感伤和聂政激越张扬的自我表现部分删除,姐弟二人就各自的“任务”和“计划”分道扬镳。从表面上看,《甘愿做砲灰》这个版本表现出了某种压抑“自我”的迹象,似乎与同时期问世的《甘愿做砲灰》中甘愿牺牲个人生命、积极奔赴前线做砲灰的高志修形成某种映照关系,暗喻浪漫主义诗人英雄情结的沉寂。
然而,从加入的第三幕《东孟之会》来看,聂政的刺杀宰相和国王这个激烈而暴力的场面得到呈现,充满了英雄传奇色彩。只见聂政着秦武士装束,闯入离宫,“逢人便斫”,“上阶直趋侠累”,只用一剑结果了侠累和韩哀侯的性命。侠累与韩哀侯倒地的同时,聂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利剑刺向秦使与武士,两人“伏尸于阶墀上下”。之后,众侍卫涌来,聂政又“以一身当众敌,杀伤颇多”。[3](P.101)聂政杀伐果断的形象跃然纸上。行刺这个惊心动魄场面的呈现,使多少年来积压在郭沫若内心的激情和生命力得以爆发。
事实上,聂政的“士为知己者死”不仅没有压抑和消解那个为民众牺牲的英雄聂政,反而是将这位英雄更进一步推进抗战现实当中。严仲子作为聂政的知己,他与侠累之“仇”,被集中在“三家分晋”问题上。严仲子主张团结,共同抵御外辱,侠累则提倡分裂,鼓动内战。并且,由分裂引起的“内战”,还是造成“乌鸦与乱草的世界”和“生民涂炭”的根本原因。聂政的刺杀对象侠累,不仅是造成三晋分裂的“罪人”,还是造成民不聊生的“天下的罪人”。聂政的“个人牺牲”为知己“殉义”与为民众的“除害”并不矛盾。因此,英雄形象不仅没有受折损,反因其解决“分裂”和“内战”问题与现实抗战中的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政治需要吻合,具有抗战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其个人英雄主义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之后,并不因此满足,他还不忘安排众多“看客”对这个激烈又传奇的刺杀场面作解释。侍女们强调聂政的杀伐果断,“那刺客的剑法真厉害。刺穿了韩侯的胸膛!”“又刺穿了宰相的颈项。”[3](P.101)卫士们说明聂政刺杀宰相和国王的原因是为了斩除“汉奸”,“他说那媚外求荣的宰相侠累,才是中原的大汉奸呢!”[4](P.103)除此之外,聂政斩除汉奸之后,郭沫若还进一步借侠累之口发表一番“忏悔”,“我自己爱树立党派,爱为自己的一党一派的私利鼓动内战,是我把晋国害了,也把中原害了。”并加以说教,“我劝你们以后,千切不要再从事内战,千切不要依仗外来的势力以图自己的安全。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呵。”[4](P.103)这个处理,将聂政流血牺牲的政治意义带入“惩恶劝善”的传统道义范畴,作品因其说教性质而带有传统旧戏色彩。
郭沫若对第三幕的“说教性”处理,与孤岛时期上海兴起的戏剧演出有关。在《甘愿做砲灰》这部具有“夫子自道”性质的作品中,主人公高志修受“塔丽雅”剧场老板再三请托,要求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新编成皮簧戏,以便演出。这说明当时的戏剧演出作为抗战宣传品逐渐流行的事实,“皮簧戏”因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民众基础得到高志修的肯定。老舍曾言,抗战的神圣性召唤着知识分子们走出亭子间,凡是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活动都应受到鼓励,“神圣的抗战是以力申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⑦所以,老舍抛下自己擅长的小说,学习创作一般民众喜爱的鼓词、旧剧、民歌等艺术形式便是对这一口号的响应。同样的道理,“皮簧戏”作为“十八般武艺”之一件,也被郭沫若应用到了《棠棣之花》当中,第三幕的行刺场面便带有作者对“舞台演出”和观众接受效果的考虑。作品被赋予了明确的抗战宣传期待,与当时纯粹出于“生意经”考虑的传统旧剧有区别。
由此可见,充满了英雄色彩的个人牺牲,在全民抗战的现实语境中,并没有因此而枯竭,反因其解除了阻碍抗战事业的“罪恶”,推动“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战争而获得了正义性和崇高性。
四、最后的成为“历史剧”的《棠棣之花》
和“诗剧”《棠棣之花》的诞生一样,1941年最后定型并搬上了舞台的五幕“史剧”《棠棣之花》,同样也是外部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灵感迸发”的产物,其中甚至还夹杂了“集体创作”的因素。但同样地,也不能因此就说它完全是一部政治宣传品,压抑了郭沫若的“自我”。
作为“寿郭”纪念活动的一个环节,五幕史剧《棠棣之花》与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一道被搬上重庆舞台与重庆观众见面。导演石凌鹤在其“自白”中说得很清楚,为了使剧本能够顺利演出,他在郭沫若的授权和指示下,对剧本进行删改。从“自白”来看,导演的删改并不“客气”,人物、对话、情节等都有改动,如“在第五幕大胆的删去了八面”,“第三幕乐队之宫女等,第五幕的卫士及士长,都经减少了数人”,“第二幕我增加了春姑斟酒一场,第四幕增加了春姑回忆的一场”。⑧修改过程中,郭沫若要求增加的一个喜剧场面也因为不符合演出要求不得不“割爱”了,可以看到郭沫若对外界演出要求表现出的“妥协”态度。
“妥协”之外,郭沫若还对剧本作了相应调整。第二幕严仲子与聂政对话处增加三千余字,原本围绕“三家分晋”展开的“主张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题被扩展为顺应民心的“抗秦派”与违背民众意志的“亲秦派”之间的冲突。严仲子道出自己与侠累“团结——分裂”的仇恨后,聂政随即就如何行刺的问题向严仲子寻求方法,严仲子却颇为感伤地抛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将聂政的流血牺牲从传统“士为知己者死”的“殉义”改写为聂政的个人选择。聂政明确站在“抗秦”立场对抗“亲秦”的侠累,“何况现在的中原分成了亲秦和抗秦的两派,我素来是主张抗拒秦国的。”[4](P.42)经此修改,聂政与严仲子虽立场不同,但在“团结”主题下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聂政前往韩国刺杀侠累和国王这个举动,一方面是以个人牺牲扫清中原内部抗秦事业的阻碍,推动中原的团结统一,抵御暴秦的入侵。另一方面,抵御秦国入侵,还将使中原人民免遭沦为奴隶的危险,是拯救中原人民的英雄行为。
郭沫若对“团结”主题的改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引发国共冲突。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周恩来在“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团结民众力量对于赢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使全中国人民认识:只有团结,才能外御其侮,只有统一,才能众志成城,打到最后。”[5]除此之外,《新华日报》第二版还印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团结”二字。然而,对于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来说,政治分歧还直接对其政治抱负造成了挤压,其“渄关工作不需人,受限只因党派异”一句,则明显带有个人的“牢骚”。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内乱”,促进团结,就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有郭沫若的个人英雄情结的考虑。所以郭沫若借聂政之口,道出心中的理想和愿望:
只要是有利于人,有利于中原,我这条生命并没有看待得怎么宝贵;但只要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而使用我这条生命,那我这条生命也就增加了它的价值。[4](P.42)
在聂政(郭沫若)看来,在人民和国家利益面前,其生命本是和“任何物品一样”无足轻重,但反过来,如果是以个人生命拯救人民和中原,这一行为自然也被赋予了至高的道德和荣誉,牺牲者聂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救国救民的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棠棣之花》公演作为“寿郭”纪念活动诸环节之一,是围绕着确立郭沫若“文化人”身份这个核心展开的[6](P.234)。作为一场戏剧演出,《棠棣之花》面向的是广大观众。所以郭沫若根据自己的“演出”理解,又在第三幕增加韩山坚与侠累对话一场,意在暴露丑恶。侠累不仅不以卖国为耻,“即使我就算把韩国出卖了,唉,我是卖了很大一笔价钱的啦。”而且其“媚秦”立场与“民心”背道而驰,“秦国素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现在有很多的人主张抗秦,严仲子所以能够收揽民心的,也就是这个缘故啦。”[4](P.54)出卖国家,违背民心的侠累,不仅是“中原的罪人”,同时也是造成人民苦难的“罪人”。
经此修改,聂政救国救民的牺牲行动使其英雄形象高大无比,相形之下,聂政刺杀对象侠累的罪恶也被暴露无遗。英雄与“罪恶”形成的极致对照,为第三幕这个流血暴力的刺杀场面注入了更多浪漫主义激情。不仅如此,郭沫若对作品的“对照性”处理,还因为借用了当时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旧剧成分,使演剧具有了“劝善惩恶”的说教性质,符合抗战演剧宣传教育民众的要求和任务,又不免透出郭沫若作为“政治人”的自觉。⑨但也正因郭沫若此时正处于由“政治人”过渡向“文化人”的“中间形态”,才使其四十年代历史剧创作在颇具张力的政治背景下获得合理性,为之后轰动山城的《屈原》演剧奠下基础。
《棠棣之花》公演后,有人对第三幕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场面破坏了全剧“诗意的统一”,而郭沫若却坚持将其认作是“诗”,“但丁不是描写过地狱,歌德不是描写过恶魔,波德莱尔不是做出了《恶之华》,罗丹不是雕出了《没鼻子的人》吗?而依然是‘诗’,依然是‘美’。大概‘诗’和‘美’底范畴相当多,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7]郭氏的辩护足以说明,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并没有因其政治宣传任务而受到压抑,反而在四十年代的抗战现实中燃烧得更加猛烈了。
结语
从二十年代的“诗剧”到四十年代的“史剧”,《棠棣之花》形式变迁背后,潜藏着郭沫若以个人政治热情对中国革命展开的历史想象。这种想象是他个人的浪漫主义激情在中国现代历史语境中的自然产物和必然结果。以往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现代艺术幻象看作是受政治等形式的压抑与反叛的思路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现代革命语境下政治与文学的同一性。浪漫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诅咒,与政治等立足于整体人类幸福而告别苦难世界的这个共同诉求,是两者携手同行的前提和基础。而前者热烈向往的所谓光明的梦境与幻象,又为政治理想——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提供了合理性方案,让政治理想反过来成为了浪漫主义艺术的生产动力。两者相互纠缠,也相互推动。这便是诗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激情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中能够前后持续二十二年,并最终在四十年代得到完成和爆发的根本原因。回顾《棠棣之花》创作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反思,还原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破却在政治里”[8](P.134)的政治性境遇。
注释:
①萧凌、邵华的《探索与思考——记话剧〈棠棣之花〉绵亘二十二年》,《郭沫若研究》第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46页。
②郭沫若:《棠棣之花·附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年10月10日。
③郭绍虞:《我的“双十节”庆祝观——革命的精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年10月10日。
④刘叔雅:《旧式革命和新式革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年10月10日。
⑤郭沫若:《棠棣之花》,《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年10月10日。
⑥郭沫若:《濮阳桥畔》,《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3月15日,第11页。
⑦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⑧凌鹤(石凌鹤):《〈棠棣之花〉导演的自白》,《棠棣之花》,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47-148页。
⑨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戏剧演出作为抗战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用。“第三厅主管宣传,包括国内外宣传及思想界、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各国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是动员人民抗战的喉舌。”(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