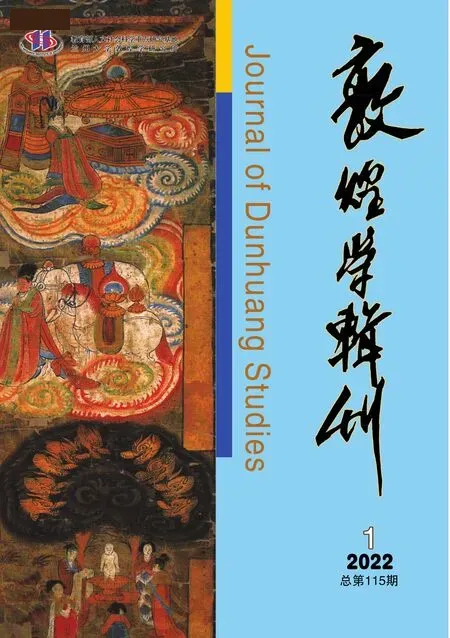西汉敦煌居卢訾仓城修筑与归属
郑炳林 司豪强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敦煌西北的大方盘城,斯坦因将其比勘为敦煌文献记载的河仓城,其后向达、阎文儒、李并成对斯坦因这一说法给予肯定①[英]奥利尔·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英]奥利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 (修订版)》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66-679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5、385页;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第96-126页;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上)》,《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第135-152页;李并成《〈沙州城土境〉之地理调查与考释》,《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84-93页。。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认为大方盘城实际上是昌安仓遗址,李氏从四方面否定大方盘城非是河仓城:其一,大方盘城距沙州里程与河仓城距沙州里程不相符合;其二,大方盘城规模远远大于河仓城;其三,两座仓城损坏程度上亦不相同,河仓城“其城颓毁,其址犹存”,而大方盘城外垣和基址皆保存完好;其四,从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关系加以分析判断大方盘城非河仓城。其后李氏根据斯坦因曾于大方盘城挖掘汉简中有一枚简记载有“昌安仓”,认为该简为昌安仓的“出入簿”,故确定这座城就是西汉昌安仓。后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玉门关外马圈湾遗址发掘有记载前往昌安仓的简两枚,确定大方盘城乃汉昌安仓①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72-80页。。李岩云《敦煌河仓城址考》认为李正宇观点是正确的,并称:“2005年七八月间,敦煌市博物馆在玉门都尉府以西的榆树泉盆地发现一座古城,其位置、规模、保存现状,与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有关河仓城的记载是一致的。”②李岩云《敦煌河仓城址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第86-92页。但这些论述仍显不足。第一,大方盘城发现昌安仓简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就是昌安仓,毕竟记载昌安仓的简还发现于小方盘城西北3.2公里和马圈湾等地;第二,即便河仓城的位置已经确定,也仅能说明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遗址,而不能说明大方盘城即为昌安仓,大方盘城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其真实称谓或与河仓城、昌安仓皆无关系。因此大方盘城在汉朝的具体称谓,很可能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根据敦煌出土汉简记载,汉代敦煌有很多仓库。敦煌郡有郡仓,其所属诸县,乃至两关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鱼泽都尉等,还有候官、交通线路上的负责接待的置和亭隧,都设有仓储机构,故根据大方盘城发掘的一枚简而确定其为昌安仓,证据稍显不足。以大方盘城这样规模的城池,并非是史籍中默默无闻的昌安仓所能比拟的③敦煌有昌安亭,昌安仓很可能仅仅是一处靠近昌安亭的“亭仓”。。在寻找大方盘城“身份”的过程中,西汉历史上著名居卢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居卢仓,敦煌汉简称之为居卢訾仓、居卢訾城。西汉最初是为对乌孙用兵修筑居卢訾仓,当双方关系危机得到化解,居卢訾仓变成西域都护府战备物资的存储基地。本节我们将从西汉与乌孙关系变化探讨居卢訾仓的修筑原因、位置、配套漕运工程及居卢訾仓权属转变等问题。
一、西汉乌孙关系恶化与破羌将军辛武贤修筑居卢訾仓
居卢訾仓是汉宣帝时西汉与乌孙关系恶化的产物。当时西汉与乌孙间的矛盾争执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乌孙王继承人选择,其二是乌孙狂王与解忧公主间的矛盾冲突。这两方面的矛盾升级导致西汉与乌孙间矛盾激化,甚至到达了战争的边缘。
汉武帝为加强与乌孙的关系,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 (又作“昆弥”,王号也)猎骄靡,猎骄靡死后,其孙岑陬即位,汉又将解忧公主嫁岑陬。岑陬死,子泥靡尚小,其季父子翁归靡继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④[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4页。,约定待泥靡大,以国归之。解忧公主与翁归靡生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宣帝本始二年 (前72),匈奴击乌孙,解忧公主与翁归靡向西汉求救。于是,宣帝五将军分道出兵击匈奴,同时“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常惠与翁归靡率领乌孙兵大破匈奴右部,乌孙自取所虏获,西汉政府又遣常惠持金币赏赐乌孙有功贵人。其后乌孙为进一步巩固与西汉的关系再次请求和亲,《汉书·西域传下》记载:
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之,征还少主。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3906页。
然《汉书·萧望之传》记载:“神爵二年,遣长罗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贵靡。”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8《萧望之传》,第3279页。《资治通鉴》亦将此事系于神爵二年 (前60)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6“汉宣帝神爵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3-874页。,这就与《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元康二年(前64)出现时间差异。《资治通鉴考异》曰:“《乌孙传》请昏在元康二年。《望之传》云 ‘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为鸿胪,盖误以神爵为元康也。”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6“汉宣帝神爵二年”,第874页。但我们认为或许元康二年是翁归靡因常惠上书请婚的时间,而神爵二年是常惠护送少主至敦煌的时间。敦煌悬泉汉简关于元康二年至神爵二年期间西汉与乌孙的通使有很多记载⑥长罗侯常惠是西汉经营乌孙的主要执行者,悬泉汉简中有关于常惠的很多记载。如:Ⅱ 90DXT0213③:5记载:“元康三年四月戊寅,前将军臣增后将……臣舜、长罗侯臣惠,承制诏侍御史曰:军司马憙与校尉马襃……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Ⅱ 90DXT0214②:298记载:“县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Ⅰ 90DXT0112③:68记载:“出鸡十只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候丞八人,司马丞二人,凡十二人。其九人再食。三人一食。”Ⅰ 90DXT0112③:69记载:“出牛肉百八十斤。以过长罗侯军长史廿人,斥侯五十人,凡七十二人。”类似记载在悬泉汉简中还有很多,这些记载印证了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营乌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说明当时西汉与乌孙来往密切。,可为研究这一阶段的西汉与乌孙关系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但无论具体时间有何差异,都不影响此次结亲的失败的结果,这使西汉与乌孙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另外,狂王泥靡与解忧公主之间不和,更使西汉与乌孙的关系雪上加霜。解忧与泥靡不睦,加之泥靡“暴恶失众”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6页。,遂与汉使魏和意、副候任昌谋杀泥靡。刺杀失败导致泥靡“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6页。,赖西域都护郑吉发诸国兵解救。后西汉政府征魏和意等归长安治罪,遣使带医药治泥靡,并赏赐安抚之,同时派遣车骑将军长史张翁调查事状。尽管西汉政府对刺杀事件显示出高度重视并竭力试图弥补,但此事还是导致了西汉与乌孙关系降至冰点。不仅如此,这场刺杀事件还成为引发乌孙国内动荡的导火索。《汉书·西域传下》记载: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7页。
狂王泥靡本就是岑陬与胡 (匈奴)妇所生子,只是鉴于翁归靡即位时约定待泥靡大,使之即位,加之其本身得到乌孙贵人拥立,属于得位正而且迅速稳定了局面,故西汉隐而未发,被迫接受了其即位的事实。此时作为“翁归靡胡妇子”的乌就屠发动叛乱,并声称“母家匈奴兵来”,即乌就屠是借匈奴之势笼络部众,弑王上位。西汉政府难以接受又一位亲匈奴的乌孙昆弥出现,毕竟连续两位拥有匈奴血统的昆弥上位对西汉政府花费经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西汉—乌孙联盟而言很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可能引发匈奴与乌孙联合③《汉书·匈奴传下》云:“(郅支单于)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匈奴郅支单于确曾联系“胡妇子”乌就屠意图建立联盟,可见西汉政府反对乌就屠成为乌孙昆弥,担忧其倒向匈奴从而对汉朝不利的确是有必要的。、汉朝在西域统治动摇等一系列坏的连锁反应。于是,甘露元年(前53)宣帝再度命酒泉太守辛武贤“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④[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5页。,居卢訾仓便在此时修筑。
二、敦煌居卢訾仓城应即大方盘城
居卢訾仓是甘露元年西汉政府为对乌孙用兵而修建的储备军事物资的仓库。关于居卢訾仓的位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⑤[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页。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居卢訾仓位置最完整明确的记载。它明确指出了居卢訾仓的相对位置是在玉门关以西,都护井以西,三陇沙以北。近世以来随着敦煌及西域地区汉简的出土亦有关于居卢訾仓的记载,围绕居卢訾仓尤其是其位置所在的讨论持续了一个世纪。王国维、岑仲勉、黄文弼、日本学者森鹿三、孟凡人、张德芳等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大致来说居卢訾仓位置出现过海头、土垠遗址之说。尤其孟凡人根据土垠遗址中发现的4枚记载“居卢訾仓”内容的汉简,认为居卢訾仓位于土垠遗址的说法①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60-83页;孟凡人《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169-186页。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张德芳最新的成果《“居卢訾仓”的记载及其百年探寻》又根据《魏略·西戎传》对孟氏之说提出质疑,虽然他没有提出居卢訾仓的准确位置,但也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认为居卢訾仓的位置当在敦煌榆树泉盆地以西至罗布泊东北岸以东寻找②张德芳已就居卢訾仓位置的诸多前人学者观点进行过梳理总结,此不赘述。在此基础上其本人亦有创见,参见氏著《“居卢訾仓”的记载及其百年探寻》,中共金塔县委等编《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20-526页。。总之,基本所有的观点都认为居卢訾仓位于西汉玉门关也即小方盘城以西至罗布泊一带,分歧之处在于有的学者认为居卢訾仓位于罗布泊西岸的土垠遗址,有的学者则认为居卢訾仓当位于罗布泊以东或东北方位。但我们经过考察认为以上这些观点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即错将《魏略·西戎传》记载的曹魏的玉门关等同于西汉的玉门关 (小方盘城)。
李正宇认为东汉时期,随着新北道的开通,汉朝在敦煌郡东部的冥安县 (唐晋昌县)新置玉门关。李并成赞成此说③参见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3页;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03-106页。。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质疑,如王素认为“伊吾路的开辟,对旧玉门关的罢废,新玉门关的设置,可能都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短期内绝不可能导致玉门关的废置”④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其主要依旧就是《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的:“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⑤[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3页。毕竟若玉门关东移,则班超无须进入玉门关,只要抵达敦煌便已进入汉地,班超的话便失去意义。此说应是。但这仅能说明班超时期玉门关应当尚未东移,却不能说明东汉末到曹魏时玉门关不曾东移。
《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7页。颜师古注云:“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7页。居庐仓即居卢仓、居卢訾仓,位于卑鞮侯井以西,亦位于都护井以西。因此前人基本认为卑鞮侯井即都护井,两者可能是不同时期对同一井渠的称谓⑧王国维《〈流沙坠简〉序》,收入氏著《观堂集林 (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岳邦湖、钟圣祖著,甘肃省文物局编《疏勒河流域汉长城考察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张德芳《“居卢訾仓”的记载及其百年探寻》,中共金塔县委等编《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第520-526页;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汉武边塞与西域屯田——轮台、渠犁屯田考古发现初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54-166页。。在这一结论基础上,我们需要重新确定卑鞮侯井也即都护井的位置①前人学者们大多接受了《魏略·西戎传》记载的都护井也即卑鞮侯井在玉门关以西的设定,因此多将这一井渠比勘为西汉玉门关 (小方盘城)以西的榆树泉盆地。但在玉门关可能发生东移的情况下,有必要再对这一井渠所在位置重新进行考量。。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大井泽,东西卅里,南北廿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汉书·西域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讨昆弥,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因号其泽曰大井泽。②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页。
这条记载表明西汉的卑鞮侯井,即孟康所谓“大井六通渠”之地,也即都护井,在唐朝被称为“大井泽”,其位置在沙州城 (敦煌城)北十五里,处于西汉玉门关 (小方盘城)以东。这就表明《魏略·西戎传》记载的“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中的玉门关与西汉玉门关相比位置已经向东转移。即到鱼豢著《魏略》的曹魏时期,玉门关应当已东移到冥安县位置。如此方能符合都护井 (卑鞮侯井)在玉门关以西的记载。至于都护井向西“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也不难理解,敦煌以西、以北地区很多都是戈壁荒漠、盐碱地,三陇沙很可能就是都护井以西一个比较典型的沙丘地区③《西河旧事》据考是东晋时期撰成,其文曰:“流沙积在玉门关外,有三断石,极大,呼为三陇。”(参见屈直敏《〈西河旧事〉考略》,《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150-163页。)此时的玉门关应指东移后的西玉门关,则三陇沙应该是因这一沙丘区拥有极大之“三断石”而得名。这或许是敦煌城西北方位,西汉玉门关内的某处盐碱地因被风割成一条条沙丘,而且从这条记载来看三陇沙实际是一块比较小的区域,它仅仅特指“三断石”所在及周边地区,而非很多学者认为它是库木塔格沙漠那样广阔的一片区域。根据本书编委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记载敦煌:“党河两岸及南湖为绿洲,周围多流沙,疏勒河终端多盐沼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6页。)可见古代敦煌城所在的绿洲周边多有流沙,出现“三陇沙”这种地貌不足为奇。,时人以此作为地标。居卢訾仓大致就在三陇沙地区以北或者西北的位置。沙西井应当就是西行路上一处取水点,而“过龙堆”就是过白龙堆。孟康的注表明卑鞮侯井,“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说明卑鞮侯井修渠通到白龙堆以东的某一土山的山下位置。这里的白龙堆应当是指整个罗布泊沙漠,也即指罗布泊至西汉玉门关之间的这片区域④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33页。。《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⑤[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汉哀帝建平四年 (前3)扬雄上书称:“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踰白龙堆而寇西边哉?”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16页。这两条记载表明敦煌郡西境与白龙堆沙漠相接,也即西汉玉门关大致就是白龙堆沙漠的西界。又,敦煌文书《寿昌县地境》记载唐寿昌县:“龙堆泉,县南五里。……今验池南有土堆,有似龙头,故号为龙堆泉。”⑦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0-61页。龙堆泉在汉时与玉门关、阳关皆属龙勒县地域,它的命名很可能就与其地理位置邻近白龙堆相关⑧《汉书·匈奴传下》颜师古注:“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观点。此前很多学者认为白龙堆仅仅是指罗布泊东部、东北部的沙漠地区,实则是缩小了白龙堆范围,这显然是将三陇沙定位在西汉玉门关以西且夸大了其范围而致误。否则罗布泊沙漠内何以出现土山?即便存在,也很难想象辛武贤能够将敦煌城北十五里的卑鞮侯井渠工程修筑至数百公里外的罗布泊沙漠之内,且不论自然条件恶劣,工程难以推进,单凭卑鞮侯井属于居卢訾仓的配套工程,是在为攻打乌孙作战前准备,就不难判断辛武贤不可能耗费如此巨大人力、时间去完成一项通到罗布泊沙漠之内的浩大工程。这样一来,进行一项短期注定无法完工的工程,岂非很容易会耽误出兵乌孙的时机?由此判断居卢訾仓和三陇沙都在西汉玉门关塞内,三陇沙在敦煌城西位置,位于三陇沙北头的居卢訾仓当在敦煌城西北位置,也即是在罗布泊沙漠以东,西汉玉门关附近或以东的位置,它处在距卑鞮侯井不太远而能够通渠抵达的地方。如此,辛武贤方能在短期内完成这项水渠灌溉工程及居卢訾仓城的建设工程,实现“通渠转谷,积居庐仓”的目标,进而能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完成战前准备工作,不会错过出兵乌孙,干涉其王位归属的时机。
此外,《汉书·西域传》记载:“破羌将军不出塞。”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7页。《汉书·赵充国传》亦称:“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5页。这个“塞”应指玉门关,所谓“不出”即指不出汉塞玉门关作战。这表明破羌将军辛武贤进行的通渠转谷、积居卢仓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玉门塞内进行,因此才有不出塞之说。孟凡人主张居卢訾仓位于土垠遗址,不仅不符合《魏略·西戎传》记载的相对位置,还存在三个不合理之处:其一,当时西汉已在罗布泊西岸进行伊循屯田,似无必要在邻近的土垠遗址再修仓库;其二,即便需要再修居卢訾仓,这项工程也应就近由伊循都尉负责,而非远在敦煌的破羌将军负责;其三,自敦煌以北十五里处的卑鞮侯井妄图穿越整个罗布泊沙漠向位于罗布泊西岸的土垠遗址修渠无异于天方夜谭,何况分明可就近引罗布泊、孔雀河水,何须舍近求远自敦煌以北引水?这些都说明居卢訾仓不可能位于土垠遗址。另外,位于榆树泉盆地以西、罗布泊以东的说法通过前文考证也可一并排除。
讨论至此,对于居卢訾仓的位置,我们基本可形成三点认识:第一,居卢訾仓处于卑鞮侯井经过通渠能够达到的地方,如此才能符合“通渠转谷”的记载;第二,居卢訾仓是在敦煌郡管辖的范围之内,也即玉门关内,以此才能符合“破羌将军不出塞”还能主持这项工程的条件;第三,居卢訾仓位于卑鞮侯井以西,卑鞮侯井本身位于敦煌城以北十五里处,以此推知居卢訾仓位于敦煌城西偏北或西北方位。目前在敦煌境内发现的汉代遗址中,仅有位于西汉玉门关所在的小方盘城东北方向不远处的大方盘城符合以上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大方盘城应即西汉居卢訾仓城遗址。
三、敦煌修筑居卢訾仓城与漕运工程
居卢訾仓工程属于系统工程,其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修建居卢訾仓城,第二是开凿通往居卢訾仓城的水上运输渠道。其中工程量最大的不是居卢訾仓城的修筑,而是水上运输渠道的开通。
敦煌大致从元鼎六年 (前111)置郡伊始就开始进行水利灌溉工程的修筑,根据敦煌文书记载马圈口堤堰等都是这个时期修筑的①郑炳林、张静怡《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3-13页。,又据悬泉汉简记载西汉敦煌郡还修筑了很多水利工程,并且设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的管理机构,为了敦煌水利工程修筑顺利发展,西汉政府派遣河津都尉巡视,解决水利工程中的问题。可以说敦煌的水渠基本上都是西汉时期开凿的,西汉敦煌郡具有开凿漕渠的能力和经验②郑炳林、许程诺《西汉敦煌郡水利灌溉系统研究》,待刊稿。。这些水利建设经验为居卢訾仓水道运输工程修建准备了条件,保障了敦煌郡居卢訾仓的修建和漕渠的开凿。
“穿卑鞮侯井以西”水利工程是以穿卑鞮侯井为起点,姑且称之为“卑鞮侯井工程”。李正宇疑作“大通渠”,并对此进行过考证:
颇疑所谓“大通渠”,不过是从敦煌向北开渠,穿过大井泽,北入疏勒河一段而已。这一段不过五十余里,既入疏勒河后,可就疏勒河道略加疏通。而西抵“白龙堆东土山下”。如此,省工省时而易办。今见卌里泽中有苦沟一道北趋,或即其遗迹。若此,则孟康注与当年之工程量、民力及地理形势皆可相合而无抵牾。③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76页。
这一考证结果结合实地考察,将疏勒河、党河的地理形势与《汉书·西域传》、孟康注乃至敦煌文书P.2005《沙州教督府图经》的记载紧密的结合起来,基本是可以采信的。如此一来卑鞮侯井工程的工程量不会太大,是辛武贤能够短期实现的目标,符合既不耽误出兵乌孙又能完成备战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辛武贤就是想通过修渠的方式将党河与疏勒河道进行连接,借助党河、卑鞮侯井工程及疏通过后的疏勒河将敦煌郡的粮食运送到玉门关附近④《太平广记》沙州黑河条载:“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潴原野。”说明敦煌的党河或疏勒河水道的确是可以通航的。又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卌里泽,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右在州北卌里,中有池水,周回二百步,堪沤麻,众人往还,因以里数为号。大井泽,东西卅里,南北廿里。右在州北十五里。”卌里泽、大井泽皆在敦煌以北。按方位来看,大井泽之外,卌里泽可能也在修渠路线上,则辛武贤修渠时很可能利用了这些天然湖泽,即将大井泽、卌里泽等湖泽进行连接可以更加节省人力与工程量。当然也可能是这些湖泽只是辛武贤修渠留下的遗迹,而非天然湖泽。,以备之后汉军出玉门关讨乌孙取用。同时出于军粮存贮和取用方便的双重考量,辛武贤选择在玉门关以东不远处修筑居卢訾仓 (也即大方盘城)。悬泉汉简中也有关于敦煌修渠及辛武贤的相关记载:
1.□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县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办与,毋忽,如律令。(Ⅱ 90DXT0114④:340A)
2.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Ⅴ 92DXT1311④:82)
3.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曰:穿治渠军猥候丞□、万年、漆光、王充诣校尉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传八百卌四。
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 90DXT0214③:73A)
5.甘露四年六月辛丑,郎中马上使护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为驾一乘传,载从者一人,有请诏。外卅一。
御史大夫万年下谓,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七月癸亥食时西。(Ⅱ 90DXT0115④:34)
6.初元年八月戊子……
御史少史任增诏迎护敦煌塞外穿临渠漕……(Ⅱ 90DXT0115③:463)
悬泉汉简中还有一些相关的简,今不一一罗列。以上仅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六枚简加以论述。通过这些简文内容可知,辛武贤率军抵达敦煌当在甘露二年正月,其出发时间更早,应在甘露元年末①张俊民《汉代西域漕运之渠“海廉渠”再议》,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简牍学研究》第7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4-86页。,与史籍记载恰好相合。辛武贤到敦煌时,随行的还有穿渠校尉。Ⅴ 92DXT1312④:21记载:“穿渠校尉丞惠光私从者杜山羊西”,为了进行卑鞮侯井工程,西汉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校尉来负责。且穿渠校尉下辖有“丞”等属官协助办公。“治渠军猥候丞□、万年、漆光、王充”等也是协助穿渠校尉的。另外,西汉政府还调集了很多外地人员 (包括刑士)到敦煌郡参加工程完成②肩水金关汉简73EJT9:322A亦载:“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所移军司马仁……□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军。”,这些举措足见西汉政府对此次敦煌修渠的重视。
通过这些简文,我们还可以大概形成这样的认识:甘露元年,西汉与乌孙间关系恶化,西汉政府一面派破羌将军辛武贤与穿渠校尉穿渠运粮、修居卢訾仓准备军事征伐;另一面派遣冯夫人前往乌孙进行政治斡旋。汉简记载显示甘露二年四月辛武贤还在敦煌,至十一月似已不见辛武贤。就是说辛武贤很可能在甘露二年四月至十一月间罢军。《汉书·西域传下》云:“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7页。反映的很可能是甘露二年四月冯夫人赴乌孙后,带去了破羌将军辛武贤已经出兵屯于敦煌的消息,于是不久后乌就屠妥协愿称小昆弥,矛盾化解,辛武贤不出塞。但是敦煌修渠的工程并没有因这次危机化解而结束,从简文来看直到初元元年 (前48)修渠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并且水道运输工程已从玉门关塞内延伸到塞外,所谓“塞外漕作仓穿渠”,就是在玉门关之外开凿水渠,修建仓库②我们认为敦煌市博物馆在榆树泉盆地发现的古城,即便可以确定是河仓城,也不太可能修建于李广利征大宛时期。彼时敦煌郡塞外还是以匈奴势力更强,将军储仓库设于塞外安全难以保障,李岩云认为该城“既有湖泊作为天然保护屏障,又有重兵防护”实际难以实现,其错误的将李广利屯兵的玉门关外等同于小方盘城所在,彼时李广利应是屯于敦煌,玉门关尚在敦煌以东而尚未西移。如此,所谓重兵屯于塞外的榆树泉不太可能。因此,我们认为若该古城果真是河仓城,可能修筑于甘露四年及之后的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时期。此时期匈奴式微,西汉控制西域,安全有所保障,且敦煌郡又在塞外穿渠作仓,位于玉门关以西的榆树泉盆地又靠近湖泽,正是穿渠建仓的绝佳之所。。
玉门关塞外有湖泽分布。《寿昌县地境》记载:“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泽迂曲,故以为名。”③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0页。P.5034《沙州地志》记载:“曲泽,东西十三里,南北十五里。右在县西北一百九十里。”④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44页。P.2691《沙州城土境》寿昌县记载:“曲泽,县西北一百九十里。”⑤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40页。玉门关在寿昌县北一百六十里,而曲泽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九十里,根据地望考之,当在今敦煌市榆树泉一带。这一带还有西桐海,P.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潜于西桐海畔,蚁聚云屯,远侦烽烟,即拟为寇。”⑥录文参郑炳林《敦煌本 〈张淮深变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141-155页。西桐海或即曲泽。所谓“穿海”应即指开凿连接西桐海、曲泽等湖泽的水利工程。张俊民研究认为从甘露元年到初年元年 (前53-48)持续进行的是一项国家级的水利工程,漕渠的名称唤作“海廉渠”,位置在敦煌玉门关塞外,大致在新疆境内。得出这种结论的重要前提是汉代之后孟康注文及敦煌卷子将敦煌北部大井泽与卑鞮侯井联系起来,是牵强揣测之词⑦张俊民、贾丽英《西北汉简中“海廉渠”初探》,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93-99页;张俊民《汉代西域漕运之渠“海廉渠”再议》,第74-86页。。由此张氏基本否定了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对辛武贤与大井泽的记载。对此,我们首先认为时隔千年,否定古人记载,尤需慎重。再者,通过现有汉简记载来看,塞外修渠事最早见于甘露四年六月辛丑,在此之前甘露二年辛武贤与穿渠校尉主持的水利工程并无任何记载表明其位置是在塞外,反而有孟康注及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都称辛武贤所修水渠是在敦煌塞内,《汉书·西域传下》的辛武贤“不出塞”也佐证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张氏所谓“海廉渠”工程的确是在敦煌郡塞外进行,但它与居卢訾仓、卑鞮侯井工程并不完全等同,二者或许是一脉相承,是同一项水利工程的不同阶段,即前期是破羌将军辛武贤与穿渠校尉负责修筑居卢訾仓及卑鞮侯井工程,后期敦煌郡的水利修筑从玉门关塞内延伸到塞外,也即所谓“海廉渠”工程。
除在塞外推进“海廉渠”工程外,敦煌郡塞内的穿渠活动也持续进行。Ⅰ 90DXT0116②:117记载:“八月己丑朔庚寅,县泉置啬夫弘移渊泉府,调穿渠卒廿一人。”Ⅴ 92DXT1410③:50记载:“初元三年正月,戍卒省助贫民穿渠冥安名簿”,这两枚简的记载似表明敦煌郡渊泉县、冥安县也是运输水渠经过的地方,进一步推测或许这些水渠也能连接卑鞮侯井水渠,运粮至居卢訾仓。果真如此,则此二县水渠可称得上居卢訾仓运输水渠的东段工程。另外,这些记载还说明直到初元三年敦煌郡的水利工程仍在进行。
通过以上考证来看,居卢訾仓漕运渠道的工程量要远超仓城修建的工程量,因此工程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很多。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对于敦煌郡诸县乃至敦煌以东地区将战略物资输送至玉门关附近的居卢訾仓,甚至玉门关塞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敦煌居卢訾仓归属西域都护府
神爵二年 (一说“三年”),随着匈奴日逐王归附西汉,罢僮仆都尉,西汉设西域都护于西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4页。。西汉派遣冯夫人镇抚乌孙,并将其国一分为二,目的就是维护西汉政府在乌孙的政治地位。毕竟此时期西汉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强大乌孙作为对匈作战的盟国,而是防范乌孙成为破坏西汉在西域统治秩序的隐患。对乌孙分而治之后,西汉政府基本无需再派遣军队征伐西域②甘露元年 (前53)西汉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征乌孙,应当是西域都护单独面对尚未分裂的西域大国——乌孙力有不逮,此后随着乌孙分裂,西域都护在西域的统治愈发从容,基本再无需敦煌发兵支援。,只需更加注重巩固西域都护在西域的政治军事地位,以此保障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在此背景下,敦煌郡居卢訾仓开始纳入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这一时期西域都护府设置不久,西域都护治于乌垒城,其职责为“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4页。。西域地区设置的驻军和屯田机构如车师戊己校尉、渠犂校尉、赤谷校尉④《汉书·西域传下》云:“汉复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三校”应指三校尉。等都属西域都护统管辖,西域都护府及各处屯田机构都需要大量的物资供给,其中很多物资都是经由河西特别是敦煌郡供给,并由交通线路转运到西域地区。
西域都护府成为西汉政府管理西域诸国军事、通使事务的机构,意味着一切军事行动都需经由西域都护进行,曾作为征伐乌孙的军储仓库被设计建造的居卢訾仓,也就理所当然划归西域都护管辖,变成西域都护府在敦煌郡设置的军事物资仓储机构。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记载:
7.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 鸿再拜言鸿□□ (马圈湾57)
8.西域都护领居卢訾仓守司马鸿叩头死罪死罪 (马圈湾95)土垠遗址出土汉简亦载:
9.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别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罗布淖尔15)
这三枚简明确揭示出敦煌居卢訾仓归属西域都护府管理的史实,前二简反映了当时西域都护使下属的“司马”(一说“守司马”)鸿兼领居卢訾仓,后一简则反映出汉成帝河平四年 (前25)居卢訾仓由西域都护府下属的车师戊校兼领。由此来看,西域都护府采取使西域任职的官吏以本官兼领居卢訾仓的方式对居卢訾仓进行管理。其实被划归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不仅只有居卢訾仓,悬泉汉简记载:
10.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九月辛亥日下铺时,临泉译汉受平望马登 (益)。(V 92DXT1310③:67A)
负责鄯善伊循城屯田事务的伊循都尉原本是受敦煌太守节制的,到此时也改由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都护同样使车师己校以本官兼领伊循屯田事务,这与管理居卢訾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表明西域都护府设置后,经历了一个职能扩大、完善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与原本负责西域事务的敦煌郡就有了职能和管辖范围的划分,原属敦煌郡下辖的居卢訾仓与伊循屯田机构应当就是在双方明确彼此职能与分工时被划归给西域都护府管理。
根据悬泉汉简记载来看,甘露四年之后,西汉政府才开始拓展玉门塞外穿渠工程,而在甘露三年几乎没有见到与此工程有关的活动。这似表明西汉政府应当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才最终决定将居卢訾仓正式划归西域都护府统辖。即西汉政府对居卢訾仓的定位开始由过去供应破羌将军及自敦煌出征之汉军的军备仓库转变成为专门供应西域都护府的军备物资储存、转运仓库,其主要职责应是将内地发往西域地区的物资集中于敦煌,然后经水道先转运至居卢訾仓,再经居卢訾仓转运至西域地区。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乌孙征伐行动取消后,与居卢訾仓配套的穿渠工程不仅没有彻底宣告结束,反而在甘露四年开始将水渠工程延伸至玉门关塞外。其原因无外乎是西域都护府力图尽可能的延长水路运输线路,以期进一步方便物资运输。由此可进一步推测约在甘露四年①从工程进度看,甘露四年的居卢訾仓已没有理由针对乌孙用兵进行通渠转谷,应是此时已转而为其他机构转运物资,这个机构就是西域都护府,因为敦煌郡塞外的事务都由西域都护府管辖。西汉政府已将居卢訾仓划归给西域都护府使用,西域都护府在接手居卢訾仓的同时,很可能选择了继续推进居卢訾仓的水道配套工程。辛武贤主持居卢訾仓工程仅仅一年,很难彻底完成与之配套的水道工程。因此甘露四年后敦煌郡境内的部分水渠修筑及塞外穿渠(即所谓“海廉渠”工程)等后续工程很可能都是在西域都护主持下,或是在西域都护与敦煌太守共同主持下完成的。乃至居卢訾仓以东的卑鞮侯井水道之后被称为“都护井”,很可能即指这项水利工程的后续工作由西域都护主持或参与完成。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卑鞮侯井水道的主要用途变为供应居卢訾仓也即供应西域都护府及西域各处屯田所需物资,所以后世将其称为“都护井”。
敦煌郡居卢訾仓改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之后,在西汉政府治理西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土垠出土汉简记载,到西汉成帝元延五年 (前8,实为绥和元年)居卢訾仓还在继续使用①罗布淖尔17简记载:“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出□尉临居卢訾仓以己卯即日到守。”。《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又表明直到曹魏时期,居卢訾仓仍然是敦煌通西域中道的必经之地。由于史籍记载的匮乏,致使很长时期内人们对其认识不足,西域与敦煌汉简的记载将尘封两千年的居卢訾仓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对居卢訾仓的探讨可以清楚看出敦煌郡在西汉经营管理西域过程中的基地作用,以及在西域都护府设置后的管辖范围扩大、明确的过程中对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