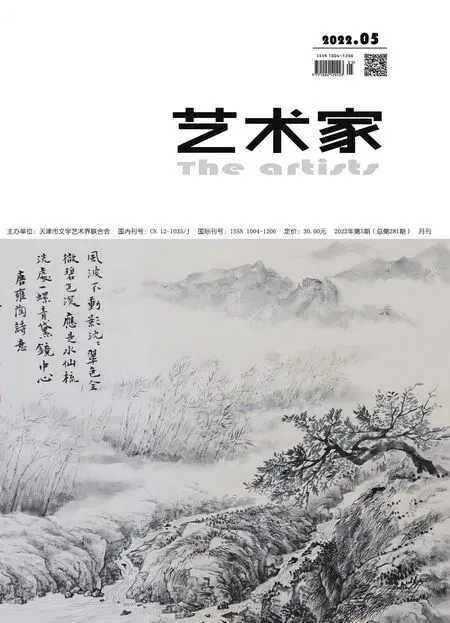回顾与思考云南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发展历史中的红色印迹
□张馨月
(张馨月/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傈僳族是讲究传统与国家认同感的民族。发展至今,傈僳族千年来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传承着自己民族的传统舞蹈艺术文化,坚守着傈僳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使傈僳传统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历史发展的峥嵘岁月,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源与流变
傈僳族是云南15 个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历史悠久,但命运坎坷。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傈僳族受战争冲突、民族压迫及生产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迁徙动荡、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傈僳族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傈僳族以鲜活生动的舞蹈和服饰为载体,其舞蹈文化与传统礼仪和习俗紧密联系,深刻影响着傈僳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
(一)发源
就民间舞蹈而言,它是人民群众直接从他们生活的需求和生活的内容出发的艺术创造,最贴近生活,接近群众,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最强烈、最直接的表露。傈僳族民间舞蹈产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中,在歌舞技巧和风格上有着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较高的观赏、参与和体验价值。傈僳族民间舞蹈多是集体舞,主要有“阿尺木刮”(同乐村)、“二十四脚锅庄舞”“三弦舞”(龙陵县)、“葫芦笙舞”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舞蹈是“阿尺木刮”。发源于傈僳族人民模拟山羊习性动作而创作的“阿尺木刮”,其舞姿生动形象、情绪欢乐热情,富于变化,充分表现了傈僳族人民对山羊的喜爱以及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保留了浑厚古朴的原始艺术风格和特色。傈僳族人民居住在崇山峻岭、斗岩峭壁的环境中,经过了无数次迁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傈僳族人民常用山羊皮制成的羊皮褂来抵御风寒、遮风挡雨,以羊肉充饥。对傈僳族人民来讲,山羊是其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其对山羊有一定的敬重心理。傈僳族把山羊叫作“阿尺”。所以,模仿山羊跳的舞叫“阿尺木刮”,即山羊舞蹈,这是傈僳族古老的羊图腾舞蹈,起源于叶枝同乐一带。“阿尺木刮”的跳法种类极多,动作及声音都明显在模仿山羊及游牧生活中的一些事,具有浓厚的原始性和自然性。它采用音乐和舞蹈结合的形式,讲述了傈僳族漫长的发展历程,表达了傈僳族人民热爱大自然、向往幸福生活的质朴情感。“阿尺木刮”就是一部包罗了傈僳族历史文化的“活字典”,于2006 年被收录进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另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为“三弦舞”。“三弦舞”是傈僳族先辈在长期的游牧涉猎、刀耕火种以及与自然环境抗争的过程中,催生的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他们从电闪雷鸣、百鸟鸣叫中受到启迪,从树影婆娑、花草摇曳的婀娜姿态中悟取灵性,慢慢应用三弦、葫芦丝、笛箫及竹口弦等乐器,创作祭祀、狩猎、情爱等主题的歌调,并创作和谐之舞,辈辈相传,代代相承。“三弦舞”(傈僳语叫“刮欠”,意即“打跳”)集歌、舞、乐于一体,伴奏乐器以三弦、口弦、土笛、葫芦丝为主,持乐者起乐慢舞,伴舞者依次加入,沿着逆时针方向绕圈,节奏由慢到快,自由掌控,形式各异,花样繁多,有单圈跳、多圈跳、合脚跳、串花跳、两排对跳及舞罢前的“回头跳”。“三弦舞”的曲调节奏多为“四二拍”或穿插“四三拍”。其舞步特点多为左脚起步,根据曲调节奏,三步一擦靠或搓脚或曲末半步收吸,欢快轻盈。“三弦舞”中的绝大部分思想内涵是健康、丰富和深刻的,集中反映了傈僳族长期演变的历史,是傈僳族人民的“根”,也是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这正是其得以传承且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二)流变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文化交互性加强,新兴文化层出不穷,国外新潮文化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这对傈僳族传统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益于相关扶贫政策的实施,傈僳族的交通闭塞问题得到了缓解。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翻山越岭出入傈僳族村寨,切实地看到隐藏在大山内的傈僳族特色风貌,以及待挖掘与传播的丰富的艺术文化资源。这使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文艺单位等团体有机会来传承与发展该传统艺术文化。2011 年4 月,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非物质遗产进校园活动”邀请“阿尺木刮”传承人李碧清走进课堂,使学生有机会深入感受与了解傈僳族文化的魅力,学习并将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加工与推广。此外,许多专业性舞蹈工作者以傈僳族为创作元素素材,将其编入舞蹈,向大众展示并参与各类舞蹈赛事,逐渐在各地闻名,受到大众的认可与喜爱。如2011 年11 月,在贵阳举行的第八届桃李杯民族民间舞大赛中,舞蹈《阿尺木刮斗嘎来》就荣获佳绩。不仅如此,许多学者将视野转移到傈僳族传统文化,为傈僳族编创对标元素训练教材,探索如何将传统民间艺人的跳法进行改良,使其体系化,增强其训练性与观赏性,从而带入课堂进行教学。
二、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中红色印迹的当下思考
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文化多样性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可转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圆”的概念建构
对于隶属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间舞蹈艺术而言,其伴随着我国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从最初的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战争性舞蹈等带有功能性的舞蹈类别,不断演变发展至今,形成一套完整的跳法套路,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中国精神的红色印迹,体现出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姿态。以傈僳族为例,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傈僳族是一个从历史中一路走来,历经艰难险阻从未中断的民族。他们披荆斩棘,颠沛流离,英勇抵御外敌,骁勇善战,保卫族人领土,保护家园,为了让族人可以生活得更加和谐幸福而顽强拼搏。傈僳族人民凸显的精神,正与革命抗战精神相契合,体现了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反观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它也是随着我国的建设发展而进步。多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拉动了傈僳族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傈僳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他们思想的改变正是通过民间舞蹈艺术这一载体呈现出来。例如,傈僳族的民间舞蹈大多都是采用“圆”的队形、路线调度,如“阿来几”(龙盘旋)、“切勒涡只泼”(旋转磨盘)、“矣然邓”(跳迎宾客)等。在舞蹈表现形式方面,傈僳族民间舞蹈主张群舞形式,男女老少皆可参加表演,期间穿插双人、三人、四人等配合调度,所行进的路线亦是以弧线为主,无不是在体现“圆”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意义建构与艺术呈现,象征着民族一家亲,人人和谐。
(二)经济与民间舞蹈艺术的关系
旅游业的兴起使各地的民族文化得到了推广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进行深度研究,经过对其整理与重构,形成许多带有民族独特文化风貌的艺术作品,成为当下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云南省人民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创设了云南民族村,历经多年建成了26 个少数民族村寨。研究表明,现在民族村内傈僳族歌舞表演是在原来基础上的简化和创新,结合了当下的时代特征,并加入带有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新元素,使傈僳族歌舞更易推广且不丢失内涵。这正是努力将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带出大山、带出村落,逐步推广至全国乃至世界,让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不仅如此,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云南跨境民族特别是傈僳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有利于促进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习俗的各境内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通婚与商贸往来。云南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在与各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频繁往来中,交流和交往变得极其便利,文化的共融也不可避免。全国各界艺术专业人士通过努力,将保护、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传承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创新。傈僳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其文化与境外相近民族有交融和文化渊源,通过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汇出新,能够使跨境民族在与境外同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交往中,顺利实现“走出去”“引进来”,增强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实力与民族自信心,有利于实现民族团结。
(三)场域与民间舞蹈艺术的关系
此外,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场域下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意义。宗晓莲在《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中提出,“场”是不同位置间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和构造。这表明,在不同的场合中,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呈现势必会出现差异,如在民族村落中的自娱自乐的舞蹈表演形式相较于舞蹈教室、艺术剧场、公园广场、旅游景点等,一定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特性。所以,场域的不同会间接对民间舞蹈艺术起到一定的改造与建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这种影响时,不能忽视民间舞蹈艺术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民族村落已不再像以往年代那样条件简陋。这就意味着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文化的表演场所环境也在悄然改变,这导致其表演形式与艺术呈现转型发展。摒弃不合时宜的艺术元素,保留并加入新的艺术元素,再加上各地文化馆的建立,这些都对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各地文化馆更多的工作是探寻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中的精神层面的宝贵资源,将其保护并发扬,对于动作层面则进行一步步地改良与完善,提高其审美观赏性,凸显傈僳族的民族风貌。对此,我们需要正视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中的红色印迹,让民间艺术保持其最纯粹、最真实、最本源的民间特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间舞蹈艺术。
回顾百年,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在不停地对民族进行建设与发展。对于傈僳族这一跨境民族而言,其民族的历史繁杂冗长,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在这条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上,虽经历了艰难险阻,但傈僳族人民始终存有端正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与其他民族像石榴籽一般拥簇在一起。在傈僳族人民朴素的世界观里,民间舞蹈艺术可以直达心灵,给予族人幸福,促进内心世界的健康、和谐,是传递特定精神思想的重要载体,其所蕴含的精神思想与我国主旋律相契合,应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从而让傈僳族民间舞蹈艺术中隐匿的红色印迹进一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