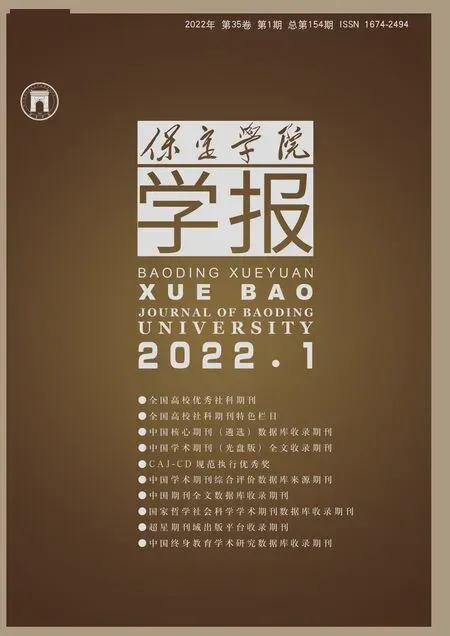清太祖、太宗对金朝皇帝称谓问题考述
——兼论清初二帝对金朝历史的改造
张又天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金朝历史对关外时期的后金(清)君主有着极高的借鉴和利用价值。昭梿《啸亭杂录》论及清太宗读《金世宗本纪》一事,称皇太极“见其(金世宗)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曾御翔凤楼传谕诸王大臣,不许褒衣博带以染汉人习气,凡祭享明堂,必须手自割俎以昭其敬。谆谆数千言,详载圣训”[1]。关于后金(清)君主对金朝历史的认知情况,一些学界前辈围绕着满洲认同这一视角进行了研究,如王锺翰先生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论述“满洲与明代女真的关系问题”时便首先提及了清太宗皇太极对金朝历史的态度[2];姚大力、孙静先生则在《“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中基于清太祖、太宗时期女真人的集体认同意识,对清初二帝的金史观念由“接续金统”向“割裂金统”转变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对于清初二帝借鉴金史的具体方面,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当属沈一民先生的《金朝史实对清初政治的影响》,该文归纳出清太祖、太宗将金朝历史应用于现实的各个方面,包括:论证得到政权的合理性、政权建设、外交活动、训诫满洲贵族等[4]。而邓涛的《清朝皇帝对金朝陵寝的祭祀》则关注到了清太宗皇太极对金朝陵寝的具体祭祀情况[5]。
此外,在《满文原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中所记录的清初二帝对金朝皇帝的称谓以及他们对金朝史实的改造颇能反映出清太祖、太宗时期的统治集团对金朝历史的认知情况和其借助金朝历史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意图。鉴乎此,这两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清初二帝对金朝皇帝的称谓与《金史》所记称谓的差异
除“盗据神器十有二年,罪恶贯盈,天所剿绝”[6]和“身弑国蹙”[7]298而被后来君主废除皇帝身份的海陵庶人完颜亮和卫绍王完颜永济外,元末修成的《金史》对金朝皇帝一般都以庙号来称呼,如金太祖、金太宗、金世宗等,这是《金史》的规范体例。后金(清)前两代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对金朝历史有过论述,但他们(尤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对金朝皇帝的称呼却与《金史》所载大相径庭。
(一)天命时期的金朝皇帝称谓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号为金,宣示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功绩及复兴旧业、独立建国的政治主张[8]。因此,努尔哈赤对存在于12—13世纪的由女真完颜氏所建之金朝的历史十分重视,并常以“先朝”“先金”等称谓来呼之。不过,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统治者对金朝皇帝却常以当时的习惯称谓——年号而非《金史》所惯用的庙号来称呼。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天命六年(1621)后金攻克辽阳(今辽宁辽阳市),明朝御史张铨拒不投降,努尔哈赤“令斩之。四王怜之而不忍杀,乃援古说之曰:‘昔宋徽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尚尔屈膝叩见,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醒耳,何执迷而不屈乎?’”[9]368四王即尚为四贝勒的皇太极。此话虽出自皇太极之口,但反映的也是天命时期的称呼习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清太宗时期纂修,到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经过修改[10],所记内容尚可接近称呼原貌。而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再经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上述四王援古劝降张铨一事中,皇太极对金朝皇帝的称谓则被润色成了庙号:“四贝勒惜铨,尚欲生之。乃援古以晓之曰:‘昔宋之徽钦二帝为金太宗所擒,尚尔屈膝伏谒,受公侯封,吾欲生汝,故为汝开导,汝何坚执不屈耶?’”[11]534当然,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将金太宗称为“天会皇帝”来看,此段史料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修饰,因为努尔哈赤当时并未称帝,他们很可能是以“汗”而非“皇帝”的方式来称呼金朝皇帝的。比勘满文文献可见,与《太祖高皇帝实录》有着密切关系[12]的《满洲实录》汉文部分对金太宗的称呼虽也是“金太宗皇帝”[13],但再观更贴近历史原貌的《满洲实录》满文部分,可发现金太宗实际上被称呼为“julgei aisin i taizung tiyan hvi ujimai han”①本文所引用的满文,均以拉丁字母转写,转写方案采用太清满文转写系统。若遵循标准发音,此段史料所引之吴乞买的名字,应作“uqimai”而非“ujimai”,这是因清初老满文对辅音字母“j”和“q”并无明确区分,而《满洲实录》在书写新满文时又未对原有老满文所记之“ujimai”作出应有调整所致,此处保留文献原貌。(先金的太宗天会吴乞买汗)。若进一步寻找《满文原档》之《张字档》对此事的记载,则可以发现金太宗干脆直接被称为“meni aisin han”[14]51(我们金汗),甚至没有指明此“金汗”究竟为哪位金朝皇帝。因此,《满洲实录》满文部分的“taizung tiyan hvi ujimai”很有可能是在《满文原档》所记之“meni aisin han”的基础上再经添加的②据赵志强先生判断,《张字档》应该是清太宗时期的誊清本,但这与天命时期的皇太极即已用年号来称呼金太宗吴乞买这一事实并不冲突。。综上可见,从“金汗”到“天会吴乞买汗”到“天会皇帝”再到“金太宗”,金朝皇帝的称谓所经历的层层修饰过程略见一斑。
努尔哈赤本人也是直接以年号来称呼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的。据《满文原档》之《张字档》,天命六年五月:
orin nadan de,han birai dergi liodon i bai dahabuha gurun be tuwame,heqenqi tuqike inenggni,ansan i fude isinaqi,gaijoqi aisin tiyan hvi han i ilaqi aniya araha jung benjirebe aqabi③赵志强先生指出:在起初的老满文中,辅音f与元音结合而成的音节可能没有fi。因此,凡用fi处,俱以bi代替。参见赵志强《老满文研究》,载于《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第31~38页。,amasi dutan de wasimbuha bithei gisun:“……ere jung de,tiyan hvi han i ilaqi aniya araha seme henduhebi,tere musei nendehe aisin gurun i aguda mafai deoi da gebu uqimai han,jai tukiyehe gebu tiyan hvi inu……”[14]109-111
(二十七日,汗阅河东辽东之处招降之国人,出城之日至鞍山城,遇自盖州来献金天会汗三年所造之钟者,遂令传谕留守之都堂曰:“……此钟字云:‘天会汗三年造’,是咱们先金国的先祖阿骨打之弟,本名吴乞买汗,另有尊号曰天会……”)显然,此钟所刻之“天会汗三年造”并非实际的字样。首先,金朝皇帝并不称汗,因而不会将“汗”字铸刻在钟上,这可能是因努尔哈赤按照自身认知将“皇帝”翻译为“汗”所致。其次,将“汗”字置于“天会”和“某年”之间书写也并非金朝铸钟铭刻字样的规范,其规范形式应当是直接铭刻“年号”+“年份”,如“天眷元年岁次戊午”即可①参见郑国平、阎雅梅《吉县安平村天眷元年三月八日所铸铁钟》,《文物世界》,2011年第1期。其他金代铁钟可见王福谆《“我国古代大型铁铸文物”系列文章之五——古代大铁钟》,《铸造设备研究》,2007年第3期。。即使此钟确实存在,也很有可能是档案记录者按照惯用称呼在年号后顺手添加了“han”的字样②《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收有《金国汗致李喇嘛书稿》一文,此段文字被译入《满文原档·天字档》,但《天字档》所涉及的金朝皇帝称谓在《书稿》的基础上增加了“han(汗)”一词。另观《满文原档》,但凡涉及金朝皇帝称谓(即使是年号),均会在此称谓后增加“han(汗)”的字样,而《明清史料》所收文稿则均无“皇帝”“可汗”类似的字样。有理由推断此乃满文档案抄录者的习惯行为。。
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原档》等较为原始的文献、档案中,努尔哈赤对金世宗和金章宗这两位金朝鼎盛时期在位的皇帝也是以年号来称呼的,如:“昔先金大定帝时,有朝鲜官赵惟忠,以四十余城叛附”[9]351、“昔定帝(应为“昔大定帝”——引者注)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9]392、“taihoo han i ningguqi aniya sunja biyade,monggo guruni ejen temujin gingjo hoton de hengkileme alban benjirebe alime gaisu seme aisin taihoo han ini eshen yongji gebungge wang be unggihe sere.”[15]350(泰和汗六年五月,蒙古国主铁木真赴净州朝贡,金泰和汗派其叔父——名为永济的王前往受之。)以上几则实例在《金史》中都可找到相应记载,但与按照古代王朝的传统体例进行书写的《金史》所不同的是,努尔哈赤几乎是全盘地以年号来称呼金朝皇帝的。这种称呼方式与当时盛行的以年号称呼帝王的方式较为一致,努尔哈赤曾多次赴明朝朝贡[16],又同西边的蒙古部落保持着文化交流,故能接触到的皇帝称谓当是以年号的形式呈现的。
不过,天命六年至天命七年(1622)间成文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以下简称《檄文》)反映出《金史》这部史籍已经影响到后金的政治活动。对此,乔治忠先生进行了详细的考析与解读[17],该《檄文》历数古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十九个事迹,其中的七例都涉及到了金朝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檄文》对金朝帝王基本都以庙号来称呼,包括“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金世宗”“金章宗”等[18]292-294。实际上,这篇檄文很有可能是出自努尔哈赤阵下的汉人之手,其文引经据典、博古通今,全篇渗透着儒家的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思想,与同时期出自努尔哈赤之口的质朴、直白语言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檄文》作者不但熟悉历朝历代的兴衰事迹,还对《金史》的文本情况了如指掌。如《檄文》所称:“又观我国史书,金太祖三世熙宗皇帝时,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寝内,烧帏幔。又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飏十数里,死伤数百人。”[18]293与《金史·熙宗纪》皇统九年(1149)四月壬申条所记几乎一字不差,明显是参照了《金史》[7]86。再如《檄文》记述海陵王“又召葛王乌禄妻乌林答氏,乌林答氏谓乌禄曰:‘我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乡自杀”[18]293。这也与《金史》后妃传所记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檄文》但凡论及有关女真先民的史事,往往在前面加上“观我国史书”的字样,如“又观我国史书,有阿古打及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辽主猎,能呼鹿制虎,搏熊放鹰”[18]292。但实际上,这则文字是参考了《辽史》的记载:“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19]故“我国史书”并非仅就《金史》而言,而是泛指记述明末女真先民事迹的众多史籍,此处,努尔哈赤借助历史为自身政权追寻正统的意图十分明显,与后文之“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18]295一语可谓相映成趣。总之,基本上可以认为,此《檄文》是秉承着努尔哈赤对待明朝的态度,再由熟悉中原典故的文士参照后金所掌握的汉文典籍创作而成,这也是这篇《檄文》基本采用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努尔哈赤本人已经使用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
从努尔哈赤口中说出金朝皇帝的庙号,需在康熙年间纂修并在之后屡经修改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寻找,努尔哈赤对侍臣说:
为臣者,若临事之时,不能勤敏恪慎、殚心厥职,岂君之任臣止为汝一身富贵耶?观此则君于天锡基业,敬以承之,举忠良,斥奸佞,日与大臣讲明治道,以致皇天眷佑、人民悦服。如古所称尧舜禹汤文武,以及金世宗诸令主休誉著当时,鸿名传后世。孰有善于此耶?[11]503
此话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无法找到(在《武皇帝实录》中也无法找到任何用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的记载)。观其文风,这段文字也很像是到了康熙以后才重新润色增入的。正如王静芳经过对比后所得出的结论:“《高皇帝实录》的内容比较全面,但湮没事实真相及对努尔哈赤的赞誉之词很多,而《武皇帝实录》的语言虽较为古朴,但记载的大部分史事都真实可信。”[20]
(二)清太宗对金朝皇帝称呼的新变化
清太宗皇太极对金朝历史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乃父,其对金朝皇帝的称呼方式较太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第一次入关,便派遣阿巴泰、萨哈廉赴房山祭拜金太祖和金世宗,祭文称“满洲国皇帝谨以太牢少牢庶羞之仪。致祭于大金太祖完颜旻、大定完颜雍皇帝神位前”[21]655,可见太宗是以庙号称金太祖、以年号称金世宗的。这段史料所涉及的人物称谓较为奇怪,首先太宗所自称的“满洲国皇帝”明系日后修饰所致,而“完颜旻”“完颜雍”则分别是金太祖、金世宗的汉名,不太像是皇太极所能够了解到的。检视《满文原档》之《秋字档》所记祭词,则可发现皇太极对这两位皇帝的称呼实际上是“amba aisin i taisu u iuwan daiding uwen han”[22]375(大金的太祖武元、大定文汗)。为何在较原始的《满文原档》中对金太祖是以庙号加谥号的组合进行称呼的呢?这可能与“太祖武元皇帝”自宋金到元明早已成为金太祖的习惯称呼有关。如明初姚广孝就曾以“金太祖武元帝陵”[23]为题创作诗词。此外,金世宗“尊谥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7]203,皇太极称金世宗为“文汗”(即文皇帝)或意在将世宗之文与太祖之武并举,以表敬意①皇太极对金朝皇帝的态度还表现为他在祭文中直书自己的本名“hong taiji”。参见《秋字档》,第375页。。到崇德年间,皇太极还是会用年号来称呼金朝皇帝:“历考辽金元之主。皆未有如大定帝者,故后世以尧舜为比。”[21]1214
不过,在天聪元年(1626)四月皇太极致李喇嘛的文书中,皇太极对于金朝皇帝的称呼已与上述“年号称呼法”不同,据《满文原档》之《天字档》:
dailio tiyan zo han umai uilen aku,aisin taisu han be waki sebi dain ohobi,aisin jangsung han umai uilen aku,monggoi taisu han be waki sebi dain ohobi.[22]46
(大辽天祚汗无罪欲杀金太祖汗,启兵端;金章宗汗无罪欲杀蒙古太祖汗,启兵端。)可见,即使在满文档案中,也已然出现了以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的现象,这种称呼差异或许与话语接受者的身份为明人有关。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特地登上翔凤楼,命内弘文院大臣向亲王、贝勒、大臣读《金世宗本纪》并向大家训谕,对金朝皇帝也是以《金史》的标准——庙号来称呼:“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21]977此后,清太宗提及金朝皇帝常以庙号呼之,如“昔金太祖阿骨打、太宗乌奇迈时,兄弟同心和睦”[24],“又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21]1019可见,由天聪入崇德,皇太极对金朝皇帝的称呼有着一个变化过程,这与《金史》的翻译以及皇太极对《金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质言之,清太祖努尔哈赤论及金朝皇帝,往往以“金汗”这样的泛称或者是以“年号”+“汗”来进行称呼,这与他对明朝皇帝的称呼一致。其原因是努尔哈赤自己是为金国大汗而非皇帝,以其对中原文化的了解程度,恐怕也难以熟知庙号这样的概念(清代的庙号制度待崇德年间方始建立)。无独有偶,约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前成书的《黄金史纲》所反映出的明末的蒙古人对明朝皇帝的称谓也是如此,《黄金史纲》在叙述“乌哈噶图可汗(即元顺帝)”丧失大都后,所涉及的明朝皇帝称谓,自洪武直至天启等16位皇帝均为年号而非庙号[25]。这反映出明末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基于自身的政权结构和文化状况等因素,易于接受年号这样的称谓概念。此种情况也与明朝基本实行“一帝一年号”制而使得以年号来称呼皇帝的方法得到传播有关,努尔哈赤所居之地近于明边,努尔哈赤可以接触到的皇帝称谓,其来源途径无非明朝中下层官吏、民间汉人以及西边的蒙古,此三者都影响到了清太祖的皇帝称谓方式。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依然广泛使用“年号称呼法”,即使他已经开始在对明文书中使用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但这种称呼的影响力还是不应被高估的,直到崇德年间太宗称帝并深入了解金史后,方开始大量使用庙号来称呼金朝皇帝。
二、清太祖、太宗对金朝历史的改造
以年号来称呼金朝皇帝的方式反映出清太祖、太宗(至少是天聪时期的太宗)对《金史》了解尚浅,也意味着出自清太祖、太宗之口的金朝历史与《金史》所载之金朝历史常有出入。清初二帝对金朝历史的这种改造是他们对金朝史实缺乏深入了解和刻意误用以服务自身政权这两个因素共同交织产生的结果。
(一)清太祖对金朝历史的改造
萨尔浒战役,后金获胜。努尔哈赤在致朝鲜的国书中言道:“先朝大金帝、蒙古帝并三四国,总归于一,虽如此,亦未得悠久于世,吾亦知之,今动干戈,非吾愚昧,因大明欺凌无奈,故兴此兵。”[9]351事实上,金朝并没有像元朝一样实现一统,而是与宋朝南北分治。努尔哈赤此语若非对金史了解甚浅,则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然建号为金,而需要抬高历史上的金朝所取得的成就,最终达到为后金造势的目的。努尔哈赤在国书中还谈到了后金与朝鲜间过往的一段纠葛:“昔先金大定帝时,有朝鲜官赵惟忠,以四十余城叛附,帝曰:吾征徽钦二帝时,尔朝鲜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国也,遂不纳。”[9]351此事可见于《金史》的《世宗纪》《纥石烈良弼传》及《高丽传》中。但实际上,《金史》对此事的记载与努尔哈赤所言大不相同。首先,赵惟忠的真实姓名为赵位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写,极有可能是因为汉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按照人名的发音翻译而来。崇德年间被提及的在“先金”历史上能够以女真、汉语分别审问女真人和汉人的“元王马大郭”[21]1019也是同样的道理,此人是《金史》中的原王麻达葛[7]190,即后来继位的金章宗。其次,金世宗拒绝赵位宠以四十余城叛附的理由也绝非高丽于金宋战争中保持中立,据《金史·高丽传》记载:
(大定)十五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晧,遣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上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宠辄敢称兵为乱,且欲纳土,朕怀抚万邦,岂助叛臣为虐。”诏执徐彦等送高丽。[7]2887
由此观之,努尔哈赤对此事的了解可能仅限于“赵位宠以四十余城叛附”。他将在金宋战争中高丽保持中立的态度①金军灭北宋之役,高丽对双方的政治态度较为复杂。高丽已然在丙午年(1126年)四月“丁未,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却在七月宋朝派侯章等人来使求援时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先是大言“言念小藩,世蒙厚德,常愿尽忠于报上,岂能无意于勤王”,又以“但为弊封,本非胜国,近经灾孽,焚尽畜藏”为说辞,欲待宋军稍有作为方才出兵。参见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1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3、447页。故高丽在此战保持中立实是因其采取虚与委蛇的外交策略所致。附会于金世宗之口,可以使后金的现实情况与“先金”历史嫁接起来,其深层目的则是论证后金与朝鲜间“吾二国原无仇隙”的关系,以图削弱朝鲜作为第三方势力在后金与明朝对峙关系中的助明倾向。
若再结合此前的一段史实来观察,便可更清晰地窥见努尔哈赤此项意图。据《满文原档》之《昃字档》,天命三年(1618)四月:
tere yamji,han gisureme monggo gurun i beile enggederi gebungge hojihon sahalqa gurun i amban sahaliyan i gebungge hojihon i baru julgei aisin han i banjiha koolibe alabi,jai hendume julgeqi ebsi banjiha.han beisei koolibe tuwaqi,beye suilame dailanduha gojime,yaka enteheme akvmbume han tehengge inu aku,te bi ere dain be deribuhengge,han i sorimbe bahaki,enteheme banjimbi seme deribuhengge waka,ere nikan i wali han mimbe korsobuha ambula obi,bi doosoraku dain deribuhe seme hendubi.[15]169
(此夜,汗向蒙古国贝勒恩格德尔额驸、萨哈尔察国的大臣萨哈连额驸讲述先金汗的往事。又言道:“观自古以来汗、贝勒故事,虽劳苦征战,未有永居汗位者,今我兴此战,非欲获得汗位而永居之,只因汉人的万历汗构怨于我,我无可忍耐而兴兵。”)
可见,清太祖所言之往事,仅仅是凭其记忆对金朝的历史兴衰作了简单回顾。此外,倾听努尔哈赤讲史的二人的身份也很特殊,恩格德尔是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首领,曾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史书中对萨哈连的详细身份语焉不详,金鑫先生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指出,此人即天命三年,趁乱脱离蒙古扎噜特部,转投后金的萨哈尔察部头目萨哈连[26]。努尔哈赤专对此二人讲授金史,其目的是将建号不久的金国同历史上的金朝接续起来,提升其政权的合法性,并结合金朝的兴衰历史,宣扬后金伐明动机的正当性,以巩固并加强伐明阵营的军事力量。
努尔哈赤晚年还对诸贝勒进行训谕:
昔定帝(应为“昔大定帝”——引者注)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9]392
从这则记载可见,努尔哈赤对此事的了解较为粗略。实际上,金世宗并非自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出发,而是从当时的中都(今北京市)返回故都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努尔哈赤引用此语意在告诫诸子励精图治,“不坠父业”[7]186。至于具体的地理细节以及金朝在宣宗时期才将首都自中都(今北京市)迁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史实则并非是他所要深究的问题。
综上,努尔哈赤所言之金朝历史只是事件的大致轮廓,但具体细节较为失真,如上述赵位宠以四十余城欲归附金朝以及金世宗在前往上京之前对太子的训言等具体信息都与《金史》所载相同。这种信息当有所凭据,很有可能是由努尔哈赤手下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讲官参照《金史》向其口授所致,这种讲授的目的仅在于传播历史大略,而非历史细节。当金代历史被努尔哈赤这位马上君王再次讲述出来时,其事件的真实性则会进一步打折扣。
(二)清太宗对金朝历史的改造
与其父相比,皇太极对待金朝历史的最大特点便是不再刻意强调,甚至是直接否认后金政权与金朝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皇太极的这种意识早在其继位之初致袁崇焕的国书中就有所体现:“aisin jangsung han umai uilen aku,monggoi taisu han be waki sebi dain ohobi.”[22]46(金章宗汗无罪欲杀蒙古太祖汗,启兵端。)此语并无任何为金章宗回护的意味,可见,皇太极从一开始就并非坚定地站在金朝的立场上论史。皇太极此超然立场还可见于其对部下的训言,据《满文原档》之《余字档》,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对诸将说:
julge aisin han nikan be dailara de,nikan i zungze gebungge amban aisin be juwan ilan jergi gidaha bi,nikan i emu amban qouha dame jifi afaki sere jaka de,heqen tuwakiyaha amban hendume,ere ninggun biya i halhun de,fusheki jafafi sebderi de teqi geli halhun kai,uksin saqa etufi geli adarame afambi seme hendure jaka de,tere gisun de qouhai niyalma afara mujilen aku ofi gemu samsihabi,emu gisun ehei turgunde,tere heqen be aisin bahabi,amin beile yung ping de tefi,musei qouhai niyalma be ehe ere qouha geli bata be wame mutembio seme henduhebi,beile tuttu henduqi,qouha niyalmai mujilen uwe buqeme afaki sembi.[27]410-411
(昔日金汗与汉人作战时,汉人中名为宗泽的大臣曾击败金兵十三次。汉人一官率兵来援,欲战。守城官曰:“值此六月之暑,挥扇坐于阴凉处尚热,如何披甲作战?”云云。士兵听闻此语,毫无战意,靡不逃散,以此一恶言之故,该城为金所得。阿敏贝勒坐镇永平时,曾言咱们的士兵力弱,能杀敌否?贝勒若言呼此,士兵孰有死战之心?)
皇太极将宋金战争中削弱全军士气的守将与丢弃永平城的贝勒阿敏比附,这就形成了以明朝对应金朝、以后金对应宋朝的略显“倒错”的王朝对应观念。可见,皇太极并不执着于站在金朝的立场上,将其作为后金的“先朝”而论史。随后,皇太极更是在致祖大寿的文书中公然割裂了其自身与金朝之间的关系:“daiming han sung han i hvqihin(应系“hvnqihin”一词的不规范写法——引者注,后同)waka,be geli nendehe aisin han i hvqihin waka.”[27]440(明汗非宋汗之后裔,我们也非先金汗之后裔。)姚大力、孙静认为,持此种立场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宋金敌对的历史记忆不利于皇太极与明朝相处或是取而代之进行统治[3]。很显然,此时金朝历史对皇太极更多的意义在于将其合理利用,从而获得更多的外交话语权。所以,当致书的对象变为朝鲜后,皇太极对待后金与金朝的顺承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番说辞,据《太宗文皇帝实录》:“瓦尔喀与我,俱居女直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原系我国人民也。”[21]781姚念慈先生指出,这段文字系康熙末年重新润饰之结果[28],其原始文本应作:“瓦尔喀与我,原系女直国大金之后。”[29]后者的文义更为直白,坦言后金之于金朝的延续性。由此观之,当现实利益需要时,皇太极便可以重新解释金朝历史,使后金成为金朝政治遗产之合法继承人。
如果说其父努尔哈赤还秉持着“独尊金朝”的态度的话,皇太极已经更多地将后金(清)政权纳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王朝谱系的延长线上,强调辽、金、元三个政权的连续性以及后金(清)对其接续的正统性。在这个过程中,皇太极还是会对历史进行新的运用:“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21]944观皇太极之意,只是为了论述辽、金、元三朝各自兴起于不同的方位而建立帝业,故而必须在地理分野上将三者区分开来。皇太极如此论史,其目的仍是以此来论证后金也可以同辽、金、元一样,获得帝位乃至“进取中原、速成大业”[30]。1636年,皇太极建号大清,改元崇德,也是其日渐增长的与明朝争夺正统的政治目的的结果。对此,萧一山指出:“大清改号,史书不详其所由,据当时之情形推测之,可知由于对明关系。”[31]在史观方面,将太祖时期“独尊金朝”的立场改为“辽金元并尊”也是这种政治态度所呈现出的一个表征。
崇德以降,皇太极仍然借助其对金朝往事的重新解读来为清朝造势,崇德七年(1642)三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朕蒙皇天眷顾,昔时金国所属,尽为我有。沿海一带,自东北以迄西北,至使犬、使鹿、产黑狐黑貂等国,及厄鲁特国,在在臣服,元裔、朝鲜,悉入版图。”[21]1378实际上,这段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金朝的势力范围深入中原,其疆域“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7]549。此时的清朝却仅仅局限于关外一隅,纵使皇太极对金史不甚了解,也不至如此不懂金史常识。何况,同年五月皇太极在致朝鲜的敕谕中就直言道:“昔大金不尝抚有中原乎?盛衰有时,具载史册。”[21]1410可见皇太极对金史的叙述并不在于其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在于向诸王、贝勒强调乃至夸大清朝所取得的版图成绩,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向臣民们宣告,清政权的国势已是蒸蒸日上,清朝终有一日会实现进入乃至统治中原的政治愿望。
与天命时期相比,皇太极在位时期的后金(清)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内在而言,皇太极通过各种手段促使后金(清)政权的上层权力结构向君主集权大幅度迈进;外在而言,太宗在位期间后金(清)国力的迅速膨胀使得其与明朝之间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蒙古各部和汉人的大量投附。因此,面对辽、金、元三史,清太宗相较于乃父有着更为开阔的眼界,仅申明金史的重要性或是宣扬“先金”政权的历史记忆实质上仍是片面强调女真(满洲)的内在凝聚力,在皇太极时期,女真(满洲)的内在凝聚力早已达到了一个相对高且稳定的水平,而在史观上将辽、金、元三史并重则可将依附后金(清)政权的其他民族纳入进来,实行更有效的统治。此外,皇太极的这种历史观念也表达出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与明朝相抗衡的北方王朝。不过,在国力大增、各部族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对女真(满洲)自身能否保持凝聚力、竞争力的担忧也同样困扰着皇太极,于是他命大臣翻译辽、金、元三史并向群臣宣讲金世宗保持女真旧俗的“光辉传统”,这种举措当然不是在史观上向天命时期进行倒退,而应被视为皇太极面对新形势下隐藏危机的应对策略,与金世宗、清高宗在面对女真人、满洲人大幅度汉化的局面下千方百计地提倡“国语”“骑射”的政治举措大有合辙之处。
结语
在清朝的官修史书《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清朝的创业之君——清太祖努尔哈赤往往会使用标准的“庙号称呼法”来指称金朝皇帝,若比勘更为原始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满文部分及《满文原档》等文献,可以发现努尔哈赤实际上是延续了明朝以来大行其道的以年号来称呼皇帝的传统,这进而影响到他们对金朝皇帝的称呼。至少到天聪时期,这种“年号称呼法”仍然较有影响力。从《满文原档》到《太祖高皇帝实录》及《太宗文皇帝实录》,清初二帝对金朝皇帝称呼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到“雅驯”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出了清初二帝自我身份的转变——从金国汗王到清朝皇帝。
太祖、太宗创业初年,对金朝皇帝辄以“年号”+“汗”呼之,这暗示出清初两位君主对金朝历史的了解途径可能并非是亲自阅读元末修成的《金史》,或者说,清初二帝是将其对金朝历史的有限了解,选择了符合当时表达习惯的称呼方式。总之,清太祖、太宗口中所言之金朝历史,与《金史》所载之历史有着一定的差异。不过,这种史实性错误并不是清初二帝所真正在意的,他们的目的是借助金朝历史来服务于自身政权,达到对内增加威望、对外扩张声势的双重目的,因此,金史知识的欠缺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共同促成了清初二帝对金朝历史的改造。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号为金,意在以此国号来凝聚明末女真人,故而时常谈及金朝历史,来强调后金政权与历史上金朝的连续性,带有明显的继承、复兴金朝正统的意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在位时期的内外形势相较于努尔哈赤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皇太极的金史观念与其父最大的区别就是由“独尊金朝”转变为“辽金元并重”,这种转变应当被纳入清太宗东征西讨、发展皇权、整合部族、与明争统的历史大脉络当中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