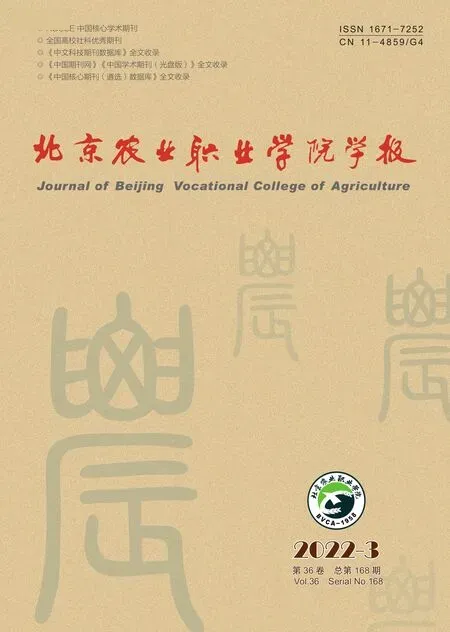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马 莉,王广斌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2020年底,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乡村振兴阶段将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低收入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2],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规避救助依赖,注重农村低收入人口长远发展[3]。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反贫长效机制,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基础上,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鉴于此,本文就相对贫困的概念、发生机理及影响因素、特征及类型、标准及测度、治理机制等进行总结归纳,揭示相对贫困的研究动态,以期为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相对贫困概念界定
相对贫困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Townsend(1971)提出的,他关注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生活水平的比较[4],认为相对贫困是个体、家庭在社会活动、文化、住房、娱乐等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被剥夺的状况,这些资源被剥夺的个体、家庭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即为陷入相对贫困[5]。相对于Townsend提出的资源的相对剥夺,Sen(1983)提出个体“权利和能力”的相对剥夺[6],他认为个体的贫困本质是因为其自身发展能力的缺失。而Chambers(1995)则认为相对贫困还表现在面对冲击、风险、压力时的脆弱性和无话语权等[7]。到二十一世纪,国内开始逐渐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同春芬(2015)将相对贫困总结为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源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生产生活水平[8]。吴振磊(2020)通过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分析得出,若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主观认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差距,即可认为有地区或阶层成员陷入相对贫困[9]。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与绝对贫困相比,在相对贫困的概念界定上,已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从“生存”转向“发展”,从“物质”转向“权利”,从“客观评价”转向“主观感受”。
二、关于相对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
关于相对贫困的发生机理,国内外学者们大致从自然、社会、个体因素三个角度来解释。
(一)自然因素
从自然角度来看,一方面,恶劣的环境条件是导致相对贫困最直接的因素。张琦(2020)在其研究中提到,某个地区的自然条件越脆弱,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越大[10];李文辉(2016)通过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户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已空前尖锐,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千沟万壑”的黄土地貌限制了当地农户的发展,黄土丘陵区的农户们长期以来受到生态恶化和贫穷落后的双重困扰[11]。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伤害和风险,对个体和家庭的破坏最直接、最严重,且恢复难度极大,最能剥夺个人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赵习枝(2019)通过分析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中自然灾害高危险区域内的贫困状况,发现位于尼泊尔、印尼、缅甸、菲律宾滑坡高危险区域的贫困人口比例均超过80%,位于阿富汗、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地震高危险区域的贫困人口比例均超过 50%[12];Carter(2007)在研究1998年洪都拉斯米奇飓风对受灾家庭的影响中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至少能够在三年间重新获得资产。但对于最低财富的家庭来说,飓风对资产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在飓风中失去资产的家庭可能永远也无法跳出“贫困陷阱”[13]。
(二)社会因素
从社会角度来看,相对贫困的产生是由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不平衡。虽然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对关注点侧重于机会缺失、权利剥夺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14](汪三贵等,2020)和不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15](李小云等,2020)。学者们分别从社会资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三个层面研究相对贫困的发生机理。Dekker(2001)认为社会资本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更为重要,并通过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回报是高收入人群的两倍[16];许源源(2020)认为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制度结构和个体行动因素双重缺失的结果,虽然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滞后,这种制度漏洞不仅限制了农民社会资本的积累,还使得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公共福利权相对缺失[17];仲超(202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也是中国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18]。
(三)个体因素
从个体角度来看,相对贫困主要源于个体的弱点和能力不足[19](Royce,2009)。一方面,She(2006)使用1996年至1999年期间SIPP(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的纵向数据,分析得出劳动适龄残疾人的贫困率是正常人的2~5倍,1997年残疾人的贫困率是10%~32%,而非残疾人的贫困率为6%[20]。另一方面,刘建(2019)认为个体的动力不足,则不具备令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陷入相对贫困[21],特别是脱贫群体,在政策帮扶下摆脱绝对贫困,若不具备可持续脱贫的能力,不仅会陷入相对贫困无法自拔,甚至会返贫[22](王思斌,2020)。
综上,围绕相对贫困的发生机理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可“不平衡”“不均等”“相对剥夺”导致了相对贫困的发生,但是对于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不足,因此,深层次地挖掘影响相对贫困的因素,应是未来研究相对贫困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对于治理相对贫困将起到“对症下药”的关键性作用。
三、关于相对贫困特征及类型的研究
(一)关于相对贫困特征的研究
关于相对贫困特征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不少观点,大致包括相对性、长期性、动态性、多维性等特征。
1.相对性
相对性是相对贫困区别于绝对贫困的根本特征,相对贫困的相对性特征体现在其被主观地设置了参照系。例如,杨亚亚(2020)认为相对贫困具有多元、动态的参考系[23]。左停(2019)认为相对贫困相对于绝对贫困包含了主观感受,是各主体与自主设定的参照系在经济、医疗、教育、公共福利等比较下相对落后的状态[24]。
2.多维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更加强调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福利等方面需求(唐任伍,2019)[25]。而现实中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福利等多维度享受的资源不平衡、不平均的状况,就体现出相对贫困的多维性。
3.长期性
自古以来,相对贫困就长期存在,没有因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消失(曾福生,2021)[26]。但相对贫困的存在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相悖。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反贫工作重点变成治理相对贫困,而治理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4.动态性
韩广富(2020)认为相对贫困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相对贫困标准的动态性[27]。与绝对贫困标准不同,相对贫困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区域设置城乡差别的相对贫困标准,并且这一标准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关于相对贫困类型的研究
相对贫困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低收入群体;第二类是脱贫攻坚时期靠政府政策兜底脱贫、无自主发展能力的政策兜底群体;第三类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想要融入城市但未能享用城市资源的城乡流动群体;第四类是在自然灾害、偶发意外面前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的突遭意外群体等[28](曹昕宇等,2020)。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过程中,个体或家庭的发展性、精神性、多维性贫困已经取代生存性、物质性、收入性贫困[29](张永丽,2019)。
总体来看,国内外围绕相对贫困的特征和类型的研究较为丰富,通过对这些研究的梳理,不难得知对相对贫困特征和类型的辨别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划定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别时可能面临着相对贫困特征和类型的交叉,难以准确划分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别。因此,如何划分相对贫困群体应是未来研究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关于相对贫困的标准及测度的研究
(一)关于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
不论中国现在适不适合采用相对贫困标准[30](汪晨等,2020),但根据发达国家相对贫困线的划定,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对制定相对贫困标准进行探索。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基于收入的相对贫困标准。王小林(2017)、叶兴庆(2019)、孙久文(2019)认为应以城乡统一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根据城乡各自经济发展水平,按照中位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60%比例法来制定城乡可动态调整的“两区域、两阶段”相对贫困线[31-33],这种相对贫困线的制定借鉴了国际标准,无论选择中位收入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设置比例制定相对贫困标准,都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制定。
第二类为基于多维度的相对贫困标准。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提出的人类贫困指数(HPI),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状况[34],采用适合当地的维度、指标,王小林(2020)提出中国可以以“贫”和“困”两个方向为主,将反映地区和个体生产生活水平的各维度纳入相对贫困标准制定中[35]。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收入是衡量个体或家庭发展的主要指标,因此,多维度相对贫困标准应以经济维度为主,兼顾社会维度、教育文娱维度、医疗健康维度、生态维度等。
第三类为基于消费支出的相对贫困标准。杨振(2015)运用恩格尔理论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对中国各省区的农村居民相对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农村的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及成因[36]。
(二)关于相对贫困的测度研究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相对贫困测度的研究比较多,从地区到家庭、从单维度到多维度、从运用一种方法到多种方法相结合。
国外方面,Atkinson(2003)将“计数法”应用于考察欧洲国家的多维贫困问题[37];Silber(2008)利用Watts多维贫困指数测算不同国家的多维贫困状况[38];随着对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逐个比较法、非加总法和加总方法等多维贫困度量方法被应用到相对贫困的测度[39](Brandolini,2009)。Alkire(2014)利用人文发展指数反映贫困个体或家庭在人文发展维度上的贫困程度[40]。
国内方面,王小林(2009)从宏观层面采用A-F方法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量[41];郭建宇(2012)从微观层面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研究了收入贫困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42]。陈宗胜(2013)运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测度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结果显示中国的绝对贫困状况逐渐缓解,但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恶化[43]。龚华(2019)结合运用基尼系数模型与A-F方法测度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和相对贫困程度[44]。
综上,国内外针对相对贫困的标准及测度颇多,虽然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来看,国内对于相对贫困标准及测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研究的应用及扩展,缺乏创新性。因此,中国在划定相对贫困的标准上虽然要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动态调整的原则,但也应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相契合,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并创建更具创新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和测度方法。
五、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研究
在解决绝对贫困之后,反贫困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断脱贫地区、脱贫户返贫,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治理相对贫困打下坚实基础。阻断返贫的有效路径要以激发脱贫地区、脱贫户的内生动力为主,以产业发展推动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带动脱贫户持续增收。蒋和胜(2020)认为应该探索构建返贫监测机制[45],通过政策干预阻断返贫现象的发生。包国宪(2018)提出构建返贫监测机制应包括社会环境监测、自然环境监测及个体及家庭监测[46],范和生(2018)认为要搭建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完善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组织决策、考核监督等返贫监测工作[47]。
反贫困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五年过渡期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国家在过渡时期采取的主要策略应集中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根据Son(2007)的扩大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比重及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比率的思想[48],豆书龙(2019)认为应着力推动扶贫产业发展多元化培育升级和低收入群体致富意识精准激发,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49],为全面治理相对贫困做好铺垫。
反贫困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治理相对贫困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然选择[50](张传洲,2020),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经开展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但取得的成效甚微。陆汉文(2020)认为相对贫困的治理应具备系统性,应处理好城乡关系和区域关系,应建立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1]。向德平(2020)提出相对贫困治理应该遵循阶段性与渐进性结合、普惠性与特殊性结合、参与性与包容性结合的原则[52]。吕方(2020)提出应建立起制度化的相对贫困治理整体性体制,由政府主导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53]。
综上,国内外对于反贫困的研究,大致以增强内生动力、推动城乡一体化为主线,近几年逐渐强调分阶段、多维度治理相对贫困,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仍略显不足。鉴于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期性,未来对于相对贫困治理的研究应以国家性政策为基础提供治理相对贫困的硬性保障,促进社会各方力量多方参与,引进市场机制,建立起多中心治理相对贫困的系统性体制导向。
六、总结及展望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有一定成果,但整体仍缺乏系统性。发达国家较早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国外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明显早于国内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2019年之前,国内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的情况展开研究,但随着国内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国内解决了绝对贫困及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国内研究焦点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国内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成果在2019—2021年呈现爆发式增长。但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研究的主体大都偏向于对个体相对贫困的研究,而以区域相对贫困作为主体进行研究的仍然较为缺乏,在解决了国内区域性整体贫困之后,区域性相对贫困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解决个体相对贫困和区域性相对贫困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而要想解决个体相对贫困和区域性相对贫困,只有通过构建反贫长效机制才能实现。所以,区域性相对贫困问题和反贫长效机制构建将成为未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