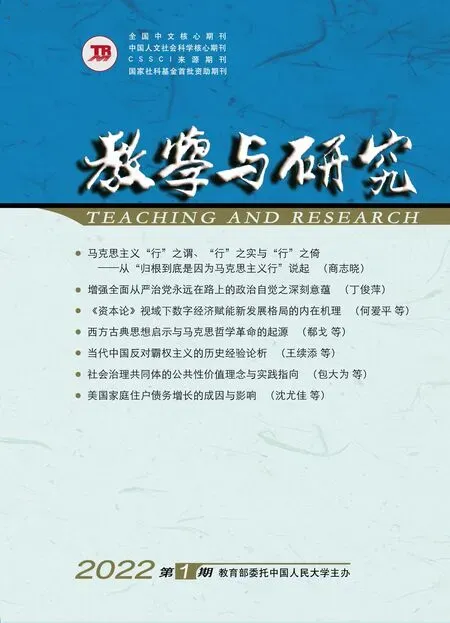西方古典思想启示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源
——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
郗 戈,张继栋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它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底蕴。而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理学家”,同样受益于其生长于其中的西方思想传统,西方古典文明构成了马克思关照现代性的关键参照性视野。古典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一生的,乃至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线索和踪迹。对此,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就曾指出马克思的古典底蕴是极其深厚的,她认为,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思想史脉络,远比通常流行见解所理解的要深刻紧密得多。(1)参见[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极其深远地影响了起源于古典思想的西方思想传统。西方思想传统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却无意识地导向了一条通向虚无主义的道路。而如海德格尔所言,马克思完成了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颠倒,也在异化理论中表达了现代文明最深刻的历史性维度。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破除了西方哲学的困境,指出了哲学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从而开启了西方哲学乃至人类文明的新视野和新出路。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与西方古典思想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作为革命家,他的观点自然是一个抑古崇今的“现代派”。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体系化、科学化的要求,满足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解放、科学启蒙与现代化的需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正确性和革命性。但是,体系化的努力也往往带来了逻辑先行的立场,特别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服从于原理教科书的需要,从而一方面忽视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反地,另一些学者看到了这种解释方式的弊端,试图强调19世纪德语学界乃至马克思本人所具有的古典立场,从“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出发,将马克思指认为一个崇古抑今的“古典派”。如美国当代学者乔治·麦卡锡就认为,“从论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及其对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开始,进而扩展至后来的历史著作,马克思将希腊社会生活的伦理典范和价值观念融入进了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解和评估当中”。(2)[美]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实际上是希腊伦理在现代世界的复兴。这种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提醒了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深邃内涵,也带来了诸如马克思与古典哲学、神话、美学传统乃至现代早期德意志浪漫主义等等一系列新的话题。但是,这种观点虽然勾连起了马克思与古典思想之间的联系,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流于复古还原主义的立场。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古典伦理理想的现代版还是基督教灵知主义的现代版,甚至是某种“浪漫诗学”,都无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身。
对于上述二元对峙观点,我们认为,无论是还原主义的观点,还是逻辑先行的观点,都预设了“古典”与“现代”的截然对立,而马克思恰恰是一位“学贯古今”的人,在其思想中古典传统与现代思想相互交融,彼此化合,共同扎根于时代精神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当中。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源期,他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借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之笔,以“普罗米修斯”的古典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他追寻自由的现代志向。而为准备博士论文所作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正是我们管窥青年马克思理解古今变迁、求索哲学变革的秘密钥匙。我们正是以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勘察古希腊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革命起源的深层关联,力图揭示马克思在传统思想与现代哲学之间的复杂思想视域。
一、思想缘起:浪漫主义、黑格尔与古希腊哲学
马克思与古希腊文化和古典思想的关系以及后者对马克思思想起源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经过了多重思想中介的复杂思想史事件。因而首先需要将其思想接受环节清晰地呈现出来。
马克思热爱古希腊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波恩大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在18世纪的德意志地区,最早自觉将古希腊作为自己思想武库的,正是以莱辛和赫尔德为代表的早期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在早期德意志浪漫主义者看来,现代世界是一个被科学所祛魅的物理世界,现代人仿佛孤舟漂泊于汪洋之上,无法在一个被牛顿力学支配的世界里找到自身意义的安居之所,甚至连人自身也从高贵的神坛跌落为钟表一样的僵死机器。而与现代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希腊世界中公民与城邦之间未经异化的原初统一,精神与物质还没有像现代这样达到二元对立的境地。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古希腊人尽管有着充分发展的精神生活,但是也同样没有忽视人的自然的一面,这来自自然的一面甚至通过希腊神话而得到了众神一般的地位。席勒为此艳羡道:“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3)[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48页。古希腊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承担了为世界重新“赋魅”的功能。不过,也正像勃兰兑斯讽刺的那样,德国浪漫主义者即便是在最激进的时候也是相当抽象和唯心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历史和外在现实畏缩不前,正是那时整个文学的特征。”(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张道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而众所周知的是,波恩大学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重镇。马克思在就读波恩大学期间曾经师从浪漫主义领军人物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并且他还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其中不乏对古希腊诗歌题材的有意模仿。
不过浪漫主义对古希腊文化的援引更多基于美学想象而非哲学思辨,真正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从选题、研究和写作起到根本性影响的,是黑格尔对古希腊哲学的重新阐释。他在多部著作和讲稿中都对希腊哲学不吝赞美,他甚至说道:“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希腊表示着精神生命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在黑格尔看来,希腊哲学的巅峰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方面是希腊哲学本身的辉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森罗万象的总体性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希腊世界的辉煌,希腊精神通过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取得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1页。而在亚里士多德哲学解体、希腊哲学迁入罗马世界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包括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派在内的独断论,其最高原则是自我意识。
黑格尔关于希腊哲学的重新阐释特别是总体性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之间关系的解释,深刻地影响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后者的领军人物布鲁诺·鲍威尔正是将自我意识作为了自己哲学的基点,从而影响到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根据学者考证,当时马克思至少准备了两个博士论文选题,除了集中讨论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的题目之外,马克思还准备了一个批判海尔梅斯主义的题目。然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下,马克思最终选择了前者作为自己论文的最终题目。(7)参见聂锦芳:《滥觞与勃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马克思后来在博士论文中表示,他的论文选题一方面意在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解释自我意识哲学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另一方面也为实现哲学变革作思想准备。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在哲学体系方面对黑格尔表示了敬意,但是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展露出了自我意识哲学在经过青年黑格尔派中介之后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之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讨论了自我意识在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乃至苦恼意识中的体现,但是唯独没有讨论在哲学史中同为独断论和自我意识哲学的伊壁鸠鲁学派。究其原因,在于黑格尔认为斯多葛主义是精神自由,与怀疑主义一起都可以被纳入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环节中,而伊壁鸠鲁作为“斯多葛主义的反面”,“他的哲学没有进步,也没有发展”(9)[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因此必须被排除在体系之外。而马克思恰恰相反,将伊壁鸠鲁哲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后哲学变革的重要古典思想资源,从而与黑格尔构建哲学体系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古典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史线索不是简单的单线联系,而是有着“古希腊哲学——浪漫主义——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马克思”在内的多重思想透镜。古希腊哲学本身的意蕴被黑格尔纳入到了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内在过程,这一过程又被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化为费希特式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而,青年黑格尔派对古典思想的再阐释,最终被马克思更为深厚的古典底蕴所改造,演变为服从于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化”这一基本问题视域的内在思想线索。
二、“诸神死了”:亚里士多德之后与黑格尔之后
青年马克思在其思想起源处究竟是如何受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启示的?从另一个方面说,马克思是在何种哲学变革的问题意识中接受和化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
首先应当注意到,对历史过程的深刻连续性和重复性的经验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早在其思想起源期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起这样一个表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而这种关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相似性”和“重复性”的认识,更早的发生于青年马克思写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期。他注意到,在哲学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两次相似的哲学变革的节点,一次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另一次则是在黑格尔哲学之后。两者作为哲学史上两座不同时期的高峰,其总体性都为后世所折服。而其解体,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对马克思而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实际上是理解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变革的参照,也是把握当时风云激荡的时代精神的指南。
在马克思看来,身处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与现代的黑格尔形成遥相呼应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精神自身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总结了古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历程,并且进一步指出,如果在哲学史的过程中,每一种哲学的发展都是一种直线运动,都是按照其自身抽象原则展开的,那么总体性哲学的出现就打断了这种直线运动。在古希腊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哲学正是这样的哲学,它为了形成对世界的全面理解而注视着外部的世界,它不是世界舞台上的行动者,而是对世界舞台的静观者(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5页。。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不动之动者,哲学以“默想神思为唯一胜业”(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5页。。同样,黑格尔哲学在思辨领域将各个哲学流派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使它们成为了绝对精神自我沉思、自我认识的各个环节,从而使近代哲学得到了完成。哲学似乎通过黑格尔掌握了世界,达到了自身的普遍性。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普遍性最终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碎片化和解体。正如伊壁鸠鲁与芝诺、恩披里克等哲学家所处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解体的阶段,德意志目前也处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阶段。一方面,随着黑格尔的去世以及普鲁士王国对其哲学的不断清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远不如其任柏林大学校长时那般如日中天;另一方面,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日益被其学生所撕裂,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各执一端,“实体”“自我意识”“行动”“类”等诸多碎片性的概念也不断地挑战着绝对精神的总体地位。
通过比较“后亚里士多德”古典希腊哲学与“后黑格尔”现代德意志哲学的相似命运,马克思把握住了二者背后共通的时代境遇。总体性日渐消隐、崩塌的哲学现实带来了“时代精神的总危机”。马克思在“笔记本二”中指出,“只有当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所以,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因而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7、61页。。在马克思看来,总体性哲学解体所带来的哲学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哲学要与世界发生联系,因此在哲学“肉身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哲学的定在都从主观的基地出发来把握世界。哲学一旦在精神领域中掌握了世界,就必然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从世界舞台的“静观者”转向“剧中人”,转向自我意识的主观形式。由此,自我意识哲学一方面许诺了新哲学的到来,另一方面也促使哲学本身不断“伦理化”,从而与世界发生更为紧密的实践关联(15)参见[美]巴拉诺维奇:《马克思与希腊哲学》,载[美]麦卡锡编:《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郝亿春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这意味着不仅是哲学自身产生了危机,更会带来“时代精神的总危机”。布鲁诺·鲍威尔在给马克思的书信中就写道,“灾难将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大的。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图景中出现这一事件更大、更可怕”(16)[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而在马克思看来,时代精神的危机实际上标志着在这个时代中,“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她还没有白昼的色彩”(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7、61页。。这不仅仅是对古罗马世界的回望,同样也是对当时德国何去何从的思索。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领域,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总危机”。
虽然后亚里士多德与后黑格尔分享着相似的时代境遇,但是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世界的总体性哲学毕竟不同于古代哲学,它是精神在历史发展更高阶段的完成,因此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蕴含着在新基础上重建总体性的可能。在古希腊哲学中,希腊哲学与希腊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精神与实体的关系,伦理实体性的希腊精神带给了希腊人与城邦共同体之间原初的、未分化的统一关系,每一个公民都是城邦的化身,而每一个希腊人都体现着希腊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美德。但是另一方面,希腊哲学与希腊精神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限度,古代世界中的哲学是实体生活的主观形式。亚里士多德哲学之所以是总体性哲学,就在于它是希腊世界的集大成者。然而恰恰由于古代哲学的根基在于伦理实体,无法脱离并彻底地反对实体本身。因此,总体性哲学瓦解之后所产生的只能是独断论式的自我意识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的作用是前提,而对于近代人来说,精神的作用是前提。只有当看得见的天空,生活的实体联系,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吸引力都毁灭时,古代人的斗争才能结束,因为自然应该被劈开以便求得精神自身的统一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7、61页。但是,在现代世界中,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时代精神,二者不再是精神与实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在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下,哲学与时代精神二者都是精神领域内部的事情。因此,不仅哲学的危机会导致时代精神的危机,而且哲学的变革也会引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
黑格尔之后各种标新立异的哲学流派并未能走出“总体性哲学坍塌”的阴影,而是纷纷陷入碎片化的思想困局。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敏锐地把握到了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提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种种思想方案。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黑格尔之所以执着于建立一个总体性的哲学体系,就在于力图调和现代性内部的异化和分裂。黑格尔赞赏法国大革命进步的同时又希望革命能够局限在精神王国内部,在坚持哲学理性的方向下,又试图为新教神学留下自己的空间。然而,黑格尔的学生们显然不满于自己老师的折衷方案,随着《耶稣传》的出版,黑格尔哲学分裂为老年与青年两派,标志着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总体性努力最终付诸东流。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如何填补当时精神领域的空白?大卫·施特劳斯的“实体”等诸多哲学流派粉墨登场,试图完成这一时代任务。这一个时代是精神领域的内战,也是“哲学的狂欢节”(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5、112页。。然而,青年黑格尔派最终也仅仅是“狂欢”,没有真正地回答时代提给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了哲学的危机,力求在哲学领域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危机的根源不在哲学内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客观矛盾和历史趋势——现代哲学中的哲学传统必须发生改变,像浮士德一样将自己从思辨形而上学转移到外部现实世界,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三、“在大海上重建新雅典”:哲学革命起源的时代氛围
对历史上和当前的哲学变革氛围的比较,深刻激发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哲学革命的理论意识。马克思对“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变革”与“后黑格尔哲学变革”之间“相似性”进行了历史性理解:两种变革都力图超越哲学崩溃和价值虚无,重建时代的总体性哲学、精神和价值。这种总体性重建并不是无中介的、直接性的,而是必须依赖“主观性环节”的中介作用。总体性的哲学在分崩离析之后,只有在哲学的“主观性形式”即自我意识哲学之中才能保存和延续其精神生命。马克思以“雅典的覆灭与重建”的史实隐喻哲学的覆灭与重建,以“在另一个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的说法来隐喻亚里士多德之后和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变革。哲学将在另一元素之上重建,这个元素就是“自我意识”。既然克服总体性哲学崩溃之后的时代危机的任务最终落在了自我意识哲学身上,那么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究竟有何特征,又如何能够承担起重建时代的总体性这一重任呢?
青年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哲学的内在性沉思向度,而以外向化的“自由意志”和“实践力量”作为自己的心脏和内核。在马克思看来,在哲学通向总体性的阶段,哲学的任务是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按照哲学本身的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这一阶段哲学研究的象征是“明亮的眼睛”,它的美德是审慎,而基础是理性。但是,随着哲学对外在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会越来越发现如果仅仅是获知越来越多外部世界的规定性实际上无助于哲学达到自身的自由,相反它意识到在外部世界中所认识的规定性不是外部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只有通过对意识自身的考察才能使哲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哲学的任务就转向了意识自身之内,以自我意识的规定来理解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在总体性哲学瓦解、自我意识哲学兴起的背景下,哲学研究的方式就不再是获取外部世界的知性知识,而是将自己外化到世界中,在哲学与世界的辩证互动过程中寻求逐步总体化的理性。哲学就作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马克思思考这一问题的中介是一位古罗马哲学诗人:卢克莱修。在“笔记本四”中,马克思对卢克莱修的评价经历了一个颠覆的过程。“笔记本四”伊始,马克思并不认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对理解伊壁鸠鲁的哲学有太多价值,但是在开始摘录《物性论》不久之后,马克思对卢克莱修的评价立刻发生了翻转。马克思被卢克莱修诗歌中勇敢和崇高的品行打动了,并对这位他原本认为没有价值的诗人进行了整整长达两个笔记本的摘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认识到卢克莱修与之前摘录的普鲁塔克相比要“明哲无数倍”,因为卢克莱修懂得“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5、112页。。另一方面,正是在对卢克莱修的摘录中,马克思引出了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最重要的内核,即原子偏离直线而运动就是“自由意志”。原子的偏斜并非是被外在事物所预定的,而仅仅被其自身所决定。当原子在自由意志的驱动下从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偏离出来时,哲学就在自我意识这一崭新的元素上创造了世界。
因此,自我意识哲学重建时代总体性的方式,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总体性哲学的太阳熄灭之后,自我意识哲学便成了黑暗中的人们为自己点亮的思想烛火。从表象上看,马克思进行的是一个古典时代的哲学讨论,但是从其问题意识上来看,却是一个在现代问题引导下的古典比喻。“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要求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转变为“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这只有在现代世界的精神性地基上才能展开。就古典世界的自我意识哲学而言,由于哲学与希腊世界关系的本质是精神与实体的关系,希腊哲学不仅无力穿透希腊世界的实体性,相反还会被希腊世界规定为有罪,因此古典世界中的自我意识哲学就表现为对外部世界采取超脱而漠不相关的态度,并追求内心的丰富和满足。而就现代世界的自我意识哲学来说,由于哲学与世界两方都在精神领域的内部,自我意识哲学就不仅获得了从自然实体向主观精神转移的可能,更获得了根据自我意识本身的规定而改造外部世界的条件。
自我意识哲学不仅要与宗教作斗争,还要与其他一般的哲学形式作斗争。“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23)借由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偏斜与碰撞的逻辑结构,马克思指出了作为自由意志的原子的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原子自身的抽象规定性与它自身的定在的矛盾,必须从自己直线运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对于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来说,正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原子的定在与其他原子的定在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双重性,就表现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与不经批判的实证主义乃至庸俗的日常意识之间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代是伟大斗争的时代,也是新的启蒙时代。它创造了新的分裂和对抗,还在通往新的整合与总体性时代的路途中。虽然没有形成新的总体性哲学,处于晦暗不明的不确定、过渡性氛围之中,但却是充满“伟大的斗争”的宏伟时代。这样的时代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马克思说:“例如,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派哲学曾是它那个时代的幸运;又如在大家共有的太阳落山后,夜间的飞蛾就去寻找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8页。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及“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哲学是马克思重建时代及哲学的总体性的第一种思想武器,它帮助马克思投入到了批判普鲁士王国精神生活的现实活动中去。但是,自我意识哲学本身的结构也预示着自身批判能力的限度,一旦跃出哲学本身的视域就丧失了威力,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自我意识哲学将精神自由看作是哲学与现代世界两方共同的基地,因而要求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要求哲学家投入到反对现象世界的斗争中去,通过揭露和批判现象世界中不合于理性要求的事物,来实现其新启蒙主义的立场,这也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着眼点。
既然黑格尔的法哲学已经揭示了政治国家与哲学的和解关系,那么“哲学的世界化”又为何会遭遇“物质利益的难题”并进而反思“理性国家”?在现代世界中,虽然政治国家与哲学之间实现了精神对精神的关系,可以通过宣布废除选举的财产限制等方式宣布自己为自由国家,但是政治解放具有自身的限度。批判哲学与在政治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的关系仍像古典世界中“实体”与“精神”那样:正如古代世界的苏格拉底生活在政治国家中,现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们生活在市民社会中,它的理论被市民社会所决定。一旦哲学家形成了超越市民社会拜物教的理论,就立刻会被后者宣布为“有罪”,就像雅典城邦判处苏格拉底因渎神而获死刑的翻版。
在通过市民社会难题的探索扬弃了自我意识哲学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识到“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而哲学总体性的瓦解仅仅是时代的一个侧面,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征。因此,如果想要重建哲学的总体性,哲学就必须再次寻找自己的新元素、新基础,实现“问题视域”的根本转换,从而以重建社会总体性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任务。
四、“古今之间”的马克思哲学革命起源
马克思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写作时间距今正好140年左右。这些文献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力图在“古今之间”求索哲学革命道路的青年思想家的思想形象。从宏观思想史角度来看,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古典启示”与“现代重构”相互交融。古典思想在启示、激发现代思想者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思想者建构、重构古典思想的过程。正是在现代思想的问题意识中,古典思想得以不断更新和再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并不存在一种本然的、未经现代思想污染的“传统思想”,也并不存在一种完全既成的、不受传统思想启迪的“现代思想”。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始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并不存在截然的分隔与断裂。
首先,“古典启示”与“现代建构”这种相互交融,体现在时代境遇与时代主题的历史性理解之上,还体现在思想变革的时代形象的历史性理解之上。《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问题意识,表明了马克思不仅是对伊壁鸠鲁的具体解读,更是深入时代精神的维度对古典与现代的总体对比和全面把握。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哲学史秘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独断论哲学不仅仅是哲学退回到主观精神领域内部的阶段,更是隐藏着新的启蒙精神的阶段,这恰恰与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发展形成了共鸣。黑格尔哲学分裂、解体之后,哲学的发展也会来到一个实现自身变革的时期。原本为总体性哲学所弥合、掩盖的精神矛盾势必重新出现,成为孕育哲学革命的时代温床。正是通过对晚期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性阐释,马克思才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现时代进行明确的历史定位。将亚里士多德之后理解为哲学变革的时代,并相对照地将黑格尔之后理解为哲学变革的时代,正是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相互型塑的结果。
“古典启示”与“现代建构”这种相互交融,还进一步体现在思想家对“自我形象”的历史性把握之上。晚期古希腊哲学变革者的思想形象构成了马克思的一个“自我镜像”,激发了马克思自我定位、自我担当与自我型塑的过程。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黑格尔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对比,古典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共同陶冶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共同为马克思的哲学探索锚定了最初的启航点,使马克思将实现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变革作为自己的哲学志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自我意识”之所以产生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成果,也离不开古典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关怀。正是凭借对古典世界的喜爱与了解,马克思才托埃斯库罗斯之口说出了现代普罗米修斯式的哲学宣言;也正是凭借对伊壁鸠鲁等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变革者的历史阐释,马克思才得以把自己历史地理解为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变革者。
总之,在马克思思想中,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隔阂而相互纠缠、相互融通,其根基在于时代精神发展及其哲学反思的历史连续性。从哲学史上来看,虽然哲学发展存在着不同的节点,但是理解这一发展背后的历史底蕴却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将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思想、同一思想中的不同人物乃至同一人物不同的思想阶段相互割裂并完全对立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重大问题,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历史、人物和思想本身。而正是由于将自己和古人同时置于这种“古今变迁的”而非“古今断裂的”历史性视域之中,马克思才能从古典思想中获得足够的灵感、勇气与智识,使自己能够担负起变革哲学的历史使命。
进而,在马克思的现代哲学革命的问题意识中,古典思想资源得以再生产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思想在自以为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顶峰之后,却陷入自身的矛盾与困境中,并不得不反复回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源头去寻求“思想灵感”甚或“精神救赎”。这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在进步与回溯之间的自我悖谬。我们在青年马克思身上看到了浪漫主义者、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子。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哲学革命氛围之中,马克思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在马克思之后,是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哲学革命?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敏锐地捕捉到了“后黑格尔境遇”与“后马克思境遇”之间极为显著的历史相似性,这仿佛就是《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遥远回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旧的时代精神分崩离析,而新的时代精神正在诞生的“哲学变革氛围”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