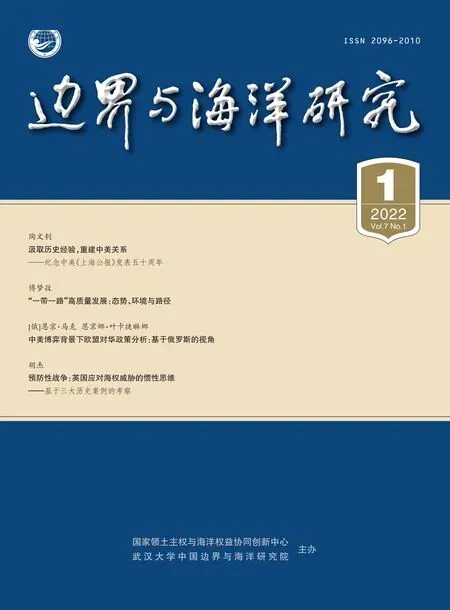中不边界谈判历程回顾及启示*
严祥海
中国的陆上邻国共有14个,其中仅同2个国家的陆地边界没有划定,即印度和不丹。同时,不丹又是目前唯一个没有与中国建交和划定边界的国家。中国与不丹有着550公里的边境线,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习惯边境线,边境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双方从未正式划定边界。(1)不丹方面公布的两国边境线长为477公里,两国在边境争议区的认知偏差、测量技术和比列尺标准等因素导致双方数据有差异。参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中印、中不卷》(中不边境概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目前学界对中不边界的研究十分薄弱,仅齐鹏飞在《中不边界述论》一文中,简略地梳理了从1984年到2010年期间双方举行的20轮边界谈判,其主要运用的是《人民日报》报道等国内资料,未参考不丹及印度方面的资料。本文拟综合中、印、不三方材料,全面回顾中不边界问题的产生、谈判历程及其特点,并据此对中不边界问题做出总结和展望。
一、中不边界问题的产生
1616年,夏仲·阿旺南杰(zhubs drungs dbang rnam rgyal)在西藏受到宗教上的排挤,逃亡不丹,随后统一了不丹。(2)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1734年,不丹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不丹德布王(Deb Rāja)受到清廷册封。(3)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5页。自此,不丹派官员常驻拉萨管理商务和朝贡事宜,官员被称为“罗贾(lo phyag)”,每逢新年之际都要朝贺达赖喇嘛和清政府驻藏大臣。(4)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1907年,乌颜·旺楚克(Ugyen Wangchuck)建立不丹王国。(5)Karma Ura,Leadership of the Wise Kings of Bhutan,Thimphu: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2010,p.32.2007年7月18日,不丹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即《不丹王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走上了民主国家的道路。(6)Karma Ura,Leadership of the Wise Kings of Bhutan,Thimphu: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2010,p.169.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在西藏帕里(phag ri)一带设立了关隘三处(哲孟山、哈尔山、宗木山),(7)黄沛翘:《西藏图考》,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界分西藏与不丹。(8)松筠:《西招图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中不之间大致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这条习惯线大致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脊而行,西起锡金、不丹、中国三国交界的吉姆马珍山(Gipmochi),(9)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东到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大约位于东经91度30分、北纬26度53分。(10)朱在明等编著:《列国志·不丹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306页。
进入19世纪后,清朝国力式微,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政治影响力逐渐衰退。1840年后,英印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纵深,不丹与清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民国以后,不丹与民国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联系,但仍与西藏噶厦政府保持着宗教上的往来。(11)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3页。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接管边防,直接破灭了印度的喜马拉雅边界幻想。(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
1951年至1959年,不丹在西藏的利益基本保持不变,中方也严禁在藏军政人员越过习惯上的中不边界线。(13)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1958年9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不丹,挑唆不丹方面在中不边界争议区设立军事哨所,由此加剧了地区局势动荡,破坏了边境的安宁。(14)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54页。1959年3月1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携上层反动贵族叛逃印度。自1959年12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开始全面进驻中不、中印及其他边境地区,从而“改变了西藏地区近4000公里边界线上有边无防的状况”。(15)刑广程主编:《“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8页。随后,在印度的怂恿之下,不丹撤回驻拉萨及其他地方办事人员。(16)[印]拉姆·拉合尔:《现代不丹》,四川外语《现代不丹》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2页。中方则取消了不丹在藏的特权。(17)[印]拉姆·拉合尔:《现代不丹》,四川外语《现代不丹》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4页。基于印度与不丹的特殊关系,(18)根据1949年8月8日印度与不丹签订的《印度—不丹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规定,“不丹政府方面同意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印度的指导”。参见严祥海、狄方耀:《遗产、重塑与挑战:不丹的国家安全困境及其应对》,《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88页。尼赫鲁在1959年8月中旬发表声明称“不丹是印度的保护国”。(19)[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79页。1959年8月28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明确表示:“保护不丹的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是印度政府的责任”。(20)朱昭华、杨三奇:《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的历史考察》,《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90页。
1959年8月至11月,印度政府就所谓不丹在西藏“飞地”的讹传(21)印度声索的八块“飞地”分别为:康格里(gangs ri/冈仁波齐)、塔尔钦拉章、泽霍尔、迪拉甫、宗杜甫、羌且、查吉普和科加,中方对之不予承认。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和中不边界问题(22)齐鹏飞:《中不边界问题述论》,《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30页。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3)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 (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49.所谓“飞地”,只是在西藏当局默许之下,不丹政府在今西藏亚东县帕里拥有的房屋和地产,及不丹竹巴噶举教派在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宗、扎达宗享有寺庙和地产,无论是不丹政府或竹巴噶举教派拥有的地产或寺院均在中国境内和其管辖的领土之上,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飞地,(24)端木正编:《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也不构成当前中不边界的争议区。印度替不丹“声索在藏飞地”不过是印度人意欲“保护不丹”的幌子而已。(25)《就印度决定要求把军队开入不丹 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2日第3版。
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发起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印关系急剧恶化,也影响到了不丹和锡金。中方始终尊重不丹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决定和不丹方面就边界问题进行单独磋商,(26)[印]拉姆·拉合尔:《现代不丹》,四川外语《现代不丹》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2页。但此举遭到印度的百般阻挠。1976年,不丹政府曾主动与中国政府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但由于印度的介入,不丹只得以“材料不足”为由终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
目前的中不边界争议区,自西向东,分别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亚东县、洛扎县和错那县以南达旺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27)[英]阿拉斯太尔·蓝姆:《中印边境》,民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62页。三段,分别对应西部的哈宗(Haa)、西北的帕罗宗(Paro)、中北部的布姆塘宗(Bumtang)和东部的扎西岗(Trashigang),争议区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28)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中印、中不卷》(中不边境概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具体包括鲁林(亦称绒林)、查马浦、基伍和墨拉萨丁等争议区。
二、中不边界谈判历程回顾
1976年7月,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中不正式开启边界谈判也随之变得顺理成章。中不边界谈判正式开始于1984年,截至2021年10月,中国和不丹已经举行了24轮边界谈判和10次专家组会议。
(一)第1—5轮边界谈判:建立互信、确立四项基本指导原则
1981年5月,不丹向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与中国建立了非正式接触。1981年6月,不丹外交部长达瓦·策林(Dawa Tshering)在国民会议(Tshongdu)上表达了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的热切愿望。不丹方面表示:“不丹愿意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划定不丹与中国的边界,并在边界谈判未解决之前保持目前边界现状。”(29)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49.
中国与不丹的首轮边界谈判于1984年4月17—18日在北京举行。在此次边界谈判中,中方明确表示,尊重不丹的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秉持主权平等、互利互让的态度,以“建立互信、奠定基础、寻求突破”。(30)齐鹏飞:《中不边界问题述论》,《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32页。中不第2、3、4轮谈判分别于1985、1986、1987年依次轮流在不丹首都廷布和北京举行。自第2轮开始,双方对中不边界问题的特征和性质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经过此轮谈判,双方建立起了互信,对边界问题的解决充满了期待。
1986年 4月,在第3轮谈判举行前夕,不丹国王吉美·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会见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时表示,不丹和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两轮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之间已建立起完全信任的关系……我们同中国没有争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真诚的关系而不是外交意义上的睦邻关系。”(31)《不丹国王说不中边界会谈很顺利》,《人民日报》1986年4月16日第6版。换句话说,谈判止于解决边界问题。国王委婉地表达了发展中不关系的敏感性,唯恐刺激和惹恼印度。
在1987年 6月9—11日的第4轮中不边界谈判中,双方一致同意在中不边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应当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此轮会谈,双方对中不边界问题的特点和性质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两国数百年来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32)谭仁侠:《不丹国王会见我副外长 中不举行第四轮官员级边界会谈》,《人民日报》1987年6月11日第6版。
第5轮边界会谈于1988年5月10—14日在北京举行。此轮会谈,两国达成“四项指导原则”(33)“四项指导原则”内容:(一)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则;(二)平等相待、友好协商,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以求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三)既考虑基于传统、习惯、使用和行政管辖的有关历史背景,又照顾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两国的国家利益;(四)在边界问题最后解决之前,保持边境安宁,维持1959年3月以前的边界现状,不以单方面行动或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参见《中国不丹第五轮边界会谈签署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88年5月15日第4版。的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34)《中国不丹第五轮边界会谈签署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88年5月5日第4版。第5轮边界会谈签署的《联合公报》所达成的“四项指导原则”为1998年两国签署的《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第6—12轮谈判:不丹对争议区的主权声索与中方“一揽子方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印度政府调整了对南亚周边邻国的政策,印度加大了对不丹的各项援助和投资,尤其是在不丹投资修建水电站和公路等。因此,印度对不丹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丹在边界谈判中的态度自然深受印度的影响。
第6轮边界谈判于1989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级别提升,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不方团长是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Dawa Tsering)。此次会谈也开始有了实质性的磋商。不丹方面声索495平方公里白玉地区的主权,不方称为巴桑弄(Pasamlung),包括贾卡尔弄河谷(Jakarlung)地区。不丹方面认为,这些河谷属于不丹的领土,因为它们位于不丹库鲁蒂区(Kurote Dzongkhang)的古汝河(Bazaraguru Chhu)的河源之下。(35)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1.
第7轮中不边界会谈于1990年8月27—29日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针对不丹在第6轮谈判中提出的主张,中方本着互利互让、兼顾历史和现实的原则,提出“一揽子方案”以解决中不边界所遭遇的困境,但不丹方面反对中方提出的“一揽子方案”,认为各争议区应分开、一一解决,致使谈判陷入僵局。(36)邓红英:《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华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第8、9、10轮边界会谈分别于1992、1993、1994年依次轮流在北京和廷布举行。这三轮谈判总体上保持着诚挚、友好的气氛,双方也达成了诸多共识,双方均愿共同努力尽早使中不边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37)齐鹏飞:《中不边界问题述论》,《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36页。第11轮会谈于1996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在此轮会谈中,不丹继续声索对西部的洞朗、沈久隆巴(Sinchulumpa)、达拉马纳(Dramana)和夏喀托(Shakhatoe)的主权,声称这些牧场对哈宗(Haa)河谷的牧民至关重要。(38)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1.不丹代表团还提出,西藏牧民进入了不丹中部的马嘉塘(Majathang)和贾卡尔弄河谷(Jakarlung),甚至建造了棚子。(39)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1.
第12轮中不边界会谈于1998年12月7—8日在北京举行。第12轮边界谈判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双方突破了谈判的僵局,同时也开启了中不边界谈判的新局面。在此轮会谈中,双方主要就不丹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争议区的“一揽子方案”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40)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2.为了突破前几轮的僵局,双方一致同意借鉴中印边界谈判经验(1993、1996年),争取达成阶段性成果。1998年12月8日,中不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此《协定》较第5轮签署的“四项指导原则”,更加强调“互谅互让”原则。(41)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4.
(三)第13—18轮谈判:跌宕起伏和裹足不前的边界谈判
1998年5月,印度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秘密地进行核试验。令人吊诡的是,印度指责中国是其头号“威胁”,导致中印关系滑入冰点。(42)赵干城:《中印关系现状·趋势·应对》,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进入21世纪初,在两国高层持续的努力和引导下,两国高层不断互访,中印关系逐渐回暖。第13—18轮中不边界谈判正好是在1999年至2006年之间,中印关系的跌宕起伏也在中不边界谈判中有所体现。尽管中不两国本着“互利互让”和“互谅互让”原则,但总体上并无太大的进展。
2000年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4轮边界谈判中,不丹方面提出了新的边界线划法,将其对边境线的主张扩大到中方提出的范围以外,还提议双方专家组先利用地图进行技术性讨论。在第15轮边界谈判中,尽管中方没有完全同意不丹的主张和声索,但中方依然怀着极大的善意、信任和谅解,坚持与不丹方面继续谈判。(43)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3.
第16轮边界谈判于2002年10月12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不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大臣吉格梅·廷礼(Jigme Thinley)。在谈判结束后,中国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吉格梅·廷礼一行。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尊重不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不丹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很好,边境地区保持了和平与安宁,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感谢不丹政府多年来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两国边界谈判已进行了16轮,双方取得了不少共识,相信本着互谅互让原则,中不边界问题最终会得到圆满解决。”(44)吴黎明:《朱镕基会见不丹外交大臣》,《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5日第1版。
第17、18轮中不边界谈判分别于2004、2006年依次轮流在北京和廷布举行。此时期正值不丹南部反政府武装猖獗,不丹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两轮谈判中,尽管不方在解决边界问题上表现得裹足不前,(45)Rajesh Kharat,“Indo-Bhutan Relations:Strategic Perspectives”,in K. Warikoo,ed.,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p.154.但不丹方面对“加强两国关系”表现得十分积极,以便专心剿灭南部反政府武装。
(四)第19—23轮谈判:边界谈判与务实合作并举
2007年,尼泊尔国王被推翻。与此同时,不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2007年2月8日,不丹与印度签署了新的《友好条约》,废除1949年《印不友好条约》中第二款“外交接受印度的指导”的规定。(46)严祥海、狄方耀:《遗产、重塑与挑战:不丹的国家安全困境及其应对》,《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88页。自2007年不丹繁荣进步党组建民选政府执政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稳定,不丹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被剿灭,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了不丹尼泊尔族的难民危机。此间,中不双边贸易发展势头良好,民间交流日渐频繁,中不边界谈判和双边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19、20轮中不边界会谈分别于2010、2012年在廷布举行。这两轮谈判正值不丹繁荣进步党执政时期。中不一致认为,双方应在过去谈判的基础上继续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2013年7月,不丹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党主席策林·托杰(Tshering Tobgay)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尽管对印度十分忌惮,但对解决中不边界问题依然持积极态度。第21、22、23轮中不边界谈判分别于2013、2014、2015年依次轮流在不丹和中国举行。在第21轮边界谈判中,双方一致同意,组成中不两国联合专家小组,对白玉争议区(不方称巴桑弄)进行实地勘察。这是对中方提出的“互利互让、互谅互让”原则及“一揽子方案”的积极回应,预示着两国边界谈判在稳步向好。第22轮边界会谈于2014年7月25—28日在中国山西五台山举行。第23轮边界会谈于2015年8月23—26日在廷布举行。此次会谈,双方一致高度评价第21、22轮边界谈判和实地联合勘察取得的积极成果,愿深化和落实两国在第22轮边界谈判中达成的重要共识,本着互利互让的一贯原则,尽快找到公平合理的办法,争取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中方还提出,欢迎不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7)外交部:《中国不丹举行第23轮边界会谈》,2015年8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80/xgxw_676386/t1291725.shtml,登录时间:2020年7月15日。但并没有得到不丹方面的正面回应。
(五)第24轮边界谈判:变局与新局
“洞朗事件”是中印关系的转折点,也迟滞了中不边界谈判进程,导致谈判出现新的变局。2021年4月,双方重启了第24轮边界谈判和第10次专家组会议,这也说明此轮边界谈判是在2016年及以前达成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的。第24轮中不边界谈判和第9次专家组会议于2016年8月11—14日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不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大臣丹曲·多吉(Damcho Dorji)。(48)“24th round of Bhutan-China boundary talks begins today”,The Kuensel,Aug.11,2016,p.5.此次谈判审议并通过了《中不边界西部争议地区联合技术实地调查报告》等文件,这预示着中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缩小,两国即将开展边界划定事宜。
2017年6月16日至8月29日,中印之间爆发了长达73天的“洞朗对峙事件”,印度方面打着“保护不丹”的幌子,非法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修路活动,此举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值此之故,2017年度的中不边界谈判戛然而止,中不边界谈判也一再迁延。
2018年7月5—7日,时任不丹首相策林·托杰率团访问印度。在此次访印中,策林·托杰把中不边界谈判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访问不丹两件事情向即将执政的新政府做了政治交代。(49)“Boundary Talks with China and Indian PM Visit Only after 2018 Polls”,The Bhutanese,Jun.7,2018,p.1.与此同时,2018年7月22—24日,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陪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访问不丹,旨在商讨两国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事宜。
2019年2月,中方提议在不丹首都廷布重启边界谈判,不方没有立即做出回应。2019年8月17—18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不丹进行国事访问。就在莫迪访问不丹结束后不久,不丹方面就向外界释放消息称,中不将举行边界谈判。(50)Tenzing Lamsang,“Bhutan-China Boundary Talks to be Held Soon”,The Bhutanese,Oct.26,2019,p.6.不言而喻,不丹有着强烈的意愿与中国重启边界谈判,印度方面表面上也支持举行中不边界谈判。2021年4月6—9日,第24轮中不边界谈判第10次专家组会议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51)“Bhutan-China Boundary Talks”,The Kuensel,Apr.10,2021,p.3.此次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以1988年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四项指导原则”和1998年两国签定的《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基础,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路线图。(52)“Press Release”,October 14,2021,https://www.mfa.gov.bt/?p=11456,visited on 10 November 2021.10月14日,中不双方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北京和廷布签署了《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所谓“三步走”的框架,即先确立边界划界的基本政治原则,再具体解决边界争议问题,最后签署协议并在实地勘界。(53)《中不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印度密切关注是否会从中作梗?专家:不排除印在关键节点设置障碍》,《环球时报》,2021年10月16日,登录时间:2021年10月16日。此次《备忘录》的签订是两国多年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划界谈判和双边关系。
三、中不边界谈判的启示
自1984年以来,中不边界谈判迄今历时37年,先后共举行了24轮会谈和10次专家组会议,边界谈判先后经历了5个阶段,即建立互信和确立四项基本指导原则(第1—5轮)、不丹对争议区的声索与中方提出的“一揽子方案”(第6—12轮)、跌宕起伏和裹足不前的中不边界谈判(第13—18轮)、边界谈判与务实合作并举(第19—23轮)、变局与新局(第24轮)。尽管这五个阶段有起有伏,但总体上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
(一)殖民遗产与现实交织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国家的边界以条约形式得以确立。中不边界问题属于殖民遗产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尽管中不边界大致遵循着传统的“自然边界”“习惯边界”,但并没有正式以条约形式清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边界。19世纪以后,英国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纵深扩张,改变了不丹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关系,也对当今中不边界造成重大影响。二战结束后,印度独立建国,继承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国的殖民遗产,影响不丹的内政和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始终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借鉴国际惯例,针对具体国情,照顾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平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本着尊重不丹的主权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立场,始终按照“友好协商”“互利互让”“互谅互让”原则解决中不边界问题,但不丹对“互利互让”“互谅互让”等政策有着不同理解和利益关切。与此同时,印度为了追求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始终扮演着躲在中不谈判桌后的“第三方力量”,从中搅局、干涉中不边界谈判和解决。
(二)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中、印、不的“三角互动”关系
依照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喜马拉雅边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和高度的敏感性。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喜马拉雅边界政策,始终追求绝对的地缘政治安全。因此,印度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和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尼赫鲁认为,“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54)[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712页。1974年,印度悍然出兵吞并了锡金,给喜马拉雅山各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面对印度的野心和霸权,不丹上下可谓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规避锡金为印度所吞并的命运。(55)Karma Phuntsho,The History of Bhutan,Deli:Random House,2013,pp.580-581.不言而喻,不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中不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具有高度的地缘政治敏感性。
不丹作为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内陆小国,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特殊的战略价值和高度地缘政治敏感性造就了其在中不边界谈判中游走于中印之间。有鉴于此,中印关系、印不关系与中不边界谈判呈现出“三角互动”关系。换言之,印不关系的“松绑”或“收拢”直接决定了中不边界谈判氛围和空间。
中印关系则是直接影响了不丹在中不边界谈判的态度和政策取向。当中印关系缓和友好时,不丹对边界谈判的态度就较为积极,也容易取得成果;当中印关系紧张时,中不边界谈判就会受阻,不丹会紧紧地与印度绑在一起,但也不会直接激怒中国,会以推脱躲闪之法敷衍应对;当中印关系处于斗而不破的均势状态时,不丹在边界谈判中一般会“左右逢源”,选择务实合作的政策取向。
(三)不丹国内政局对中不边界解决构成的潜在挑战
《不丹王国宪法》规定,任何边界变动都必须得到不少于四分之三的议会议员同意。这也就是说中不边界划定若要得到实现,法定程序上必须得到不少于四分之三的议员同意方可;若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全民公投。不言而喻,这些条款对于中不边界的解决存在着潜在的障碍。
自2007年以来,不丹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在多党制的情况下,执政党与反对党就某一议题要达成共识,可能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在中不边界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丹国内政局可能会对中不边界谈判和解决可能构成潜在的挑战。
(四)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不边界解决可能构成的潜在挑战
2017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这一战略也影响到了不丹,进而波及中不边界问题。2018年9月27日,不丹临时政府首席顾问、首席大法官策林·旺楚克(Tshering Wangchuk)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向美方表达了不丹的关切,希冀美国和联合国等继续在促进世界和平、区域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56)“Picture Story”,The Kuensel,Sep.28,2018,p.11.
2019年8月11—1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John Joseph Sullivan)率团访问不丹,会见了国王、首相等不丹高级政要。访问期间,沙利文在接受不丹官媒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务院愿为不丹教育项目提供“一揽子”资金,以改善不丹的教育状况,虽然美国与不丹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通过驻新德里大使馆与不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承诺捍卫不丹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地位,支持不丹的独立主权。(57)“US Govt. Commits Support to STEM Education”,The Kuensel,Aug.14,2019,p.10.对不丹而言,若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将大大改善不丹的安全环境,也可以抵消过度依赖印度的负面影响。尽管不丹作为一个小国,政治影响力有限,但美国等域外国家也会极力拉拢,以实施“遏华”的战略。这些都对中不边界谈判乃至解决构成潜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