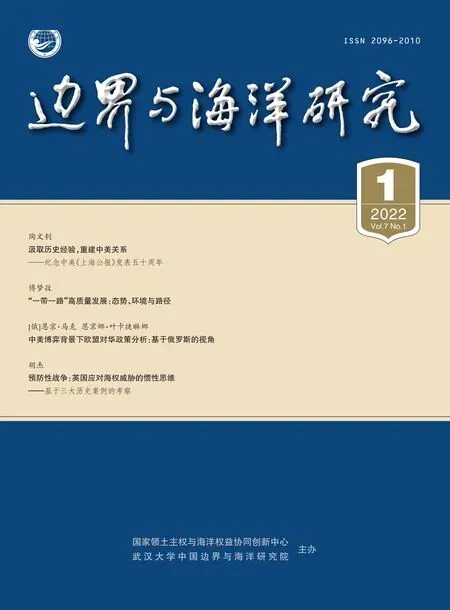汲取历史经验,重建中美关系
——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五十周年
陶文钊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应邀访问中国,会晤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此后中美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这次“破冰之旅”所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结束了中美两国的对抗和隔绝,是冷战时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使亚洲的冷战比欧洲的冷战早结束十多年,使亚太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大大降低,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摆脱冷战阴霾的亚洲国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和解是亚太地区快速崛起的重要历史条件,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关系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既有比较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许多的坎坷、曲折,如今又处在一个决定前途和去向的十字路口。五十年前两国领导人果断决策打开关系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可以作为今天处理两国关系的借鉴。
一、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世界和国际形势
在中美开启和解进程之前,两国有过长达22年的敌对和隔绝。由于美国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新中国与美国的敌对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更由于朝鲜战争引发的抗美援朝运动,也使台湾问题复杂化,更加深了双方的敌对情绪。全球的冷战主要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在亚洲,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对抗“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并把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边境作为在亚洲大陆的遏制线。(1)U.S.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FRUS),1950,Vol. 6,pp.625-626.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长期的封锁和禁运,甚至在朝鲜战争以后仍然对中国维持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更严格的禁运。1954年12月美国与中国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使中美的敌对和隔阂以这种契约的方式固定下来。中国也援助了越南的抗美战争。总之,在二十多年中,中美两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相互隔绝,没有人员、货物的交流和往来,这就使双方对对方的认识固定化了,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固定化的认识,双方关系就只能僵持下去,继续把对方视为敌人,彼此对对方发出的信息也会朝着固定化了的方向去进行解读。
然而,国际形势是在变化的,中美两国也处于变化之中。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变化,科学地评估自己的国家利益,使中美双方的决策者都强烈地感觉到与对方和解的必要性。
对美国来说,打开两国关系的需要是很明显的。首先,美国陷在越南战争之中多年,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分裂了美国社会,损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就面临国内要求结束越战的压力。而中国是越南抗美斗争的大后方。美方认为,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其次,美苏竞争日趋激烈,美国面临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空前的扩张,中美和解将成为对苏联扩张的重大牵制,便于美国“重建某种均势”。(2)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11,p.387;基辛格:“序言二”,张德广、杨文昌主编:《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再次,新中国经受住了美国及其盟国20多年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没有倒下,而且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尼克松对中国的巨大潜力深信不疑。
对中国来说,改变中美关系的必要性一样明显。首先,“文革”使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这种局面亟待改变,由于美国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有助于中国恢复和拓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安全威胁,改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国对付苏联的威胁。第三,由于美国深深地介入了台湾问题,中美和解有助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中美双方互有需要,又都认为搞扩张的苏联对各自的威胁超过了中美对彼此的威胁,“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基辛格1971年7月 10日会晤周恩来时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往来,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陈东林、杜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1966—1971),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4页。美方甚至认定,如果中苏真的发生战争,而苏联占了优势,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4)Henry Kissinger,On China,p.218.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中美走到了一起。
中美虽然长期隔绝,却都十分关注对方的状况,以及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双方对对方的看法也在缓慢发生变化。尼克松是共和党里的右派,20世纪50年代以坚决反共著称。但他的观点是在变化的。1967年10月,他在著名的《外交》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文章,其中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亟须把握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简直就付不起让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5)Richard Nixon,“Asia After Viet Nam”,Foreign Affairs, Vol. 46,No.1,October 1967.毛泽东本人敏锐地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篇文章。1969年1月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再次阐述了这一意思:“要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本届政府任内所有联系的渠道都是开通的。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对各种思想、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都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活在孤立状态之中。”(6)Richard Nixon,“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1996,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39549.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中美关系。中方注意到这个讲话,并且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做法:毛泽东亲自批准在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发了这篇演说的中文译文,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谓破天荒,美方不可能忽视。同日的报纸上还登载了一篇批评尼克松就职演说的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很低。但尼克松并不因此轻视中国。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即他在提交给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他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的贡献,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7)Richard Nixon,“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February 18,1970,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40665.1971年7月 6日,就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的前三天,尼克松特地在堪萨斯城对中西部地区媒体主编作了一场关于世界上“五大力量”的演讲,谈到“五大力量”就是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他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民”,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本届政府有必要采取主动来结束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孤立状态,中国的孤立“是对世界一个不可接受的危险”。(8)Richard Nixon,“Remarks to Midwestern News Media Executives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Domestic Policy in Kansas City,Missouri”,July 6,197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 presidency.ucsb.edu/node/240377.尼克松的这些讲话表明,他认识到,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掌握了核武器,又即将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势在必行。那些媒体主编们未必特别看重尼克松的这个演讲,但中方却很在意。基辛格到北京后,周恩来在第一天的会谈中问他是否看到了尼克松的演讲,并表示中国不会参与“超级大国”的比赛。这使基辛格略感尴尬,基辛格说,他只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总统的演讲。第二天早餐时,基辛格就看到了周恩来派人送来的尼克松的演讲稿,上面有周恩来作的记号以及他的中文批语,而且写着“仅此一份,阅后归还”。(9)Chris Barber,“Nixon on the Record:End China’s Isolation”,July 6,2015,https://www.nixonfoundation.org/2015/07/president-nixons-america-multi-polar-world/.
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由于美国还在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关系一直是毛泽东心中放不下的问题。1965年1月,中方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再次访华。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天南海北”式的长谈,其中中美关系是重点。毛泽东说:“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人民被分开了。15年了,老死不相往来。今天,隔阂更大了。不过,我是不相信最后会以战祸告终的。”(10)Edgar Snow,“Interview with Mao”,The New Republic,152,No.9,Issue 2623,February 27,1965,https://newrepublic. com/article/89494/interview-mao-tse-tung-communist-china.斯诺把对毛泽东的长篇访谈发表在了美国的《新共和》杂志上,可惜,这篇访谈没有引起美方足够注意,美国官方一直把斯诺看作是为共产党搞宣传的。1969年10月以后,中美双方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小步舞”、通过种种渠道发出信息,包括通过多个第三方的传话、乒乓外交,终于实现了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商定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
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中美关系解冻发生在冷战的高峰时期,而冷战的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是有我无敌的。中国与美国本来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现在又处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之中,再加上二十多年的隔离所造成的种种误解、错觉和误判,两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表现在官方的宣传和政策上,而且深入到了普通民众的思想之中。正如尼克松所说:“二十年来,我们两国搁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这就肯定造成了误解。经常有作出错误估计的危险。缔造持久和平也成为不可能的了。”(11)Richard Nixon,“Fourth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ay 3,197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55404.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交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是这个原则的缔造者、践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左”倾思潮蔓延到外交领域,尤其是在批评了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所谓“三多和一少”理论后,(12)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对我国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意见,主要是:对外政策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应采取和缓方针;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考虑采取新措施,打开中印关系僵局;对别国革命的支持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毛泽东在1962年9月批评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多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缓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多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当代世界》,2006年第9期;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8—569页。在世界革命的宣传方面越来越 “左”,鼓吹“四面出击,打倒一切”。但尽管中国表面看来十分强硬,要维护自己“反帝反修”的革命形象,实质上中国外交在行动上是谨慎务实的,中国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也意识到行为的界线,对维护国家的利益需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和判断。因此中国没有派兵出国去促进别国的革命,也没有侵略、颠覆别国政权的事情发生。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外交也逐渐回到了比较正常的轨道。(13)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33页。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国家,“美国特殊论”无处不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流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把外交政策建筑在价值观之上” 是从决策者到一些外交从业人员的口头禅。人们普遍相信,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证,很多分析家几乎把这一命题奉为信条。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14)Henry Kissinger,On China, p.274,425;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郑州:河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在对华关系中,美国人也总是抱着一种“传教士”的热情,有一种改造中国的强烈欲望,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但美国可以指导中国进行改革,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之际,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aurt)大使还在策划国民党政权的改革。在二十多年的隔阂时期,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及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一直是比较僵硬的,但一些比较现实、客观的看法也在逐渐萌芽。1959年的《康仑报告》,(15)如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318页。1964年3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发表的《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和由他主持的听证会及98名专家联名发表的公开声明,都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打开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为尼克松政府的政策转变做了舆论和民意上的准备。
在中美关系走向和解的过程中,可否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切割开来是一个大问题。双方决策者都清楚两国之间巨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双方都是从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与对方进行和解,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信仰、理念和生活方式。尼克松和基辛格懂得,西方的人权和个人自由的理念难以直接照搬到一个几千年来依照不同理念组织自己生活的文明中去,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16)Henry Kissinger,On China, p.426.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一开始就说: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你们坚信,你们的信念必胜。我们对于未来也有我们的信念。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说:我们知道,你们深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也不会要我们在原则上让步一样。(17)Henry Kissinger,On China, p.264.他在人民大会堂答谢宴会致辞中说:“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18)Richard Nixon,“Toasts of the President and Premier Chou En-lai of China at a Banquet Honoring the Premier in Peking”,February 25,1972,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 presidency.ucsb.edu/node/255121.正因为双方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是从各自的理念和信仰出发去要求对方,避免了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两国的和解才得以进行下去。
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苏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白皮书》中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清扫”和“消毒”,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开展了全面深刻的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教育,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多次运动。与此同时,苏联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这些影响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苏共对中共内部的影响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地步。中苏交恶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核心是国家利益,但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强烈,直至双方进行公开的论战,中方正式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提出:“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说明他认为“反修防修”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此后“反修防修”的告诫不断升级,直至1964年7月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9)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505页。这就是说,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相比,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实际上,正是这种状况推动了中美和解。正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当中苏两国军队在西伯利亚冻土地带一条默默无闻的冰封的江面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20)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认为,决策者的决定和行为要受民意和舆论的制约,这没有错,但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决策者足够果断,足够大智大勇,并且认准了方向,拿定了注意,那么他也是可以反过来引导舆论、教育舆论的。本文列举的尼克松的多次文章和讲话,实际上都是对美国舆论的一种引导。尼克松派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是要冒风险的,美国国内和盟国都可能对此作出反弹,他是要押上自己的政治资本的。但结果,打开与中国的关系比先前估计的更容易让美国政界和民众接受。尼克松访华的首席翻译傅立民(Chas Freeman)在访华后的一年中,收到了上百份邀请,要他去介绍访问的情况,介绍中国。由于二十多年的隔绝,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无知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21)Nancy Tucker (ed.),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279.结果是,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了与中国的和解,美国媒体的反应也基本是正面的。
三、聚焦于解决关键问题
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是美国在台湾的介入妨碍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美和解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基辛格1971年7月、10月对中国进行两次访问为总统访华做准备。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开门见山直奔台湾问题。周恩来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指出台湾属于中国有1000多年了,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中美和解提出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限期从台湾撤走所有军队;废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条约。这样,周恩来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的三项基本要求。基辛格表示,随着印度支那战事的结束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将减少驻台军队,军事问题不会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他承诺:“至于台湾的政治未来,我们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政治演变很可能朝着周恩来总理向我指出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当时认为,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台湾除了接受某种形式的统一外将别无选择。基辛格还保证,美国不支持所谓“台湾独立运动”,美国政府中的任何部门与‘台独’都没有关系。(2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Kissinger and Chou Enlai”,July 10,1971,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66/ch-36.pdf;Alan Romberg,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American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U.S.-China Relations,The Henry Stimson Center,2003 p.33.基辛格向中方交了底,这是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得以顺利成行的前提。
尼克松在1972年2月 22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再次确认了美方对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
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发表类似“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
第二,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美国在逐渐撤出台湾时,会竭尽所能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入台湾;
第四,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
第五,不支持台湾方面“反攻大陆”。
这几点是1971年周恩来与基辛格反复讨论过的问题,现在由尼克松总统系统地予以确认,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承诺。其中第四点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美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一贯要求,中方从未接受过。周恩来清楚地表示:如果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就会妨碍中国政府行使主权,就等于接受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中方对此不能接受。(2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ixon and Chou Enlai”,February 22,1972,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982.pdf?v=05b196a88fec4b3489bf30e792e11f2a.
尼克松访华最重要的成果是中美双方达成了《上海公报》。由于中美尚处于和解的初期,双方对许多国际问题都有不同看法,公报采取了双方各自坦诚地分别阐述对各种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立场的做法,使公报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外交文件。美方关于台湾的立场是这样表述的:“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s),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4)钟建和编:《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这一说法确认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即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就明确了台湾的主权问题,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第二,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第三,美国对上述两点没有异议。由于当时美国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因此美方表述中的“中国”的涵义是不清楚的。美方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但没有提及1954年的美台条约,即是说留待以后解决。基辛格后来写道,在《上海公报》中双方商定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表达方式: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把解决的办法留给未来”。(25)Alan Romberg,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p.47.不管怎样,《上海公报》中美方的这一表述走出了对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上海公报》中的遗留问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简称《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 17日)》(简称《八·一七公报》)解决的。《中美建交公报》载明:美方“承认(recognizes)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样,“中国”的涵义就清楚了。“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台之间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这是美国在处理任何涉台问题上的一个总的原则,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中美建交公报》还重复了《上海公报》的说法,美方“承认(acknowledges)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26)钟建和编:《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144—145页。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明确和确认。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留下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这是由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27)《施燕华大使见证中美建交谈判》,2008年12月15日,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jxE。但邓小平在当时果断拍板,中美先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这个决定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1982年4—5月间,在中美关于美台军售问题的谈判期间,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一再分别致函中国领导人赵紫阳、邓小平和胡耀邦,强调美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强调中美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的重要性。他在1982年5月3日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中说:“我们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会允许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一原则的承诺。”(28)U.S. Department of Stated (ed.),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82,GPO,1985,pp.1028,1030.经过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严肃的谈判,中美双方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八·一七公报》。公报中美方再次承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虽然美方先前做过类似的表态,但在美国的任何官方声明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一说法,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两国之间的公开文件中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力度更大的重申。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售台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29)钟建和编:《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148—149页。在这里,美国政府作出了三项承诺:“不超过”“逐步减少”“最后解决”。公报虽然仍然没有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的承诺仍然带有模糊性,但它对美国是个约束,也为中美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坚持原则,展现灵活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述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具体谈判过程中,中方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做法,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表述的灵活性结合,彼此有多处相互妥协。
《上海公报》的主旨是要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但如何提出、如何措辞是很有难度的,尤其是在当时美国尚未与中国建交,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的情况之下。最后,双方同意了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即中方阐明自己的立场,美方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立场“不提出异议”。
周恩来提出了三项要求,在《上海公报》中美方回应了从台湾撤军的要求,但对“废约”的问题却没有提起。美台条约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也是1971年7月基辛格在与周恩来会谈中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时,既对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的进步表示赞许,又幽默而宽容地把美国政策变化比作“猴子变人”,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30)见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而对于公报中未提美台条约,美方代表团有成员十分不满,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 Marshall Green)认为,它就像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 12日的讲话中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一样。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有记者提到这个问题,基辛格回答说,今年早些时候总统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了。(31)Nancy Tucker (ed.),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pp.275-276.
建交谈判是要把一个中国的原则具体落实下来,双方遇到的困难更多,主要的妥协有三项。第一,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废除1954年的美台条约,但表示,废除一项条约必须通过国会,国会有繁琐的程序,还会有辩论、要表决,这就可能耽误正常化。美台条约本身有一个“终止条约”的机制,即缔约一方将终止条约的通知送达另一方一年后条约终止生效。终止条约可由总统做主,无须经过国会,美方希望采取这种方式解决“废约”问题。中方考虑到美方的实际困难,也是为了不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出现意外,接受了这一解决办法。(3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施燕华大使见证中美建交谈判》,2008年 12月15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jxE。第二,美方要求中方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遭中方拒绝。美方退而求其次,提出要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发表一项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要求中方不予以反驳。中方回应说,中方也要发表一项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33)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版)》第3卷,1972—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60页。第三,最棘手的是到了谈判的最后关头,美方又提出,1980年后美国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对中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同意美方条件,售台武器的问题可能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拒绝,正常化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邓小平权衡利弊,最后果断决定,先建交,售台武器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34)《施燕华大使见证中美建交谈判》,2008年 12月15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jxE。这也是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由来。
《八·一七公报》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双方的主要争议是:(1)中方要求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中双方确认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接挂钩,美方反对;(2)美方要求将其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与中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直接挂钩,遭中方拒绝;(3)关于美方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中方力求尽可能明确,即美方要确定一个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美方则力求含混。(35)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261、266—267页;Nancy Tucker (ed.),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pp.362-363.正因为美方在公报中的承诺中尚有模糊之处,8月 17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了美国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进一步阐明了中方立场,要他向里根总统转达:第一,期待美方认真履行承诺,不要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涵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第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前提。第三,《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有很大的机动权限,美方应正视这个问题。(36)薛谋洪、裴建章等编著:《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239页;采访朱启帧大使。
五、汲取历史经验,重建中美关系
四五十年来,构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的两国关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而且帮助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今天,两国关系却处于“破冰”以来的低点,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提供了部分答案。他说:最近中国有了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研究设施,世界上运算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建造新的机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37)Barack Obama,“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5,201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89120.“斯普特尼克时刻”指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航天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人普遍产生了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焦虑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底的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面临“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的地位。而奥巴马明确宣布:“我不接受世界第二的地位。”(38)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7,2010,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87936.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事实上,这个战略的实施并非特别得力,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也不大。
特朗普是借助美国的民粹主义当选总统的,他把中国当做美国经济不景气、中产阶级萎缩、丢失就业岗位的替罪羊,不仅发起了对华贸易战,而且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使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也严重伤害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拜登政府就任后,对特朗普留下的遗产抛弃的少,继承的多,没有根本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却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激烈的战略竞争对手,把中美关系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者的混合物。虽然拜登口头表示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但美方说一套,做一套,实际是在强化同盟体系,指望盟国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对中国再次挥舞人权大棒,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在对台关系上打“擦边球”,继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中美关系到了需要再次重建的关键时刻。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四五十年来两国关系的历史就是双方不断确认共同利益的过程。现在,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都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双方应该以拓展共同利益为导向来处理两国关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的两个大趋势是全球化和多极化。中美两国间彼此相互依存是几十年全球化的结果,要单方面 “脱钩”是脱不了的,几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为了赶超美国,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实力。中美双方在《上海公报》中就确立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在《建交公报》中又重申了这个原则,中国历代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霸权主义,不搞霸权主义。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39)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30/c64094-24773108.html。希望美国决策者走出对中国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不再把中国当“假想敌”,如实看待中国的发展,像当年打开中美关系的前辈那样,与中国一起实现中美关系的新和解,“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这才是对两国、对地区和世界都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