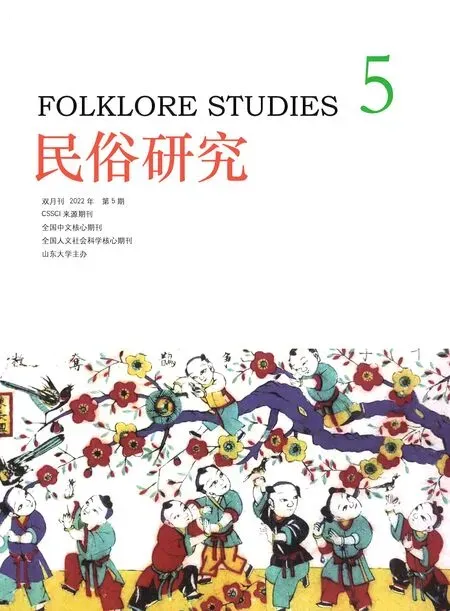采风: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变
祝鹏程
本文中的“采风”指的是采录民间的言语表述和艺术素材,通过加工创作出全新的表达方式和文艺作品的行为。在中国文化史和民间文艺学科史上,采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界对采风一直有着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从文本真实性与学术伦理的角度对其展开批评(1)如刘魁立:《谈民间作品搜集工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32-48页;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连载于《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2004年第2期。;另一些学者则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具体时段对采风的意义多有肯定(2)参见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价值的认定与把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毛巧晖:《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以1949年至1966年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两种论述立足于学科建设的不同侧面,均有其价值。
采风的复杂性在于,其不仅是一种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方式,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文化生成方式。正如刘宗迪在讨论20世纪50-60年代民间文学工作时指出:“民间文学采集、整理和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文学创造和文明传承。”(3)刘宗迪:《超越文本,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有可深化的空间,尤其应该突破文本本位的视角,去发现实践的社会效应,并注意到其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和沿革。对于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实践,如能借鉴文明论的视角,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明体,在长时段中考察采风的流变与传承,“从当代中国经验中追溯出‘传统’的影响,强调在长时段视野中思考中国文明的当代性”(4)贺桂梅:《“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则能更充分地发现采风的价值。
因此,本文将采风这一概念置于中国整体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语境中,并结合现代民间文艺的学科进程与社会境遇展开考察,梳理采风的知识谱系,揭示采风行为背后的认知与实践逻辑,重新发现其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
一、“采诗观风”:作为礼乐文明生成方式的采风
关于“采风”的记录古已有之。《周礼》《国语》《孟子》《史记》等典籍或隐或现地记载了“王官采诗”的行为。其中尤以《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最为全面:“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5)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2-1573页。尽管有学者怀疑西周已有采诗的实践,认为是后世儒家增饰的结果(6)相关质疑参见崔述:《读风偶识》,《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3页。,但考察近年来出土的一些先秦文献,如上博简《孔子诗论》(战国),其中记载的“《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采)焉”(7)对本段文字,各家有不同的识别和标点,但并不影响全文大意,此处采用王志平先生的释读。参见王志平:《〈诗论〉笺疏》,朱渭清、廖明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等内容,无疑支持先秦存在“王官采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王官采诗”虽然深入到民间,但采诗形成的文本并未回到民间去,其主要在贵族和士人阶层中流传,在王朝和士人阶层间发挥作用。
对于“采风”之“风”,最早的解释来自《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8)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按这一解释,“风”包含两层意思,一为教化,二为讽谏。这体现了汉儒的政治与文学思想,即利用诗歌含蓄委婉的特点展开上对下的教化与下对上的讽谏。历代不断补充阐释,尤以朱熹《诗集传》最为典型:“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9)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此论继承了汉儒的教化观,又强调风是民间歌谣,再经郑樵等人发扬,在后世广有影响。在历代儒家文献的反复书写和解读下,“采风”被赋予了双重的涵义:一即采集民间的风谣、舆论与谶语;二即从采集的文本了解地方风俗、民意,使其服务于国家管理和教化。
在儒家设想的政治蓝图里,“声音之道,与政通焉”(10)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077页。,草野的“民风”与朝廷的“政风”紧密相连,故采风很早就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生成机制。《毛诗序》指出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显示出民谣诗歌与礼乐文明的关联。“礼”与“俗”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12)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第1页。,采风在传统王朝的社会整合中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采风是信息流通的渠道,士人(或与统治者相对应的其他群体)可以借助这一渠道,通过搜集、增饰里巷歌谣和童谣谶纬,来表达特定的意愿。有学者指出,《诗经》中的诸多篇章蕴含了西周后期贵族阶层对王权的政治诉求,经由“采诗”而成的不少篇章,颇似今日的“报告文学”。(13)李山:《礼乐大权旁落与“采诗观风”的高涨——“王官采诗”说再探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
自上而下的管理与教化:各家对采风的描述不同,但大致可以概括为“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5页。等四个步骤。派人在民间广泛采诗,再由专人整理后上呈给为政者。为政者借此了解民间舆情,反思、调整自身统治。同时借此传播教化,如在礼仪场合演唱、展演整理后的文本,使得参与的贵族士大夫受到教育,再由他们将相应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传导给次一级的民众,从而达到风行草偃般的治理效果。
可见,从诞生之日起,采风就离不开相关人员(王官、乐官、文人等)的加工(包括意识形态上的规训和修辞韵律上的修整)。借助加工和传播,采风起到了贯通上下、沟通礼俗,即联系统治者、贵族士人和民间的作用,执政者以此了解民风民情、传达王政、化民成俗;搜集者借此制造舆论,将民意反馈给执政者。采风寄寓了为政者通过建立王朝、贵族和民间的良性互动,达到政通人和的理想。采风者将地方社会的历史与传统发掘出来,并加以整饬,再将其整合到国家大一统的文化与历史中。“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15)刘志琴:《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这种文化的黏合作用有力联系起中央与地方,王朝采诗所到之处,即是王风教化所及之地,而地方献诗便表现了对王朝的臣服。
采风者将社会舆论与国家导向统合起来,产生新的文本,再将新文本传播开去,完成文本的再生产。在传统“天命”观念的作用和“天籁”的浪漫化修辞下,形成自然化、道德化的文本,起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权威效果,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统一性与权威性,是通过民间、王朝权力与贵族阶层在“化礼成俗”与“以俗入礼”的多元参与中得以确立起来的。“正是建基于地方社会的多样性与国家大一统之间相互吸纳、不断磨合的历史过程,以礼俗互动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才得以奠定”(16)张士闪:《眼光向下: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
因此,采风不仅是一种文本采录活动,更是一项社会整合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程,其建构了一套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设计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活动,产生出一批整合性的文本,从而引导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信息和舆论,并印证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维系国家运转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基于民间文化资源而展开的文明创造与文化生产,采风不是对民间言说的刻板实录,采录者往往会对文本做加工修饰,包括对作品主旨、音律、句式、韵脚等的调整。采录文本脱离原生语境,被注入新的政治理想与美学追求,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后世往往被用作“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工具。如《诗经》既在仪式仪典中沟通人神,也可在国家间交涉中婉转达意;既可作为贵族之间互相赞美或讽劝的依据,亦可作为展示读书人修养的文学言辞。(17)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196-211页;夏承焘:《采诗与赋诗》,陈水云编选:《词体与声情》,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第18-29页。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郑伯请晋国的赵孟、鲁国的叔孙豹等人会宴,郑国的子皮赋《野有死麕》末章,以男女情话“无使尨也吠”喻指不要让敌国有可乘之机。赵孟以《棠棣》应和之,号召各国应像兄弟般团结以镇服敌人。(18)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635-636页。这里的赋诗超越了原诗的含义,一变而成为外交辞令。
先秦的“采诗观风”主要体现为信息传播与社会整合功能,在后世发展中,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借助采风来推动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通过吸收民间文艺的素材和形式,加以符合时下志趣与主张的改造,产生了大量流派与作品,如在乐府诗基础上形成的歌行体、脱胎于民间传说的唐传奇、深受民歌影响的竹枝词、广泛吸收通俗俚语的元曲等。尤其是明清以降,市民文化崛起,进一步催生了“真诗在民间”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等观念,汲取民间资源,以风谣直抒胸臆的特点补救当时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学风气,从而催生出具有创新性的文体形式,更是成为新的文艺作品生成的重要途径。冯梦龙、凌濛初、郑之珍、蒲松龄等人在创作中直接大量吸收并借鉴了民歌、传说故事与俗曲小戏,让“民间性情之响”可以“列于诗坛”(19)冯梦龙:《叙山歌》(《山歌》序文),参见冯梦龙原著,顾颉刚校点:《山歌》(娄子匡主编“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2种),东方文化书局,1970年。,开创了近世通俗文艺繁荣的局面。这些作品尽管多有“发名教之伪药”处,但总体上仍是为了达到让“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20)冯梦龙编著,陈熙中校注:《喻世明言》,中华书局,2014年,“叙”第3页。的教化效果。
古代的采风由官僚阶层和士人群体主导。当代表皇权的意识形态下达时,士人群体和乡村精英就起到了衔接官与民的作用。尤其是明代以来,随着士绅阶层出现,采风实践逐渐下移,众多乡绅大夫身体力行,将民风民情的采集传播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基层文化建设,如宣讲圣谕、制定乡约家训、开办会社书院等,大力推动了“礼”的民间化过程。很多采风形成的文本也不再仅仅流传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而是传播到了市井民间。但在儒家文化对“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划分下,士人和民众之间仍存在巨大的阶层鸿沟。民间流传的蒲松龄以摆茶摊搜集聊斋故事之说尽管浪漫,但并不符合传统读书人的行为规范,恐怕只是后人编造的美谈,鲁迅早已做出“不过委巷之谈而已”(21)该说见于晚清文人邹弢的《三借庐笔谈》,相关质难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不足为信的论断。对于传统采风中士人和民众的接触程度,后人不必太过高估。
自诞生之日起,采风就是一套伴随复杂权力运作的文明生成方式,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更是国家了解民间舆论、传播意识形态、沟通礼俗文化的有力手段。经由采风,俚俗的乡土之音被转化为温柔敦厚、辅助政教的诗乐,被赋予“兴、观、群、怨”的功能、敦礼明伦的教化职责和中正平和的审美风格,成为儒家文明的有机组成;里巷风谣被赋予新的意义,承担起翻新传统、激活文化的责任。可以说,将民间文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于时下的文明创造,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二、从“创造新文化”到建构“民族形式”:采风的现代转型
晚清以降,在外侮入侵与传统崩坏的双重危机中,中国走出“天下”,进入“万国”,开始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征程。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浪漫主义和启蒙思潮的催动下,他们把视野投向民间,发起“眼光向下的革命”,担负起了救国新民的历史使命。
在反封建的时代主潮下,知识分子展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他们对儒家礼教展开激烈批评,视其为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要否定旧的统治秩序,就要彻底打倒礼教的规训。他们在研究中激烈批评历代儒生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认为儒家为了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歪曲了《诗经》原意,将民歌变成了维护礼教的工具,极大歪曲了原本的民间意趣。钱玄同、顾颉刚、郑振铎等新文学学者努力为经典“袪魅”,钱玄同大胆论断:“《诗经》只是一部最早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22)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3页。因此,要“把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爬扫开来”(23)郑振铎:《读毛诗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通过研究,将其由政治教化的文本,还原成反映民间生活和民众情感的艺术性文本。
在知识分子眼里,民间文化是一笔复杂的遗产。一方面,他们对“民间”多有着浪漫化的想象,认为民众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民歌谣谚、故事传说、方言土语中蕴含着粗糙、朴野的诗性智慧。故他们大力肯定了民间文学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刻画,和其中蕴含的自然真挚的情感、质朴清新的语言,视其为“民族的文学的初基”(24)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江阴船歌〉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集类编·花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和建设新文化的基础与源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高度评价民间文学“自然、活泼、表现人生”的特点,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和“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25)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页。的观点,试图通过将中国文学的源头定位为“民间”,为新文学发展寻找新的坐标与动力。
当然,他们也充分意识到民间存在着“落后”的面貌。如顾颉刚点明“民众文化虽是近于天真,但也有许多很粗劣许多不适于新时代的”,因此,民间文化必须经历现代性的价值评估,才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源,即“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26)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苑利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页。在这里,民间文学被视为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国民想象和国家建构的重任。
现代民间文艺学由此诞生,并产生了“为学术”与“为文艺”(27)周作人:《〈歌谣周刊〉发刊词》,苑利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两大诉求,展开了歌谣运动等一系列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运动。一批知识分子选择了“为文艺”的方向,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资源加以利用。如歌谣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从民歌等民间文艺中吸收养分来推动新文艺发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便认为搜集民歌“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同时引用意大利外交官、北京民歌搜集者卫太尔(Guido Amedeo Vitale,通译韦大列)的话,表达了民歌之于新诗的意义:“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28)周作人:《〈歌谣周刊〉发刊词》,苑利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胡适、刘大白、沈尹默、康白情等取法歌谣,或借鉴格律形式,或吸取语言风格,或直接以方言俗语入诗,创作了一批别开生面的新诗。
传统往往有极大的约束力,尤其是已经内化到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采风,更是有着无可比拟的惯性。尽管“五四”一代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儒家倾向,但他们对民间文艺的利用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辈的行为模式——从民间文艺资源中熔铸出国家层面的新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做高高在上的“读书人”,试图重塑自身与民间的关系。但他们与民众的接触程度相对有限,很多采风都是依托个人兴趣与偶然机会展开,往往又会因偶然事件影响而结束,使实践缺乏系统的计划。如顾颉刚对《吴歌甲集》的搜集,就缘起于他回乡养病。正如洪长泰所说,“五四”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实践仍停留在想象和理解民众的阶段。(29)[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对于新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吸收民间文化资源,各方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趣味给出不同的方案,产生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20世纪30年代,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抗战激发的民族救亡意识的高涨,促使左翼知识分子思考如何建构一种更具统合性的国家想象。自毛泽东1938年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要建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0)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后,延安的文艺界迅速提出了“民族形式”的命题,并作为“兼顾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国家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性方案”(31)贺桂梅:《“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尽管各家对“民间形式”在“民族形式”的建构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多有争论(32)当时的讨论在概念使用上较为混杂,如“旧形式”“民间形式”“地方形式”等,这些概念既有重叠,也有差异,相关概念的辨析可参见徐逎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但大都承认“民间形式”是新文艺“民族形式”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不仅可以为“民族形式”的构成提供基质和活力,还能够拓展新文艺的群众基础,产生喜闻乐见的效果。
周扬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里,明确了利用“旧形式”(即旧白话小说、唱本、民歌、民谣,以至地方戏、连环画等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形式)的目的:“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加坚实与丰富。”(33)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21-622页。柯仲平亦言:“若不从利用旧形式做起,那末,我们实在找不出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其它更好的办法。”(34)柯仲平:《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徐廼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了“工农兵文艺”的范畴,完成了“一种建立在新的政治主体和文化想象基础上的国家构想”(35)贺桂梅:《“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从而发展和深化了“民族形式”。《讲话》如此论述民间文艺的价值: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相对于“五四”学者的书斋立场,延安知识分子在边区建设中形成了更加现实的民间观,他们对民间文艺的价值和弊端有着深切的认识。从民族主体建构的角度说,民族形式的形成不能离开民间文艺,民间文艺作为新文艺的基石而存在;但在全新的文艺标准前,它又呈现出“粗糙”“萌芽状态”的局限性,如秧歌,其固然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但因形式简单,无法表现复杂的情节、塑造鲜明的人物。因此,在将“矿藏”和“原料”转化为新的文艺时,只有以新文艺的体裁(即“五四”以来借鉴西方形成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对其进行“去粗取精”的改造提升,才能将其转化成为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艺作品。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3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页。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改造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旧形式,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展开价值和形式的提升,使其变成具有民族立场和现代性追求的新文艺,进一步将“民族形式”的追求落实到实处。
《讲话》发布后,解放区正式形成“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的大众化。知识分子通过深入民众采风,采录了大量故事、歌谣、说唱、戏曲、舞蹈、剪纸,结集为《陕北民歌选》《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等成果。马可、李季、赵树理、丁毅、贺敬之、林山等艺术家得以涌现,他们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掇英撷华,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艺术形式,如马可等人结合民间秧歌剧与西欧歌剧而产生的民族歌剧;赵树理综合传统说书与现代小说的叙事优点而产生的通俗化小说;贺敬之、李季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的新诗等。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更是结合了优秀的民间文化和新文艺的美学和政治理想,在最大程度上兼顾了革命的需求和民间大众的欣赏趣味。
以民族歌剧《白毛女》为例,此剧改编自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为了将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改编成革命通俗文艺,周扬等人给出了全新的主题设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38)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全剧充分吸收了秧歌剧的风格,为了能够突出人物性格,又借鉴了西洋歌剧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塑造了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性格鲜明的音乐形象。而在表现这些形象时,则充分使用了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如用河北民歌的欢快曲调来描绘喜儿的天真,用山西民歌低昂的旋律塑造杨白劳的忠厚,用高亢的山西梆子表现喜儿的抗争。有论者还指出,《白毛女》的政治宣传充分依赖对民间家庭伦理的确认。(39)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58页。扎根于民族传统,又对传统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得《白毛女》成为“歌剧民族化”的典范,从而构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真正内涵。
在抗战的炮火声中,左翼知识分子最终在众声喧哗中胜出。新文化的建设被归拢为一个目标——建构“民族形式”,塑造具有民族主体立场、属于人民大众的新文艺。它不同于“五四”“抑礼扬俗”的态度,更多强调的是对雅俗文化的调和与萃取,在此基础上创造现代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主体性。(40)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503-1507页。平心而论,这种做法无疑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在一些情境中极易被庸俗化。但它为民间文艺参与现代社会的建设和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切实的方案,有力激活了传统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正如周扬所说:“解放区的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保持了密切的血肉联系。”(4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9页。
“民族形式”是在现代价值与民族主体意识之间获取平衡的策略,其充分吸收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同时又经过必要的提升,使得民间文艺脱离了传统社区的局限,产生出综合民族气派和现代追求的新形式。新形式融合了现代意识与乡土内容,既回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又蕴含了丰富的民间素材和地方文化因素,便于民众的接受,并有力推动了民众对国家的想象与认同。这一做法也回应了《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2页。的期待,而所谓“提高”,仍然是一种由“俗”中提炼、产生出新的文化,并以此推广到全国的做法。
三、“恢复”人民的主体性:新中国采风范式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构成新时代的国家主体,《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对民族形式的追求被延续下来,并推广到全国。建设工农兵大众的“人民文艺”成为文艺的主要任务。“人民性”成为文学评价的首要标准,“人民口头创作”一度取代“民间文学”,歌谣、故事、传说等因承载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抗争,受到高度肯定。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文简称“中国民研会”)成立大会上,主席郭沫若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如《诗经》、楚辞、六朝民歌、明清小说等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提出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是:(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二)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五)发展民间文艺,“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43)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贾芝主编:《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五十年》,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他同时呼吁:
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44)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贾芝主编:《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五十年》,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页。
郭沫若的讲话有意强调了采风传统的延续性,将当下的采风视为对古代“采诗”传统的致敬。除了第四点外,其他各点都指向进一步的文明创造,即将民间文艺从其原生语境中提炼出来,加以改造,成为独特的文艺作品。
当时颇有影响的《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也指出:
较之民间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形式。因此文学要吸收民间文学,主要是对民间文学所产生的艺术原则加以创造性的采用,多方运用民间创作的多式多样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文学中必然会站在决定的地位,它们经过熔炼被有机地吸收到文学中来,成为作品内容和风格的不可分割的部分。(45)[苏]索科洛娃等:《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刘锡诚、马昌仪译,参见钟敬文著,董晓萍编:《钟敬文全集》(第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77页。
显然,新中国首先将民间文艺视为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资源,赋予民间文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任。人们相信,挖掘优秀的“人民口头创作”,利用其中的民族性因素,以新的标准对其改造提升,可以克服民间文艺在表现形式上的局限性,创造出全新的“人民文艺”。
正因为认识到民间文艺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故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自发松散、承载了差异化的趣味和追求的采风实践,新中国的采风工作得到国家体制的支持,呈现出了鲜明的制度化与规模化的追求。社会主义采风能够展开,得益于新中国强劲的国家政权建设能力。国家建立起“一个深入乡村社会并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的政权体系”(46)董宇:《国家治理视域下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形成一套高效的动员机制,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民间文艺的新时代来临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承担起全国民间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与高校、各级政府的文化与宣传机构,以及基层的群众艺术馆、文化站紧密协作,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深入民众展开普查,并发动基层的爱好者参与其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联结中央与基层、发动全民参与的采风制度。
任何时代的“俗”都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民间文艺存在着因果报应、封建迷信以及低级趣味等因素,如何将其提升为具备“人民性”的艺术?对采录文本的修改就成为必然。为了在大规模的采风实践中确立文本改编的合法性,一套独特的修辞应运而生。
这套修辞首先承接了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又受到新中国阶级论的影响。当浪漫主义与“人民性”的话语结合起来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民”的理想化认知。在面对民间时,采风工作者预设了一个纯粹的、理想化的民间,这个民间是由阶级成分单一的“劳动人民”组成的,具备了完美的属性,蕴含着自由不羁与个性解放的“真精神”。这些因素不是后天赋予的,而是本来就内在于民间的。
因此,在采风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有利于呈现民间理想形象和劳动人民阶级本质的故事和歌谣,才被认为是人民的口头创作。而任何有悖于“人民性”原则的文本,比如歌颂统治阶级的歌谣、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趣味不高的荤段子,往往被认为或是腐朽的时代和统治者从外部污染民间的结果,或是统治阶级篡改民间意志,将剥削阶级的思想强加给人民造成的。正如孙剑冰所说:
材料是有差别的,有真也有假。什么叫假?凡是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实质,而又冒充劳动人民的材料,可以说是假的。这样的材料的确是有的。其次,有的材料不能说全假,但不能表现劳动人民最美的质地,有点含混,也就是说掺进了游离的因素。(47)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钟敬文编:《中国民间文艺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因此,在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眼里,采风不仅是涉及搜集整理的技术问题,更事关社会主义国家阶级主体的确立。对文本的“真”或“假”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实证立场做出的,而是以能否“恢复”人民本就具备的美德、凸显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为标准。他们从来不会胶柱鼓瑟地理解“忠实记录”,将其简单等同于“一字不易”,相反,他们强调应该把采风看成是突破纷繁的叙述表象,使文本的精神内核得以忠实呈现,真实恢复人民本应有的阶级面貌的行为。职是之故,采风所采用的搜集整理就与现实主义文艺的典型化创作有相似之处,即透过“表象真实”去追寻“本质真实”,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针下,通过直译、改写、润饰、修改、伸展、补缀、删节等整理办法(48)光未然:《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代跋)》,光未然写定:《阿细的先鸡》,北门出版社,1945年,第156-168页。,“‘恢复’这个故事的本来面目”(49)[苏]阿·托尔斯泰:《俄罗斯民间故事》,任溶溶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序”第2页。,使民众的主体性,以及民间文艺本真的美感得以呈现。有论者一语道破:“必须要在原作中去寻求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把那些倾向良好的,富于人民性的发扬光大起来,把那些含有封建糟粕的东西,足以使珍珠蒙灰的尘土揩净。”(50)蓝鸿恩、莎红:《关于〈布伯〉的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0年,第39页。
对文本的加工处理因此具有了合法性。诸如,很多整理者会把少数民族长诗中的仪式性内容替换成一般性民歌,删改涉及迷信的内容;在搜集徐文长、罗隐等人的传说时,搜集者往往会删改其中猥亵庸俗的成分,将其改为宣扬民众智慧的“机智人物故事”;张士杰等人在采录民间故事时,会根据主题的需要,选取不同异文中的理想成分糅合到一起,无疑都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劳动人民本该具备的先进形象,塑造出最为“典型”的劳动人民。在“恢复”的修辞下,这些做法不再是违背“忠实记录”原则的行为,相反是为了呈现民间最“本真”的面貌而进行的必要工作。综观新中国那些引起较大反响的采风作品,如《阿诗玛》《召树屯》《阿细的先基》《龙牙颗颗钉满天》等,往往都是在“忠实记录”和适当的加工编辑间取得平衡的产物。
除了修改文本以凸显民众的主体地位外,还要通过采风者和民众的互相协作,来凸显民众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在理想状态中,加工编辑不应是采风者的专权,而是由他们与民众对话协商的结果。采风者采取“三同模式”,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语言,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另一方面继承“五四”的启蒙使命,将先进的思想带到民间去。如在下乡的过程中,一些采风者往往会在采录之余,辅助以放电影、开留声机(51)覃桂清:《记录整理“八大苗歌”的回顾》,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回忆录:我与民间文学——建国三十周年特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27页。、办夜校、办扫盲班(52)孙庭华:《在蒲松龄故乡搞社会实习——谨以此文悼念关德栋先生》,关德栋等搜集,关家铮、车振华整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民间文学采风资料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971页。等,丰富农民的生活;还有的会在搜集完故事后,“向群众好好做宣传工作,把自己对这些材料的认识说一说,供群众去思考”(53)孙剑冰:《略论六个村的搜集工作》,钟敬文编:《中国民间文艺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因此,很多采风文本是在知识分子“参与他们(人民)的创作活动”(54)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00页。中产生的。如当采录的文本不那么完美时,采风者往往会采取“命题作文”,将所要表现的主题和要达到的效果告诉民众,让他们现场创编出更具思想性和仪式性的文本,如彝族长诗《阿诗玛》中的很多段落就是如此完成的。(55)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阿诗玛〉专辑》,内部资料,1979年,第29页。一些采风者在完成文本整理后,还会将新的故事讲述给当地民众,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完善,循环多次才定稿,如张士杰在搜集义和团传说时,便采取了这一手法。(56)张士杰:《我的体会和认识》,钟敬文编:《中国民间文艺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31页。这些行为在执行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从而使效果打折扣,但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在互为主体的立场下合作对话,互相学习与互相启蒙的愿望,更寓含着通过“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融合与改造,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主体的理想。
可见,新中国的采风既是民间文艺的生产环节,也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石,通过对采录文本的改编和提高,可以让口头文本进入更大的社会流通(57)刘宗迪:《超越语境,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还是一种极具参与性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机制。采风由此具备了象征意义:发现善于讲述的故事家,让他们的言说得以面世,象征着民众经由解放推翻三座大山,真正当家做主,获得了“开口说话”的权利。文艺工作者通过发扬民间文艺中反传统和反秩序的因素,并将新的意识形态植入其中,形成一种富有“人民性”的艺术形式。“恢复”的修辞,使人们对“民间”的认知装置发生了颠倒(58)[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24页。,将种种后设的价值,颠倒成为民间本身具备的素质。经此处理,民间的理想信念得以确立,民众天然就具备了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诉求。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现实需要的文本改编与加工也不再显得突兀,而是成了对人民固有面貌的再现与还原。
四、从文明生成方式到搜集技术:学科的张力、转型与采风的污名化
通过梳理可见,“五四”时期的采风形成于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影响中,试图通过发掘民众的反传统因素,将之转化为新的文化建构(包括新的语言和艺术形式,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以此辅助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现代国民的培养。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左翼知识分子登场,将这种新文化落实为对“民族形式”的追求,通过对民间文艺的移植与提炼,创造出兼顾民族立场和现代诉求的艺术形式。新中国的采风则进一步强化阶级的视角和“人民性”的意识形态,以创造属于工农兵大众的“人民文艺”为己任。在这一过程中,采风先后服务于民族主体的构建和阶级主体的建立,随着“劳动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采风的文化立场逐渐下移,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也日益紧密,采风形成的文本也逐渐平民化,由精英作家的书斋创作转变为普罗大众阅读与欣赏的艺术。
在现代民间文艺发展中,“为文艺”和“为学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来说,“为文艺”在现代国家建构中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时代需要民间文艺学首先应是一项文化事业,其次才是一门学科。对于这一使命,民间文艺从业者(尤其是领导者中国民研会)无疑是清楚的,正如贾芝指出的,当时的工作重心在于“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59)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1958年7月9日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苑利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4-68页。。
在当时的民间文艺知识生产格局中,采风这种以文明生成和传播为目的的范式无疑有压倒性优势。在很长时间里,民间文学的“整理本”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往往比“资料本”更受重视,也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试看当时流行的经典文艺作品,如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小说《锻炼锻炼》《李双双小传》、美术片《渔童》《金色的海螺》等,无不是在充分吸收民间文艺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经整理后的优秀文本直接参与国家文化的构造,不仅得以登上《人民文学》等顶级文艺刊物,还借助现代传媒,以电影、戏剧、美术片等更直观的形象,深刻塑造了民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世界。
但民间文艺从业者也并未完全废弃“为学术”的追求。当时的知识界在唯物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思考如何科学对待传统和文化遗产,力图“建立劳动人民的文艺科学”(60)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205页。。故在具体的工作中,“科学”与“客观”原则仍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构产生极大影响,学者并未完全忽视民间文学的“科学性”。作为学院派旗帜性人物的钟敬文,努力将实证研究的精神与方法纳入“人民口头创作”的学科建构(61)如钟敬文在编辑《民间文艺新论集》时,既收录了何其芳、王亚平、林山、李季等延安知识分子谈民间文艺的文章,也收录了自己撰写的《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文章既强调“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的重要性,又非常注重搜集的科学性,强调要全面记录与故事相关的风俗制度、讲述人的经历与文化程度等信息,足见他调和两者的苦心。参见钟敬文:《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1年,第191-208页。;即便是走延安路线的贾芝、毛星,也极重视这一点。(62)参见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195-244页;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180-194页。贾芝在1960年展开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讨论中,明确反对对搜集文本进行无节制的“丰富”和“提高”,强调“不应当把记录民间的东西与个人进行创作混淆起来,也不可把搜集作品与科学研究工作对立起来”(63)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18-219页。。在中国民研会机关刊物《民间文学》的《稿约》上,也能清楚地看到科学性对文本采录的影响:“要求作品记录忠实,注明讲述或演唱者的姓名、年龄、职业和有关情况及记录时间、地点、作品流传地区、有关风俗等。”(64)参见《稿约》,《民间文学》1963年第1期,封三。
在很长时间里,“忠实记录”(“为学术”)与“采风掘宝”(“为文艺”)并存。采风工作者一般都会将前者奉为理想的工作法则,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往往更偏向于作为时代主潮的采风。因此,很多有影响力的搜集实践,如张士杰对义和团传说的采写、陈玮君对浙江民间故事的搜集、董均伦与江源对山东民间故事的采录,都是在“忠实”的公开追求下,形成了艺术化加工的默契,故都有着在艺术上被充分肯定,但在忠实性上遭到质疑的经历。(65)如陈建瑜:《也谈义和团故事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0年,第106-121页;刘魁立:《谈民间作品搜集工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32-48页,等等。但在自辩中,他们都没有否认“忠实记录”的铁律,或是以提供原始记录稿的形式来“自证清白”(66)张士杰:《义和团传说的原始记录及有关材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五辑),内部资料,1963,第79-98页。;或是将搜集与整理分开,以不同的“真实”标准来要求两者(67)陈玮君:《必须跃进》,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0年,第187-203页。;或是以“恢复”的逻辑来论证搜集是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心声的(68)董均伦、江源:《关于刘魁立先生的批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73-81页。。足见“为文艺”与“为学术”在民间文艺实践中的纠葛与张力。这种张力最为集中地表现在1958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制定的充满矛盾的工作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忠实记录,适当加工,大力推广,加强研究”(69)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1958年7月9日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苑利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66页。上。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基层政权体系的改组中,采风的制度性支持逐渐丧失。与此同时,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与学科范式的转型,讲求科学的学术共同体形成。在新的知识群体面前,旧有的范式呈现出了局限性。学者反思过往的知识生产,指出采风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重视文本搜集而轻视学术研究,且无法确保文本的科学性,导致很长时间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都停留在思想内容分析等领域,无法获得更深入的成果。反思之下,学者不再将民间文学单纯视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而是“具有美感效应的日常生活方式”(70)万建中:《“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催生出了“立体描写”与整体研究的学术追求,加之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海外方法的推动,学科知识生产范式由采风、文艺作品的生产转向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发展出一套充分依仗田野作业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力推动了民间文艺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受此影响,采风的实践逐渐衰落,在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后,再也难以出现深入基层、规模宏大的实践。如今正在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尽管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再具备原先那种深入基层的动员能力,故多数只能靠对已搜集文本的编选来完成。
上述对采风的反思无疑是积极的,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大有裨益。但一些批评也存在着囿于当下实证化的学科框架,将采风等同于技术性的搜集整理,仅围绕着文本的真实性、可信性等角度评论其得失的问题,从而在无形中将采风窄化为一种落后的、需要被取代的采录技术。而将采风和与此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激进革命一并否认,也就难免有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泼掉之嫌。“以纯粹学术的尺度,实际上是无法对文艺派或采风派工作的价值做出评价的”(71)刘宗迪:《超越文本,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这不仅会忽视采风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否认采风作为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历史传统与独特智慧。
显然,采风与基于田野作业的民族志研究是民间文艺知识生产中两种不同的“知识型”(episteme)(72)[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页。。民族志研究深受实证主义影响,以获得“科学”文本为目的,文本是作为研究的资料而存在的。采风则与社会治理、文明生产紧密相关,它不以获得本真的文本为追求,往往需要经过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加工,因此产生了更具实践性与感染力的文本。文本中的“民众心声”并非是桑间濮上的自然呈现,而是由民间言说与时代意识形态糅合而成。针对这样的文本,人们确实无法展开“科学”的研究,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出它的社会效应。而20世纪以来的采风,更是在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当下民间文艺学科的知识生产格局中,高校负责学术研究,而采风似乎成为专属于地方文史工作者和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职责。但在社会运作与民众生活中,它至今仍有鲜明的生命力。因此,有必要看到学院派的知识生产与民众实践之间的裂隙,对采风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作出公允的评价。
五、结 论
在文明论的视角下,我们得以放开视野,将采风放置到中国整体的历史视野中,从而发现采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带有“原型”色彩的文明生产模式。从传统的诗教到“五四”的新文化创造,到左翼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追求,再到从民间文艺到“人民文艺”的加工提高,尽管采风的主导思想有变化,但在实践方式上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它们都有着同一种生产范式,即通过精英阶层的文艺加工,将民间传统提升为国家性文化,如“礼乐”、新文化、“人民文艺”等。它们虽称谓有异,内涵不同,但都担负起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功能。
首先,产生出了具有民族统一含义的新形式。通过提高和改造,民间文艺突破了传统社区面对面的传播环境,从原先地域性、阶层化的“小传统”,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大传统”。与原先良莠不齐的民间艺术相比,新的形式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下的价值取向与美学标准,创造出一种处于雅俗文化之间的、带有民族统一含义的艺术形式,从而推动了文化的统一。
其次,新形式兼顾精英观念与大众传统,担负起了沟通官方(精英)与民间大众的使命,融合了不同阶层的知识和观念,体现了贯通雅俗、消解阶级隔阂、整合不同群体知识与信息的智慧。
最后,起到了确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作用。古代采风者将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诉求植入采录文本中,再由民众在传播中完成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在新产生的文本中,这些后加入的因素被自然化与道德化,被表述成“向来如此的民意”,起到了统合政统与道统的权威效果。新中国则通过“恢复”的修辞,将新的文化创造转变为对民间伟大传统的接续与致敬,产生了古今一脉相承的效应。也正因此,采风成为国家文化整合的强劲力量,无论是依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化之力,还是借助现代国家深入基层的管理能力,均产生了深远的文化与政治意义。
因此,我们如今看待采风,就不应该仅将其视为是一种文本的搜集方法或民间文艺生产的环节,更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转化与生成方式。经由这套方式,草野中的民间文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转化为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新文化。当它进入更大的社会流通中,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经由他们的口耳相传后,又会再次汇入民间文艺中。官方与民间、雅与俗、口头与书写之间呈现出生生不息的良性互动,国家得以良性运转。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这种既具有民间文化的群众基础,又具备现代艺术追求的新文化更是成为民族想象与建构的基础。
尽管在当下学科知识格局中,采风已日益被边缘化,但这种历史悠久的实践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传达民意、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在“朝向当下”的学科追求中,突破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回到具体语境里去重新思考采风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者克服只有“眼光向下”,过度强调研究对象与精英文化对立的弊病。受采风的启迪,学者可以在文明进程的整体性的视野中看待民间文艺的价值与地位,展示出当代中国人生活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及其参与主体的复杂性、广泛性。同时,致力于发现采风作为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独特价值,对于接续传统,让民间参与到整体的社会文明建设中有着积极的意义;而揭示采风特有的知识谱系,探究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对于进一步发掘“采风”作为本土概念所具备的理论前景,建立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亦不乏借鉴意义。
此外,“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换”往往是一体两面的。(73)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序”第2页。作为深刻介入民众生活的实践,采风确实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与反思的地方。比如,在民间言说与意识形态糅合的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如何界定“记录”“改编”和“造假”的边界?采风者的身份和局限性如何影响采风?这一模式如何框定了我们对于民间文学的认知,又带来了哪些学科伦理问题?让民众“开口说话”的理想是如何因权力和知识的暴力而湮没的?“改造民间”的尺度何在?等等,这些只能留待另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