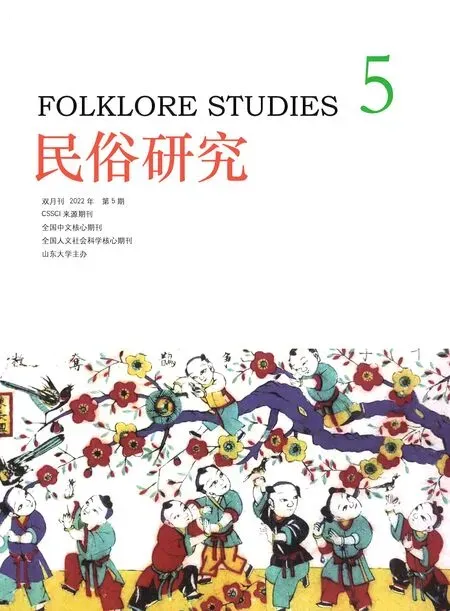村级治理中革新力量与风俗的博弈
——以翟城新政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为例
察应坤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由米迪刚主导的翟城村治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乡村地方自治的源头。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茹春浦便认为“谈乡村自治者,必自翟城村始”(1)茹春浦:《序》,杨天兢:《乡村自治》,大东书局,1931年,第1-2页。。冷隽直言“翟城的自治实为我国村治的最早者”(2)冷隽:《地方自治述要》,正中书局,1935年,第79页。。陈序经则表示“乡村建设实验工作最早的,是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提倡与创办这种工作的中坚人物是米鉴三,米迪刚先生们”(3)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年,第5页。。早期中共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农村派”代表李紫翔也认为“我国农村运动的历史,可以远溯至1904年米迪刚先生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4)李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千家驹、李紫翔编著:《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第2页。。遗憾的是,上述评论者未曾对翟城村治的推行进行深入探究。2021年8月,王先明团队详细地介绍了“米迪刚与‘翟城村模式’”,并指出“1915年米迪刚在翟城村确立起具有近代地方自治意义的自治制度”,“米迪刚主持和影响下的‘翟城村模式’应是20世纪前期各种‘乡村建设模式’中极具特色和重要地位的模式之一”(5)王先明等:《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55、262页。,翟城村治被其视为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典范。然而细致梳理翟城新政的发展过程,笔者发现翟城村治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引发的“迎神赛会停办风潮”导致了新政主推者米迪刚的离开。其后,翟城村在米迪刚二弟米晓舟主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新政。后来被社会各界广泛称颂的翟城新政,实际上是在米晓舟主导下实现的。发生在翟城的迎神赛会停办风潮,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深入解析这一历史事件,能够看出翟城新政在当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具有的深层社会意义。
一、村治初办:翟城新政的缘起与实施
翟城村治发轫于清末新式学校的兴办,开创者是米鉴三。其时翟城村共有19姓,米氏占全村人口的40%,是村中最大的家族。族人米鉴三受聘“办郡中学务,遂倡议在本村创办国民学校、半日学校,并自办女子私塾,听村人附学,旋创办本村高等小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女子高等小学校,皆自备所需,不糜公款,任事数载,勤劳备至”(6)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8页。。在当时的新政环境下,这些被委以监察村庄教育事务的负责人通常承接原来“乡保”身份协助地方治理。米鉴三“性谦和,素为村人所翕服,遇有疑难纷争,多取决焉。以故十余年,本村无讼事……兴办村治,尤能宽猛并济,拳匪之变,亦赖有村治之组织,得以除莠安良,独未受扰”(7)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8页。。
1908年,米迪刚(名逢吉)自日本回国后,遂与其二弟米晓舟(名逢清)、三弟米阶平(名逢泰)跟随其父米鉴三由办理新式教育入手,筹办本村自治新政。但到了1911年,翟城村在办理教育方面受到官方表彰的有三人:村董事文董米晓舟、村正米琢、村副徐进。(8)参见《直隶提学司详定州董事米逢清等捐助学费请奖文并批》,《北洋官报》第2995期,1911年。显然,被官方认可的承接其父主导翟城村新式教育的是米晓舟。其后,米晓舟在1915年10月经推举就任村长,米琢、徐进担任村佐。三人密切合作,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从这一事实来看,前前后后主持翟城新政的是米晓舟,而非米迪刚。即便是受米迪刚邀请为“翟城村自治规约”做序的省公署教育科主任李琴湘(他曾两次到翟城村实地考察)也只是说米迪刚“亦即组织本模范村之一员也”(9)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29页。,并没有指出米迪刚在村治中的主导作用。
介绍翟城村治新政最为详备的资料莫过于米迪刚和尹仲材合编的《翟城村志》。当时尹仲材追随米迪刚办理《中华日报》,任该报总编辑。在此书中,尹仲材把翟城村治的开展分为“组创、组成、保守、改进”四个时期。“在组创时期,应属之米鉴三先生;组成时期,即属之迪刚先生;至于保守时期,则应属之村治组成及各种章程厘订后之在职各员;至近年乃入于改进组织时期。其握原动力以启新机缄者,则皆此创造与保守各份子之合作精神,有以致之也。”(10)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页。从这种划分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尹仲材为米迪刚在翟城村治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也能看出翟城村治由“组成”到“保守”恰恰是米迪刚离开翟城村之后所发生的一个大的转折。尹仲材所谓的“村治组成”至少应该包含“拟定好村治组织大纲”和“村公所和村会的成立”两大要素。本村组织大纲“于民国四年二三月间,乃由现村长米君逢清与村佐等,邀同村人,共为筹商”(11)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1页。,而“村公所三间,至九月间(1915年,笔者注)落成,举凡最要之规约,亦相继订妥备案,所议举之村长村佐及各区区长,于十月六日推举就职,各股员均议定专人,村公所得完全成立,凡向日由公差局存管之公款,亦尽数接收,而自治基础乃大定矣”(12)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0页。。这两大要素均是在米晓舟的主持下完成的。将这些功绩硬套于米迪刚身上并不妥当。尹仲材或许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故为米迪刚开脱说道:“即以迪刚先生论,亦始终未充当村长,今吾人苟能除净虚荣心,不耻灶下之炊,但求农村之乐。事事先之以诚,尽其在我,但求于事有济,不必功自我成,则彼土豪劣绅,其将奈此有志竟成之善士何哉。”(13)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9-40页。这一说辞并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点出了实情,牵扯出米迪刚与本土豪绅的矛盾。
作为米氏父子四人革新团队的一员,米迪刚对于翟城村村治新政并非没有贡献。他所提出的两项举措,推动了前期村治的实施。一是提出建立“教育费贷用储金会”。1908年翟城村立初等小学甲班有7名学生因为家庭清贫而无力升学,米迪刚与当时的村正米琢、村副徐进商议,拟定借贷章程,从村学校经常费羡余项下,贷给每人18银元,使7人得以升入城内高等小学。按照章程规定,待他们自立后,除偿还借贷本金外,还需缴纳利息。其后要求“凡本村人民在外作事,赞成本会宗旨者,须按所得薪水数目,捐助本会百分之三以上”(14)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0页。。再其后,将贷用储金按照筹集和使用范围,具体划分为“农村教育费贷用储金”“族姓教育费贷用储金”“家庭教育费贷用储金”三类。翟城村设立教育会,公举学务委员一人为教育督导,拟定《教育会章程》《教育普及计划书》《学生贷费章程》等并付诸实践。
米迪刚推行的第二项村治举措即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因利协社。因利协社,取自孔子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尧曰第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194页。,开办动机就是顺应农民农业生产合作的需要。具体组织办法是以因利协社为总机关,以平民银行(金融协社)为主体,其他如消费协社、购买协社、贩卖协社等为附属,本着互助精神,共谋协力发展。米迪刚于此颇为得意,对此举也甚为期待,认为如果因利协社日见发达,“则共同生活之无限美感,油然生矣。届时吾人理想中之所谓大同世界者,将不期其至而自至”(16)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0页。。在实施过程中,因利协社改称为因利协会,平民银行改称为“因利钱局”,因利协会由因利钱局处理具体事务。
无论是教育费贷用储金会的设立,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因利协社的创办,共同的指向是本村公共财政的分配和使用,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村治将举步维艰。米迪刚当时“首感困难者,则经费问题与村人风气不开,遇事每致发生阻力也,于是统筹全局,兼程并进,一面设法筹款,一面消除障碍”(17)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附刊》,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页。。而米迪刚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遇到的障碍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传统主义的权力”(18)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1,p.95.转引自李怀印:《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页。,这一传统权力如韦伯所言,“在总体上和从长期看来,都更为强大,因为它始终在不停地运作,并且有最紧密的人际组织在支撑”(19)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1,p.95.转引自李怀印:《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0页。。
二、迎神赛会停办风潮:新政与旧文化网络的碰撞
“当权者和被治理者之间配合或矛盾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都是由政治决定的。”(20)[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8页。一种新事功的开创往往会遭到旧传统的抵制,新事功的迫切程度与面临的困难正相关。翟城村治中的迎神赛会停办风潮凸显了这种矛盾的尖锐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通过诉讼了断。究竟是何种情势导致了这一结果?或者说这一冲突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2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这种文化网络的形成其实是乡村以家庭为单元而自然多元参与的组织关系结构,它的稳定建立在内部各方利益相互平衡这一基础之上。“权利、声称和责任分担总是紧密相连,如果它们分离了,政治冲突导致的力量变化能够改变财产控制的秩序,对它的责任、收益及豁免等权利配置,也会跟着变化。”(22)William H. Riker and Itai Sened,“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Property Rights:Airport Slots”, in Lee J. Alston, Thrinn Eggertsson and Douglass C. 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86.转引自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页。
翟城村“历来相沿迎神赛会之举,尤特盛行,如演戏跑马烟火神棚等会,竟有三十余起之多”(23)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附刊》,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页。。在翟城村举办新政之前,迎神赛会是该村最重大的公共活动,除了临时敛钱来支撑此类活动举办之外,办会固定款项来自迎神赛会名下的公田。翟城村戏会下有田一顷二十五亩五分,马会有田二十八亩,驴牛户有随差地三十亩。迎神赛会的组织者在办会过程中逐渐形成地域性的民间信仰团体——民众祭祀组织。这一组织负责赛会的召集、管理赛会名下的田土收入及活动收支、主持祭祀等。在沿袭村庄历年形成的文化网络中,他们与当地政治势力、宗族势力重合交叉,利益盘根错节。据李景汉在1932年所做的定县实地调查反映,其时“全县尚有偶像之庙宇几近千座。……最普通之庙宇为五道庙、老母庙、关帝庙;其次为真武庙、三官庙、奶奶庙、玉皇庙、龙王庙;再次为药王庙、马王庙、虫王庙、观音庙、二郎庙、三义庙、土地庙、财王等庙”(2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社会学杂志》第4卷第11期,1932年。。定县民间庙会数量多、分布范围广,隐藏在庙会背后的各种民众祭祀组织自是不计其数。
迎神赛会对于民众来说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具有祭祀神灵的宗教性功能,更是民间平淡无奇或者贫穷苦闷日子里最欢欣鼓舞,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而尽情狂欢的重要时刻。(25)赵世瑜总结庙会狂欢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特征。但严格说来,因为庙会的地域性问题,这三个特征其实都是相对的,迎神赛会的各个环节、具体参与人都有严格的约束规则。参见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8-119页。迎神赛会的主体内容是搬演戏剧或跳神游行,但此时祭祀神灵已沦为配角。更多的是民众的狂欢,民众实则借娱神来娱己。据李景汉20世纪20年代末对翟城村及其附近两个村庄的34户农民生活费的调查显示,这34户家庭均有赶庙会、看戏、祭祀的支出。其中赶庙会每家平均花费0.75元,看戏每家平均花费0.55元,祭祀平均每家花费0.70元(包含香纸、锡箔、供品等),这三项费用之和(2元)均高于家具费用(1.62元)、教育费(0.54元)、卫生费(0.61元)、医药费(1.22元)的支出。(26)参见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6-311页。李景汉调查定县乡村娱乐情况时指出:“乡人一方面来烧香还愿;一方面来看演戏,借此消消积年的苦闷……有的戏也能给她们一种新体验,新刺激,新知识。乡民的生活不但简单而单调无味……所以能够调剂他们的干燥生活的,也全赖每年中演唱戏剧。”(27)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7-358页。戏曲故事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调节提供了价值观和评判是非曲直的武器。
1914年,孙发绪上任定县县长后,大力破除迷信,将245个庙宇摧毁或移作他用(改为学校或办公处)。(28)参见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2-423页。面对整个社会破除迷信的趋势和定县知事孙发绪之明令,翟城村迎神赛会组织者并未在明面上表达意见,但当米迪刚力主将迎神赛会下的田亩收入以及他们苦心募集、开源节流而得到的会款一律归公时,他们极为不满的情绪随之爆发。当时迎神赛会名下有田亩一百八十三亩五分,剩余会款制钱660串,归公后,翟城村原迎神赛会的组织者不能参与财务管理,更不能再有任何机会动用这些财产。在过去,这些资产收益则由他们进行支配。
经济利益的受损,使寄托、寄生在迎神赛会各个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包括会首、道士、和尚、戏人、租佃户、集市商人、普通村民,以及借机敛财之土豪劣绅、赌徒、吸毒者等受到直接冲击。对于组织者来说,米迪刚的改革举措破坏了他们“捞取油水的天赐良机”(29)[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页。。对底层民众而言,祭祀共同体名下的财产被强势夺取,这标志着为他们在歉收时提供保障的资源消失了;而且他们在贫苦日子里可以尽情狂欢的权利也被无情剥夺了。各民间信仰组织的会首抓住农民心理,煽动村民力争权益,“村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财产和节日,邻近村庄的人也赶来声援他们。为此而引起一场持久的诉讼”(3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根据米迪刚的记述,他着手经营农村开始于1902年,“时记者年甫弱冠,血气未定,对于处理一切事宜,及今思之,稍失过当者,实所难免,然其心无他,完全为村人生活向上”(31)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附刊》,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6页。。米迪刚力主将本村迎神赛会积储款项转为教育及共有事业基金,并严厉打击“棍徒匪类”。然而,这些主张遭到了村民的反对。对于这件事,米迪刚认为是“恶恶太严,宵小生心,顽固者流,又见因迷信而得储存之会款,一旦归公,最动村人之反感,乃互相挑拨,群起反抗……竟致发生得未曾有之大讼案,相持终年,筋疲力尽,始告了结。当是时也,记者(32)米迪刚常常自称为记者,是针对他创办天津《河北日报》和北京《中华日报》所言。之身家性命,频于危者屡矣。终以是非原自有真,所有兴革,无非村利民福。效果既见,反对心理,自然消除,所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也”(33)米迪刚:《论吾人之天职》,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附刊》,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18页。。孙发绪饬令拆除庙宇体现的是国家政治力量的下渗,有着强烈的政治控制导向,他不允许在地方政权之外发展出任何宗教的或者世俗的与主流政治相抗衡的力量。米迪刚村治新政的推行无意识地在乡村社会变革中充当了政治权力的工具,尽管这是米迪刚村级治理革新价值理性的一个典型体现。(34)孙发绪任县知事自1914年5月12日到职至1916年9月26日离职,共在任2年4月24天。继任者为谢学霖,1916年9月26日任职,1919年3月3日离职。目前还没有见到谢到任后对此事态度的文献记录。孙谢两人的任职时间引自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9页。米迪刚父子及其新政改革跟随者固然也是对乡村旧有生活方式改造的支持者,然而生硬取缔迎神赛会,一方面是原来在暗处“阳奉阴违,趁机渔利”者从中作梗、阻挠破坏,一方面是由迎神赛会而带来的集市经营链条的从业人员利益受损奋起反对,新政改革并没有使农民在生活上“获得真真切切的实惠”(35)[加]伊莎白、[美]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邵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xxii页。。客观来讲,从米鉴三到米迪刚、米晓舟、米阶平,他们父子四人领导的新政,必然造成翟城村“基层政治家族化”的局面,必然会对原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微妙平衡造成冲击。“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36)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七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1836页。对由米氏父子所组成的政治团体而言,他们所标榜的新政,是积极正面的,是“有裨于村利民福”的。但对于其反对者来说却是消极负面的。民众以“个人利害”为判断标尺,如若其未得到切实利益,无论何种主张、何种措施则均被认为是他人谋利的手段。加上下层民众惰性思想根深蒂固(37)参见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所有反对者均借机而起,抵制米迪刚的变革,以至于他不得不将村务交给二弟米晓舟和三弟米阶平,自己则远赴塞外绥远,购领荒地数十顷,力谋垦殖边荒。后来他在《第一次呈定县知事文》中检讨了自己的“急进主义”作法:“自涉世以来,对于地方事,恒持急进主义,终以愚戆成性,于社会心理,致多扞格。”(38)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65页。地方官员向来把社会稳定、无讼事作为政绩,孙发绪也不例外。米迪刚离开翟城村的第二年,孙发绪总结翟城自治经验,并在向政府递呈的文书中写道:“言讼案,则半年统计,该村无一控诉之人。”(39)《孙发绪条陈自治两办法》,《申报》1915年8月2日。由此可见,米迪刚所引致的迎神赛会停办风潮及旷日持久的诉讼或许也曾让身为地方官的孙发绪头疼不已。
三、革新力量的适应性与社会组织的坚韧性
米迪刚离开翟城村后,米晓舟继续在该村推行新政。他在孙发绪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套充分照顾村内各组织利益的自治框架,形成了以村会及村公所为统领、以各协会代表村内各利益集团为基础的纵向权力机构。自治讲习会、教育董事会、通俗讲演社、阅报所、图书馆、教育会、学堂、卫生所、爱国会、改良风俗会、农产物制造物品评会、勤俭储蓄会、乐贤会、宜讲社、辑睦会、德业实践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村公所作为村会的执行机关,代表村庄主导村内一切事务,村内各组织参与部分村务,两者相互协商有关政策的制定。村公所下设财务股和庶务股,财务股职掌全村纳税、银钱簿籍、出入款项、预算决算等事项,由村佐米琢负责,其他不属于财务股的一切事项由庶务股掌管,由村佐徐进负责。这一权力结构有效承接了既有的权力框架,同时将村内各利益组织关联到村集体的决策体制中。这是一种法团主义(40)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机构中去。参见张静:《法团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3页。的框架结构,既保持了地方权威对村庄秩序的控制,也实现了教育、生产、保卫、金融、卫生、慈善等各种功能的整合。从“翟城村职员一览表”可以看出米晓舟、米琢、徐进三人分别交叉担任了上述大部分社团的正副职职务,并广泛吸纳了村内其他各个姓氏和家族的代表参与其中。这一举措保证了“既代表‘公’利,又代表‘私’利的组织共同参与决策过程”(41)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实现了学龄教育普及、村务参与扩大、生产合作广泛、村民纳税积极、村风民俗改良、村容村貌改善,在一村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均展现出农村社会良善进步的倾向。这是迎神赛会冲突后,村落相关各方在新的人事安排上达成一致,取得新的共识和新的认同的结果。翟城村自治效果明显,获得直隶、教育部、内务部的赞许:翟城村治在“民智未开,自治能力尚成薄弱”局面下“自治事业,成绩斐然”,为“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全国模范”。(42)《直隶巡按使第二次饬文》,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73页。翟城自治,自此闻名遐迩。“其时朝野名贤、先俊莅本村参观,咸以本村自治各事宜,在东西各国,亦无愧色云。”(43)尹仲材编述:《翟城村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8页。
翟城村“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体现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坚韧。引起“迎神赛会”冲突的,并非是“迎神赛会”本身,而是农村社会各种组织团体把迎神赛会当做一个展现、释放自身势力的角力场与表演舞台。迎神赛会体现了不同村落共同体之间的交往。附着于迎神赛会上的各种仪式、各种物品都是体现某种村落共同体的象征和符号体系,是对“我者”的强化与对“他者”的区隔。(44)参见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页。这一形式也为其他边缘人群跨越宗族势力走向某一村落共同体提供了一种路径,这种参与感与归属感满足了这些民众的心理需求。这是不同的村落共同体对国家与国家交往的一种模仿,只要有国家存在,这种交往的体现形式就会存在下去。由此观之,在中国乡村长期接续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三种势力。一种是被国家政权认可的乡村政治组织,一种是家族宗族势力,还存在一种民间组织势力(含民间宗教组织、民间信仰组织及其他各种团体)。后两种组织形态隐约浮现于社会现实中,民间组织势力形态尤具隐秘性。这三种势力各有自己的范围和界限,平时以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共存,彼此并不越界,也不会构成挑战。
农民的生存依赖于他所归属的社会组织,而每一种社会组织都会为占有资源采取特定的策略。特别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一定的生存策略会导致反政府行为”(45)[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民间信仰组织亦不例外,若国家政权强,则依附之,若国家政权弱,出现区域“政治真空”,则会伺机而动,挑头谋事。这一组织群体“相互扶助”并形成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且总是以其切身利益为核心价值追求。如若村治组织的行动合乎他们的追求,他们会积极配合。反之,则会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天然带有“威胁性并且如魔鬼一般的控制力”(46)[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2页。,“生活习惯的养成,宗教仪式的反复进行,与大自然循环节律之间所存在的神秘对应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深刻,由此在民众心灵深处,就蕴积为一种可传递、可唤醒的深厚文化力量”(47)张士闪:《佳作赏析〈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三种势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未此消彼长,基本面仍然存在。翟城村迎神赛会风波作为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不仅承接了帝制时代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态势,而且预示了中国在迈入现代国家政治体系中国家政权建设将会遇到的阻力和挑战,同时也反映出民众日常生活所形塑的心理力量的坚韧性。
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在根除迎神赛会中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糟粕之外,迎神赛会所具备的缓解压力、娱乐身心、促进商贸发展、稳定乡土秩序、振兴地方等“精神信仰和生活实用”(48)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的社会功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概视之为“陋习”难免有态度武断和认识偏颇之嫌,其发挥的社会功能难以被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替代。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却对“迎神赛会”抱有充分的好感,曾言:“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49)鲁迅:《五猖会:旧事重提之四》,《莽原》第1卷第11期,1926年。基于自身的经验,他在1930年提出:“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50)鲁迅:《习惯与改革》,《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未慎重考虑便推行的改革,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抗。(51)参见鲁迅:《习惯与改革》,《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四、与民众生活合流:破解社会改革困境的关键一着
翟城新政所引起的迎神赛会停办风潮并非个别现象。作为“帝国的隐喻”(52)[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序”第1页。,迎神赛会往往是地方士绅、民众对官方祭祀行为的模仿或活用。迎神赛会一方面是中央政治稳定的显示器,一方面由于其产生于民间社会,天然具有非正统性的基因,在政权鼎革之际,它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新观念和新举措的对立面。晚清民初,迎神赛会奢靡攀比、劳民伤财、借机敛财、聚众赌博、拐骗妇女、践踏田苗,可谓弊端迭现。地方政府注意到问题所在,对“迎神赛会”持批判态度,各地不同内容的迎神赛会均在严禁取缔之列。江苏巡抚丁日昌态度尤为坚决:“饬县随时访查,嗣后如有首倡迎神赛会者,不论绅董、民人,准其照例严办……该地方文武官弁如不严行禁止,亦即随时参办。”(53)丁日昌:《禁迎神赛会示》,《中国教会新报》第2卷第66期,1869年12月。晚清时部属和省属官报如《北洋官报》《秦中官报》《山东官报》《浙江官报》《南洋官报》《云南教育官报》等多有对中央与地方政府查禁迎神赛会的通报。民间新式报纸《绍兴白话报》《广益丛报》等也都刊发了知识界主张禁止迎神赛会的呼吁。1910年始,各地禁止迎神赛会的报道犹如泉涌,既表明了官方的查禁态度,也说明了迎神赛会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依然如故。有报道称:“镇海柴桥,巨镇也。本月六日为例行迎赛之期,民间输捐异常踊跃,各处有刘盘龙癖者亦争先恐后,麇集其间,盖该乡赌风之盛甲于各属,大者一掷千金或数百金,少者亦数十金。地方官知之而不能禁也。”(54)《迎神赛会之踊跃》,《新闻报》1910年3月23日。进入民国后,地方政府对迎神赛会的查禁仍然是不了了之。上海地方政府从1912年到1919年每年发布查禁告示以致最后用警力介入,试图以强力扭转“屡禁不止”的尴尬局面,然而拘押会首不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大规模的警民冲突,激化了矛盾。(55)参见《禁止迎神赛会》,《新闻报》1919年3月29日。
中国文化传统积淀深厚,民众习惯和意识的改变往往滞后于时代发展。新的事物进入不了民众的生活、不能转化为其切身利益,就很难找到伦理情感上的认同。梁漱溟在1928年4月递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中就曾指出:“乡治之行非有合于乡间固有之习惯心理必难成功。”(56)梁漱溟:《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5页。即便是到了1930年代,菏泽县政建设实验县主导者孙则让建设“村学”时,也因为大拆庙宇遭到民众非议,“计建四百二十一个村学,最可痛心者,为去年春天开始建造,不到两个月,菏泽即发生大地震,死伤一万二千余人,我们的校舍也就全被震塌了,民间于是传说了,说这是拆庙的报应”(57)孙则让:《菏泽的乡村自卫》,《教育与民众》第9卷第4期,1939年。。民众心识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是作为其他问题被附带论及,特别是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心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王汎森所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不留意下层人民的心识状态,往往会错解重大的历史现象……晚清以来新政、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启蒙人物都呼吁新政或现代化将造福国家与人民,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下层百姓往往是新政或现代化政策的损失者或受害者,最常见的情形是国家的新政或现代化往往会加重财政或其他负担,故其心识中每每产生一种反对的心态,这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惰性或抵制性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58)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改造民众传统意识,克服习俗中的落后因素,在具体策略上应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协商,祠庙资源为教育、公共事务和地方崇拜所共有,就容易使类似事件得到平和解决。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平民教育会在重庆璧山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在这一点上就比较注意,成效显著。当时的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教授梁桢总结说,璧山的社会改革方案重视立足于人民的需要,注重与人民日常生活相结合,注意人民以怎样的态度接受这种改革。“植根于中国泥土之中,已与赤足露肩的农民生活合流,这种工作,能在全国广大民众身上开花结果是可预期的。”(59)梁桢:《璧山归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编:《乡建工作经验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在实验区温家湾村,由乡村建设工作人员苏正家所推动的国民学校生产合作社“得到了校内外人士的拥护”。该合作社以本村庙宇为办公场所,“这个庙宇香火非常兴旺,但平教工作展开后,地方人士已将神像地位,让出一大部分,辟为教室、办公室”(60)梁桢:《璧山归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编:《乡建工作经验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三个滩”村的龚家祠堂也变成了既是小学校又是合作社又是妇女班的办公地址。按照当地风俗,女人不能进祠堂正堂,但因为乡村建设工作人员黄开文工作到位,“致使龚族改变了传统的规定,特开二门,准其办公出入之便。不仅如此,黄同学没住处,他们反而欢迎她即宿此正堂”(61)梁桢:《璧山归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编:《乡建工作经验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8页。。在狮子乡,“教员办公就在堂屋,办公桌与天地君亲师的供桌并排着”(62)梁桢:《璧山归来》,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编:《乡建工作经验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梁桢在总结中只记述了上述三村的实验工作开展情况,三村的乡建工作人员都得到了当地的信任,风俗传统的灵机变动反映了当地民众对社会改革的拥护和支持。
风俗传统的微妙变化往往是社会改革成败的风向标。如果在这一点上采取强力介入,不过“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63)黎澍:《彻底之底》,《群言》1988年第5期。。卢作孚一生追求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主张用“微生物”“弹棉花”的方式进行社会建设。他认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和由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一时不容易治疗得好的。”(64)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在农村文化土壤的沉浸中成长起来并对农村有着深入调查的毛泽东对此的主张是:“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6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第191期,1927年。到了1940年代,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自然而然革命化”的观点,认为“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66)曾岩修口述,李晋西整理:《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即使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在斗争激烈的海丰农民运动中也对乡村社会中的“神明”采取不排斥的态度。在彭湃最初发动村民加入农会时,彭湃的最早追随者林沛告诉彭湃:“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彭湃当时很为接受:“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67)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3期,1926年。费正清曾有过非常清晰的分析:“中共从很早以来就是农村组织者,很接近并且依靠农民,所以它知道怎样采用渐进的方法以达到最后的目的。”(68)[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社会变革要达到社会基础结构和制度的改变,要想赢得农民的支持,需要采取“较为保守的姿态”而“做出必要的让步”,满足农村集团相当具体而温和的盼望和要求。(69)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1、368页。在农民“劳动者”和“私有者”二重属性之中,应该顺应、适应、鼓励其“私有者”属性的发展,以经济发展、社会开放打破其“劳动者”属性对自然经济条件下共同体“束缚-保护”功能的追求。
既往的改革认识惯于强调对以往传统的改造,而未曾注意“发掘、提炼并诠释中国基层社会现存的大量民间信仰活动所蕴含的‘真精神与正能量’”(70)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基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前提的认识与理解”(71)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6页。,黎澍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它无声无息地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制约的、推动的乃至革命变革的作用。这是缓慢的发展过程,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较之暴力革命的作用更深刻、更广远。”(72)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力量在对地方社会的改造进行总体评估后,要积极引导各种力量发挥正面作用,科学、冷静、客观地看待革新与风俗的博弈即应有之意。两者博弈处于一时的胶着状态,恰恰是两者正在走向微妙的、妥协的平衡状态的前奏。一种渐进的而非暴风骤雨式的进展正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节奏合拍。抱持这一态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变革”(73)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也更能够“在一个和平但社会关系复杂多变的年代……让每一个普通人而不仅仅是领袖和精英,都能从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历史氛围中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历史教诲”(74)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五、余 论
因迎神赛会而出现的冲突,是翟城村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首先是隐藏在此问题之下的村级政权更迭、各方力量的角逐;其次是围绕革新举措与迎神赛会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因素的纠葛,新的制度和方法没有对农民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再次则是村内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交锋,特别是新的鼎革力量与旧的文化传统的抵牾。政治、经济、宗族、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全部交织在一起,在具体的迎神赛会停办斗争上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冲突。旧的文化网络潜滋暗长,米迪刚在对翟城村内部进行整合时,轻视了宗教信仰与心理因素在文化网络中的坚韧生命力,其主张的教育革新、生产革新,又将村庄民间信仰组织这一部分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排除在外。新政唤醒了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却迟于在政治结构中为民众参与预留足够的释放空间。因此,在翟城村新旧交替之际,米迪刚既没有成为旧文化网络的领袖,也没有发展成翟城自治持续推进的决定性力量。旷日持久的停办风潮,从微观层面而言,一方面显示出米迪刚个人并未得到来自村庄内部的认可,没有确立合法化的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则表明这种新生的自治政体需要不断进行共存共生性的修缮。从宏观来看,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自下而上的本地社会的支持基础之上,包括当地经济财富、政治权力、社会舆论等力量的认可,而最重要的是民众的心理认同。
在基层社会,要确立和巩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仅形成一套新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在民众中养成一种生活方式。基层政治体制的根本活力在于国家政治价值和民众社会价值的有效关联和有机融合。在政治家视野下的政策革新运动,在民众眼里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尊重民众日常生活,顺应民众心理,理解民众无论是基于政治、宗教、宗族、信仰还是基于职业或经历而形成的群体认同,是改革举措得以有效落实的前提条件。必须在各种关系生态中暗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文化网络,与民众生活合流,培养社会美德,照顾人的精神关切,维持社会各团体之间的多样化发展和相互适应性,使得新制度下的人养成新的思维方式、道德习惯和行为规则,形成新的风俗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政治事务的制度”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制度”的根本性差别,就在于此。只有后者才能使得每个人真正关心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内,社会组织的公共空间必须积极回应私人领域的个体利益和诉求,并且这一回应应当是积极的、正向的、有效的,如此,才能使被动后觉的后来者跟随主动自觉的先行者共同营造新制度下的社群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