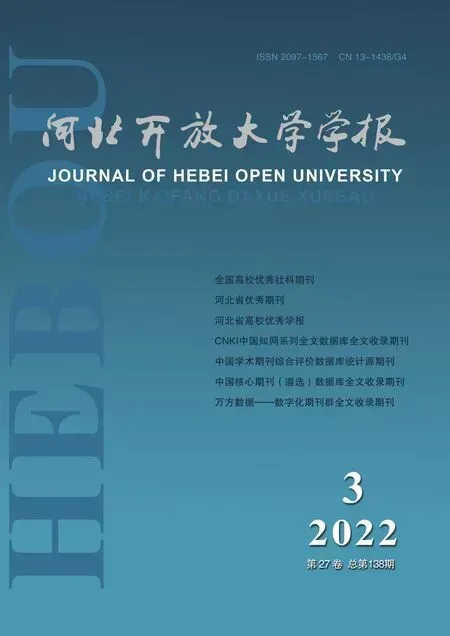艾略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接受
石苗苗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是现代派代表诗人之一。1922年,艾略特发表《荒原》,震惊文坛,奠定了其现代主义大师的地位,1948年凭借《四个四重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早在20世纪20年代,艾略特就被引入中国,在近百年时间的译介、研究中,艾略特诗歌在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梳理过往评介的过程,也是解读诗人“历史的意识”的一种方式。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的,诗人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同样,通过梳理艾略特的评介,挖掘艾略特诗歌中的“过去性”与“存在性”,发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和当代的关系”[1],以及在中国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与文化界在与艾略特诗作的对话交流中也撷取其中精华,并结合中国话语,产生了众多精彩的文化作品,丰富了我国的诗歌文学创作。
一、相对集中的国内艾略特诗歌译介
艾略特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史已近百年,成果丰富,但是主要集中在他著名的长诗《荒原》。在艾略特最初被介绍至中国的十年就迅速引发了学界对他现代主义作品的极大热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现代派的先锋思想掀起了文学创作高潮,震撼了国内广大学者对现实的思考。最早在学术刊物提及艾略特的是茅盾,他在《文学周报》(1923年8月27日)的《几个消息》中简单谈到了艾氏。1927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刊登了时任清华大学教授R.D. Jameson撰写的《纯粹的诗》(Pure Poetry),译者为朱自清,文中再次提到了艾略特。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可谓艾略特译介的高峰,各种评论、介绍艾略特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1932年,黄清嵋翻译了《文艺批评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对艾略特进行了介绍。1933年,荪波在《新月》(第4卷第6期)介绍F.R.利维斯的新书《英诗的新动向》,该书第三章称赞艾略特在文学中创建了新的开始。1934年10月《现代》发行“美国文学专号”刊(第5卷第6期),其中刊登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深入分析了艾略特的创作特色。
艾略特诗歌翻译的热点当属《荒原》。1936年,应戴望舒之邀,赵萝蕤翻译了《荒原》,次年由叶公超作序的译作由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这一译作的诞生,离不开当时学术氛围的滋养。在此之前,艾略特的研究专家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此外,温德也曾在清华大学授课,并在课堂上详细讲解了《荒原》。赵萝蕤谦虚地表示,自己的译注采用了温德的授课内容。当然,更离不开译者对于艾略特诗歌的理解以及对现代派诗歌的宏观把握。赵氏《荒原》中译版的发表,引发了学术界的诸多赞誉与持续不断的讨论热情。1940年,邢光祖在《西洋文学》发表书评,称赞赵译“是我国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半个多世纪之后,对赵译《荒原》的研究热度也有增无减。刘树森《一位学者与翻译家半个世纪的足迹》(1994)认为:“纵观赵萝蕤的译作,尤其是诗歌翻译,可以发现崇尚直译是贯穿其中的突出特色。”[2]傅浩《〈荒原〉六种中译本比较》(1996)指出,赵译《荒原》“虽完成于三十年代,但今天看来,仍流利畅达,不失为佳译”[3]。董洪川《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2006)将赵萝蕤的翻译策略总结为三点:“信”字为先;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原作的陌生度;具有灵活性的“直译法”[4]。黄宗英等人撰写的论文《“灵芝”与“奇葩”:赵萝蕤〈荒原〉译本艺术管窥》(2014)将赵译与其他几个译本的《荒原》相比较,探究赵萝蕤“直译法”,发掘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翻译原则的实践价值。2013年,黄宗英编著《赵萝蕤汉译〈荒原〉手稿》,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将赵手稿附在译文左侧,给翻译爱好者提供了真切的实践样本。总的来看,学者普遍认同赵萝蕤的“直译法”。赵萝蕤本人也对该译本直言“不自觉地当了一名‘直译者’,本能地按照原作逐字逐句翻去,丝毫没有想到要打乱原诗固有的秩序”[5](P241)。
艾略特的经典诗作常常一诗多译。《荒原》中译本另有其他五个版本,译者有裘小龙、赵毅衡、查良铮、汤永宽、叶维廉。傅浩对这些译本评价如下:“裘小龙、赵毅衡的译本显然受了赵萝蕤的影响,但未能过之。查良铮译本的文字朴实自然,也堪称佳译。汤永宽译本虽最晚出,但理词和雅语混杂,行文不够简练。叶维廉是海外华人,其措辞时有佶屈聱牙之处,也不失为一种风格。”[6]董洪川基本认同以上评价,但他“更推崇穆旦的译文,因为穆旦的译文在整体风格和气势上更接近于原文。这恐怕与穆旦本人的个性气质有关”[7]。
除了《荒原》,艾略特的其他诗作也受到译者欢迎,前后有多个译本。1942年,黎子敏最先翻译了《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此外,查良铮、裘小龙、汤永宽、蓝仁哲亦有译作。董洪川针对查良铮、裘小龙、汤永宽的译本撰写论文,通过具体译句的比较分析,认为“每种译文都有一些‘误读’”[8],但是又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指出译者考虑到在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了文学再创造。《四个四重奏》也有多个译本,如赵萝蕤、裘小龙、张子清等。但是目前国内除了《荒原》与《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其他诗歌的多版本译作尚无论文探究异同。
二、成果丰硕的国内艾略特诗歌研究
国内学界对艾略特诗歌的研究有着深刻的评判维度与独特的审美思考,研究论著成果丰富,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第一个对艾略特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非叶公超莫属,他自己也说:“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9]叶公超发表过两篇艾略特的专论,不仅体现出很强的批判精神,而且表现出对艾略特诗歌的深度理解。1934年4月,《爱略特的诗》发表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文章标题下列举了两本艾略特研究专著,分别是威廉生(Hugh Ross Williamson)撰写的《艾略特诗学》(The Poetry of T.S.Eliot)以及马克格里非(Thomas McGreevy)所著的《艾略特研究》(T.S.Eliot, A Study),还有艾略特的作品选集(Selected Essays)。该专论以艾略特作品为讨论的基本出发点,批判性地研读了这两部研究专著。叶公超认同威廉生书中对艾略特创作技术的赞同,但是他对于威廉生提出的艾略特技术特色是“内感与外物契合”[9](P118)的观点不甚苟同。叶指出艾略特的独到之处是,于隐喻的意象中暗含诗作的意境。相比之下,叶公超认为马克格里非是“一种趁火打劫式的批评家”[10](P113),文章语言不够精练。叶公超肯定了马克格里非书里的精华,即艾略特“做诗最主要的技能,就是用意象来想见的力量”[10](P113),但是叶公超不认同马对于艾略特早年诗作创作的态度,他认为艾诗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同时,认为该书过于强调宗教信仰的作用,轻视了艾诗的技术。在叶氏看来,艾略特的成就在于他横贯古今的诗风打破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界限。其实叶公超对于艾略特有独特的见解,所以无论批判或是赞成两本专著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突出叶氏的既有观念,即艾氏运用意象表现历史意识的诗艺。
叶公超的另一篇专论《再论爱略特的诗》,是赵萝蕤1937年初版《荒原》的序言。该文深入地讨论了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创作技巧,以及与中国古诗之间的联系。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与他的诗学理论相互印证,艾略特注重用典,将观念内含于意象中,诗人应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将其写入作品中。此外,一般青年诗人过于看重艾诗的技术,而忽视了诗中所具有的伦理功效,诗歌应当强调内心的改造,营造宗教的心境,获取希望。艾略特的诗歌很少有抽象的东西,诗歌的格式也是依据内容自由变化。叶公超又将艾略特主张用典与中国古代诗学相联系,指出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就是利用过往的旧句,使得传统文化补充作者个人的才能。叶文最后大赞艾略特“可以说是文以载道者……假如他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者”[10](P126)。
在对艾略特的诗论进行深刻分析与借鉴的基础上,叶公超又撰写多篇文论,针对中国当时诗坛现状展开剖析,将艾略特的创作理论与中国文坛具体情况进行了有机结合。叶公超1936年发表于《自由评论》的《谈读者的反应》,运用了艾略特《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文中的观点,讨论接受理论与读者接受对于理解中国古诗的作用。1937年刊于《文学杂志》的《论新诗》更是大幅引用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分析国内新诗创作中的问题,提出新诗作家应学习古诗,洞察中国创作背景之后,重视传统文学的力量。
赵萝蕤作为叶公超的学生,在艾略特的研究方面,既传承师训,又有自己独特的心得。赵萝蕤翻译《荒原》之后,应宗白华之邀撰写《艾略特与〈荒原〉》讲述研究体会,该文发表于1940年5月14日《时事新报》。但是该文对于艾略特用典的意图却展现出与叶公超所提出的“夺胎换骨”不尽一致的观点,赵文认为艾略特的广征博引往往为烘托自己的情绪或营造特殊的意象,常常脱离了原典故的束缚,“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情绪,和脱胎换骨的天衣无缝并不相同”[5](P13)。1986年,赵萝蕤在《国外文学》发表《〈荒原〉浅说》,再度详细深入地探究《荒原》的艺术魅力,认为诗作具有持久普遍影响力的原因在于诗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典型气息,即“一战”之后人们颓丧不振的精神面貌。为了理清诗中难解的典故,赵萝蕤细致解读了每一诗节的引用,并讲解与主旨的关联,最后谈到艾略特的思想内涵,大赞他是现代派中的大师。1999年,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诗选》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赵萝蕤为此撰写《〈艾略特诗选〉序言》。该序言简要分析了艾略特的诗歌作品,并提及他的戏剧与文学评论。
袁可嘉作为研究现代派诗歌的专家,对于艾略特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发表过多篇专论。其中《诗与晦涩》刊登于《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关于现代诗的晦涩,赵萝蕤在《艾略特与〈荒原〉》(1940)一文中也曾提及,她认为,之所以感觉诗作晦涩难解,多因为没有充分了解诗人的创作技术以及诗歌内容。相比之下,袁可嘉将诗晦涩的原因作了更为深刻的研究,共有五点:其一,20世纪初传统价值观解体,诗人根据个人体验,创造独特再现思维的制度;其二,现代诗人偏爱从复杂离奇中寻找丰富的创作来源,袁文以《荒原》众多的典故与不同种类的文字举例说明;其三,诗人借情绪渗透抒发情怀,以《普鲁劳克情歌》为例;其四,诗人运用特殊的隐喻明喻;其五,诗人故意使用荒唐文字,展现人类心智的真迹。此外,袁可嘉的《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发表在《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6年9月15日),借用艾略特的《荒原》与他“客观联系物的观点”阐释诗歌境界的拓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袁可嘉撰写的《从艾略特到威廉斯——略谈战后美国新诗学》(1982)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了艾略特及其诗论的文学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威廉·卡洛·威廉斯为代表的美国新诗,更加适应当时的美国社会大环境,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艾略特经院派的诗风开始衰落。这篇文章从社会背景的转换去看待艾略特诗歌的接受流变,提供了一种较为辩证的视角。
在此之前的艾略特研究,学者更多注重中国的文坛现况与社会实情,紧扣艾略特文论的精髓,分析中国诗坛动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方向更为多元,主要从宗教思想、时间空间、社会文化研究(身体、女性、生态等)等视角,挖掘诗歌对于当下社会的启迪。
就数量而言,艾略特其他诗歌的研究远没有《荒原》多。《四个四重奏》也是研究较为集中的,众多论文就其中的时间主题展开了不同的探讨,碰擦出学术火花。史成芳《无常与永恒之间——〈四个四重奏〉的时间编码》(1993)认为,艾略特秉承了伯格森的时间观,通过对《四》每一部分的细致解读,指出绝对与相对的时间观在诗歌中所起的作用,为的是表达诗人所追寻的“永恒”。蒋洪新《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1998)除了探讨时间与永恒话题,更挖掘其中深刻的历史意义,从而能在时间之中找到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刘立辉《〈四个四重奏〉的时间拯救主题》(2005)将拯救时间的原则解释为基督教“道成肉身”,从而实现永恒的理想境界。围绕《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展开的探讨数量上非常之多,但是总体来看,依旧将艾略特的时间观与他所追求的永恒世界相联系。《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也是艾略特被研究较多的诗歌作品之一,多数研究者关注作品中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如“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诗歌中的展现。
此外,艾略特的其他诗歌目前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反映出国内对于艾略特诗歌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不应只局限于《荒原》等耳熟能详的作品,并且研究方向也有待深入挖掘,艾略特各诗作之间的关联也可以作为研究的角度之一。
三、国内诗歌界与艾略特诗作的对话
艾略特诗歌被引入中国之后,在国内诗坛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众多流派诗人的关注与学习,也对国内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漫长的文化接受过程中,中国诗坛的诸多流派,如“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都对艾略特的诗歌有着深刻而又各不相同的反应。
“新月派”的诗歌虽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但是很多主要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和孙大雨等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借鉴了艾略特的诗歌与文论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月派”的创作理念与艾略特的诗论不尽相同,然而“新月派越来越清醒地反对过度的浪漫抒情和主观宣泄,强调对情感的节制和诗歌形式的约束却为即将到来的现代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
闻一多对艾略特的《荒原》有着深入的思考,这体现在他的诗集《死水》中,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展现出对悲惨现实的反思,强化了抨击黑暗社会现况的力度。《死水》一诗中写道: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从“一沟死水”“青蛙”等生活中的平凡意象入手,刻画出无奈绝望的生活现实。这与艾略特《荒原》第五章“雷霆的话”所描写的苦难现实采用了相近的意象与创作手法,皆是围绕“枯竭的水”展开对残酷无情生活的抨击。通过《死水》与《荒原》的对比阅读,不难发现艾略特诗作对于闻一多的影响,均由简单的意象引出对现实的反思,用相近的艺术手法干净利索地揭示出现实的悲惨,展现了诗人们内心的绝望与苦闷。“闻一多和艾略特所处时代的文学主流都是反传统的,面对现代/传统的问题,两位学者的相同之处是站在现代的立场,阐明传统对现代的影响。”[12]在艾略特诗论的影响下,“新月派”的诸多诗人也都开始采用现代的视角,去描述意象并抒发情怀,从而阐明对传统更深层的理解。
不同于“新月派”,中国新诗“现代派”对于艾略特诗歌与文论的接受显得更为自然,也更有深度。从社会历史语境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饱受战乱侵袭,诗人们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况,渴望运用文学作品开拓这片“精神荒原”。不仅如此,“现代派”的诗人也认可艾略特的诗论理念,在诗歌中重视经验的抒发,避免诗人的个人情感在文学中所占比重过大,体现出艾略特“非个性化”的原则。
“现代派”中的代表诗人卞之琳与艾略特之间有着奇特的“共鸣”。卞之琳曾说:“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13]这种文学上的“共鸣”来源于卞之琳对于现代派,尤其是对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理念的共识。艾略特在《荒原》中运用简练冷峻的笔墨刻画出现代人精神的荒漠,通过客观意象展现出萧索绝望的社会画卷。这对处于内忧外患国情中的诗人卞之琳来说,自然是有着极大的共通之处。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诗人应努力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非个人化”原则,在卞之琳的很多诗作中都能找到对于艾略特诗论的应用。卞之琳在《春城》中写道: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你哪
……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诗作中的意象如“垃圾堆”“风筝”“蝴蝶”“鹞鹰”“家”“坟”,无疑是诗人寻找到的“客观对应物”,从而让诗人处于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描绘这凌乱无序的世道,表达内心的无奈感慨。这样的诗风与艾略特在《荒原》中的若干诗句有着相似的意味:
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根在从
这堆乱石块里长出?人子啊,
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
一堆破烂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不使人放心,
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只有
这块红石下有影子。
两篇诗作都是借助于“客观对应物”进行对意象的描绘,挖掘出隐藏在意象之中对现实的批判,舍弃诗人个人情感的主观表达,转而注重让读者发挥想象的作用,从意象中解读出诗人的冷静思考。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原则与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观念给予卞之琳以及其他“现代派”诗人极大的启迪,推动中国新诗“现代派”在现代诗歌潮流中探寻到合适的契合点,得以将民族情感与现代艺术有机结合。
相较于“新月派”与“现代派”,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对艾略特的诗论有着更深的理解,以及更为全面的接受容纳,并且在诗作中展现出了其诗论的精髓。这与“九叶诗人”的创作年代和当时的社会国情有着紧密联系,国难当头,容不得诗人们抒发个人的内心感伤,转而需要他们运用恰当的诗句点燃民族斗争的热情,诗人们“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他一定的意义”[14]。而艾略特的诗论就与“九叶诗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其中袁可嘉、唐湜、辛笛、穆旦(查良铮)等是“九叶派”中最具代表的诗人,他们将艾略特的诗论与诗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体现在了各自的创作中。
以穆旦的诗歌创作为例,可以发现他早期与后期的诗歌有着微妙而又重要的嬗变,也表现出诗人对于各种流派,尤其是艾略特诗论的吸收与再现。早期诗歌《一个老木匠》着重于刻画人物形象,注入了诗人对于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辞藻间更多地流露出诗人的主观感慨。
孤独的,寂寞的
老人只是一个老人。
伴着木头,铁钉,和板斧
春,夏,秋,冬……一年地,两年地,
老人的一生过去了;
牛马般的饥劳与苦辛,
像是没有教给他怎样去表情。
也会见:老人偶而吸着一支旱烟,
对着漆黑的屋角,默默地想
那是在感伤吧?但有谁
知道。也许这就是老人最舒适的一刹那。
诗句中饱含着诗人充沛的情感与深切的体验,这代表了穆旦早期创作的方法与风格。“‘艾略特传统’在中国诗坛的播撒为穆旦的创作带来了奇迹般的转变。他从对浪漫主义以及前期象征主义的热爱转向了对后期象征主义的偏好……转向了对艾略特、奥登的借鉴与融汇,诗风不再是过分的抒情、柔美纤细或浪漫幻想,而变得更为硬朗凝练、坚实,乃至神秘、晦涩。”[15]穆旦深受艾略特诗论的影响,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对现实的艺术再现中,特别是运用独特的“‘现代感’,即用一种与前人不同的方式去感受现代社会的种种事物”[16],去表现中国国情之下的人生百态。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用冷峻的笔法刻画出了抗日战争年代人民生活的凄苦: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村庄,
岁月尽竭了,牲口憩息了,村外的小河冻结了,
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
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
他想什么?他做什么?
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诗句通过对黑夜的描写,营造出哀伤绝望的气氛,若干意象诸如“平原”“田野”“大麦”“灯光”“脸”形成“客观对应物”,刻画出如同《荒原》里冷漠无助的世界。诗人从这些典型农村意象着手,又融合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对于主观思考的表现,借由“他想什么?他做什么?”的发问,让读者沉浸在诗歌悲凉意境的思索中。艾略特诗论对于穆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穆旦将现代派诗歌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体国情恰到好处地相结合。
艾略特诗歌引入中国后,在中国诗坛掀起了文化巨浪,从“新月派”“现代派”至“九叶派”,可以发现诗人们都是结合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与文化背景,吸纳融汇艾略特的诗论,随着时代发展,中国诗人逐渐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步入现代主义文学之中,最终迸发出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诗歌作品。
四、结语
在艾略特诗歌的百年译介研究过程中,虽然还有很多国外诗歌研究的译介较为缺乏,而且研究也集中在少数耳熟能详的名作中,但是也不难发现艾氏诗歌的艺术已经逐渐融合在了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学术氛围中,碰撞出了更多学术火花,激发中国文坛产生了更多样的文艺作品。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