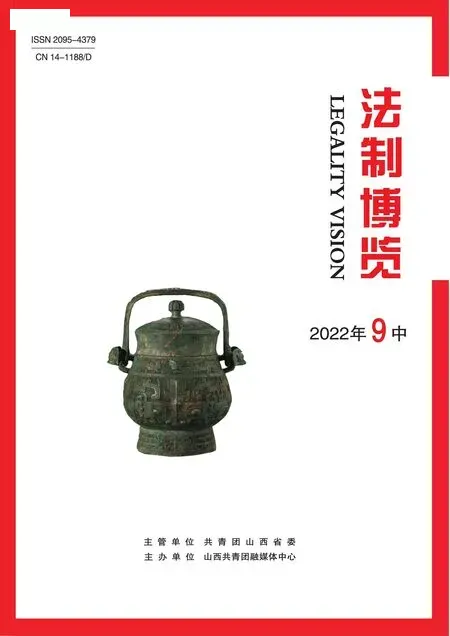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执行弊端与解决建议
刘吉熙
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四川 绵阳 621000
一、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弊端
管理人合同解除权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充破产财产,以保障全体债权人得以最大限度清偿,单从此点出发其实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设计目的,且该制度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破产”或“支付不能”制度中均有类似规定,属于国际通行做法。但笔者认为我国与美、日、德等国存在一定的经济文化差异,因此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应密切联系我国的具体状况,以保障其制度价值的发挥不脱离必要的合理性,而合理性的考虑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特别是当制度的执行涉及关联方重大利益问题时,该制度就不应仅仅追求其最初的设计价值,还应考虑该价值的实现是否给关联方带来了难以承受或是超出普通大众认知范围的负担。
二、《企业破产法》自身不具有化解管理人合同解除权弊端的能力
《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管理人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或者有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事项的,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而《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拟履行债务人和合同相对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或者其他对债权人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应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
从上述规定可知,立法期望通过上述规定对管理人行为进行限制,以保障债权人重大利益不受侵犯,防范显失公平的情况发生,但笔者认为该两处规定以及其他相关法条并未限制“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反而规定“在管理人要求继续履行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时,合同相对人可以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由此可知立法认为合同的解除更符合合同相对人的权益,这显然忽略了一些情形下解除合同将对合同相对人可能造成更大损失的可能。例如债务人为房企,在房价飙升的状态下,管理人拟对买卖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购房合同进行解除(仅支付部分首付,后续分期尚未向开发商支付完毕,当然此处并非指银行贷款分期)。
有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管理人行使涉及债权人重大权益的行为需要经过人民法院同意”,因此人民法院自然会在面对特殊事项时予以考虑,否定管理人提出的合同解除要求,以此消除特殊情况下合同解除权带来的不公,因此对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担忧是多余的。但笔者想要表明的是,只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行使解除权时需要经人民法院同意,但此后的只需向债权人委员会或人民法院报告即可,所以特殊情况下,合同相对人的重大权益仍然存在遭受严重不公可能。
通过对上述条款分析可知,现行《企业破产法》在立法设计中已经考虑到不公情形的防范手段,但是在设计防范手段时考虑并不充分(这也和新生经济事物超出立法预见有关),由此导致在特殊情形下适用管理人合同解除权所造成的矛盾无法通过《企业破产法》制度本身进行消除。
三、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受到限制
根据列举的法条规定可知,当前的法律框架下,通常而言只要是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都有权决定是否撤销合同,但笔者认为,无论理论上的权限如何,管理人最终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需要符合制度设计目的,该管理人撤销权是限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撤销权,而《企业破产法》的设立目的是“最大限度增加债务人财产数额,维持公平受偿次序”,也就是说,只要管理人认为撤销双务合同有利于增加全体债权人受偿额度的,其就有权利、有义务解除合同。但是笔者同样认为,即便是为了有效推动破产程序的实施,制度的设计和执行都不应偏向于某一方,而应综合考量其制度的执行是否会对其他民事主体带来显然的不公,应该是谨慎的和被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
既然从现行制度规定本身无法消除解除权给合同相对人带来的不公,那么就应从对管理人合同解除权制度的理解和适用方面加强对其的限制。我国法律制度深受日、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企业破产法》也不例外,既然体系之间存在联系,那么制度矛盾的解决也必然存在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日本,笔者认为其在合同解除权制度遭遇特殊情形时的处理方式就有可借鉴之处:
《日本破产法》也规定了管理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日本最高院在个案的受理过程中当法院认为管理人合同解除行为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会驳回管理人的解除行为,法院的说理核心内容是“法律赋予破产管理人解除权的根本目的是在个人的公平保障和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合同解除已经对当事人显著不公,则管理人不得解除该合同。”[1]
笔者认为《日本破产法》“允许基于对个人实质公平保障,而禁止管理人行使解除权”,便是前述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就我国而言,在无明确的禁止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对于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还需要办案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有益的判例创设,并不断积累最终实现由量到质的改变。通过上述法条及案例借鉴,可以得到启发,即立法赋予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目的是促进破产程序与社会间总体之平衡,当这种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反而会因合同解除权遭到破坏,那么这种追求社会总体之平衡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平衡的,那么其适用就应得到限制。
四、解决建议
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消除合同解除权的弊端,一是直接限制管理人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范围,从源头上消除给合同相对人造成的影响;二是充分保障合同相对人在合同解除后的权益保障,合同解除将给整体债权人带来清偿率的提升,而因此受到影响的合同相对人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具体建议如下:
(一)事前限制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使用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是理解和适用该条内容的核心,例如,王欣新教授在《破产法理论与实务疑难问题研究》中提出的,未履行完毕的义务是属于实质性的核心义务还是附属性义务,这是判断合同解除是否给相对人带来显著不公平后果的要素之一[1]。因此,如果未履行完毕的义务仅指主要义务的,对于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的,就不应再将合同视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至于如何认定已经完成合同主要义务,应根据不同事项由受案法院具体认定,如果案件是破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则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的“限制取回权规则”。
当然也有观点会指出,《企业破产法》对此本就有规定,例如《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三十五条:“出卖人破产程序中,若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但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管理人则可以取回标的物,但如果买受人已经支付了约定价款75%以上的除外。”和第三十六条:“出卖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决定解除任何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并取回标的物,买受人若以其不存在违约理由为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管理人解除权在破产领域属于特殊法规定,且《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实施时间晚于《买卖纠纷解释》,属于新法,根据特殊优于普通,新优于旧的原则,合同能否解除应以《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为准,所以《买卖纠纷解释》在此不具有引用价值,也没有借鉴的必要。
对法律适用原则问题笔者并不反对,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些特殊情况,例如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归属于保留所有权的合同(理由详见《买卖纠纷解释》第三十四条),而《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所指的对象均为保留所有权买卖的合同,既然如此则不适用于房产买卖合同,但《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终究是新于《买卖纠纷解释》中的“限制取回权”,所以在此也只能将“限制取回权”作为今后限制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参考,而不是对抗解除权的直接依据。
(二)事中纠正显失公平的管理人合同解除行为
法院可以根据案情,灵活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以及第二款,管理人要求解除购房合同的,无论是否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人民法院都应基于对整个破产程序的监督要求管理人征求法院意见,对于管理人已经做出解除决定相对人诉至法院后,法院基于重大公平考虑可以对案件作出倾向于合同相对人的个案裁判,以图有效监督和限制管理人对合同的解除,纠正因管理人合同解除制度造成的显失公平弊端。正如前文所述,《企业破产法》赋予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核心目的是在对个人的公平保障和破产程序的有效推进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若合同解除可能对合同相对人造成显著的不公或者超出普通大众认知的后果,那么法院应限制管理人对该合同的解除。
(三)事后弥补因管理人合同解除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合同相对人
对于行使合同解除权造成的损失,《企业破产法》仅规定相对人有权申报债权,但对所申报的债权性质是普通债权还是共益债务并无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后经过《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三十六条:“出卖人破产其管理人决定解除买卖合同的,若买受人已经依法履行了买受义务的,买受人有权要求管理人,就该合同解除而形成的损失作为共益债务进行处理”和2002年《优先受偿权批复》第一条、第二条:“通常情况下,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一切债权甚至是抵押权,但该权利也不得对抗已付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将消费者的认定范围,限定在名下没有其他房产,因而购买商品房用于居住,并已支付合同价款超过约定总价50%的情形”的补充规定才确定了如下清偿规则:
1.对于管理人解除的保留所有权合同,造成的损失为共益债务;
2.已经支付大部分房款的购房者,管理人解除合同而形成的债权虽不是共益债务,但其效力优先于工程优先权和抵押权。
根据上述归纳可知,仅在部分情况下合同相对人已经支付的合同款项可转为共益债务或优先债权,但对于其他情形下产生的债权性质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处理,例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房地产企业破产中,采用的就是普通债权说。笔者认为,管理人为了扩大破产财产而解除合同的行为,是为了大部分债权人的利益,那么由此产生的应支付给合同相对人费用符合共益债务的特性,应作为共益债务处理。但在当前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合同解除产生的全部债权认定为共益债务并不现实,也不可能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因此必须要有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一定的支撑,笔者认为可以从合同解除行为具有追溯性的这一观点入手解决这一问题[2]。理由是合同的解除,其解除效力溯及于已经履行的部分,破产债务人也再无持有合同相对人已支付款项的正当理由,则该款项的性质应归类于不当得利债务,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给合同相对人,以弥补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给合同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依据是《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
五、总结
通过对《企业破产法》的分析,可知立法者也考虑到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等职责可能引起的不公,并制定了防范措施,但这些防范措施并不全面。例如特定情况下的交易合同的解除将给合同相对人带来显失公平的后果,而法律制度的灵魂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间寻求总体平衡,显失公平已经绝对打破了这条平衡的底线。笔者坚持认为,在法律赋予管理人特殊解除权的同时,本就应该同等赋予合同相对人特殊的保护,以防止权利的天平终倾向于破产管理人,况且合同解除相对人所做出的牺牲将惠及全体债权人,正所谓“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立法更应对这样的奉献理念保驾护航。在当前无直接法律依据可用于维护合同相对人应享有之权益时,在个案的操作中应该严守法律于社会之平衡底线,限制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并充分保障合同相对人的生存权,不因制度的机械执行而遭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