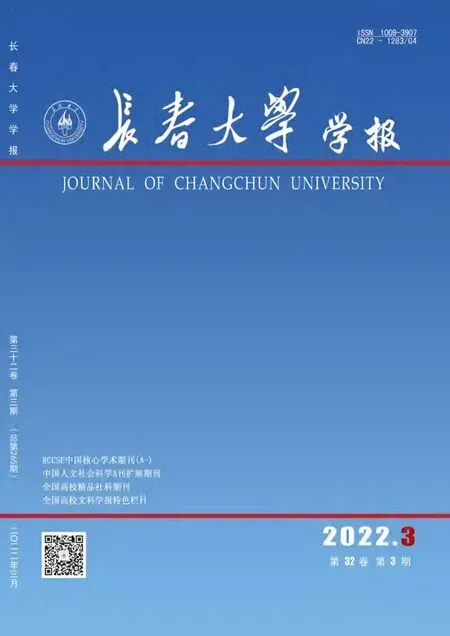从文化自觉观看贵州民俗文本英译
夏 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民俗文化是国家或民族在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习俗风尚,是展示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路径,也是集体性文化沉淀与常见文化现象,所体现的民俗文化精神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具备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是千百年来社会民众所创造的认知系统,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口头与行为传承的一类文化模式[1]。
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文化展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不同民族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经济水平各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各民俗文化中也有所体现。为了让我国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输出需求逐渐增加,无疑推进了文化互动交流,促进本土与世界文化系统之间的建构、融合。
现在学术界对“民俗文化”“翻译”“文化自觉”等相关研究成果中,多数以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原则与策略为研究方向,其中李睿认为,要对民俗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翻译需要保留原文的文体特征[2];李金涛以《诗经》为例,提出在翻译中需要采用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3]。也有对民俗文化翻译的其他研究,提出“多异化、少归化”,可以应用明示法、置换法、文化意象阐释法等。总之,现有研究多集中为汇总、归纳翻译策略,在研究视角上比较固化,在研究深度上有待挖掘。
本文基于文化自觉观研究视角,突破以往研究领域对民俗文化翻译的局限性,对贵州民俗文化英译展开剖析,目的在于促进贵州民俗文化走出国门,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一、文化自觉观概述
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期提出“文化自觉”,他从功能论角度出发,将“文化”看作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力,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等。他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的是,生活中具备一定文化认知的人,对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具体来历、形成过程、所形成的特色与发展去向,不存在任何“文化回归”意思,并不是绝对的“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他化”[4]。“文化自觉”是指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费孝通先生呼吁“文化自觉”,其实质就是希望社会大众对自身文化有一种由内到外的认识,加强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能够适应新环境的自主地位[5]。
在新时期背景下,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是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创新、超越的实践过程。本文基于文化自觉观的研究视角,以期为贵州民俗文化文本英译研究提供参考。
二、贵州民俗文本蕴含文化内涵
贵州地区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多民族特色,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民族风情独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呈现了全新样貌,不断激活其中蕴含的中华民俗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呈现出极具朝气活力的文化风貌。贵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有极具文化内涵的谚语诗歌、神话史诗、迷人的音乐舞剧、节日庆典、民风民俗、民族服饰、民族用语等,形成贵州极为丰富又极具魅力的民俗文化资源。以《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族源及民俗文化符号》为例,它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贵州17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让读者直观、理性地认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及其民俗文化的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6]。
为了体现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贵州民俗文化文本翻译的风貌,本研究所选取的贵州民俗文本大都出自《中国民俗(英汉对照)》《贵州民族民俗概览》《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族源及民俗文化符号》,结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从“求同”“存异”两方面剖析贵州省民俗文化文本的英译。
三、文化自觉下民俗文化英译策略
从文化自觉这一视角来看,民俗文化英译需要在原文与翻译文本之间达到文化平衡,译者要适当调整和取舍原文文本的内容,让原文所要表达的民俗文化融入翻译文本;同时,还要保持译文读者对于原文文化的探索欲,以“求同存异”的翻译原则对翻译资源优化整合形成文化自觉。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涉及对原文文本的适度编译,通过“求同”尊重原文文本内容并适当采用交际翻译等手段达到“存异”的效果。
(一)重视编译的“求同”
“求同”要求译者保留原文文本中的文化内涵,考虑译文读者所能够接受的原文文本文化内涵的程度情况,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适当地删减转换,让最终所翻译的文本与西方受众的思维认知需求更相适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受众往往更愿意了解与本土文化思想相通的信息,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的润色加工。例如可以适当地编译、节译,选择性翻译原文本所要传达的重点信息,将部分无关紧要以及理解难度较大的内容进行删减,这样可以方便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无障碍地对我国民俗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达到预期的英译效果。要认识到,“求同”并非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内涵,而是在翻译中能够让译文受众理解原文文本所要传输的内涵并产生共鸣[7]。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译文读者往往对易理解和熟悉的信息接受度更高,所以,通过适当加工修改原文文本,对文本段落次序重新整理,这样能够让译文读者无障碍地理解中华民俗文化的诸多方面,达到跨文化交流的效果。
例1 人体内共计十二条主经,阴阳各六条,以及其他遍布全身的小经脉,共同形成了全身经脉网络。每一条经脉都连接脏腑,十二经脉根据循行顺序……分别包括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
译文:Twelve meridians include Hand Taiyin Lung Meridian, Hand Yangming Large Intestine Meridian, Foot Yangming Stomach Meridian, Foot Taiyin Spleen Meridian, Hand Shaoyin Heart Meridian, Hand Sun Small Intestine Meridian, Full Sun Bladder Meridian, Foot Shaoyin Kidney Meridian, Hand Jueyin Pericardium Meridian, Hand Shaoyang Triple Jiao Meridian, Foot Shaoyang Gallbladder Meridian and Foot Jueyin Liver Meridian.
对于十二经脉中“阴、阳”等此类常见文化词的翻译,可以直接根据音译法译成yin、yang,但是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此类具体名称,因为翻译文本受众对于我国的复杂中医学术用语并不了解,所以可以适当编译,将脏器名称翻译出来即可。译文充分考虑了西方受众对中医知识的认知局限,精心设计文化知识表达形式,让翻译效果自然得体。
(二)关注译文的“存异”
“存异”需要在民俗文本英译中对原文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给予充分尊重,让译文不失原文体现的地域特色,充分体现民俗文化的异质性。通过在民俗文本英译中关注“存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拓展译语的表达形式,让译文读者能够更充分地感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新奇感、陌生感与探索欲。在输出民俗文化时,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音译等多种翻译结合法,能够帮助译语读者获取与原民俗文本相近或相同的阅读体验,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感知原文民俗文化传播中特有的文化内涵。
贵州地区作为多民族聚集地,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积淀,在社会各方面都体现了当地民俗文化,也在多年发展中产生多样化的专有名称。为了避免民俗文化空缺,这在英语翻译中就要采用直译或音译以及必要的注释,保证翻译文本中蕴含原文本的文化内涵。譬如对“赛芦笙”“苗王鱼”“苗年”“侗年”等专有名词均可采用音译并辅以加注的翻译策略[8]。
例2(1)经过芦笙匠的改造,侗族芦笙共有“伦正”、“伦尼”、“伦我”、“伦略”等17种类型。(2)侗年,侗语称为“年更”,是榕江县侗族村寨的传统节日。虽然各地侗族过侗年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多在农历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进行。
译文: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usheng craftsman, there are 17 types of Dong Lusheng, such as “Lunzheng”, “Lunni”, “Lunwo” and “Lunlue”.
The Year of the Dong, called “Nian Geng” in Dong language,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Dong villages of Rongjiang County. Although the time for the Dong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to spend the Dong Year is different, they usually take place between November and December of the lunar calendar.
该例英译文采用音译或直译,并向译文中移植文化内涵。作为此类异化翻译策略的一种,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民俗文化英译的可理解性,所以有必要添加注释,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俗文本英译的理解缺失。
例3 贵州地区盛行的“芦笙”,其前身为中原汉族的竽,后唐朝时传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踩芦笙”,规模宏伟,芦笙高大。
译文:The “Lusheng”,which is popular in Guizhou, originallya type of musical instrument called “yu”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was introduced to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ang Dynasty. “Cailusheng” in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splendid and magnificent.
译文对“芦笙”“踩芦笙”“芋”采用直译、音译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极具民俗特色的社会风情。因此,译文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内容,并说明不同年代、历史所蕴含的相关文化信息,让译文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历史文化,恰到好处地向目的语读者展现贵州民俗风貌。
不仅如此,在民俗文本英译中,有时候也需要增译,让原本模糊的信息更为明确,必要情况下可以添加“注释”。这里的注释主要指解释性翻译,依据原文的表达习惯与文化需求,在翻译中适当补充文化信息,一般表现为语言信息的增译。
例4 在苗家,每年都要举行几次盛大的芦笙节。节日里,苗族人民盛装前往,各寨芦笙手云集芦笙坡,平时寂静的青山翠谷,顿时汇成芦笙歌舞的海洋,满山遍野,一望无际。芦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民族乐器,而且是苗族男女青年成婚的重要“媒介”。
译文:In the Miao family, several grand Lusheng Festivals are held every year (The Miao language is called Jibie, which means climbing a high slope in Chinese). During the festival, the Miao people went there in costumes. The reeds of all villages gathered on the slopes. The unfrequented green hills and green valleys suddenly merged into an ocean of reeds singing and dancing. Lusheng is not only a simple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marriage of young men and women of the Miao ethnic group.
译文中增加了“The Miao language is called Jibie, which means climbing a high slope in Chinese”(苗语称基别,为汉语爬高坡之意)的注释,能够让译文读者更形象地了解“芦笙节”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节日。
以“存异”为目的的翻译中,需要强调民俗文化主体意识,在翻译中不仅要对民俗文化做到充分尊重,还要尽最大可能让译文读者以最易接受的方式了解原文蕴含的民俗文化精髓。在实际翻译中,可以根据不同民俗文本的情况巧妙应用翻译策略,在译文表达中糅合民俗文化与话语方式,保留原文精髓的同时,补充注释介绍历史文化背景的相关信息。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译语读者对我国民俗文本的阅读兴趣,也可作为对外推介我国民俗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
四、结语
本文基于文化自觉观的研究视角,从“求同”与“存异”两个方面对民俗文本进行了剖析。通过分析归纳认为:“求同”要以国外读者对我国民俗文本的阅读需求为依据,可以采用节译、编译等翻译策略,为读者呈现民俗文本中最纯粹的部分,增强民俗文化的国际交流效果;“存异”则要坚持保留我国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异质性,向译文读者传递历史文化信息,可以综合应用直译、音译、加注等翻译策略,让西方读者对我国民俗本土文化有进一步了解,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