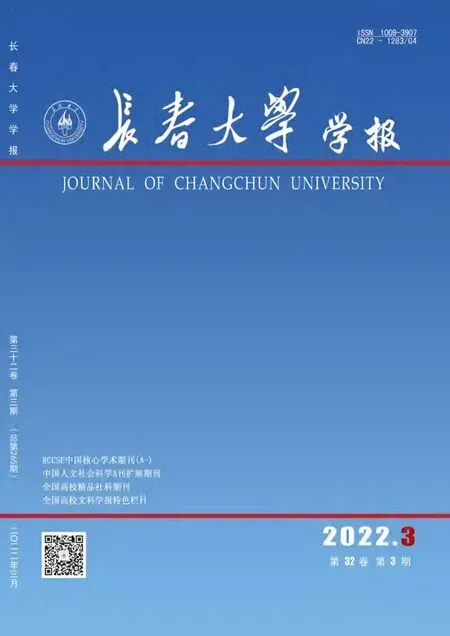村落变迁中的信仰空间重构与文化传承
——以洪洞县士师村皋陶信仰为例
高忠严,关旭耀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31)
皋陶为舜帝时期的圣贤人物,因其最早被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士”及其对中国古代监狱、律法所做出的贡献而被认为中国司法的鼻祖。山西洪洞县士师村作为皋陶出生地而在村落得名、故事传说、祭祀空间等方面体现着浓厚的皋陶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1949年以后,该地区村落发生重大变迁,皋陶的信仰空间与其中深藏的地方文化不断经历着消解的过程。2007年,华夏司法博物馆的修建使皋陶信仰这个曾经维系村落的精神纽带以一个新的面貌回归民众的视野。2020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十三),首届法祖皋陶寿诞大典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地方文化的认同。通过对士师村皋陶信仰的考察,剖析该村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信仰空间与文化传承所发生的重构现象,能够窥探皋陶信仰在当代乡村社会中普及法律、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
一、士师村皋陶信仰的形成
士师村原名皋陶村,因皋陶生于此地而得名,后改以皋陶的官职“士师”为名。皋陶因创立监狱、法典的历史功绩而演变为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狱神与司法神,而士师村的皋陶信仰除了体现出狱神、司法神崇拜外,当地民众还将皋陶认定为祖先,并围绕皋陶庙与皋陶墓展开祭祀活动。
(一)信仰与业缘、血缘、地缘的结合
士师村有着浓厚的皋陶信仰,根据历史典籍记载,皋陶本为舜帝时期的司法官,从《尚书·舜典》“(舜言)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1]18可见,皋陶是在国家外受异族侵犯、内有贼人作乱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士”的。士师的职能据《周礼·秋官》记载为“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2],可见皋陶正是当时掌管国家法律与管理刑罚的司法官。社会的动乱是舜帝任命皋陶为士师的直接原因,而在这种严峻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监狱与司法部门的设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皋陶的任命是出于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奇幻色彩,早期对皋陶的崇拜也应当是民众对司法崇拜的具象表现。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民众逐渐为皋陶创设监狱、掌管司法等历史事件添加奇幻的情节,使皋陶逐渐有了神格从而成为民众祭拜的神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有“皋陶画地为牢”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期中国本没有监狱,皋陶在地上画圈关押犯人,创作了华夏首所监狱。中国各行各业多将创立行业的始祖奉为行业保护神,监狱行业也不例外,依据皋陶创设监狱的传说,监狱从业人员多祭拜皋陶。据馆藏民国抄本《重建皋陶庙记》记载,元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在皋陶庙立有一碑,上刻碑文《重建皋陶庙记》,其中就记有皋陶为狱神的内容。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与社会稳定,中国古代的监狱设立非常广泛,皋陶拥有神职后,“我国古代监狱多建皋陶庙,奉皋陶为狱神”[3]。监狱从业人员将皋陶作为行业神进行祭祀,显然表明了业缘组织对该信仰生成的影响。
村民或出于地方文化的认同,或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首先以地缘的优势将皋陶神纳入当地的神灵体系中,并在社会生活中有意识地加强对皋陶信仰的宣传与利用。《洪洞县志》载:“皋陶故里在县南十五里皋陶村,相传皋陶产此,或曰高阳也。”[4]397该村正因皋陶生于此地而得名,后相传为避圣人名讳而改以其官职“士师”为名。但不论是以“皋陶”还是“士师”为名,都在宣示皋陶生于此地的历史事实。村民在地缘关系的作用下将皋陶认作先祖并开展祭祀活动,尝试从血缘关系上拉近村民与神灵的关系,使作为司法神灵的皋陶具有祖先神的职能。这种血缘关系的提出可能与皇权的推崇相关,唐朝时皇家认定皋陶为李姓祖先,并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唐玄宗追封皋陶为“德明皇帝”。神职的确定与皇权的推崇,催发了民间皋陶信仰的发展。今士师村所修建的华夏司法博物馆中展示有皋陶及其后人分布的脉络图,根据馆内资料,皋陶后人共分化出皋、李、徐、赵等三十六姓,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北、江苏、台湾等省份。士师村中几个大家族姓氏则被认定为皋陶的直系后裔。此外,村民为了凸显皋陶作为祖先神的职能,便结合历史事迹建构出皋陶显灵保佑子孙的许多传说。其中在当地流传最广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皋陶显灵护村的故事。“相传原来皋陶庙有个牌楼,上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皇帝过来龙行三步’,曾经慈禧老佛爷路过此地也必须遵守此项规则。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不讲这个规矩,有个日本的高级军官带领日军进行扫荡,但是到了士师村口的时候,日本军官没有下马,他坐下的战马就带着他绕着村口转圈,怎么也进不了村子,最终使得村子逃过了日军的扫荡。”(1)访谈对象:华夏司法博物馆管理员袁小牛。访谈人:关旭耀。访谈时间:2020年11月14日。访谈地点:华夏司法博物馆内。这种神灵护佑百姓的传说虽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但在多代村民的共同塑造下成为了当地民众记忆中的“真实事件”,并在村落周围广泛传播,进一步凸显了皋陶作为地方保护神的神力,也加深了村民对皋陶的崇拜。
皋陶作为狱神、地方保护神、民众先祖的多重身份结合体,使得士师村的民众既作为神治理下的子民又作为神的子嗣而存在,反映出神灵与民众在神缘、地缘、血缘上的结合。这种多维度的结合不断加深了当地民众对皋陶信仰的认同,也使得该村的皋陶信仰活动在千百年的时光中不断流传。
(二)祭祀时间、空间的确定
民众个体对于神灵的祭祀活动有着较大的自主选择性,但是集体性的祭祀活动却是民众长期协商后得到的结果。皋陶作为当地重要的信仰对象,当地民众共同约定俗成的祭祀时间与地点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士师村皋陶祭祀活动的时间地点的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崇宗敬祖观念。
士师村民众主要选择农历九月十三与清明节开展对皋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所分别为皋陶庙与皋陶墓。村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将农历九月十三约定俗成为皋陶诞辰,并于当日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诞辰是中国晚辈为长辈举行庆贺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但是庆生活动在长辈过世后就要停止举办。神灵在民众的观念中能够超越生死,皋陶因为有神职,所以他的寿辰活动可以一直举办下去。民众受到乐生恶死心理的影响,往往对长寿有所祈求,故对皋陶诞辰的祭祀活动十分重视,举办得盛大而隆重。其诞辰祭祀场所选择在博物馆内与村口广场,这里曾是皋陶庙旧址。士师村皋陶庙的修建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据《洪洞县志》记载,“皋陶祠在县南士师村东北高阜处,元元统二年里人段亨建”[4]429,可推测士师村皋陶庙本为元代的皋陶祠;另外,今博物馆内现存的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石碑上镌刻着“增修有虞士师庙记”字样,显示在明嘉靖年间原皋陶祠已经被扩修成庙宇,足见当地皋陶信仰存留存之久远。
除了农历九月十三皋陶诞辰外,民众还在清明对皋陶进行祭祀。清明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主要的功能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此节日期间祭祀神灵的现象很少发生。皋陶作为民众祖先的身份,则为清明节的祭祀活动提供了合理性。墓葬与庙宇不同,神灵可以在不同地区有多种分身,故作为神灵居所的庙宇可以有多处。但墓葬是后世子孙纪念祖先的地方,往往只能有一处。《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5]内容显示,皋陶死后其后代被封到安徽六安地区。而在《左传》中提到:“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6]从臧文仲在听到六国灭亡后就认为皋陶没有人祭祀了,足见安徽六安地区祭祀皋陶历史之久。且在1989年安徽六安市东郊“古皋陶墓”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皋陶葬于六安的史实基本为学术界认可。但墓地作为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对士师村的民众有着重大的意义,士师村皋陶墓的存在也经历了极长的历史时期。早在元代洪洞县县令也速歹儿所题《重建皋陶庙碑记》就记载有“洪洞之南十里有丘焉,曰皋陶之墓,以先正之所卜兆也,代历数千载,虽陵谷迁易之馀而邱垅在焉”[7]。另根据民国时期县志记载,“虞士皋陶墓在县南十三里,皋陶村东南,塚高五尺,周围十步,碑高一丈,文剥落不可读,石器尚存,四周有垣今圮”[4]502。根据上述史料可见,士师村皋陶墓虽有较长的历史,但是远不如六安东郊皋陶墓的史料记载久远,士师村民众对皋陶墓在六安的认定有着相当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背后所体现的是村民意识中比历史真实更为重要的地方文化认同。
二、皋陶信仰空间的消解与重构
信仰空间随着村落的变迁而经历着消解与重构的反复过程。1948年,皋陶庙被拆毁,1958年,皋陶墓被改为耕地,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皋陶消失在乡民的视野中。直至2007年在司法部门的指导下,皋陶庙以华夏司法博物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民众的眼前,皋陶信仰被赋予了符合当代价值观的内容。
(一)传统信仰空间的消解
祭祀空间的消失与村落组织的转变,使士师村皋陶信仰在1948至2007年间呈现消解的态势。
1.传统皋陶祭祀空间的消失
旧时期中,农历九月十三作为皋陶诞辰是当地人神共娱的重要节日,当地民众为了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崇拜会极尽能力做到热闹。据当地老人回忆,在祭祀活动开展的几天时间里,士师村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村民会自发聚集起来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并聘请戏班搭台演唱。另外,皋陶庙会还具有促进商业交流的重要功能。根据当地老人回忆,“皋陶庙会是洪洞地区最大的庙会,号称骡马大会,每逢举办庙会,当地周围商客云集于此,当时,官府在庙会立上木桩,商人需每人买一桩位,其余在庙会期间所贩卖商品皆不收取任何税费,是皇家庙会的特赦” 。1948年因战争的影响,该庙宇遭到极大损毁,后期原庙遗址也被划为居民用地,庙会活动也随着庙宇的消失而在民众的记忆中淡去。
清明祭祀活动主要有上坟、烧纸与祈求农业丰收等仪式。在过去的“里甲”制度下,这些仪式需要与士师村同属一里的冯张、左南、上桥、下桥、杨曲、沙掌等七个村村长共同完成,足见皋陶清明祭祀活动在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但随着皋陶墓在1958年的平田整地活动中被改为农业用地,清明祭祀活动就失去了展演的场所。2014年,相关部门在皋陶墓遗址上修建起皋陶纪念碑,并将周围农地改为硬化路面。此举虽方便了民众的参观与祭祀活动的展开,却限制了最能表达当地民众对祖先纪念之情的上坟、栽葱等活动。随着祭祀空间的消失,群体性的祭祀活动在乡民的视线中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里,村民不断更迭,祭祀皋陶一事只存留于老人的记忆中,新生代村民逐渐遗忘了祭祀皋陶的传统。
2.村落组织形式的转变
1949年后,洪洞县的村落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旧时期“里甲”制下,士师、冯张、左南、上桥、下桥、杨曲、沙掌等七村同属一甲,共同参与祭祀活动。皋陶信仰圈以士师村皋陶庙为核心向四周扩布,地缘组织使七村在皋陶祭祀活动中形成合力。而对皋陶祭祀权力的争夺则体现着村落之间的权力争夺,各村村长为了在村落交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争相在祭祀活动中出力,上坟次序的先后、在诞辰活动中出资出力的大小都体现出这七个村落之间的暗斗,以至出现“县长率众上坟……,四面八方的来人,纷至沓来,成千上万、摩肩接踵、异常隆重”[8]的现象。但依据1949年后的城镇规划,原处一里中的七村被分别划归甘亭镇(管理士师、上桥、下桥、杨曲四村)、曲亭镇(管理沙掌村)、大槐树镇(管理左南、冯张二村)三镇进行管理,新的行政区划分散了原祭祀圈中的人群。在党的宏观调控下,各村落不再需要通过对皋陶祭祀权的争夺来提升村落的权威,况且如今将七个村联合起来开展祭祀活动还存在不小的困难。对皋陶祭祀活动的记忆逐渐从皋陶祭祀圈的边缘向核心区域消失,现如今的皋陶祭祀活动主要存留于庙宇所在的士师村与墓地所在的上桥村中。另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上桥村中已有部分村民遗忘了皋陶(yáo)的真正读音,而采用皋陶(táo)的错误读法。自1958年皋陶坟被平到2014年纪念碑的建立,在时隔近60年的消解过程中,处于祭祀圈核心区域的上桥村民众已然对皋陶的记忆变得模糊,而处在祭祀圈边缘的其他村落对皋陶信仰的淡忘程度可见一斑。
(二)当代信仰空间的重构
出于对法制精神的弘扬,2005年,洪洞县政府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开始策划在皋陶庙原址上修建华夏司法博物馆,该馆最终于2007年10月正式落成。华夏司法博物馆的建成使士师村村民对中国的法律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皋陶信仰重新回归到地方民众的视线中。但是,作为在官方倡导下的皋陶信仰空间,其内涵已然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当地村民虽然习惯性地称华夏司法博物馆为皋陶庙,而且馆中的皋陶展厅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当地民众祈福禳灾、请愿还愿的职能,但该馆与旧时代的庙宇始终是不同功能的建筑。庙宇是承载民众信仰与祭祀行为的场所,民众希望通过对神灵的祭拜获得福泽。民间信仰在当地呈现着俗信化的趋势,如钟敬文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文化的提高、人们的鬼神观念日趋淡薄,信仰方式不断简化。”[9]民间信仰很难完全消逝或者被改造,但其中不符合时代的部分是可以被剥离的。
其次,华夏司法博物馆的建立使皋陶的祭祀空间转变为普法场所,促使当地皋陶信仰趋于俗信化,将皋陶的狱神、地方神等神职转变为古代司法精神代表的人职。目前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分别展示中国司法的来源、中国古代司法人物、皋陶与地方姓氏文化、中国法制变革等内容。在主馆中,皋陶则被认定为中国司法人物的先驱。当地民众观念中的庙宇与现代博物馆的结合使民间祭祀神灵的空间转变为法制宣传空间,既给当地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慰藉,也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祭祀空间形态的转变也在引发祭祀活动形式的转变,皋陶信仰中封建愚昧的事象不断减少,扬法、普法的内容逐渐增加。此外,该博物馆还被认定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承担着红色革命精神的宣讲功能。
三、司法神崇拜中的文化传承
作为士师村统领式文化的皋陶祭祀活动,根植于当地的历史之中,并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着应有的功能。它与当地诸多的民俗事象相互牵扯融合,已然成为地方文化的标志。当下对皋陶祭祀活动的重建,在传承当地民俗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
自2007年华夏司法博物馆建成,地方民众便自发恢复小规模的皋陶祭祀活动。2020年农历九月十三日首届法祖皋陶诞辰大典的举办,使士师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皋陶祭祀活动中,传统民俗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2020年的皋陶祭祀活动中,士师村民众自发组建庙会委员会并安排活动的彩排,这次活动以华夏司法博物馆为中心,历时五日。在对法祖皋陶的祭祀过程中,庙委会成员严格按照旧时期中的祭祀仪式开展,祭祀活动中使用的贡品也是当地为长辈庆生时使用的花馍,体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在表演活动上,庙委会聘请洪洞青年蒲剧团在博物馆门前广场搭建戏台,演唱极具地方特色的《赵氏孤儿》《蝴蝶杯》《清风亭》等剧,并组织当地民众表演极具地方特色的秧歌舞,以表达对皋陶的尊崇。同时,羊獬村村民作为皋陶的神亲,在本次活动中上演了晋南地区特色的威风锣鼓,增强了村落间的互动。皋陶祭祀活动从暂停到恢复,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恢复过程,而祭祀活动的展开更为当地民俗提供了展示平台。当地民众出于祭祀的需求,重新拾起他们曾经表演与享受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活动作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随着皋陶祭祀活动的展开而持续下去。
(二)法制精神的传承
皋陶所倡导的法律精神与当代依法治国的法制观念有着很大的契合度。华夏司法博物馆建成后,这里除了是祭祀活动的空间外还是普法基地,常有中小学师生到此研学。管理人员义务向学生们宣讲皋陶的事迹与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为学生普及中国司法历史。皋陶注重刑法,主张通过法律来约束普通民众的行为。他的法制理念不仅在于“教化民众”,还针对司法人员的品德提出“九德”作为考核目标。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37。他认为能做到三者可治理家,做到六者可治理邦国,而做到全部则可治天下。2019年,最高法院与中国法院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华夏司法博物馆进行考察,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司法人员对皋陶精神的传承,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当前农村是我国普法的重点与难点地区,而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建在农村,正为农村普法工作提供了新的阵地。如今该馆被认定为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作为皋陶后人的士师村民众在博物馆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不仅主动去学习法律知识,还向周边村落民众进行法律宣传。
四、结语
在村落变迁中,士师村皋陶信仰经历了不断消解重构的过程。在当代法制化宣传的主旋律下,皋陶信仰呈现着俗信化的趋势。皋陶信仰是士师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特殊的力量约束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对待村落信仰,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引领,深层发掘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鼓励开展民俗活动,在活动中积极引导民众合理参与,让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并享用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