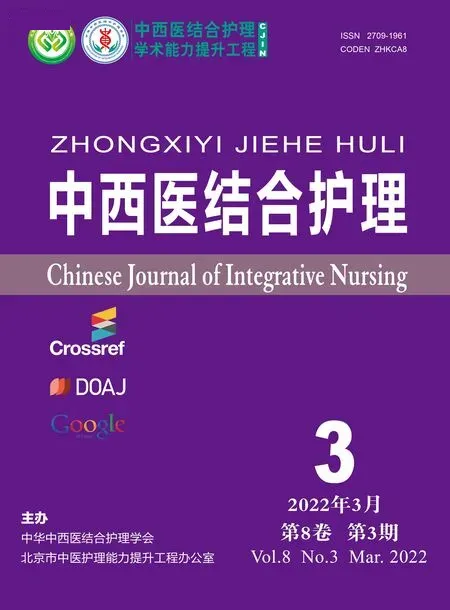中医饮食护理溯源
王亚丽,张凯烨,唐 玲,魏永春,鄂海燕,姜 婧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肛肠科,北京,100078;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护理部,北京,100078)
中医护理源远流长,它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充实、成熟五个阶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护理学内容、方法、理念和思想。中医饮食护理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护的原则,给予适宜的饮食,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1]。中医饮食护理基于整体观念和辨证施膳理论,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得以儒养,人体气血得以充盈[2]。随着中医学不断发展,饮食护理从早期简单的充饥果腹到现代的食疗养生,逐渐发展并日臻完善。本文从历史脉络角度阐述了饮食护理的发展史,现总结如下。
1 萌芽阶段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类的生活十分艰难。古代人们为了生存,将石头打造成各种工具进行狩猎生食,即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汉代刘安《淮南子》曾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螺蚌之肉”[3]。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及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类能够获得更多的动物类食物。火的发现和使用,彻底改变了“食草本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原始饮食方式,使人类的饮食从生食进入到熟食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始人类的患病几率,正如《礼记》记载:“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
2 形成阶段
夏至春秋时期,是中医饮食护理的形成时期。早在夏禹时代,酿酒技术便已被先人所掌握。最初,酒作为治疗疾病的一种剂型,能够通经活血,发散风寒。到了殷商时代,《汤液经法》中首载汤液药酒治疗疾病。发展到西周时期,官府将医者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类,其中食医排行第一,可见其对食疗的重视。而除食医之外,疾医和疡医在治疗疾病时同样采用食疗方法治愈疾病。《周礼·天官》关于食医的记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4]。而在与《周礼》成书同为周朝的《礼记》中更是进一步呼应了的食物疗法:“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蓏”[5]。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记载的110多种药品中,有很多既是药物,也是食物。
3 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医饮食护理的发展时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中大量篇幅论述了饮食护理,不仅详细列举了四性五味归经,更是倡导三因制宜与辨证施食,对中医饮食护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的饮食调护完善了对先秦饮食护理的认识。
3.1 饮食有节
《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6],说明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便能保持人体健康和神情饱满,长命百岁,终老天年。
3.2 饮食有方
3.2.1 因时制宜:《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记载:“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7]。以五脏应四时,根据五脏乘克关系,使五脏之气处于平衡状态,不至于太过或不及。
3.2.2 因地制宜:《素问·异法方宜论》曾记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说明地域不同,气候、环境、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也存在差异,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食养也需参考地域差异。
3.2.3 因人制宜:因为年龄、性别、体质的差异,在饮食调养上也会有所不同。《灵枢·五音五味》记载:“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说明性别不同,饮食护理的角度不同。就体质而言,有“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8]。
3.2.4 谨和五味:食物有四性(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各有归经,可调节脏腑阴阳平衡。《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了沿用至今的饮食五味养生大法,即“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别,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
3.3 饮食有忌
饮食护理中饮食禁忌十分重要。临床上许多疾病难愈,或愈而复发,很多与不注意饮食禁忌有关。《千金方》记载:“大凡水肿病难治,瘥后持须慎于口味,又复病水入多嗜食康,所以些病难愈也”[9]。《本草纲目》记载:“妊妇以鸡子鲤鱼同食,令儿生疮”[10]。
3.4 辨药施食
《伤寒杂病论》中“嘿嘿不欲饮食”、“呕不止、心下急”、“不能食、胁下满痛”等关于患者服药前后饮食变化的描述作为重要信息,被大多数医家在临证时所借鉴。同时在遣方用药时注重食疗的配伍运用以增强疗效,如《伤寒论》桂枝汤方的服法“上五味,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11],便明确要求药后饮粥以保证疗效。
4 充实阶段
魏晋隋唐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饮食养生的著作,进一步充实了中医饮食护理理论。魏武帝的《四时御食经》创建“饮食制度”;晋代王叔和《太平御览》则指出“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当时或无灾患,积久为人作疾,寻常饮食,每令得所;多食则令人彭享短气,或至暴疾”。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篇》、《千金翼方·养性服饵篇》以及《孙真人摄养论》等篇章中对唐代以前的饮食护理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成食疗专卷,标志着饮食护理专科研究的开始。《千金要方》中:“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强调了饮食宜忌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夫在身所以多疾此皆由……饮食不节故也”也说明饮食有节的重要性。《备急千金要方·食治》中的大量内容更是表达了他合理饮食的观念,如“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9]。
5 成熟阶段
随着医学流派的兴起,中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全新局面,中医饮食护理也逐渐完善成熟。金元四大家之一“攻下派”代表张从正主张“养生当论食补”,在其《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中提出“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肯定了以饮食养生的重要性。“滋阴派”代表朱丹溪在其代表作《格致余论》中明确提出了关于饮食养生及致病的观点:“味有出于天赋者,有成于人为者。天之所赋者,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认为均衡饮食对人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补土派“医家李东垣的《脾胃论》对饮食护理的原理、内容、方法以及忌讳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实完善,其所谓:“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13]。
北宋官方所著的《太平圣惠方》对宋代之前的饮食理论及临床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专列卷为“食治篇”,分门别类地收载食疗药膳配方,治疗各种疾病。书中“人予养老之道……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味相扰,食之不己,为人作患,是以食敢鲜肴,务令简少,饮食当令节俭”[14],重新强调了孙思邈关于饮食护理的观念。
元代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其“食疗”与“食补”并重的观点,是中医饮食护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医饮食护理的成熟。其中“春气温,宣食麦,以凉之,不可一于温也。禁温饮食及热衣服......夏气热,食宜茮,以寒之,不可一于热也。禁温饮食,饱食,湿地,濡衣服......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食,寒衣服......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禁热饮食,温炙衣服”[15],详细阐述了人们在四季中应如何合理饮食及起居,使中医饮食养生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
6 完善阶段
明清以来,随着中药性味归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食物的性味理论也得到了相应提升,饮食调护普遍受到当时医家的重视,以食疗养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亦明显增多,中医饮食护理的发展达到全新的高度。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载食物达391种,可谓饮食养生之总。高濂在其养生学著作《尊生八笺》中强调合理的饮食护理可以延年益寿。而明代太医龚廷贤的《寿世保元》着重阐述了饮食失调的危害。清初医家汪昂在《本草备要》提出了食物功效的具体概念:“每先辨气味形色,次著所入经络,再为发明其功用,而以主治之症具列于后”,彻底改变了以往食疗、药疗史上多言某食药治某病,而少言其功能的局面。至清代,中医饮食护理理论进一步完善。章穆的《调疾饮食辨》将食物按功用分为发表方、温中方、行气方等56种;而费伯雄在《费氏食养三种》按风、寒、暑、湿、燥、气、血、痰、虚将食物进行分类,更是强调了食物在疾病治疗、转归及预后的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传统的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中医丰富的饮食疗法正是寓治疗于饮食护理之中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治病当论药功,养病方可食补”,结合病情选择具有针对性的中医饮食护理,能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促进健康[16]。从春秋战国,中医饮食护理论的初步形成,到《黄帝内经》对饮食护理的丰富完善,再到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篇》对饮食护理的重视,至宋金元时期,各类医学流派皆提倡饮食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形成了中医饮食养生的集成大作,中医饮食护理在不断拓展延伸。饮食养生专著在推广健康饮食的同时,饮食护理作为中医疗法也得到进一步推广与普及[17]。中医护理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基于历史悠久的中医基本理论,加以极具特色的中医技术及食疗、运动、情志护理等方法,重视人体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护理体系[18],这是中医饮食护理的源流所在,也是未来人类健康的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