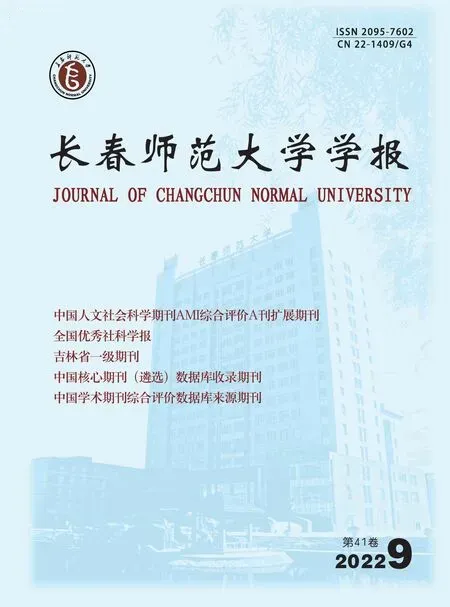宛敏灏先生词学思想探赜
——围绕《词学概论》词调观展开
沈文凡,林婉心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词原是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才脱离音乐关系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1]3词在刚刚兴起时,并无所谓词学。两宋以来,词乐研究、词史研究、词谱研究等逐渐兴起,明清时期达到兴盛。近百年来,词学进一步发展,大家名家辈出。其中宛敏灏先生潜心研究词学,不仅在词人别集方面有颇多建树,还将数十年研究心得汇编为《词学概论》,推动了词学知识的传播与发展。
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上不类诗,下不似曲。从词的本体论而言,词调是词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显著标志,是词之为词的本质特征。在《词学概论》中,宛敏灏先生从整体上展现出词调史的起源发展,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辨析词调三分的标准,阐明调题离合的问题,体察入微,论析精警,立论公允。
一、概论词调沿革
词调研究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词乐文献的缺失、研究方法的不足等原因,词调研究相对落后。研读《词学概论》,可知宛敏灏先生早于几十年前已从多侧面、多角度探讨词调,不但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词调史,还形成了词调以节拍而非字数进行划分的判断,并总结了词调别体产生的三条途径,具有极强的问题敏感性和学术前瞻性。
(一)提纲挈领的词调史概述
随着乐曲的流变与声韵的发展,词调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现存的千百个唐宋词调经历了几百年的变化,追述其源头极为困难。宛敏灏先生溯源析流,阐释了词调的由来与繁衍,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语言精省且锤炼得当,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宛敏灏先生遍查古籍,剔抉爬梳,先将音谱的来源归为六类,即“截取隋、唐的大曲或引用琴曲”“由民歌、祀神曲曲、军乐等改变的”“从国外或边地传入的”“宫廷创制”“宋大晟乐府所制”“词人自度(制)曲”;并指出这六种来路中,“前三种属于因袭,后三种则出自创新”[1]70,以极简洁的方式勾勒出词调的来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类来源举证,如“从国外或边地传入的”这一类中举出《菩萨蛮》《苏幕遮》《普赞子》《蕃将子》《八声甘州》《梁州令》《氐州第一》的词调;“宫廷创制”一类中又划分为“出自帝王”的《水调》《河传》《破阵乐》《雨霖铃》《燕山亭》和“出自乐工”的《夜半乐》《还京乐》《千秋岁》;“词人自度(制)曲”一类中特别强调:“柳永《乐章集》里用调达一百二十个,但仅有七个同于敦煌旧曲。其《昼夜乐》《佳人醉》《殢人娇》等,可能都是为歌妓制作。”三言两句间把自己潜心考辩的成果呈现出来,足见其扎实低调的治学态度。
在词调发展历程中,自度腔、自制腔是其繁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后世常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率意吹管成腔,然后填词,这种叫做自度腔;先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制谱,就叫做自制腔。”[1]73词人往往在序言中说明所创制的词调为自度腔或自制腔,如《扬州慢》:“因自度此曲。”《长亭怨慢》:“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淡黄柳》:“因度此曲,以纾客怀。”经考证,这类记载和真实情况颇有出入,这是因为宋人已将两者混淆,后世之人更“不复措意”[1]75。除了这两类出自一人之手的词调外,还有“又一体”。“又一体”即词调的别体,表现形式多样,实质是“把旧调平仄互换”,是明清学者对词调规律的总结。万树《词律》、杜文澜《词律补遗》中记载,别体有成千上百之多。
“词体发生史的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历史本身’,乃是产生于人们的实践、凝聚着历史‘行为过程’的词(词调、词体、词文)。而‘词调’研究则是破译词体‘起源’发生密码的关键之一。”[2]24-34辨明源头、疏通脉络,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宛敏灏先生在概述词调发展的来源后,从因袭和创制两个角度说明了音谱的发展,并详细说明了自度腔、自制腔和“又一体”,繁简得宜,详略得当。
(二)见解独到的词调“三分”考论
词调“三分法”是明清词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3]。“三分法”是指将词调划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这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纳和认可,但划分的依据有待商榷。
明清以来,一般以字数为划分词调的依据。毛先舒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此古人定例。”但沈雄说:“唐、宋作者只有小令、曼词,至宋中叶而有中调、长调之分,字句原无定数,大致(中调)比小令为舒徐,而长调比中调尤为婉转也。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中调以六十字起至八十九字止,遵旧本也。”[1]46-47两种说法虽然都以字数为标准划分词调,但彼此之间存在出入。朱彝尊和万树也曾对此论点提出质疑,因此宛敏灏先生指出:“这类按字数来严格区分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47这是对前人观点的反思和判误,展现出辩证的学术思维。
词调“三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令、引、近,慢的名称,是表示就节拍的不同来区分曲类”[1]50。宛敏灏以王易和吴梅的说法佐证自己的观点。王易在《词曲史》中提到:“令、引、近,慢在宋时名曰小唱,惟以哑觱篥合之,不必备众乐器,故当时便于通行。其节奏以均拍区分,短者为令,稍长者为引、近,愈长则为慢词矣。”此外,王易将“均”作为节拍的标准,指出:“故不少六均之调,明称为令;八均之调,明称为引,近者;至于八均以上之慢,又不胜数矣。”吴梅认为,“词中之引,即如大曲之散序,无拍者也;近、令者,有节拍者也;慢者,迟声而歌,如后世之赠板者也。”[1]50这两种说法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都表明词调的差别在节拍而非字数。唐圭璋和夏承焘先生也有类似观点。唐圭璋在校释《云谣集》杂曲子时,发现同一词调字数不定的现象,如“《竹枝词》第一首五十七字,第二首则六十四字。《花间》亦有同调不同数之词,是知唐词往往如此,不似后世不能歌之词,一字不容出入也”[4],夏承焘说:“这种完全以字数划定词调的方式十分机械,令、引、近、慢的区别是由歌拍节奏的不同决定的。”[5]42-43可见,词调以节拍而非字数进行划分的观点被普遍认同。
词调“三分法”作为词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对推动词谱编订、促进词学批评具有积极影响,但该观点仍有不完善之处。宛敏灏先生提出词调划分的依据是节拍而非字数,认为在掌握相关拍眼名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词调音乐性的了解,有利于掌握词的本质特征,展现出审慎严密的学术判断和深微独到的学术见解。
(三)简明扼要的词调别体阐释
词调作为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指词的文词和音调;随着词体中音乐性的消亡和文学性的突出,变为专指律词的格调。词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衍生现象。“词之为调,有六百六十余,其体则一千一百八十有奇。”[6]44这些别体列在词调之后,称“又一体”。别体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宛敏灏辨其来源、梳其根本,总结出由简而繁、由繁而简、谱拍间的变化三条途径。
首先,由简而繁的特点往往体现在“先有小令,后来又有同调名的中调或慢词”[1]77。以常见的《忆江南》为例,皇甫松的“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共二十七字。吴文英同词调“又一体”五十四字,而冯延巳的“又一体”为五十九字。吴文英和冯延巳的“又一体”在皇甫松的基础上加了一叠,从单调到双调,由简省到繁复,这是别体出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次,由繁而简指的是“先有大曲、法曲,然后有歌头、摘遍等”[1]78。大曲指唐宋时代的大型歌舞曲,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而法曲作为大曲的一部分,因融合佛门、道门曲而得名。《词学概论》以三个词调说明此类途径。吴文英的《梦行云》看似与一般的词一样,但根据词人自注,“即六幺花十八”,可知其摘自大曲。除了详细说明吴文英《梦行云》的来源,宛敏灏还指出:“《泛清波摘遍》、《法曲第二》等都是从大曲或法曲摘取其声音美听而又能自为起结的一遍,单独谱唱成为一般的词。”[1]78论据充分,详略得当,说明了别体出现的又一途径。
最后,谱拍间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增减腔调因而字数亦有变动者”[1]79和“因律调的变动而成为新体者”[1]80。其中,南唐李璟《摊破浣溪沙》、宋代张先《减字木兰花》《偷声木兰花》、唐代白居易《杨柳枝》以及后蜀顾敻《添声杨柳枝》是因增减字数而发生词调的变化;转调的《转调踏莎行》、犯调的《凄凉犯》则是因律调的变动而改变词调。考察词调别体的变化途径,除了以词调本身的转韵结构为规律外,词人的自序往往是最直接的依据,姜夔在《湘月》的自序中提到:“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
词调别体产生的三条途径是宛敏灏先生在考辨、深思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他不仅将千头万绪的别体途径归纳清晰,为词调衍生变化厘清头绪,更通过丰富的论据阐明观点,可见其学识之丰富、态度之严谨。
二、辨析调题一致
词调是词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区别于声诗、乐府、曲体的标志,调名则是指每一个唐宋词调的名称。苏轼提出“自是一家”的词学主张后,词调和词题、词作内容的关系逐渐疏离,常常出现旧调作新词的情况,如今学界也往往只将词调名作为区分声调格律的标志。事实上,“词调最初创制的时候,应该都有意义,而且和内容有密切关联,大多数调名也就是词的题目。”[1]71宛敏灏先生主张最初词调与词题相一致,且与词章内容密切关联。
“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体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7]21《花庵词选》表明词调最初与词题相合,词作内容也与词调契合,后来因为宫调失坠、乐谱失传、词律演变等原因,词调与词题逐渐疏远。《词学概论》详细论述了调题离合问题,指出调题最初是紧密联系的,强调了词调本事的重要性。
宛敏灏先生将调名的来源分为沿袭与创新两类。沿袭这一类恰好可以说明词调与词题的离合问题。起初,词调与词题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以所咏之物命名的,有写摸鱼的《摸鱼子》、写卖卜的《卜算子》、写梁祝故事的《祝英台近》、写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仙》、写南方风的《南乡子》、写迎神祀庙的《河渎神》、写江妃水媛的《临江仙》等。再如,以本词的字数或词句命名的,有《十六字令》(全首共十六字),《三字令》(通首为三字句)。之后,由于摘句成名等情况的出现,词调和词题、词的内容的距离不断疏远,关联也逐渐变小。
近代以来,有颇多学者与宛敏灏先生的观点一致。吴梅在《曲学通论》中认为,调名“有取古人诗词中语名者”[8]201。詹安泰在《论调谱》中探讨调名之由来,在“以所咏之物命名”“就本词的字数或词句命名”两类之外,还有“以词中情意为调名”“以句举词因而为调名”“以句法为调名”“取古人诗语为调名”“以非所咏之物为调名”“以地名俄日调名”“以人名为调名”等共计十一类[9]71-76。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提到:“诗文都有题目。一般说来,根据题目就可以推知诗文的内容。词则不然。有的赋调名本意,词的内容与调名相合,那么其调名也就是词题。有的与调名无涉,其调名不过是表明所用的曲调声腔,那么就无法根据调名窥知词意。”[10]133田玉琪在《词调史研究》中也说:“词调命名原理与汉魏乐府题名十分相似,多以本意命名,即叙何事、赋何物即用何名。”[11]62
宛敏灏先生值得称道的不仅是于细密幽微之处发现问题,更能在剖析问题之后寻找出问题本质与学术内核。以调题的离合问题为例,宋代以来,便有人主张词调与词题存在由合向离的发展趋势,几百年间多有相似言论,宛敏灏先生却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他指出:“知道创调时原词的内容写的什么,可以作为了解这一词调声情的参考,因而调名起源确可考查的不妨搞清楚,如将那些来历不明的也都加以悬揣附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1]73发现问题往往不是最终目的,透过问题回归学术研究的初心,理性思考问题背后折射出来的种种现象才是目的。若还能为后来研究者拨开谜雾、扫除荆棘,才真正称得上是大师名家。
词调与词题最初具有一致性,词章内容和传达出的声调情也与调题紧密关联。因此,掌握词调本事对词意解读、词作鉴赏等具有重要作用。调题一致的主张,不但促进了宛敏灏先生词调观的完善,而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词调是词的本质属性,词调本事反映出词调与词题之间的离合关系。“在词乐尚未完全失传以前,有部分腔调已逐渐失去音谱,无法歌唱;作者依照旧词填写,也无意为应歌之用。另一方而,乐工和文人根据需要,继续不断地在创制新调并填词。”[1]73由于各种原因,词调与词题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不可否认的是,词调创制之初,调名即为调题,与所咏内容密切相关。《清平乐》“乐”字读音看似在讨论读音问题,其实是词学知识在当代社会中应用实践的体现。在了解调名起源的基础上,才能考察词调声情,也就不难反证词调的读音。
三、阐释选声择调
“词,既已成为格律诗体之一,则运用旧形式而赋以新内容应是可行的。”[1]335《词学概论》由宛敏灏的课堂讲义补缀而成,不仅在理论建构层面论述词学知识,详述词调主张,更在学术实践层面帮助后学者厘清概念,指导学术创作。宛敏灏先生从应否依照格式和怎样选调两个方面阐释选声择调,主张作词应当巧妙使用选声择调的技巧与方法,在既有的规范体式内进行灵活创新。论述语言精简洗练、一语中的,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一)详谈“应否依照格式”
“作词之法,论其间架构造,却不甚难。至于撷芳佩实,自成一家,则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所谓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有一成不变之律,无一定不易之文。”[6]43作词之难,不仅体现在讲究词境、词意、词法,更体现在词调、词韵、词律的使用。宛敏灏先生主张以旧形式写内容,写词应当依照格式。
首先,在写词的实践中,应当依照格式。若袭用旧调而改其格式,则丧失了词调的价值。“词,早已成为‘句读不葺之诗’。它源于乐府,并各有词牌。我们现在所谓填词,实际是旧瓶装新酒。倘取消这一包装,那就完全失去再用旧称的意义。”[1]345有学子请先生给自己所写的《西江月》提意见,先生说:“只有个别字建议改一下,最好是《东江月》,‘南’或‘北’也行。以你‘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豪气,何苦老守什么《西江月》的清规戒律受罪呢?”面对习作,先生并未疾言厉色、大声呵责,而是通过幽默的比喻、活泼的语言阐释观点,认为填新词可不受旧词《西江月》的束缚,尽可率性而为、施展才华;欲填旧词而出新意,则需严守词牌词调的限制,不妨在内容上创新,以旧形式写新内容。先生认为,随着词谱的遗失、词律的演变,词的音乐性不断减弱,“词至今日,已和诗中的近体同属于格律诗。”[1]346但是格律诗包含的内容多、范围广,词则各有词调。既然词调各异,声情、体式自然更不相同。
其次,“自度曲”重在音谱而非歌辞。有学子问及,随意所作的长短句自命为“自度曲”是否正确。先生认为,“关键在于其人是否也作了乐谱,否则只可视为一首杂言的古体诗。倘他人代配乐谱,则应如现代分别标明某人词,某人作曲,不存在是否自度的问题了。”[1]346词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本质属性是音乐属性,自己谱曲、作词方为自度曲,若无曲则是杂言古体诗;若由他人谱曲,便属于现代音乐的范畴。在开门见山说明观点后,先生以委实详尽的论据进行佐证。《白石道人歌曲》中记载姜夔常在小序中指出词调情况,如《长亭怨慢》:“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说明作词制谱的先后顺序;《玉梅令》:“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说明旁谱为范家新曲,而白石仅依谱填词。此外,其他自度曲也有类似情况,如《扬州慢》“因自度此曲”、《淡黄柳》“因度此阕”、《惜红衣》“自度此曲”等[1]346。可见古之“自度曲”的形式多样,重在音谱而非歌辞。
“为配合音乐而提出的严格要求当然不必墨守,但如忽视必要的格律,也是不成其为词的。”[1]346现代人写词可以创新,可以用旧形式写新内容,但不能完全忽略格律形式。面对旧体诗词在新时代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时,宛敏灏用质朴平实、言简义丰的语言解释词学理论,又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方式开导解惑,说理有逻辑,释疑有方法,实为大家之风。
(二)细说“怎样选调”
作诗择诗体,作词择词调。“调有定格,字有定音”[6]1。词调选择颇有讲究,从千百词调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并不容易。“择调不当,或声文乖戾,或有误美听,或不合曲名与传统作法,都将妨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10]119选声择调要从长短和声情两个方面考察。
一方面,小令、慢词各有所长,要根据作者需求选择。从初学者的角度而言,应先写小令,不作孤调僻调。宛敏灏先生引用张炎《词源》和蒋兆兰《词说》的说法,认为“初学宜从小令入手,渐进而及于慢词。”[1]348张炎说:“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若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人来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说明大词可为小词,小词却不能展为大词。他又说:“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瑕之玉。”[1]347说明慢词需字字琢磨、反复修改。蒋兆兰说:“初学作词,如才力不充,或先从小令入手。若天分高,笔姿秀,往往即得名隽之句。然须知词以沉着浑厚为贵,非积学不能至。至如初作慢词,当择稳顺习用之调,平仄家可移易者为之,庶几不苦束缚。既成,再将词律细心对勘,务使平仄悉谐,辞意双美,改之又改,方可脱手出以示人。逮至功夫渐到,然后可作单传孤调及研究上、去声字。”[1]348强调作词择调应当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另一方面,词调固有长短之别,但更重要的是声情的区别。哀怨或是愉悦,刚劲或是柔婉,急促或是轻缓,“由于字句的长短、声韵的平仄都是互相配合的,不能皮相观察。惟有反复吟诵,才能悠然心会,更好地领略其声情。”[1]350由于词律的变化、词谱的遗失等因素,考察词调本身的声情难度颇大。部分词调可以从最初的词中感受,“如《忆秦娥》最早的一首‘箫声咽’见于《花庵词选》,题李白作,其词幽咽悲凉。后来贺铸改为平韵‘晓朦胧’,亦未改变其怨抑的情调。《望海潮》始见于柳永《乐章集》,极写钱塘的繁华。秦观依调作洛阳怀古,仍然是写胜况多而凭吊意味少。”[1]348-349然而大部分词调属于旧调新作,早就失去最初的声情,难以考察。如“《鹧鸪天》这一词调看:贺铸曾以之写悼亡词(中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句,易名《半死桐》),张孝祥却以之写春游雅兴‘日日青楼醉梦中’。在姜白石词里,既有‘歌以寿之’,也有抒写元夕的伤感。”[1]349因此,先生总结道:“一句话,情调是欢愉的还是悲伤的,主要只看歌辞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而已。所谓从文字去探索某一词调的声情,也只是求得其近似而已。”[1]349-350
在作词的实践中,循旧例而出新词需要通晓词学基本知识,掌握选调的基本方法,审慎考察词的长短和声情,由小令到慢词,由简易到困难,循序渐进,时常吟诵,把握声情。宛敏灏先生从实践指导角度深化了词调理论,于细微处展现出完备严谨的词调观。
四、结语
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词学家,宛敏灏不仅总结了传统词学,也奠基了现代词学。《词学概论》涉及词的章法、句法、体制、词韵、词调、词话等词学知识,面面俱到,包罗巨细。词调观是宛敏灏先生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整体上把握了词调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词调三分的依据是节拍而非字数,并总结出由简而繁、由繁而简以及谱拍间的变化等三条途径,还强调了调题一致的词本事的重要性,其中颇多简明扼要、切中肯綮之言,注重普及与拔高的结合,既能帮助初学者得其门径,也能使精通者完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