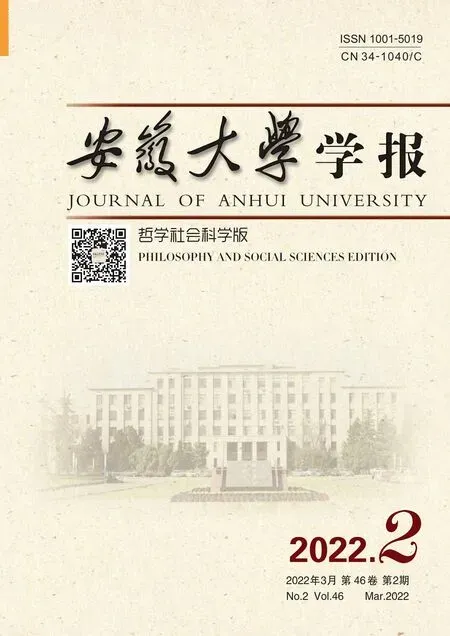乾隆朝制科、科举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杨青华
乾嘉考据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代表,关于其成因的探讨,一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热门议题,前辈学人多有论及。各家主张虽有差异,然大体而言,无外乎外在政治因素和内在学术理路两种思路(1)关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原因之探讨,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其较著者如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余英时、朱维铮、王俊义、孙钦善、漆永祥等。章太炎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清代文字狱、愚民政策联系起来,即所谓的“政治高压”说[《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2页]。梁启超在“文字狱”外缘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以复古为解放”的理学反动说,其实坚持内在与外在两重因素说(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页)。钱穆持两说,一为“压迫”说,一为“每转而益进”说(分见《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册,第3页、414页)。余英时在外在社会与政治外缘的基础上提出“内在理路”(《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页)。朱维铮则提出“文化分裂政策”说(《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131页)。王俊义在不否定“文字狱”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密切相关(《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6~224页、225~237页)。孙钦善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取决于学术本身的发展,是清代考据学者批判明代空疏学风、继承考据学悠久历史传统、选择务实学风的结果(《清代考据学》,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0~25页)。漆永祥则认为“文字狱”与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并无直接关系,前人说法有夸大之嫌,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是各方面综合的结果,与清廷的文化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乾嘉学者的经世心态、学术的内在发展规律密切相关(《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7页)。。其中外在政治因素牵涉清廷的文化政策,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文字狱联系起来,认为乾嘉学者埋首考据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二是以此为清廷大力提倡的结果,然而多视之为清廷的愚民政策(2)此说产生于清末反满革命的背景下,以章太炎为代表,之后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如侯外庐、陈祖武等皆持此说。可参阅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0页;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相较“文字狱”的讨论,关于清廷的倡导如何促进考据学兴起的讨论显得较为单薄,还有深入探讨之必要(3)就笔者所见及,关于此问题探讨最为全面系统者,当为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对此有系统探讨,所论虽全面然而亦较简略,个别问题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本文通过梳理乾隆朝的科举以及科举之外的博学鸿词、保举经学等制科的具体历史情势,试图从抡才制度层面探究清廷的文化政策与乾嘉考据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深化对乾隆朝文教政策与乾嘉经史考据学关系的认识。
一、科举之外的举措:乾隆朝博学鸿词、保举经学与经史实学之风
(一)乾隆朝博学鸿词与经史实学之风
清初,为了缓和满汉矛盾,笼络汉族士人,清廷于科举之外,分别于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元年(1736)三开博学鸿词,除雍正朝因应者寥寥而不果外,“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右文之盛,前古罕闻”(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6《选举一》、卷109《选举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099页、3178页。,后世分别称之为“己未词科”和“丙辰词科”。抛开政治效用,仅就学术层面来讲,无论己未词科还是丙辰词科,一批热衷功名的汉族文士及学者因此被清廷所延纳,其中康熙朝应者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五十人,皆授以翰林官,助修《明史》;丙辰科应者一百九十三人,录取仅十五人,仿康熙朝例,亦皆授翰林官。
康熙、乾隆两朝的博学鸿词名虽同,然而时迁世易,其具体情势已大为不同(5)孟森于此曾言:“己未惟恐不得人,丙辰惟恐不限制。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己未为上之所求,丙辰为下之所急。己未有随意敷衍,冀避指摘,以不入彀为幸,而偏不使脱羁绊者,丙辰皆工为颂祷,鼓吹承平而已。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乃士有冀幸于国家,不可以同年语也。”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8页。。不唯政治效用及应试者心态不同,其实两场博学鸿词的考试程序、内容亦不相同,此反映出康、乾两朝词科不同的取士倾向。康熙朝博学鸿词科注重文藻瑰丽、文辞卓越(6)《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1,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0页。,因此仅试以诗赋,“试一场,赋一、诗一”(7)陆以湉:《冷庐杂识》卷1“博学鸿词”条, 崔凡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从康熙己未词科录取名单看,所取者多为文学之士,如施闰章、陈维崧、尤侗等,其中虽有如朱彝尊、毛奇龄等善经史考据者,但二人亦颇具文名,正如四库馆臣所论:“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之内,已与王士祯声价相齐。博识多闻,学有根柢,复与顾炎武、阎若璩颉颃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5《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第732页。奇龄亦是“著述之富,甲于近代”,经史子集无学不究,其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3《西河文集》,下册,第1524页。。正如胡琦指出的,“康熙虽高悬‘鸿儒’之名,却并未接受理学士大夫‘师儒’自任的姿态,实际所重,乃是文藻瑰丽的‘词臣’”(10)胡琦:《己未词科与清初“文”“学”之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78页。。
相比康熙朝词科,乾隆朝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11)《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50《选举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2页。,此在考试内容上即有所体现,“试二场,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经、史、论各一”(12)陆以湉:《冷庐杂识》卷1“博学鸿词”条,崔凡芝点校,第4页。。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说得较为明白:“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下吏部议,最终定为两场,赋、诗外增试论策。在乾隆二年补试时,采纳御史吴元安之议,顺序亦有所调整,“定为两场,首场试以经解一篇,史论一篇,二场照例试以诗、赋、论三题”(13)《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50《选举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第262~263页。吴元安《请定试博学鸿词之例疏》言:“臣窃思考试之法,向例以诗、赋、论三题,限以终日。诚恐淹迟敏捷,各异其资,在沉潜淹贯、积学深思者,或不足以尽其所长,而纤才薄植、工于摹拟者,或转得邀其幸试。臣请敕定,首场试以经史,发难论辨,觇其抱负,越日,二场试以诗、赋,拟古应制,观其词藻。”《皇清奏议》卷33,《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较康熙朝词科,乾隆朝词科在诗赋的基础上增加策论,更为重视经史实学。如丙辰词科,与齐召南一起应选的还有大才子袁枚,但袁氏却落选,袁氏言:“乾隆元年秋,余与齐公次风同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一时士论,佥以实学推公,及榜发,钦取十五人,公果与选,余虽报罢,而公念同征之谊最殷。”(14)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5《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2册,第279页。袁氏虽落选博学鸿词,然三年后亦中进士。袁、齐二人的词科际遇很能体现康熙、乾隆两朝词科取士的异趣。又如浙东学派全祖望亦赴乾隆朝博学鸿词,因已中是年科举而罢,但其因精通经史之学而卓荦于众人,阮元曾言:“先生举鸿博科,已官庶常,不与试,拟进二赋,抉《汉志》《唐志》之微,与试诸公皆不及,精通经史故也。”(15)阮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揅经室集》上册,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4页。由此可见精通经史之学者在乾隆朝词科考试中占据优势。
乾隆朝博学鸿词注重经史实学,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乾隆帝继其父雍正开博学鸿词敦崇实学、稽古右文之志。雍正十一年曾举博学鸿词,后虽不果,但其立意甚为明白,即敦崇实学,诗赋、经史并重,以示稽古右文之意。世宗诏开博学鸿词曰:“朕延揽维殷,辟门吁俊,敦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鸿词之选者,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16)王先谦编:《东华录·雍正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71册,第501页。其二,与御史吴元安开博学鸿词陈奏直接相关。吴氏《请定试博学鸿词之例疏》云:“臣伏思,博学鸿词原非以记问夸多,词章竞艳者也。古圣心传,昭著于经,历朝政治,胪列于史,是经史者,人品之模范,即为学问之渊源,必融会熟习于胸中,自学为有用之学,而言亦有用之言。内外大臣果能真知灼见,慎厥保荐,斯可以称得人之庆,而备睿问之选。”(17)《皇清奏议》卷33《请定试博学鸿词之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第279页。吴氏生平学行,相关文献无多,此疏是因自己学术立场而陈,抑或领会上意而奏,均不得而知,然其主旨甚为明白。首先,其“博学鸿词原非以记问夸多,词章竞艳者也”云云,既可能是因当时士风学风有感而发,亦可能针对康熙朝词科取士偏重文藻瑰丽、文辞卓越的有为之言。其次,就是注重经史之学,认为经史之学切己实用。
康熙朝与乾隆朝虽两开博学鸿词,但因时代不同,政治环境各异,因此程式及效用差别明显。康熙朝词科较重诗赋文辞,选中朱彝尊、毛奇龄等擅长经史考据者仍属无心插柳之举。然此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确实影响甚巨,是为乾嘉考据学的先驱,为乾嘉诸老所称道(18)阮元论毛奇龄学术言:“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僿,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祖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揅经室集》上册,邓经元点校,第543页)关于康熙朝己未博学鸿词科在清初学术界的影响,目前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研究。一是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康熙朝词科与其选者多为当时文坛名宿,对之后的清代文学生态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从经史实学的角度展开,主要集中于毛奇龄、朱彝尊等人,如张立敏《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昭梿《啸亭续录》言:“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19)昭梿:《啸亭杂录》之“啸亭续录”卷2“考据之难”条,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8页。此即将毛奇龄、朱彝尊与顾炎武并列,视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人物。
乾隆朝的博学鸿词是乾隆帝提倡经史实学的重要举措和表征。其中杭世骏、齐召南二人,经史考据为其擅场,此属于有心栽花的结果(20)乾隆元年博学鸿词还有擅长经史考据而未能录取者,如徐文靖“考据经史,讲求实学”,龚元玠亦善经学,皆未被录取,后乾隆十九年中进士科。参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册,第5482页、5488页。。齐召南,字次风,善经史、地理之学,著有《尚书注疏考证》《礼记注疏考证》《汉书考证》《水道提纲》等,其《水道提纲》,“故所叙录,颇为详核,与《水经注》之模山范水,其命意固殊矣”(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9《水道提纲》,上册,第616页。,其《汉书考证》亦为清代《汉书》学的代表著作,曾参与《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等纂修事务。杭世骏,字大宗,学问博洽,著述宏富。著有《石经考异》《礼例》《续礼记集说》《续方言》《经史质疑》《两浙经籍志》《续经籍考》等。其《续方言》“搜罗古义,颇有裨于训诂”,“引据典核,在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其《石经考异》“较顾炎武之所考,较为完密”。其《三国志补注》“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于史学不为无补”(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0《续方言》、卷86《石经考异》、卷45《三国志补注》,上册,第343页、743页、405页。。杭氏还参与校勘《十三经》《二十四史》,并纂修《三礼义疏》。正如毕沅所言:“梨洲、宁人振实学于前,而竹垞、西河继之,堇浦先生其学之博而精,实足以继朱毛而追黄顾。”(23)毕沅:《道古堂文集序》,转引自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第327页。可见后世将杭置于顾、黄、毛、朱之后,惠、戴之前,实为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先进。
(二)乾隆朝“经学保举”与经史实学之风
乾隆朝的“经学保举”是乾隆朝词科的继续,其目的亦甚为明确,“时承平累叶,海内士大夫多致力根柢之学,天子又振拔淹滞,以示风劝,爰有保荐经学之制”(2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9《选举四》,第12册,第3178页。。乾隆十四年,乾隆帝下诏内外诸大臣留心经学,谕曰:
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以诗赋,颇致力于词章,而求其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训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欤?抑有其人而未之闻欤?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巨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剪彩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称朕意焉。(2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52,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清实录》第13册,第860页。
清承明制,科举考试,尤重《四书》文,因此清初至乾隆朝初期,庙堂之上,翰林词苑之中,或多为理学之士,或善诗文辞赋者,而鲜通经之士,此从《清史列传》之“儒林”“文苑”二传所录乾隆朝以前学者之学行即可得而知。乾隆帝推行经学保举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士人或因功名而汲汲于制艺,或为邀圣宠而致力于辞章,鲜有博通经术者,乾隆帝对此颇为不满;二是乾隆帝认为经术事关治术,良关世道人心,因此着意经学,试图以其抡才。
其实乾隆帝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有端倪。除上述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取士注重经史实学,乾隆三年,乾隆帝训导士子留心经学,命各省学官广泛印刻康熙朝御纂经义诸书,以备士子学习之用,以达“明道经世”之目的。谕曰:
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是在各省学臣谆切提撕,往复训勉,其有不率教者,即严加惩戒,不少宽贷。至于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务期有益于胶庠。(2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10册,第243~244页。
由此可知,乾隆帝早已对科举士人汲汲于帖括时文而无真才实学、言行不一深表不满,其论调与举行经学保举的原因大体无二。可以说,十四年的经学保举是乾隆帝此种认识的继续和发酵,并由学校文教改革而扩展至选举抡才实践(27)关于乾隆朝“经学保举”具体过程,可参宋元强《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乾隆朝“经举”本是高宗创举,其选录程序、标准皆无故事可循,内外臣工对此多持观望态度,因而历经三年始告完成,最终录取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2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92,乾隆十六年六月丙午,《清实录》第14册,第153页。。
在所举四人中,尤以顾栋高声名最著。顾栋高,字复初,康熙六十年进士,他“少与同里蔡德音、金匮吴鼎精心经术,尤嗜《左氏传》,遇拂意,家人置《左传》于几上,则怡然诵之,不问他事”(2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76页。。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四库馆臣论曰:“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3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9《春秋大事表》,上册,第241页。陈祖范,字亦韩,雍正元年举人,四库馆臣论其学曰“学问笃实”,多“通达之论”(3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3《经咫》,上册,第279页。。吴鼎,字尊彝,乾隆九年举人,著有《易例举要》《十家易象集说》《东莞学案》,曾与蔡德音、秦蕙田等举办经学会。梁锡玙,字确轩,雍正二年举人,膺荐时,以《易经揆一》进呈御览(3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78页。。乾隆三十年,阮元奉命纂修《国史儒林传》,高宗降谕,明示要表彰四人(33)高宗谕曰:“且如《儒林》,亦史传之所必及。果其经明学粹,虽韦布之士不遗,又岂可拘于品位,使近日顾栋高辈,终于淹没无闻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44,乾隆三十年九月戊子,《清实录》第18册,第192页。,顾氏等因此而被列为《儒林传》之首(34)阮元言:“臣等今纂《儒林传》,及于顾栋高、陈祖范等,敬录圣谕,冠于传首,庶仰见崇经博史,表著寒儒之至意。”阮元:《儒林传稿》卷1《顾栋高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21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乾隆朝国子监的改革也体现了乾隆帝敦崇实学、倡导经学之意,且与此次经学保举相关。乾隆二年,时任刑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孙嘉淦向乾隆进言,改革国子监,严立课程,勤其考校,设经义、治事二条,规定:“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中》《传说》诸书,探其原本,于人伦日用之理切实讲明。”(3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8,乾隆二年八月癸亥,《清实录》第9册,第826页。在十四年经学保举之后,吴鼎、梁锡玙皆因通经学而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清史稿》评论道:“举人吴鼎、梁锡玙,皆以荐举经学授司业。……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3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6《选举一》,第12册,第3103页。
保举经学的同时,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颁赐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以“资髦士稽古之学”(3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84,乾隆十六年三月戊戌,《清实录》第14册,第44~45页。。可以说,高宗提倡经史实学,表彰经史之士不遗余力。于此,昭梿《啸亭杂录》云:“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38)昭梿:《啸亭杂录》之“啸亭杂录”卷1“重经学”条,何英芳点校,第15~16页。陈康祺《郎潜纪闻》亦言:“我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39)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郎潜纪闻二笔》卷8“进呈著述”条,晋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2~463页。
二、乾隆朝科举与经史实学之风
如果说“博学鸿词”“经学保举”是乾隆帝在科举制度之外招揽经学之士的非常规举措,那么乾隆朝科举试策则是他提倡经史实学的主要途径,一大批经史通明之士通过科举取得高位。
清代科举大体沿袭明制,然而亦多有损益,其程式及内容的改革体现了清廷文化政策的转向。自顺治二年(1645)开科至乾隆二十年,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为《四书》《五经》,分别作文三篇和四篇;第二场为论、诏诰、表、判;第三场为经史时务策。自明代以来,科举考试中虽并试《四书》《五经》,然而《五经》却素不为士子所重,如何平衡《四书》《五经》的位置,一直是清代科举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顺治二年清廷举行第一次科举就实行“五经中式”之制,以扭转、平衡士子偏重《四书》、不重《五经》的风气。无奈“五经中式”在具体实践中弊端丛生,并不能有效选拔经史实学之士,因此在乾隆朝遭废除。如何处理《四书》《五经》在科举中的位置仍是乾隆朝科举改革的重头戏。因此,乾隆二十一年废除第二场论、表、判、策,将《五经》文置于第二场,此亦体现乾隆帝提倡经学之意。乾隆帝言:“今士子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剿说。而阅卷者亦止以书艺为重,即经文已不甚留意。衡文取士谓之何?此甚无谓也。三场试以书艺、经文,足觇素养。继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负之深浅,又何庸连篇累牍为耶。”(4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清实录》第15册,第625页。安东强认为乾隆二十一年的改革,将《五经》文移至第二场,是乾隆帝默认科场重《四书》、轻《五经》的风气(《清代乡会试五经文的场次及地位变化》,《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84页)。然而从乾隆改革的初衷来看,只是对原先第二场论、表、判“雷同剿说”之风深表不满,并非有意贬低《五经》的地位,由其“三场试以书艺、经文,足觇素养。继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负之深浅”云云可知,在乾隆帝看来,首场《四书》、二场《五经》、三场时务策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模式。当然,乡会试考官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对待《四书》《五经》则是另一问题,并不能算是乾隆帝科举改革的初衷。此后形成首场《四书》文、二场《五经》文,三场时务策的基本格局。并且为一改清初以来《五经》文专经中试的弊端,乾隆六十年科举开始,轮试《五经》,使得士子不能投机取巧而只钻营一经,须博通《五经》。可以说乾隆朝的科举改革鲜明地体现了乾隆帝重视经史实学之意。
科举最后一场为殿试,内容为时务策,由皇帝出题亲试,最能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据《清实录》统计,康熙朝举行正、恩科会试凡21次,其中康熙三十年、四十三年、五十一年、五十四年、五十七年殿试策论间有涉及经学问题,但基本不涉及史学。雍正朝举行正恩科会试凡5次,殿试策论未有涉及经史之学。但至乾隆朝,在殿试考试中,经史论题明显增多,此亦与乾隆帝素重经史实学密切相关。如乾隆元年科举,乾隆帝直言:“欲令士敦实学,明体达用。”(4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乾隆元年四月丙寅,《清实录》第 9册,第428页。笔者统计,乾隆朝一共举行科举27次(42)据笔者统计,乾隆朝会试正科、恩科凡27次,分别为乾隆元年、二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八年、六十年。,殿试策论中涉及经史论题达19次,未及者仅8次。这8次的内容大体如下:元年,宽严相济、为政执中之道(4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乾隆元年四月丙寅,《清实录》第 9册,第427~428页。;二年,任官举贤、君臣之道、开言路、劝农桑(4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2,乾隆二年五月戊子,《清实录》第9册,第 746~747页。;四年,赋税、物价、河工、吏治(4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丁丑,《清实录》第 10册,第 385~386页。;七年,君民之道、治道、君臣之道、徭役耗羡(4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庚寅,《清实录》第11册,第59~60页。;十七年,边防、吏治、农桑、科举抡才、学校校士(4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23,乾隆十七年九月癸未,《清实录》第14册,第538~539页。;四十五年,治统与道统、民风与吏治、仓储与民生、刑政(4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清实录》第22册,第802~803页。;四十六年,吏治、士风与朋党、刑政(4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子,《清实录》第23册,第90~91页。;六十年,田赋、刑律、海防、商贸、科举(5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77,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清实录》第27册,第729~730页。。
从时间看,乾隆帝在科举中始倡经史之学当为乾隆十年科举殿试策论,论曰:
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所素服习敬业者询之,必有以导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将欲得贤材,舍学校无别途,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多士宜有以奋发敷陈,启迪朕蔽。(5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清实录》第12册,第81~82页。
此类论题在其后的科举策论中亦多有出现。如乾隆二十六年试题曰:
夫学者载籍极博,必原本于六经,《易》有四尚,《诗》有六义,《书》有古今,《礼》有经曲,《春秋》有三传,能举其大义,详其条贯欤?注,一也,而有曰传,曰笺,曰学,曰集解之别。疏,一也,而有曰释,曰正义,曰兼义之殊。立博士者,或十四人,或十九人,先后何以不同?立石经者,或一字,或三字,纪载何以互异?多士亦能洞悉其源流而略陈其梗概否也?朕崇尚经术,时与儒臣讲明理道,犹复广厉学官,蕲得经明行修之士而登之,其何以克副期望之意欤?(5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35,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庚寅,《清实录》第17册,第90~91页。
又如乾隆三十一年策论:
六经之旨,千古范围,约举数端,以觇诵习。《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著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穷经致用,先务贯通,《彖传》《象辞》何以《乾》卦独立于爻下?二典三谟,何以左氏引以为《夏书》?《王风》《鲁颂》,编《诗》何以独异?《左传》《公》《谷》,经文何以互殊?以《礼记》为《曲礼》,易《周官》为《周礼》,始于何人何代,能确凿言之欤?史以垂彰瘅,而体例不必尽同,《循吏》《儒林》始于《史记》,《文苑》《独行》始于《后汉书》,《忠义》始于《晋书》,《道学》始于《宋史》,其分门各当否?《梁书》有《止足传》,《隋书》有《诚节传》,《唐书》有《卓行传》,同异果何如也?(5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清实录》第18册,第357页。
又如乾隆四十三策论:
前言往行,悉载于书。自周有柱下史,汉魏有石渠、东观,以至甲乙丙丁之部,《七略》《七录》之遗,代有藏书,孰轶孰传,孰优孰劣,可约略指数欤?乃者命儒臣辑《四库全书》,搜访校雠,亦云勤矣,而网罗犹有放失,鲁鱼犹有讹舛,何欤?(5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55,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辛亥,《清实录》第22册,第99页。
这些策题不仅是经学史、学术史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乾嘉考据学者津津乐道并皓首穷经所要着意解决的学术问题。由此,乾嘉经史考据学与乾隆朝科举之关系明白可见。
纵观乾隆朝科举殿试所出试题,皆是有为而发,均与乾隆朝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无论是边防、财赋、农桑、河工,还是吏治、文教,都是乾隆帝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边防、财赋等,文教似乎不那么紧要,而事实却非如此。乾隆帝如此积极提倡经史之学,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倡经史实学,以杜浮华,正士风、民风。明末清初,出于反思明亡之教训,一批遗民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塨、颜元等,或倡经世之学,或重躬行实践,一改晚明疏陋、浮华之习。但康熙中叶以来,政治上,清廷在全国的统治渐趋稳固;文教上,由于顾、黄等大师渐次凋零,清廷以八股制艺取士,因而时人多汲汲于科举帖括及辞章诗赋,学术又渐趋空疏。全祖望曾言:“国初多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为词章之学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55)全祖望:《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志铭》,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全氏所言正是对当时学坛状况的有感而发。乾嘉学者汪中论乾隆初期的学术情势亦言:“国初以来,学士陋有明之习,潜心大业,通于六艺者数家,故于儒学为盛。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56)汪中:《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并序》,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03页。此为康熙中后期至乾隆初期的学术之大体情势。乾隆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且试图力挽颓风。如乾隆十三年科举殿试,策题曰:“多士修之于家,宜有明治体,知治要,以期自见于当世者,而事词章而略经术,急进取而竞声华,论文体则尚浮辞而乖实义,于圣贤道德之实,未有能体之于心,修之于行事者,将教化之未明欤?抑积习之难返欤?其博思所以端风尚而正人心者,切言之无隐,朕将亲览焉。”(5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卯,《清实录》第13册,第138页。可知,乾隆帝对当时士人汲汲辞章之学,导致学问空疏浮华、言行不一的现象深为不满。在他看来,“经术”为端风尚、正人心的有效手段。如上述,乾隆举行“经学保举”,其原因之一即是为此,特别强调:“穷经为读书根本,但穷经不徒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汝等自己躬行实践,方能教人躬行实践。”(5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78页。二者用意实相同。此种认识在乾隆朝初期的科举策论中时有体现,如乾隆十九年策论题曰: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制义,即古者经疑经义之意也。文章本乎六经,解经即所以载道。《易》曰“修辞立其诚”,《书》曰“辞尚体要”,文之有体,不綦重欤?朕于场屋之文,屡谕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尚久矣,乃者或逞为汗漫之词,徒工绮丽,甚至以汉唐词赋阑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无当也。文之浮薄关于心术,王通论之详矣。今欲一本先民,别裁伪体,岂惟文治廓清,抑亦所以明经术而端士习也。……民俗之厚薄,视乎士风之淳漓,士习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荣进素定,干禄之学,圣人弗许,志一不立,而寡廉鲜耻,卑污之行随之,居家或不免武断之习,应试或尚怀干进之私,浮薄流传,竞相仿效,士习将何由而正乎?(5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清实录》第14册,第989~990页。
在乾隆帝看来,文以载道,六经是基础,文辞为其末,而当时科举士人多无实学,为文多汗漫绮丽,文风绮靡,而文风又是心术之体现,心术不正,士人一味汲汲于声名利禄,则鲜廉寡耻,往往身行有污,且士风不振还会造成民风浇离,此良关政教风俗。乾隆二十二年科举策论则更为明白:“士也者,四民之首,如表臬焉。表正则影正,斯其所系非浅尠也。朕屡降明诏,谆谆以勤励纯修、精研实学为务,乃今者读书敦品之士虽多,而标榜声华、追逐时好者尚未尽绝,其故何欤?夫心术不正,则聪明才智,适以助其诐淫邪遁之资,虽文彩可观,而本根已拔,曷足重乎?”(6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38,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庚子,《清实录》第15册,第800页。为了改变科举制艺中士人的空疏浮华之风,乾隆十九年,高宗特命方苞编订《四书文》作为时文范本,“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而杜竞尚新奇浮浅之士,达到正人心、端士习的目的(6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60,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清实录》第14册,第976~977页。。可见乾隆帝提倡经史实学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端士风、正民心之政教目的。
第二,经术事关治术,通经以致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以经术缘饰吏治,因此经学素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亦是如此。无论是顺治朝推行,后成定制的科举、经筵讲学,还是康熙朝提倡朱子学,开博学鸿词,其原因均在于统治者认为文教事关政教,于治国理政、保境安民效用匪浅。顺治帝曾言:“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62)《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清实录》第3册,第712页。康熙帝认为,“帝王道法,载在六经”,“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63)《御制日讲易经解义序》,《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清实录》第5册,第170页。,且屡屡强调“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64)《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三月乙亥,《清实录》第6册,第552页。,“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准收录”(6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庚申,《清实录》第5册,第336页。。雍正帝亦认为“六经皆治世之书”(66)《御制书经传说汇纂序》,王顼龄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第396页。。
乾隆与乃父乃祖的认识一样,认为“《五经》乃政教之原”(6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 ,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清实录》第 9册,第501页。,且对经学的提倡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在科举策论中体现尤为明显,如乾隆十年科举策论,乾隆帝开篇即曰:“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6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清实录》第12册,第81~82页。又乾隆十六年科举策论:“朕抚御鸿图,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嘉与海内臣民,懋登上理,深惟政治之易弛,风俗之易奢,士或荒于经术,备或懈于边陲,保泰持盈,其道曷以?……胶庠之士,乐化育而咏作人,经术昌明,无过今日,第考之于古,议大政、断大狱、决大疑,辄引经而折其衷,此穷经之实用也。今欲矫口耳之虚文,以致实用,其要安在?……凡此皆关于制治保邦之要,久安长治之道,莫切于此。”(6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88,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清实录》第14册,第97页。汉代经学与政治关联的表征之一就是经学史上常言的“《春秋》决狱”,因经术而影响治术。“通经致用”成为传统士人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经学史的一大传统。从此策论可知,乾隆帝显然受此观念影响甚深,认为经术在于实用,事关安邦保民。此类认识在之后历次的科举策论中时有论及,乾隆十三年科举策论曰:“朕惟制治在审其时宜,论治必征诸实用。《书》曰‘明试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绩’。士先资其言,必度可施之行事,为济时之良画,斯足以应天下之务,而国家收其实效。”(7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卯,《清实录》第13册,第137~138页。乾隆二十五年科举策论:“帝王心法治法之要,莫备于经。”(7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戊申,《清实录》第16册,第876页。乾隆三十一年科举策论:“惟经学为出政之原,史册为鉴观之本,察吏治以底绩,疏选法以程材,将以监古宜今,胥规实效。励官造士,共勉永图,兹当临轩发策,延揽维殷,伫献嘉言,以佐予休治。”(7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清实录》第18册,第357页。
对于史学,乾隆帝亦有同样的认识,其言曰:“夫史以示劝惩,昭法戒,上下数千年治乱安危之故,忠贤奸佞之实,是非得失,具可考见。居今而知古,鉴往以察来。”(7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清实录》第12册,第729页。凡此种种,皆见乾隆帝推重经史之学的用意所在。
第三,标榜稽古右文之治。乾隆帝为政处处效法其祖康熙帝,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明君圣主形象,其中表彰经史之学,展现稽古右文之治,为其重要手段。乾隆四年,高宗采纳张廷玉等人建议,刊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乾隆十二年刻成,乾隆帝分作《御制重刻十三经序》《御制重刻二十一史序》,明示自己效法康熙帝,表彰经学,示稽古右文之治(7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清实录》第 12册,第728~729页。。乾隆六年,高宗效法汉代石渠、天禄故事,命各省督抚、学政搜求遗书,不拘刻本、抄本,以广内府之藏,以示“从古右文之治”(7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4,乾隆六年正月庚午,《清实录》第10册,第941页。。如前所述,乾隆帝早年提倡经史之学是为了纠正浇离的士风民风,为治国理政选拔德才兼优的实学人才,至乾隆朝中后期,其稽古右文的心态则愈发浓厚。乾隆三十七年,高宗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示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7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00,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清实录》第20册,第4页。。乾隆三十八年采朱筠之建议,诏开四库馆,访求遗书,以明文治光昭,嘉惠艺林(7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34,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己未,《清实录》第20册,第567~568页。。乾隆四十七年又命续缮《四库全书》三份,分庋文汇、文宗、文澜三阁,示其“稽古右文,究心典籍”之意,从而达到“嘉惠艺林,垂示万世”(7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0,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甲辰,《清实录》第23册,第538页。的文治目的。乾隆三十九年,高宗敕建文渊阁贮藏四库书,亲撰《御制文渊阁记》曰:“国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而礼乐之兴,必借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68,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乙未,《清实录》第20册,第1211页。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搜罗遗逸。琅嬛异笈,宛委珍函,莫不乘时毕集。图书之富,旷古所无。”(8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5《经义考》,上册,第732页。此种心态在科举策论中亦有所体现,如乾隆四十年科举策论:“朕表章经籍,用光文治,搜罗遗典,咸集石渠。特简儒臣,俾司编纂,亦既具有条理矣。顾四库之藏,浩如渊海,必权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请罢黜百家,专崇孔氏。陶弘景则一事不知,引为深耻。今将广收博采,而传注时多曲说,稗官不免诬词,异学混儒墨之谈,伪体滥齐梁之艳,于人心世教未见有裨。如但墨守经师,胥钞语录,刊除新异,屏斥雕华,则九流之派未疏,《七略》之名不备,抱残守匮,亦难语该通。至于忠臣孝子,或拙文辞,宵小佥壬,间工著述,文行相左,彰瘅安从?他如《略》《艺》编摩以后,晁、陈著录以前,门目各殊,规条歧出,此增彼损,甲合乙分,不有折衷,孰为善例?”(8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81,乾隆四十年四月戊戌,《清实录》第21册,第96~97页。
经过数十年的提倡之后,一大批通经博史之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逐渐成为学坛名宿,不仅直接促进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同时也为乾隆帝的稽古右文之治提供了人才保障,乾隆朝三礼馆、通志馆以及后期纂修《四库全书》等等皆与此密不可分。
三、乾隆朝科举中的考据学者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康熙中叶以来,清廷出于治术的需要,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与元、明一样,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功令的钦定教材,一时朝堂之上,理学之士如熊赐履、陆陇其、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皆因朱子学而登高位。如《清史列传·儒林传》未循《宋史》别儒林、道学为二传之例,而是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道学家为主,或宗程朱,或尊陆王;下卷为经学家,多录以经史考据见长者。下卷所载经学诸家,乾隆以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明末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钱澄之、张尔岐、朱鹤龄等人,这批学者不少在明时已有功名,其中个别学者如毛奇龄等,本为诸生,后以康熙朝博学鸿词入仕,这批学者大多功名不高;一类是清人(入清后出生者),其中取得科甲高第者也为少数,仅有惠周惕、惠士奇父子和顾陈垿等寥寥数人而已。
至乾隆朝,经乾隆帝的大力提倡,一批学者通过科举仕途而跻身翰林,因此在生活上可以无忧,进而从容地悠游圣域,研经探史。他们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就《清史列传》之“儒林传”所载来看,乾隆朝屡有以科甲高第进升通显者,而至乾隆十七、十九年两次科举达致高峰。乾嘉考据学的代表学者纪昀为其同年李封撰写墓志曾言:“公与余同以乾隆甲戌登进士,是科最号得人。其间老师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学,以词章名世者不一;经济宏通、才猷隽异,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酒斗茶、留连倡和,以风流相尚者亦不一。故交游款洽,来往无夙期,宴会无虚日。”(82)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16《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459页。纪氏所言之“甲戌”科即乾隆十九年会试。在此之前,乾隆十七年的进士中亦有不少学者以考据名家。此两科中式者中,纪昀、朱筠、翁方纲、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更是乾嘉时期学坛领袖人物。卢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屡掌文衡,常以经术导士(8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93页。。翁方纲,乾隆十七年进士,常典试、督学地方,“与同里朱珪、献县纪昀,俱以宏讲风流为己任”(84)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95页。。王鸣盛,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以经术文章发海内者数十年,大江南北承学之士知究心经术者,实奉先生与竹汀少詹为归焉”(85)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揅经室集》上册,邓经元点校,第545页。。王昶,乾隆十九年进士,推崇汉学,博通四部,“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经请业,舟车错互,屦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且屡典乡会试,“皆以经术取士,士之出门下为小门生及从游受业者二千余人”(86)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揅经室集》上册,邓经元点校,第423~424页。。钱大昕,乾隆十九年进士,主讲钟山、娄东、紫阳诸书院,以训迪后进终身。其中尤以朱筠最为典型。朱筠,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福建乡试正考官,安徽、福建学政,“博闻宏览,以经学六书倡,谓经学本于文字训诂……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奖掖后进,惟恐不至”(8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497页。,当时绩学之士莫不与之游,“凡春秋两闱,校士恒以对策为主,尝言‘以此观士所学之浅深,若持权衡以测轻重’云”(88)李威:《从游记》,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第114页。。
对此,钱穆曾言:“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8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页。“主张于庙堂”即指统治者之提倡,“鼓吹于鸿博”则指朱彝尊、毛奇龄、杭世骏、齐召南等以博学鸿词进升者,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则当指乾隆十七年、十九年以科举而入翰林的钱大昕、朱筠等人。钱氏已然认识到了康、乾学术与清廷抡才政策之关系,然并未深论。嘉道时期学者方东树亦言:“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其著书专门名家者,自诸经外,历算、天文、音韵、小学、舆地、考史,抉摘精微,折衷明当。如昆山、四明、太原、宣城、秀水、德清,根柢学问,醇正典雅,言论风采,深厚和平,夐矣,尚矣。虽汉、唐名儒,不过于斯矣。及乎惠氏、戴氏之学出,以汉儒为门户,诋宋儒为空疏。一时在上位者,若朱笥河先生及文正公昆弟、纪尚书、邵学士、钱宫詹、王光禄,及兰泉侍郎、卢抱经学士十数辈承之而起,于是风气又一变矣。”(90)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6《复罗月川太守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348~349页。方氏出于汉宋门户之见,批评考据学不遗余力,然所谓旁观者清,对乾嘉考据学兴起的认识可谓洞见。其“在上位者”正如上文所指的这批乾隆十七年、十九年出身的以经史考证名世的学者,他们倡导经史考证之风,以奖掖后学、振兴文教为己任,使得乾嘉考据学得以在士林中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一代学风。清末学者陈澧曾有诗云:“国朝经史学,彬彬称极盛。风气最精博,乾隆与嘉庆。贤相为提倡,文达与文正。近者卅余年,儒风乃不竞。不复讲经史,但以小楷胜。人才骤衰颓,天下自此病。何人坏风气?后世有论定。”(91)陈澧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陈东塾先生遗诗·读书八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0~571页。陈氏亦认识到了乾嘉考据学风与当时“上位者”提倡的关系,其中“文达”与“文正”正是指纪昀与朱筠。而乾嘉名儒戴震、汪中二人的学术经历最能说明问题。
戴震号称清代考据第一人,早岁虽在南方学界颇有令名,但并不为北方学术文化中心的京师学者所知。乾隆二十年,戴初入京师,客于旅社,时人皆视之为狂生,其生活更是朝不顾夕,颇为困顿。机缘巧合下,戴氏获交已在京师享有大名的钱大昕。当时尚书秦蕙田著《五礼通考》,求善推步之学者。戴氏早年随江永问学,江氏长于算术、地理等推步之学,戴氏得其真传,钱于是向秦荐戴,后尚书王安国亦延请戴氏课其子王念孙。获识这批在朝的翰林学士纪昀、朱筠、钱大昕、卢文弨、王鸣盛等南北学界翘楚之后,戴震个人乃至其师江永的盛名才在南北学界传播开来,“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戴先生震传》,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630~631页。,戴震也因而能够在人才林立的京师站住脚跟(93)洪榜:《戴先生行状》,《初堂遗稿》不分卷,《清代诗文集汇编》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3~99页。。
戴震曾言:“余窃谓授经一事,一二人启其端,必同时英彦笃守之以广其传,夫然后师友之气振,而其学久而弥著。”(94)戴震:《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8页。乾嘉学者凌廷堪亦言:“今夫天地之气,一盛一衰,学术之变迁亦若斯而已矣。故当其盛也,一二豪杰起而振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34页)戴氏此言用以说明以他自己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亦若合符节。其中的“同时英彦”可指朱筠、钱大昕、纪昀、戴震诸人,这批学者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奖掖后进,引领风气,使得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而“师友”可为段玉裁、王念孙等戴氏门徒,使考据学逐渐走向精深,达至顶峰。
汪中的学术成长及声名传播与乾隆十七年、十九年这批翰苑词臣密切相关。孙星衍曾述汪中学行:“朱学士筠督学安徽,中往就之。……翁阁学方纲、朱侍郎珪先后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试。乾隆丁酉岁,谢侍郎墉来督学,选拔贡生,中不应朝考,亦不就试,益以经义自娱。当是时,四库馆开,海内异人异书并出,经学、小学、算学、词章、金石之学卓然以撰述自见者有钱少詹大昕、王光禄鸣盛、卢学士文弨、孙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孙、段大令玉裁、戴编修震、王副宪昶、蒋编修士铨、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于诸君为后进,皆辩难无所让。”(95)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五松园文稿》卷1《汪中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第489页。在汪中的学术交游中,谢墉、朱筠最为关键。谢墉,字昆城,乾隆十七年进士,平生究心实学,经史百家,靡不综览,尤以经史、小学为本。谢氏久掌文衡,多次典试、督学江南,又曾任《四库全书》总阅官,“论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经义策问,尤急甄拔”,阮元、孙星衍、焦循等皆出其门,“江、淮南北怀经握椠者,靡不服公之学”(96)阮元:《吏部左侍郎谢公墓志铭》,《揅经室集》上册,邓经元点校,第427页。。乾隆四十二年,谢墉提学江苏,颇重汪中才学,拔贡之时,欲将其拔诸头名,曾言:“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学,当北面事之矣。”(9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下一》,第17册,第5537页。此时,谢墉早已是学坛、政坛名宿,却愿以弟子礼事汪中,可见其奖掖后进的谦逊之风。汪中以一介布衣,与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袁枚、王昶、戴震等一批翰林学者究学辩难,此对其学术成长及声名的传播效用匪浅。
在乾隆朝,除以上所举之外,身有科举功名而擅长经史考据者还有不少。漆永祥对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200名考据学者的科举功名进行了统计,身有功名者凡142人,在乾隆一朝,荣登进士鼎甲的考据学者14人,进士者46人,诸生20人,特科6人,总计86人,占比超60%,不仅远超过康熙、雍正两朝(98)这些学者有不少历经康雍乾三朝,其功名在康熙、雍正朝取得。如惠士奇,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为乾嘉考据学派的先驱。,亦超过其后的嘉庆朝。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学与乾隆朝科举、特科之关系(99)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第十一章,第297~332页。。
四、结 语
科举制自隋代创建以来,至清代已经沿用一千余年,虽说弊端明显,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和较为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故而仍以之为抡才的首选。至乾隆时期,清初的满汉隔阂逐渐消弭,社会也相对安定。在科举时代,科举无疑是儒家士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最有效途径,也是改善自身阶层与处境的一种有效方式,乾嘉考据学者亦不例外(100)此从钱大昕与其父钱桂发的科举经历可见一斑。钱桂发一生汲汲于科举,年近四十始补学官弟子,但乡试屡踬,至其子钱大昕因高宗南巡献赋,后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桂发才绝意仕进,以诗酒自娱。由此可见举业对于一般士人家庭的重要性。参见钱大昕《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先考小山府君行述》,《潜研堂文集》,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第764页、768页。。其中虽有不少是自幼爱好经史、追求学术真理的学者,即“为学术而学术”者,但金榜题名、学以致用仍是大多数士人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治经之暇,便习时文;考古之余,兼求制艺”(101)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第195页。。陈寅恪论清代经学与史学之发展情势时,一方面承认清代的文字狱使得时人埋首考据,一方面又认为“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102)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就乾隆朝制科、科举与考据学兴起的关系看,陈先生之论可谓颇中肯綮。乾隆朝,清廷在以博学鸿词及经学保举等特科、科举等抡才时,以“经史实学”“根柢之学”鼓动学风,因而一批优异的学者得以通过科举仕途而成名。他们入仕后,或入翰林,或督学一方,互相切磋琢磨,共同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他们成功的经验在当时及后世亦有很大的榜样作用,乾、嘉两朝,擅长经史考据之学并且进士出身的学者均为清代之最,与此密不可分。他们当中有不少还久任疆臣,如阮元、毕沅、谢启昆等既是学者又久居封疆,提倡经史考据,网罗人才不遗余力,使得乾嘉考据之风流衍于全国各地(103)对此,可参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因此,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恐怕有待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