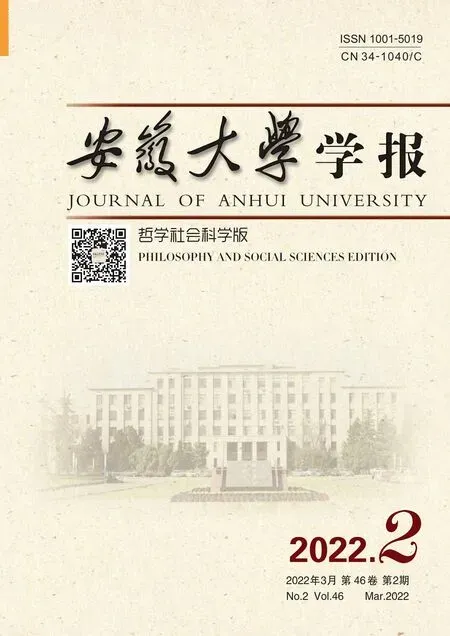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
张知强
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翻检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官职显赫者颇多,如陈用光曾任福建、浙江学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等。在直接帮助之外,他们还会通过幕府的形式,为桐城派成员提供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如陈用光、姚莹、曾国藩一直到民国的徐世昌,都曾开设幕府。邓廷桢幕府也是其中的代表(1)关于邓廷桢幕府,王达敏有简略而精当的论述。此外,王达敏对桐城派发展与政治的关系,亦有梳理。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17~227页。。
游幕是桐城派成员的主要谋生途径之一。从早期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到晚期的范当世、马其昶、吴闿生,许多桐城派成员都曾入幕府。根据张秀玉的统计,桐城派至少有76人有游幕的经历(2)张秀玉:《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4、86~88页。。这种经历对成员的生活、文学创作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加快了桐城派向全国各地的传衍。
一、“后姚鼐时代”的邓廷桢幕府
邓廷桢(1775—1846),字维周,又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历官安徽巡抚、两广总督等,有《双砚斋诗钞》《双砚斋词钞》等传世。据《邓尚书年谱》记载,道光六年到十五年邓廷桢任职安徽巡抚时,“公幕中人才甚盛,如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异之、汪钧平甫、马沅湘帆、桐城方东树植之、阳湖陆继辂祁孙、长洲宋翔凤于庭,皆其卓卓者也”(3)邓邦:《邓尚书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此外,通过梳理各种材料,可知邓廷桢幕府成员还有吴梦笔、李元祺、罗凤藻、张虎儿等。诸人均为有名的学者、文人,可以想见当时群贤毕至的情况。幕府成员中,管同、梅曾亮、马沅、汪钧、罗凤藻、张虎儿为江苏上元人,陆继辂、宋翔凤与邓廷桢均于嘉庆五年江南乡试中举,方东树、管同、梅曾亮与邓廷桢均曾问学于姚鼐,李元祺与邓廷桢为亲属(4)李元祺:《佩文广韵汇编》,道光十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可知,邓廷桢的幕府成员主要是其同乡、同年、同门、姻亲。陈寅恪云:“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963页。各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构成邓廷桢的社交网络,也是其幕府成员的主要来源。
邓廷桢连续担任安徽巡抚达十年之久,客观上有较为安定的环境;加之政务熟悉,幕友众多,因此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切磋。正如梅曾亮《青嶰堂诗集序》所云:“每辰巳时见属吏,议事毕会食八箴堂。时管异之、马湘帆、汪平甫俱在坐,方植之亦时来,和章联句、诙调间作。”(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安徽巡抚幕府诸人的入幕时间,主要集中在道光六年到十一年,陆继辂、管同、梅曾亮、方东树、马沅、汪钧等人在幕中。宋翔凤于道光十四年、十五年入幕(7)李南《宋翔凤年谱》道光十四年、十五年条,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0~144页。,诸人或已去世、或已离开,并未形成交集。
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规模虽然并不大,也并非当时桐城派成员聚集的唯一幕府,但在时间、地点、人员构成等方面有其独特性。
其一,时间上的独特性。从桐城派传衍的时间脉络上看,在嘉庆二十年姚鼐去世之后、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前,中间有一个“低谷”时期。虽然“姚门四杰”等弟子仍在努力弘扬师说,在京师、江南等地传播古文,但桐城派缺少标志性的人物。章廷华云:“道咸间,桐城派之说盛行,而实为其学者甚少。”(8)章廷华:《论文琐言》,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10页。说明当时桐城派处境之艰难,而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正好处于这个时期。
在姚鼐去世之后,桐城派的发展模式由“中心式”向“分散式”变化,围绕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梅曾亮形成了四个传播中心(9)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17页。。具体来看,这四个传播中心形成的时间各有先后。
在姚门弟子中,陈用光在京师传播桐城派的时间最早,也最久。“从嘉庆二十年姚鼐卒于江宁书院到道光十二年梅曾亮京师传授古文之前,这一时期桐城古文在京师的传播主要是陈用光的推动”,若从幕府的角度来看,陈用光在“道光八年至道光十一年、道光十三年至十五年分别任福建、浙江学政”(10)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0页、21页。,虽取得不少成绩,但时间、地点相对分散,持续时间不长。姚莹幕府的持续时间较长,“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这是他传扬桐城派的一个重要时期”(11)汪孔丰:《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时间虽然长达六年之久,但稍晚一些。梅曾亮形成影响的时间也相对较晚,至少在道光十八年之前,还未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古文圈子(12)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第103页。。而邓廷桢从道光六年到十五年一直担任安徽巡抚,在桐城派成员主持的幕府中,属于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稳定的状态有助于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围绕幕府,能够聚集一批志趣相投的成员,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学、学术群体。群体对于桐城派的传衍而言有特殊意义。从早期姚鼐执教钟山书院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到之后梅曾亮在京师形成的古文群体,再到围绕曾国藩形成的湘乡派群体,以吴汝纶、张裕钊为核心的莲池书院群体,以徐世昌为核心的幕府群体,无不对桐城派的传衍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群体在时间上是接续的,没有发生断裂。邓廷桢幕府在客观上起到接续钟山书院群体与梅曾亮京师古文群体的作用。
其二,地域上的独特性。“后姚鼐时代”的四大传播中心,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京师(陈用光、梅曾亮)、安徽(邓廷桢)、江苏(姚莹)、福建与浙江(陈用光),均为当时文学、学术兴盛的地区。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位于桐城派的发源地——安庆,是桐城派的大本营。
桐城派虽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流派,但不能忽略其发源地的意义。“桐城三祖”之外,姚范、方东树、姚莹、刘开、戴钧衡等桐城籍文士在桐城派的传衍脉络中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徐雁平认为:“欲探寻这一文学流派延续及拓展的机制,有必要回到‘较长时间’(近似‘中时段’)并落实到具体空间来考察,也就是说研究桐城派要回到桐城本土。”(13)徐雁平:《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桐城模式——基于萧穆咸同时期日记的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因此,重视桐城派在桐城乃至安庆、安徽的发展情况,有助于加深对桐城派的理解。
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重视与当地人士的互动。其对桐城派在安庆传衍所做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书院教育中融入桐城派因素、刊刻桐城派成员著作两个方面。
邓廷桢重视书院教育。道光九年,邓廷桢《覆试书院生徒,文艺多可采览,欣然有作》云:“今岁都官作都讲,直从低首共诸君。”(14)邓廷桢:《双砚斋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2页。亲自给生员命题考课。敬敷书院是安庆有名的书院,邓廷桢自然非常留意。“安庆敬敷书院为人士荟萃之区,公尤留意培植。试之日,集诸生于院署,手评其文而面教之。”(15)邓邦:《邓尚书年谱》,第147页。亲自评点生员的文章。此外,邓廷桢还曾刊刻《敬敷书院课艺》。管同《刊刻敬敷书院课艺序》云:“世言我朝古文桐城有三家,怀宁则诗人辈出。”(16)管同:《刊刻敬敷书院课艺序》,《管同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在书院课艺中提及地域文学传统,尝试将桐城派古文与敬敷书院教育进行结合。
敬敷书院与桐城派成员联系密切。刘大櫆曾在此讲学,姚鼐于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嘉庆六年至九年先后两次担任敬敷书院的山长,共十二年。乾隆四十五年,姚鼐编选《四书文选》,“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17)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7册,第599页。。姚莹在敬敷书院跟随姚鼐读书,“惜抱先生主讲敬敷书院,府君岁试,居院中,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18)姚炂昌:《姚石甫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528页。。在教授应试之文外,“学问文章之事”也是姚鼐所重视的内容。可见桐城派对安庆当地文教之重视。因此,管同的序文不仅有当下的关怀,也与桐城派的统系、敬敷书院的历史相呼应。
道光十五年,宋翔凤《举乡贤,励风纪也》云:“公抚江淮阅几秋,关心旧德肆旁搜。桐城已推姚比部,宿松更及朱编修。文章道义俱无匹,俎豆千秋名称实。”(19)宋翔凤:《洞箫楼诗纪》,《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3册,第208页。专门指出邓廷桢对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章、道义的推崇。管同、宋翔凤关于书院、乡贤的诗文中都出现“桐城”的字样,不仅与安徽巡抚驻地安庆有关,还指明桐城派诸人扩散桐城派主张的意图。流派的发展,离不开成员的用心经营和有意识地传播。
弘扬乡贤之外,邓廷桢还刊刻当地学者或桐城派成员的书籍。管同去世之后,其作品《因寄轩文集》《七经纪闻》均由邓廷桢刊刻。邓廷桢幕府刊刻桐城派相关书籍,大多有方东树的参与,如刊刻方东树父亲方绩的《屈子正音》《鹤鸣集》。此外,邓廷桢还与幕府外其他桐城派成员商议刊刻姚鼐的著作。陈用光《同日得筠潭、嶰云、介航、晴峰书,喜成一律》云:“盼将师说锓遗编。”并有注解:“余昨寄嶰筠札,属其重订姚师所选经义。”(20)陈用光:《太乙舟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439页。《惜抱轩尺牍》中,姚鼐多次与陈用光商议其著作的刊行事宜,邓廷桢也曾参与其中,但少有人提及。作为姚鼐直系弟子中少有的高级官员,陈用光、邓廷桢在弘扬师说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其三,幕府成员的独特性。邓廷桢幕府中,“姚门四杰”中的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均曾入幕。邓廷桢幕府不仅为桐城派诸人提供了一个聚集、交流的安定环境,而且为梅曾亮、方东树后来的发展,为桐城派在全国的扩散积蓄了实力(21)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2页。。
在姚门四弟子中,历来关注点多在方东树、梅曾亮身上,管同和刘开因为早逝,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对两人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管同为例。从道光六年开始,至十一年去世,管同在邓廷桢幕府中连续停留了六年,时间最长,深受邓廷桢的器重。管同在幕府内主要从事教育邓廷桢之子、为邓廷桢代笔、与诸人诗酒唱和等活动。诗酒唱和虽为幕府生活之常态,但关注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的唱和,可以辑录管同的诗歌,加深对管同诗歌创作、文学风格的认识。
桐城派虽以文章出名,但包括刘大櫆、姚鼐、管同、梅曾亮在内的许多成员都会作诗,因此有“桐城诗派”的说法。关于管同的诗歌创作,时人多有评论。首先,姚鼐十分推崇管同的诗歌,《与管异之》云:“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俊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古文若更欲学,试更读韩、欧,然将来成就,终不逮诗。”(22)姚鼐:《与管异之》(前月得寄书并诗文),见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7页。认为管同的诗歌成就在自己之上;就当时管同的诗歌、古文创作而言,姚鼐认为文不如诗。不仅如此,姚鼐还多次对门下弟子谈及管同的诗歌。《与陈硕士书》云:“此间作古文有荆溪吴仲伦,作诗有江宁管同。”(23)姚鼐:《与陈硕士书》(所寄来诗文),见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54页。鲍桂星《得姬传先生书因寄管异之》:“来书云:近求得武进黄仲则诗读之,固亦有才,然未为绝出。若管生,异日所就,当或过之。”(24)鲍桂星:《觉生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6册,第433页。管同的诗名在姚门内部得到广泛认可。
其次,在长辈的推许之外,同辈中也有认可管同者。如方东树云:“其诗缔情隶事,创意造言,得坡、谷朗峻,爽气鲜意,近世诗家亦罕有到此者。”(25)方东树:《七经纪闻序》,《考盘集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187页。可知其诗歌风格,偏向宋诗。管同去世后,方东树有诗怀念,云:“百身难赎秦淮海,并世谁齐杜审言。可但生传万人敌,夜台犹压众诗魂。”(26)方东树:《即事有怀亡友管异之》(其二),《仪卫轩遗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86页。提及管同的诗歌成就,并对管同的早逝感到惋惜。
可知,在管同生前,其文学创作的名声由诗歌和古文共同支撑。但在管同去世后,仅有文集行世,诗名反而不彰。留存的资料对文人的评价有很大的“干扰”作用,管同的“文名”由此被建构起来。因此,有必要对管同的诗歌展开辑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管同的文学风貌。
管同的诗文集,除《因寄轩文集》《二集》外,《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管同有诗集二卷(27)《同治上江两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27页。,《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亦同(28)蒋启勋、赵佑宸修,汪士铎等纂:《同治续纂江宁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册,第79页。,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管同”条著录有《因寄轩诗集》(29)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3册,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511页。,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有《因寄轩诗集》二卷(30)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徐天祥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版,第151页。。但目前尚未查阅到管同诗集的馆藏信息,盖已亡佚。马沅刊刻的《八箴堂诗课》收录道光六年至道光九年之间邓廷桢幕府的部分唱和诗歌(31)马沅:《八箴堂诗课》,道光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其中保存有25首管同的佚诗。此外,检索邓廷桢《双砚斋诗钞》、方东树《半字集》和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中的唱和之作,可以找到8首管同的诗歌、1首联句。至此,通过唱和诗,可以辑录出33首管同诗歌、1首联句。这些幸存的唱和诗均创作于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时期,属于管同的晚期之作,弥足珍贵。对管同诗歌创作的部分还原,也可以丰富对桐城诗派的研究。
二、幕府中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与论争
尚小明认为,学人幕府与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幕府所具有的开放和流动特性使它成为学人荟萃之地,从而为学者们创造了许多交流学术的机会,使游幕成为清代学人在函札往来之外的又一条重要的学术交流途径,同时也使幕府具有了传播学术文化的功能。”(32)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416页。正如方东树描述幕府诸人论文的情形:“开府匡时切,论文暇日亲。”(33)方东树:《嶰筠中丞以〈双研斋诗集〉命为作序,因题其卷》,《半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28页。邓廷桢幕府首要的贡献,是为桐城派诸人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切磋的环境。幕府诸人既有诗酒唱和,也有文章创作方面的切磋、学术方面的交流。
幕府诸人在闲暇时经常举行集会,诗酒唱和。主要集会地点便是抱甕园与八箴堂。管同记录集会的盛况云:“分请诸君,各输素艺。或文腾藻丽;或诗耀葩采;或师小令于温、韦;或仿八分于李、蔡;或虫书玉篆,抚炎汉太学之文;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34)管同:《五月五日八箴堂小集序》,《管同集》,第152页。集会的方式不仅限于诗歌,还有文章、词、书法、绘画等。马沅《八箴堂诗课》的刊刻,就是幕府文学活动的产物。诗酒唱和中,免不了竞争、逞才的发生,而管同的身影尤其活跃。《八箴堂诗课》收录的十六次唱和中,有九次唱和为管同写第一首,引领唱和。有九次是管同与他人、或自己的同题共作,如第十一次唱和时,梅曾亮与管同均有《栗趺》诗;第十五次唱和时,管同创作了两首《屏》。在八次唱和中,管同分别创作有两首或两首以上的诗,如第六次唱和时,管同有《限韵》《包韵》两首诗;第十六次唱和时,管同有《国公酒》《太师饼》《宋嫂鱼》三首诗。可见管同诗思之敏捷。
诗酒唱和是幕府的常态,但文章代笔的同题共作、文章观念的论争对桐城派有独特的意义。
作为幕僚,职责之一便是为幕主代笔。管同和方东树均曾为邓廷桢代笔,代作中存在同题共作的情况。方绩《屈子正音》有方东树《刻屈子正音序》、管同《屈子正音序》两篇序言,均为代邓廷桢而作。邓廷桢最终采用方东树的序文。这两篇文章相似之处颇多,可以推测,或者两人一起写作,或者相同部分是邓廷桢的主张,二人在此基础上敷衍成文。进而可以思考代笔的机制:幕主不一定只让一个人代写,有时也会让多人同时创作,最后选用其中一篇。如此,对于代笔之人,便有同题共作的竞赛意味。
方东树为邓廷桢代笔的作品中包括《许氏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序》《七经纪闻序》,同时,方东树又以自己的名义再作两篇序文。方东树的两篇《七经纪闻序》,考虑到“主体”身份不同,序文内容也有不同之处。代作对管同颇有揄扬之意。方东树自作文的风格便有不同,云:“虽然,是书也,吾友在日,数以相视,固尝共商榷矣。当时论说未尽,今复审之,凡其所质疑于朱子者,于吾意多有未喻,故既为之釐定部帙,勘正脱误,间附鄙说其下,以折衷之。”颇有与管同讨论学问的意味。“人之学与年俱进……安知吾友若在,不自改其初说?奈何执其误以遂其非也?”(35)方东树:《七经纪闻序》,第187页。表达了对管同部分观点的不认可,以及对自己观点的坚持。这种“异见”,显然不可能在代作中表露出来。而方东树与管同的争论,已成为一种常态。以至于管同去世之后,方东树仍会在梦中与管同论学:
文章一小道,于学非本务。所恨知者少,遂觉涩难遇。哲匠不比肩,扬马君齐步。君笑我何必,求足此名数。闻言惊欲请,展转忽已寐。(36)方东树:《梦异之》,《考盘集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44页。
二人在文章创作中的竞赛、在学术观点中的论争,表明桐城派并非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更为复杂的机制。内部成员的互相交流、切磋,在坚持流派核心理论的同时,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也有利于流派长久地保持活力、创造力。
关于文学创作,管同和梅曾亮一直有交流。桐城派重视古文,对骈文较为轻视。梅曾亮少时颇好骈文,管同曾多次进行规劝。道光六年,管同与汪钧同在邓廷桢幕府,作《赠汪平甫序》,论及骈文与古文之优劣:“科举之文,凡物之形也;骈丽之文,佳物之形也;司马迁、韩愈之文,异物、尤物之形也。虽然,皆形而已矣,以言情,则未也。”从“形”的角度看,古文明显优于骈文。但文章终究仍是属于“物”的层面,没有达到“情”的高度。在文章的末尾,管同写道:“书以赠平甫,并寄伯言,以为与君之言变者孰拙而孰工也。”(37)管同:《赠汪平甫序》,管同:《管同集》,第121~122页。有与梅曾亮论争的色彩。事实上,两人关于此话题的争论,在钟山书院时就已经开始。管同去世之后,邓廷桢刊刻《因寄轩文集》,梅曾亮参与文集的编次,并有《管异之文集书后》一文。在文中,梅曾亮详细记录与管同讨论骈文之事:
曾亮少好为骈体文,异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固不快耶?而贱之也?”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词,不足以尽其一意。”余遂稍学为古文词。(3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109页。
记录二人激烈讨论的场景。梅曾亮推崇骈文,受到管同的批评。管同并非一味否定骈文的长处,承认其文辞之华美,但形式的华美会影响到内容的表达,因此有很大的缺陷。辩论的结果,是梅曾亮转变对骈文的态度,开始学习古文。梅曾亮在同年所作的《马韦伯骈体文叙》中,也记录有二人争论的场面,但气氛比较缓和:
昔会课钟山书院中,每论文,讼议纷然,忘所事事。异之色独庄,盛言古文。余曰:“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异之不复难,曰:“君行自悟之。”时韦伯在坐,亦右余言。(39)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110页。
梅曾亮认为,文体并非决定性因素,只要有利于表情达意,选择骈文或者散文均可,并无高下之分。或许是因为马沅也支持梅曾亮的缘故,管同的回应只是“君行自悟之”,辩论的兴致不大。
梅曾亮非常看重与管同的讨论:“今异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为吾言之。异之亡,余虽于学日从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忧而可喜也,故益念异之不能忘也。”(40)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109页。二人的论争,既可以看出桐城派内部对于骈文看法的复杂性,并非只是一味打压,也有认同骈文者;亦可以说明桐城派成员有引导他人创作古文的自觉性。记载管同和梅曾亮辩论的文本所发生的场域、涉及的对象,如管同与汪钧的相会、《因寄轩文集》的刊刻,都与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有直接的关联。幕府为桐城派内部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融会提供了可能性。
管同与梅曾亮围绕骈散进行的讨论,对梅曾亮和桐城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梅曾亮虽然并未完全放弃骈文的创作,其文集中仍有骈体文二卷,但他接受管同的劝告,开始学习古文。如此,梅曾亮在行文时便有融合骈散的可能。如作于道光八年的《吴松口验功记》,吸收汉魏六朝的辞采,突破桐城派文风过于简淡的弊病(41)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127页。。其次,对桐城派文论而言,梅曾亮的融合骈散,是对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桐城派先驱忽视骈文的一种修正。事实上,这种改变始于姚鼐,他在《古文辞类篹》中加入辞赋,以增加文章的华彩。梅曾亮继承姚鼐的观念,并将骈散结合的理论应用于创作实践(42)吕双伟:《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桐城派文学理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保持活力。
文学之外,还有学术方面的交流。方东树之父方绩著有《屈子正音》一书。道光七年,邓廷桢组织方东树、管同校勘、刊刻此书。《屈子正音序》云:“先生此书作于乾隆壬寅,其时顾氏书虽行,而江氏、戴氏之书犹未盛出,段氏、孔氏抑又后矣,故其分部、审音,如鱼侯、萧尤之类,不能无小失。”(43)邓廷桢:《屈子正音序》,见方绩《屈子正音》,《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第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指出方绩的不足。注文中有“今按”“东树按”“同按”等,乃邓廷桢、方东树、管同之补充、商榷文字,且三人关注点各有不同。方绩指出《广韵》韵字收录有误,对音韵学感兴趣的邓廷桢于此多有商榷,如: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诗·清人》首章、《有女同车》二章、《著》三章、《沮洳》二章并同。《韵补》收入“十阳”。《广韵》入“十二庚”,误。今按,《广韵》:“庚,古行切。”以“英”入“庚”,不误。(44)方绩:《屈子正音》,第118页。
邓廷桢对方绩此类观点的讨论,《屈子正音》中共有16次,主要在《离骚》中。邓廷桢并非一味袒护《广韵》,也会指出其不足之处。如《广韵》韵字收录之误,针对“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中“辅”的韵部,邓廷桢云:“辅,《诗声类》以为当入‘姥’。《广韵》入‘九麌’,误。古音语、姥同部,麌、厚同部。”再如《广韵》部首用字之误,针对“虽信美而无礼兮,来委弃而改求”中“求”的韵部,方绩认为《广韵》入“尤”有误,当为“游”韵,邓廷桢则依据古音做出判断,认为“《广韵》以‘游’‘求’等字入‘十八尤’,不误。但‘尤’字古音隶‘之’部,不当以为‘游’‘求’等字部首耳”。“尤”字之外,邓廷桢还分别指出“宥”“有”等字亦不适合作为部首(45)方绩:《屈子正音》,第120页、121页、130页、137页。。
相对而言,方东树、管同的注文较少。在字形、字音方面,方东树对方绩的观点有所商榷。同时,对汉学家过分依赖《说文》也有批评:“古字虽多,由改隶而亡。然近世尊《说文》者必执《说文》所无即非字,亦过矣。《说文》实有脱阙不全也。”(46)方绩:《屈子正音》,第136页。管同主要负责不同版本的对校工作,并不涉及音韵的讨论。可见诸人兴趣点、分工之不同。诸人的注文与原文进行互动,形成一个对话的“场域”。诸人共同参与《屈子正音》的校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汇聚各方意见,形成新的文本;群体之间的互动,也在客观上形成一部融会桐城派学术观点的文本,体现桐城派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具有的凝聚力。
尼克·克罗斯利在《走向关系社会学》中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互动之网”:“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研究时,最恰当的分析单位应该是行动者(包括个人和法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互动之网”;“至于行动者如何行动,则在各个层次上受到他们所处的情境、相关的他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形塑”(47)[英]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刘军、孙晓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在姚鼐去世之后,邓廷桢安徽巡抚幕府便是这样一种凝聚了诸多桐城派成员的“社会关系及互动之网”。诸人依托于幕府,在文学、学术方面进行讨论、竞争,形成一个共同体。而且,幕府的“社会关系及互动之网”并不仅限于桐城派成员之间,也体现在桐城派与其他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
三、桐城派与幕府中“他者”的互动
桐城派是个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流派。这不仅体现在成员之间良性的交流;还体现在文学理论的与时俱进,自我更新,如逐渐接受骈文;更体现在桐城派与其他学术群体的互动,既有与阳湖派的交流,也有与汉学、实学思潮的互动。
邓廷桢幕府成员较为复杂,邓廷桢并不以“派别”作为选择幕僚的依据,因此,幕府中桐城派、阳湖派、汉学家均存在。陆继辂属于阳湖派,宋翔凤属于汉学阵容,再加上马沅、汪钧等人,桐城派成员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
与阳湖派的交流,主要与陆继辂相关。陆继辂参与《七家文钞》的编纂,收录方苞、刘大櫆、姚鼐、朱仕琇、彭绩、恽敬、张惠言七人的文章,包含桐城派与阳湖派代表人物。从陆继辂《七家文钞序》的行文安排来看,有彰显阳湖派的意味(48)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第44页。,但仍承认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师承渊源。曹虹云:“以陆继辂的《七家文钞》为标志,显出不以斤斤于家数之辨为怀的意向。”“《七家文钞》的结集,反映了选编者对桐城派求同胜于求异的倾向。”(49)曹虹:《阳湖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28页。《七家文钞序》作于道光元年,可知,在入邓廷桢幕府之前,陆继辂便有兼取桐城派、阳湖派之意。
在进入幕府之前,管同与陆继辂发生过争论,涉及姚鼐与王芑孙之间的一桩“公案”。王芑孙在文章中对姚鼐“盛称之”,因此姚鼐《与王铁夫书》对王芑孙颇有溢美之词,认为能得归有光之真传(5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此事姚鼐亦在《与陈硕士》中提及,评论王芑孙“其文章不愧雅驯,亦今之奇士矣”(51)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64页。,评语较《与王铁夫书》更为平允。吴德旋《书王惕甫文集》涉及此事,认为姚鼐对王芑孙的过分夸赞属于反言讥讽,因为王芑孙“与熙甫无一毫似”(52)吴德旋:《初月楼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11页。,为姚鼐进行辩解。陆继辂《与吴仲伦书》云:“姬传续出之文,颇有违心徇人之作,而序惕甫集为尤甚。足下服姬传过当,知其言之失而将蒙不知文之诮也,曲为护前之说,以为反言讥之。夫君子之于文也,恶有所谓反言者哉?”(53)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第272页。认为姚鼐之文是“违心徇人之作”,对吴德旋进行批评。管同《与吴仲伦书》既反对吴德旋的“反言讥讽”说,也批评陆继辂因不满王芑孙之为人而“痛诋其文”,认为姚鼐写作此文的目的,只是“诱掖奖劝”而已(54)管同:《与吴仲伦书》,《管同集》,第115页。秦威威《管同年谱》对此事亦有论述,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11页。。
抛开事件的是非不论,陆继辂眼中的姚鼐和吴德旋、管同眼中的姚鼐是有所区别的。在作为“他者”的陆继辂看来,姚鼐并没有作为流派领袖的“神圣性”,是可以对其进行批评的,因此有“姬传续出之文,颇有违心徇人之作”的结论。而吴德旋、管同均为姚鼐的弟子,他们眼中的姚鼐,兼具老师和流派领袖的双重身份,有维护其形象的必要。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学术背景,会影响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事情的看法。
管同与陆继辂的争论,并未影响二人的关系。在进入安徽巡抚幕府之后,二人的交流仍然密切。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中颇多与管同唱和之作,管同《复陆祁孙书》亦记载二人讨论音韵之学(55)管同:《复陆祁孙书》,《管同集》,第149页。。而且,管同多次应陆继辂之请作文,如道光六年作《贞珉录后序》、七年作《饯秋唱和诗序》等。
进入幕府之后,面对众多桐城派成员,作为“他者”的陆继辂在积极交流、互动之外,仍有自己的坚持。在学术方面,陆继辂对邓廷桢非常重视的“双声叠韵”说持谨慎的态度。陆继辂《嶰筠先生与客谭古韵,成诗十章见示,奉和如数》第一首云:“双声叠韵本天成。”承认“双声叠韵”在音韵研究中的意义。但他认为此方法不可滥用,因为后人以此方法解读杜甫、李商隐的诗,就有错误。如第三首:“落木长江君听取,不关杜老误千秋。”注云:“落木、长江,浅人误指为叠韵。”(56)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第319页。第七首与《合肥学舍札记》的记载相同:“双声叠韵,盖本同音相训之例……近人尤好言之,至改李义山诗‘郎君下笔惊鹦武,侍女吹箫引凤皇’为‘弄凤皇’,以‘惊鹦’为叠韵也,则可笑矣。”(57)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2页。陆继辂并没有因为邓廷桢对“双声叠韵”的偏好而刻意逢迎,而是选择劝告邓廷桢应采取谨慎的态度。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幕府内部良性的交流氛围。
“汉宋之争”是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现象。方东树作《汉学商兑》,批评江藩《汉学师承记》推崇汉学、贬斥宋学的观点。此后,方东树尚有《书林扬觯》之作。道光五年,方东树在学海堂,为回应阮元“学者愿著何书”的问题而作此书(58)方东树:《书林扬觯》,李花蕾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并于道光十一年刊行。方东树云:
实体难工,空摹易善。近世著书者皆据此以尊汉学名物训诂而薄宋儒空谈义理,诚亦不可谓非知言也。……如典章名物固是实学,若施于时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禄田、考工、车制等,不知何用,则又不如空谈义理犹切身心也。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今之为汉学者,言言有本,字字有考,乃至音诂佐证数百千条,确凿无疑,反之己身本心,推之家国事物之理,毫无益处,徒使人荡惑狂狙,失守而不得其所主,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59)方东树:《书林扬觯》,第32~33页。
将理学与经世之学建立关联。程朱理学“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虽虚而实;汉学的名物考证之学,看似有关典章制度等实学,但“若施于时用,不切事情”,似实而虚。正如钱穆所云:“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6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7页。《书林扬觯》仍然坚持程朱理学,对汉学持批评的观点。但方东树也认识到宋学存在空疏的问题,承认讲习理学者中亦存在“老生学究腐谈”的现象,并非一味偏袒。因此,与《汉学商兑》的激烈态度相比,《书林扬觯》的态度稍显平和。幕府诸人对此书颇有揄扬,道光七年,管同有题辞;陆继辂、梅曾亮亦有题辞。道光九年,梅曾亮有《书林扬觯书后》之作,以“引伸其说”(61)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104页。。陆继辂在题辞中写道:“《汉学商兑》所以直入诸家之胁,全在理精义确,可谓搏虎屠龙手。其著书大旨则尽于此书中。”(62)方东树:《书林扬觯》,“书林扬觯题辞”,第1页。也意识到两本书之间的关联。
陆继辂赞扬《汉学商兑》《书林扬觯》“理精义确”,并不意味他赞同汉宋对立。相反,陆继辂主张汉宋调和。其《删定望溪先生文序》云:“(方苞)溺宋学而诋汉儒,至言訾謷程朱,类多绝世不祀,甚哉,方氏之陋也!”(63)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第177页。反对方苞分隔汉宋的门户之见。在《汉学商兑》的题辞中,陆继辂云:“丳穿群籍,兼综百氏,康成也;理足辞明,折衷平允,质之前圣而无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书,实兼是二者。”(64)方东树:《汉学商兑》,漆永祥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3页。认为方东树在推崇理学的同时,也不完全否认汉学的成果。陆继辂一直致力于调和论战的双方,面对高扬宋学旗帜的桐城派成员,如方苞、方东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幕府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的学术观念,为论争提供了土壤。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文学创作的需求以及外部形势的变化,“汉宋调和”逐渐为更多的桐城派成员所接受。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同时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邓廷桢幕府中,陆继辂、梅曾亮、方东树、管同诸人均有用世之志。汪钧《河兵谣,咨访河务也》关注河堤的修筑(65)汪钧:《心筠堂诗钞》,《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42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陆继辂虽然“不肯轻涉世事”(66)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李兆洛:《养一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3册,第197页。,但也会对当时女性的生存环境进行反思、关注治下贵溪县民风之浇漓(67)陆继辂:《触事有感》,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第259页;陆继辂:《喜雨》,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第374页。。梅曾亮《记棚民事》关注棚民开山之事的利弊(6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226页。。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云:“先生少补县学生,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方东树并不以文士自居,“四十以后,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义理,而最契朱子言。”(69)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方宗诚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页、58页。管同与方东树有相似的看法。道光七年,管同作《方植之文集序》,云:
四十以来,悟儒者当建树功德,而文士卑不足为。以语他人,怃然莫应也,植之独深然之。(70)管同:《方植之文集序》,管同:《管同集》,第125页。
将“儒者”和“文士”区别看待。“少可多否”的二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71)方东树:《管异之墓志书后》,《考盘集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208页。。管同作于同一年的《刘明东诗文集序》,引用姚莹的观点,亦认同刘开的经世实践。管同经世思想的理论依据,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方植之文集序》云:“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专注于“立言”的文士,显然是位于“建树功德”的“儒者”之后。
管同历来关注经世,文集中颇多关注现实之作。《拟言风俗书》发现当时风俗之敝:“今之风俗,其敝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并提出解决办法:“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主张由上而下的教化。《拟筹积贮书》针对京师藏储之粮“不过仅支一岁而止”的现状而发,提出裁汰闲散工匠、削减旁支宗室俸禄的建议。《答某君书》更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实学”的重视:“惠书教以专治时文,俟得科名,然后更求实学。异哉!斯言,非仆夙所望于足下者也”;“为士而但务时文,亦士之自甘卑陋而已,固非国家育才官人之本意”(72)管同:《管同集》,第32页、34页、43页。。在表明心志的同时,也劝诱对方关注实学。
邓廷桢也重视实学。道光十五年,宋翔凤作《善政乐府十首》,其中《课书院,明实学也》云:“独标古均许识字,还明实学敎通经。”(73)宋翔凤:《洞箫楼诗纪》,第208页。表明邓廷桢在书院教育中重视“实学”“通经”的理念,引导一地文风的走向。幕府上下这种“建树功德”“实学”的思想,也是姚门弟子的普遍追求。如陈用光《邓东岚太守寿序》云:“余好论经世务,自二十后,游四方,尝乐就贤士大夫访求当世利病及措置农桑、兵刑诸法。”(74)陈用光:《太乙舟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677页。关于陈用光的经世观念,可参考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第21~36页。直到晚清,受桐城派影响的莲池书院推崇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75)徐雁平:《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以同光年间莲池书院之讲习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桐城派成员并不是封闭在自己的圈子中,而是一直与现实紧密结合,并随时调整自己的主张、策略,即梅曾亮所谓的“因时”。
梅曾亮的“因时”说可以作为桐城派经世观念在文论中的反映。道光五年,梅曾亮《覆上汪尚书书》云:“夫君子在上位,受言为难;在下位,则立言为难。立者非他,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已。”(7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30页。君子提出的主张,不能只是刻板地套用过去的经验,而应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灵活应对,即“通时合变”。至道光二十七年,《答朱丹木书》云:“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77)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38页。明确提出“因时”。言论、文章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而存在,必须能够反映当时的“风俗好尚”。梅曾亮对“时”的关注,与桐城派重视经世的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通时合变”“因时”都强调“变”,反对陈陈相因,这与桐城派强调文学理论的更新也是一致的。
此外,桐城派文论中也有对“经济”的关注。姚莹重视为学之“用”,《与吴岳卿书》云:“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78)姚莹:《姚莹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方宗诚与戴存庄编选《桐城文录》,“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79)方宗诚:《桐城文录叙》,《方宗诚集》,第115页。,亦有“经济”在焉。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8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将四要素纳入孔门四科的范畴之内,“都具有圣门合法性,所谓汉宋两派争当孔门的正统而排斥异己实无必要。”(81)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作为桐城派中兴的功臣,曾国藩的观点可以作为晚期桐城派的代表。因此,桐城派的文论不断扩容,成为包括文章学、理学、考据学、实学等众多因素在内的流派。文学理论的更新,说明桐城派并不自我封闭,而是与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潮相互动,甚至结合。
在大致同一时期的江南,还有另外一个桐城派幕府,即姚莹幕府。道光十一年到十七年,姚莹在常州、扬州任职时,身边聚集了李兆洛、方东树、潘德舆、包世臣、周济、吴德旋等一批知名学者,成为一个文人群体。该幕府也非常注重经世之学(82)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33页、150页。汪孔丰:《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这两个桐城派幕府中均有汉学家、阳湖派中人,可以为思考桐城派与汉学、阳湖派的关系提供新的角度。可知,这种与“他者”的互动在桐城派并非个案,而是桐城派成员普遍的追求。因此,桐城派的发展壮大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必然性交织的结果。
四、结 论
桐城派是古代著名的文学流派。关注桐城派的文学创作、评点固然重要,但从文学之外的角度,如成员的交游、幕府的开设等,探寻桐城派传衍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人能弘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一代又一代成员从不同的方面为桐城派发展贡献力量。
桐城派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据王达敏统计,姚门弟子身居高位者有陈用光、姚莹、邓廷桢、鲍桂星、姚元之、李宗传、康绍镛、周兴岱等(83)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3页。,诸人多有担任学政、主政一方的经历。除借助乡试、会试影响士子学风、助推桐城派的传播之外,这些有力者也会在身边营造充满桐城派气息的小环境,即开设幕府。道光四年,梅曾亮《与容澜止书》云:“人皆戒子弟以无交梅、管两生,两生多误人。”(8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上册,第28页。可见以古文为志向者在当时的困难处境,亦可见桐城派成员之间互相帮扶的重要。而邓廷桢幕府在当时就承担了这样的功能。从时间脉络看,在姚鼐去世与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间,邓廷桢于安徽开设幕府,将“姚门四杰”中的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先后招致幕下,为诸人提供安定生活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聚会、讨论的机会。依托幕府,团结桐城派的有生力量,以群体的方式壮大桐城派的声势。同时,桐城派诸人也会与桐城派之外的群体、思潮进行交流、互动,并不故步自封。这也是桐城派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存世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流派成员最多的文学流派的原因之一。
桐城派文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更新的。文论的发展涉及多重因素,如桐城派文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社会风气的互动等,关联到文学、政治、思潮等多个角度。以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为例,戴名世、方苞、刘大櫆轻视骈文,姚鼐开始肯定骈文,姚门弟子中刘开、梅曾亮重视骈文(85)吕双伟:《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经过历代成员的反思、努力,骈文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也应注意到,姚门弟子中仍有坚持“古文至上”者,如管同。桐城派内部并非如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不同的观念,管同和梅曾亮的骈散之争就是不同观念碰撞的结果。从历时的角度看,桐城派重视骈文是大势所趋,但其脉络也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有波动、反复。因此,研究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应注意到流派成员的复杂性,不能笼统言之。
虽然姚门弟子对于古文各有不同的理解,也会发生一些争论,但他们弘扬桐城派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所言,经过姚鼐和姚门弟子的不懈努力,桐城派在巩固江苏、安徽、北京等阵地的同时,还扩散到江西、广西、湖南等地,逐渐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