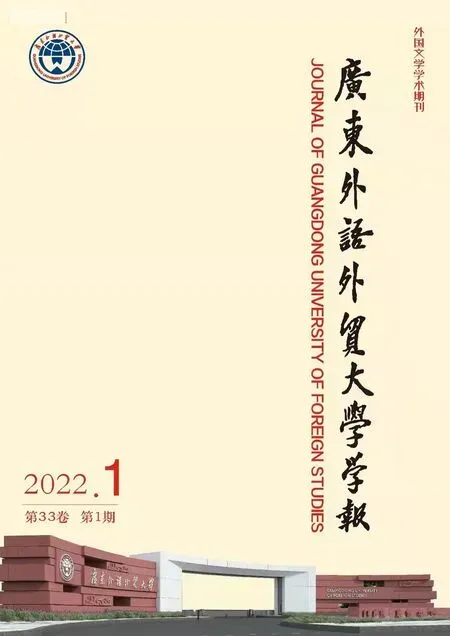节奏潜能与节奏美学:以《只是想说》的文本细读为例
黎志敏
引 言
“节奏”是中西诗歌的共同特征。什么是节奏呢?卢卡奇(Georg Lukács)引用毕歇尔的话说:“我们总是把具有同一强度和在同样时间内运动的规则性重复看作节奏”(卢卡奇,1986:208)。例如,乐队鼓手就是以同样强度、规律性地敲击来确定乐队节奏的。类似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卢卡奇等人对节奏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对相关生活现象观察的基础之上。不过,他们对于节奏的理解并不全面。
卢卡奇等传统学者认为形成节奏的关键之一在于“间隔时间相等”(isochrony)。可是,现代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试验者在听到可以用机械测量数值差别的间隔时间不等的电子铃声时,也会报告自己听到“有节奏”的声音(Couper-Kuhlen,1986: 52)。伊丽莎白·库珀库伦(Couper-Kuhlen,1993:12)对此解释说:“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节奏中的‘间隔时间相等’是不可能的;而从感知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象”。彭斯·库珀(Cooper,1998:18)指出,“(各种实验)表明节奏感知过程是一种主观乃至阐释性的活动”。在严格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现代学者认识到节奏的“主观性”特征,这是现代节奏研究区别于传统节奏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节奏并非纯粹客观的存在,而是主客观互相作用的产物。声音节奏的形成,必然经历这么几个过程:1)发声体发出声音;2)通过媒介传播;3)为人类感觉器官感知;4)被人类认知,并且在人类大脑中形成“节奏感”。现代学界尤其重视人类的主观节奏认知能力在“节奏感”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彭斯·库珀(Cooper,1998:3)认为,“人类一生下来就在心跳、吃奶、呼吸等生理层面表现出节奏感。而且还有一种学习走路、说话甚至音乐的节奏潜能”。人类依赖自身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拥有的节奏潜能,能够对外界刺激进行节奏化的处理(即形成节奏感)。理查德·卡尤顿(Cureton,1992:119)也说:“节奏经验是人脑的一种自在能力的产物。我将人脑的这种能力称为‘节奏潜能’”。因为人类具有节奏潜能,所以我们才能将不符合“间隔时间相等”的声音也进行“节奏化”处理,并且形成节奏的感觉。
理解人类的“节奏潜能”以及节奏的主观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与节奏美学,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幅全新的诗学图景。
认知机制视角下的节奏美学
从认知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西诗歌中的节奏问题,包括节奏的划分、诗行的长度、诗歌和哲学文本的不同特征等。诗歌中的节奏,归根到底是为人类的认知服务的,“包蕴着丰富的参与性精神”(孙美萍,2021:117)。具体而言,诗歌节奏的目的在于突出意义效果,增强情感表达,从而促使读者产生更好的认知效果。
中西诗歌节奏的构成要素并不一样,在汉语诗歌中,最小的节奏单位是“字”(即一个音节)。在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传统诗歌中,一个汉字就可以读为一拍。而英语诗歌中最小的节奏单位是一个音步,至少包括两个音节,例如抑扬格、扬抑格、扬扬格等。
汉语发音和英语发音很不一样,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汉语有声调,而英语没有。汉语的一个声调相当于英语的一“格”(即一个音步)。汉语四声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赵元任以五度记音制将它们的调值分别标记为55、35、214和51;从音高变化上来看,我们可以以汉语的四声对应英语的扬扬格、抑扬格、抑抑扬格和扬抑格。汉语中还有一种“轻音”,不过其数量极少,在此不论。
在汉语中,比单音节词更大的节奏单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因此,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节奏单位是双音节词。在以双音节词为节奏单位的现代诗歌作品中,每个双音节词的发音时值大致相等。不过,双音节词中所包含的两个汉字的发音时值却并不一定相等,有时更重要的那个字会被重读,而且占据更多发音时间,以此更多地吸引读者的注意。
在汉语诗歌中,节奏的基本单位都是具有意义的“词”,不论是单音节词、双音节词还是多音节词。下面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做一简单的节奏分析: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汉语诗歌以“意义单位”作为节奏单位,符合人类认知机制的要求。在对“轻轻的/我/走了/”这句话的认知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先单独处理“轻轻的”“我”“走了”三个片段信息,然后再综合起来处理这句话的意思,从而完成对整句话的信息处理。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节奏的作用是(1)在“轻轻的”“我”“走了”三个词的后面分别造成些微停顿,便于我们的认知机制分别处理这三个词的信息;(2)然后在这个句子末尾造成更长一些的停顿,便于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处理整句话的信息。
对于“轻轻的我走了”这句话,显然不可能这么断句:“轻轻/的我/走了”,——因为“轻轻/的我”会给我们的认知造成麻烦。有趣的是,英语诗歌中的节奏划分却常常出现这种“打乱意义单位”的情况:英语诗歌不是按照“意义单位”而是依据“音步”来划定节奏单位的。例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为著名的“哈姆雷特独白”,其节奏如下所示:
|ˉ ' | ˉ '|ˉ ' |ˉ ' | ˉ ' ˉ |
|To be,|or not|to be:|that is|the question:|
| ' ˉ |ˉ '| ˉ ˉ|ˉ ' |ˉ ' ˉ|
|Whe ther|’tis no|bler in|the mind|to suffer|
| ˉ ' |ˉ '|ˉ ˉ| ˉ '| ˉ ' ˉ |
|The slings|and ar|rows of|out ra|geous fortune,|
|ˉ ˉ| ' ' | ˉ ' |ˉ ' |ˉ ' ˉ |
|Or to|take arms|against|a sea|of troubles,|
|ˉ ˉ|ˉ '| ˉ ' ˉ |
|And by|oppo|sing, end them?|①
在这一小节中,很多节奏线(例如“’tis no|bler in”“and ar|rows of”“out ra|geous fortune”)都处于单词的中间,不可能造成有益于认知的些微停顿,也就是说,这里的节奏线是“虚的”,在实际诵读中不会停顿。其中最后一行“|And by|oppo|sing, end them?”中的第三个音步事实上并不成立,因为这一行中最大的停顿应该是在“opposing”和“end them”之间的逗号处。因此,第三个音步是破碎的,或者说是不成立的。一个正常的音步应该在这一音步结束之后稍作停顿,如果这个音步在中间的停顿反而比在这一音步结束之后的停顿时间更长,那么这个音步就是破碎的,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音步。
传统英语诗歌中意义停顿和节奏停顿的不一致现象,表明传统英诗格律体系具有较大的瑕疵,这是后来庞德打破“抑扬格五音步”格律模式的合理性之所在。在打破抑扬格五音步的同时,庞德提出“在节奏方面,不要按照节拍器的机械节奏、而要根据具有音乐性的词语的序列来进行创作”(Pound,1968: 3)。这样,诗人们就可以按照语言意义单位来建立诗歌节奏,从而尽量规避意义停顿和节奏停顿不一致的现象。
以上从认知角度所谈的是诗行内部的节奏划分问题,同样地,我们也能从认知角度很好地解释诗行(诗句)的长度问题。事实上,诗行的长度是由人类的认知处理能力所决定的,同时也和诗歌的载体(口语还是书面语)相关。中西诗歌都源于口语诗歌,在口语诗歌时期,为了方便记忆以及理解,诗句(诗行)一般比较简短,例如中国的《诗经》大多为四字一句,而英语民谣(Ballad)中每节是由二个四个音步诗行和二个三个音步诗行交叉构成。这些诗歌作品中的诗行比较简单,容易为人类大脑记忆、理解,有利于口头流传。
在传统汉语诗歌中,四言、五言、七言最为常见,原因就在于它们较为简短,利于读者认知。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可谓“言之有文,行之远矣”呢?答案很简单,其实就是有利于读者认知,能够给他们留下比较深刻记忆的文字。从反面来看,传统汉语诗歌中极少出现11个字以上的诗句,原因就在于11字以上的诗句太长,读者的认知机制处理起来比较困难,不容易留下深刻记忆。
同样道理,传统英语诗歌中最常见的是三音步、四音步、五音步,其原因在于它们较为简短,利于读者的认知。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有的中国译者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文中的每行10个音节对等翻译为10个汉字,这种翻译方法在表面上看是“对等”的,实质上却并不对等,原因在于:一个汉字的发音时长长于一个英语音节的发音时长,从音调变化的视角来看,一个汉字的发音等同于英语诗行中的一“格”(即一个音步)。因此,将十四行诗的一行10个音节翻译成为10个汉字,事实上大大加长了该诗行的发音时间,增加了译文读者的认知处理难度,因此并不合适。从认知角度来看,将十四行诗的一行10个音节翻译为汉语的5至7个音节较为合适,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对等”。
有没有诗行很长的作品呢?也有,不过十分少见。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垮掉派代表人物之一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代表作《嚎叫》。如果说传统诗歌中的一句(一行)可以称为“一读”(即读完一遍就能理解),那么,《嚎叫》中长长的诗行则需要“几读”。这种诗行较长的诗歌作品具有更多书面诗歌的成分,需要更多智性成分的参与,和传统更为口语化的诗歌具有显著区别。从认知角度来看,这种诗歌的成功,需要一定的特定前提:1)读者必须熟知诗歌内容,从而比较容易理解长长的诗句(诗行);2)诗歌内容是社会热点,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3)诗歌措辞准确,具有散文的描述性特点。第1)点和认知直接相关,第2)、3)点可以吸引读者阅读,以通过多次阅读的方法帮助认知机制完成认知过程。历史上以长诗句(诗行)形式创作的诗歌作品成功率较低,因为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前提条件的作品并不多见,因此在诗歌市场不具吸引力。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认知角度简单比较一下哲学思想类和诗歌艺术类作品的不同特点:哲学思想类作品着重于意义的表达,擅长表达曲折、复杂的各种思想,它并不强调语言的节奏。相比之下,诗歌作品追求节奏美学,它表达的意义相对简单,不过力度却更强大。好的诗歌节奏能够帮助诗歌作品中的特定字词在读者大脑那里获得更为充分的认知注意,从而使它们在读者认知中留下深刻而强烈的印记。换言之,哲学思维更为精密,而诗歌语句更有力度,更有冲击力。
诗歌节奏对诗歌内涵的彰显:以《只是想说》为例
美国后现代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名作《只是想说》(“This Is Just to Say”)只有30个单词:“This is just to say I have eaten the plums that were in the icebox, and which you were probably saving for breakfast.Forgive me! They were delicious: so sweet, and so cold.”(只是想说:我吃了冰柜里的李子。也许,你打算拿它们当早餐。请原谅:太好吃了! 真甜。真爽)。这是一张便条,其内容本来稀松平常,不过,威廉斯通过“分行”处理,在赋予其诗歌节奏之后,就创作出了20世纪英语诗歌世界里的一篇经典作品。
This Is ' Just to ' Say
I have ' eaten
the ' plums
that ' were in
the ' icebox
and ' which
you were ' probably
' saving
for ' breakfast
For ' give me
they were de' licious
so ' sweet
and so ' cold②
在这首诗中,威廉斯彻底摆脱了传统英诗格律的束缚,不再按照“音步”而是按照“重音”来划分节奏,是一首“重音诗”(accentual verse)。重音诗的特点是以重音数目来计算诗行节奏,即一个诗行有几个重读音节,就读为几个音步。这首重音诗符合按照“意义”划分节奏的做法,没有出现“破碎”的节奏现象。而且,这首诗是一首非常特别的重音诗,即每行都有而且只有一个重音。
全诗一行标题,3个诗节,每个诗节4行诗句,共13行。从语法上来看,标题和前两节共9行是一个句子单位。威廉斯通过对这个句子进行诗歌节奏化处理,将它切割成了9个语义单位,延缓了句子意义在读者大脑认知机制中的显现速度,使得读者能够充分观照每个字词的意义,从而加强了它们的显示强度。
诗歌和哲学的差别之一在于后者的文本结构是比较纯粹的“意义结构”,因为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追求“意义的明晰”;而前者的文本结构不仅具有“意义结构”,还具有“情感结构”,有时“情感结构”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意义结构”,诗歌不仅需要表意,更需要抒情。在《只是想说》一诗中,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表意”(即不是为了说自己“吃了李子”这件事情),而是想找一个话头(即诗歌内容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话头”),以一种幽默风趣的语气,和妻子进行日常情感沟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创造诗意之美。作者通过对便条内容进行“分行”处理,加强了诗歌文本的显示强度,引导读者的注意力超越文本的“意义内涵”,因而得以充分地体味到文本中的“情感内涵”。
以下尝试以语词为单位,分析《只是想说》一诗的诗意形成过程。在标题中包含这样几个单词:“This”(代词),“is”(系动词),“just”(副词),“to”(小品词),“say”(动词)。在第一次阅读中,读者在认知上倾向于理解这几个词所构成的“意义内涵”,会感觉其意义平淡。
该诗第一节包含这样几个单词:“I”(代词),“have”(助动词),“eaten”(动词),“the”(定冠词),“plums”(名词)。这一诗句的意义“我吃了李子”也比较平淡。接下来是“that”(关系代词),“were”(系动词),“in”(方位介词),“the”(定冠词),“icebox”(名词)。从意义上来看,依然比较平淡。
该诗第二节包含这样几个单词:“and”(连词),“which”(关系代词),“you”(代词),“were”(系动词),“probably”(副词),“saving”(动词),“for”(介词),“breakfast”(名词)。单独地看第二节,其意义比较平淡。不过,如果将第一节和第二节联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一对矛盾:即“我”吃了“你”留下的李子,而这对矛盾构成了某种艺术张力。
该诗第三节在措辞上和第一、二节大不相同。“Forgive me”这个词的情感内涵大大超越其意义内涵,具有较强的道歉情感色彩。“delicious”一词在意义上表示“可口”,不过同时具有明确的情感内涵即表示“愉快”。“so sweet”和“so cold”中的“so”一词具有强烈的情感内涵,而“sweet”和“cold”二词中的情感内涵的重要性也超越了其意义内涵。尤其是“cold”一词,其本义表示“冷”,其情感内涵本来是“不愉快的”,不过,在这一特殊的诗意语境中,其情感内涵已经转化为“非常愉快”了,在一首诗中,某个(些)语词的情感内涵发生改变的现象,往往可以视为这首诗歌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的“诗意”,在这种现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下面对本诗中的两个核心词语“sweet(甜)”和“cold(冷)”的诗意形成的认知过程,进一步进行阐释。“甜”的所指意义:是指糖分对于人类味觉器官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反应,具体地说,就是指李子里面所含的糖分对于“我”的味觉器官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反应。“甜”的这一所指意义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糖分对于任何人的感官刺激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反应结果。“甜”的这一所指意义本身不带任何“情感”倾向,是完全中性的。尽管糖分对于不同人的感官刺激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反应结果,然而,不同人对于这种感觉反应结果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却不相同。例如,当一个不喜欢“甜”食的人吃到“甜”食(或者听到“甜”食)时,他在认知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不快”的情感体验。相反,当一个喜欢“甜”食的人吃到“甜”食(或者听到“甜”食)时,他在认知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情感体验。这是一种刺激条件反射。刺激物是“甜”食(或者“甜”食这个语词),反应是一种“不快”或“愉快”的情感体验。
在本诗之中“甜”的所指意义,是诗人的味觉器官对于糖分的感官感知。诗人在进行这种感觉感知之时,其情感体验如何呢?在这首诗之中,“甜”是对于“delicious(可口)”的进一步解释说明。“可口”直接表明诗人喜欢李子的味道,由此可见诗人喜欢“甜”。也就是说,当他尝到李子的“甜”味时,他的情感体验是愉快的。因此,当他说李子“甜”的时候,也是在表达一种“愉快”的心情。于是,语词“甜”在该诗之中就具有了双重内涵:其一是指一种“甜”的感官感知,其二是指一种“愉快”的情感体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甜”的意义内涵,而在诗歌研究中,我们还要充分重视“甜”的情感内涵——因为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言情”的文学艺术。在该诗之中,当语词“甜”从一种感官感知的指代,上升到一种情感体验表达的时候,即当它拥有了确定的“情感内涵”的时候,它就从一个一般的语词变成为了一个充满情感的诗意语词,我们称之为诗歌语词。
在该诗中,语词“cold”的意义内涵是指人类感官对于低温的感知。一般来说,“冷”会刺激人产生一种“不快”的情感体验。不过在该诗之中,“冷” 和“甜”并置,都是对于“可口”的解释,因此,“冷”的情感内涵不是“不快”,而是一种爽快、一种兴奋。“冷”和“甜”的意义内涵不同,不过它们的情感内涵却是类似的:都是一种“愉快”的情感体验。因此,“甜”和“冷”在诗中的先后出现,就产生了一种“愉快”情感的叠加效果,加强了诗作的感染力。
人们在阅读自己所喜爱的诗歌作品时,往往在“一读”之后,还会进行“二读”“三读”,直到烂熟于心。在“二读”“三读”时,会超越诗句的前后语法逻辑关系,以一种“共时”的方式来进行,换言之,就是读者进一步超越诗歌的意义内涵,而将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情感内涵。在对《只是想说》进行多次阅读之后,我们对它的意义内涵(即诗人偷吃了李子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在意,却对它的情感内涵(即诗人对他的妻子所表达的那种“甜蜜”)感觉越来越深刻。从情感内涵出发,我们发现整个诗歌的文本不是一种线性的语法关系,而是一种“共时”的存在,诗中的所有因素都围绕着一个语词(即甜“sweet”)在起作用。
任何语言都有很多表示不同程度的词语,例如开心、高兴、狂喜等。不难看出,当人们对于某事某物的感觉程度变化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就会创造一个新词来对应它。不过,通过造词的方法来表现不同的心境,其可操作性毕竟是有限的。有些心境,通过造词没有办法实现,只能通过语篇来呈现,就如《只是想说》中的那种“甜蜜”,通过造词的方法无法表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首诗。从这一角度来看,诗歌的价值的确是独特的、无可取代的。
结 语
传统诗学界误以为诗歌节奏是完全客观的,因此他们所构建的传统节奏美学主要体现为种种严格的格律模式。现代学者发现了节奏的主观特性,发现人类天然具有节奏潜能,能够对并不完全符合“间隔时间相等”的客观刺激做出节奏处理。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基于人类认知机制的现代节奏美学。
人类天然的节奏能力是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求生本能,它可以帮助人类在认知世界万物时降低能耗,提高效率,有益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上,人类天然具有将认知对象进行“节奏化”处理的倾向,例如小孩吃奶,吃顺之后就很有节奏;又例如我们走路,走顺之后就走出节奏感来;再例如学生们在将一篇课文读熟之后,就自然而然地读出节奏感来……现代诗歌在打破传统诗歌的严格格律模式之后依然具有节奏感,是因为读者自身具有节奏潜能,能够主动地对诗行进行节奏化处理(黎志敏,2008:163-170)。
人类的节奏潜能是语言进化的核心动力所在。例如汉语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四字成语,就是人们对语言进行节奏化处理的结果:四字成语最具有节奏感,最符合人们的节奏偏好。此外,古代很多朗朗上口的诗句走进人们的日常用语,从诗界的小众语言变成了普罗大众的语言,也是人类的节奏偏好使然。同理,一些缺乏节奏感的语句,会因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逐渐淡出主流语言体系。一方面,人类的节奏潜能赋予了语言节奏之美,另一方面,诗人们也有义务创造出具有优美节奏感的诗篇,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人类的节奏潜能。人们的节奏潜能有层次差别,一般来说,通过专业训练的诗人、音乐家的节奏能力要比一般人强得多,他们创作的优美的艺术作品,可以帮助普罗大众提高节奏感知能力。节奏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智力要素,一般而言,音乐、诗歌教育越是普及的国家,其国民智商的平均水平也就越高。
诗人们利用人类的节奏能力规律,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节奏美学,其中最有效的做法是以诗行形式来引导读者的认知注意力,通过节奏划分让部分诗歌语词在读者大脑中得到凸显,激发读者领悟到奇妙的诗歌之美,正如威廉斯在《只是想说》中所做的那样。
注释:
① 孙大雨是国内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的“读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② 原文与译文均可参见:黎志敏.2018.剑桥读诗:现代英语诗歌精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72-73。文中以“'”作为重音标记,表示它之后的音节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