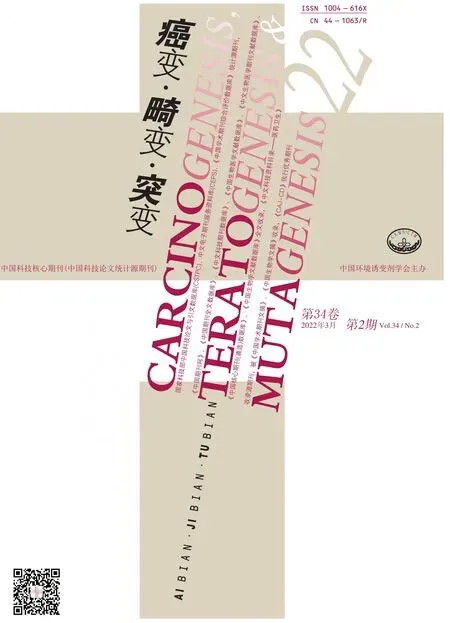PPAR-γ在巨噬细胞炎症调控中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进展
涂永梅,彭 洁,龙 子,孔德钦,陈宇豪,覃梓瀚,刘 瑞,李文丽,*,于卫华,*
(1.空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毒理学教研室,陕西省自由基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特殊作业环境危害评估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32;2.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学员大队,陕西 西安 710032;3.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属于核受体转录因子超家族的关键蛋白,主要通过配体结合途径激活,参与调控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肪酸代谢,在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巨噬细胞作为机体的主要炎症效应细胞,其浸润激活与肥胖、肿瘤、脓毒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急慢性炎症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2]。近年来研究表明,PPAR-γ信号在T细胞和巨噬细胞功能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3],PPAR-γ表达可影响内脏脂肪组织中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及其免疫功能。此外,PPAR-γ信号还参与调控巨噬细胞的促炎和抗炎分化走向,其激动剂可增强机体抗炎反应,有效改善多种急慢性炎症疾病[4]。因此,明确PPAR-γ在巨噬细胞中的抗炎机制有望为炎症疾病防治提供新策略。
1 巨噬细胞的炎症调控作用及其生物学意义
炎症反应是人体中最基本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其本质是炎性细胞浸润和炎症因子大量释放,形成以血管为中心的局部或全身反应。巨噬细胞是一种来源于骨髓,由单核细胞转变而来的固有免疫细胞,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组织器官内,其主要生物学功能包括抗原呈递、介导炎症反应和吞噬病原菌作用,在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5]。巨噬细胞是机体内最主要的炎症效应细胞,按照其功能及表型可划分为促炎(M1)型和抗炎(M2)型两大类。在感染、创伤早期,病灶周围募集M1型巨噬细胞,产生大量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一氧化氮(NO)等促炎因子,帮助机体清除病原菌和外来异物;而在感染和创伤后期M2型巨噬细胞转居主导地位,能够吞噬凋亡和碎片的中性粒细胞,并分泌大量抗炎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参与调控机体炎症消退和创伤愈合。当M1型巨噬细胞持续激活或者M2型巨噬细胞活化不足时,机体内促炎因子大量分泌,容易导致炎症持续存在和创伤难以愈合,进而形成慢性炎症疾病[6]。临床研究提示,在急慢性感染导致的肝炎、肺炎和脓毒症患者中,M1/M2型巨噬细胞比例失调,具体表现为M1型巨噬细胞比例升高,而M2型巨噬细胞比例降低,因此,调控巨噬细胞极性能够减轻感染性疾病。最新报道发现,在肥胖、脂肪肝、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梗死等非感染性炎症疾病中,也存在M1/M2型巨噬细胞比例失调,通过药物干预降低M1型巨噬细胞、升高M2型巨噬细胞,有助于减轻机体炎症水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修复受损血管组织,进而达到改善病情的作用[7-8]。此外,巨噬细胞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也发挥关键作用,M1型巨噬细胞有助于杀伤肿瘤,是正常情况下机体清除恶性转化细胞的有力武器;而肿瘤微环境中巨噬细胞被驯化为M2型,又被称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参与肿瘤的生长、生存、侵袭转移和耐药抵抗等一系列过程[9]。许多临床证据也表明,肿瘤组织中M2型巨噬细胞比例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正相关,靶向干预巨噬细胞是近年来肿瘤研究和治疗领域的国际热点[10]。因此,调控巨噬细胞的分化方向,抑制机体过度炎症,可能是感染和非感染性炎症疾病治疗的新思路。
2 PPAR-γ的结构、分型和生物学功能
PPARs是一类核受体转录因子超家族蛋白,主要有PPAR-α、PPAR-β/δ和PPAR-γ三种亚型。作为一种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子,PPAR-γ活化后进入细胞核与视黄酮X受体(retinoid X receptor,RXR)结合形成二聚体,与PPAR应答元件(peroxisome proliferator response element,PPRE)作用后,可以激活或抑制靶基因表达[11]。PPAR-γ蛋白由4个功能结构区域组成:①A/B区含活化功能域(activation function-1,AF-1),位于氨基末端,该位点丝氨酸磷酸化能够抑制PPAR-γ与配体结合激活;②C区是PPAR-γ的DNA结合域,与RXR形成二聚体;③D区为铰链区,含DNA结合域,赋予配体结合域灵活性;④E区为配体结合区域,位于PPAR-γ与RXR的二聚体区域。PPAR-γ基因按5′端序列不同可产生3种mRNA,分为PPAR-γ1、PPAR-γ2和PPAR-γ3。其中,PPAR-γ1与PPAR-γ3 mRNA翻译后生成蛋白质完全相同,而PPAR-γ2蛋白N端相较PPAR-γ1蛋白多出30个氨基酸序列。PPAR-γ1是PPAR-γ的主要形式,表达范围相对广泛,主要在脂肪细胞,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平滑肌细胞和肝脏细胞大量表达;而PPAR-γ2表达范围较窄,主要在脂肪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内表达;PPAR-γ3仅表达于巨噬细胞和大肠中[12]。PPAR-γ在调控脂肪细胞分化和脂糖代谢中发挥关键性作用,阻断PPAR-γ信号激活可抑制脂肪合成[13]。此外,PPAR-γ信号还与机体胰岛素抵抗的形成密切相关,PPAR-γ敲减小鼠会出现脂肪萎缩、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等症状[4]。最新研究发现,PPAR-γ信号抑制与多种炎症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正常人群脂肪组织PPAR-γ保持稳定活性,巨噬细胞数量较少且呈现M2型,这有利于维持胰岛素敏感性;而肥胖患者脂肪组织中PPAR-γ表达和活性降低,巨噬细胞数量增多且为M1型,呈现一种慢性低度炎症状态,是导致糖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发生的重要基础[14]。研究提示,PPAR-γ基因突变或敲减后小鼠对化学因素诱导结肠炎敏感性增加,过敏性哮喘和胰腺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也提高。PPAR-γ激活还可诱导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炎症效应细胞凋亡,抑制机体过度炎症,提高脓毒症动物存活率[15]。不仅如此,PPAR-γ还能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参与调控肝癌、胃癌、食管癌和卵巢癌的发生及发展[16]。
3 PPAR-γ在巨噬细胞炎症调控中的作用及机制
PPAR-γ与巨噬细胞成熟过程密切相关,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过程中PPAR-γ活性逐渐升高,并随分化成熟达到峰值,PPAR-γ激动剂可刺激人单核细胞中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CD163和CD36表达升高[17]。不仅如此,PPAR-γ可通过调控氧化还原平衡、抑制促炎信号通路和激活多种抗炎因子表达,最终决定机体巨噬细胞的炎症走向。
3.1 PPAR-γ抑制M1型巨噬细胞促炎信号的启动
M1型巨噬细胞的促炎反应是导致多种急慢性疾病的始作俑者,抑制其过度激活对于脓毒症、肥胖和心脑血管等疾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多种信号通路参与调控了巨噬细胞的促炎反应,其中最主要的包括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核 因 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激活蛋白1(activator protein 1,AP-1)、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COX-2)、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STAT)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OS,iNOS)等[18]。大量研究提示,PPAR-γ信号激活可显著阻断TLR4、NF-κB、AP-1和COX2等转录因子与靶基因启动子中同源位点结合,抑制巨噬细胞TNF-α和IL-6的表达,进而改善小鼠脓毒症[19]。PPAR-γ的激动剂曲格列酮、罗格列酮等可抑制骨髓原代巨噬细胞的M1型极化和促炎因子转录表达。此外,大黄素能够激活RAW264.7巨噬细胞中PPAR-γ信号,抑制LPS诱导NF-κB及下游促炎信号启动[20]。高良姜素可激活小胶质细胞中PPAR-γ信号,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细胞黏附分子表达[21]。上述结果表明,PPAR-γ可抑制M1型巨噬细胞促炎信号的启动。
3.2 PPAR-γ促进M2型巨噬细胞抗炎信号的过程
此外,PPAR-γ信号可能参与M2型巨噬细胞抗炎信号的启动。研究[22-23]报道,PPAR-γ激活可促进巨噬细胞M2型极化,并上调CD206、IL-10和Arg1等抗炎因子表达。Odegaard等[24]报道显示,骨髓细胞PPAR-γ敲除小鼠的M2型巨噬细胞减少,脂肪组织抗炎因子表达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和胰岛素抵抗风险增加。在高脂喂养的动物模型中PPAR-γ表达和活性降低,促进Kuffer细胞M1型比例升高、M2型比例减少,进而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且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巨噬细胞中PPAR-γ活性与M2型标志物表达呈正相关,激活PPAR-γ可促进单核细胞向M2型巨噬细胞分化。此外,IL-4能够诱导STAT6表达升高,与PPAR-γ结合促进其转录激活,进而启动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中抗炎信号表达[25]。研究表明,姜黄素、白芦藜醇和小檗碱等多种中药单体能够激活PPAR-γ信号,启动RAW264.7巨噬细胞的抗炎症反应。Yao等[26]发现PPAR-γ激动剂可与整合素αVβ5结合,进而促进M2型巨噬细胞抗炎信号Arg-1和Fizz1的表达。
3.3 PPAR-γ通过氧化还原调控巨噬细胞分化
大量文献显示,氧化还原(Redox)信号与巨噬细胞极化和炎症调控密切相关[27-28]。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不同剂量对炎症信号的影响也存在差异,ROS增多或抗氧化减弱调控巨噬细胞向促炎分化,ROS减少或抗氧化增强有利于巨噬细胞向抗炎分化[29]。生理条件下,机体中PPAR-γ内源性配体富含不饱和双键,极易被ROS攻击,形成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30],失去对PPAR-γ的激活作用。本课题组前期发现,在高糖培养肝细胞和胰岛β细胞中ROS升高,而PPAR-γ表达和活性降低,提示ROS可能是PPAR-γ的负向调控因子[31]。PPAR-γ激活可抑制小胶质细胞ROS和促炎因子的释放,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此外,在帕金森动物模型中使用PPAR-γ激动剂可抑制氧化损伤,减少促炎因子表达,增加抗炎因子释放,发挥神经保护作用[32]。因此,PPAR-γ信号激活可能通过氧化还原平衡调控巨噬细胞炎症反应。
4 PPAR-γ激动剂在炎症疾病中的应用
按照来源,PPAR-γ配体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配体包括亚油酸、亚麻酸和二十二碳四烯酸等多不饱和脂肪酸及其代谢产物15-脱氧前列腺素J2(15d-PGJ2);外源性配体包括罗格列酮、吡格列酮等噻唑烷二酮类(thiazolidinediones,TZD)类抗糖尿病药物以及GW1929等。研究表明,15d-PGJ2、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等可阻断M1型巨噬细胞NF-κB及下游促炎信号激活,并促进M2型巨噬细胞抗炎因子转录表达[33]。15d-PGJ2和TZD类药物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肿瘤、抗纤维化和抗血管生成的作用,在多种炎症疾病治疗中具有应用价值。
由生物和化学因素导致的肠道炎症疾病是近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大量研究发现提高PPAR-γ配体水平对多种肠道炎症疾病具有保护作用[34]。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干预可改善三硝基苯磺酸诱导的大鼠结肠炎症反应和黏膜溃烂[35],小鼠肠道上皮细胞中过表达PPAR-γ可抑制LPS等诱导的炎症反应。此外,共轭亚油酸也可通过激活PPAR-γ,调控野生型小鼠肠道M1/M2型巨噬细胞比例,减轻炎症反应和肠道损伤,但对结肠特异性敲除PPAR-γ的小鼠则无明显保护作用[36]。临床试验也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PPAR-γ表达显著减少,而七叶皂苷(aesculin)可通过激活PPAR-γ途径改善肠道炎症[37]。
脓毒症是一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易导致多器官衰竭和死亡,而巨噬细胞M1型激活及其介导炎症风暴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基础。大量研究表明,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抑制脓毒症小鼠巨噬细胞的促炎分化,并增加抗炎因子的分泌,抑制肝脏、肺脏和脑部等组织的炎症损伤[38]。临床研究也提示,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降低脓毒症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6等促炎因子表达,改善其肺部和肝脏等组织的炎症反应[39]。
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是指自身抗原免疫紊乱导致机体炎症损伤的一类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研究发现,PPAR-γ激动剂吡格列酮和罗格列酮有助于促进单核细胞向M2型巨噬细胞分化,预防小鼠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40]。此外,吡格列酮可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椎间盘退变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的IL-17A、IL-22和IFN-γ表达,减少脾脏巨噬细胞IL-6的分泌,延缓病情进展[41]。TZD类药物还能够诱导滑膜细胞凋亡,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滑膜细胞中TNF-α和IL-6的分泌。
代谢性炎症是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以往研究认为,TZD类药物可通过激活PPAR-γ调控脂肪细胞分化和脂糖代谢,能够改善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最新研究提示,罗格列酮调控肝脏和脂肪组织的巨噬细胞M1/M2型极化比例,减轻动物胰岛素抵抗,罗格列酮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的抗炎特性[42]。此外,吡格列酮能够改善非糖尿病患者的代谢综合征,服药6周后患者血清和单核细胞中促炎因子表达下调,抗炎因子升高[43]。
5 小结
作为机体的固有免疫和炎症调控的核心组分,巨噬细胞的数量和功能稳态对于维持机体健意义重大。PPAR-γ是一种配体依赖的核受体因子,是机体维持正常脂糖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的基础,在肥胖、脂肪肝、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PPAR-γ还与巨噬细胞的极化和炎症调控息息相关,不仅可抑制M1型巨噬细胞促炎信号激活,还能促进M2型巨噬细胞抗炎反应。PPAR-γ激活还可影响巨噬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进而间接发挥抗炎调控功能。TZD类PPAR-γ激动剂在脓毒症、肥胖、肠道炎症和自身免疫炎症性疾病中发保护作用。但也有研究指出,长期服用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等药物能够导致机体体质量增加,增加膀胱癌和慢性肾炎的发生风险。此外,姜黄素、二苯乙烯苷、丹皮酚、人参皂苷等中药单体也能促进巨噬细胞抗炎反应,减轻机体炎症损伤。因此,PPAR-γ是调控巨噬细胞炎症走向的核心分子,其激动剂在各种急慢性疾病中应用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