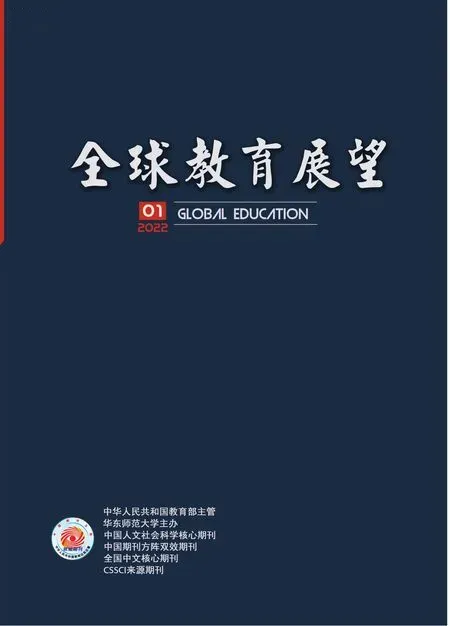教材≠教科书: 俞子夷在小学教材思想上的一个创见 ①
丁道勇
今天,很少有人会公开主张“教材中心”的立场,“课程资源”也成了一个得到关注的教育概念[1],但在小学教育领域,“教材”事实上仍被当作教、学、考的一个法宝,是教师不敢轻忽的一件重器。如果进一步具象化,这里的“教材”往往就是指“教科书”(或者更口语化的“课本”)。“教教材、考教材”至今仍是我国小学教育界的顽疾。在作此类批评时,人们真正不满的是教师在教材问题上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教科书”上[2](1)关于“教教材、考教材”这个问题,已出版的一些文章使用了“大教材观”“教科书使用”“调适教科书”等关键词。另有一些中小学教师用“教教材”和“用教材教”讨论了相关的话题。。
俞子夷(1886—1970)自1907年开始做教师,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几乎从未离开过基础教育界。他做过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又做过大学教授、教育厅长;他教过小学,也研究过小学,是小学教育真正的行家里手。俞子夷明确区分了“教材”和“教科书”,反对把“教材”等同于“教科书”。他对小学教材的这一理解与他在众多教育问题上的主张有关,也始终体现在他本人的教育实践当中。只要“教教材、考教材”的现象还未绝迹,俞子夷在小学教材思想上的这一创见就仍有回顾和讨论的价值。
一、 什么是教材?什么不是教材?
譬如在秋季里和小学生研究向日葵,不留心的教员,只拿了教科书中的课文,向学生空讲,学生即使能把课文读得烂熟,也不过鹦鹉学话,实际没有学到什么。学生心理上关于向日葵方面没有多少生长,那末这一课的课文,当然不好算是教材。园地上有好多向日葵生长着,我们同学生到园地去,实地研究,学生的经验中,比了未学以前,当然扩充了好多。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学生已经在学习。那末园地上的向日葵,仿佛是教材了。不过学生没有去研究时,这几株向日葵,决不能算是教材。我们同学生研究过以后,离开园地时,向日葵虽仍生长着,仍不能说他是教材。只有在教学时,用了可以使学生经验改变的,才是教材。[3]
向日葵是实物,一般读者往往不会把它和教材挂起钩来。但是,在俞子夷看来,只要教师在教学中用到了向日葵,并且由于这种应用“扩充”了学生的经验,向日葵就可以被称为教材;相反,被许多读者等同于教材的教科书,如果教师在教的时候只是“空讲”,让学生“鹦鹉学话”照着念几遍,那么这里的教科书反而不能被称作教材。寻常事物可以是教材,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反而不见得是教材。这个判断颠覆了某种“常识”,不再把教材等同于教科书。
“只有在教学时,用了可以使学生经验改变的,才是教材。”类似的意思,俞子夷在别处也曾表达过,比如“……在人类文化中去挑选些精华出来,用作激发儿童学习的刺激,供给儿童心理生长的滋养料,就是教材。要是写在书里,不发生上述功用,依旧不是教材。”[4]“书不是教材;杯、纸、火、水、盆,都不是教材。做把戏也不是教材……凡是可以用来真正教学的,才是教材。”[5]这样看来,是不是书本、是不是专门的教学用出版物,在教材问题上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得到妥善应用,以至于产生了切实的功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概括来说,在什么是教材、什么不是教材的问题上,俞子夷给出了两项判断根据: 第一,在教学中是否得到了应用;第二,是否发展了学生的经验。
那么,俞子夷为什么要把“教科书”和“教材”区分开?在其30岁时出版的《余之教育观》中,俞子夷把“教育终极之目的”定义为让儿童实现“自觉的、意识的进化”:“学校教育之作用,非拘留儿童也,非传授字典、百科全书也;当精选多方可经验之材料,以其善良之本能为基础,使儿童一一自己经验之。其不良之本能,则利导之,使代以有价值之经验。重演吾祖先精当之经验,而使经验之。此为教育之第一步。本此经验,而使能为自觉的、意识的进化,此为教育终极之目的。”[6]在这篇文章中,俞子夷在谈自己的“教育观”之前,先行介绍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伦理观、生死观。其中,在关于“人生观”的部分,他对“自觉的、意识的进化”做了说明:“自觉的、意识的之进化,别名之曰社会之发达。”两处联合起来,可以看到俞子夷眼中的“教育终极之目的”,明显是社会本位的。在他眼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自食其力、能够服务社会乃至推动文明进步的人,“读死书”的“两脚书橱”“书呆子”显然都不合格。
教科书上的教材,只能采取一部分,不能全体都用。如果你全体的教材都取之于教科书,或以为教科书就是教材,那末你就得陷害儿童落入读死书的窝臼而不自觉,你所办的教育,就会失败。[7]
高深的学问,要建筑在日常极通俗极浅近的经验上。先叫小朋友接触事事物物,教科书放在后面。开始就打开书来教,是永远教不好的。充其量教成功,两脚书橱罢了。[8]
教员拿教科书做教材的全权代表,学生便拿教科书当作学问,那末强记背诵,成了惟一的学习方法。这种教育愈普遍,世上有用的人愈少。要是这种教育普及以后,全国民不将尽变成书呆子![9]
俞子夷多次戏称,教材之于儿童就像是“粪土”之于农作物。植物生长需要土壤、肥料,类似的儿童“心理生长所须的养料便是教材”[10]。这个比喻我们完全可以接着说下去,以便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俞子夷的教材思想。比如,为了确保农作物长势良好,需要适宜的墒情、肥力。为程度参差的同龄儿童提供进度、内容完全一致的教材,就好比是用同一套耕作方法对付不同的农作物。俞子夷说:“教材要合儿童经验,要顾到儿童个性的不同。有一个浅近的比喻,儿童与教材的关系,仿佛肥料、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教材一律,硬叫个性不同的儿童来迁就,实在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办法。”[11]这个比喻义可以进一步联系到活用教科书、教材地方化、弹性编制等问题上去。又比如,植物生长需要天时地利多种条件的配合,仅仅提供足够的肥力未必能确保丰产。让儿童只读教科书,和一个总给花浇水、把花活活浇死的门外汉一个样。这个比喻义可以进一步联系到乡土教材、联络教材、补充教材等问题上去。
只要教师放弃教材等于教科书的想法,教科书的神圣地位也就动摇了。俞子夷写道:“(教师)肯留心的话,那么山边、水畔、旷野间、田地上、场角、屋旁、林间、草上,凡眼睛所能看得到的,耳朵所能听得到的,远近上下,何时何处不充塞着丰富的教材?肯留心的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2]古今中外、天上地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处、无一物不可以拿来作为教材。“因为教育是一种生长;教材是生长所须的滋养料。我们不必问教材的种类,我们最紧要的,是问教材能不能滋养儿童的正当生长。有利于正当生长的,都是好教材。”[13]教师认识到这一点,就再也不会满足于教完眼前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了。“教材≠教科书”这个公式在改变教材内涵的同时,也改变了教师和教材的关系定位。
二、 教师与教材
一旦接受“教材≠教科书”这个公式,教材的取材范围、题材类型就拓展开来了。“教科书不可以当作教材的全权代表;真正良好的教材,常常在实际生活中,教科书以外。”[14]有了这个认识,一切对儿童经验发展有裨益的东西,都可以放心大胆地拿来用在教学上。当然,这个公式并没有否认教科书的实用价值,毕竟不是每位教师都有能力自编教材,成熟、可靠的教科书仍然有价值。
我想不熟练的教师,还是有比较呆板些的工具较妥。从呆板中练习到自由,所谓熟能生巧,是学习必经的步骤。大多数教师,尤其是才从师范学校或短期训练班出来的,不给他们一个正常的样,凭空叫他们自由运用,恐怕会任意乱用到一事无成。这种平凡的工具,原是拿一般平凡的情形作对象的。技术高明的教师自由运用他精巧的工具,必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何必拿粗劣的工具束缚他们![15]
对于“技术高明的教师”来说,教科书是“粗劣的工具”。这是因为在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当中,教科书的重要性愈是得到强调,其形式和内容的选择空间就愈是受限。俞子夷写道:“无论那一科目的教科书,总要得到一个具体而微的格局,才可以免去眭一漏万的顾虑。”[16]在篇幅既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眭一漏万”,编写者往往选择点到为止的写法。结果,在内容上固然兼顾了全面性,在表现方式上却往往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如果教师不提供相应的补充读物,学生单凭这样的教科书不容易得到确凿、生动的认识。
俞子夷的点评,暴露了“用教科书教”时容易出现的两大缺点: 第一,由于篇幅狭窄、内容广博,教科书很难充分展开所有内容主题。更何况,小学教科书往往分科编写,结果同一个主题的相关内容常常被弄得四分五裂。换句话说,教科书能给学生的主要是一些相对破碎、梗概式的东西。第二,用教科书教,占据了教师、学生的大量时间。大量正在发生的、非文字形态的、尚未有定论的内容被排除在课堂以外。教科书原本是为了服务教师和学生,但在得到应用以后,教科书在事实上成了教师和学生的主宰。靠一本教科书来学习的学生,仿佛生活在桃花源以内,被隔离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进程以外。可惜的是,早在俞子夷的时代,就已经有教师“始终被一年一本的教科书支配”[17]了。
“教材≠教科书”这个不等式的高明之处在于,当教材和教科书的对等关系被打破以后,教师就通过解放自己的头脑来解放了自己的手脚。他们当然可以继续用教科书,但是再也不必拘泥于教科书那一方狭小的天地,而把来自自然、社会的丰富馈赠置之不理了。“……教科书编者,决不敢在标准以外,别创一格,因为这是审定时决计通不过的。通不过,便不准印行,不许采用……标准统制着教科书,教科书统制着教员。”[18]为了打破诸如此类的禁锢局面,教师至少可以采取以下六种策略,来实现教师与教材关系的转变。
(一) 活用教科书
“教科书贵活用。”[19]与“活用”相对立的是“呆用”,就是守着一本教科书,不管内容匹配学生的程度如何,一步不落、从头至尾地教完。尽管教科书可能有委曲求全、粗枝大叶的毛病,但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仍要使用教科书,那就可以采取“活用教科书”的策略。俞子夷介绍了三类活用教科书的方式[20]: 第一,删改教科书。全体学生仍用同一种教科书,教师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教学的先后次序或者干脆删除部分不适宜的内容。比如,要讲“武昌起义”这一课了,可距离纪念日尚有时日,这时教师就不妨把相应的内容延后。第二,补充教材。教学要用到某些材料,可教科书上恰恰没有,这时教师不妨额外选编一些材料,利用补充教材满足学生需求。第三,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教材内容可以来自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同一班学生准备的教科书可以不同。在教某个学科时,师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交替使用,从不同版本教科书中寻找更适当的内容。比如,班上一部分学生准备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另一部分学生准备儿童书局的版本。同样是人手一册,但是全班有两套教科书备用。[21]这三项折衷的办法,都是在保留教科书的情况下,设法“活用教科书”的策略。
(二) 联络教材
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主要以分科方式进行。但是,在俞子夷看来,“科目不好算是教材的范围,不过是习惯上的一种分类罢了”[22]。尤其是在小学,如果把相关事实分散到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中去,学生学起来容易感到不便[23]。此外,同一本教科书也往往包含若干彼此缺少关联的部分。这样看来,无论是在学科间还是学科内,都出现了联络教材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教材内容的琐碎与割裂。关于学科间的联络教材,俞子夷介绍了两个方式[24]: 第一,保持学科界限,但会把性质有关的教材放在一起教。比如,寒暑表、时钟、经纬度的认识和计算,在当时国语、常识、算术等学科的教科书里都有记载。教师可以预先计划好,避免各科教学内容的重复。在国语课上,可以讲工作、休息、惜阴、守时的观念,在常识课上可以研究时钟的构造,在算术课上可以研究日、时、分、秒的认识和计算。[25]第二,打破学科界限,完全围绕中心问题组织教材内容。比如,中心问题是“家”,教学时就可以分别涉及海滨的“家”、乡村的“家”、城市的“家”、鸟的“家”、鱼的“家”等等。当然,这种方案事实上已经取消了联络教材的必要,因为已经不存在等待联络的分科课程标准和分科教科书了。最后,关于某一本教科书内部的联络问题,俞子夷主张用“故事体”编写教科书,以避免课与课之间前后不连贯的弊病[26]。他做了一个比方: 在章回体小说里,每到章节完毕就会有“要知后事怎样,且看下回分晓”的字样;如果在某个单元学完以后,学生马上心心念念想着与此有关的下一个单元[27],那么联络教材的任务就可以说是彻底完成了。
(三) 补充教材
在《教算一得》中,俞子夷提到了小学教科书的一个常见缺陷: 新内容学完以后,在下个单元往往完全看不到踪影。这种教科书编写法不难理解——下个单元的篇幅毕竟有限,需要集中起来处理新内容。问题是,如果新单元要用到前一个单元甚至前一个年级的内容,就只能假设全体学生都已经掌握完备了。谁能保证这个假设能成立呢?在俞子夷看来,教师要在教科书以外,看到学生还有哪些需求并及时做补充。他写道:“教科书或者因为纸张关系,不便附带旧的材料。那末做教师的应当用些聪明,补充教科书的缺隙。这是教师最重大的工作。呆照教科书讲讲,把应做的题目数告诉学生,不必用活的教师,只须灌好留声机唱片,叫人开唱便行。再省便些,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代替。死用教科书的教师,实在可以说是一架活的留声机罢了。”[28]俞子夷说的“活的留声机”,就是不顾学生程度,一心照着教科书赶进度的教师。从这些教师的角度看,一切仿佛平稳有序、进展无虞,可是因为没有补充教材从旁襄助,学生只能跌跌撞撞跟着教师的进度赶路或者干脆被淘汰,游离在课堂以外。与上面两项策略相比,无论是“活用教科书”还是“联络教材”,重点都是在教科书本身下功夫。当这两种加工策略仍无法满足教学所需时,教师就有必要亲自操刀补充教材。俞子夷甚至认为,在教科书十分恶劣时,废止教科书也不是不可以:“教科书尽可不用,补充读物却不可不看。既经到了这等情形,何勿干脆些,取销了教科书和补充读物的界限!”[29]
(四) 教材地方化
承认教科书可以活用、可以跨学科联络、可以做篇目上的增删改动,这已经极大动摇了教科书的地位。俞子夷写道:“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的生活情形不同,所以选择教材的第二点应注意到本地的需要。”[30]时空两个方面条件的差异都会提出教材地方化的诉求。如果本地盛行蚕桑,教材就可以侧重种桑、养蚕;如果本地主要种植水稻,那么教材就可以侧重种稻、耘田;在种麦的地方,教材应该多用麦子做教材;在工业环境,要注重工业;在商业环境,要注重商业。[31]又比如,战时劳作课的主题应与和平时代不同: 同样是园艺,太平时节可以种观赏用的菊花,战时就可以多学萝卜、山芋、青菜的种植;同样是烹饪,太平时节可以学奶油蛋糕的做法,战时就可以多学一学埋锅造饭。[32]教材地方化和这几项教材调适方案,在精神上完全一致,都是设法让教材更匹配教学所需。在讨论教育中的“划一主义之利弊”时,俞子夷写道:“所贵乎教育者,为其能养成自己活动之人间也。教育者受划一制之束缚,已无丝毫自己活动之地步。被教育者之不能自动,可想而知矣。不能自动者,木偶也。国民类木偶,其国亡;民族类木偶,其族灭。呜呼!划一制者,亡国灭族之教育也。”[33]“以南北延长七千余里之大国用同一之课程、定划一之放假期……”,就是划一主义的表现之一。教材地方化以及上述各项策略,都可以看作反对划一主义的具体举措。一个例外是,对于国语学科俞子夷是支持统一教科书的,他的目标是“竭力使全国的语言统一,并且设法使方言标准化”[34]。
(五) 乡土教材
俞子夷对于乡土教材的讨论,可以认为是“教材地方化”的一个特例,也可以认为是“活用教科书”的一个特例。“教育的重心在初等教育,中国初等教育的重心在乡村教育。换句话说,中国的乡村教育有救,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35]因此,乡土教材不只与乡村教育有关,也与中国教育的前途有关: 乡土教材关心教材与乡村学生的配合,而教材与学生的配合是中国教育的普遍难题。与一般的认识不同,俞子夷不认为乡土教材能自动引起乡村学生的学习动机。恰恰相反,因为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物,学生反而容易感到乏味。怎么办呢?俞子夷的办法是“要在熟悉中挑拨到生疏”。比如,饭锅要加盖、不加盖饭煮不熟,这些大家都知道。可是,如果追问一句为什么,就未必人人都能说得清其中的道理[36]。出现不明所以的地方,学生就有了学习的愿望。再者,编制乡土教材、让学生有机会学习与乡土有关的内容,这本身不是教学的终极目的。俞子夷写道:“乡土不是我们教学的终极目的,要是我们的教学,只限于乡土,那末将来的人民目光短浅,地域观念便做了封建思想的基础。只知有家乡而不知国家的人民,不是一盘散沙,无由团结!从乡土推到宇宙,才合了由近及远的原则。”[37]“总之,经验是有连锁性的。从古到今,从家庭到世界,从个人到全人类,都相关联。一定要拿远的古的算是教材,固然错误,只拿近的现在的算是教材,也是一样的错误。经验是扩张的,由近及远,由今推古,才合教材范围扩张的原则。”[38]这是编制乡土教材的原则,也是一切教材调适工作的原则。
(六) 弹性编制
与上述五者不同,“弹性编制”不直接针对教材本身下功夫,而是通过改变学生编组的方法,改善教材与学生个性的匹配程度。俞子夷写道:“在个性差别没有被人注意的时代,先产生班级教学的制度,跟着便产生了班级教学中应用的同一的教科书。近年来班级教学的缺点,因个性差别的发现而显露了。改革的方案如分团制,导尔登制,文纳特卡制等等,也渐渐的盛行了。然而班级教学用的教科书却依然存在,封面的学年学期却依然印着。要是个性差别是我们承认的事实,那末封面上的学年学期,非立即取消不可。采分学年学期,是和个性差别不能并立的。”[39]一直以来,小学多会在每个学科指定一种教科书。因为学生程度互有参差,所以马上出现了教科书匹配何种学生的问题。没有教师会承认自己的工作只面向部分学生,善良的教师总会设法让全体学生都能明了。可是,全体学生都能明了的教材不是恰恰有可能过分简单了吗?上面那段俞子夷的话,表达的就是统一教材与学生个性的冲突。为了解决班级授课制的这一难题,需要改变按自然年编制学级的常规做法,让学生在校内可以方便地找到匹配其能力水平的班级。这时,虽然教科书仍旧统一,但是因为同一班学生的能力水平更趋于一致,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问题的严重性。
三、 俞子夷的小学教材实践
无论是作为小学教师、小学教学法的实验者,还是小学教材的编写者,俞子夷都反对把“教材”等同于“教科书”。这一思想支持他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教育创新——作为小学教师,他通过“活用教科书”等策略,让教材适应学生程度;作为小学教学法实验者,他通过“乡土教材”等策略,让学生带着目标去学习;作为小学教科书编写者,他强调“活用教科书”“补充教材”等策略,让学科内容更匹配学生需求。总之,俞子夷的教材实践和教材思想是始终一贯的。
(一) 个人教学工作中的教材实践
俞子夷的第一份教职开始于1907年(时年21岁)。次年,他在上海浦东川沙龙王庙青墩小学教常识时,得到了省视学侯鸿鉴的激赏,被评为“通省之冠”。侯鸿鉴当日看到的,就是俞子夷使用乡土教材进行教学的情景,在学级组织上也已经有了单级复式的雏形。以下是俞子夷的回忆:
前清时的小学,初级原没有什么常识一类的科目。高级里才有理科史地。我自己爱好理科,所以一到青墩便加设理科。这是违背章程的。但是省视学亲临视察,并不申斥,反而说我们加设得合理,教得好……教科书,当然是不用的;复式用的教科书更找不到。试行起来,并不发生困难。白扁豆、南瓜、鱼、蛇,就地取材,俯拾即是。我愈教愈开心,学生也愈学愈高兴。[40]
当时研究的题目,都是就眼前看见的发生。水桥边竹篱上的白扁头为什么会爬得上去的?碗大的蕃瓜花,何以会结出石础般大的瓜来?何以蕃瓜要晒老了吃,才有甜味?这是农作物上发生的问题。补习班人数不多,室内研究,室外观察,多很便利。棉花田里,差不多天天有我们去的足迹。花萎了,果结了,果绽了,絮出了,天天有种种的报告。他们天天带着实在的东西来上学,还有好多心上的疑问提出,棉果绽了生絮,植物本来要絮什么用的?我们人类怎样的利用棉絮?这种问题,便是一个例子。[41]
1938年,浙江大学避战西迁,俞子夷因故留在金华,借住在杭师文牍员王汝铨家。主家的儿子王渭铨当时12岁,读五年级下学期,但是算术水平还不到三年级。俞子夷在暑期的49天里,每天抽出30分钟左右帮他补习。对于这段经历,俞子夷有过概括:“我的补习工作,差不多完全在调整教材进程和他能力间速度的平衡。”[42]换言之,他的主要经验是“活用教科书”,让教材“适合程度”,既然学生程度没到五年级,教师就不要怕麻烦,要让学生有机会从更低年级内容补起来。在《教算一得》中,俞子夷把补习比作治“肠胃病”,致病原因在于教材,治病的办法也要从教材里找:“教材不合学生消化力,学生已犯了严重的肠胃病。补习是一所疗养院,一面用药治疗,一面使消化力渐渐恢复。”[43]如果学生已经犯了“肠胃病”,那么教师给再多富含营养的东西也是白费。在这种状况下,教师按部就班地照着教材教,学生只会“病”得越来越严重。(2)《教算一得》中体现的学习原理,可以概括为《学记》中的“学不躐等”。参见: 丁道勇.把握学习的节奏: 俞子夷补习算术的原理[J].中小学管理,2015(4): 53-54。俞子夷看到,王渭铨升入五年级下学期时九九表还未掌握。于是,他准许这孩子在计算时查九九表,直到自己嫌麻烦宁愿记熟时为止。这是俞子夷给他服的第一味“药”。这大致属于上文谈到的“活用教材”以及“弹性编制”,目的是让学生恢复“消化力”。当然,如果教师一早就能注意,不让教材和学生脱节太久,始终让教材合乎学生需求,那问题就不至于那样严重了。
(二) 教育实验中的教材实践
在回顾抗战期间的经历时,俞子夷概括了自己教育思想上的两个新发展:“(1) 国化(民族化),取洋之长,以补国之短。移植必服水土,乃能生根。全盘洋化或洋化过度,不合国情,所长变为所短,无益而有害。(2) 接近乡村之日久,故知须乡村化。国化而只适大城市,对绝大多数乡村仍无裨益,则国化不能彻底。”[44]这里提到的“国化”和“乡村化”代表了俞子夷对于各种引进教学法的总体态度。可以想象,有这样的态度,俞子夷在做教育实验时不会过分纠结是否正宗的问题,而会因应国情、校情、学情做必要的调适。
俞子夷写道:“没有引导,听凭学生做去,不是设计教学法。硬迫学生去做,指挥学生,命令学生,也不是设计教学法。引导学生向上发展,才是真正的设计教学法。”[45]这段话区分了三种教法: 第一种教法强调“做”,关心学生是否动了起来。至于行动的标准,这不是教师关心的。比如,在东大附小试行设计教学法的第一年(1919年),“教师看见儿童能够自由活动,以为已达试验的目的,表示愈分的满足。因此,儿童作业,因无确定目的,工作结果,往往今天和明天,前月和后月,常在同一水平线上,没甚进步发展可说”[46]。第二种教法强调“学做”,关心学生的操作是否达标。可是,“若是某种作业仅能把本身的作业完成,不能从这作业里发生新活动的动机,那末设计的学习和徒弟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了”[47]。在学徒制当中,师父关心徒弟做得对不对,但是不太关心徒弟的心智发展。这就是一种“学做”的情况。第三种教法是“从做中学”,这时,行动有一定标准且有教师指导。最终目的不是“做”本身,而是更有利于“学”。俞子夷又写道:“设计教法的名称,未必能包含一切真理,但是教育应使学生自找办法实现目的,确实值得采用。我们在独断教育与自由教育的歧途上彷徨着,差不多把这三十年的光阴,浪费了大半,实在可惜!今后建国,必须迎头赶上。”[48]这两处评论,可以对照着看,所谓的“自由教育”,往往只强调“做”,或者至多关注到“学做”的层次,不关心“从做中学习”。这就放弃了设计教学法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让学生在完成有目的活动的同时完成学业。此时,教师不必扮演强迫者的角色,反而有可能成为学生完成活动时的咨询者、支持者。师生携手并进,共同对付眼前的难题。
设计教学法的教材,自然不止各种“做”,还包含有助于“做”、可以扩展“做”的一切实物、书本。有人提出困惑,认为在施行设计教学法以后合用的课本很难找。俞子夷回答说:“行设计法以后,不是死照了课本学的。所以只要课本里有可用的资料,便拿来做参考。”[49]在别处,俞子夷写道:“设计的教学法,一方面是教材的新组织,拿生活环境做根据的,不是拘守科目的。设计的教学法,他方面是方法的一种新精神;把学习的原理,实地去应用,学生的作业,具有真正的目的。”[50]可以想象,设计教学法一定包含“活用教科书”“联络教材”“补充教材”等策略。学科边界、教科书是设计教学法首先要打破的东西。
(三) 教科书编写中的教材实践
俞子夷曾多次编写小学教科书。根据《俞子夷教育论著年表》[51],他编写、出版过的教科书类的作品有: 《初小新体算术》(商务1916)、《幼稚园小学校音乐集》(商务1924)、《算术练习书》(大东1934)、《电的常识》(中华1936)、《发报机及播音机的造法》(中华1940)、《初中物理》(未出版)、《初中平面几何讲义》(未出版)、《农村算术》(正中1944)、《初级珠算教材》(自印1947)、《算术(小学课本)》(大东1949)、《算术课本》(人民教育1952)。下文就以他编写的三套小学算术教科书为例,呈现他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中体现的教材思想。
1924年版《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第三册的开篇写道:“一个日本的女小孩八重口述: 1. 今天是三月三号,是日本洋娃娃节期。从这天起日本国里所有的洋娃娃要陈列三天。那几天是洋娃娃的节期?2. 八重有10个娃娃是她自己的,17个是她母亲小孩时候的,27个是她祖母的,50个是她的曾祖母的。她共有洋娃娃多少?3. 八重的洋娃娃有许多种类。那个像皇帝的是94岁。八重今年7岁。洋娃娃比八重大几岁?4. 她有四打小孩形状的洋娃娃是顶好玩的。里头有9个像男孩,5个像婴儿,其余像女孩,女孩形状的洋娃娃有多少?5. 今天八重要有一个新的洋娃娃了。她的父亲给她16钱(日币)。16钱值中国币一角二分。她的母亲给她12钱。12钱值中国币多少?八重共有钱多少?”[52]借助八重小朋友的故事,日期、两位数加减法等算术问题都得到了呈现。
又比如,在1947年版新小学文库中,俞子夷编写的五、六年级(每个年级各四册)算术工作书的题目分别是《远足圆明寺》(整数)、《湖口百货店》(复名数)、《白乐小农场》(面积)、《小毛过生日》(分数)、《庆祝双十节》(整数)、《预备过新年》(复名数)、《喜儿卖老饼》(分数上)、《娃娃伤了风》(分数下)。诚如标题所示,每册书都包含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相关算术内容寓于其中。以六年级第四册《娃娃伤了风》为例,开篇的故事就充满了童趣:“瑞宝从学校里回家,看见他玩的娃娃躺在窗外的桌子上。他对妈妈说:‘今天风很大。我的娃娃睡在这里,伤了风了!’妈妈笑着说:‘要不要请大夫替娃娃看病呢?’瑞宝说:‘好的。’//他们就扮演医生看病了。小林扮医生。他诊了娃娃的病说:‘不要紧的。喝两天药水就会好的。’小安扮演开药房,替瑞宝配药水给娃娃喝。他找了旧的药水瓶,在瓶里头装了些水。他对瑞宝说:‘分做两天喝,每天喝三小格,每次饭后喝一小格。’……”[53]当然,这个故事不是说说而已,接下来的分数加减法、分数化简等内容都要从“娃娃伤了风”这个故事牵引出来。
最后一例,来自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算术课本》。这套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供应的第一套小学数学统编教科书。它的前身就是俞子夷在大东书局出版的《算术课本》。这套书在编写风格上,已经和俞子夷此前编写的教科书有了重大区别,比如不再用儿童故事作为主线。不难理解,在应用诸如“八重口述”“娃娃伤了风”这样的故事时,数学知识要见机插入才不会显得突兀。结果,学生在同一节课上可能会先后遇到加法、减法、除法问题。1952年这套《算术课本》借鉴了苏联教科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知识必须是完整的,有系统的,而不是零星的,杂乱的”[54]。在另一处,俞子夷把这套教科书与此前的教科书做过比较:“编排进程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过去的情况,恰和这原则相反,往往事前丝毫不作准备,突然提出一种理论。”[55]尽管不再以儿童故事为背景,但是这套书仍旧贯彻了俞子夷的一部分教材思想。比如,这套《算术课本》初小第五册开篇就要求教师在教新课前先了解学生对此前内容的掌握情况:“(一) 在开始进行教学前,应先了解学生对于前二册的内容,有哪些已经学得相当熟练,有哪些只知道一些大概,有哪些是一知半解或完全不知道。(二) 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再把本册的内容作一个进程的大纲;预定哪部分可以照本册的进度进行,哪部分还得先补充了才进行。脱节处可以用前二册的材料补习。重复处如学生已经完全明白,可以加快速率,删节一部分的练习,但不宜全部跳过。”[56]这是教科书编写者在主动要求教师“活用教科书”,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实际设计“补充教材”。这是俞子夷长期、一贯的教材思想。
除以上三组教材实践,俞子夷还表达过对于战后教师生涯的展望:
假若复员后我仍当教员,不论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无论上什么科目,我都不用单纯的读书、讲解、说明或讲故事算是教学。第一步,我当和学生商量,共同或个别做一件事;做一件于自己个人或公众团体有利益的事。第二步,我帮助他们用种种方法做成功这件事。倘若书可以帮助他们,便领导他们读书。倘若讲解、说明、故事或示范等等可以帮助他们,便给他们讲解、说明、讲故事或示范。
休息是必须的,娱乐、运动、消遣更不可少。但是几十分钟一课,几分钟休息等等呆板的日课表应当废止。专心工作,到必要时散心休息。另外,不但没有上课退课的信号,就是出入教室的行动,也不用军队式的管制。机会是有益的。定期的、临时的都应当有,但是仍须先和学生商决了再实行。
教室内,除集会外,不限定用呆板的排列,应当视工作的需要决定布置的方式。我们必须打破入学就是读书的旧观念。可以在田里耕种一整天,可以在工场里做工一整天,可以在外面参观一整天,也可以部分人排演一个上午或下午。[57]
这三段文字不再是回顾,而是对于未来可能有的教学实践的展望。可以看到,俞子夷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不只是教“书”的愿望,但是“书”仍旧是他期待的那种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还未到来的阶段,教室内外、学校内外、书本、实物都可以成为他的教材。毫不夸张地说,“教材≠教科书”这个公式始终贯穿在俞子夷的小学教材实践当中。
四、 结论与讨论
和俞子夷不同,在更多教育讨论中人们还是会不加区分地使用“教材”“教科书”“课本”。比如,在倡导教师“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时,就恰恰是在把“教材”等同于“教科书”。当教师缺少专门概念去指称“教科书”以外的其他“教材”时,即使他们认为教科书以外也能找到有价值的课程资源,在行动上也倾向于放弃对“教科书”以外的“教材”的关注。当教学的内容范围蜕变成“教科书”时,教师也被“教科书”紧紧束缚住了。自俞子夷的时代直至今日,把“教材”等同于“教科书”的观念,就一直是束缚教师手脚的东西。
在分析教育哲学领域,谢富勒(Israel Scheffler)把教育讨论中的各种定义区分为约定型定义、叙述型定义和计划型定义三个类型[58]。其中,计划型定义的用意“不在传达实际用法”,而是“作为实际行动的前提”。对照这个分类框架,可以说俞子夷是通过一种对“教材”的计划型定义,挑战了关于教材的一种既定用法(叙述型定义)。“教材≠教科书”这个公式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允许教师跳出“教科书”来思考“教材”问题。这个公式完全可以用来统合俞子夷在教材领域的众多主张和行动。正是基于此,本文把“教材≠教科书”视为俞子夷在小学教材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创见。这种计划型定义在推动教师进一步行动上的可能价值,是本文所期待的。
当然,学习困难未必都能靠着在“教材”方面的举措来解决。实际上,俞子夷本人就经历过由重教法到重师生关系的转变,他在《教算一得》中记录的那段补习经历就是一例。正因为如此,俞子夷说教师工作是“一种领导”,而要实现这种“领导”,首先就要“使他(指学生)信仰”[59]。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的意思吧。不过,换个角度想,师生关系与教材、教法又何尝没有联系?一个眼睛只盯着教科书的教师,在师生关系上恐怕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个摆脱了教科书的束缚、眼界足够宽广的教师,更有可能建立彼此相得的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