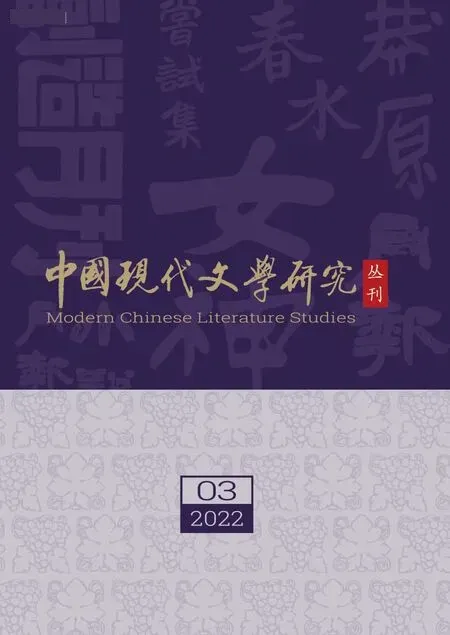营垒的澄清
——重识1930年代小品文论争
方 园
内容提要:发生在1934年春的小品文论争,对于论争双方均具有澄清文学立场与写作态度的重要意义。对林语堂来说,这次论争是他由同路人逐渐转向右翼的起点;对“左联”来说,这次论争是他们坚定其文学立场、澄清其文学态度的重要一步。双方由此分道扬镳。
1931年秋至1935年冬,是“左联”在理论与行动上采取攻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左翼文坛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将营垒分清”①鲁迅:《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的文艺论争。1934年春在左翼青年与林语堂之间展开的小品文论争,就是其中的一场。
一 论争前:1932—1933年
要讨论小品文论争,首先必须追溯林语堂在1932年至1934年文艺立场的变化。1932年9月,《论语》创刊,林语堂任主编。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林语堂任中央执行委员。此时的中国连年内战,水灾空前,并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对外卑躬屈膝,对内以横暴手段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与爱国的言论。舆论凋敝至极点。《论语》的创刊,意在打破沉默。同盟的成立,旨在援助因爱国而获罪的政治犯,为民众争取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一切真正民权之利益。
民权同盟成立后,林语堂以他的法治主张声援民权运动,指出当时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在于有人治而无法治。官僚权力缺乏法律制约,致使官吏常常以权肥私,虽犯罪而不受制裁。人民的言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因而人人明哲保身,以莫谈国事为训,“结果遂有四万万同胞如一盘散沙之现象”,公民少而私人多。林语堂由此提倡韩非法治学说,认为中国“得法治则治,不得法治则乱”①语:《半部〈韩非〉治天下》,《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论语》是林语堂发表其法治主张的主要阵地,林语堂在其中发表的相关文章有《半部〈韩非〉治天下》《脸与法治》《又来宪法》《变卖以后须搬场》《适用青天》《谈言论自由》《梳,篦,剃,剥,及其他》等。②见《论语》第3、7、8、10、11、13、17期。而法治主张也成为此时《论语》办刊的核心思想,林语堂在第3期的《编辑后记》中就明确表示:“论到思想,我们是反对儒家仁义之谈,而偏近韩非法治。”
此时的《论语》,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在文学上提倡幽默。然而,虽然自称“以提倡幽默为目标”③青崖、语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但它对于幽默做出的两种解释,却都接近于讽刺。第一种解释认为,幽默是视世察物,别具洞见,观点透辟,不落窠臼,“以其新颖,人遂觉其滑稽”④青崖、语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受《论语》推崇的萧伯纳,正是这一意义上的幽默大家。萧伯纳以其善于撕下绅士淑女们的假面而被鲁迅赞为“伟大的感叹号”,可见幽默的这层含义离“温柔敦厚”颇远。此外,幽默还指一种写实主义。这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社会重浮言而不务实际的风尚,尤其针对当局在宣言、通电中满纸正经救国策,在行动上却潦倒无比的现象。林语堂认为,只要旁观者把中国政治、教育等各界的言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坦白地说出来,就自成其幽默。⑤《我们的态度》,《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幽默的这层含义,战斗意味更其鲜明。此时的《论语》,泼辣锐利,富有生气,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论语”与“古香斋”两个栏目,前者是政治、社会新闻之短评,在嬉笑中针砭时弊,后者是荒诞不经的社会、政治新闻之摘录,虽是述而不作,批判意味已彰。
《论语》锐利的风格一直保持到第19期。在这一期上,尚有林语堂观点激进的《民众教育》与《郑板桥共产党》,前者指示教育普及之重要性,后者夸赞郑板桥的名士骨气,说他是个“最普罗”的作家,假使“生于今日,必为共产党无疑”。这期杂志出刊于1933年6月16日。两天后,6月18日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杨杏佛(铨)遇害。7月1日,《论语》第20期出刊,风格大变。发表在第20期上的《不要见怪李笠翁》,是林语堂态度转变的标志。这篇文章为李笠翁辩护,认为笠翁在文字狱层出不穷的乱世选择避祸自保,情有可原,因为在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中国,“骂笠翁不效方孝孺、杨继盛”,无异于“劝笠翁伸首待斩。须知斩首在旁人虽好看,可以街巷为虚,而身历其境者,却甚觉得无谓”。从此之后,林语堂自敛锋芒,以图保全,不再谈论政治,改谈大暑养生、避暑之益,讲他怎样买牙刷、怎样写“再启”……这些文章,并不如一些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无聊低俗,它们毕竟出自林语堂之手,清新可读,而且与他在《论语》初期写的批评学分制教育的文章一起,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有着一贯的主题:批判中产阶级文化。
林语堂转变后,《论语》的风格随之变化。发表在第21期上的《谈女人》,表明《论语》同人“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此后,幽默被重新定义,成为超脱是非的人生态度的代名词。对幽默重新作出解释的关键文章,是发表在1934年初《论语》第33、35期上的林语堂的《论幽默》。这篇文章将不计是非利害的人生态度称为幽默,又将幽默分为讽刺与闲适两种,前者酸辣有余,温润不足,后者淡然自适,有孤芳自赏之清高,无激越衷愤之尖利。林语堂推崇的是后一种闲适怡情的幽默。这篇文章出来后,“幽默”与“闲适”几乎成了同义词,它们不仅指文学上的一种笔调,更代表一种从容超脱的人生态度,是林语堂对于自己从战斗者到“隐士”之转变的自辩。
“幽默”既已“闲适”,不久后,专登闲适小品文的《人间世》的创刊,也就顺理成章。
二 小品文论争:1934年春
《人间世》创刊于1934年4月。这是一本现代隐士的同人杂志,它以超逸的隐士精神为思想之核心,以恬淡的归隐生活为杂志之内容。登在创刊号刊首位置的,是现代隐士之代表京兆布衣知堂先生的近影,以及知堂自述隐者心境的《五秩自寿诗》。周作人在诗中以蛇在严冬的不得不蛰伏,比喻自己在黑暗环境中的不得不隐居,以颇为风雅的“玩骨董”“种胡麻”,颇为放诞的“咬大蒜”“拾芝麻”,概述其隐居生活。
创刊号一出即引来左翼青年的批评。批评直指《人间世》的超逸风格。在首篇批评文章——埜容(廖沫沙)的《人间何世?》中,有自寿诗的和诗一首。埜诗沿用周诗中蛇的意象而改变了意象的含义,指出隐者的清高与无奈背后,另有“自甘凉血”的一面,指出风雅放诞的归隐生活,实质是“怕惹麻烦爱肉麻”。①埜容:《人间何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4日。
古董的《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对文人的“隐”表示同情,但也忧虑这高逸的隐士文化,将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造成“悠悠然”的社会风气,致使青年男女“工愁善病,弱不禁风”,“没有一点刚强的气魄,深邃的思想”。②古董:《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3日。
左翼的批评除指向隐士精神及其社会影响外,还涉及《人间世》的内容。《人间世》的《发刊词》自诩其内容无所不包,“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但创刊号所谈无不琐屑,给人只见“苍蝇”不见“宇宙”之感。③埜容:《人间何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4日。左翼青年于是发出了“欲行大道,莫示小径”的劝告,认为如果要在文学上有所提倡,还是提倡伟大的东西较有意义,“故作仁人义士,摩顶放踵,虽然可以不必,但坐在黄河决口里犹自飘飘然,却未免使人黯伤”④大野:《关于小孩》,《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6日。。
左翼的批评促使主编林语堂起而为《人间世》辩护。关于杂志的内容,林语堂认为,《人间世》好谈“苍蝇”并无不妥,因为琐屑的话题自有其谈论的意义,小品文不会因为受到左翼的指摘而减损其价值,指摘者反而暴露了自己是一群好谈世道人心却不近人情的假道学。⑤林语堂:《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日。论及社会风气,林语堂表示,他的创办《人间世》,不过是随性所近有所提倡,并非要使小品文成为文学正宗。虽说中国效颦者多,一家提倡,家家跟风,但社会风气之责任不该由初倡者来负。⑥林语堂:《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日。关于《人间世》的思想,林语堂认为,隐士精神本无不妥,周作人诗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世间俗人”不懂得此诗的“寄沉痛于幽闲”而妄加訾议。①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6日。林语堂将鄙夷“苍蝇”好谈“宇宙”,好将文学与社会风气、国家兴亡挂钩的左翼批评总的称为“方巾气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批评“只能诋毁,不能建树”。②林语堂:《方巾气研究》(三),《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3日。
这次论争的主要文章集中发表在1934年4月14日至5月9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林语堂写有《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周作人诗读法》《方巾气研究》。左翼方面的文章除前文引到的三篇外,还有胡风的《“过去的幽灵”》,吴容的《论“天真”》,痰迷的《“请教先生‘两’首诗”并序》等。除《自由谈》外,左翼的批评文章还散见于各种报刊,这众多文章之中,确实杂入了个别不能切中要害甚至夹杂恶语之作。不过,左翼的批评虽然存在问题,但总体而言,立场明确、坚实,其中不乏“热心人的谠论”,亦有青年对于前辈的诚意劝谏,并非“只善摧残”。其中也有文章正中隐士之痛处,并非不懂“寄沉痛于幽闲”的“伧夫竖子”的妄加訾议,不是一句“方巾气的批评”所能抹杀的。相比之下,林语堂辩护的理由反而显得薄弱。然而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此时距林语堂的思想转变不到一年时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重构坚实的思想体系并为之辩护,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一场由左翼青年引起的论争,并未能将林语堂拉回战斗者的阵营,只是再次确认了他的隐士立场,同时也暴露出这一立场缺乏坚固的思想体系作为后盾。这促使林语堂在论争结束之后,依旧以左翼批评家为隐性的论争对象,继续进行着一场持久而无声的自我辩护,并在这样的自我辩护的基础之上,调整他的政治立场,重建他的思想价值体系。
三 论争后:1934—1936年(上)
初创时的《论语》杂志,以进取的韩非法家为思想之根基,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在文学上提倡倾向于讽刺的幽默。当杨杏佛遇害后,林语堂决心不再谈论政治,幽默也随之变为超脱是非之意。但此时林语堂的超脱立场尚不具有十分明确的含义。比如,这样一种“寄沉痛于幽闲”的立场,“沉痛”占几分,“幽闲”又占几分?超脱是非的立场,超脱的是哪一种是非?这些都不明确。最为重要的是,林语堂立场背后的思想根基不明朗。这样一种含混的立场,显得既可进,又可退,使论者难以把握。而论争中左翼青年在评价这种立场时,确实也表现出把握这种立场的不易。比如,胡风的《“过去的幽灵”》表达了对周作人的隐士立场的困惑,不知周作人是真的决心不再干涉世事,还是说,他的隐士立场本身就是对于社会黑暗的不满和反抗。①胡风:《“过去的幽灵”》,《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17日。古董的《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对隐士立场中的某种危险倾向进行了预警,但对隐士立场本身依旧表示了理解与同情。这些都从侧面说明着林语堂立场的含混性。
1934年春的小品文论争,加速了林语堂思想观念与政治立场的明朗化。在论争后,“近情”哲学与“无为”思想,正式取代韩非法治,在林语堂的思想中占据新的主导位置。超脱是非的隐士立场,也具有了比论争前更为明确的含义。
林语堂阐释下的近情哲学有三大要义,第一是捍卫人的个性,第二是捍卫思想的自由,第三是以情理对抗主义。
林语堂认为“方巾气”的一大特点在于压制人的个性。他将左右两派文人对于《人间世》的批评分别概括为“清谈亡国”与“游山碍道”,认为这样的论调是继承了宋儒的真道学的今儒的伪道学论调。②语堂:《游杭再记》,《论语》第55期,1934年12月16日;语堂:《我不敢游杭》,《论语》第64期,1935年5月1日。在林语堂看来,人的心灵总是一张一弛,“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愿与潇洒”。哪一方面消灭都是一种不幸。然而不论古之真道学家,还是今之伪道学家,都只注重人生严肃拘谨的一面,压制潇洒放逸的一面。①林语堂:《说潇洒》,《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拘泥虚伪的人生观,使古今腐儒不敢展露性灵,人生乐趣全失,为人为文都了无个性。②语堂:《说浪漫》,《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因此,林语堂着重为人生潇洒放逸的一面辩护,为真实的个性辩护,他认为现代的人生观不该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应该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③语堂:《小大由之》,《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除压制个性外,林语堂还指出古今道学的另一种恶影响,那就是追求单轨思想、一道同风,欲“纳天下人之意见同于自己的意见,纳天下人之议论于自己的法轨”,“必欲天下人之耳目同一副面孔,天下人之思想同一副模样,而后称快”。林语堂称此为思想上的“缠足运动”,认为这将造成思想上的“阿斗”与“顺民”,使人仅有门户之见,失却自主思考、自辨是非的能力。④语堂:《说大足》,《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他因此反对政治上的一切主义,不论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们不仅意味着政治与军事上的独裁,而且意味着思想上的极权。林语堂也反对一切以主义为根据的文学。他认为文学是个人心灵的自由创造,文学的作用并非教化读者、统一读者的思想,而是真实地反映复杂的人生,使读者“带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一点”。而一切以主义为根据的文学,把复杂的人生“硬塞到一种主义中去”,“把文学放到政治的仆从地位”,这会限制“人类心智的自由创作”⑤林语堂:《米老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使文学失去其“通明和博大”⑥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冯克利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那么如何反对一道同风、捍卫思想自由?林语堂给出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答案:以情理对抗主义。情理,即情与理的调和。讲情理,意味着在处理事情时将情理置于道理之上,依靠健全的常识作出判断,而非仅仅遵照理论。这样一种讲究情理的精神,是有着中庸文化传统的中国最所不缺的。中庸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保守性,这在林语堂看来是一种优势,它使得中国人在思想上成为天生的自由主义者,本能地抵斥彻底的理论。林语堂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因为它对生活的设计“太制度化、太不近人情”①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85~86页。,不符合中国人调和的性格。“即使发生共产主义掌权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宽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②2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85~86页。
林语堂在1934年至1936年提出的小品文、语录体的文学主张,均以近情哲学为精神内核。理解捍卫思想自由、崇尚情理与个性的近情哲学,是理解林语堂文学主张的关键。
林语堂提倡小品文,开始于《人间世》的创刊。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小品文被定义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一种“个人笔调”。林语堂根据笔调的不同,将散文分为学理文与小品文两种,学理文是“载道派”,做“正经文章”,谈“廓大虚空题目”,写“陈言烂调”;小品文是“言志派”,“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无拘无碍”。③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人间世》第6期,1934年6月20日。这样一种二分法,显然受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影响。但林语堂又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特色,指出小品文作家之所以敢于打破桎梏,解放性灵,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是现代的人生观,是观察的,体会的,怀疑的,同情的,很少冷猪肉气味,去载道派甚远”④语堂:《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人间世》第24期,1935年3月20日。。近情的人生观,可以说是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的内在精神。
林语堂的提倡语录体,开始于1933年10月。最早的相关文章是发表在《论语》第26期上的《论语录体之用》和《可憎的白话四六》。据林语堂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提倡语录体,是因为白话做文虽然“天经地义”,然而“今人做得不好”,“噜苏”而“浮泛”,他正是要纠正白话文的这一弊端。所谓的语录体,是模仿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文体。林语堂认为语录体结合了口语的平易与文言的简练,“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
学术道德学术研究的第一特征是科学性、严谨性和严肃性,“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学术活动中,研究生必须做到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辛,勇于攀登,这是学术研究者的内在动力和要求,也是学术诚信的本质特征。有些研究生在学术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在学术活动中往往浅尝辄止,态度浮躁,不深入探究和思考,于是乎出现了剽窃、照抄别人论文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等不良行为。
对于林语堂自述的提倡语录体的原因,论者不宜过于较真。事实上,林语堂在1933年10月的提倡语录体,与他此时的谈女人、谈养生一样,是避祸手段之一种,称不上是十分严肃的文学主张。提倡半文半白的语录体,与将内含不少激进文章的《大荒集》做成线装、以仿宋字排印一样,都是林语堂给自己涂的一层政治保护色。要等到小品文论争后,尤其是在大众语运动展开后,语录体主张作为大众语运动的反对意见,这才开始具有严肃的文化意味。
大众语运动发生在1934年夏秋间,然而它的核心思想,早在1931年至1932年就已由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文章中奠定。要而言之,“大众语”被左翼文人提出,同样是出于对白话文的不满,但这不满,并非针对它修辞上的不通,而是针对它的使用者的狭窄,它的与一般大众的无缘。瞿秋白认为,文学应该被交给大众,为此应该有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应该通过这场新的文学革命使民众获得参与“文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工具”,得到最大限度地“接近文化生活,参加文化生活的机会”①宋阳:《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识字者“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②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的当时的中国,语文的简化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着重讨论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简化问题。参与讨论的左翼文人的意见较为驳杂,但他们在两点上是一致的:第一,他们都沿着瞿秋白提出的新的文学革命的思路讨论问题;第二,他们都希望通过提倡大众语把文字、文学、文化交付给本应得到享有它们的机会的大众。
大众语的讨论展开后,林语堂以此为契机,对自己早已提出的语录体主张进行完善、总结,以此作为对于大众语运动的一个回应。③林语堂提倡语录体的文章,写于大众语运动后的,有《一张字条的写法》、《大众语论坛·林语堂先生的复信》(《社会月报》第1卷第4期)、《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与徐君论白话文言》等。写于大众语运动前的,有《论语录体之用》《可憎的白话四六》《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语录体举例》《关于〈中郎尺牍〉复黄杰书》等。林语堂的总的观点,是认为打倒白话而另立大众语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纠正白话文修辞上的“噜苏”“浮泛”的弊病。如何纠正?林语堂提供的方案是:洗炼白话,调和文白。中国的古文典雅、抽象,白话矫健、具体,两相调和,加以锻炼,必有极灵健的文学语言。④语堂:《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最为关键的是他把讨论的范围局限于文体,以此回避大众语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学革命的层面。这与林语堂反对一切以主义为根据的文学的态度是一致的。既然服务于主义将使文学失去其“通明与博大”,为了保全文学,最为安全的做法自然是主动将文学与政治隔离。不过,这样的做法固然能够确保文学的纯粹性,但能否保全文学的通明与博大,却显得可疑。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将文学隔离于政治,即等于将文学隔离于时代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使文学所能谈论者仅剩下“性灵”。林语堂对此是完全自觉的,在写于1934年6月的《行素集》序言中,他承认自己“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但他又对这个“牛角尖”表示了满意,因为:“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制,遂亦安之。”
四 论争后:1934—1936年(下)
在1934年至1936年,除近情哲学之外,在林语堂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道家主张逃避尘世,归返自然,以无为养精蓄锐,延年益寿。这一思想主导着林语堂的文学与政治行为,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林语堂大加提倡的近情哲学。甚至可以说,近情哲学只是此时期林语堂思想的表层,无为思想才是真正重要的内核。林语堂无为思想的流露最为集中的一处,是写于1934年春夏秋三季的《吾国与吾民》。这本书的统领思想,正是道家的无为思想,而林语堂又赋予这种思想以极具诗意的表述:新秋精神。
《吾国与吾民》写于中国“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①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身处于这黑暗之中,林语堂对于国家的命运作出了最为悲观的预测,认为祖国已经迈入它生命的秋天,死亡的严冬即将来临。林语堂并不预备做任何的挣扎与反抗,而是以宿命论者的坦然接受了这一命运,并且顺着“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②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自序》,《人间世》第40期,1935年11月20日。,决定抓住寒冬之前的最后时光,尽情享受生活:
我们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生活;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以备冬天之不测。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被剥夺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①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41、42,47~52页。
这样的新秋精神,在同一本书中更为直露的表述,是借鉴李四光博士的论文《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每八百年一个周期,每个周期都以外族入侵开始。在林语堂执笔的当时,中国正处在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端。在林语堂看来,外族的征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也许是必要的”②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41、42,47~52页。,因为它能平息中国内部的纷争,造成强有力的统一,从而促成文化的繁荣,新的血统的注入也为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活力。③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41、42,47~52页。
这种面对外族入侵时无为而圆通的态度,使林语堂颇以坚决抵抗者为迂腐。在写于1934年8月的《山居日记》中,林语堂提到了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本书——《甲行日注》。这本书的作者叶绍袁,身历明末清初之乱世,当国破家亡之际,不愿削发为虏,宁愿去发为僧。这被林语堂认为是读书读坏了心胸:
读《甲行日注》,见初段辞别家人入山甚苦,尔时稍读书明理之女人,即知劝儿剃发为僧,不可剃头事虏,回想若钱谦益辈益不齿为人类矣。大人先生行径本来如此,可见书不可读得太多,可读坏心胸也。
在林语堂写于1934年至1936年的文章中,颇有几篇对日本的行径表示不满。这似乎与他无为而圆通的态度相矛盾,其实并不如此。比如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固然表达着作者对于日本的横暴的不满,但作者并不由此产生奋斗、反抗的心情,而是希望日本在统治外族时能有“更大的机智”,能放弃军国主义的傲慢态度,采取更为柔和的手段,只有这样,“中日两国的接近……才可以想象到”,否则,日本不仅将使自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也将难以平复中国的反日感情。④林语堂:《中国人和日本人》,《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了解林语堂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悲观预测,是理解他纵论中西文化的超然立场的关键。1920年代,身为《语丝》同人的林语堂曾经主张“精神之欧化”,主张以刚健进取的西欧精神救疗中国民性中的惰性、奴气、敷衍、安命、中庸、识时务、无理想、无狂热的病症,从而重振民族精神、改变国家命运。①林语堂:《剪拂集》,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7~19页。这与鲁迅当时的“思想革命”的主张同调。在1930年代初,林语堂依旧保持着这一西化立场。1932年春,林语堂在牛津大学做题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的演讲,演讲中“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当讲稿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林语堂加了一段长长的按语,表明他的意见。他认为东方文明固然有极优异之点,然而对于东方文明的赞许,在外国讲讲则可,在中国则不合时宜,因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乃是“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图之精神”②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申报月刊》第1卷第1号,1932年7月。。
1933年夏,林语堂由进取的战士变为避祸自保的隐士,他的文化立场也随之变化。1933年11月,林语堂首次将他的新的文化立场概括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③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1933年11月1日。。
转变后的林语堂开始“重新发现祖国”④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他不再吝啬曾经有意压制的对于东方文明的赞许,并花费大量精力,探究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探究的一大成果,是用英文写作的、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吾国与吾民》。这本著作对中国人的性格、思维习惯、人生理想作出了极精辟的分析,对中国的传统文学与艺术作出了极精彩的解读,诚非浪得虚名之作。相比之下,林语堂对于西方文化反而谈得不多。但实际上,西方文化正是林语堂评论东方文明时的坐标。正是因为西方的机械文明过于追求高效,导致西方人“无暇享受自己创造的一切”⑤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未受现代文明影响、保持着田园生活的和缓节奏的东方文明,才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生活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压抑,带着山林隐逸之气的平静和谐的中国艺术,才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在林语堂笔下,中国的隔绝于现代文明,似乎不是一种有待改变的落后状态,而是一种心满意足的主动选择:“他们(中国人)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爱简朴的生活,他们发明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朴归真’……通过对文明的一种本能的怀疑与坚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退化。”①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2页。
在《语丝》时期与《论语》初期,林语堂曾经提醒国民认清东方文明的真相,正视西方文明的优点,莫“以保守为爱国,改进为媚外”,不要因为“爱国心切,反而间接减少中国变法自强的勇气”。②林语堂:《大荒集》,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9、16页。这是对于国家的落后状况有着清醒认识而又有奋起之心的弱国国民的立场。而当林语堂纵论东西文化之时,这样一种鲜明的立场,已然不见踪影。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模糊,他的文化认同主要在西方一面,但又穿华装、谈国粹,以东方文明的能够补足西方文明之缺陷自傲。这样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本位,以东方文化为调剂的立场,乍一看似乎文化自信十足,实际上却是在对国家命运已然悲观的情况下,为了替国家在国际上谋求一个“侍从”地位而作出的打算。而超然独立的批评家的身份,也是林语堂为自己——一个即将被征服的国家的文人——安排的最佳出路。鲁迅曾经准确地指出这种超然独立的立场背后的“西崽相”。③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367页。
不过,林语堂并非全然超脱,《论语》初期进取的法家思想依旧在零星地闪现,这使林语堂在自去锋芒以求保全之时,依旧时而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激愤,使他在1933年秋写下《〈论语〉周年秋兴有感》《民国廿二年吊国庆》,哭元气尽丧之祖国;在1934年写下《中国人之聪明》,责太识时务的中国人未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迂腐;在1935年写下《哀莫大于心死》,呼唤孤贞节烈之气;在1936年出版《中国新闻舆论史》,暴露当局压制下凋零的舆论与消沉的民气;写下《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外人之旁观者》《告学生书》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临别赠言》中要求当局开放言论、尊重民权。由此可见林语堂所谓的“寄沉痛于幽闲”并非全是虚言。然而其“沉痛”过于零星,其“幽闲”过于浩渺,“沉痛”之于“幽闲”,难免如沧海中之一粟,湮没而不可见。
五 鲁迅的态度
1933年1月,鲁迅被推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从这时起,到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因杨杏佛遇害而无形中解散为止,鲁迅和林语堂同为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在政治与文化倾向上相互接近。他们都不满于当局对外卑躬屈膝、对内以横暴手段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与爱国的言论,都意图暴露黑暗,在一片沉默之中发出挣扎与奋起的战叫。在此期间,《论语》上发表、转载了为数众多的鲁迅的杂文,这说明左翼与自由主义文人的某种联合。
在杨杏佛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内,鲁迅与林语堂依旧维持着朋友情谊。在《论语》发行满一周年之时,林语堂尚能以老朋友的身份“命令”鲁迅做文章,而鲁迅在“应命”写的《“论语一年”》里,也颇说了一些只有老朋友之间才会直说的关于“幽默”的异见。几乎与《“论语一年”》同时写下的,还有一篇《小品文的危机》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小品文论争中左翼立场的基调,然而鲁迅在写作的当时,并不特别针对林语堂,因为此时提倡小品文的《人间世》根本尚未出世②鲁迅此时针对的当是由《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近代散文钞 上卷》所引发的小品文热。二书均出版于1932年。。
1934年春,小品文论争发生了。鲁迅在论争期间写了一篇《小品文的生机》。这是一篇在林语堂与左翼青年之间打圆场的文章,意在说明论争起于误会,双方并无实在分歧。在同时期的私人信件中,鲁迅对于《人间世》的隐士立场颇为同情,甚至认为左翼青年的批评《人间世》是在“攻击身边朋友”,“与并非真正之敌寻衅”。③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155、158,158、197页。可见鲁迅在当时仍将林语堂当作老朋友,甚至是联合战线上的盟友看待。因此,严格说来,鲁迅并不能算是真正地参与了小品文论争。
然而,小品文的“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而又铺天盖地,终于使鲁迅感到“真真可厌”。林语堂的“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似日渐陷没,然颇沾沾自喜”,使鲁迅的态度逐渐与左翼青年接近。④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155、158,158、197页。从1934年5月26日发表《“……”“□□□□”论补》起,鲁迅开始了对小品文的批判。
鲁迅批判小品文的文章,根据内容和批判策略之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章指出《人间世》内容上的空洞无聊。这类文章以《“……”“□□□□”论补》和《零食》为代表。《零食》将文学中的小品比作食物中的零食。①莫朕:《零食》,《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6日。《“……”“□□□□”论补》由于讽刺意隐晦,鲜为论者注意,其实是对于发表在《人间世》第4期上徐訏的空洞长文《“……………”“□□□□□”论》的戏仿与讥刺。
第二类文章指出小品文之提倡者,不是本身学识不够,就是提倡的态度不诚恳,因此,他们的提倡根本不值得读者认真参考。那证据,就是他们在标点自己推崇的明人小品时连连点出的破句。点破句,即是读不懂的明证,既然读不懂,“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②张沛:《点句的难》,《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10月5日。态度不诚恳的提倡与反对,不过是“玩玩笑笑,寻开心”,读者如果当了真,那才是上了大当。③杜德机 :《“寻开心”》,《太白》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5日。这类文章,有《正是时候》《点句的难》《骂杀与捧杀》《“寻开心”》《从帮忙到扯淡》等篇。
第三类文章道破小品文的实质,揭示小品文流行的原因,指出冲破小品文所营造的精神幻境的方法。这类文章包括《读书忌》《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隐士》《“招贴即扯”》《杂谈小品文》《“题未定”草(六至九)》等,是鲁迅批判小品文的文章中最为重要者。
林语堂将小品文定义为一种“个人笔调”,以独抒性灵为特征,以近情哲学为内在精神。鲁迅避开了这一堂皇的论调,径直指出,小品文乃是刻意剪去文章中感愤、严肃的部分,放大其恬淡、闲适的部分而得到的一种文体。比如,被《人间世》塑造为小品文老师的袁中郎,原有着关心世道人心、佩服“方巾气”的一面,《人间世》避开了这更为重要的一面,只突出他的赞《金瓶梅》、做小品文,使读者误以为这便是袁中郎的全部。④公汗:《“招贴即扯”》,《太白》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明清小品,原本也并非清一色闲适,小品文作者身历明末的虐政及异族的入侵,文字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①旅隼:《杂谈小品文》,《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12月7日。。鲁迅将这样单取“闲适”一面,加以放大、抬高,以此概括作家全体的做法,称为“摘句”。摘句“以割裂为美”,人为地虚造出一个“静穆”的“极境”,“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②鲁迅:《“题未定”草(七)》,《海燕》第1期,1936年1月。。
虚造极境的小品文为何会在1930年代忽而流行?鲁迅以为,其中一个原因,是1930年代连年内战,水灾空前,外族入侵,耳闻目睹,难免心有所感,落得终日难安。身处这样的环境而仍要保持平和的心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世事“浮光掠影”,随时忘却,对现实“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再有就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③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作为“麻醉品”的小品文,正应了“蔽聪塞明”与“自欺欺人”的需要。
小品文流行的另一原因,是国家正处在存亡未卜之际,既不打算奋起,也不预备与国家同存亡,而又以笔墨为生的文人,对于自身出路的一种较好的设计,便是写小品,谈性灵,当隐士。这样,“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④旅隼:《杂谈小品文》,《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12月7日。。潇洒超脱的小品文的内里,正是这样一种实际的打算。当隐士,正是特殊时期特殊的“噉饭之道”。在鲁迅所写的文章中,与上述这层意思相关的,另有《儒术》与《采薇》两篇。《儒术》评论的是元好问在金元之际为降于元的叛将崔立起草功德碑的事。鲁迅认为,元好问拟好的功德碑虽然最后没有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⑤鲁迅:《儒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这不由使人想到1930年代事,国家虽然最后没有亡,但当时也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采薇》写的是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谏阻,在武王灭商后,耻食周粟,采薇为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事。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的征伐“不合先王之道”⑥鲁迅:《采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419页。,因而耻食周粟,最终饿死,这样的举动,正是林语堂所说的读书读坏心胸的、“方巾气”的举动。“坚守主义,绝不通融”⑦鲁迅:《采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419页。的伯夷与叔齐,正是近人情、忘是非的隐士的对立面。
那么,要如何冲破小品文所营造的精神幻境?鲁迅的看法是,小品文既是“摘句”,要打破其“魔力”,最好的办法便是还原其全篇。明清小品既是“血泊里寻出”的“闲适”,最好的办法便是还原其血泊。因此当《人间世》流连于湖光山色之时,鲁迅却在谈明季的酷刑,忠臣的被虐杀。①鲁迅:《采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78页。他认为明人小品并不坏,然而“《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也应该标点、翻印,“给大家来清醒一下”②鲁迅:《读书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与《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反对研究者根据选本评论作家,认为应当“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能够知人论世,“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扬抑,更离真实”。这样的主张,同样是针对“摘句”的思维方式。
六 结语
1932年9月,《论语》以独立而进取的姿态出现在文艺界。它在文学上提倡幽默,在政治上主张法治,以暴露和反抗当局的虐政为己任,在倾向上一度与左翼接近。1933年6月,杨杏佛的遇害使林语堂决定自去锋芒,以图保全。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林语堂开始调整立场,但总体而言,他此时的隐士立场含义尚不十分明确。发生在1934年春的小品文论争,加速了林语堂思想观念与政治立场的明朗化。林语堂形成了以近情哲学为表、无为思想为里的儒道结合的思想,并明确了他在国家存亡之际的无为而圆通的政治态度。这又促使鲁迅站在左翼立场做出相应批判。到1936年止,《人间世》作家群与左翼知识分子作为对立的双方,已然营垒分明。面对国难,前者颓唐、自欺,预备以圆通的态度应对或将到来的危难,后者“迂腐”而“方巾气”,下定了战斗、挣扎、硬干到底的决心。因而在文学上,当《人间世》标举个性、主张自由、追求雅致之时,左翼作家却以国家命运、社会变革为关切的中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文学作为宣传与教育的工具,将清醒、粗犷、奋进作为自身的美学风格。文坛的队伍于是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