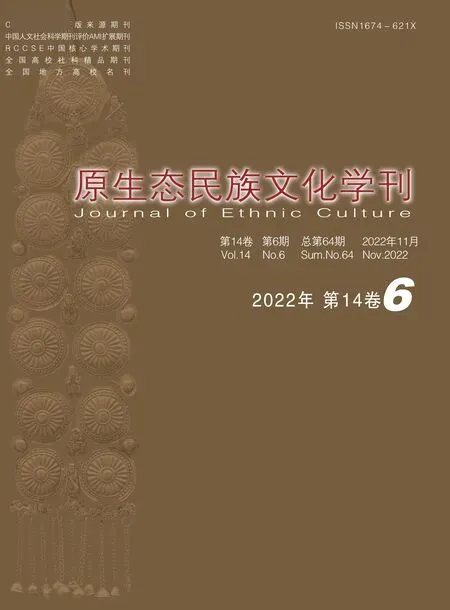意大利所藏西南民族图志价值研究
张宝元
一、引言
在无法保留影像图志的时代,编绘少数民族图志被作为记录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及其生产生活、历史变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以清代以来形成的“百苗图”系列抄本最具代表性。“百苗图”以绘图资料为主、文字资料为辅,其源头发端于清人陈浩所纂《八十二种苗图并说》[1]79-85。至今,“百苗图”系列的民族图志资料,已经历了200 多年的光阴,其提供的资料价值依然历久弥新。该系列民族图志除了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外,还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
但“百苗图”系列的民族图志资料在抄绘和流播过程中,抄临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有限地改变原有的内容,同时又赋予一系列抄临者所处时代的新内容,最终使得当代能够找到的“百苗图”传世文本千姿百态、花样翻新。如此一来,流传至今的“百苗图”诸抄本不免会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如传承至今的100多种抄临本,就几乎很少能够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版本。这些抄本中,有些是文字有出入,有些是绘画内容有出入,更不用说文字表述和绘画细节上的差异了。以至于,不同“百苗图”抄本的版本来源、传抄时间、传抄意图的考订等等,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从而造成不同抄本之间的文物价值差距。
事实上,就文物价值而言,当前能够获知的无论是哪一个抄本均不能与陈浩原作相媲美。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相关藏本的文物价值不断跌落的同时,其内容中呈现出来的差异却具有不可低估的资料价值,此前研究者却往往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看,这是某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问题,然其背后却隐含着一个原则性的学理问题,当下研究成果中的诸多误解与误判也因此而来。如果不及时澄清所凭借文本资料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还将会干扰到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顺利推进。
近来,有幸从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获得该机构所藏中国西南民族图志资料的全部电子文档,其中包含了11种不同的“百苗图”抄临本。这批资料在传承前代“百苗图”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改画和修订,不仅绘制出了贵州各民族的人物形象、生产生活情景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内容,还清晰地呈现出相关民族的服饰特征、饮食特点、艺术场景等文化要素。此外,该批资料中的多个抄临本所涉内容均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无论是新增加,还是另外改动的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均聚焦于20 世纪初贵州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实情[2]125-134。与国内所藏的其它“百苗图”抄本相比,这批资料在绘画技艺和风格上明显有别,其中的得失利弊也互有短长。作为丰富这一研究领域的资料,这批抄临本显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但其文物价值比之于陈浩时期的抄本则必然有所降低。这批规模性呈现的绝版文本资料,可望为“百苗图”系列抄本的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澄清和化解提供重要依据和机遇。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从意大利藏本的文物价值呈现、资料价值呈现以及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尝试性剖析,并立足于这一批新资料中有关“百苗图”抄临本的相关内容加以举例证明。鉴于这一论题的艰巨性,笔者才疏学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海外贤达不吝赐教,以利改正。
二、意大利藏本的文物价值呈现
经初步整理、鉴定后,大致认定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所藏的这一批珍贵的西南民族图志资料中,《连山厅连州分辖瑶排地舆全图》(该函的意大利收藏编号为“000062”)和《永北地舆并土司所属夷人种类图》(该函的意大利收藏编号为“000070”)两个文本编绘于清代中期,保存相对完好,因而其文物价值较高[3]1-20。除此之外,其他的15 函民族图志,特别是关于“百苗图”的文本资料,几乎都是20世纪初的抄临本、改绘本和装帧本。这将意味着,这批资料中的部分函套,若按照现行文物的评定标准,显然不能与国内各博物馆和研究部门所收藏的“百苗图”抄本相媲美,其文物价值必然相对低下。其间,有待澄清的假象反而值得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防贻误以后的研究工作。
在这批意大利所藏抄本(以下简称为“意藏本”)中,编号为“68”的函套共收藏了12帧精美绘画。然有图无文,甚至绘画应归属于“百苗图”中的哪一个条目,所绘主题是什么,均缺乏起码的文字说明。为了其后研究时方便,吉首大学团队已分别为之代拟了相应题目[3]1-20。在这12帧绘图中的第一页左下侧明确书写有“焦秉贞绘”字样,署名之下还加盖了两方分别刻写有篆文“秉”“贞”二字的印章。单凭这样的署名和印章,如若不认真考订,不免会让今天的研究者误以为这12帧绘图真是出自清康熙朝的宫廷藏品。
考虑到焦秉贞其人确实是清康熙朝代的宫廷画师,而且还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学生。如果这12 帧精美绘图真的出自焦秉贞手笔,那么其文物价值将可称得上是连城之璧。焦秉贞的传世画作并不多,目前有《仕女图》《耕织图》等一些作品传世。因而在中外艺术界,焦秉贞的名望很高,传世画作也极为珍贵。然经过仔细比对后却不难发现,这12帧看似极为珍贵的画作,却是20 世纪初冒伪绘制的赝品。而要揭破这样的假象,这12 帧绘图所能提供的本证就已足够。
进一步整理研究后发现,这12 帧绘图的内容和主题与“意藏本”中题名为《黔省苗图》(该函的意大利收藏编号为“000057”)抄本极为相似,其中的9 帧附图均可以在《黔省苗图》中找到相对应的条目。如电子文档编号为“F.cin_68_012”的一帧绘图,在《黔省苗图》抄本中可归属为“女官”条目,只不过其编绘者将条目名称改写为“耐德”。查“耐德”二字,出自彝语音译[4]243。笔者为该图所绘内容代拟标题,称之为“威仪启归图”(图1),含义是说彝族的土司正妻按照从三品官员礼仪准备出发,回归故里。辛亥革命后,土司制度被废除[5]1-6,这也意味着其贵族地位被废弃。所以此处不再称之为“女官”,而是“耐德”,由此可以证明此抄本抄成于20世纪初期。

图1 “威仪启归图”(杨庭硕供图)
更值得一提的是,“意藏本”《黔省苗图》抄临本中,标题“黔省”二字值得深究。纵览明清两代,包括民族图志在内的所有贵州官方乃至私人著述,书名的撰写习惯是将贵州省简称为“黔”或者“贵州”,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还未有题写“黔省”之例。因而,单凭这一书名的题写方式,就不难认定该抄本的抄临者和装帧者明显错用了书名题写的惯例,没有意识到在明清两代的著述中,“黔”字本身就是贵州省的简称,“贵州”二字也是贵州省的简称。但到了辛亥革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成了全国的主流用语习惯。再加上,为了防范初通汉字的外国人误解书名的内涵,才有意识地将书名题写成《黔省苗图》,如此一来,更有利于与外国人交易收购时获取暴利。因而,一个“省”字的妄添,本身就是一个冒伪的铁证,足以佐证不管是妄称焦秉贞函套的12帧绘图还是《黔省苗图》函套内所涉的18帧图文,所呈现的资料都是民国时期的产物,绝对不会是清代前期的焦秉贞真迹。
然而,尽管这12 帧绘图并非是焦秉贞真迹,但“女官”条(编号为“F.cin_68_012”)绘图中,整幅画作灵动传神,图中所绘的背景更其精美,整个庭院威严、华丽,充分显示出了土司衙门的庄重、豪华,编绘者甚至对地板砖的颜色都做出了精心的刻画。遗憾之处仅是在于,绘图中所刻画的只是一瞬间的情景。虽然只是保留了一个瞬间,却是此前传世的“百苗图”各抄本中所未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称得上是对20 世纪初残存土司衙门的最后一次如实描绘,所以其文物价值并不低。
考虑到这帧绘图描绘的位置乃是明代水西土司所建位于贵州城北郊的办事休闲衙门,地处今贵阳市黔灵镇的镇政府所在地。①黔灵镇,隶属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贵阳市成立九区时,今辖区分别属七区和九区,其中,九区设在红边门,辖红边门、贵乌路、装店街、百花山、筑东村、大宅吉、小宅吉、鹿冲关一带。1952年6月,五、六、七3区合并为郊区,下分5乡。其中,第三乡(即黔灵乡包括建水村、大宅吉、小宅吉、市北、黔灵、大洼6行政村,23自然村)。其中的宅吉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宅吉路。宅吉分大宅吉和小宅吉,后合称宅吉。宅吉是贵阳老城区外的一块产粮富庶田坝,当地人称宅吉坝,又称则溪。“则溪”为彝语,原意为仓库或粮仓。明代水西安氏按宗支各占一片土地,分为十三则溪。贵阳城北有部分地区亦在则溪范围内,安氏曾筑宅第于此。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机轰炸贵阳后,则溪成了贵阳人“跑警报”的临时场所之后逐渐变成了人口聚集的住宅区。当地百姓称“则溪”为“宅吉”意为吉祥的居所,“宅吉”之名沿用至今。辛亥革命后,该衙门由地方政府接管,接管后闲置到20 世纪中期,直到50 年代彻底毁弃,如今该遗址已改建成镇政府办公处。因此,这帧绘画虽说立意不够新颖,且是民国初年所绘,但绘画的背景却再现了20 世纪初土司衙门遗址的格局。因而,仅就这一意义而言,尽管这12帧绘图并不是焦秉贞原作,但它也不失其一定的文物价值。
总之,尽管该批意大利所藏西南民族图志资料中的部分函套,被认定为编绘于20 世纪初期,就历史时限而言,远远逊色于早期的抄临本。但是就稀缺性、可鉴赏性而言,又不失其特有的文物价值。无论如何,该批抄本中所新增的内容均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贵州各民族的文化实情,其资料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
三、意大利藏本的资料价值呈现
诚如上文所言,“意藏本”中的这批珍贵的“百苗图”资料,其文物价值无法与国内传世的“百苗图”抄临本中的佼佼者相媲美。虽然其文物价值并不算高,但其资料价值却是此前已发现的“百苗图”系列抄临本所无法比拟的。其间的理由在于,意大利所藏的这批“百苗图”资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保管质量较高,基本保持了流出中国时的原貌,其中所包含的反映20世纪初贵州各民族文化实情的资料没有受到人为毁损。另外,相关抄本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涉及面较为全面,具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自然与生态,乃至外部社会的准确定位,因而其资料价值远胜于此前大家所熟知的国内其他藏本。不过,要发挥其资料价值,就必须明确界定所涉资料的性质和功用,若错用其适用范围和功能,同样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阻碍。
这批民族图志资料抄临、改绘、装帧于20世纪初期[3]1-20,而在这一时段内中国的国内形势乃至国际形势均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学术思潮纷纷被引进到中国,并付诸实践应用。具体到“百苗图”的传抄而言,新进传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在这批资料中都可以得到直接和间接反映。鉴于“意藏本”中有关“百苗图”的部分内容,在此前的“百苗图”传世文本中根本不可能具有,因而更显得其资料价值的弥足珍贵,足以为中国当代民族学史的研究提供确凿可凭的物证资料。在此前编成的“百苗图”传抄文本中,由于编撰者和绘画者进入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圈具有很大的难度,即使进入后也根本无法在民族地区长住,因而所能够获得的资料和印象大多具有走马观花似的特点。加之,这些汉族文人受其传统的汉文化支配,对某些异民族文化事项还保持着鲜明的规避和曲解性质。而这批意大利藏本所能提供的资料却一改此前惯例,能够直接切中此前未能涉及的内容。以下几个例证就足以揭示其间资料价值的不可替代性。
“意藏本”中题名为《百苗图》(该函的意大利收藏编号为“000060”)抄本中的“白倮㑩”,其附图“积薪火葬图”(图2)逼真传神完整的描绘了彝族实施火葬的具体情景,包括当事人的表情、火葬的用具等都做出了精准的描绘,信息含量极为丰富,实属任何文字表述都难以企及。已有研究可知,实施火葬本来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彝族社会中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6]1-3。但通检国内此前已有的“百苗图”诸抄本,尽管文字表述中提及过火葬,①如“博甲本”中关于“白倮㑩”的丧葬记载为:“人死,以牛马皮革裹而焚之”。但在图志编撰时却从未看到过相关附图。凭借“意藏本”中《百苗图》的“白倮㑩”附图为依据去探讨20 世纪初彝族火葬的具体内容,其可靠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才可以获得起码的保障,这也是国内已有的其他“百苗图”诸抄本所无法具有的资料价值。

图2 “积薪火葬图”(杨庭硕供图)
同样,因为此前传世的“百苗图”诸抄本难以摆脱走马观花似的文化资料获取方式,对各民族家庭生活细节的描绘,不仅在附图资料中一概告缺,文字资料的表达也属模棱两可,不得要领。随着国内形势的剧变,以及有着民族学素养的学者能够长住少数民族村寨中后,有关婚姻家庭的细节性描绘资料,也就因此得到如实的揭示和表达。过往涉及婚姻家庭的文化事项时,此前国内传世的“百苗图”诸抄本总是千篇一律的描绘跳月择偶的歌舞盛况,或者抛球择偶的热闹场景。但跳月后如何展开感情交流,过上常态化的家庭生活,此前的“百苗图”抄本中,无论是文字还是附图都一概告缺。相反,“意藏本”中收藏编号为“000059”函套内的“花苗”条目则描绘了跳月后的情侣幽会场景,“紫薑苗”条目则是描绘出了对子女的养育场景。通过这些附图,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出20世纪初贵州各民族文化变迁中的新内容。这些新增资料的丰富和深入程度,都足以填补此前国内“百苗图”抄临本的资料荷载短缺。
凭借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民族学学科的传入事实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图志资料的获取和编绘方式。透过这样的改变,我们可以进而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其实始终与中国发达地区处于同步发展的大轨道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外学科的引进,不仅对汉族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对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也不例外。由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进行精确、生动的记载和描绘,已成为20世纪初不争的现实。不过,简单地举例还不足以揭示这批资料所涉民族文化事项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因而有必要对一些特定条目的附图展开进一步探讨,才能够引起读者对这批藏本独特资料价值的重视。
此前国内已出现的“百苗图”传世文本中,对所称“西溪苗”的婚俗描写和绘图说明,总是聚焦于热闹的跳月场面或者是前往跳月途中的充满期待的路途行进场景。但这样的婚俗是否会发生变化,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此前的文字描写和附图根本没有反映出这样的深层次内容,大多数都只是机械传抄和改画,留给读者的印象几乎都是亘古不变的跳月择偶而已。而“意藏本”中收藏编号为“000059”函套内的“西溪苗”条目则不然,笔者为其构拟的附图标题为“至亲阻婚图”(图3)。通过这帧绘图,我们几乎可以直接目睹和感受到,20世纪初发生在这一苗族群体的新旧婚俗之间的剧变和冲突。

图3 “至亲阻婚图”(杨庭硕供图)
图中所绘背景是在村寨之间的乡间通道上,绘图的左侧从北向南有一条小溪流过,溪上架有一座石拱桥。如若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往往会误以为平淡无奇,只是编绘者随意作画。但仔细比对不同时代的“百苗图”抄临本和相关文字说明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幅绘图的刻画真可以称得上是入木三分。图中共绘有4人,其中一名男子肩扛农具,从右至左正在过桥。右侧的桥头则描绘了两女一男,处在中间的女子肩扛锄头,衣着整洁,装扮得体,但却面带愁容。在这名女子的右侧是一位青年男子,左手握住了这名女子的右手手腕,正在神情凝重地劝诫她不要前行。这名女子的左侧是一位年纪稍长的女子,右手正搭在这名女子的肩上,似乎也是在阻拦她过桥,避免其追随前方的男子而去。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和田野调查的印证,可以从中得知绘图中所反映的这一苗族群体和很多苗族群体一样,早年都是按照传统的“出面”婚俗择偶成婚,婚配对象大多都是姑舅表亲[7]537。此前各“百苗图”传世文本仅是描写出他们的热闹择偶场景,通过文字介绍还可以进而获知,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之间在择偶定亲后,女方就可以住到男方的家族村寨中,正式过上夫妻生活。其后,要生下头胎子女并等子女断奶后,夫妻双方才携带新生儿一同返回到女方的家族村寨中赠送聘礼,并在女方家族正式举行婚礼。结婚过程中,当事人新郎在婚前根本无须征得女方家族的同意,女方家族的任何成员没有理由,也不会阻拦婚事。而这正是“出面”婚俗的特点所在[8]139。这当然与汉族的传统婚俗大不一样。到了20 世纪初,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公认的婚姻体制在全国的推广实行,也理所当然地波及“西溪苗”这一苗族群体。以至于这一群体中,了解外部形势变化的青年人,会根据当时的婚姻制度将这种传统的“出面”婚俗视为陋习和非婚生子,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婚姻方式。从而在传统婚俗依然执行的过程中,会很自然地出现阻拦自己亲人按传统方式操办婚事的事件发生,认为他们应该按照新的婚姻制度,办完婚礼后才算正式成家。这正是以上附图所描绘的瞬间情景,以及当时整个社会剧变的缩影。
这帧绘图通过某一瞬间的情景来揭示一个民族文化变迁的重大实情,及其由此引发的多重牵连性文化事项和结构的剧变,真可以称得上是以小见大、静中见动了。其间的资料内涵,可以说是无比丰富多彩,甚至各位当事人的心理感受都可以从中得到领悟,其资料价值实属其他文本的附图不可替代。
19 至20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加深,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愿也日趋强烈。于是,洋务运动、实业救国、激活市场等一系列新观念、新主张相继出炉,并由此深远地影响到了不同民众的生活,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也随之被激活。如专业化的作坊出现,市场的扩大,民众生活的改变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发达地区,不要说专家学者,即使是普通民众也不会感到意外。但若发生在偏僻边远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则往往被视为无稽之谈。长期以来,不少人总是习惯性认定,这些少数民族封闭落后,与世无争,甚至直到20 世纪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看法纯属误判。意大利新获的这批民族图志资料,正好可以为此作证。鉴于这批新资料的内容过于丰富,要提供这样的证据几乎是俯拾即是,在此仅列举一例,以期读者能够举一反三,全面了解这批藏本的独特资料价值。
再看此函套内的“谷蔺苗”条,其附图“专业送染图”(图4)中央描绘了一座高拱的石桥,桥上有路人来往通过,行人或抱或背着布匹正在穿行。桥边右侧上方则绘有一名青年男子扛着白布胚,稍作休息的同时正往绘图的右侧看去。单看这幅绘图,如若不结合当时民族地区的文化实情,又不与此前传世抄本中“谷蔺苗”条目的附图作对比,今天的读者,甚至是专业研究者,都无法猜透这帧绘图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是什么。查阅相关文献后可知,此处所称的“谷蔺苗”,是一个有着悠久纺织工艺传统的苗族群体[9]85。此前国内传世的“百苗图”诸抄本,无论是附图,还是文字说明,都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纺纱织布出售白布胚的场景,致力于凸显他们长于纺织的文化特性。但“意藏本”该抄本中的这帧附图,其突出特点则在于,过桥的人手中的白布胚都被染上了鲜艳的颜色,而没有过桥的男子肩扛的则全是白布胚。通过这一细微的差异,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猜到,在这幅绘图的右侧隐藏着一个从事专业印染行业的作坊。绘图中不同肤色的人,都是为了染布这一加工过程而采取了自己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手中的布匹更加美观,更适合衣着。桥上从右至左行走着的人,背着染好颜色的布匹,并带着满意的神色回家,而从左至右行走着的人,所抱的布匹数量不多,虽然也染上了颜色,但表情却十分凝重,并不愉悦。从这样的表情差异中不难猜出,他们是因为染色加工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要求,准备去找染色作坊讨公道,或者要染坊重新加工,或者要退货。至于没有过桥的人,他们是要将手中的白布胚,付钱让染坊给自己的布匹批量加工,全部染上色。总之,整个画幅表达虽然含蓄,甚至有些隐晦,但却能让所有的人经过思索后领会到绘画的主题,即在绘图右侧的深处隐藏着一个专业从事染色加工的作坊,染坊已经在这个偏僻的民族地区站住了脚跟。也是因为这一作坊的存在,才驱动了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来实现产业上的合作和配合。

图4 “专业送染图”(杨庭硕供图)
经过系统地历史沿革考订,进而可以知道,此处所称的“谷蔺苗”,祖祖辈辈生活在今天的惠水县、罗甸县之间[7]281,而与之毗邻的濛江河谷地段很适合种植木棉,“谷蔺苗”也因此而建构起了自己特有的纺织工艺。但这个地方不产染料,20世纪初要想将白布胚染出鲜艳的颜色,不仅要从外地购买染料,而且还要招募染色工匠。一方面受国内社会剧变的驱使,另一方面是盈利空间的巨大,才使得汉族的印染工匠抓住这一商机,深入到这一民族地区后创建了专业性染坊,这帧绘图所表达的一切也才得以呈现在我们眼前。只需弄清楚其间的前因后果关系,这帧只能展示一个瞬间的绘图,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民族地区社会剧变的资料荟萃。其间的汉族工匠、商贩和少数民族民众所表达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心理互动,都可以在这帧绘图中得到印证。该帧绘图所涉及的文化资料信息,大大地超过了绘画本身,极大地填补了相关文字说明的不足。所有这一切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跨世纪之交,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实和汉族发达地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同步中华。他们同样也进入了专业作坊加工和市场化的新境界,此前只知道出售白布胚的时代已经成为他们的历史记忆。
总之,意大利所收藏的这批“百苗图”抄临本,虽然文物价值并不起眼,但其资料价值却无可替代。事实上,时至今日,能够直接反映20 世纪初期贵州各少数民族同步中华的文本资料,特别是绘图资料和摄影资料,直到今天依然感到十分稀缺。而意大利所藏的这批西南地区民族图志文本,恰好能够填补这一资料空缺,值得当代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探讨。
四、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
不管任何意义上的传世文物,包括传世文本在内,其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总是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制约。这一点对讨论意大利这批藏本资料而言,也不例外。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混用。一旦违反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导致研究结论偏离历史真相。文本资料的文物价值,通常是取准于其历时性、真实性、完整性、稀缺性和可鉴赏性。上述5 个方面达到的水平越高,那么其文物价值也就越高。而资料价值则不然,除了追求资料的真实性以外,还需要追求其信息含量、适用范围以及可利用性。两者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各不相同,既不能相互重合,也不能相互替代,但其间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一件传世文本,如果真实性可靠,保存又完整,那么其资料价值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因为可以借助其文物价值揭示和界定其所涉资料价值的可适用范围。而资料价值的可利用性越高,那就足以支撑相关文物的可鉴赏性,也就提高了其文物价值。换句话说,只有人们深刻认识到资料价值后,其文物的鉴赏价值也才随之而得以提升。然而,即使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鉴赏性都很高的文物,如果它的信息含量很低,那么其资料价值就不会很高。
举例而言,一件极为稀缺的传承至今的宋代秤砣,其信息含量十分单一,最多只能让今天的人从中获知宋代的度量衡与当下的度量衡之间精确的折算关系而已,其他的信息含量几乎无从谈起。这将意味着它的文物价值很高,但其资料价值并不可观。反过来,一份历史上长期传承下来的文本资料,即使保存有所残缺,但其信息含量却十分丰富,然而信息含量丰富并不能替代它的可鉴赏性,也不能代表它的稀缺程度,因此其资料价值虽然很高,但其文物价值却也显得十分有限。
对“百苗图”各种传世抄本而言,其文物价值虽不能与陈浩原件《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相媲美,但其资料价值却不容低估。而这批意大利藏本临摹、改绘、装帧于20 世纪初期,与国内早期的其他“百苗图”传世抄本相比,其文物价值虽并不高,但却有着十分明确的时间、空间定位和传承脉络的记录,因而其所包含的资料价值,即可认知性和可利用性必然很高,这也将意味着它的资料价值无可替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我们忽视其间的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之辩证统一关系,那么在研究中形成的结论就会出现严重的偏颇。
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百苗图”的起源探讨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例如胡进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不完全是哪一个人通过实地调查而产生的,也不是某一时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真实写照,因而《百苗图》所反映的内容,是层叠累积的结果[10]74-80。李宗放推断《百苗图》作者陈浩应在乾隆时期任八寨同知,从而断定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本在乾隆时成册[11]31-36;沈福馨和邓光华也认为《百苗图》系乾隆时陈浩奉命所绘[12]132、[13]48;黄才贵认为《黔苗图说》之类的写本,多出自乾隆盛世之年前后[14]173;美国学者劳拉·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r)指出乾隆朝重视以汇集帝国境内各种人民的信息来实行有效统治,才有l8世纪中叶关于82 个族群划分的人种志的出现[15]162。而对于“百苗图”研究最为集中及成果最多的杨庭硕认为,陈浩原作《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撰成于清嘉庆初年[1]79-85。《百苗图》成书时间的扑朔迷离,也自然影响到“百苗图”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因此,以上各种结论都有必要遵循上述原则加以反思,均不得视为最后的定论。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外国人得以在中国内地游历、收购文物,是发生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后的事情。国内传世的珍贵的“百苗图”诸抄本,本身就极为稀缺,而流传至国外的抄临本却多达100多种,这显然是一个非正常的现象。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至少可以表明,国外所藏的“百苗图”抄本中,编绘于《天津条约》以前的具有文物价值的藏本,肯定极为稀少,凤毛麟角,除非是外国侵略军直接从故宫实施掠夺,早期的真文物才有可能流落在他们手中。再加上中国的文物贩子和书商也有他们的经营规则和投机取巧惯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出售真文物,而是以真文物作为蓝本制作仿制品,出售牟利。就这意义上而言,虽然今天从外国引进藏本困难重重,甚至堪称稀缺,但要把它们作为真文物对待,进而证明“百苗图”抄本的源头,就犯了“以假乱真”和“以今拟古”的错误研究思路。时至今日的事实一再证明,现在已知的、甚至公开出版的国外“百苗图”藏本,大部分都是在20世纪初期流出国外的抄临本和改写本,和这批意大利藏本资料一般无二,真正早于辛亥革命以前流入国外的“百苗图”的真实抄临本,仅法兰西藏本而已[7]序。其他见诸报道和引用的文本,都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流出国外的复制文本。仅仅凭借文本的稀缺性和获取的艰难性,就误以为其文物价值很高,进而无条件的认定其资料价值也很高,实属研究思路上的短视,需要借助理性分析去加以匡正。
事实证明,国内保存的“百苗图”早期文本,其真实性更加可靠,完整性也较国外藏本强很多。因而在文本的资料价值选用时,过分倚重国外所藏“百苗图”抄本之举并不可取。同样的道理,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传世文本,如若研究者一律按心目中最可信的文本去做出裁断,也需要加以匡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本身是可变的,无论选用哪一个文本作为依据去展开分析,无论出现多大的偏差,都需要就事论事,必须考虑到抄本编绘内容是否符合当时的民族文化实情。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所选用的抄本越接近心目中的版本,其资料可信度就会越高。这批意藏“百苗图”系列文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及时将20世纪初期发生的文化变迁如实记录,因而才成为探讨当时贵州各民族文化面貌的第一手资料和不可替代资料来源。我们不是希望将这批资料奉为高等级的文物去对待,而是希望从中发现其资料价值以及对现代的借鉴和启迪意义,更不会想凭借这样的资料去追溯“百苗图”编绘的源头。要知道,资料价值是具体的,是有特定使用对象和范围的,超越了这样的限度去随意使用,就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极大失误。因此,只需要坚持文物价值与资料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原则,时下的相关争议也就可望得到澄清,达成共识也就指日可待了。
尽管意大利藏本具有其特定的、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但其资料价值仍然无法证明“百苗图”的起源,试图用某一藏本、图志或诗词等内容去证明“百苗图”起源的做法,均属以偏概全之论,有待进一步考订。而以20 世纪初的资料去推测18-19 世纪的情况,这种“以今拟古”的做法也不可取,因为20世纪初的资料无法证明一两百年前的事情,它的资料价值仅能够说明20 世纪初的情况和面貌,不能说明更早年代的情况。因此用这些资料去研究“百苗图”的源流变迁,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靠性,试图突破资料价值的适用范围,显然也是一种研究思路上的失误。
五、结论与期待
以上所述可知,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的藏本,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附图描绘,都富有特色,传抄者不是对20 世纪以前中国传统民族图志的机械临摹复制,而是与时俱进地对西南各民族地区重新做过田野调查和史料核对后,将新的内容增补到复制工作中,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西南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断代依据,具有其他“百苗图”抄临本所不具备的民族资料价值。然其文物价值却远远逊色于国内其他的同类传抄文本,这将意味着我们对这批所获的珍贵资料,今后将主要用于探讨20 世纪初贵州各民族文化变迁之用,而不是作为稀缺的文物去藏诸秘阁,不以示人。相反,是要将它尽快地校勘、整理,做出符合民族学研究规范的示范性研究,以期助推民族图志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但愿这一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响应,能够将这一批珍贵的国外民族图志资料,尽快地加以发掘利用,以满足我们这一时代认知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文化的需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绵薄之力。当然,如果时机成熟,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也希望这批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物归原主,回归中国。